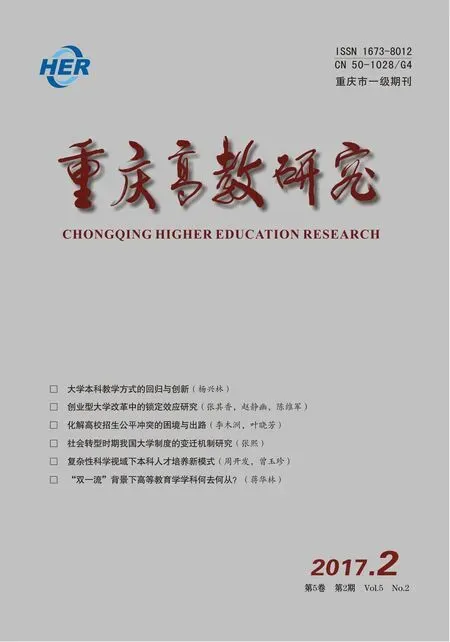“双一流”背景下高等教育学学科何去何从?
蒋华林
(重庆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重庆 400044)
时论与争鸣
“双一流”背景下高等教育学学科何去何从?
蒋华林
(重庆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重庆 400044)
“双一流”建设是现阶段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战略。在此背景下,一些高校为了入围或为了有更多学科入围“双一流”,采取“二进制式”策略调整学科结构布局,高等教育学学科“合法性”存在面临困境。研究发现,高校如此作为的背后具有复杂的制度性动因,包括高等教育发展的政府主导模式、高校资源获取的学科捆绑式分配机制、高校之间的“晋升锦标赛”政绩竞争以及高校内部学科建设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机制等。对此,除了要从制度层面破解外,高等教育学学科自身还应坚持特色发展,强化服务理念和加强学科渗透,从而在“双一流”建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双一流”;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二进制式”思维
一、“双一流”背景下的学科调整
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并规划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同期,教育部启动了第四轮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向各学位授权单位广发“英雄帖”(《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邀请函》),评估的首要目的即是服务“双一流”建设大局。虽然教育部一直在“争取尽早出台”的“双一流”建设实施办法迟至2017年初才正式发布,期间还否认发布过“双一流”大学名单,但各高校及社会各界普遍认为,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必将与“双一流”建设挂钩。于是各高校无不全校动员、全力应对、全面参评,掀起新一轮学科建设大潮。
部分高校更对学科布局进行了大手笔调整,对一些学科实力较弱或难以为“双一流”建设加分的学科,直接“除名”或“合并”,表现为一种“二进制式”建设思维:要么是一流而大发展(1),要么是非一流而失去生存空间(0)。根据2016年10月19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关于下达2016年动态调整撤销和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名单的通知》,全国共有25个省份的175所高校撤销576个学位点,包括大量博士学位授权点。由此引起了广泛讨论,以至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强调:“‘双一流’是建设高教强国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1]
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高校以“壮士断腕”的勇气,裁撤教育学院,撤销教育学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等,大有山雨欲来之势。高等教育学界不仅有“唇亡齿寒”之忧,更有“居危思危”之虑。2016年11月13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兰州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9所“985工程”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更齐聚杭州,研讨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发展面临的挑战。
二、高等教育学学科“合法性”困境的制度分析
高等教育学学科,除了在学理上长期存在“学科论”与“领域论”之争而面临学科合法性质疑之外,更因其“后发性”而在许多高校发展滞后成为“弱势群体”。即使那些在本学科内享有较高学术声誉的学科点(学院、研究院),在其所在高校也常因显得渺小而被选择性忽视(其他弱势学科也有类似情况)。当前的调整与挑战,不过是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被放大了,而且还动了以研究思考“双一流”建设策略为己任的高等教育学学者的“奶酪”。对此,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些高校为什么要拿高等教育学学科开刀?可以想见,“这种现象的生成和存在具有复杂性和多元因果性,需要我们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中,寻找和发现那些重要的甚至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2]。而在所有因素中,“制度构成着关键的社会资本”[3],为此可以从制度层面进行分析。粗略地讲,高等教育学学科“合法性”困境的制度性原因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一)高等教育发展的政府主导模式
众所周知,二战后,由于高等教育越来越重要,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并逐渐成为社会的轴心,成为社会“动力站”和“加油站”,而且由于其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使“大学已经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一个主要工具。这是前所未有的,是现今席卷我们大学改革之风的实质”[4]63。鉴于此,国家或政府愈来愈多地通过法律、政策、经费、行政等手段介入和干预高等教育。这在高等教育由政府主办与主管的中国体制下显得尤为突出,政府不断出台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直接指挥高校发展,高校对政府表现出极强的依赖性甚至依附性。
同时,“每个国家,当其变得具有影响力时,都趋向于在其所处的世界上发展居领导地位的智力机构……伟大的大学是在历史上伟大政治实体的伟大时期发展起来的”[4]63。当前,我国经济体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位,正在为“两个一百年”目标奋斗,力争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此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的战略决策,要求“扎根中国大地,遵循教育规律,创造性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之路”[5]。各高校无不闻风而动,积极响应,能否建成、何时建成“一流”暂且不论,但首先必须“政治正确”,并采取一些所谓的改革动作以彰显“政治正确”。因为高等教育学学科的“软柿子”地位,对其进行改革或调整所产生的冲击最小,但又能显示高校的改革决心、改革作为,何乐而不为?由此可见,高等教育学等学科被调整或面临调整危机,与这种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下高校的被动响应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高校资源获取的学科捆绑式分配机制
我们知道,“大学是深度资源依赖型组织”[6],高校的发展离不开强大的资源支撑。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一流大学必定是富有的大学;反之,只有富有的大学才可能成为一流大学。如2007年度美国有76所大学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上,最富有的5所大学依次为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德州大学。其中,普林斯顿大学拥有资产158亿美元,计算下来每名学生可分得200万美元的资源[7]。国内高校实力与经费收入之间也呈现某种正相关关系。根据2016年教育部直属高校收支决算总额,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排名前列,收支决算总额都超过100亿元,清华大学更是超过了200亿元,远远领先于其他高校[8]。
“双一流”建设启动后,教育部对“不利于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规范文件进行了专项清理”[9],其中包括部分“211工程”“985工程”建设文件,低调宣布“211工程”“985工程”停止执行。这意味着原先重点建设的资源配置政策要为“双一流”让路,要根据“双一流”入围情况来重新分配资源。2016年4月15日,李克强总理在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座谈会上强调,要抓紧出台建设一流学科的具体措施,促进率先突破,带动提升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可以预期,“双一流”建设的资源分配模式是“学科捆绑式”,即按照各高校拥有的一流学科建设数量来倾斜分配资源。教育部等新近出台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教研〔2017〕2号)提出的“遴选条件”,无论是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还是一流学科建设高校,都有数量不等的“高水平学科”要求。各高校为了获得更多的一流学科数,必定会对高等教育学等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能或不可能入围一流学科的弱势学科进行“外科手术式”调整,或裁撤或整合,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三)高校之间的“晋升锦标赛”政绩竞争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但事实上,高校应该拥有的办学自主权或者法律规定应该享有的自主权,并未真正落实,以至于时至今日,我们还在探讨大学必须拥有怎样的办学自主权[10],高校仍然是一个高度“行政化”并与政府高度“同构化”的机构。高校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校长(和党委书记)都是一定级别的干部,都由上级组织任命。能够被任命为校长或要成功守住校长位置,甚或晋升担任更高层次高校的校长以及调任政府官员等,往往需要凭政绩说话(学术成绩也是一种政绩)。这必然促使各高校之间展开“晋升锦标赛”式政绩竞争。
晋升锦标赛理论(Rank-ordered Tournaments)由莱瑟尔和罗森(Lazear&Rosen)于1981年提出[11]。它是指上级单位对多个下级单位的负责人设计的一种晋升竞赛,竞赛优胜者将获得晋升,而竞赛标准由上级单位(领导)决定。它的主要特征,是参赛人竞赛结果的相对位次而不是绝对成绩决定最终的胜负(排位赛),因而易于比较和实施[12]。显然,在“二进制式”“双一流”建设思维下,各高校必定会理性地采取“短、平、快”的措施,全力“打造”一流学科,以在取得“一流”政绩中抢占先机,占据好的晋升位次。而整合部分弱势学科实现“学科合并”,或把那些不能成为一流的“末段学科”统统干掉,由此提高“一流学科率”(指一流学科数占全部学科数的比例),甚至争取由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升格”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显然不失为立竿见影之优先选项或最佳博弈策略。
(四)高校内部学科建设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机制
上述3个方面的制度分析,强调的是起关键性作用的外部因素,除此之外,高校内部学科建设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发展机制亦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众所周知,一段时间以来,国内高校通常以学位授权点数量的多少作为衡量学科建设水平高低的主要依据,将学科建设等同于获得学位授权点。于是纷纷“大干快上”(特别是在高等教育规模大扩张阶段),有条件要申请学位授权点,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申请学位授权点,重“铺摊子”而轻“经营管理”[13],学科建设处于粗放式扩张的无序状态。
近年来,随着教育评估理念的深入,尤其是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自2002年启动学科评估(以及其他民间学科排行榜发布)以来,高校学科建设再也不能藏在深闺之中,而必须“拉出来遛遛”。为此,高校在因应外部评估的同时,逐步建立健全内部评估机制,对校内各学科分出三六九等,着力构建有序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机制,提高学科建设有序度。我们可以看到,“双一流”实施前,一些高校由于打不开情面或缺乏改革勇气,多半只是实施了某些微调;“双一流”实施后,高校抓住机遇,狠下决心,对那些一直想动而不能动的学科进行了调整。一些高校的高等教育学学科也正是在这样的机制下“躺枪”的。
三、高等教育学学科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思考
上述分析回答了高等教育学学科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面临合法性困境的制度动因。为此,我们首先需要从制度上提出宏观政策建议:
一要改变政府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设计者、发动者、推动者”的角色[14],切实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由高校根据学术逻辑甚至市场逻辑而非行政逻辑来规划学科发展,避免或减少政府对高校学科建设的直接干预。
二要优化学科发展资源配置机制,保持学科多样性、层次性,构建以一流学科为高峰的高校学科发展生态系统。要认识到一流学科不是学科建设的全部,纠正学科建设的“二进制式”思维。
三要改革和创新高校(校长)的政绩考核体系,破除急功近利的学科建设政绩观,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政绩观,“切实抓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
四要优化学科建设机制,加强高校学科建设顶层设计,并保持必要定力。要做好学科建设前期论证和后期评估,避免走“先建设后淘汰”之路。要正确认识学科建设与学位授权点建设之间的关系,形成良性循环。
但这样做还不够,它至多从面上解决了外因问题(并非高等教育学学科独立面对的问题),还需要从高等教育学学科内因上进行分析,提出对策。我们知道,部分高等教育学学科被撤销或教育学院被裁撤,不是由于自己“点儿背”,是“无妄之祸”,因为“同病相怜”的还很多。从内因看,主要问题是:部分高校高等教育学学科特色不突出或没有特色,与其他学科(学院)之间的融合互动缺乏,对学校改革与发展的支撑作用不足。为此,高等教育学学科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练好“内功”:
(一)坚持特色发展,确保高等教育学学科有特色
特色是学科建设的生命力,也是一流学科的本质要求,加快特色优势学科发展或发展学科优势特色是“双一流”建设的必然选择。反观高等教育学学科,近年来,伴随着高等教育发展的显性度提升和复杂度增强,从高等教育研究而衍生出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布点快速增加。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全国就已有近100个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在读硕士生超过2 000人,指导教师超过500人,均比10年前有数倍增长[15]。大体上讲,除一些综合实力较强的高校外,相当部分高校的高等教育学学科都存在特色不突出,甚至没有特色的问题,很多是模仿甚至照抄别的学校,同质化严重。
核心竞争力是“抄”不来的。各高校高等教育学学科要想拥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在“双一流”建设大潮中能“向涛头立”,应当结合所在区域实际,尽量避免“同城德比”,防止近距离同质化竞争。尤其要结合所在学校实际,根据办学目标和既有特色优势学科,采取嫁接或“杂糅”方式,实现交叉融合创新发展。
(二)强化服务理念,发挥高等教育学学科对学校改革发展的支撑作用
我们常将“无用之用是为大用”观点拿来反对或抵制“吹糠见米式”的学科发展要求或学术市场化倾向。但“人是寻求意义的动物”,“大用”总是要用证据或事实来说明“有多大之用”的。我们还往往强调“大学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自己”,呼吁高校领导和政府主管部门重视,以此来为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争取合法性。但高等教育学学科怎么证明或说明自己就研究了或很好地研究了“自己的大学”或“大学自己”呢?高等教育学学科当前面临困境,也许症结就在于此。
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解决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实践问题,通过对实践问题的研究而累积知识,从而为学科知识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支撑[16]。为此,高等教育学学科尤其是量大面广的面临生存危机的硕士学位授权学科,需要从高等教育学学科特点出发,牢固树立服务理念,强化“大局意识”和“看齐意识”,密切关注所在学校的发展战略需求,加强院校研究,打造高水平智库,为学校改革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舆论支持和社会支持”[14]。
(三)加强学科渗透,推进高等教育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互动发展
学科互动、交叉、融合与渗透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和途径。关于高等教育学的多学科研究、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与多学科研究方法等主题,已有一些学者做了研究。在此想强调的是,大多数高等教育学学科在所在学校都很难有大的体量,不要说与理工类学科比,就是与经济、管理、法律、文学等文科相比,也常常望尘莫及。如果“单打独斗”搞“个体户”,很容易在资源分配或各种票决中被边缘化、底层化。很多学校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纯粹做所谓的学术研究,难以获得有力支持,是没有生命力的(同时要避免走另一个极端,只搞狭隘的院校研究:撰写调查报告、起草讲话稿等)。为此,高等教育学学科不应只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应强化“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的理念,发挥自己的学术特长,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互动互渗,为他们的发展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并从互动中获得学科发展的养分。
“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并消逝着。”[17]高等教育学学科面临今天被裁撤的困境,符合高校学科建设“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要求,有其合理性。但就当下语境而言,其根本原因是“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很多高校简单地采取了“二进制式”学科建设思维:要么是或有可能是一流学科,要么就不要存在,即要么是“1”,要么是“0”。如果将来有一天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成为高校学科建设的”指导者”,那我们今天的选择又该作何反思与弥补?
[1] 王鑫昕.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双一流”是建设高教强国一部分但不是全部[N].中国青年报,2016-11-10(03).
[2] 蒋华林.从“条块分割”到“块块分割”——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转型中的地方政府竞争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5:143.
[3]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7.
[4] 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陈学飞,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5] 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EB/OL].(2015-11-05).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11/05/content_10269.htm.
[6] 程瑛.社会转型期我国大学资源竞争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1:195.
[7] 陈琳.大学的财富鸿沟[N].第一财经日报,2008-02-28(C07).
[8] 2016国内高校年度决算盘点:清华收支超200亿[EB/OL].(2016-09-12).http://mt.sohu.com/20160912/ n468250937.shtml.
[9] 关于宣布失效一批规范性文件的通知(教政法〔2016〕12号)[EB/OL].(2016-06-23).http://www.jyb.cn/info/jyzck/201606/t20160623_663290.html.
[10]宣勇.大学必须有怎样的办学自主权[J].教育发展研究,2010(7):1-9.
[11]LAZEAR E,ROSEN S.Rank-ordered tournaments as optimal labor contracts[J].Political economy,1981,89(5):841-864.
[12]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
[13]蒋华林.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学科综合性建设的路径探析——以重庆大学为例[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36-139.
[14]张应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反思和再出发[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140-155.
[15]李均.当前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三大困境[J].江苏高教,2011(1):46-48.
[16]张应强,郭卉.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定位[J].教育研究,2010(1):39-43.
[1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2.
(责任编辑 蔡宗模)
What Path to Follow for the Discipline of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rate Construction
JIANG Hualin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China)
At present,Double First-rate construction is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China higher education.In order to become the Double First-rate university,the binary tactics is adopted by som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o adjust discipline structures and layouts.In this context,the discipline of higher education faces the dilemma of the legitimacy.The study found that some complex institutional factors exist behind the behaviors of th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including the government dominant mode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disciplines bundled resource distribution mechanism,university’s achievement competition of Promotion Tournament,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mechanism from disorderly to orderly in universities and so on.Therefore,in addition to taking measures from the institutional level,the discipline of higher education itself should adhere to the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strengthen the service concept and enhance discipline penetration so as to find its own position in Double First-rate construction.
Double First-rate;discipline of higher education;discipline construction;binary thought
G40-05;G640
A
1673-8012(2017)02-0122-06
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17.02.016
2017-02-12
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五大功能区高等教育质量差异化提升策略研究”(2015-GX-001)
蒋华林(1972—),男,四川广安人,重庆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
蒋华林.“双一流”背景下高等教育学学科何去何从?[J].重庆高教研究,2017,5(2):122-127.
format:JIANG Hualin.What path to follow for the discipline of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rate construction[J].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2017,5(2):122-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