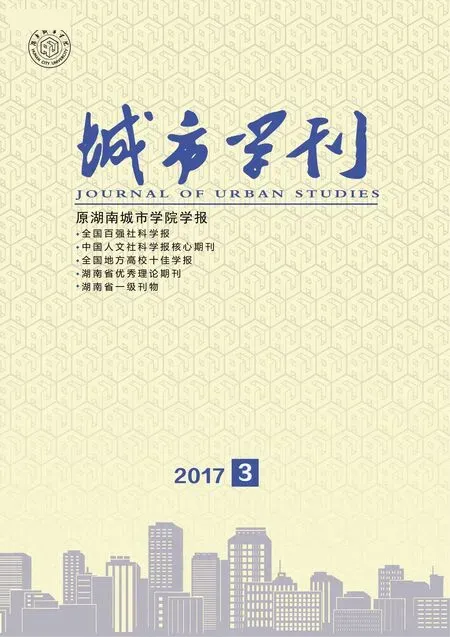顾炎武“经世致用”伦理思想及其价值影响
匡列辉
顾炎武“经世致用”伦理思想及其价值影响
匡列辉1, 2
(1. 湖南城市学院师德教育研究基地,湖南益阳 413000;2.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经世致用”是顾炎武伦理思想最突出的特点,有着鲜明时代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末清初大动荡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状况。顾炎武“经世致用”伦理思想所内含的对现实人性的道德思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注重“以名为治”的道德教育和严谨求真的为学作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由于其时代所限存在着难免的局限性,但我们可从他的思想中超越时空的普遍性从而受到深刻启迪,进而对其思想价值进行现代转化,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的新发展。
顾炎武;伦理思想;“经世致用”;价值影响
明朝清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处于“天崩地坼之日”。[1]顾炎武所主张的“经世致用”的伦理思想反映了明末清初大动荡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状况,体现出了当时代鲜明的特点。由于时代所限又存在着难免的局限性。但可以从他的思想中超越时空的普遍性,感悟内在人文精神的实质,从而受到深刻启迪。
一、顾炎武“经世致用”伦理思想之“原”与“源”
从发生学理论的视角看,一种思想产生、一种社会文化的出现,都是有其发生的“原”与“源”,由“原”与“源”两者交互综合作用而发生与不断完善。“原”是指这种思想文化所产生的社会本原。包括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阶级矛盾冲突及变革。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社会现实决定了这一思想文化的阶级属性、价值导向和朝代特征。“源”则是这一思想文化产生的具有典型民族特点的传统历史文化资源。任何思想文化都是以其传统文化为既有前提,而后在此基础上生发建构形成。“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2]599“原”体现思想文化的现实性。“源”彰显其历史演进与传承特点。
(一)顾炎武“经世致用”伦理思想之“原”
恩格斯曾说过:“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3]600作为思想之“原”的当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生发和决定着上层建筑中的思想意识。顾炎武求学时代的明末王朝内外危机四伏,官场黑暗腐败,国内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关外清军虎视眈眈,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历史剧烈的动荡时期。年青时期,顾炎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发奋读书。开始编写了《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1645年,清兵入关,直抵南京。顾炎武深感亡国的屈辱,积极串联组织爱国志士举起“反清复明”的义旗,经历了十余年的抗清活动。这期间,抚育他长大成人的嗣母王氏绝食半月而死,遗嘱中叮嘱他“勿为异国臣子。”嗣母以死抗争的忠烈精神对顾炎武的影响十分大。在昆山抗清活动失败后,顾炎武为了躲避政治迫害,自1657年起,他身怀亡明之痛,开始了其后半生长达25年的流浪游历生涯。在游历中,他“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豪杰长者,考其山川风欲,疾苦利病”。其目的是念念不忘复明之举而时刻准备着寻找治国安帮、恢复明朝的有效之道。他甚至到了晚年还孜孜以求关心天下大事,其暮年定居在陕西华阴的原因“华阴绾谷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4]足见他对光复旧朝的意志和决心之愈老弥坚。与顾炎武理想社会截然相左的黑暗社会现实和个人坎坷的人生经历反映在他的经世致用伦理思想上,就要求密切地与改变现实相联系,哪怕是“引古筹经,亦吾儒经世之用”,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热忱担负起即使一个普通人也都应有的道德责任。
(二)顾炎武“经世致用”伦理思想之“源”
“经世致用”思想源远流长。儒家思想的创造人孔子在他和其弟子的多次谈话中都提到了,读书做学问,最终都要运用了生活实践当中去,以自己的才华去影响和改变社会,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5]强调读书的最终目的是能够“达政”,能够“专对四方”。除了在治学上,他广泛涉及政治伦理等经世之学外,还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历尽千辛万苦,周游列国,宣传推广其政治主张,希望诸侯士大夫们能采纳儒家的德礼之治,成就经国济世的理想蓝图。其后继者孟子、荀子等对孔子的经世致用的伦理主张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发展为“内圣外王”之道。个人通过加强道德自律以提高自身修养,同时又要在独善其身的基础上创造条件使之“达则兼善天下”,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和主观能动性去改变社会现实。经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后,儒学更是成为一家独大的官学、显学。封建统治者为了达到治国安邦、政权稳固长久的目的,采取了儒家德主刑辅的理国施政方针。汉章帝时期,还通过白虎观会议,以官方的决议方式明确了把“三纲五常”作为当时的社会核心价值来树立和践行。宋元明时期,经世致用伦理思想尽管被当时的读书人还是认为其作为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人生目标的一种价值观念而存在。但是很多儒生们一辈子皓首穷经,把读书只作为博取科举功名的手段,但真正做到经世致用的就很难了。特别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兴起,更是只注重个人内在心性的修养,读书与社会严重脱节,至于济世安帮的经世致用就更无从谈起了。明末时期,明王朝政局处于风摇雨摆之中,民族危机也日见深重。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道德风俗急剧变化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些开明的进步知识份子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为了改革时弊,挽救封建制度的危机,对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检讨和自我批判。他们痛责空谈心性的危害,力主读书做学问要紧密联系社会现实。强调以“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以“修身”,通过“修身”从而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经世之理。通过践履道德理想发挥致用的功能,积极地面向现实、影响和干预现实。与黄宗羲、王夫之一样,顾炎武“经世致用”伦理思想都是肇因于对明末灭亡惨痛教训的总结。彻底清算和揭露“宁赠外邦,不与家奴”这一反动政治伦理思想对中华民族的严重危害,成为了顾炎武着力解决的重大历史课题。在这一方面,无论是黄宗羲还是王夫之都没有象顾炎武一样下大力气去用心。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经世学派’之昌,由于诸大师之志存光复”。顾炎武正是梁启超所认为的最为重要的大师之典范。顾炎武通过自己一生不懈努力将儒家“经世致用”的伦理思想发展丰富到一个新阶段。
二、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的深刻内蕴
(一)对现实人性的深刻道德思考
顾炎武对人性的道德探寻没有脱离儒家传统的性善论范畴,但他从身处的社会现实出发,对人性论做出了其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深入思考。他认为孔子所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意味着人之性善都大体接近。但是现实中多有性恶之人,那么人之性相近就不能一概而论。所以他从现实的人性角度出发,提出“所谓善也,盖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论其变也。”人性近于善,但是不排斥有恶人,人性在后天生环境和个人的主观努力下是可以改变的。试图构建一个与现实相切合的道德行为规范体系。他反对宋明道学的“性善情恶论”、批判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思想,对人存私欲的合理性给予了积极肯定。认为个人私利的存在是客观事实,为人之常情,无可非议。他说:
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建国亲侯,胙土命氏,画井分田,合天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王政也。至于当官之训则曰以公灭私,然而禄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无将母之嗟,室人之谪,有所以恤其私也。此义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也。[6]425
在他看来,自形成了家庭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单元以来,人们为了养家糊口生存延续,就有十分稳固的亲缘关系维系着,成员之间偏袒爱护,存有私心。这是不可避免的人性合理的要求,无可非议。当政者应清楚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施行正道达到至理。而所谓的“以公灭私”论调,只是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禄足”、“田足”一己私欲,而宣传散布的欺世大谎。一方面,统治者极度骄奢淫逸,另一方面却高调让他人抛掉个人私求,这不是诈欺之言又还会是什么?只有承认个人都存有私利的合理性,才能在此基础上“合天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天下之公”社会公利的实现应以社会成员个人的私利实现为前提和条件。为治理好天下,统治者就必须满足人们的私利,而非打着“以公灭私”的旗号来欺瞒百姓。“为天子,为百姓之心,比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然矣。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7]378
承认私利的合理存在,就意味着在经济上要鼓励百姓发展生产,增加收入。顾炎武反对言不及利、讳言生财的虚伪道德理教。明确指出,在他那个时代,百姓生活没有依靠、生存都十分困难的境况下,要人们不争利、讲道德的说教是苍白无力的。只有改变民众的贫穷生活现状,在大家富起来后才有可能恢复封建人伦纲常秩序,“欲使民兴孝兴悌,莫急于求财。”同时,他提出为了使人近于善,还必须采取奖励等激励措施,对名节突出的人给予物质奖励或赐以官职,造成“以名为利”的氛围,引导人心向善,淳化风俗。
(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
中国封建社会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础,家国一体,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封建帝王“家天下,”要求移孝于忠,君为臣纲。顾炎武对君主专制、君为臣纲的封建道德律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明确区分了“保国”与“保天下”的不同的利益与责任。他认为: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8]1230
顾炎武“亡国”、“亡天下”之分,反映了明清之际,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渐萌芽,封建自给自足的农耕自然经济开始缓慢解体,使先进的知识分子透过封建宗法关系的密网,朦胧发现了另一个世界,即人们的产业行为。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日相磨擦而更使人们开始思考民富与国富的关系、国家与天下的不同。顾炎武认为,“亡国”代表着改国易号,一家一姓的君主政权的消亡更迭;但“亡天下”则是由于社会政治黑暗、腐败横行而至“仁义”受阻,伦理道德的沉丧,老百姓无法生存下去。避免“亡国”是统治集团为了一家一姓的封建王朝的稳固而殚精竭力考虑的事情;而百姓的性命攸关、社会伦理道德的兴沦却关乎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每一个普通的“匹夫”也应有为天下兴亡、民族振兴而尽自己最大努力的担当与责任。
顾炎武的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试图把民众从千百年来对君王的“愚忠”思想的迷雾中唤醒。他在《日知录》中旁征博引,论证“君”并非封建帝王专称,而是“上下之通称”。他认为,“为民而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9]顾炎武尖锐地指出,在道德责任上君王与地主官僚、士大夫们都是平等的,没有超乎民众之上的老爷,身份与血统上也并不是绝世之贵。“为民立君”所指君王产生的根源在于“为民”,为民谋利,使民幸福。对于普通的民众,做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要有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心以及为理想奋斗的决心,就是要以“经世致用”处世原则,以“明道救世”为己任。他明确表示他所有著作都是有明确的救世目的。撰写《日知录》的目的就是“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编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其书名就明确说明了所记载的材料都是“有关民生利害者。”顾炎武所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担当精神,唤呼着人们以民族复兴为己任,蕴涵着拳拳的爱国赤诚之心和伟岸高洁的民族气节。
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伦理精神出发,顾炎武在长期的飘泊游历考察中发现,落后腐朽的社会风俗是落后的封建道德滋生成长的土壤,要想整治人心,熄灭传统落后的封建教思想的毒焰,就必须涤荡落后的社会风俗。他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在《日知录》中,他特别对当时的官场吏风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嘲讽:“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自阍人之手。”“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无守不盗窃……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10]946官风腐朽至如此地步,以致于本应是熟读诗书,深谙礼义廉耻、以达经世致用的读书人却是不顾廉耻,趋炎附势,为利禄而蝇营狗苟。怎么有效改变这种恶俗,他开出了一剂药方——“清议”,即他所讲的“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11]785通过社会舆论的道德力量来变化社会风俗。体现了顾炎武对道德作用认识的深化,其言论自由的倡举,又为近代资产阶级“新民”思想的源头之水,具有进步的启蒙作用。
(三)注重“以名为治”的道德教育
顾炎武非常注重伦理道德对人心的教化和合理社会秩序的调节功能。他认为,道德是“治人之大法”、“立人之大节”。提出了“以名为治”的道德教育原则,主张道德教育以“正人心,厚风俗”,并认为这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方法。
顾炎武针对封建王权的专制主义所施行的严刑峻法而提出的“以名为治”的道德教育,是因为看到了封建法治对人性的残害与对社会发展的桎棝。他认为,封建君主所提的法治,是维护其个人专制独裁的统治为目的。君主“欲专大利”,就自然“用权于法。”刑罚虽然会使行恶者有所收敛,有所顾忌,但是也会使人们在严刑峻法面前,如履薄冰,谨小慎微。既不能对民情时政自由发表“清议”,也不敢在行为上放开手脚,发挥个人的才华与创造力。所以,他对封建严酷刑罚高压下的社会现实十分不满:
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缚,至不可动,而人之智虑,自不能出于强绳约之内,故人材亦以不振,今与人稍谈及度外之事,辄摇手而不敢为。[12]2010
严酷的刑罚不仅会压抑人性,束缚个人自由。而且还会助长官吏专权的嚣张气焰。一旦手持法治权柄,他们就会为所欲为,无恶不作,造成士大夫权贵阶层的道德败坏,吏风影响民风,从而导致社会风气的恶化。当然,顾炎武并没有武断地一概否定“法”在治恶方面的作用。但是要让天下承平,民风敦朴,最重要的还是加强道德教育,实行“以名为治”。通过“礼义廉耻”等作为当时社会最高名节的道德规范的教育来整治人心,营造人人重德向善的良好社会风尚。具体的道德教育措施除了之前论及的以“清议”来发挥社会舆论的力量和作用以外,还要注重劝学奖廉,对学问做得好、个人的思想道德有美好名声的人要通过田地或官爵等重奖来扩大影响,鼓励后进。同时,顾炎武提出还要利用封建家族宗法制度在当时的特殊地位进行道德教育。他认为在一家之中,可以通过父亲兄长,在一个族中可以通过宗族长老进行道德教育,这样就可以将不善的萌芽及早地消除在家族的墙门之内。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见,顾炎武在考察道德教育的路径及方法上从个人、家族、社会三方面思考得相当全面、深刻。今天,我们对个人的道德教育的实行也都必须注重对个人向善的激励、家庭氛围的感染和社会大环境包括社会舆论等的监督。
(四)严谨求真的为学作风
顾炎武把匡时济世当作自己终身追求的学术抱负,“以经学济理学之穷”,试图复兴经学,把经学引导到经世致用的道路上来,以拯救明中叶以来考证之学日益刻意“求博”的流弊。“求博”是博骄夸耀的意思。博骄则失去扎实问学、实事求是之心,而力追哗众取宠、标新立异之意。纪昀曾说过:“明人著书,好夸博奥,一核其实,多属子虚,万历以后风气类然。”[13]对于这种为学的恶俗,顾炎武十分揪心,并身体力行鄙弃这种浮华的治学态度,以求真务实的为学态度和踏实严谨的作风引领学术发展方向。
顾炎武治学求是求真,以经文为原本,以考订为方法,以通经为目的,不突显今文古文之别,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对今文古文一视同仁。他的经学对古今学术门户既不一味维护,也不刻意贬损,不以人废言也不以言废人,坚持客观公正的是非评判标准。在《日知录》中,卷二《司空》篇对古文学家孔国安提出了质疑批评,卷五《莅戮于社》篇他又引用孔国安的相关论述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凡此种种,在他的《日知录》《肇域志》等著作中常常出现,说明了他学术胸怀的开阔豁达、学术态度的理性严谨。
顾炎武对汉唐旧注、宋明新说都细细考证,辨伪存真,没有丝毫马虎。在考证经文和史实过程中,他特别注重辨明其正误,审查其源流,阐释其疑义,钩沉其潜在,阐发其幽微,做到考据真实详尽。为了治史,他广泛收集史料,经史子集、邸报实录、章奏文册、笔记杂录、方志谱牒、文物古迹、金石碑刻、等等无一不仔细考察,反复筛选。尤其是他一生游历祖国南北,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每到一处,不仅拜访当地名儒,而且还留意遗迹碑贴,在过往历史遗存下来的珠丝马迹中寻找失去的历史真象。通过考史辨妄,索隐发微,使一些晦而不明、幽冥隐匿的史实得以彰显与突现。
顾炎武一生治学求真严谨,以音韵文字考据为治学路径,以经世致用为治学目标,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兴太平为为学宗旨。他激烈反对空谈心性、奢言玄理,认为那是不务实际的无用之学,主张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明道淑人、抚世载物。学问不仅要修养身心,更要务实致用。可以说,顾炎武严谨求真求实的为学,既可坐而言,同时又可起而行。
三、顾炎武“经世致用”伦理思想对后世的重大影响
(一)对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重要启蒙作用
顾炎武“经世致用”伦理思想的提出,对长久以来宋明理学给人们带来的思想禁锢给予了巨大的冲击,为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重要启蒙作用。顾炎武的“经世致用”的伦理思想兼融并蓄着孔孟及其后继者儒家积极和济世思想又内含着当时代民族危难之期可贵的民族气节民族大义,影响深远。丁寿昌先生对顾炎武“经世致用”的伦理思想给与了高度的赞誉:“顾氏举康成以示不敢专辄,更可为师法,并推及宋明义之改经亦多可议矣。明人经学承宋元之后,师心自用,家法荡然。自亭林出而知求之注疏,证之史传,可谓卓识。但蹊径初开,说犹未畅,后之儒者知尚实学,不为空言,我朝经学,直接汉唐,先生轫始之功,不可没矣”。“致用之学,自亭林以迄颜李,当时几成学者风尚”。[14]2431可见其影响之大。晚清时期龚自珍针对当时人们做学问脱离社会现实专注经书音韵及辞章考据情况和“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社会现状,在其《对策》一文中认为:“不研乎经,不知经术之为本源也;不讨乎史,不知史事之为鉴也。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15]做学问要通乎当世之务,这自然是对顾炎武“经世致用”伦理思想的传承。魏源对顾的人格和思想十分敬仰,在他所编《皇朝经世文编》中就选取了97篇顾炎武著作,是他所精选的经世文章中选录最多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更是对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伦理”推崇倍至,“要之其标“实用主义”以为鹄,务使学问与社会增加密度,此实对于晚明之帖括清谈派施一大针砭;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告示于文人,实炎武启之;最近数十年以经术而影响政体,亦绍逮炎武之精神也。”[16]81
(二)对当代知识分子为学担当精神的重要启迪
明末清初,剧烈的社会大动荡、大变迁,极大地冲击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很多人出于明哲保身的目的,躲进书斋,空谈心性,远离世务,以致学风空疏。顾炎武为之深深忧虑,他倡导“清议”,认为读书人做学问应当面对现实,致力于转移人心,救正风俗。顾炎武不仅认识到了这一点,同时也把其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目标,表现出他对社会现实强烈关注的担当精神,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进步思想家的卓著。这种忧时虑世的责任与担当对当代知识分子为学有着重要的启迪价值。首先,为学要有老老实实的态度。顾炎武对当时“文章之病,全在模仿”的学风十分不满。他认为,写文章著书立说一定要有严谨务实的态度。他恪守“良工不示人以璞”之古训,把著书比作是“采铜铸钱”,一定要精雕细琢。《日知录》的结撰,不间寒暑,精益求精,耗尽了顾炎武毕生心血。当今社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或受困于生计,或为追求蝇利浮名,急功近利,普遍缺失了这种踏实严谨,久久为功的学风。特别是有些人将别人的成果通过一番改头换面、精心包装,就改编成自己的东西。这种学术的腐败之风不仅吞蚀着读书人的良心,也造成了极度恶劣的社会影响。顾炎武将这种作法比为“废铜充铸”的“窃书”行为。“窃书者”更被他斥为“钝贼”。其次,为学要有担当精神。白居易曾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做学问要有现实的担当与责任,要有时代使命感。顾炎武更是指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时代的积极关注,“匹夫”应如此,知识分子更是要如此。他强烈地批判了那种“置四海困穷而不言”的不良学风,认为这是一种逃避社会责任的消极思想。他指出文人不仅要“博学于文”,而且要“行己有耻”。作文要经世致用,强调与实际相结合的“实学”。处于社会大转型大发展的当代知识分子,更应像顾炎武所提倡的那样,认真深入社会实践,聆听时代发展的心声,用心去感悟、体念时代,做出有益于国家与时代进步的真学问。
(三)对当代政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启示意义
顾炎武“经世致用”伦理思想所涵括基于对人性的善恶思考之上提倡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清议”的政治监督举措以及“以名为治”的道德教育,尽管囿于其所处时代、阶级而存在着难免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是后时代社会发展所隐现的,但在当时确乎是顾炎武针对明末清初皇权高度集中的封建专制弊端提出的具有当时代意义的解决方法。其“经世致用”伦理思想中道德教育与责任担当意识意蕴深长。在封建专制之下,世风没落,世人道德堕落,内患不断,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焦虑感让顾炎武从现实的人,包括君、臣、民等,尤其是从“私”与“欲”的现实人情人性出发,希冀通过“以名为治”等措施来实现道德人心的转向,来促进社会世风的趋好,这些都展现了对中国传统政治治理近代转型的理性思考,体现了极其宝贵的民主性思想精华。如,顾炎武在对当时社会“无官不赂遗”、“无守不盗窃”、“上下怀利以相接”的丑恶现状作出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基础上,从人性的分析出发,他认为导致官吏极度贪腐的深层原因源于制度建设的缺失。所以他提出了加强制度建设的种种措施,并将法制建设与道德教育结合起来,“以名为治,”“清议”,将官僚的道德品质的高下与其切身利益的获得紧紧相连,“既体现重在防止政府官员犯罪的立法精神,又充分发挥道德舆论对于官员的监督作用。”[17]对当代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加强社会道德价值建设中的“制度建设”、“核心价值观培育”、“舆论监督”等都有隐约的内涵上的相通,可以借鉴其优秀精神,化而用之。又如他的“天下之才皆可由天下之人举而荐之”的主张,正是其深研自隋唐以来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的弊端,特别是明朝以八股文取士将这些弊端发挥极致后所提出的修正科举制度、选拔有真才实学人才的政治主张,等等。这些都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因之,今天我们研究顾炎武“经世致用”伦理思想,就是要于其中找到他伦理思想中超越时空的普遍性,感悟内在的人文精神,从而受到深刻的思想启迪,进而对其思想价值进行现代转化,在继承基础上实现创造性的新发展。
[1] 顾炎武. 亭林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4] 顾炎武. 日知录集释全校本[M]. 黄汝成, 集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5] 吴长庚. 试论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思想[J]. 江西社会科学, 2007(10): 66-70.
[6] 顾炎武. 日知录校正[M]. 丁寿昌, 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7] 龚自珍. 龚自珍全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8]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9] 许苏民. 论顾炎武政治思想的三大理论特色[J]. 湖北社会科学, 2006(8): 90-95.
(责任编校:彭 萍)
Gu Yanwu’s Ethics of Studies for the Purpose of Application and Influence
KUANG Liehui1, 2
(1. Research Base of Teacher’s Ethics Education, Hunan City University, Yiyang, Hunan 413000, China; 2.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Gu Yanwu’s ethics of Studies for the administering state affairs reflects of social upheaval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reflecting the era when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1644-1911) period. It is pondering its meaning and moral reality of human nature, the concept of “the rise and fall, everyone is responsible”, the responsibility to play and focus on “rule called” moral education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future generations. Because of its time limitations, it also had inevitable limitations. But you can transcend time and space from his thoughts by the profound universality that is to enlighten and modern transform its ideological value and to achieve new development in the creative basis of inheritance.
Gu Yanwu; ethics; idea of administer of state affairs; value influence
B 249.1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7.03.018
2096-059X(2017)03–0094–06
2017-03-12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5YBA073);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15C0271)
匡列辉(1974-),男,湖南益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伦理学、法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