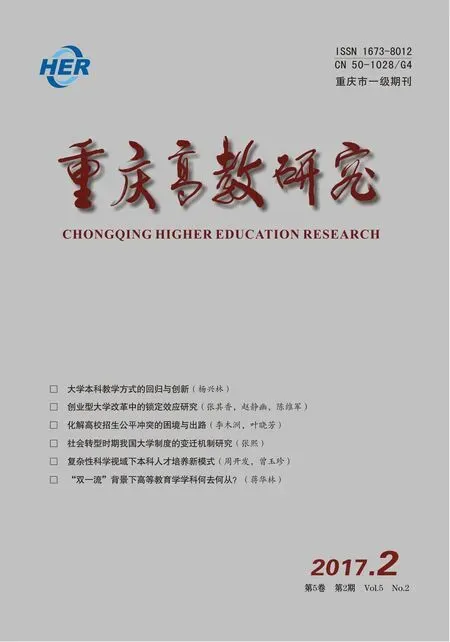化解高校招生公平冲突的困境与出路
——基于《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的分析
李木洲,叶晓芳
(1.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武汉 430079;2.湖北大学 教育学院,武汉 430062)
高考改革专题
化解高校招生公平冲突的困境与出路
——基于《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的分析
李木洲1,2,叶晓芳2
(1.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武汉 430079;2.湖北大学 教育学院,武汉 430062)
主持人语:
高考公平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多年来,学术界关于这一话题虽然有了丰富而深入的阐述,但随着高考的不断改革,如何进一步维护高考公平,又应该如何看待高考公平,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做到推陈出新、与众不同,不免小有难度。本期我们选编的3篇文章,都在高考公平这一话题上另辟蹊径。李木洲和叶晓芳对《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的思考,可谓把握了高考研究的“前沿”。这一计划自2016年5月出台以来,成效有待检验,经验值得总结,问题需要反思。作者从美国“平权行动”由“种族平权”向“经济平权”转移的趋势中受到启发,提出进一步落实我国高考公平的途径在于不断缩小区域、民族及群体间的经济地位与收入水平差异,这一观点既具有国际视野,也相当深刻。刘庆龙关注的高考命题“城市化”现象则是一个“旧问题”,但他一反传统观念,认为高考命题适度的“城市化”是必要的,并非“不公平”的体现。维护高考公平不能寄望于高考试卷的“去城市化”,而是要从消除城乡教育质量差异的角度着手。观点虽略显“反叛”,但也言之成理,能够自圆其说。郜丹丹则从统计数据出发,揭示了从科举考试中延续至今的“分省定额”制在高考录取当中造成的差异,进而提出高考公平的内涵不是单一的,我们需要在人口公平、考试公平和区域公平三者之间取得相对平衡。总的来说,3篇文章各有所长,颇具特色,相信能给高考问题的研究者和关注者带来一定的启发。
厦门大学 周 序
《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作为完善高考制度设计和促进高考公平的重要举措,当前面临三大困境:一是在制度层面招生协作计划指标分配亟待优化;二是在实践层面存在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三是在现实层面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有待均衡。基于罗尔斯的正义论,《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符合正义原则,现阶段有进一步推行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从现实国情来看,当前化解高校招生公平冲突有两条可供选择的路径:其一,坚持差异化原则,根据全国高校的不同类型与层次进行分层调控;其二,坚持补偿性原则,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弱势地区加大投入和建设力度,力图优质均衡。从长远来看,结合美国“平权行动”的实践经验与发展趋向,即“平权”的原始逻辑开始由“种族平权”转向“经济平权”,要实现我国整体的高水平教育公平与考试招生公平,其根本途径在于不断缩小区域、民族及群体间的经济地位与收入水平差异。
招生协作计划;考试公平;区域公平;平权运动
2016年5月上旬,湖北、江苏两省几乎在同一时段发生了针对《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以下简称《招生协作计划》)的“高考事件”。该事件的发生反映出当前中国高校招生存在较严重的“公平冲突”:一方面是国家为缩小区域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通过对省区间高校招生指标的宏观调控,促进区域教育公平协调发展;一方面是高校生源指标调出省份的考生家长从本省升学利益出发,要求减少生源指标调出数,以维护考试公平。其实,纵观中国千年考试史,“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如影随形,亦被学界称为千古难题。时至今日,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能否合理化解这对矛盾,不仅事涉中国教育公平的标准与价值观,还事关《招生协作计划》的存与废。本文基于正义论的视角,在检视《招生协作计划》历史成效的基础上,试图廓清实施《招生协作计划》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并尝试提出建设性对策。
一、《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的成效检视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正在经历一个由大众化向普及化迈进的阶段。然而,由于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原因,我国区域间社会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够均衡,在分省定额与分省命题两个配套政策之下,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学生考取高水平大学的机会存在较大的不平等现象。2007年8月,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要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同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把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作为高校招生工作的一个重点。”[1]2008年,为切实促进国家区域整体协调发展,解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区域差距问题,教育部制定并实施了《招生协作计划》,即由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办学条件较好的省份及直辖市面向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匮乏、高考录取率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招生,旨在为中西部学生提供更多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缩小区域入学机会差距[2]。
据统计,从2008—2016年,每年从支援省份向受援省份安排的招生协作计划依次为3.5万人、6万人、12万人、15万人、17万人、18.5万人、20万人、20万人和21万人,连续8年呈增长态势[3]。根据教育部统计测算,仅2008—2012年,《招生协作计划》惠及8个中西部省区,包括山西、广西、云南、河南、安徽、贵州、甘肃、内蒙古,招生规模等同于在发达省市建设了68所年招生量为2 500人的专门招收中西部地区考生的普通高校[4]。需要指出的是,支援省份和受援省份及其输出和划拨的招生数额是动态调整的,多到数万名,少到几百名不等。2016年支援省份增至14个,受援省份由最初的4个增至10个。从支援成效看,《招生协作计划》的持续推行,明显缩小了高考录取率的区域差异,到2015年,高考录取率最低的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从2010年的15.3%缩小到5%以内[5],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另外,在均衡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方面,有学者利用2012年和2014年“985工程”高校招生数据,研究发现:与2012年相比,2014年协作计划输出省份“985工程”高校招生减少了5%,而中西部地区协作计划输入省份招生增长接近12%,大幅度增加了中西部地区考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且省际差距也在逐渐缩小[6]。上述统计与研究表明,在国家现有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格局之下,《招生协作计划》通过指标分摊补偿的方式在全国高考录取率、城乡高考录取率和部属高校录取率等多个层面促进了高考区域公平。它不仅是高校招生计划管理模式的创新,也是推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有力举措。
二、《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面临的主要困境
《招生协作计划》尽管对促进高考区域公平效果显著,但现阶段依然存在难以克服的三大困境:一是招生协作计划指标分配的制度设计问题,二是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实践矛盾问题,三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现实问题。
(一)制度层面:招生协作计划指标分配亟待优化
《招生协作计划》卓有成效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触即发的利益矛盾,这些矛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输出省份的招生名额配比。如2016年《招生协作计划》安排总量增至21万人,湖北、江苏两省分别为3.8万人和4万人,两者之和占比37.1%,而湖北、江苏两省近3年的一本录取率大概在10%左右,处于全国中等水平,与同期排名前三的北京、天津、上海相比差距甚大,均不及三者的一半。由此出现的“劫贫济贫”而非“劫富济贫”现象,导致两省考生家长认为这样大量的名额调控不合理、不科学、不公平,会直接损害本省的高考升学利益,进而引发了对招生指标外补的政策不认同。二是输入省份的招生名额配比。对中西部省份而言,它们不仅关注输入的招生名额总量,更关注输入的高水平大学的招生名额数量,因为当前中国已进入“上大学不难,难的是上好大学”的时代。然而,从输出省份发布或通告的招生名额分配单中不难发现,输出省份都以不减少本省重点高校招生计划总数为前提,用于支援中西部省份的多为一般本科院校及高职(高专)院校的招生名额,这种“优先自保”而非“均衡普惠”的做法,不仅难以吸引中西部省份的优秀考生,甚至还存在地域歧视的误会风险。因此,通过制度设计优化或合理分配各级各类输出与输入省份的招生协作计划指标是进一步推动实施《招生协作计划》的关键所在。
(二)实践层面: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矛盾难突破
《招生协作计划》产生“公平冲突”并非偶然,其症结在于政府追求的区域公平遭遇考生家长期待的考试公平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区域公平”与“考试公平”之间的矛盾古已有之,且有沉重的血的历史教训。第一次针锋相对的较量发生在北宋年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北方士人主张“逐路取人”,旨在确保不同区域的人才都有获得选拔的机会;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南方士人主张“凭才取人”,强调严格按科举成绩的高低论才选拔。第二次悲剧性较量发生在明洪武年间,即著名的“南北榜事件”,当时为平息科举风波,避免引起北方政治动乱,朱元璋不惜无视“考试公平”,牺牲南方士人的利益,而完全倒向“区域公平”,强行再考皆录取北方士人,涉案官员及南方考生大多遭受惩处,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7]。此后,直到清乾隆年间,采取兼顾区域公平与考试公平的分省定额制,才算找到了能较好平衡二者的制度设计,并一直沿用至科举制废止。有研究指出,“1 300年的科举演变史表明……无论怎样发展,在基本遵循考试规则的前提下,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都只能是相对的”[8]。而“古今900余年来关于这一两难问题讨论的观点如出一辙,不存在绝对的公平和完美的解决之道”[9]。同科举考试一样,作为高竞争、高利害、高风险的人才选拔考试,高考的绝对公平是理想的,可以成为追求的目标,而相对公平是现实的,只能最大限度地去实现[10],它始终只能是一个由实然状态向应然状态努力发展的过程。
(三)现实层面: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有待均衡
所谓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指那些拥有更多、更好、更有利于高级人才培养的各级各类高等院校(也含具有招生资格的科研院所),即俗称的“高水平大学”。由于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原因,我国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尤其以“部属大学”(即中央各部委及国务院直接管理的高校)为代表或主体的高水平大学表现最为突出。目前,在代表中国最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39所前“985工程”院校中,位于东部地区的有27所,位于中部地区的有5所,位于西部地区的有7所。在116所前“211工程”院校中,位于东部地区的有77所,位于中部地区的有15所,位于西部地区的有24所。相比东部密集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中西部除湖北、陕西、湖南、四川、重庆外,多数省区的高水平大学数量明显偏少。如河南作为人口过亿的大省,现仅有1所“省部共建”的前“211工程”大学——郑州大学,既没有前“985工程”大学,也没有教育部或其他部委直属的高水平大学[11]。显然,当前这种分布失衡的高等教育结构与格局有必要做出合理化调整。
三、美国高校招生“平权行动”考察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公认的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大学入学考试制度设计一直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考察美国大学考试招生中的公平与权利问题,对解决当前我国高校招生公平冲突具有较强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一)“平权行动”及其正义性选择
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Kennedy)与约翰逊(Lyndon Johnson)先后签署了10925号和11246号行政命令,这些行政命令旨在消除美国全国范围内在教育机会、就业待遇、政治投票等方面对黑人及其他少数族群的歧视与排斥,由于其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公民的平等权利,被称为“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又称“肯定性行动”)[12]。“平权行动”明确规定,为消除弱势阶层的不利地位和发展障碍,“各类机构和法院按平权行动采取正当行为,不得因为种族、肤色、性别和原国籍而对一部分人实行歧视政策”[13]。而为切实帮助在美国社会长期受到歧视的群体争取教育与就业的平等机会,当时美国大学必须根据联邦政府的要求在招生中采取配额制,且黑人及其他少数族群与弱势群体可以优先入学。“平权行动”的效果立竿见影,最典型的例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到90年代中期,一个曾经近乎‘纯白’的学校已变得五颜六色:39%的亚裔;32%白人;14%的拉美裔;6%的黑人和1%的印第安人”[14]。
罗尔斯是自由主义平等观的典型代表,其正义论既有平等主义的倾向,也有自由主义的倾向,这一点从他提出的公平正义两大原则(自由平等原则、机会的公正平等及差别原则)和两个优先规则(自由优先、正义优先于效率和福利)可见一斑。然而,在美国,左派(平等主义者)和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者)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解存在明显分歧。左派主张只有“平等公平”才符合正义理想,认为罗尔斯强调自由优先性不利于实现平等与正义,依然有利于强势阶层。右派主张个人自由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认为罗尔斯突出倾向于最少受惠者没有充足依据,而这将侵犯人们的自由权利[15]。事实上,“平权行动”在美国引起的争议,也与这种激烈争论有着某种理念与认识关系。在约翰逊总统之前强调的是机会平等,不问种族、肤色、性别及原籍,一视同仁。之后开始转向对少数族群的优待或补偿,在强调自由、机会平等时,更寻求事实和结果的平等,即要求增加最少机会者的机会。因此,从本质上看,“平权行动”体现的是罗尔斯第二正义原则(差别原则)的补偿正义。
(二)“平权行动”有效平衡“效率与公平”
公平与效率是高校考试招生制度中的一对固有矛盾,在多数情况下表现出两种实然状态,即要么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要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现实中很难达到二者并重或同时兼顾的理想状态。美国的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在实践中也存在着处理二者关系的问题。譬如,在追求新生选拔效率方面,美国的高水平大学普遍实行择优录取的政策,招生特别强调综合评价,即以统一考试的SAT或ACT成绩、高中学业成绩(GPA)以及班级排名(CR)为主要学术标准,且在同等条件下更看重GPA、CR以及修读AP或BI课程的表现。美国大学研究集团(CRG)依据SAT或ACT成绩、班级排名、录取率3项综合选拔指标,把选择性大学分为强竞争性、高竞争性、较高竞争性及竞争性四类[16],上述3项综合选拔指标的要求与学校的层次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美国高校为避免人权与教育权争议,又特别注重招生公平,并通过立法形式强制执行。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为解决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的少数民族问题,颁布了《民权法》,后来为促使高校切实落实《民权法》的有关规定,又通过了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收少数族群考生的高校招生政策,即“平权行动”[13]。此后,联邦政府还相继颁布了《初中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中等收人家庭学生资助法》等一系列高等教育补偿性政策与计划。可见,“平权行动”在美国高校招生中发挥着促进考试公平与教育公平的功能,为避免过于注重招生效率起到了有效的平衡作用,较好地处理了高校招生中存在的效率与公平这对矛盾。
(三)“平权行动”的政策目的与趋向
对美国黑人及其他少数族群而言,要缓解由于历史遗留的压迫、歧视性地位以及低教育程度而造成的现实困境,仅靠自身努力很难实现,必须借助政策性外力加以补偿,因此“平权行动”在理念和理论上均具有很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通过高等教育帮助弱势群体提高社会竞争力,从而缓解种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实现社会融合是美国高等教育“平权行动”政策的根本目标[17]。然而,在实践中,“平权行动”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争议不断。近年来,其争议主要集中在:一是“平权行动”可能导致反向歧视;二是“平权行动”会造成少数族裔的内部不公平;三是“平权行动”本身会给少数族裔们打上“破格录取”的烙印,造成对有能力的少数族裔的歧视。此外,随着经济两极分化,影响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因素或深层次的原因已演变为经济地位,而非种族。因此,有学者认为,在贫富差距显著的背景下,对少数族群倾斜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更多考虑其社会经济地位。换言之,在促进教育与就业机会均等过程中,经济平权比种族平权更为重要,以至于美国有些州开始重新审视“平权行动”存在的必要性,目前已有8个州明确禁止在州立大学录取中实施“平权行动”计划。由此可见,“平权行动”作为美国促进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的一项重要制度,经过几十年的推行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其“平权”的原始逻辑正在逐渐发生转变,即出现由“种族平权”转向“经济平权”的趋势。
四、化解高校招生公平冲突的根本出路
在西方,正义被认为是关于权力和利益的正当性分配原则,是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伦理基础。然而,长期以来,对正义的理解,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有布坎南、哈耶克、诺齐克、罗尔斯等。布坎南认为,正义应注重规则,强调程序正义和机会公平,但其正义观具有个体主义、边际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特点[18]。哈耶克也认为,正义规则的核心内容是程序正义,但遗憾的是他对自由、平等、正义等范畴的理解存在片面性。诺齐克则认为,“正义意味着个人权利不受侵犯,国家权力仅在于维护过程的公正”[19]。与前三者不同,罗尔斯的正义观是公平正义观,他在“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条件下论证道:正义的出发点是公平,即公平的就是正义的,而所谓公平应包含起点平等、机会平等以及结果平等。事实上,罗尔斯并不否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重要性,只是主张对于由自由引发的不平等应该通过国家再分配的方式来实现最大程度的平等,其理论本质上强调的是平等的价值[20]。或可说,在罗尔斯看来,公平正义不是纯粹的平均主义,而是要求把不平等限制在公平原则要求的范围之内。一言以蔽之,罗尔斯所提倡的正义属于“实质正义”,是对西方其他学者正义观的一种扬弃与超越。
显然,一项制度正义与否,事关其存废。正如罗尔斯所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安排有序,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21]3。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国家实施《招生协作计划》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在现阶段有进一步推行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从现实国情来看,当前化解高校招生公平冲突有两条可供选择的路径:一是坚持差异化原则,根据全国高校的不同类型与层次进行分层调控;二是坚持补偿性原则,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弱势地区加大投入和建设力度,力图优质均衡。
(一)坚持差异化原则,实施分层调控
当前,在全国平均高考录取率超过85%的背景下,国人对高考的追求已由“上大学”转向了“上好大学”,也即转向了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集中追求。然而,在分布不均、省部共建及分省定额等现实与政策背景下,尽管教育部明确规定部属高校属地招生比例不得超过30%,但依然存在区域间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较大差异,成为高考公平的一大弊病。因此,应根据全国高校的不同类型与层次进行差异化分层调控。目前,根据我国高校现有类型与办学水平,大致可分为前“985工程”大学、前“211工程”大学、“省部共建与地方重点综合性大学”、“一般本科院校”及“高职高专院校”5个层次。按照有利于确保国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效益最大化,有利于国家战略性高精尖人才的培养,有利于满足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有利于保障广大中间高考利益群体的“升本”利益,有利于形成层次分明、类型多样的高等教育生态格局和多样化人才培养系统的原则[22],具体招生计划可调控如下:
其一,前“985工程”大学定位于精英教育,严格控制招生规模,在确保一定比例的区域性(民族、贫边、国际)名额外(不超过30%),“唯才是举”面向全国招生,改变其地方化招生倾向,让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性大学甚至国际性大学。其二,前“211工程”大学人才培养介于精英人才与大众化人才之间,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导向,在注重生源多样性的前提下,允许较高比例(不宜超过40%)的地方化招生,以满足区域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要。其三,“省部共建与地方重点综合性大学”以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可更大比例地面向本省份招生,以满足行业性及地方性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其四,“一般本科院校”及“高职高专院校”以社会服务型与技能型人才培养为主,依据办学定位、特色及生源情况,可完全自主地决定招生名额的分配。
(二)坚持补偿性原则,推进优质均衡
罗尔斯认为,机会的公平是一种形式的公平,实质公平的实现应基于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并适当结合补偿性原则。它要求国家通过强制性政策对社会成员的资源占有差别进行合理调节,给予处于劣势地位的弱势群体以适当补偿。也就是说,尽管社会成员在经济、权力甚至智力等方面客观存在不平等,“但只要其结果能给那些最少受惠者以利益补偿,它们就是正义的”[21]77-79。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原因,我国区域间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平衡,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也不均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学生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也不平等。因此,要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国家需要坚持贯彻补偿性原则,加大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和建设力度,缩小我国中西部地区同东部地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差距,向优质均衡的目标迈进。从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来看,有两种较好的解决方案:
其一,增设教育部直属高校。根据现有高水平大学(以教育部直属高校为主体)的分布格局,在前“985工程”与前“211工程”不再继续实施的背景下,通过政策调整和相应投入,在目前13个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省区选择1~2所办学基础扎实、办学水平较高的省属院校或省部共建高校,将其升级为部属大学,或许是一个较为可行的办法。正如刘海峰教授指出的,解决当前高考录取的地域不平衡问题,在像河南这样的中西部人口大省,若能增设1所教育部直属大学,要比教育部从东部省市拿出几百个名额来给河南要立竿见影得多[23]。因此,在均衡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方面,作“区域增量”比作“区域均量”更为重要与有效。
其二,以“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为契机,重构优质高等教育格局。即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通过优质资源向薄弱地区的倾斜性输入及合理配置,着力在中西部省份打造若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至少打造若干国内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逐步使全国中、东、西部总体形成较为均衡的优质高等教育新格局。当前,我国每年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已超过4%,可重点考虑向中西部地区合理倾斜,加快优化区域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总之,在政策和经济条件都允许的条件下,抓住“双一流”建设机遇,也是推进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均衡化的重要途径。
此外,有学者提出要真正实现教育公平,可以考虑打破分省按计划录取的制度,实施“全国统一考试+大学完全自主招生”的改革方案[24]。该设想虽符合考生平等自由择校的权利诉求,但从科举的历史教训和国家整体利益来看,完全以考试公平为核心的制度设计,不利于区域间人才选拔与培养的均衡化发展,长此以往势必影响区域稳定与共同发展。因此,理想的高校招生制度设计应坚持兼顾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这一基本原则。
五、结语
高考“上连高等教育,下引基础教育”,是国家的基本教育制度,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高考制度改革过于追求考试公平或过于强调区域公平,都将产生严重的影响与后果。化解“公平冲突”,既要从制度设计层面抓住主要矛盾,透析实践之争,又要从现实条件出发,寻找最大公约数,将考试公平和区域公平统一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上。总之,基于罗尔斯的正义论,高考制度改革中的高校招生计划调控问题,必须根据现阶段的国情、教情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在兼顾国家利益与考生利益的基础上,注重宏观调控与微观指导,坚持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相协调的基本原则。而《招生协作计划》的改革,也只有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及其价值立场,才能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各利益主体的共同支持。当然,从美国“平权行动”的实践经验与发展趋向来看,要实现我国整体的高水平教育公平与考试招生公平,其根本途径还在于不断缩小区域、民族及群体间的经济地位与收入水平差异。
[1] 唐景莉.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谈“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N].中国教育报,2008-03-17(01).
[2] 关于下达2008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的通知[EB/OL].(2008-04-28).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892/201001/xxgk_77150.html.
[3] 张男星,孙继红.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实施的成效及意义[EB/OL].(2016-05-17).http://opinion.people. com.cn/n1/2016/0517/c1003-28358048.html.
[4] 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EB/OL].(2012-09-03).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 moe/s6811/201209/141512.html.
[5] 万玉凤.协作计划不影响支援省份高招录取率[N].中国教育报,2016-05-16(01).
[6] 张小萍,张良.中国高校“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实施成效分析——“985工程”高校为例[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5(3):48-56.
[7] 刘海峰.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1):157-173.
[8] 郑若玲.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高考录取中的两难选择[J].高等教育研究,2001(6):53-57.
[9] 刘海峰.高考改革中的两难问题[J].高等教育研究,2000(3):36-38.
[10]李木洲.高考公平的元思考[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2(8):29-33.
[11]刘海峰,李木洲.教育部直属高校应分布至所有省区[J].高等教育研究,2012(12):17-25.
[12]林杰.加州大学平权法案危机的政策分析与组织模型[J].高等教育研究,2013(2):100-109.
[13]吴向明.美国高校招生的公平与效率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08(10):17-21.
[14]刘瑜.“平权运动”中的程序正义与补偿正义[EB/OL].(2016-10-06).http://www.aisixiang.com/data/57844.html.
[15]肖地生.肯定性行动与美国高等教育入学平等——自由主义平等的正义审视[J].高等教育研究,2016(7):98-103.
[16]College Research Group of Concord,Massachusetts.200 most selective colleges[M].New York:Simon&Schuster,Inc.,1991:xxxi.
[17]张玉.美国高等教育“肯定性行动计划”政策价值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2007(6):69-73.
[18]马玉林.布坎南的正义观及其困境[J].科学·经济·社会,2014(2):34-39.
[19]朱春晖,罗建文.否定性的、寻求个人自由的社会正义观——哈耶克的社会正义思想评析[J].哲学动态,2015(12):57-63.
[20]陈志.罗尔斯与诺齐克的正义观比较研究[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8-13.
[21]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2]李木洲.高考改革的历史反思——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2014:227-228,381.
[23]刘海峰.可尝试在中西部人口大省设若干“985高校”[N].21世纪经济报道,2012-06-27(02).
[24]熊丙奇.从“生源调整风波”看如何推进我国高考公平[J].上海教育评估研究,2016(8):39-42.
(责任编辑 蔡宗模)
The— D—ilemma and Outlet of Resolving the College Enrollment Fair Confli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upport of the Mid-West College Enrollment Cooperation Program
LI Muzhou1,2,YE Xiaofang2
(1.College of Education,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2.College of Education,Hubei University,Wuhan 430062,China)
A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mprove and promote the fairness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The Support of Mid-West College Enrollment Cooperation Program is facing three major difficulties:one is the need to be optimized the enrollment collaboration planning index distribution at the level of system;the second is the existence of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examination fairness and the regional fairness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the third is the distribution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resources to be balanced in reality.Based on Rawls’s theory of justice,The Support of Mid-West College Enrollment Cooperation Program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and at this stage there are necessity and rationality for further implementation.From the reality of China,there are two alternative paths to resolve the conflicts of college enrollment:firstly,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differentiation,stratified controlling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ypes and levels of universities;secondly,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compensation,to balance the distrib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resources.In the long run,combined with the“affirmative action”of the practice experience and development trend,namely“original logical equality”started by“racial equality”to“economic equality”trend,a high fairness level of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 can be achieved in China.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 is to decrease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economic status and income level of groups.
The Support of Mid-West College Enrollment Cooperation Program;fairness of examination;regional fairness;civil rights movement
G521
A
1673-8012(2017)02-0022-08
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17.02.004
2016-11-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转型与构建:高考制度现代化研究”(CAA140117)
李木洲(1981—),男,湖北广水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湖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院校研
究中心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考试制度及高等教育理论与历史研究;
叶晓芳(1992—),女,河南鲁山人,湖北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李木洲,叶晓芳.化解高校招生公平冲突的困境与出路——基于《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的分析[J].重庆高教研究,2017,5(2):22-29.
format: LI Muzhou,YE Xiaofang.The dilemma and outlet of resolving the college enrollment Fair confli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upport of the Mid-West College Enrollment Cooperation Program[J].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2017,5(2):2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