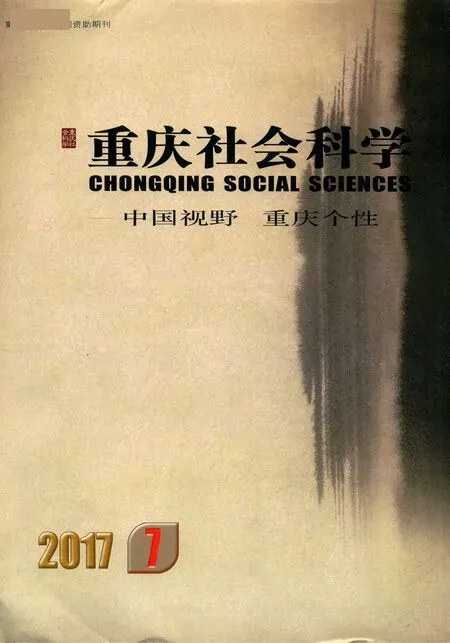“互联网+”时代的行政法律规制*
严新龙
“互联网+”时代的行政法律规制*
严新龙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必然导致传统市场经济模式发生深层次变革,互联网技术与市场经济深度融合。在此背景下,作为行政法原则的公共利益内涵与外延进一步拓展,公共利益主体的年龄大为降低、作为内容的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进一步扩展、“互联网+”成为扩充私权的手段并大大拓展了大众福利的存在空间。因此,“互联网+”时代的行政法律规制应以网络安全、网络诚信与网络创新为目的。“互联网+”时代的行政法律规制分为实体规制与程序规制,互联网法作为行政法的子部门应构建包括国家层面立法、行政法规、部门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独立、有序、协调、统一的互联网法律体系。行政法的程序规制包括行政程序应促进公权力与私权力协同治理,行政程序应促进政府监管职能的转变。
“互联网+”行政法律 公共利益 程序规制
党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拓展网络经济空间。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将“互联网+”界定为:“‘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这表明我国“互联网+”时代的正式到来,这必然导致传统市场经济模式发生深层次变革,互联网与经济发展关系更为紧密,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与创新要素。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比如:“人肉搜索”所带来的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知识产权人权益保障与社会公众获取知识权利之间的冲突,表达自由与网络谣言的冲突等。逐渐出现海量的商业交易和发展迅速的业态创新,各行各业均与互联网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一个“网络社会”,而“网络社会”是在“互联网+”时代新出现的崭新概念,由于互联网技术进步太快,因此远远走在管制、管理与规则前面,“互联网+”时代的行政法律规制成为一项时代新课题。
一、“互联网+”时代公共利益内涵与外延的拓展
作为行政法的原则,公共利益的界定是一个令人困扰且聚讼纷纷的问题,正如庞德所说,“公共利益是一匹非常难驾驭的马,你一旦跨上它就不知道它将把你带到哪儿。”[1]这里从主体、内容、功用三个角度简要梳理一下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公共利益的多元学说。在主体方面,公共利益的界定包括:全体社会成员、人民代表、不特定多数人、国家、政府;在内容方面,公共利益的界定包括:个人利益的集合、代表统治阶级的政府利益、整体利益、共同利益、综合利益、公共需求、经济利益、非商业性利益、在人类不自觉活动中实现的利益、行政政策目标、一种价值,公共利益的内容是公共利益内涵和外延的核心要素,具体可分为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非经济利益主要包括公民的人格利益 (人格尊严)。在功用方面,公共利益的界定包括:公共利益是限制私权的依据、具有法律和道德的正当性、有利于平等公民身份与民主价值的注入。据《CNNIC:2016年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下同),截止2016年6月,我国域名总数为3698万个、网站总数为454万个、网民规模达到7.10亿。互联网为市场经济提供了新的基础设施与创新要素,这必然导致经济形态的变革,网络空间独立于实体空间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活动领域,“互联网+”时代的行政法律规制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其根源首先在于“互联网+”时代公共利益内涵与外延的拓展,表现为公共利益主体、内容、功用的进一步扩展。
(一)公共利益的主体
《民法通则》第十一条规定了公民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最低年龄为十八周岁 (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传统公共利益的主体一般为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空间与实体空间相比对公民的年龄要求大为降低①截止2016年6月,10-19岁网民群体占20.1%,同时与2015年底相比,10岁以下儿童群体与40岁以上中高龄群体占比均有所增长,互联网继续向这两个年龄群体渗透。。“互联网+”时代公共利益主体年龄降低与公共利益的活动领域是截然不可分的,网络空间逐渐发展成为独立于实体空间市场经济的重要领域。伴随着互联网的广泛连接、融入,其实际上正在成为“信息时代的电力”,即成为支持其他形式的生产、参与和社会发展的必要媒介。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十八周岁以下的公民被排除于票决民主之外,然而“互联网+”时代所形成的独立的网络空间领域却是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的重要活动领域。“公共领域的核心力量在于,公民在交流的自主领域中能够自由参与理性辩论,远离国家、大媒体公司以及侵犯他们日常生活的社会不平等结构的控制和影响”[2],而民主并不以价值的一致为先决条件,民主是把相互冲突的价值联系起来,并把解决价值冲突放到公开参与公共领域那个过程提供一种方法。网络论坛、微信群、即时通讯有利于将民主价值注入公共利益之中,从而有利于恢复市场经济被经济利益所遮蔽的“非商品价值”与“集体保护”,这是参与民主、协商民主在网络空间重要的价值目的,基于此公共利益主体突破了传统市场经济民事行为能力对年龄的限制。
(二)公共利益的内容
传统公共利益的内容以经济利益为主,兼采其他非经济利益,“互联网+”时代在拓展经济利益广度和深度的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非经济利益内涵。“互联网+”时代拓展经济利益广度和深度的途径至少体现在两方面:(1)营销模式的改变。“互联网+”首先是商业概念,企业的营销战略定位、营销策略以及营销组合在 “互联网+”时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企业的营销战略定位逐渐由“线下”向“线上”扩展,传统企业的营销战略定位主要针对“线下”客户,2016年上半年,商务交易类应用保持平稳增长,网上购物、在线旅行预订用户规模分别增长8.3%和1.6%。“互联网+”时代促进企业深入挖掘“线上”用户需求,拓展多样化、差异化的服务类型,制定针对性产品同时满足“线上”、“线下”各种生活需要的营销战略。营销策略与营销战略定位紧密相连,具体包括产品策略、价格策略、渠道策略和促销策略,“互联网+”促进了产品本身的快捷化、匹配性,目前深入各行业的“团购”体现了价格策略、渠道策略、促销策略的结合①网络购物逐渐超越实体购物成为销售的主体方式,截止2016年6月,网络购物占购物总量的63.1%,比2015年12月提高3.1%,半年增长率达8.3%。。在“互联网+”时代,企业的营销组合不再局限于“线下”实体营销组合,而是实现了“线上”与“线下”的营销组合,传统的社会服务不断地推向“线上”,实现了社会服务的便捷化、智能化、个性化,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网络“私人定制”营销模式。(2)虚拟化、便捷化、概念化消费的形成。“互联网+”时代突破了传统产业+互联网的简单结合,促进了传统市场经济模式的创新,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实现了“以信息的互联为前提,以信息的获取、开发和利用为中心,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是消费领域和生产领域的有机联系与融合”[3]。虚拟化、便捷化、概念化消费具体表现为网络购物平台从购物消费模式向服务消费模式的转变,进一步提高消费模式的人性化;“电子货币”消费模式向各个行业、领域的渗透,大大挤压了现金消费的空间;文化消费逐渐占据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商品在“互联网+”时代获得极力扩张与拓展。作为公共利益内容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利益在 “互联网+”时代,随着传统市场模式的变革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公共利益的内容同样包括非经济利益,上文所涉及的非商业性利益、在人类不自觉活动中实现的利益、一种价值均可归入非经济利益的范畴。“互联网+”时代内涵于参与民主、协商民主之中的非经济利益主要表现为一种表达自由,“表达自由的价值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意义上的价值(自我实现的价值),即个人通过言论自由,发展自己的人格;二是有助于民主政治的社会意义上的价值(自我统治的价值),即通过言论活动,国民参与政治意思决定”[4]。在表达主体方面,随着网民年龄的低龄化,更多的年轻网民参与到信息化如此进步的现代社会,截止2016年 6月,10岁以下网民达 2059万,比2015年6月增长了0.2%。在表达内容方面,互联网信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在反腐倡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凸显了国民参与政治意思决定的作用;在表达渠道方面,“互联网+”时代为表达自由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基础设施与创新手段,一方面突破了演讲、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表达自由实现的渠道,另一方面扩大了传统表达自由渠道的社会影响,进一步丰富了表达自由的价值。
(三)公共利益的功用
“公共利益是公共行政的概念属性和功能属性,是公务人员执行职务的基础……公共利益是所有行政活动的理由和界限所在,也是行政机关追求的大众福祉与私人追求的与大众福祉有关的利益的区别所在”[5]。“互联网+”时代拓展了大众福利的存在空间,由原来的实体空间进一步向网络空间扩张,在网络空间以自由权为内涵的国民主观权利在隐私权获得保障的前提下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主观权利所具有的确保自由的意义,被认为应该为主观权利提供一种道德权威,这种道德权威既是独立于民主的立法过程的,又是无法在法律理论内部加以论证的”[6]。同时在“互联网+”时代公共利益不仅不是限制私权的依据,反而成为扩充私权的重要手段,以表达自由为中心的个人公共利益得到充分彰显,将释放出比实体空间更为广阔的话语空间以及更强的话语能量。而这与“互联网+”时代对个体国民隐私权的保护截然不可分离,“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一网络流行语体现了互联网时代对个体国民隐私权的维护。“隐私权被认为是值得保护的不可分割的个人权利,它应该独立于任何特定的实体经济环境,即使在保护财产权的市场经济中也是如此。 ”[7]
二、“互联网+”时代行政法律规制目的
“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维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必须完成的治理任务。”[8]在“互联网+”时代,行政主体应提高政府运用大数据能力,增强监管的有效性;提高政府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加强社会协同治理,实现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的有机结合。“规制以解决市场失灵、维持市场经济秩序为目的,基于规则对市场经济及相应经济活动加以干预和控制”[9],“互联网+”时代的行政法律规制目的具体包括网络安全、网络诚信与网络创新。
(一)网络安全
2016年11月7日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第一条明确了该法的立法目的,“为了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健康发展。”网络安全包括网络自身的安全以及网络背后涉及的国家权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个人合法权益的安全。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成为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基础设施与创新要素,因此针对互联网自身所实施的违法行为,其本身属于侵犯国家权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个人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如不构成犯罪,应由行政机关予以制裁,网络安全是行政法律规制的底线目标。
“互联网+”时代,网络安全所涉及的侵犯网络背后的社会公共利益同样属于行政法律规制的重要方面,主要涉及网络信息安全与文化安全。基于“互联网+”时代公共利益内涵和外延的进一步拓展,网络安全在“互联网+”时代涉及面将更为广阔与深入。在“互联网+”时代,行政主体在保护公共利益方面往往面临这样的二元悖论,即如何协调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实现监视、隐私与安全的动态平衡。市场经济主体可分为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 (少数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一般主体包括营销者与消费者,作为消费者当他们购买消费品、使用金融服务或者是申请社会福利时,往往会自动地提供个人信息,行政主体可据此建立信用档案,同时对于营销者应建立产品信息溯源制度与产品质量追溯体系,以保障以互联网为平台的交易安全,行政主体对于一般市场经济主体信息监控的目的在于更好地为其服务。“互联网+”时代为那些没有政治权力的人来跟踪和监督特殊主体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即存在多数人监控少数人的情形,托马斯·马西森称之为“聚合主义”。由于特殊主体对市场经济活动的推动与破坏作用要远远大于一般主体,行政主体应加大行政监管的力度,防止其利用互联网平台滑入网络犯罪的深渊。
(二)网络诚信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空间的虚拟生活方式打破了传统的实体性占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互联网成为经济活动的基础设施,所有人在网络空间均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具有物理尺度、年龄、身份、社会地位、经济能力或阶层的可识别性,而完全抽象为平等的人。人们在以互联网为交易平台时,可查询的仅为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的IP地址,被民法学学者称为帝王条款的诚实信用原则将受到互联网匿名性的巨大冲击。“互联网+”时代对诚实信用原则冲击的还包括互联网的虚拟性与无国界性,虚拟性一方面表现为对现实社会实际存在事物的仿真、模仿,比如对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另一方面表现为虽然符合现实世界的规律和惯例但客观事物尚不存在,而依据互联网进行数字化模拟与展现,比如各种网络游戏。这些虚拟现象产生的社会关系冲击着诚实信用原则。由于“互联网+”时代存在的网络空间,是一种迥异于实体空间的新型空间,对网络空间发挥功能的是社区边界而非国家边界,地域疆界不再成为互联网应用的重要障碍,互联网用户可利用互联网这一交易平台登录任何国家的网站。这必然对法律适用和争议管辖提出新的挑战,诚实信用原则遭遇主权限度。“互联网+”时代的行政法律规制应根据市场经济模式的变革作出相应调整,创新政府服务模式,确保实现网络诚信这一基础性目标。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行政主体建立市场主体准入前信用承诺制度;建设地方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部门和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推出机制;加强对市场主体相关信息的记录,形成信用档案。
(三)网络创新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创新不仅指互联网技术本身的创新,更重要的是指一种融合创新,互联网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创新要素。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从而成为经济发展的新支柱、新动力。“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成为重要的基础设施,互联网技术本身的发展将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运行平台。互联网推动传统产业的更新升级,全面实现“互联网+传统产业”,互联网在传统产业中除发挥基础设施的作用,更表现为在充分了解各传统产业的基础上,找到其薄弱环节,扬长避短,实现互联网与传统企业的深度融合。在实践中,与互联网首先结合的是第三产业,比如门户网站、淘宝、QQ等,并逐渐向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推进。在互联网与第二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可借鉴德国的“工业4.0战略”和美国的“工业互联网”①工业4.0与工业互联网的概念基本等同于“互联网+工业”,只是工业4.0与工业互联网更侧重于对制造流程及技术的创新变革,“互联网+”更注重对传统行业结构、行业规则的改革,剔除行业弊病,打破以往行业格局,用互联网概念对传统行业进行改革,建立新的行业秩序,包括制造、营销等环节,特别是服务品质的提高。。就目前而言,第一产业与互联网结合尚待进一步推进,促进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转变是第一产业与互联网融合的捷径。互联网还促进新兴产业的产生与发展,“互联网+”侧重于从线上到线下的过程,比较典型的是淘宝网为代表的网商以及网络直播服务②据《CNNIC:2016年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2016年6月,参与网络直播服务的用户达32476万,占网民使用率的45.8%。。
三、“互联网+”时代行政法律的实体规制
除《网络安全法》外,目前关于互联网的立法尚处于“+互联网”时代,其立法主旨为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各环节、各领域涉及互联网的,则制定相应的单行法律,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以下简称《电子签名法》),或者在其他部门法中纳入互联网法律规范,因此其整体立法体系必然存在支离破碎的窘境,包括监管法、促进法与保护法。为较好地适应、促进“互联网+”时代,行政法律的实体规制应制定以互联网为主体的统一而协调的行政法律规范,构建行政法独立的的子部门法——互联网法。
(一)国家层面的立法
目前被称为互联网行政法“基本法”即国家层面的法律的是 《网络安全法》与 《电子签名法》。这两部法律在一定意义上反应了 “互联网+”时代市场经济的变革的特征,尤其是2016年11月7日通过的《网络安全法》,广泛适用于我国境内建设、运营、维护、使用网络与网络安全监管,涉及网络安全的各方面,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法,但究其性质而言,《网络安全法》是一部目的单行法。2015年修订的《电子签名法》将“取得法人资格的企业”纳入“提供认证服务”的范畴,同时删除了“取得认证资格的电子认证服务者公布名称、许可证号”的强制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但《电子签名法》究其性质是一部行为单行法。据统计,国家层面还有21部涉及互联网的相关性立法,这使互联网法落入“行政法难以法典化”的怪圈。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法在法律体系中应归入哪一个法律部门,这是探讨其行政法实体规制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由于互联网与社会经济生活的高度融合,作为基础设施与创新要素的互联网应纳入“公共利益”的范畴,属于行政法的调整领域。同时根据《网络安全法》第二条,该条将网络安全监管独立出来,而监管的领域涉及网络的建设、运营、维护和使用,体现了全面监管的立法精神,这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相契合,因此互联网在法理上应属于行政法的子部门法。虽然行政法的法典化遭遇传统与现实的困境,但“行政法的部门化取得了优先地位,立法机关醉心于‘修缮’立法和措施性立法,听任立法分散发展”[10]。为避免立法的混乱与冲突,保证互联网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协调性,鉴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制定出两部单行法——《网络安全法》与《电子签名法》,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法》,作为网络法的真正基本法,以统领各层级立法主体的互联网立法活动。鉴于在世界范围内,尚没有国家或地区制定统一的网络法,我国所制定的网络法应侧重于原则性立法,其目的并不在于囊括所有的互联网现象,而在于统领与协调互联网法律体系。
(二)行政法规
“经济时代正在发生剧变,但整个监管体系以及监管的理念、思路却未必与时俱进。互联网具有极强的虚拟性、互动性、广域性和即时性,大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当前,‘互联网+’相关产业的发展,都面临着一定的法律风险,遇到了不少法律问题。”[11]就目前而言,对互联网进行专门规范的行政法规及具有行政法规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达51部,比如《电信条例》《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立法项目众多、类型繁杂而无序,即使如此,也难以穷尽“互联网+”领域的所有立法,比如个人信息保护、电子商务税收、虚拟财产等领域则存在立法空白。由于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与社会经济生活已难以割舍,因此有多少行政法实体规范就有可能存在多少部互联网行政法律。为摆脱互联网行政立法在行政法规层级“疲于奔命”的窘境,国务院应根据互联网行政目的的多元化来制定指导性、统领性的行政法规,比如网络安全、网络诚信、网络创新行政法规,将一系列互联网单行法律规范下放至国务院各部门、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目前《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即遵循此思路。但是,国务院于2016年5月13日发布的 《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则与此思路不甚符合,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体现在网络安全、网络诚信与网络创新的客观要求,其既是国家的发展战略也是“互联网+”时代的重要视阈,国务院应就此制定专门的行政法规,以法律规范替代政策指导。目前国务院制定的51部行政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因过于庞杂极易导致互联网立法“虚无化”的尴尬局面,必然导致立法权威的降低与减弱。国务院应以目的立法以及行政指导立法为主,难以穷尽的单行立法应放还给国务院各部门、设区的市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同时通过确立行业自治规则,能够综合运用更多的技术手段,直接实现治理目的[12]。
(三)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
截止2016年6月,与互联网相关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达800多部,司法解释及司法性文件40多部,行业自治规范达50多部。当前涉及互联网的规定错综复杂,且大多分散在其他法律法规中,这种情况已经难以满足统一、有效“互联网+”时代的立法需求,因此作为行政法的子部门必须建立互联网领域独立的法律体系,整合相关的规则和解决方案才能适应当前瞬息万变的新情况、新问题。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 《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对互联网法规建设确立了重点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表,要求建立系统的互联网信用制度、完善互联网服务制度、加强互联网监管制度,并就相关制度设立了时间表。这是政府在推动“互联网+”行动计划中的重要举措,但是作为“互联网+”时代法规建设的重点,部门规章并不具有完全的司法效力。这要求部门规章与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相协调,包括地方规章、司法解释、行业自治规范等。同时应充分发挥我国“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政体模式的宪制功能,实现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宪制模式在“互联网+”时代立法、司法、执法协调配合,目的在于构建独立、有序、协调、统一的互联网法律体系。
四、“互联网+”时代行政法律的程序规制
“行政程序法典的核心或所解决的实质问题是处理公共行政与社会公众的关系问题”[13]。伴随着“互联网+”时代公共利益内涵与外延的进一步拓展,公共行政与社会公众的关系已经由原来的市场经济实体空间向实体空间与网络空间同步推进,因此应加强行政法的程序规制。
(一)行政程序应促进公权力与私权力①公权力主要指公部门为维护公共利益行使的权力,私权力则指私部门为维护公共利益行使的权力,如论坛坛主、网络管理员、淘宝“宝主”为维护网络空间的公共利益所行使的权力。协同治理
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网络空间与实体空间相比具有自己独特的规律性,互联网所具有的多变性、匿名性、虚拟性增加了传统行政权对网络空间实体介入的难度,与实体空间相比,虚拟空间更加依赖于市场主体的行业、论坛的自律,包括论坛坛主、网络管理员、淘宝“宝主”等网络空间主体的自我规制与约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行政主体在“互联网+”时代完全失去的管控的可能性,只是应加强公权力与私权力协同治理。由于传统的行政程序主要规制公权力,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必然存在公权力与私权力的协同治理,行政程序进行变革是时代的要求,也符合广大网民的利益诉求。在 “互联网+”时代,行政程序设置目的不应仅仅是价值与利益结合的交易关系,更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基于相互认同的合作目标;在“互联网+”时代,随着公共利益内涵与外延的扩展,公益与私益的联系更为紧密,例如不同的网站、论坛、QQ群、微信群,各自相对而言是私益,但在各自网络空间中又涉及到公益,因此行政程序应促进公益与私益之间有效的平衡;伴随着公益与私益的融合,行政程序的变革必须吸纳更多的契约形式与精神,告知程序、听证程序等行政协商程序的适用比重应进一步加大,并增设更多的行政协商程序以应对私权力对传统公权力的挑战。“通过制定相应的行政协商程序,变通地规范公私权合力中履行公共职能的私权力部门,不仅可以为公私权合力产生的争议确立司法审查原则,也可以将承担行政管理职能的私权力部门置于行政程序的监督之下,有利于保护网民的合法权益,使公私权合力的救济机制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14]。
(二)行政程序应促进政府监管职能的转变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行政主体建立市场主体准入前信用承诺制度;建设地方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部门和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加强对市场主体相关信息的记录,形成信用档案。这表明在“互联网+”时代,政府的职能已由行为监管向体系监管转变。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应为网络安全、网络诚信以及网络创新提供良好的网络环境,因此政府的监管职能应突破行为监管的传统模式,转向网络体系安全的整体性、系统性、防范性监管。行政程序在促进政府监管职能方面应实现从刚性程序向柔性程序的转变,促进政府的监管职能由填补性到建构性升级,传统的政府监管模式往往是一种填补式的监管模式,制止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行政不法行为,行政程序在制约政府权力的过程中彰显一种刚性特征,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技术日新月异,市场经济的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不断出现,政府职能应由填补式监管模式向建构性监管模式转变,在建构性监管模式的形成过程中,行政程序应向指导、协商、建议等柔性方向发展;促进政府监管职能由国家性向民间性的位移,“互联网+”时代已实现互联网与各行业、各领域、各阶段实现了深度融合,传统硬法难以在“互联网+”时代面前随机应变,为促进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监管职能不得不依赖于于网络自治、自律规范,实现硬法与软法的合作与创新,柔性行政程序无疑有利于推动政府监管职能由国家向民间性的位移;行政程序促进政府监管职能由经验性向创新性的转变,客观行政法强调行政法的系统化、总体法律制度以及公共行政的法律形式,主观行政法则重视行政法的法律主体、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以及行政法的权力义务,尤其强调行政相对人的主观公权利①指臣民相对于国家的地位,国民据此有权通过法律行为或者根据为保护其个人利益而制定的、可以针对行政机关适用的法律规范向国家提出要求或者针对国家实施一定的行为。,主观行政法有利于促进行政法的创新,在“互联网+”时代行政程序应积极促进主观行政法在网络空间的创新性;行政程序应促进政府监管职能由强制性向协商性转变,“‘互联网+’新业态中的民间交易规则、自律规范和交易习惯的迅速崛起,则是更多地体现了互联网的开放、平等和分享精神”[15],因此为促进政府监管由行为监管向体系监管的转变,行政程序应强化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平等协商。总之,行政程序由刚性向柔性的转变,有利于促进政府监管职能由行为监管向体系监管的转变。
[1](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三卷),邓正来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205~206页
[2][7](英)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任孟山译,华夏出版社,2010 年,第 89、364 页
[3]梁志文:《“互联网+”经济法治的基本理念与进路》,《江海学刊》2016 年第 3 期,第 141~146 页
[4](日)芦部信喜:《宪法》,林来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3页
[5][10](德)汉斯·J.沃尔夫 奥托·巴霍夫 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323、5 页
[6](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11页
[8]黄璜:《物联网+、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电子政务》2015年第7期,第54~65页
[9]马英娟:《政府监管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页
[11]吴志攀:《“互联网+”的兴起与法律的滞后性》,《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 3期,第39~43 页
[12]蔡文之:《自律与法治的结合和统一》,《社会科学》2014年第 1期,第 72~78页
[13]关保英:《论行政合作治理中公共利益的维护》,《政治与法律》2016 年第 8 期,第 2~13 页
[14]谢鹏远 周敏:《公私合力背景下行政程序的变革与走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5年第4期,第 70~77页
[15]马长山:《互联网+时代“软法之治”的问题与对策》,《现代法学》2016 年第 5 期,第 49~56 页
(责任编辑:王立坦)
Aderminstrative-law Regulation of the “Internet Plus” Era
Yan Xinlong
The coming of the “Internet plus” era is certain to cause the deep evolution of the traditional marketeconomics mode,the deep amalgamation of the internet-technolegy and market-technolegy.In this context,as the administrative-law principle,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public-interest expand furtherly;the age of the public-interest body reduce largely;as the content,the economic-interest and non-economic benefits expand furtherly;as the means to expand the private right expand the existing-room of the public-welfare.As that,the adminstrative-law regulation of the “internet plus” should consder the internet-safety、internet-sincerity and internetinnovation.The aderminstrative-regulation can divide the entity-regulation and the procedual-regulation.As the subsidiary department,The internet-law should constitute the independent、ordered、coodinate、unified law-system of internet,constituting the legislat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department regulations and other normative document.The procedural-regulation contained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shoul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governance of public power and private power,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shoul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regulatory functions.
“Internet Plus”,adminstrative-law,public interest,procedural regulation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江苏泰州 225300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互联网+’社会的行政法律治理”(批准号:2017SJB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