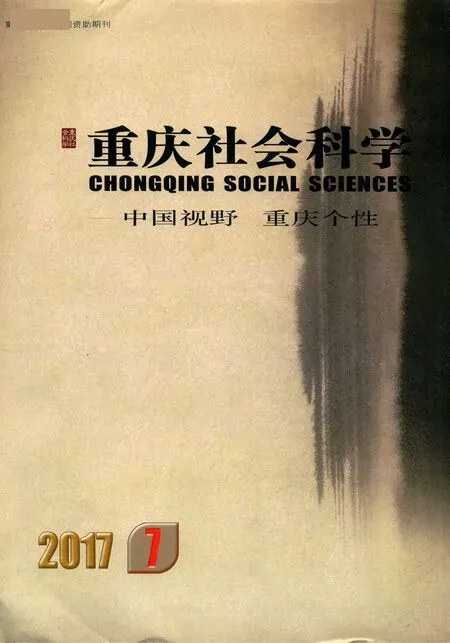西方个人财产权观念的变迁
龙 江
西方个人财产权观念的变迁
龙 江
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资本主义法律的核心原则之一,也构成了资本主义法制体系的基石。随着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其个人财产权观念也经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这里阐释了近代前后西方个人财产观念,分析了近代个人财产的地位:正当化和神圣化。旨在借鉴西方私产观念理论,为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一定的政策性思考。
西方 个人财产权观念 变迁
资本主义法律强调个人财产不可侵犯,个人财产不可侵犯奠定了资本主义法制体系的基石。20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纷纷增加了对个人财产的限制性规定,但是对个人财产的严格保护仍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制的根本特点之一。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建国伊始,就在其法律体系中确立了个人财产至上乃至神圣的地位,这是西方社会对于个人财产的认识和思想观念的影响使然。西方人相应的认识和思想观念的形成,是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使然,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一、近代之前西方人的私产观念
西方个人财产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方文明的摇篮时期,即古希腊,到了罗马时期,实际上个人财产观念已经十分发达,这充分体现在罗马法中。但是,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历史进入到中世纪,在神学对精神世界一统天下的局面之下,个人财产观念受到了抑制,直到在欧洲商品经济重新兴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出现,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个人财产观念才再次得到伸张。
(一)古希腊
在古希腊时期,虽然私有制和个人财产早已是客观存在,但是对于个人财产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希腊人却尚未形成共识。柏拉图就是贬低甚至否定个人制和私有财产的最著名的代表。他认为,一个人有自私和贪婪之心是和他拥有的个人财产和家庭分不开的,追求财产会导致个人的野心和堕落,暴力和纷争,拥有的金钱越多,美德就会减少,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理想国的哲学家和战士不应有家庭,也不应有个人财产,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民阶层除外。[1]柏拉图晚年或许意识到了个人财产不可避免,但仍主张将其限制在一定的程度下,比如不准超过最低财产标准的五倍。[2]柏拉图对个人财产的轻视在思想家们更关注道德正义的古希腊并非偶然,认为物质财富自身不能独立存在,物质财富是为知识德行、健康而存在,他进一步阐释了苏格拉底的财富可用性观点;亚里士多德则对个人财产的态度较理性,他认为个人财产不能消灭,并且具有积极意义:个人财产比公有更有效率,因为公有财产更少受到人们的关心。[3]希腊人这种对个人财产的不同认识也可以找到实证的依据。在雅典民主的奠基者梭伦的改革中,他将公民按照财产的多寡分成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这个事实证明了个人财产不仅得到法律的保护,[4]更证明了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可以说这是个人财权具有宪政意义的最早的证明。但是,在梭伦的改革中也颁布了“解负令”,将作为债务抵押品的土地归还原主并恢复债务奴隶的自由,又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其对私有财产保护的不力。
在古希腊,思想家们不仅对于财产应否私有这个具体问题有争议,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而且在更宏观的层面来看,希腊时代的思想文化中普遍缺乏对于个人主义的论述,最杰出的思想家都是关心城邦利益胜过关注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者。即便是反对柏拉图共产主张的亚里士多德,其关于正义、公平、善德等问题的论述,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一样,仍然是以城邦的集体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属的,而那个时代最具有个人主义色彩的思想家普罗泰哥拉同样也缺乏对个人利益论证。可以说在这种个人主义缺乏的思想文化背景之下,个人财产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是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论证的,更谈不上对个人财权保护的具体制度设计,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在古希腊为什么私法并不如其法律思想甚至公法发达。
(二)古罗马
如前所述,在罗马时期,个人财产观念的发达程度与古希腊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达到了古代社会的最高峰,这个观点仅仅从罗马法发达的事实上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很简单,罗马法的主体是私法,而私法即以保护个人权利为目的,而个人权利的内容在那个时代当然包括个人财产。罗马人已然将个人财产作为个人权利的当然客体,换句话说,罗马人已经超越了希腊人对财产应否私有的论证,罗马人发达的私有财产观,其与罗马人发展出的个人权利观念密不可分,[5]而罗马人的个人权利观念又源自其对希腊人提出的正义的创造性理解。
在希腊罗马时代,法律思想中一个核心话题就是正义论,包括什么是正义、法律与正义有无关系,是何种关系等基本问题。通过希腊思想家的努力,对于正义的内涵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认识,而且对于法律与正义的关系也形成了法律是正义的体现,或者说法律以实现正义为目的的共识。到了罗马时代,罗马人面临的使命在于,用法律来实现正义。乌尔比安就在这种情况下对正义进行界定:“正义就是给让每个人的权利得到永恒的意志”,[6]这个概念中,乌尔比安将正义落实为个人的权利,作为正义的体现,法律自然以维护个人权利为目的。“法律保护权利和确定权利,权利是法律所维护的利益。”[7]正是乌尔比安解决了这个前提性的问题,才使得以维护权利为目标的罗马私法的蓬勃发展具有了理论基础,而其中罗马人的个人财产观念甚至个人财产权观念的发达就是不证自明的了。当然,罗马人的个人财产权观念再发达,也绝不能够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个人财产权观念相提并论,比如,奴隶被视为财产、家父制度等就注定了那个时代的个人财产观念的局限性。
(三)中世纪
中世纪西方人的个人财产观念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可以以11世纪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中世纪前期,基督教完全垄断了知识文化,主宰了欧洲人的精神世界。在信仰高于理性的背景下,人们沦为了上帝的奴仆,不但失去了追求世俗幸福的权利,也丧失了作为人所具有的思考能力。早期的基督教发源于底层的穷苦人们,对财富阶层采取敌视的态度,其基本教义对于物质财富也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甚至提倡禁欲主义,要求放弃对尘世幸福的追求。所以在主流文化中,个人财产的地位不值一提。由于基督教的发展,教会的物质财富不断增加,实际上已经达到富可敌国的程度,于是保障财产的主张开始出现,但只是就教会财产而言,对于普通教徒的个人财产,神学仍然缺乏正当性的论证。非但如此,教会征收的什一税和要求教徒捐赠财产更是对个人财产的一种剥夺。再加上中世纪前期欧洲经济生产方式主要为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人们缺乏商品经济条件下对个人财产保护的那种强烈需要,在这个时期,西方人是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财产观念的。
到了11世纪的时候,在意大利、英国和荷兰等航运条件较好的地方,贸易重新发展起来,并带动了商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开始在欧洲出现,再加上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传播,人们心中对于世俗幸福的愿望被激活,那种否定物质享受的和财富价值的传统基督教官方意识形态受到了怀疑,人们开始发出了关于个人财产的合理性和保护个人财产的呼声。这种呼声得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回应,作为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承认了私有财产对于人们生活的必要性:第一,相对其他事务,所有人只对自己占有的东西更加关注;第二,人类的事务要有秩序,是由于每个人都管理好自己的事情;第三,纠纷会发生,是因为人们共同拥有某物。对物不能拥有独自的所有权,于是相互之间不能友好相处。[8]作为基督教的官方哲学家,其以现实的态度对待个人财产,承认个人财产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那个时代在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之下,人们个人财产观念复苏并发展的有力证明。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场旨在将人从神的脚边解放出来的文艺复兴运动从14世纪席卷了西方世界和西方人的精神空间。人们重新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和自己的幸福。关于个人财产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论证也成为了文艺复兴时代思想家们考虑的问题。马基雅维利和布丹的思想代表了被唤醒的人们对于个人财产的认识。马基雅维利认为,每个人的人性都是自私的,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人民的个人财产,统治者要想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去碰人们的个人财产;而布丹则论述了人民的世俗幸福的重要意义,并提出国家的目的就在于保障人们的物质幸福,从逻辑上讲,对于个人财产的必要性的认识自在其中。[9]到中世纪晚期,西方人重新认识到了个人财产保护的重要意义。不过就欧洲大陆而言,人们的认识仍然与现代相隔遥远,因为无论是马基雅维利还是布丹,都没有像随后那个时期的思想家那样将提升个人财产的地位,更遑论基督教的经院哲学家了。即便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尽管其提出了保护个人财产的主张,但是却是以巩固君主的统治为着眼点。
二、近代个人财产的正当化和神圣化
总的来看,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西方个人财产权和财产权观念高速发展时期。在这个阶段,个人财产在西方人的思想观念里,地位不断上升,个人财产权被推举到天赋人权的高度,再到后来,个人财产权被赋予物质利益之外的更多的意蕴,直至在观念上被神圣化。同时在政治和法律实践中,个人财产也受到了越来越严格保护。个人财产在这个时期地位的上升,是与古典自然法思想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多位自然法学家对个人财产的正当性、神圣性和宪政意蕴进行了接力赛式的论述,构成了个人财产的地位在近代史上的逐步上升的图景。
(一)正当性
在近代最早对个人财产的正当性进行论述的思想家当属格劳修斯、普芬道夫和霍布斯。作为古典自然法的早期代表,格劳修斯是从自然法的高度来论证个人财产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的。他认为,由人类的行为产生的东西和自然本身产生的东西,都受到自然法的尊重,例如,“财产”是客观存在的根据个人意志而产生的东西,违反个人的意志而拿走他人的东西就是违法的,违背了自然法。[10]在格劳修斯列举的自然法的原则中,至少有四条就与个人财产的保护直接相关:第一,不得触犯他人的财产。第二,把所有权属于他人的东西及其获得的收益归还他人。第三,由于自己的过错对他人的财产造成损失,应当赔偿。第四,应当履行契约,遵守诺言,承担义务和责任。[11]格劳修斯恢复了自然法至上地位、强调自然法相对于上帝的独立性,他从自然法的高度来论证保护个人财产的重要性,无疑为个人财产的正当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论证。另一位古典自然法学的早期代表霍布斯虽然对个人财产关注较少,但是他对人性自利进行了那个时代最为理性和客观的论证,间接地为个人财产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提供了理论支持,并且在其自然状态说中,也承认了个人财产权的自然权利属性。此外,思想家们也从道德的角度为个人财产的正当性进行了证明,比如霍布斯断言,没有财产权就没有正义,财产权乃正义的源泉。休谟认为“分立的财产得到承认,标志着文明的开始,规范产权的规则是一切道德的关键之所在”。[12]孟德斯鸠则说“所有权是道德神、私有财产是道德之魂”。[13]
(二)绝对化
近代思想家对个人财产地位的最大幅度的提升是在天赋人权理论出现之后的事情。处于同一时代的斯宾诺莎和洛克不约而同地阐述了天赋人权或曰自然权利的理论,但明确将私有财产权纳入天赋人权的范畴并给予其正当性的最有力论证和其神圣性的初步论证的是英国的洛克。洛克断定,在自然状态之下,每个人都享有与生俱有的、不可剥夺的普遍的天赋权利: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洛克对于财产权给予了特别的论证,洛克认为上帝将世界给予人类,就是让人类为了生活的需要而对世界加以利用,因而人们对于土地及其产出物的支配是一种天然的权利。在后来人们通过契约而结成共同体的过程中,从未被转让出去的是包括财产权在内的天赋权利。除了这个超验的角度,洛克也从经验的角度论证了个人财产的正当性和不可剥夺,他认为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享有所有权,而其身体所从事的劳动的产物当然也属于本人。经过上述的论证,可以说在洛克这里私有财产权的正当性已经无可争议。实际上洛克对私有财产权的认识还不止于此。在三种天赋人权之中,他甚至认为财产权具有重要和基础地位,生命权和自由权是财产权的延伸。由此他认为政府的核心目的是对公民财产的保护。[14]一个政府,如果侵犯公民财产权,不保护公民私有财产,这样的政府不能称其为政府。于是我们就看到洛克在西方历史上首次赋予了财产权以至上的地位,并与个人的自由、政府的目的联系起来。个人财产权的正当性得以完全确立,神圣意蕴得以初步阐述。洛克的思想后来为布莱克斯通和黑格尔所发展,而在实践上则影响了美国和法国的政治建设。
与洛克大致同时期的英国思想家哈林顿虽然对大资产阶级无限的财产占有欲望进行了谴责,并设计了一个以控制财产所有权为基础的共和国方案,体现了与这个时期个人财产权观念发展趋势不一致的观点,但是他看到了财产与政权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政权以财产为基础,政府的形式和国家的性质受财产的影响,从侧面论证了个人财产权对于政治的重要意义。
继洛克之后对个人财产权的崇高地位进行论证的主要思想家是法国的孟德斯鸠。孟氏在其对民法的相关论述中强调了个人财产与政治国家、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对等关系。孟德斯鸠认为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保护私有财产是民法的根本任务。“同样他们(人类)放弃了他们天然的财产的公有而生活在民法之下……民法使人类获得财产”,[15]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借口公共利益的重要而侵犯公民个人的利益,公共利益绝不是用政治性的法律去剥夺个人的财产,就是说,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公家需要与个人财产之间存在对立的时候,需要进行协商,在平等的原则上进行交换或者赔偿,故而孟氏说“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睛里,每个人就是整个国家”。相比于洛克,孟德斯鸠对个人财产的正当性的论证可能从高度上有所欠缺,但是却从务实的层面提出了保护个人财产权的基本原则,其对于私有财产权的崇高地位的论证效果和对西方人观念的影响,并不输于前者。
(三)神圣性
经过前述几位思想家的论证,个人财产在西方人的思想观念中,必要性、重要性和正当性已经不再是问题,并逐步绝对化,而且由于与自然法、上帝联系起来,其神圣性的色彩已经非常明显。但是西方人并没有就此停住,他们将个人财产权与自由、民主以及限制政府权力联系起来,发掘出了个人财产权的政治意蕴,这样便为个人财产权找到了世俗的神圣性来源,因为宪政在当时不仅仅是一个世俗的政治目标,而且本身成为了一种信仰,具有神圣地位。如前所述,实际上在洛克思想中,他已经指出了个人财产权对于自由和生存权来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但是他没有能够深入下去,这个工作则是由德国和美国的思想家来完成的。
19世纪的思想家认为人格尊严和个人意志可以通过财产权来表现,通过对他人财产的尊重来体现对人格的尊重。康德认为主观的占有行为引起了原始的财产权的出现,原始的财产权是人格的延伸。黑格尔认为,对个人的自由而言,财产权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次在财产中,纯粹主观的内在的个人意志变成了 “实在意志”,通过将他的意志在物中表现出来,使之成为它的财产,通过他的财产,个人就与他人联系在一起,超越了自我……财产权是自由的原因,是由于它提供个人行动的范畴,并且使他的人格进一步延伸和扩展。[16]简言之,黑格尔提出“财产是自由最初的定在,它本身是本质的目的”[17],财产权成为个人自由的外部表现。要成为一个法律意义上的人,需要拥有财产和财产权,拥有健全的人格,这样才会被社会所尊重和接受。在他看来,人只是在对财产的绝对占有和支配中才具有人格和价值。“惟有人格才能赋予对物的权利,所有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物权就是人格本身的权利。”[18]因此,侵犯私有制权就是侵犯了人格和自由,就是“不法和犯罪”。
如果作个简要的归纳,可以发现这个时期思想家们关于个人财产的政治意义的见解,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人财产权是个人政治权利的奠基石;第二,个人财产权限制了政府权力;第三,个人财产权是民主的体现,也是法治的标尺。总之,通过思想家们的论证,在文艺复兴以来到19世纪末期以前,个人财产和个人财产权经历了正当化、绝对化和神圣化的过程,正当性日益增加,神圣色彩日渐浓厚,最终取得了有史以来最高的社会地位和名誉,这不仅得到理论上的普遍认可,而且也得到了《人权宣言》、美国宪法修正案和法国1799等宪法和法律文献的确认。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护个人财产是政府的主要目标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法制的基本精神。
三、19世纪后西方个人财产权观念的新发展
经过文艺复兴以来两百多年的论证之后,在思想观念领域,个人财产的正当性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个人财产权的地位也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法律的确认。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近百年的时间里,西方的个人财产权观念处于应用阶段,总体上没有发生大的理论更新,直到世纪之交。20世纪以来,西方个人财产权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的推动下又有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来源于近代个人财产权观念的固有缺陷。
这个固有缺陷就是前文提到的个人财产权的绝对化,这充分反映在布莱克斯通的个人财产权理论之中:保护私人权利比保护公共利益更重要。体现了他对个人财产权的极端维护。而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中也包含着同样的因素。布莱克斯通和孟德斯鸠两人的主张具有相似性,有其现实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而且在19世纪前期,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积极性,客观上需要建立绝对化的私产保护理念与制度。而自由竞争和私产保护绝对化的负面效果在资本主义政权的成长阶段还没有体现出来,因而与绝对的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和个人利益至上相联系,个人财产权的绝对观念与实践既是合理可行的,也是必要的。随着19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推动,自由竞争和个人主义的负面效果开始显现。形式上的公平和自由竞争为实质上的不平等和垄断所代替,经济危机频发,贫富分化严重、阶级对立加剧,社会运动此起彼伏,西方世界孕育着深刻的危机,而固守守夜人角色的政府却对此无能为力。在这种条件下,受到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一部分思想家开始注意到现实中广泛存在的分配不公,他们抨击不择手段追求财富的社会现象,对传统的个人财产权观念进行了反思,重新考虑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对私有财产的神圣色彩进行淡化,主张行使个人财产权需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形成新的个人财产观:财产权社会化。
英国思想家霍布豪斯认为:财富有社会基础和个人基础。[19]而财产的社会基础的意义在于:一是社会因素体现在财产价值中,如财产所有者利益要得到保护是通过组织社会力量来保护;二是社会因素影响着财产来源的生产过程。他举例论证,“伦敦一块地皮的价值主要应归于伦敦而不归功于地主。说得准确点,价值一部分归于伦敦,一部分归于英帝国,再有一部分归功于西方文明。”[20]因而,传统的排斥了社会公益的绝对财产权观念亟待修正。H.D.劳埃德超越了传统的原子化个人主义,他认为世界是社会性的,由朋友、同事、邻居、母亲、儿子、父亲等社会关系组成,作为个人不是孤独存在的。如果每个人考虑自己的利益将促使社会走向毁灭。美国总统老罗斯福说:“在财产和人类福利的关系上人们有新的看法……有人认为利润没有人权重要,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每个人拥有的财产使用到什么程度按公共福利的需要来规定,都要服从社会的安排。”1912年,罗斯福更明确地谈到:“如果富人遵从社会普遍权利,按照公共福利要求的那样,将其财产用于生意经营。富人的权利会获得国家的保护,国家主张财产权,但更主张人权。”[21]德国法学家耶林认为所有权应当社会化,他认为行使所有权的目的,不仅考虑个人的利益,也有社会的利益。其后基尔克继承并发扬了他的这一思想,他在《德意志私法论》中指出:所有人根据各个财产的性质与目的,依照法律程序来行使自己的权利,所有权绝不是完全不受限制的与外界对立的绝对性权利。[22]此外,在法律思想领域,一些新的流派如连带主义法学派、社会法学派也提出了各种不同于传统的私有财产权理论。
个人财产权观念的这种新发展也当然地体现在法律条文之中。1919年魏玛宪法第一次规定了公共利益对私有财产权进行限制的法条。如财产权受宪法保护,财产权受法律约束。行使财产权要有助于公共福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宪法较多地限制个人财产或对个人财产课以更多的义务,对公共利益限制私有财产权的原则进一步扩充。如日本宪法第29条规定,为了满足公共福利的需要,应由法律规定财产权的内容。实际上,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罗斯福新政以来,政府的角色发生了转变,由传统的私有财产的保护者转变为社会财产的控制者,私有财产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民法、经济法的限制。
总之,20世纪以来,社会性因素被纳入西方人的个人财产权观念中,公共利益对传统的个人财产权绝对、神圣的地位进行挑战,这个趋势至今未变,以至于有人认为如果说在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财产还代表着权力,那么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财产在法律上却代表着责任。如对财产所有者的种种限制反映在各种立法中。在美国财产法中增加了生态限制的内容。而且在美国,“新财产权”观念取代了传统的财产权观念。所谓“新财产”泛指那些来源于国家政策的各种利益,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福利权是公民权利得以保证的基础。当然,福利国家削弱私有财产权,也正遭到新保守主义思潮的责难,指其挫伤投资积极性,降低了工作意愿等。
需要说明的是,西方个人财产观念出现的这种新的变化,绝不是对传统的私有财产权观念的否定,而是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原因很简单,现代西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力度与其近代的差距,远远小于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
四、结语
西方个人财产权观念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私产的地位也不断上升。私有财产权保护有助于社会经济、政治和人权保护的发展,这个客观规律被无数人探索并证明。我们要认识私产保护的重要意义,根据现实需要,借鉴近代西方的私产观念和理论成果,为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政策依据和理论支持。
[1](美)理查德·派普斯:《财产权》,蒋琳琦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页
[2][3]颜一编:《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49、57~63页
[4][5]崔兰琴洪森:《西方近代权利观发展综述》,《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6期,第 39、38~39 页
[6][7](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页
[8](爱)凯利:《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王笑红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143页
[9](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 83~84页
[10][11][12][13]西方法律思想史编写组编:《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年,第 138、147、147、147 页
[14](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7页
[15](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90页
[16][17][18](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50、50、46 页
[19][20](英)霍布豪斯:《形而上学的国家论》,汪淑钧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9页
[21]刘军:《西方财产观念的发展》,《文史哲》2007年第6期,第76页
[22]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 246~250页
(责任编辑:王立坦)
The Changes of the Concept of Individ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West
Long Jiang
The concept that the individual property is inviolable is one of the core principles of capitalist law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capitalist legal system.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s,economy and culture in the West,the concept of individual property rights has also undergone a changing process.Through expounding the concept of individual property in the West before and after modern times and analyzing the status of individual property in modern times-justification and sanctification,this paper is aimed to bring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our countr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concept of individual property in the West.
the West,the concept of individual property rights,changes
重庆工商大学法学院 重庆 40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