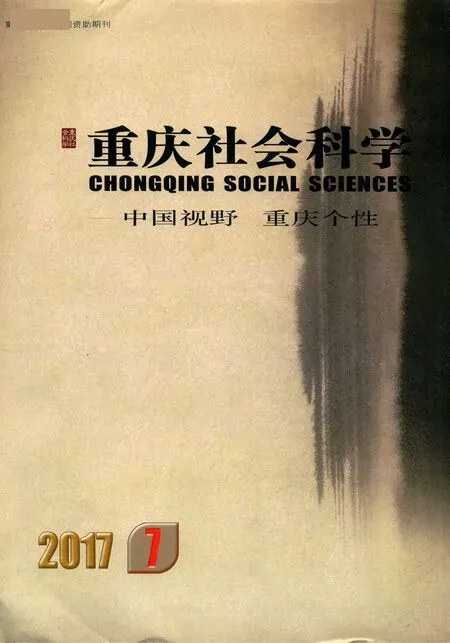社会系统理论视角的农村社区管理*
陈 强 林杭锋
社会系统理论视角的农村社区管理*
陈 强 林杭锋
加强农村社区管理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管理的重要课题。文章回顾了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及其特征,并对农村社区管理进行了再思考。从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农村社区显然是客观的,在封闭的同时又具有开放性;在强调自主性的同时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在推进农村社区管理过程中,必须将农村社区当作一个客观存在的系统并予重视,在推动农村社区系统内部管理主体和管理机制的自我成长,也要为农村社区管理建立具有张力的、良好的外部环境,并通过有效的引导,实现系统内外要素的充分互动,从而实现农村社区的“善治”。
卢曼 社会系统 农村社区管理完善
农村社区既是社会的有机构成,也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丁元竹认为 “社区应该是指可以满足居住和生活在其中的居民的基本需要的居住区。”[1]费孝通先生把农村社区描述成一种“礼治秩序,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及熟人社会;无为政治,基层社会结构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2]詹成付等人认为,“农村社区是农村基层管理与服务的基本单元,是聚居在城镇以外的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具有一定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口群体和社会组织,是农民长期居住、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区域共同体。”①陈圣龙:《农村社区组织管理体制研究——基于对60个 “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示范单位”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刘长明认为,农村社区“指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主的,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以农民为居住主体的,具有文化的同根性,习俗的相近性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①刘长民:《山东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研究——基于对德州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考察》,中国海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可见,关于农村社区的定义尚未形成一致,但人们都认同其就是一种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自然规律而形成的,包含了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生产、生活设施,有一定的成员认同感,是一个融合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多种功能在内的社会系统。一般来说,作为社会的构成,农村社区通过自身的生产与活动以及与其他系统的交换,来维持自身的发展,并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变迁,因此,有必要加强农村社区的管理。
农村社区管理实际上就是社区管理的一种形态。而何为社区管理,目前学界并没有形成共识。王金荣(2012)把我国社区管理的概念分为四种类型:从历史的角度来讲,社区管理是不断演变的;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讲,社区管理就是为了实现特定的公益性的目的而对社区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的过程;从管理的目的来讲,社区管理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这一目标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公共性;从管理的角度来讲,社区管理依托社区中的各类主体广泛参与,它要求不同的主体在这一过程中“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张兴杰把社区管理定义为“在社区范围内,由社区内的基层政权组织、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群众为维护社区整体利益、推进社区全方位发展而对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的自我管理。”[3]汪大海等人则认为,社区管理是“指在政府的指导下,社区职能部门、社区单位、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的自我管理。”[4]在实践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农民的需求模式、需求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党和政府通过完善村民自治、村务公开等诸多措施完善农村社区的管理,并最终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主导,民间组织,政府、社区互助,政府、社区、社会互助等五种类型得农村社区管理体制[5]。然而,城镇化的持续推进、经济社会转型的加速,最终引发了农村社会内部结构的变迁,这又进一步导致了现有农村社区结构与传统社区管理体制之间的摩擦,使得农村社区管理面临严峻的挑战。于是进一步推进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理解和认识农村社区?又如何重构农村社区管理机制?这显然亟待我们探讨。我们以为,作为观察和理解现代性的一种理论,卢曼②卢曼,也译为鲁曼,全名为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是德国社会理论学家,也是当代社会系统理论的创始人。的社会系统理论显然给我们解答这些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话语和视角,这也是本文的要旨所在。
一、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及其核心要点
在构建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卢曼重新修正了社会现象的观察方法,并建立了“系统自身的观察理论”,即“二阶观察”理论,对社会诸功能系统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观察与探索。1971年,《社会的理论或社会技术——系统研究提供了什么?》文集出版,该书记录了卢曼与哈贝马斯关于社会理论或技术等方面的争论,也对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1984年,奠定了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的基础《社会诸系统》的问世,标志着社会系统理论的形成,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回顾
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体系十分庞大,在社会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全方位分析基础上的产物,对于认识、解读现代社会及推动现代社会的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许多学者对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及其实践应用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一些学者如丁东红、肖文明、高宣扬都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肖文明认为,“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为我们观察和理解现代性提供了一套全新的理论话语和视角。”[6]高宣扬则认为,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运用独特的视角,揭示了社会的复杂分化情况。而从实践应用上看,吴泽勇(2004)、翟小波(2007)、泮伟江(2014)等人利用该理论对法律方面的议题进行了研究,葛星(2012)利用该理论对媒体、媒介进行研究,刘力钢 (2004)利用该理论对企业管理,杨丽茹(2009)和吴立保(2010)分别利用该理论对教育、大学生工作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既有文献几乎没有运用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对社区治理的问题,从这一理论研究农村社区管理问题的成果更是几近空白。实际上,作为一种社会构成,农村社区具有典型的系统的特征,在对农村社区进行管理的改革与创新的过程中,显然需要我们在全局的角度对其进行思考。因此,利用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研究我国农村社区管理问题,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
(二)社会系统理论的主要观点
1.社会系统是客观存在的
理论与经验都证明,社会系统是客观存在的。这种“系统”,不仅是社会学上的一个分析概念,也是一种现实经验的存在。按照卢曼的说法,人类的生活与活动,导致了系统的出现,“一方面正是人类社会的特征,决定了社会的系统性;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观察和思考世界的方式及其模式,决定了系统的普遍性……社会始终是作为社会系统而存在的。”[7]事实上,系统不仅普遍存在,并且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思考与生活。这就要求我们在看待任何一类事物的时候,应当将其视为社会系统并用系统的分析方法研究这一事物。
2.强调系统与环境、封闭与开放的关系
一般系统论十分强调整体和局部的关系。然而,卢曼的社会系统论独树一帜,更强调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从整体与部分到系统与环境的转变,也促成了社会系统理论范式的第二次转变。卢曼认为,“系统理论是以‘系统和环境的差异的统一体’为出发点的。环境对于这样的差异结构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契机,因此对于系统来说,环境具有不输于系统本身的重要性。”[8]也就是说,系统与环境两者之间,同等重要且相互依存。当然,这种同等重要且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不代表着系统与环境之间完全开放,他们之间也存在一种界线:这种界线就是基于封闭性的开放性。卢曼认为,系统首先是封闭的,只有封闭,系统才能进行自我组织、调整、自我指涉和自我再制,而后才能对环境开放;只有开放,系统才能得到更新与发展,否则,系统与环境之间的依存,也就无从谈起。
3.社会是一个自我指涉和自我再制的系统
卢曼用“自我指涉”和“自我再制”替代了一般系统论中的“输入—输出”系统。“自我指涉系统通过将其与环境不断区分开来的过程不断指涉自身,而这一过程也构成了功能分化的过程……强调了诸系统的自主性和它们之间的差异。”[9]而根据卢曼的自我再制系统理论,“功能系统只能自我调控,无法由外部加以调控,而且一个系统正常操作的前提是,其它的系统亦能正常操作,履行其各自的功能。”[10]事实上,个体正是凭借自我指涉和自我再制的运作,实现其主体性,从而也区别于其他系统。“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性是不受制于外部环境或其它系统的。外部因素或其它系统的作用只限于提示一些可能的自我确认方式,只有当个体或系统接受了这些提示,并将其纳入自我再生运作中时,这些外在的影响力才有意义。”[11]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中的自我指涉和自我再制,强调了内因在事务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指出了差异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差异性的存在,世界的丰富多彩才得以实现,而这也造就了不同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形式多样的联系。
二、作为社会系统的农村社区
毫无疑问,作为一种村民生产与生活的共同体的农村社区,实际上是客观存在的。借助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视角对“农村社区”的内涵进行再解读,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充分地把握农村社区这一系统的内在特征及其与外部之间的联系,从而正确地认识和解读农村社区。
(一)农村社区:客观存在的社会系统
聚落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生存的需要。农村社区则是人类最早的聚落。虽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城市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聚落”,非农产业生产成为人类主要的生产活动,其在人类生产与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与之相反,农业生产愈加显得轻微,比如,世界银行的相关资料显示,2014年美国的农业生产总值仅占全美GDP的1.45%,同年我国农业生产总值也仅占9.16%。但作为承载着农业生产功能的农村社区,其本身不会轻易消失,比如,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但是农村依然分布广泛,欧美国家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的现象;我国虽然已经成为工业大国,但是,农村、农业与农民依旧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实际上,“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无可回避的问题,也是我国民族复兴伟大事业成败的关键。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而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对农村社区这一承载着农业生产、生活在内的多种功能的社会系统进行系统的,科学的“再造”,从而建立一种完善的管理机制,助力农村社区的发展。
(二)作为系统的农村社区的两个面向:封闭与开放
作为社会系统的农村社区在“系统—环境”的框架下通过“封闭—开放”的机制来维持系统的运作。所谓封闭,是指系统具有不容其他系统介入并篡改“编码”的自主性。农村社区作为一个社会系统,明显具有这种封闭性: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农村社区有固定的成员,有特定的文化,生产、活动方式,管理风格和权力运作模式,这也是其成为农村社区以及区别于其他系统的重要因素。也正是这种封闭性,使其能够在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外部环境中,保持自身的特点,维持自身的秩序,形成自己的特色。当然,它又具有开放性,肖文明认为,“封闭性并不意味着系统是遗世独立的,相反它与环境中的其他社会系统有密切的关联,存在一种所谓的结构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关系,系统是开放的系统,它开放地承受着其他系统对它的刺激和影响,但这种开放关系并不同于传统的输入与输出模式,后面的这种模式更强化的是系统间的相互依赖。”[12]实际上,农村社区这一系统承受着外部环境的各种“刺激和影响”,并与其他系统紧密联系,比如自然环境系统、生产资料市场系统、销售市场系统发生变化的时候,农村社区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就需要进行调整,如果社会政策发生了变化,比如国家提出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那么,农村社区中的权力结构和管理方式就可能发生变化。所以,在推进农村社区管理过程中,就应该注意从内、外两个角度思考问题。
(三)作为自我指涉和自我再制的系统农村社区:自主性与多样性
系统通过自我指涉和自我再制,以此形成和维护系统的自主性或者自我特质。虽然外部环境可以通过“沟通”的方式,影响系统边界的内部要素,但如前所述,这些因素必须得到内部要素的接受并进入自我再制的环节,才能发挥其作用,这也导致了农村社区的多样性。比如,同样一个地区的农村社区,虽然有同样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和制度安排,但是,每个社区的“个性”却不尽相同:民风淳朴或民风彪悍;以传统农业生产经营为生或以外出务农务工为生;社区管理民主或管理独断等。可见,外部环境的相似性并不否认社区的独立自主和多样性。究其原因,正是由于系统内部要素的不同及其对外部因素的“主导”:对外部环境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不同,最终形成了农村社区的差异化与多样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农村社区进行管理的时候,应该“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当把每个农村社区当作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个体,承认其差异性,并通过民主、科学的途径与农村社区内部的要素有效“沟通”,获得系统内部的认可和接受,从而影响农村社区的变迁过程。
三、社会系统理论对农村社区管理的启示
从社会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农村社区作为一个系统,显然具有社会系统的特征。其是客观的,在封闭的同时,又具有开放性;在讲究自主性的同时,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因此,我们在推进农村社区管理过程中,必须注重从系统的角度理解和观察这一系统,并运用系统的思维与方法重构农村社区管理机制。
(一)重视农村社区管理:从边缘到重心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农村社区的管理工作。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把农村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但是,由于农村社区地理区位的局限以及在赶超战略①张双娜(2006)认为,赶超战略是指发展中国家高度动员有限的资源,依靠工业化实现经济增长的战略。新中国建立之后,在国内外压力下,为了尽快摆脱贫苦落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我国实施赶超战略(参见张双娜发表于2006年第1期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的《我国赶超战略的代价分析》)。的影响下,我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向来以城市建设、GDP、经济发展为导向,而轻视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以致于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社会的演进过程同时也就是农村社区建设的边缘化、真空化的过程。”[13]然而,从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来看,农村社区是客观存在的,从我国社会发展来看,农村社区的发展是我国现代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正视农村社区的客观存在性,构建一个主体多元,功能齐全完善,发展健康有序的现代化的农村社区,应当说,是推进我国现代化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从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到地方管理层面上,都应当重视农村社区的管理,将重心回归到社会建设上来。
(二)转变农村社区沟通方式:从单向沟通到互动沟通
按照卢曼的观点,内因是系统变迁的关键,外部要素只能透过“环境”,与内部要素适当地沟通,才能影响内因并发挥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农村社区管理的过程中,必须从单向沟通转变为互动沟通。单向沟通速度快,但是其不足也十分明显:“单向沟通中的意见传达者因得不到反馈,无法了解对方是否真正收到信息,而收受者因无机会核对其所接受的资料的正确性,内心有一种不安和挫折感,容易产生抗拒心理。”[14]所以,在推进农村社区的管理过程中,必须转变沟通的方式,通过有效互动,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从而增进了解,形成共识,最终实现对内部要素的有效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首先要尊重村民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村民是农村社区的主体,也是农村社区管理的客体,因此,必须认真倾听村民的诉求,并创造条件,完善制度,鼓励和支持村民对本社区治理的参与。其次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以合理而有效的程序制度为保障,推进农村社区的协商治理,从而通过充分而有效的辩论、讨论等方式,实现对话双方的有效沟通,最终达成共识,以获得村民的理解和认可,获得村民对社区管理的服从与支持。
(三)完善农村社区内部治理:从不成熟到成熟
农村社区内部的有效治理,不在于提供了多少制度,多少方法,也不在于为农村社区管理提供了多少资金,而在于农村社区治理机制的成熟与完善。因此,加强农村社区管理,应当使社区的内部治理从“不成熟”走向“成熟”。②这里借用了克利斯·阿吉利斯的 “不成熟—成熟”理论,他认为人的个性发展,是一个不成熟到成熟的连续的发展过程(参见毕蛟发表于1998年第2期《管理现代化》的《阿吉里斯与“不成熟—成熟理论”》一文),社区治理机制的发展,也是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一要在坚持和完善农村社区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的条件下,优化农村社区的治理结构,不断完善社区中的非政府组织(如村委会等)的建设,提高其独立性和权威性,强化其在社区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完善农村社区的治理制度。要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进一步完善村务决策、执行与监督机制,强化村务公开,进一步畅通村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规范社区治理各个主体的权力和责任,推进社区的有效治理。三是要提高村民对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治理参与能力。社区是社区的成员的共同空间。没有社区成员的认同和参与的社区治理,是不成熟的治理。这就要求在强化对社区成员的引导和教育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根据地方特色和实际情况,创造条件、创新机制、完善制度,从而理顺居民与自治组织的关系,提高居民参加社区建设,参与决策过程,监督执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优化农村社区管理的外部环境:从“标准化”到多样化
管理追求效率、经济。在管理的范式下,管理主体受工具理性影响,通过权力、资源和制度对管理的客体进行控制,从而寻求以更少的“消耗”实现某种目的。应当承认,工具理性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积极的意义,其所具有的非人格化特征、效率优先逻辑,追求形式合理性,对于管理的现代化、合理化,政治生活的规范化以及权威的合法化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工具理性所具有的过度理性、工具化、精细化与计算化的特征,导致我们在推进社区管理的时候,习惯于“统一”“标准”“一刀切”,用一种思维去分析不同的系统,一种制度去管理不同的客体,用一种手段去处理不同的事情,这种“标准化”的外部管理环境,对于多样化的社区说,显然是不够的,也无法适应多样化的农村社区的需求。因此,面对存在差异化和多样性的农村社区,政府应当从工具理性转向 “价值理性”,承认农村社区的差异化和多样性,充分认可和尊重不同社区的现状、文化、风俗和利益诉求,并据此设计不同的管理形式、管理方式形成不同的管理风格,从而为农村社区管理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五)改变农村社区管理的手段:从控制到引导
国家基于实现一定的秩序的目的而对社会进行控制。然而,控制却存在一种失灵悖论。张康之认为,“近代以来的情况显示,政府往往试图通过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去提供社会秩序,然而,却经常性的陷入社会失序的境地……所以,一个控制导向的政府并不能真正赢得其治下的社会安定,即使有着强大的暴力机构做后盾。”[15]因此,在对农村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应当通过引导而非控制的方式,从而获得农村社区这一系统内部不同主体的认同和接受。这首先需要政府一方面做到“简政放权”,还权于社会,避免对社会系统的过度干预和控制,推动市民社会的发展,提高社会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成长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切实的从具体的行政事务过程中抽离出来,从“划桨”到“掌舵”,实现对社会的价值的有效引导。其次,在推动农村社区管理的过程中,要站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上,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为农村社区治理制定“元”战略,提供战略方向的引导和规划,具体到农村社区治理来说,就是要在制定农村社区治理“元”政策的基础上,继续鼓励和支持社区自治,通过农村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与自我服务实现社区的成长。
四、结论与思考
不能否认,农村社区管理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的研究及其应用也颇多。但从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研究农村社区管理,则显得较为稀少。因此,从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考察农村社区管理问题,确有其理论意义,也为我们完善农村社区管理提供了新视角: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在推进社区管理的时候,更侧重从外部的角度来为社区管理提供不同的驱动,而忽视了作为社会系统的农村社区其所拥有的自主性。然而,从社会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系统,农村社区通过封闭性维持自身的特征,通过开放性与外部环境进行交流,外部环境只能通过“沟通”的方式,获得系统的认可和接受。所以,在重构农村社区管理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以“社会系统”的观点与方法,审视、反思农村社区及其管理:重视农村社区的管理,认识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加强其管理的必要性,必须注重农村社区管理的多样性、灵活性,注重引导与沟通,注重内部要素的成长与发展。
应当承认,在社会系统理论视角之下的农村社区管理的具体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思考和论证。卢曼本人也认为,社会系统理论本身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观点上的”分析工具,所以本文的观点只是基于观察而得到的思考,其并不能直接操作,但这并不能否认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的独特价值,也不能否定其对我们重构农村社区管理的启发。显然,推动农村社区管理创新,实现农村社区管理的“善治”,需要我们“摆正”立场,也需要我们借助该理论,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农村社区管理机制。
[1]丁元竹:《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9页
[2]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22~23 页
[3]张兴杰:《社区管理》,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5页
[4]汪大海等:《社区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 9页
[5]李增元 田玉律:《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第29~34页
[6][9][12]肖文明:《观察现代性——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新视野》,《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第 57~69 页
[7]高宣扬:《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
[8]葛星:《N·卢曼社会系统理论视野下的传播、媒介概念和大众媒体》,《新闻大学》2012年第3期,第7页
[10]张嘉尹:《国家理论——系统理论的观点》,《淡江大学法政学报》1985年第5期,第87~107页
[11]丁东红:《卢曼和他的社会系统理论》,《世界哲学》2005年第 9期,第 34~38页
[13]殷翔:《农村社区的边缘化及其重建的路径依赖》,《社科纵横》2004年第8期,第69页
[14]陈莉:《管理中的有效沟通》,《企业文明》2001年第6期,第16页
[15]张康之:《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240~241页
(责任编辑:张晓月)
Rural Community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ystem Theory
Chen Qiang Lin Hangfeng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rural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the current social management of our country.The article reviews the theor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uhmann’s social system theory and reconsiders rural community management.The paper argues that rural communities are a typical social system,which is objec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uhmann’s social system theory.It has its closeness and meanwhile it has its openness,which shows its autonomy as well as diversity.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rural community management,the rural community must be regarded as an objective system and must be paid enough attention,the internal governance and the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 should be improved,the favorable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should be built for the rural community management and effective guidance should be developed in order to let these inner elements interact fully and finally achieve “good governance” in rural communities.
Luhmann,social system,the perfect of rural community management
三亚学院法学与社会学学院 海南三亚 572022
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2016年度规划课题“三亚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的农村社区管理问题研究”(批准号:HNSK(ZC)16-3);海南省教育厅2015年度规划课题“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会管理问题研究——以三亚为例”(批准号:Hnky201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