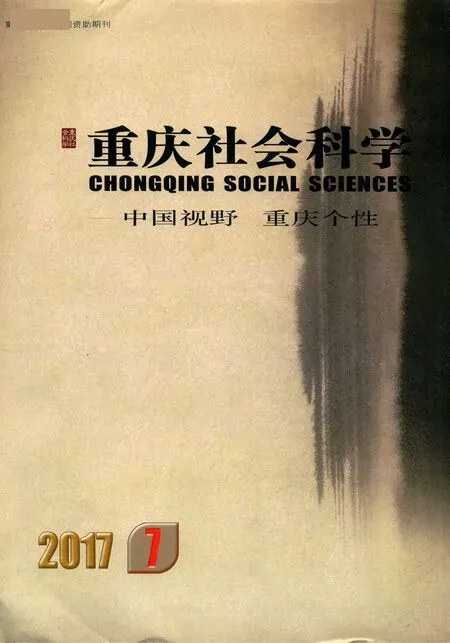康德的两大发现及其当代意义*
张廷国
康德的两大发现及其当代意义*
张廷国
通过对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批判,康德的最大理论贡献在于他的两个伟大发现:一是“人为自然立法”;二是“人为自己立法”。第一个发现使得他在知识与信仰之间划清了界限,从而一方面为自然科学知识提供了形而上学奠基,另一方面又为人的信仰保留了地盘;第二个发现在于他确立了“定言命令”的绝对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这就使得他的伦理学与功利主义、快乐主义等伦理学有了根本区别。迄今为止,康德的这两个发现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仍然具有当代意义。
知识与信仰 定言命令 启蒙 全球化治理 康德方案
康德的批判哲学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直到今天它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康德的批判哲学之所以能具有这么深远的影响,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他通过对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批判所提出的两大发现:“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1]换言之,我们也可以把康德在这里所发现的“两样东西”表述为:一是他发现了人类经验性知识的开端在于主体,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二是他发现了适用于所有人类的“定言命令”,提出了“人为自己立法”。本文的目的正在于,通过康德的这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来阐释康德批判哲学所蕴含的当代意义。
一、人为自然立法
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去重新评价康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时,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康德之前是一个世界,康德之后则是另一个全新的世界。如果说康德批判哲学之前的世界是朴素的,并且受到各种不同科学领域和不同知识渠道的影响,那么在康德提出他的批判哲学之后,就有了一个完全明晰的和无法伪装的自然科学导论。
在康德看来,人在自然界面前并不是一个消极的直观者,而是一个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主体。当科学家们通过大量的科学实验来获取源源不断的自然知识时,他们必然已经领会到,理性只会看出它自己根据自己的策划所产生的东西,它必须带着自己按照不变的法则进行判断的原理走在前面,强迫自然界回答它的问题,而不是亦步亦趋地跟在自然界的后面,因为否则的话,那些偶然的、不根据任何先行拟定的原理和计划而随意作出的观察就不可能具有法则的普遍有效性。所以,“理性必须一手执着自己的原则(惟有按照这些原则,协调一致的现象才能被视为法则),另一手执着它按照这些原则设想出来的实验,而走向自然,虽然是为了受教于她,但不是以小学生的身份复述老师想要提供的一切教诲,而是以一个受任命的法官的身份迫使证人们回答他向他们提出的问题。”[2]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通过对人的主观认识能力(主要是感性和知性)的批判考察,不仅第一次对自然科学领域作出了规定并精确地作出了相互之间的区分,而且与此同时,他也一劳永逸地划清了哲学与神学的界限,认为数学和自然科学只是关于“现象世界”的知识,而与作为“自在之物”的上帝无关。
也正是由于康德对知识与信仰或者说哲学与神学的划分,可以说当时他承受了很大的舆论压力,尤其是来自教会的压力,甚至直到今天为止,康德的批判哲学也没有得到教会的真正宽恕,因为在传统的教会看来,正是因为康德的知识批判,才使得神学即关于上帝的科学丧失了应有的至高无上的信誉,并被无情地驱逐出了知识论的领域。
至于康德为什么非要坚持这种划分,其实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他已经为自己作出了辩解,他是这样说的:“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为信仰保留位置。”[3]因为在康德看来,上帝根本就不属于现象界,因此是人类的经验知识所无法认识的。但是,上帝作为纯粹理性的先验理念,并不意味着它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余的和无意义的,即使它不适用于理性的构成性原则,但它毕竟适用于理性的调节性原则。把它作为一个调节性原则来运用,至少可以防止人们任意地夸大有限的理性认识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只有当我们把上帝当作理性的调节性原则来使用时,我们才能使从自然领域到实践领域的过渡成为可能。但是,如果人们试图摆脱理性的调节性原则而转向理性的构成性原则,那么,理性就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引入歧途。换言之,如果我们把上帝的理念当作构成性的原则来运用时,就会把一切自然科学的研究都看作是完成了的,从而放弃对理性的正确运用,导致理性的懒惰。
与此相关,对康德还有一个指责,恰好因为康德对知识与信仰所作的这一划分而在事实上使他成为了宗教的掘墓人。因为就信仰与知识所具有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而言,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肯定是更加依赖科学知识而不是信仰。因此可以说,自《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出版以来,自然科学所取得的进步事实上已经与康德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康德通过对人的认知力的分析和批判,不仅指出了自然界是可以按照理性制定的构成性规则来认识的,进而论证了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是可能的,而且他那具有革命性的知识批判第一次提出了清晰的方法论,从而建立起了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体系。正如他所要求的那样,自然科学知识尽管离不开先天的直观形式和纯粹范畴的先验条件,因而尽管有构成先天理论的可能性,但它却必须始终都要在经验性上和感性上成为可实现的,因此这也就为实验科学的兴起提供了方法论的奠基。这就意味着,一种理论模型是否可以偶然地由观察获得,或者相反,自然界是否可以在事后借助一种理论模型而被观察到,这都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知识都必须始终是经验性的,因而是可重复的。必须在这个严格的前提下,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才会一次性地成为可比较的,才会推动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二、人为自己立法
如果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贡献在于发现了“人为自然立法”,那么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的贡献则在于他在此发现了“人为自己立法”,即理性能够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即人自身)先天地规定所有人都应当遵守的道德法则,这就是他所说的“定言命令”或“绝对命令”:“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4]
康德的这一“定言命令”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二百多年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称赞和崇敬,但也有来自一些批评的声音。例如,当代德国哲学家舍勒就指责康德的这个命令太过于抽象和形式化,因而不过是一种形式主义的伦理学。这一形式主义的特征使得它必然缺失现实的价值和具体内涵,如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等。舍勒之所以不赞成康德的伦理学,在于他认为,在现代社会我们更需要的并不是康德意义上的纯粹形式的伦理学,而是一种具有实质内容的伦理学。虽然舍勒提出的这一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批评很快就沉寂下去了。因为事实上,在康德提出的这个“定言命令”中,其实已经含蓄地包含了非常具体的内涵。譬如康德写到:“现在我要说,人以及一般的每一个理性的存在者,都作为自在的目的本身而实存,不仅仅是作为这个或那个意志随意使用的手段,而是在他的一切不管指向自己还是指向其他理性存在者的行动中,都必须总是同时被看作目的。”[5]显然,在康德的这个表述中其实就已经插入了如下见解:作为人格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得到尊重。人不可以被滥用为单纯的手段,相反,每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都是“自在的目的本身”,正如作为整体的人性一样。因此,每一个单个的人都有权按照他自己的目的和目标来发展他的人格性。而且康德由此引出的第二条“定言命令”的表达方式也再一次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你要这样行动,把不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任何其他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任何时候都同时用做目的,而绝不只是用做手段。”[6]
由此可见,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之所以被称之为“人格”(Personen),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本性已经表现出他们就是自在的目的本身。在这里,作为人的行动准则,对由单个的人格构成的人性的尊重不仅要求相应的作为独立人格的权利,而且除此之外,也要求绝对的平等。所以,虽然人们对康德的伦理学提出了这样那样的批评,但对他提出的这个“定言命令”,应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有颠覆性的批评。因为它已经包含了世界公民的自我认识,而要具体实现这种自我认识,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从“定言命令”这一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出发,我们有理由说康德的伦理学只是一种义务伦理学。根据康德的观点,甚至于一个有公益心的和亲切的行善者,如果他仅仅是因为帮助他人才能感觉到一种内在的愉悦时,那么,他的行动就不是真正道德上善的,因为他是出于爱好而不是出于纯粹的义务来行动的。但对康德而言,在这种情形下的这类活动,无论多么地合乎义务,多么地值得爱戴,但却不具有任何真正的道德价值,而是和其他的爱好是同一层次的,比如,对荣誉的爱好,如果它碰巧实际上符合公共利益,并且是合乎义务的,故而是值得赞赏的,那么,它至多应当受到表扬和鼓励,但不值得非常尊重。“因为这种准则缺乏道德的内涵,也就是说具有道德内涵的行动并非出于爱好,而是出于义务去做。”[7]
当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会觉得康德提出的这个“定言命令”太过于苛刻和严肃,而且康德本人也承认,要始终并且到处都能够满足这个“定言命令”,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康德看来,“定言命令”作为理性的调节性原则只是一种先验的道德理念,而且这一理念能够持续地鞭策我们。除此之外,这也是康德哲学中最重要的暗示,即每个人都能够自己决定什么是道德上善的,没有人可以并且必须完成他无法负责的指令。因为在最终的审级中我们只对自己负责,我们在自身中就具有至上的道德法则。根据康德的这个观点,围绕着我们的整个世界都必须用这一法则加以衡量,假如一切价值都是有条件的、偶然的,那么对我们来说就将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什么至高无上的实践原则了。
三、全球化治理与康德方案
虽然“定言命令”仅仅是一个应然而非实然的命令,虽然它让人感到很严肃,但是在本文看来,对康德的这个“定言命令”的一贯运用从来就没有像今天变得这么重要和迫切。当今社会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作为地球村的一员,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既是相互独立的又是休戚与共的。每一单个的人、民族和国家在实施自己的政策并采取自己的行动时,都不能只是单单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及他人的利益,都不能仅凭自己的习俗、爱好和任性而不顾及他人的感受。例如,在当今关于世界气候的争论中,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在世界气候会议上是否能够一致同意降低有害物质的排放?未来数十亿的私人家庭是否表明,可持续性的经济就要决定性地依赖我们是否能够成功地把我们的工业化的行动原理与全体人类的行动联系起来?只要有个别国家或个别公民以功利主义或利己主义的方式优先给自己的利益提供一种普遍典范的解决方案,那么,对我们生存环境的掠夺式开采就还会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就会继续生活在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的“座驾”之中,沦为技术的奴隶。
与之相反,作为一种选择,人们间或需要尝试康德开出的启蒙方案,在此我们不妨将之称之为“康德方案”。按照康德的方案,我们在讨论国际重大问题时,如关于世界气候的变化问题,似乎就有必要要求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参加每次峰会之前都必须接受一次康德哲学课的启蒙,而在课程结束时让他们牢记康德的劝告:“你要这样行动,把……人格中的人性,任何时候都同时用作目的,而绝不只是用作手段。”[8]虽然这一方案只是一种假设,但作为一个理想目标,的确值得我们期待。
世界各国关于世界气候的谈判,从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到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议书》,再到2016年的《巴黎协定》,在经历长达20年的谈判中,在关于温室气体含量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等涉及世界气候变化问题上,迄今为止之所以难以达成让各国政府都能够一致同意且愿意贯彻实施的方案,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各国的领导人作为国家经济利益的代表,在谈判的过程中只会遵守如下的命令:要这样行动,你要确保你自己国家的富强和繁荣,这样你就要把其他国家作为这个目的的手段来使用,就要争取让他们自愿地降低有害物质,并同时以最小可能性的方式放弃本国的利益来保护你自己国家的利益。当年美国和加拿大主动退出《京都议定书》,如今美国又公然退出 《巴黎协定》,其实他们所遵守的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本国的利益第一,本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当我们超越个人和国家去进行思考和行动时,康德“启蒙”的暗示虽然已被许多人所理解,但却仍然没有丝毫改变。甚至康德本人也知道,启蒙的批判运动绝对还没有结束,这从他写于1784年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可以得知:“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那么回答就是:不是,但确实是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9]
如果考虑到必须以新的方式方法去思考目前全球化治理所提出的新问题和新挑战,那么康德的劝告,即我们必须遵守启蒙的方案恰好也适用于当今的时代。但也许有人会质疑,这是不是已经太迟了?全球生态的破坏还能够得到遏制吗?如果按照当代德国哲学家阿多诺的看法,工具理性已经完全被客观理性所排斥,我们只能听任工具的利益考虑和资本利益的摆布。这样一来,启蒙的方案最终将被判处失败。但康德并不这样看,他认为从非理性转向理性在原则上是有可能的,而且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要变得有理性和明智,这从来都不会太晚;但如果洞见出现得晚,那么要实施它在任何时候都会更加困难。”[10]
事实上,与人类的历史相比,康德得到的关于未来必须在生态上可持续性地去管理世界的洞见已经很晚了,因为自从有了人类以来,我们就已经为了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而习惯于对地球的伤害和剥削了。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一种新的批判性思维,来取代《圣经》中关于“让大地听命于你们”的戒律。但是,如果说在哲学史上存在过一条这样的伦理原则,而这条原则又完全支持地球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和全球治理的话,那么,它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它只能是康德所发现的“定言命令”。所以,只有当我们真正地理解并主动地接受康德的这一“定言命令”时,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把康德的“定言命令”当作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时,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治理才有可能。
四、结语
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家,康德同其他的启蒙思想家一样,不仅要求用一种理性批判的态度来取代中世纪的神学思维,而且要求在政治上彻底摆脱君权神授说的影响并建立起现代的民主制国家。而要实现这一划时代的历史变革,康德认为,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进行理性的启蒙,因为只有经过了真正的和彻底的理性启蒙,才能够“让人从其自身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中摆脱出来”。在这里,人的“不成熟状态”之所以是“自身招致的”,正是因为我们很久都没有运用我们自己的理性了。正如康德所说,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对社会和自然力量进行批判性的追问,人们自然就会在宗教势力的强迫之下而感到恐惧,并因此而宁愿相信那些流传下来的迷信。所以,“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缺乏勇气……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身招致的。”[11]
由于人们缺乏勇气去追问占统治地位的教条,因此,长期以来君权神授说一直都未受到质疑,国王之所以被当作国王来接受,乃是因为他是前任国王的儿子。但是,后来因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这一切才开始发生变化。尽管康德对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并不怎么感兴趣,但总的来说,他与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还是相当一致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还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政治上的同情者和理论上的同盟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要求人们要“公正地把康德的哲学看成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12]所以,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虽然康德本人生活在普鲁士王国,但他却要求在理论上对一切传统和教条进行理性批判的检验。这正如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版序中所说:“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通常,宗教凭借其神圣性,而立法凭借其权威,想要逃脱批判。但这样一来,它们就激起了对自身正当的怀疑,并无法要求别人不加伪饰的敬重,理性只会把这种敬重给予那经受得住它的自由而公开的检验的事物。”[13]本文认为,康德对批判一切的这种强烈要求,在当今时代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然有效。这也许恰恰是康德的批判哲学留给我们的最为重要的遗产。
[1][4](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220、39 页
[2][3][13](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 2004年,第 13、22、3页
[5][6][7][8](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杨云飞译,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62、64、18~19、64 页
[9][11](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9页
[10]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前言,第2页
[12](德)马克思:《法国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马恩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100页
(责任编辑:张晓月)
Kant’s Two Great Discoveries and Their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Zhang Tingguo
For the reason of his critique on pure reason and practical reason,Kant’s bigges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lies in two great discoveries:One is the thought about “the human being’s legislation for nature”,the other is about“the human being’s legislation for himself”.The first discovery enables him to draw a clear boundary between acknowledge and faith.Thus he provides a metaphysical foundation for the scientific acknowledge and meanwhile keeps room for the faith.The second discovery lies in his establishment of the absolute necessity and universal validity of“categorical imperative”,this fundamentally distinguishes his ethic from utilitarian and hedonic ethics.So far,this two great discoveries are not out of date,but rather have their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cknowledge and faith,categorical imperative,enlightenment,global governance,Kant’s solution.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湖北武汉 430074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德国古典哲学与德意志文化深度研究”(批准号:12&ZD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