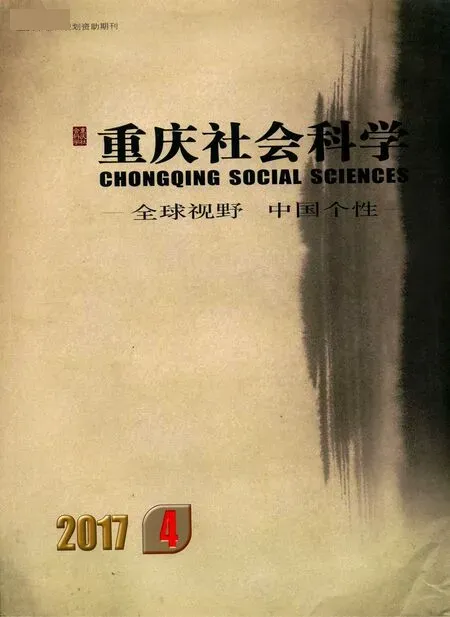村民自治、成员主体与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
杨成胜 刘丽娟
村民自治、成员主体与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
杨成胜 刘丽娟
内源式发展立足农村社区,挖掘内部社会、经济、文化资源,以社区内部成员为主体,通过外部资源带动实现本地区的自我发展。村民自治制度是农村社会基层组织和管理制度,是农村居民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进行自我治理的制度和行为。农村社区发展与村民自治密切相关。应遵循农村社区发展的逻辑,整合农村内部的自治元素,培育农民主体性,重构农村自治组织体系,从而走出一条自我、内源、持续发展道路。
村民自治 农村社区 “三农”问题
农村社区发展一直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事物发展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根本原因。内源式发展是我国农村发展的理想模式,即立足农村社区,挖掘内部社会、经济、文化资源,以社区内部成员为主体,通过外部资源带动实现本地区的自我发展。在我国,村民自治制度是农村社会基层组织和管理制度,是农村居民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进行自我治理的制度和行为。村民自治制度通过确定农民的主体地位,将分散的农民吸纳进国家治理体制中来,以此实现对国家的认同,达到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我管理的协调。这里从农村社区的内源性发展角度,探讨村民自治如何实现与农村社区的共同可持续发展。
一、农村社区内源性发展的理论阐释和路径建构
内源式发展最初源于经济学理论的内源性增长理论,现广泛应用于农村发展中。“二战”以后,高速的工业化、城市化一方面带来了世界城市地区的飞速发展,同时也造成了乡村地区逐渐衰弱。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乡村地区的问题引起各国广泛重视,“内源式发展”作为解决乡村发展问题的一种新模式不断开始得到建构。
Christopher Ray认为,内源式发展是一个与外生式发展相反的概念,它的重点在于恢复和创造,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物质和人实现地区的增值。内源式发展的核心不仅包括当地的知识、文化和技巧,而且包括当地公共的、私营的和自愿性的组织能参与到发展建设中。内源式发展的同义词为自下而上(bottom-up)、草根(grass roots)和参与(participation),对地区发展的设计和控制过度依赖外来力量持批判态度。[1]Paul Cloke在对欧盟的新内源性农村发展的研究中也提到,新内源性的内生部分是自下而上(bottom-up)的发展轨迹,重点在于寻求当地发展的资源和机制。新内源性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和其他发展活动通过开发当地的资源实物和人力实现,并且发展的利益最大化地保留在当地。二是发展的重点在于当地人的需求、能力。这种发展模式强调当地参与设计和行动的原则和过程,在发展干预中考虑当地的文化、环境和社区价值观。[2]
内源式发展是农村发展的理想模式。农村社区是农村居民生活的最基本单元,是指以农业生产为主要活动内容而聚集起来的人们的共同体。[3]农村内源式发展是一种在充分利用本地物质资源、文化资源以及人力资源的基础上,以社区内的农民为参与和建设的主体,并积极培育基层社区组织,逐渐摆脱对外在力量和资源的依赖,从而实现本地区的自我生长的发展模式。
对于农村内源式发展的路径,学者也进行了探讨。黄高智从文化角度论述了内源发展的路径,即以文化为基础,以人类本身为中心实现民族发展。[4]徐国亮在论述社区的内源性发展时提出社区内源性发展是一个有机整体,社区发展并不仅是由经济或文化决定,而是社区这个有机整体中的各环节和各层面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社区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不断递进的发展趋势。社区内成员之间也具有互动性,相互依赖。[5]蒋健提出社会变迁是随着社会内部要素的改变而变化,内源式发展是为了满足新的需要对原有社会结构所作出的逐渐变动的过程。[6]整合发展是农村内生式的发展路径,杜慕文将农村发展内核系统划分为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子系统,并且和发展外缘系统进行着交流。人处于这些子系统的中心,是影响其他三个子系统的主导因素。[7]由此可见,农村内源式发展是一个不断递进发展的过程,应立足挖掘农村内部资源,整合农村内部力量推进社区建设,实现国家理性和农村理性的良性互动,从引导社会资源向农村积累和配置。从根本上说,农村社区发展最终目标在于赋权于民,培育社区居民自主性,增强农村社区自我整合和发展的能力,最终走上自我发展、内源发展、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村民自治的内在价值
(一)村民自治的自主管理和主体间性
根据吉登斯现代性的分析,当代社会是现代化高度发展的产物,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8]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层面。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基本属性是机械团结,是“家族结构式的社会”。传统乡土社会依靠血缘、地缘和族缘建构起来的民间网络构成共同生活体。乡里组织、宗族和乡绅等在不直接依赖皇权的情况下,依据宗法伦理、地缘情感和熟人社会法则自行处理乡村社会内部的共同事务。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主要是一种“无为政治”,“横暴权力”虽在名义上可以说是“专制、独裁”,但从人民实际生活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9]传统社会国家的正式机构难以深入到乡村的基层,只能达到州县一级,皇权不下县的这种传统乡村社会自我管理模式不具备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开展自我管理的乡里组织、宗族和乡绅这些主体也缺乏主体性认同。传统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并未成为国家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社会的管理权力未得到政治制度认可与规范。
与传统社会的乡村自我管理模式不同,村民自治制度是一个现代性概念。所谓村民自治,就是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形式,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过程。这就包含了现代性的自主管理和主体间性两个特征。[10]一方面,村民自治体现了自主管理。通过自治村民以及社会自治体可以作为独立的行动主体,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达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目的。村民自治为农民提供了政治参与的渠道,使村民能够参与本社区政治经济等事务的决策管理与监督,培育了农民的公共意识、参与意识和契约精神。自治是一种自主行动、自主管理的现代品质。另一方面,村民自治体现了主体间性的现代治理理念。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主体间性是指主体互相把对方看作平等、独立的行动者,追求相互理解、沟通的交往理性。[11]首先村民自治作为基层组织和管理制度,是国家制度体系的一部分,自治体不仅有自主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力,并拥有政治参与、利益诉求的制度化渠道。其次政府对自治体给予信任和指导,在一定范围内提供帮助和支持。自治体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体,在社区管理等公共领域是合作关系,对政府存在监督作用。
(二)村民自治与农村社区发展的内在契合
村民自治与农村社区之间关系密切。一方面,农村社区是农民在长期相互依赖的生产和互动基础上形成的相互信任,有着共同规范的共同体,即“熟人社会”,这一场域的存在给村民自治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另一方面,村民自治是农村社区建设的社会基础,它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内部支撑,有效提高了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能力。
一方面,村民自治整合了农村内部资源,提高了农村社区的自我管理能力。从农村社区发展历程来看,农村社区建设是一场规划性的社会变迁过程,政府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政权下乡和政党下乡在乡村社会建立了人民公社体制,这是一种在社会一体化的基础上将国家行政权力和国家权力高度统一的基层政权组织形式。人民公社体制过度依赖政治权力等外部力量,是行政力量强力推行的产物,缺乏乡村社会内在动力的配合。不仅建设和管理成本高,而且影响农民和乡村社会的参与主动性。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为克服乡村社会的失序,村民自治制度应运而生,它的确立表明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关系由行政指令性转向乡村自治的民主性。它是一种新的乡村整合方式,具有社会自发和自我组织的特点,以民主的方式重新整合乡村社会。村民自治通过将权力下放给基层社会和公民,重新构造社会整合体系。激发和调动社区内部成员的积极性,将分散化的村民整合起来,优化了农村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有效地降低了国家管理成本,从而摆脱依靠国家行政力量支持外部性供给困境,走出一条可持续内源性发展的农村社区建设道路。
另一方面,村民自治能提高农民政治认同,重塑农村共同体。贺雪峰在《新乡土中国》中提到村庄共同体由自然边界、社会边界、文化边界构成。自然边界是构成人们交往的空间和基础;社会边界是对村民身份的社会确认;文化边界则是村民是否在心理上认可村民的身份,是否看重村庄生活的价值,是否面向村庄而生活。[12]农村社区成员的大部分生活都在本社区完成,是农村居民生活的最基本单元,村民的社会认同感是农村社区建设的关键。但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农村社会内部变迁以及城镇化等外在力量影响,传统文化和信仰被挤压而难有生存空间,村庄共同体逐渐走向解体,农民向“理性经济人”发展。农民大多数只关注个体自身利益和眼前短浅的利益,对于社区整体的公共事务关注不高,农村社会共同体的凝聚力下降。[13]在村民自治制度的框架下,村民本着自身的意愿依法处理农村社区内各项事务。村民作为自治的主体,村民自治制度赋予了村民自治的权力,同时也有效地规范了其行为。在对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参与中,逐渐提升了对社区的归属感;并且村民在彼此的互动中,扩大了社会网络,强化了社区规范和社区认同。只有村民真正在心理上认同村庄共同体并面向村庄生活,才会真正为社区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通过村民自治机制的有效运转,增强农村社会的吸引力,重新塑造农村社区的凝聚力。
三、村民自治制度促进农村内源性发展的路径
利用村民自治制度促进农村内源性发展,应重点从三方面着手。
(一)遵循农村发展逻辑,适应性嵌入农村社区场域
农村社区场域是指在农村区域内所形构的具有自身逻辑和社会空间网络及系统间的互动关系。农村社区是基于“行动者-制度-环境”互构过程中的场域空间建构行为逻辑,嵌入其中的组织、制度及社区发展制度,为具体的组织及行动者提供环境。就农村社会本身的发展逻辑来看,它不是激进也不是躁动的,而是始终遵循着平稳中和的演进模式。任何违背这一规则的制度和政策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退出历史舞台。农村社区发展具有递进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因而农村社会制度、合作行动与系统结构也在发生复杂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村民自治制度,农村社区传统系统在不断同新的系统要素互动中走向新的均衡。村民自治无论作为一种理念还是一种制度,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并在特定的场域中演绎和发展。要使其在农村社区真正获得长久发展的稳定基础,契合于社区场域的发展,符合农民群众的需要,应适应性嵌入农村社会的治理环境和农民的生活规则。
社会内部自行运作的规则就是资源,需要社会以外的力量来予以维持、推动的规则就是制度。农村社区内源式发展的实质就是充分调动和运用社区内部自身资源,将一个自上而下安排的规则内在化,挖掘内部自身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了使村民自治更好地嵌入农村社区治理场域,一要完善法律制度,明确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行使主体,赋予其完整的权力,为自治提供法律保障。二要明确职能定位,合理划分国家和乡村社会权力的管理界限。三要规范村级推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程序,保证村民对村庄事务的全面参与。四要规范权力,约束村干部的行为,比如推行民主评议的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以保障村民的监督权利顺利实现。
(二)明确农民主体地位,提高村民自治能力
就农村社区发展而言,外部力量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内生力量是其发展的根本;外部力量是国家和社会提供的制度、经济等行政支持,内生力量是农村社区内部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内生力量和外部环境互相作用。当前农村社区既要整合外部力量为农村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又要激活内部资源,形成自我发展的内源式模式。要走上一条自我、内源性、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首先必须保证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让自治成为农民的一种生活方式”[14]。农民不仅有权自主处理自己的事务,并且也可作为主体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有提出自己利益诉求、参与社区决策的权利,如进行选举、村务决策等活动。参与精神是主体意识的重要表现,要引导广大农民从“要我参与”向“我要参与”转变。
真正实现农民的主体地位,一要提高农民对于社区的认同感,激发其对社区建设和发展的责任意识。激发农民的主体性,可以将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作为契机。通过改变资源输入进入村庄的方式,将部分资源直接投放到村一级而将剩余的交予村民自行分配和使用。给予村民自主权,如此将国家资源与农民切身利益紧密相联,农民主动性便能被充分调动。通过将农民的利益与现实需求相联系,从而形成具有共同利益纽带、互动畅通的村庄共同体。只有农民认识到自己是社区的建设者和受益者,才会主动参与到社区管理中来,从而节省农村社区治理成本。
二要加强农村社区村民的教育培训,提升村民自主管理的能力。根据农民实际情况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宣传科技文化知识以及法律知识,逐步破除农村封建迷信思想,树立科学和现代化的思想,使农民在参与农村社区事务管理中不断提高自治的素养。在赋权于民的同时,让农民做到合理有效地使用权利,真正实现自主管理。
三要注重“乡村能人”的挖掘和培育,充分发挥能人作用。在“乡村能人”的带领下,村庄资源才能更加有效整合。乡村能人是农村社区发展的内生力量重构的重要力量,当前农村的人力资源丰富,但是人才匮乏,因而农村要实现内源式发展离不开“能人”的带领。有学者分析,当前我国农村有四种能人:一是先富裕起来的资本型能人;二是有一技之长的技能型能人;三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文化型能人;四是有威信的政治型能人。[15]乡村能人能够利用他们的优势和力量,通过整合乡村社会资源,将外部力量转化为农村社区发展所需的内生力量。
(三)完善自治组织体系,提升农村社区自我管理能力
村民自治制度缘于农村社区内部,其生命力取决于农村社区内部对于自治的需求承载力。从目前村民自治实施的现状来看,村民自治组织的行政倾向明显,自主性匮乏,组织规模偏小,承接力不足,制衡性缺乏,开发程度低,制约了村民自治制度的深入开展。[16]村民自治组织体系的发展实质是社会发育与国家建构的过程,对于目前村民自治体系存在的问题,应该从乡村社会需求出发,培育和丰富村民自治的组织基础、扩展和重构村民自治的组织体系,构建一个更具自主性、开放性、承接力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
第一,减少行政力量的干预,为自治组织发展提供良好的自由空间。良好稳定的社会秩序来自于内部有效组织与良性互动的结果。因此,政府应逐步放松对乡村社会的直接控制,消除行政权力对村民自治的干预,释放村民自治生长的空间。让村委会和多元的自治组织根据村民实际需求开展管理提供公共服务,使村民自治权逐步回归于民。自治空间的建构仅为现代自治提供舞台,多元而理性化的村民自组织的体系才是农村公共领域内的“主体角色”。
第二,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完善自治组织体系。多元化的村民自治组织是实现自主治理的基础。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群众的需求日益多元化,原有的村民自治体系难以承载。因此,需要注重农村民间组织的建设,与原有的村委会、村民代表会等自治组织相互补充。将新的农村社会自治组织纳入村民自治体系中,弥补原有自治组织体系的不足,满足村民的多元化社会需求。如“农村金融互助”、“老年人协会”这些民间社会组织的出现就是农民基于共同的需求与利益自愿联合而成的自我组织。民间自治组织具有强大的内在动力,为农民提供具体服务的同时将农民的主动性与主体性调动起来。社会组织作为农民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已经成为多元村民自治组织体系的一种重要内源性组织资源[17],因而可在引导、培育和扶持农村社会组织成长的同时予以必要的政策和财政支持。
四、结论与思考
农村社区发展和村民自治目标是一致的,两者都是为了完善农村社会管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良性运行。村民自治与农村社区发展互为基础、紧密相联。一方面农村社区建设为村民自治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场域环境,另一方面村民自治的施行为农村社区发展提供了内部支撑,挖掘社区资源有利于提高社区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能力。
从我国现代化进程发展趋势看,对农村社区治理的制度设计应从长期以来的由政府外部行政推动逐渐朝向内生能力促进的政策导向转化。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制度框架能增加逃避义务的风险,增强互利合作的习惯,达到抑制这种本能性机会主义的目的”[18]。建立在合理的制度框架体系中,通过政府有效干预和必要机制,才能规范主体的发展。因此,村民自治应在政府有效指导下,以挖掘和培育农村自生组织要素和资源为中心,帮助农村建立自主秩序。切实做到从农村发展自身规律,从农民真实意愿出发,真正建立农民主体性。要逐步放松政治生活的管制,归还本来属于民间生活的自治性权力;借助政策和经济、社会资源,为农村社会肌体输入正能量,增强新时期农村整体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的治理质量,全面提升农村社会组织能量和效度,为建设和谐的现代化新农村,实现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乃至国家现代治理体系的构建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1]Christopher Ray.Endogenou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uropean Union:Issues of Evaluation,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00(16):pp.447~458.
[2]Paul Cloke&Terry Marsden.Patrick Mooney,Handbook of Rural Studies.Sage Publications Ltd.,2006,pp.278~279.
[3]徐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江汉论坛》2007 年第 4 期,第 12~15页
[4]黄高智:《内源发展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
[5]徐国亮:《论社区的内源性发展》,《文史哲》1997年第 6期,第 35~39页
[6]蒋健 吴量亮:《农村发展的“内源性”视角探讨》,《南方论丛》2007 年第 8 期,第 20~21 页
[7]杜慕文:《人类社会协同论——对生态、经济、社会三个系统的若干问题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30~51页
[8](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9]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出版社,1998年
[10]安建增:《自治的现代性及其培育——对当地中国村民自治的审视》,《天府新论》2012年第 3期,第 111~114页
[11](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12]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6页
[13]何平:《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的共生、共建与联动》,《青岛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 37~41 页
[14]于建嵘:《让村民自治成为农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农村工作通讯》2010年第1期,第40~41页
[15]杨守宝 王全美:《资源再造和内源性机制形成的路径选择——新农村建设的能人视角》,《乡镇经济》2008年第 1期,第 87~89页
[16]刘宁:《村民自治组织体系的建构体系建构:组织培育与体系重构——论村民自治组织体系的生长逻辑、发展限度与路径建构》,《晋阳学刊》2013年第 4期,第 115~121页
[17]徐勇:《农村微观组织再造与社区自我整合——湖北省杨桥镇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河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8~11页
[18]柯武刚 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
Villagers’ Autonomy,Villagers’ Subjectiv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mmunities
Yang Chengsheng Liu Lijuan
Endogenous development bases on social,economic and cultural resources from local area,makes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s the main body and takes advantage of external resources to realizing self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Villagers’self-government system is the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s at the grass-root level and management system that the rural residents in certain region within the scope of self-governance.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villagers’autonomy.Followiing the logic of the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making integration of rural autonomy within the element,cultivating farmers’subjectivity,reconstructing rural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system,and thus out of a self,endogenou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oad,so that rural community runs a self,endogenou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oad.
villagers’ autonomy,rural communities,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farmers”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0
*该标题为《重庆社会科学》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村民自治与农村社区自我、内源、持续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