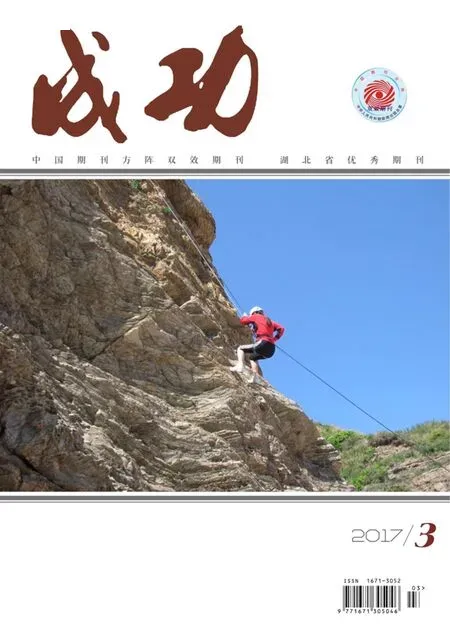古诗词英译过程剖析
曾杭丽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浙江杭州310015
古诗词英译过程剖析
曾杭丽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浙江杭州310015
诗词是内容与形式联系比较紧密的一种形式,译者在翻译之前首先要总体审度,制定合适的翻译策略,内容上忠实于原文;除此之外,还要不断地修改,采用诗化翻译技巧,通过音节缩略、信息转移、调序等方法,做到形式上也忠实于原文,不断推敲,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通过对这首诗词翻译过程的剖析,以期给典籍英译提供一些启示。
翻译研究;翻译过程;总体审度;诗化翻译技巧
一、引言
传统的翻译研究以翻译标准、翻译原则和译者主观性等方面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些研究大都以翻译产品为导向,很少关注翻译过程[1]。然而,综合的翻译学研究不仅应该关注翻译成品,也应该关注翻译过程。对于翻译过程的研究可以促进翻译学研究的发展,为典籍英译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提供借鉴之道。下面以一首《江南春·波渺渺》翻译为例,探讨其古诗英译过程,以期获得关于典籍英译模式的灵感。原诗如下:
波渺渺,柳依依。
孤村芳草远,
斜日杏花飞。
江南春尽离肠断,
萍满汀洲人未归。
此词是宋代政治家、诗人寇准的词作,前四句“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描写的是景,勾勒出一幅江南暮春图。以上四句有强烈的画面感,具有丰富的意蕴,以景寄情;后两句“江南春尽离肠断,萍满汀洲人未归”直抒胸臆,江南的春已远去,离别的愁绪让人断肠。水中的水草长得茂盛,布满了整个小沙洲,可远去的人啊,还没有回来。这两句将主人公的离愁抒写得淋漓尽致,道出伤春怀人的主旨。全诗清丽婉转、柔美多情,以景起,以情结,情景交融,表达了诗人如美人迟暮般的感慨。先看卓译一稿:
Spring South to the River
The waves of yearning vast,Willows drooping in memory of the past.
A lone village listlessly faces the grass vanish.
Apricot flowers floating in the setting sun.
Spring elapses in the south of the river,
grief over separation rends the heart,
Duckweed swarm in sandbar of Dingzhou,
yet my man’s not yet returned.
二、典籍英译的总体审度
词语、诗句、诗节和诗章的正确理解有赖于对全诗总意象的把握,而要把握总意象,就必须对诗人和诗作进行一番深入细致的研究,以便对诗人的思想、风格、对诗歌的创作背景、表现手法及意象、意境、音韵、节奏、类别和形式做到心中有数,这就是所谓总体审度。[2]
卓译一稿中,语义上忠实于原文,译文中“thewave”,“willows”,“village”,“apricotflowers”,“settingsun”等再现了原文中的意象。通过“yearning”,“inmemoryof”,“listlessly”,“lone”,“grief”等词传递了原诗中诗人伤春的情感。“a lone village”说明主人公心情之孤寂;“the setting sun”表达了迟暮的凄凉与感伤;“yearning vast”,“in memory of the past”,让人看到佳人想起当年惜别之情景,同时感怀望穿秋水的深情,译文比较合适地再现了意美。译文基调与原诗一致。形式上也再现了原文的诗词结构,以诗译诗。
三、诗化翻译技巧
以总体审度的尺度衡量英译是否保持、再现或在多大的程度上保持、再现了原诗的节奏美、音韵美、形式美、风格美、情感美和意境美是可行的。[3]但是,原诗美学价值的保留与再现,并不是做好总体审度就可以了。还存在一个诗化的过程。诗歌是内容与形式结合最为紧密的一种形式,诗歌的翻译必须兼顾内容与形式,做到形神兼似。把汉诗译为英语的散文之后,译者还要面临如何将它诗化。这就需要从样式、节奏和押韵等方面进行探讨。请看卓译二稿:
Th’willows drooping,the waters vast,
The village lonely,far and wide the grass extends.
At sunset apricot flowers fall thick and fast.
Spring over in th’south,my heart grief o’er separationrends.
Duckweed all o’er Dingzhou,would he return ere my bloom spends?
相比于一稿译文,二稿译文在形式和押韵上做了很大的调整。原诗共三句,每句前后对仗,字数一致,为“三三、五五、七七”形式,体现了这首诗词的形式和节奏美。在二稿中,译者将译文修改为5行,将一稿中“The waves of yearning vast, Willows drooping in memoryofthepast”这两行合并为二稿中的一行“Th’willows drooping,the waters vast”,通过音节缩略,将“Th”代替“the”,译文中第四行也同样采取音节缩略法,以“o’er”代替“over”;英语的一些specific words(与general words相对)不但形象生动,而且十分简约,可供选择[4]。译者以“farand wide”,“thickand fast”这些具体形象的词汇来再现原文杨柳、杏花的意境美。此外,译者通过调序,使得所需音节落在韵脚的位置,如“far and wide the grass extends”将“far and wide”置前,“at sunset...”将“at sunset”置前,以此实现押韵,一、三押韵,二、四、五押韵。
再看译文三稿:
Th’willows drooping low,the waters of yearning vast,
The village lonely,far and wide the grass extends;
At sunset apricot flowers fall thick and fast.
Spring over in th’south,my heart grief o’er separation rends.
Duckweed all o’er Dingzhou,would he return ere my bloom spends?
三稿在二稿的基础上做了再次加工,主要体现在第一句诗词的英译上,原诗词中“波渺渺,柳依依”,勾勒出一幅一泓春水,烟波渺渺,岸边杨柳,柔条飘飘的江南暮春图。三稿将其译为“Th’willowsdroopinglow...”,与二稿的译文“Th’willows drooping,the waters vast”相比,增加了“low”和“yearning”这两个词汇。“low”字与原文基调一致,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暮春时杨柳的状态,“droopinglow”再现了杨柳依依不舍的画面感;“yearning”一词“渴望、向往”之意,“waters ofyearningvast”,再现一江春水的浩浩渺渺、水波延伸至很远很远的意境感。通过这些诗化翻译的深加工,译文不仅在内容上最大限度的还原了原诗的意象美、意境美,而且还巧妙地实现了形式的对等,使得第一行的音节与二、三行一致,同为6个音节,五六行同为7个音节,同时形成“ababb”押韵形式,与二稿中“4,6,6,7,7”的音节数相比,此稿进一步再现了节奏美,韵律美。
四、结语
翻译不易,翻译古诗词更是难中之难,翻译好一首古诗词,需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断地进行推敲,这就需要译者同时具备理解,感受原诗的能力,和驾驭英语的能力。理解原诗词是第一步,除了理解字面意思外,译者需要对原诗作者的思想、生平,作品的内容、形式、风格、类别、创作背景等等做深入细致考究,以便对作品的总意象、总情感及预期翻译本文的定位做到心中有数[5]。有了这些考究,才能在翻译时,做到内容上忠实于原文。古诗词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它的形式跟内容一样重要,这就要求译者在内容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以诗化的语言和风格来翻译原诗词。这就需要译者的“诗化加工”了,这包含了对译文音节的加工,节奏的加工,韵脚的加工,样式的加工等等。当然这些加工不是画蛇添足,而是忠于原文的基础上,进行的修改润色,决不能损害原意而为之。这些诗化加工是有技巧可寻的,可以通过音节处理、信息转移、调序、及使用具体词汇等方法来实现。因此在翻译一首古诗词时,译者首先需要进行一番细致的研究,按照总体审度的要求,把握全局,制定出恰当的翻译模式和策略,选择恰当的翻译技巧,做到不仅在语义、风格、意境上忠实于原文,也能在音节、韵律和节奏等形式上忠实于原文,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
[1]崔霞.译者的翻译过程探讨[D].中国海洋大学,2004.
[2][4]卓振英.汉诗英译的总体审度与诗化[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4).
[3][5]卓振英.汉诗英译论纲[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曾杭丽,1986.2-,女,浙江温岭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