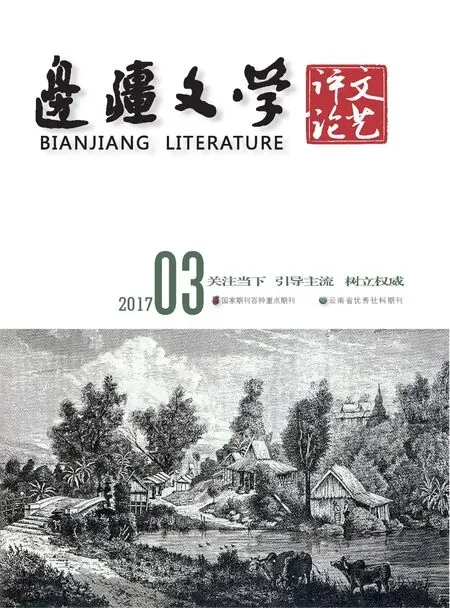诗是他的宗教
——评周良沛先生的《诗歌之敌》
陈中亮
诗是他的宗教——评周良沛先生的《诗歌之敌》
陈中亮
“诗人,真正的诗人,诗是他的宗教,是一生与之相依为命的精神之神。”(《诗歌之敌》)这位从革命战火中成长起来、在反右运动中遭遇二十年劳改的革命知识分子,依然表现出对诗一如初始的执着与痴情。春城的冬日,我有幸拜访了已经80多岁的周良沛先生,听他畅谈中国新诗的源流发展。在他侃侃不绝、爽朗洪亮的谈笑声中,我心中不由得蹦出了这样的两句话,这是周老自己一生与新诗结缘的自我写照。他一辈子写诗、评诗、编诗,为此青春飞扬慷慨悲歌,为此遭遇困顿身陷囹圄,为此仗义执言遭人白眼,却依然心如磁石,不指诗歌誓不休。这是一个真爱诗歌的人。
当诗歌评论集《诗歌之敌》拿到手上时,我感到了它的厚重。翻开书页,作者的诗情诗思,穿越历史的时光,扑面而来。在书中,作者对“朦胧诗”、“现代派”、“表现自我”、“扩张自我”、“危机与繁荣”、“诗与政治”、“新诗与传统”、“理想与标准”、“含蓄与晦涩”、“崛起的美学原则”等许多问题都做了具有个性的思考与答辩。它比较全面完整地体现了周先生对诗歌、诗坛的看法和态度,也展示了他从事诗歌创作多年来的心路历程。不管是专门的论述文章,还是诗集的序跋,作者都能秉着既有原则,又有包容的评论态度,尽力展示自己的诗歌观点。他特别强调:各种观点、理论的确立成形,常常是无法避免与其他异见的摩擦、对立、争辩和斗争,才得以丰富和强壮。任何一个真正的诗人,要写出像样的作品,即便不是那么自觉,也无法离开他民族、哲学、文化的基础。任何“配合政治”,远离文学自身特质的分行文字不可取,那些远离人间烟火之颓废、虚无的、纯以自慰的诗之梦呓,同样不可取。周先生在谈到新诗为新而新,误入歧途时,语重心长地强调:诗道有正有歧,有大道有小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出发的初衷。诗歌和文学传统是薪火相传的,传承绝非保守封步,恰是拓展开阔诗路的起点。坚持人生信仰,包括对诗的真诚,分清晦涩、含混、凌乱、恍惚,剔除非诗、伪诗、假诗、赝诗,诗歌才能大步前进。
对于诗歌,周先生历来主张:“诗就是诗”,认为诗最根本的就是思想与情感的结晶,是具有诗思之诗美,并具相应的艺术方式所表述之作品。虽然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诗歌他也有认同甚至欣赏,但他无疑偏向于现实主义诗歌。他的诗评和诗论都很强调现实主义。我们在看他评价戴望舒时,可以看出这样的偏向:“他写的全是亲身感受,诗人的文字功力表达了真情时,就闪出了艺术光彩,为了真情的表达,不论其表现手法掺有什么其他艺术流派的因素,也使他终于走向现实主义大道。”(《〈戴望舒诗集〉编后》)他的这段话在理论上当然有不确切处,因为,不管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都能表达真情,然而由此却能明显看出他是偏向现实主义的。这点,从他最欣赏聂鲁达一段话也可以看出:“诗人之敌,莫过于他自己没有与同时代的最被忽视、最受剥削的人们找到共同语言的能力。”“诗人不是‘小上帝’,决不是‘小上帝’。他并没有超越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之上的神秘命运。我过去常说,最杰出的诗人乃是每日供应我们面包的人,也就是我们身边的、不自诩为上帝的面包师。他们为了尽社会的义务,从事揉面、上炉、烘烤和每日送面包这样一些既崇高又卑微的工作。如果诗人有这种纯朴的觉悟,也就有可能把这种纯朴的觉悟组成一个其结构既简单又复杂的伟大的艺术品的一部分;这就是建设社会、改造人类生存的,为人们提供面包、真理、美酒、梦想……”总之,他认为,让诗歌和文学成为建设我们新生活的钢铁与面包,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国家与诗之根本的根本。
正因为秉持这样的观点,他的诗评就有了根基、有了筋骨,甚至有了烈度。敢于讲真话、讲正气,是周良沛诗论的一条主线与“文脉”。周良沛说: “我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即便它是有问题的、错误的,也不需要羞羞答答。只有毫无保留,像说知心话一样告诉大家,只有痛快淋漓地,像读宣言似的表达我的立场,才可能有自己的对诗的真诚。”他还说: “一说话,难免得罪一些人,得罪的可能还是朋友、好人。可是,闷着嘴也不行。”(《诗歌之敌》)因为有定见,所以有定力,才能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坚持自己认定的真理,敢讲无愧内心的真话,保持一份独有的清醒与超然,由此多了几分清奇,少了几分俗气。上个世纪80年代,在西方诗歌的影响下,“朦胧诗”“新潮诗”“现代派”“后现代”等流派异军突起,形成一时热潮。作为中国传统、中国气派诗歌的拥趸者,周先生甘触众怒,勇立潮头,他不否认诗歌需要含蓄,不能过于直白,口号式的政治诗歌他一向是反对的。但是当“朦胧”脱离了生活,脱离了大众,他冒着落伍的讥诮挺身而出,唱出老调:“生活本身,就是一条新诗的大道,拒人民的生活与斗争于新诗之外,要新诗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一句空话。当艺术只有一条‘崛起’之路,它也就当仁不让地取代了人民所要的百花齐放。这和当今现存的、人民生活的广阔天地之文化秩序背道而驰。”(《‘新的美学原则’之‘崛起’》)。面对成为个体梦呓般的喃喃私语的现代诗,他尖锐讽刺说: “别人看不懂你的东西,你向谁表现自己?若是自己表现给自己看,睡到被窝里表现好了,何必要写在稿纸上还想方设法发表呢?一赞成诗要写得让人看懂,有人就把明确与含蓄对立起来,把‘懂’作为‘假、大、空’的同义语,含蓄与朦胧又混为一谈,这不是胡搅蛮缠吗?”(《‘新的美学原则’之‘崛起’》)90年代,随着“告别革命”、“淡化意识形态”等观念在诗坛崛起,他坚持己见,不随时势,不愿将诗歌和政治对立起来。今天看来是常识,在当时却需要额外的勇气。周良沛指出: “你的‘美学原则’可以另撰历史,可历史却无法选择那‘美学原则’对历史的虚无。人们为此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愤激之情,显然是为如此推翻历史,篡改历史。新诗,乃至整个文学、文化,都是随着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运动的。”“‘淡化意识形态’的口号提出,恰恰是极其虚伪又特强烈的意识形态之所为,要别人‘淡化’,无非是便于他等的意识强化得以长驱直入。诗坛如此弊,正是‘新思维’治诗的恶果。”(《诗歌之敌》)在这些铮铮直言中,你可以不认同他的观点,但你很难否认他具有洞察力的。新时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精神领域的失落和沉沦越来越甚。被选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 2001 文选》中的《诗歌之敌》一文中,周先生批评了诗人的浮躁、趋利、非诗化、玩诗造假、虚无历史、稀奇古怪等诗歌之敌后,引用美国中情局的《中国十诫》中“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行,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指出一些诗人、诗论家这些年搅得诗坛乌烟瘴气的“消解崇高”、“不屑于表现丰功伟绩”等类似口号,与美国《十诫》“不是接轨得很好么”?除了露骨的诗之政治主张外,各种以假乱真的“主义”对广大读者之诗心伤害很深,“有什么问题会比非诗与反诗的问题更严重呢?”它就是“诗歌之敌”,“最危险之敌! ”这些论点,振聋发聩,并且具有现实性。
周先生写诗评,对“诗歌之敌”固然横眉冷对,就是对自己的师友,他也秉承公心,严把艺术之关。五十年代中期,他坐在编辑室里天南海北地论诗,“对诗友以至对诗界的前辈,也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如对艾青诗歌的评价,在给艾青的一封信中,他细致分析了艾青《春天》诗集的艺术成就,尤其是为《他睡了》和《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所作的辩解和分析,讲的是那样透彻和贴切,无疑触到了这些作品的独有神韵。同时,作者又坦率地指出艾青的诗也免不了“有些败笔”。这主要表现在“凑些应景之作,流于空泛的议论”。所谓“试验民歌的风格……正是服了某种理论给新诗开的药方的后果”。(《灵感的流云》)周先生一贯认为,一味恭维,“是葬送诗人的一副催命剂”。只知拔高、著文欺人,是缺乏文德的表现。写得诚实,褒贬适中,说得极为准确、科学,是周先生为作品写序跋的一个特色。
敢恨就敢爱。有人说:“良沛的诗评比诗好,为人比诗评更好。”这样的评价,非知己者不能道。新时期以来,为了中国新诗,他住在北京简陋的三人宿舍中,每天夹着包,奔走不息。为的是搜集已故诗人的作品、访谈故居亲友。寻找、编辑并出版胡也频烈士的遗诗,他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编戴望舒的诗,寻找被毁、被荒草埋没了的戴望舒坟地,他也不辞辛劳……青年诗人曲有源写诗笺给他,说“一个提包挟着你全部的友谊、思想、爱情、家产……”,他不以为苦,反而甘之如饴。为作品写序,作者也是本着为社会主义文学培养新人的精神进行评价,提携奖掖优秀的后来者。在“关系学”盛行的今天,有些诗坛新秀,需要有独到眼光的老前辈来发现,推重。周先生通过为其作品写序,培养了一批新人。当然,投机之辈的溜须拍马周先生也是清楚的。面对此文坛歪风,他旗帜鲜明:“不正之风猖獗时,正派的评论对一个没有门路的作者的支持,足以促进一个同志健康地走上文学道路,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所以,努力让正派的作家脱颖而出,不致埋没,是一个有良心的诗评家的职责所在。他这种乐为他人作嫁衣的精神,是有榜样的。他的老师严辰多次对他说过:“只要看到写诗的年轻人中有苗头走正路的,一定得给予支持,设法评介,尽力开拓点路子为他们出诗集。”(《严辰,一个严肃的诗人》) 周先生不仅是诗人、诗评家,同时还是著名的新诗选家。戴望舒、徐志摩、胡也频、闻一多、“七月”诗派等现代诗史上著名诗人和流派的诗集他都编选过。比较有名的还有《新诗选读111首》《抗战诗钞》等,这些新诗选,作者坚持不因人废诗、不因人论诗的态度,既选了许多名家的作品,也选了名字不够响亮的新人。这些作品,当然不能全面代表新诗的特色,但仍能窥见入选者的风格特色。附在每篇作品后面的评价文章,也可看出编选者的良苦用心和理论素养,它写得言简意赅,堪称出色的诗评短论。
当然,周先生的诗评也有短处。由于历来很重视诗歌的思想性,即使在他主要是强调诗歌要表现作者真实的主观感情的时候,也不忘记同时指出理性以至思辨因素的重要性。在相当一部分评论中,受制于时代和视野,未能从艺术和时代的高度,给出更高视野,更有说服力的恰当评价,又确实是存在的。具体来说,就是周先生对于政治与文学、政治与诗歌的关系,稍缺系统的理论瞰视。他一贯强调反对口号式的政治诗,也乐于看到“纯诗”。但是,在具体的评论中,他过于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对诗歌的匡正,而对于政治将诗歌功利化的一面警惕不足。其实,政治对于文学的过分干涉,是新时期诗歌有脱离政治倾向的前因。大量直白的政治诗歌,由于缺乏作者真实的情感体验,流于口号化、程式化,为后来者所诟病。普列汉诺夫指出:“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注意到艺术,自然就总是偏重于采取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它为了本身的利益而使一切意识形态都为它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服务。”不了解此前因,就不能对诗歌与政治的龃龉产生历史性同情。新时期以来,国家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了将文学工具化的政策,也是考虑到了文学本身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然,政治是诗歌的重要内容,这是常识。诗人,一切文人,是站在时代前面的人。民间的痛苦,社会的窳败,道德的虚伪,没有人比文学家更早、更深刻的感觉到。文学家永远是民众的非正式代表,不自觉的代表民众的切身的苦痛与快乐、情思与倾向。在此意义上来说,即使表现政治,也意味着文学中的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不是高度重合的。它具有特定的民间性、时代性。这点,周先生在评论时也没有强调。其实,任何遵命文学都不是好文学,文学家不接受谁的命令,但是要遵从内心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当然,这些问题周先生在不同地方以不同方式都提到过,只是由于多是短篇,浅尝辄止,没有深入讨论,未免让人遗憾。

杨瑞洪 黄河No.1 180×180cm 布面油画 2012
总体而论,周先生论诗,确实颇见艺术眼力,品评臧否,多有独到之处。他写的诗评,与人论辩者,从不跟风,不计毁誉,离弃平庸,坚持知识分子的良知。所写的短篇评论,常常能娓娓道来,亲切,自然,有独特的欣赏品位和人生体验。加上他熟知诗坛掌故趣事,常能增添别人没有的历史真实与沧桑感,读来比较舒服。
(作者系文学博士、讲师)
责任编辑:万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