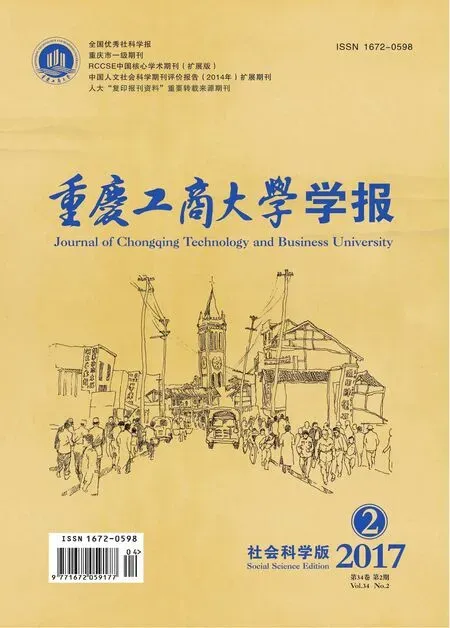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引导下的贪贿类司法解释评析及完善
陈 伟,石 莹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1120)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引导下的贪贿类司法解释评析及完善
陈 伟,石 莹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1120)
刑事政策催生刑事立法的问世,不同时期的刑事立法也是顺应刑事政策的结果呈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是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又是评判立法科学和司法公道的标尺,在该刑事政策的映照之下,贪贿类犯罪的司法解释,既彰显远见卓识,又难掩其瑕疵缺憾可能致使刑事司法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基于现存问题和法治化思维,需要从体系化视角出发提高法律运用的协同性,严格把控量刑情节,合理适用终身监禁制度,引入保安处分措施等,实现司法解释的效益最大化,达到公正处罚贪污、贿赂犯罪的价值目标。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解释;刑法;量刑
市场经济的逐利性,使得传统经济模式下长期受抑制的个体欲望得以强化,贪污、贿赂犯罪日益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之一。近年来,腐败犯罪呈现高发态势,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我国已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确立为反腐败的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会议上强调,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地将腐败斗争进行到底。[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律解释》)虽在千呼万唤中落下帷幕并正式实施,但绝非尽善尽美。通过对《法律解释》的整体梳理,针对现有疏漏,在刑事政策的引领下,探求解决对策,已然成为刑事法律妥善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有效路径。
一、《法律解释》与刑事政策及现实国情的内在暗合
《法律解释》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与遵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又是《法律解释》的指导性原则,发挥高屋建瓴的作用。成文法自颁布之日,就滞后于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针对愈演愈烈的犯罪态势,司法实践难免束手无策,贪污贿赂类刑事法律的具体适用亟需权威部门出台文件作统一引导,《法律解释》应运而生。
(一)《法律解释》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与遵守
1.人道情怀彰显刑罚的宽厚仁慈
首先,贪污、受贿犯罪中入罪门槛提高,《法律解释》生效之前,个人贪污数额五千元以上即可入刑,个人受贿数额达到五千元以上,即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随着最新司法解释的生效,贪污、受贿行为的入罪标准提升,虽然与经济发展速度及货币通货膨胀率有诸多关联,但是大批犯罪分子因尚未达到刑事处罚的标准,在刑法谦抑的退让下免受牢狱之苦,在纪律处分下弃恶从善,幡然醒悟,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体现了刑罚对于触犯微故细过者的宽宥仁慈。
其次,为鼓励犯罪分子如实供述罪行、悔过自新,对于贪污、受贿数额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影响极其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本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如有坦白、自首、立功、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损害发生等情节,可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留其一条生路,彰显刑罚的人道主义情怀。发挥这些情节在限制死刑方面的作用,不仅契合罪刑法定原则,而且有利于犯罪分子与司法机关积极配合,从而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和国家财产的损耗。
再次,《法律解释》第十四条规定,行贿人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中的“重大案件”是指“已经或可能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的。”“重大案件”一词在现行刑法中适用频率极少,仅在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中出现一次。又在对刑法第六十八条中“重大立功”的司法解释,即《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惊鸿再现。虽然两处表述完全相同,但含义却并非如出一辙。犯罪分子重大立功的表现之一“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这里的“重大案件”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或者……等情形”,相比之下,行贿人减轻或免除处罚中“重大案件”的标准较低,体现了对因行贿而误入歧途者的网开一面。
最后,《法律解释》中关于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范围较为广泛,不仅包括简单纯粹的“主动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重大案件线索”,而且包括间接的“虽不属于重大案件的线索,但对于重大案件的侦破有重要作用的线索”,还包括“主动交代的行贿事实,对于重大案件和证据收集、追逃、追赃有重要作用”。扩大对主动交代行贿事实的不法分子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范围,给因行贿而触犯法律者增添改过自新的机会。
2.“从严从重”昭示《法律解释》的严惩不贷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原有的社会模式被逐渐解构,传统的“差序格局”模式已悄然变化,*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认为,传统中国的人际关系如同水面上泛开的涟漪一般,由自己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亲疏关系永远很明确,只有离中心最近的家庭成员才可能密切生活在一起,相互之间产生一定的权利义务。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6-27.离中心较远的非家庭成员之间也会发生某种程度的联络,逢年过节时献礼表达心意也属人之常情。如何对日常生活中的礼尚往来与贿赂犯罪中的“收”和“受”作出合乎常理的划分、机关单位中“感情投资”与不法行为间如何合理界定以及如何判定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这些都是司法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难题。
对此,《法律解释》做出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管理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以“三万元”为明确标准,作为区分日常往来与贿赂犯罪的界标。礼节性的馈赠和犯罪行为的界限,应当考虑公务人员与赠予人的关系、社会地位、财产价值等,最终以社会一般观念加以认定,在超过此界限时,即便是以中元、岁暮等名义赠予的,也是贿赂。[2]反之,和职权毫无关联的赠予行为并不是贿赂。
对于所谓的“感情投资”,只要超出正常的社交礼仪范围,推定与其职务存在对价关系,特定主体接收时即成立受贿罪的既遂,而无须查明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或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者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其将来实施的职务行为,有被置于先前行为的影响之下,从而有损害职务行为公正性的现实危险,不仅使得普通民众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将来能否公正履行职务产生怀疑,而且也会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整体,即政府本身的信赖大打折扣,因此将超出社交礼仪范围的“感情投资”作为犯罪处理有其必然的正当性。职务关联性的有无,亦是区分正常社交礼仪范围内的馈赠与贿赂犯罪的关键。
又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时并未承诺为他人谋取私利,但事前答应他人请求,并做出允诺;行贿者在送礼时未曾明确提出请求,但以其他方式做出暗示;履职时并未请托,但事后却基于此种事由收受他人财物,且达到定罪标准,对于上述情形中国家工作人员的主观心态,《法律解释》做出明确回应。*《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由”、“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履职事由收受财物”应当认定为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评判标准。再如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晓真相之后,没有及时退还或上交,亦认定其主观上具有受贿故意。
再如,纵观《法律解释》中关于挪用公款罪的规定,挪用公款罪分为如下行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超过三个月未归还”。相比之下,前者的入刑数额标准明显低于后者;而关于挪用公款罪量刑时“情节严重”的衡量尺度,前者则更为严密,后者与前者相比,采取减半标准,体现了法律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进行非法活动行为的严加惩处,决不姑息纵容。另外,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收受他人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假公济私,如同时构成受贿罪和渎职类犯罪的,《法律解释》规定对其数罪并罚。
(二)《法律解释》因现实的司法困境应运而生
1.鉴于法律适用的严峻形势
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司法实践存在主刑与数额不成比例、针对部分犯罪者将不法财产用于捐赠或公务支出的裁判有失公正等问题,由于司法对社会百态具有公正评判的作用,这些严峻形势有待新的解释予以纾解。
(1)所判刑期与犯罪数额不成比例
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正式实施,对于贪污、受贿犯罪的惩处分为“数额较大或有其他较重情节”“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三个档次,一改往昔以单一数额为主要衡量尺度的惯常做法,运用“数额”加“情节”的双重标准对贪污犯罪者的性质恶劣程度加以评判。但是标准过于笼统,导致司法实践中不同案件判决结果却不约而同,或类似案件最终裁判却大相径庭的混乱局面。
综观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关于贪污受贿的案件,无论是同一量刑幅度还是不同量刑幅度内的犯罪数额与所判刑期并不呈任何比例关系。贪污、受贿犯罪均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是一种非物质性法益,国家工作人员非法获取财物数额的多少恰切体现了权钱交易的实际程度。[3]在具体的司法操作中,过高的数额标准,无法有效打击犯罪,亦不能准确体现贪污、贿赂犯罪的本质危害,如果入罪数额标准过低,又难以对危害程度不同的行为作出区分。虽然数额不能作为量刑时的唯一标准,但在犯罪主体同属国家工作人员,均不存在其他量刑情节时,犯罪数额与主刑刑期缺少逻辑关联,则暴露出在案件裁判环节中,主刑判处的随意性,判决结果无法做到公正平允,也难以使民众信服。
(2)将不法财产用于捐赠或公务的裁判有失公正
某些贪污受贿者在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敛取财物之后,为了回赎内心的罪恶,将部分财物捐赠,或是听到纪委部门的风吹草动,立即将赃款赃物用于单位公务开支或者捐献给贫困山区,这样的情景在司法实践中数见不鲜。有的司法机关鉴于犯罪者将赃款用于单位公务开支,就不追究其刑事责任,有些地区将捐献的款项予以扣除,判处犯罪分子轻刑,甚至缓刑,使此类据心不良的贪财利己者,抱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而屡屡得逞。
如原湖南省新田县教育局局长文建茂收受他人贿赂,但是将其中的部分钱财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二审法院在认定捐赠款可以抵扣受贿款、收受相关单位礼金属于人情往来的情况下,改判文建茂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国家工作人员一旦实施利用职务便利非法聚敛钱财或者向他人索取贿赂的行为,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及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即蒙受损失,若是仅仅因为尚未将这些款项挪走私用,就不定罪处罚,法律的公平正义将无安身立命之处。将未曾挪走私用的部分予以扣除亦于法无据,长此以往将会成为贪污受贿犯罪分子逃避法律追究的一种遁词。
2.司法解释对贪贿类犯罪引领之体现
《法律解释》呼应了司法实践的恰切需要,聚焦于“数额”和“情节”是本次司法解释的显著特征。运用双重标准定罪量刑、确定贪污、贿赂犯罪新的入罪数额标准以及不法财物排除私用不影响定罪,量刑时可酌情等是《法律解释》引人注目的亮点。
(1)运用“数额”和“情节”双重标准定罪量刑
面临“数额”与“情节”在实践操作中的纠葛,《法律解释》采取“两套标准”“三个档次”。标准之一为“数额标准”,分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三个层级,依次由轻至重配置三档法定刑。标准之二为“情节标准”,或“情节+数额标准”,区分为“其他较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三个档次,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配置轻重有序的法定刑。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对犯罪数额和案件情节方面的内容进行积极调整,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实现刑事法律的与时俱进以及刑罚与社会发展、社会秩序维护间的协调一致。
在“数额+情节”模式下,如果犯罪人的行为契合《法律解释》第一条中“其他较重情节”的规定,则大体上犯罪数额采取减半标准予以适用,从而使得除“数额”外的“情节”成为影响定罪量刑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数额标准与情节标准(或“情节+数额”标准)是并行不悖、彼此独立的两套衡量体系,形成互补关系且均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另外,此处的“数额减半适用标准”与两高《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确定盗窃罪“数额较大”的标准不谋而合,符合刑法体系性思维。如果没有统一标准,不同地域的法律工作者在司法实践中难免畏首畏尾,甚至停滞不前。双重标准模式的运行不仅使司法工作者有法可依,而且给予其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够满足司法实践复杂现实的需要。
(2)贪贿财物排除己用不影响定罪,量刑时可酌情
贪污、贿赂犯罪的行为人一旦实施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攫取公私财物的贪占行为或索取、收受请托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承诺谋取利益的行为,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私财产所有权被侵害的后果就不可逆转,犯罪形态也即完成。贪污贿赂犯罪属于结果犯,法定的犯罪结果发生即为犯罪既遂,一旦行为人将公私财物的控制权转移就构成犯罪,而不论之后用于自我消费抑或其他用途。行为人捐献贪占的财物或改变收受财物的用途都是犯罪的后续行为,不会改变贪污、贿赂犯罪的性质,也不应与其他构成要件一并予以评价。
《法律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将赃款赃物用于单位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的,不影响贪污罪、受贿罪的认定,但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将非私用部分予以扣除会给职务犯罪的侦查活动带来诸多不便,也会使犯罪人心存幻想,即将赃款赃物用于符合“常理”的用途便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在这种心理预期的支配下,行为人一旦发现情势不妙,只要制造出用于“合理”场合的假象即可免于刑罚制裁,难免给犯罪分子预留脱罪空间并助长其犯罪动机。综观我国对盗窃罪中赃物的处理,无关犯罪构成要件,不影响罪名的成立。依此类推,将贪贿赃款用于公务支出,只是犯罪既遂后赃款去向的一种,无论行为人如何处理赃物都不能改变犯罪行为已经完成、法定结果已经形成、法益已被侵害的事实。
二、反思两高最新贪贿类司法解释的瑕疵
在反腐政策的高压态势以及刑事立法紧紧跟进的双重作用下,我国反腐败工作卓有成效,全球清廉指数由2014年的第一百名升至2015年的第八十三名。*全球清廉指数由“透明国际”发布,“透明国际”作为当今世界上重要的国家腐败状况主观评价组织之一,是专门致力于反腐败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每年均发布“清廉指数”。调查按受访者对某国家或地区廉洁程度的观感评分,包括政府惩治贪官的力度、社会贿赂的普遍性,及市民对公共部门问责的能力等,一百分为满分。参见刘仁文.贪污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3最新出台的《法律解释》对司法实践中的已有问题做出部分解决,但尚有不足之处需加以完善。
(一)“坦白”“退赃”等量刑情节适用紊乱
纵观王昭耀受贿被判死缓案、徐国健受贿被判死缓案、李纪周受贿被判死缓案、王华元受贿被判死缓案等涉案数额近千万元的重大受贿案件,卖官鬻爵程度之严重,受贿时间之长久、种类之繁多实属罕见,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理由无非是能够坦白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全部退赃或赃款被全部追缴。而审视李培英贪污、受贿案件,其归案之后,如实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主要犯罪事实,并未当庭推翻供述,所涉受贿款项虽然数额巨大,但并未造成特别重大的经济损失,其近亲属已代为退缴全部受贿赃款,犯罪情节并非特别严重,却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法律必须靠原则的公正及国民对它感兴趣才能获得支持。”[4]面对相差无几的情节,判决却是如此悬殊,量刑情节适用混乱,有损法律的公正平等。一般认为,自首制度在贿赂犯罪中的应然作用在于分化、瓦解行贿和受贿的利益共同体,从而使二者之前建立的信任关系不攻自破。自首制度也是衡量犯罪人认罪悔罪的重要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虽然腐败分子主动投案率较低,但司法实践中却存在自首认定率高的现象,贪污、贿赂犯罪者不是主动自首,而是“被自首”。
贪污贿赂犯罪的死刑适用存在令人瞠目结舌的宽严失据,“坦白”+“悔罪”+“退赃”成为高官名副其实的免死路线,“数额特别巨大”沦为吓唬鸟雀的“稻草人”。[5]司法实践中相当部分腐败犯罪案件是在纪检监察机关“两规”后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但对于两规期间如实供述罪行能否被视为自首的问题,《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坚决否定。*“两高”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指出:“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讯问、采取调查措施或强制措施期间,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针对的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司法实践中对“自首”的认定大打折扣,法律的宽容并非无止境的容忍,宽容亦有其自身的边界和底线。
(二)追诉时效制度使诸多犯罪者遁于无形
根据《法律解释》的规定,贪污或受贿金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如果没有其他情节,依法应当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贪污或受贿金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没有其他量刑情节,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结合刑法总则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即犯罪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下,若没有其他加重量刑情节,距今已超过五年,公安机关将不再追诉。贪污或受贿金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也无其他加重量刑情节,若距今已逾十年,之前的罪行也被免予追诉。在《刑法修正案(九)》生效之前,根据原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追诉时效为十年;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追诉时效为二十年。
贝卡里亚认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6]对于曾经犯下的罪行,仅仅因为司法解释的出台而不再追究,将有损刑法长久建立的威严。基于此,对犯罪分子触犯法律的恶行,绝不能因追诉时效的限制而听之任之,放任自流。
(三)终身监禁制度有失合理
《法律解释》第四条第三款规定“符合第一款情形的,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裁判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至此,我国出现三种最为严厉的刑罚措施:死刑立即执行、普通死刑缓期执行、死刑缓期执行且终身监禁。从特殊预防的角度观之,死刑立即执行和终身监禁均属于永久隔离排害的、根除犯罪条件的严厉措施。终身监禁制度不仅完全堵塞犯罪人回归有期徒刑的自新之路,而且经不起人道主义的拷问。对于被告人立功的行为不予褒奖,不但会使其负隅顽抗,而且不利于深挖犯罪、追查余犯,对被告人和国家而言都毫无益处。
终身监禁所彰显的报应与预防的刑罚功能不容置疑,我国刑罚的特殊预防主要体现在改造、消灭肉体、剥夺犯罪条件三个方面,对于贪污贿赂者动用特殊预防措施价值不大,且有重刑主义倾向。而对极端主义犯罪、暴力袭击犯罪者实施终身监禁则更为可取,如昆明火车站“3·1”严重暴力恐怖犯罪案件的极端暴恐分子,设立此项制度,让其“把牢底坐穿”,给其他同类犯罪者以警示。根据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所做的一项调查可知,重刑犯被关押 15 年之后,其基本上已经丧失再犯可能性,刑罚的特殊预防功效已基本实现,*2004年年初,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对北京市在押的3426名重新犯罪的罪犯(截至2003年12月31日)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从上一次所判刑罚来看,被判刑10年以下的占总数的89.4%,被判刑10年以上的占总数的10.6%。参见:北京市监狱管理局“重新犯罪”课题组.北京市在押犯重新犯罪情况的调查分析[J].中国司法,2005(6):23.因此,仅因身份的特殊性,对贪污、贿赂犯罪者适用终身监禁制度且不得减刑假释有失合理。
现代刑事政策原理主张,刑事政策必须以人为本,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满足和解决人的需要,尊重人性尊严,促进人的发展,注重人权保障,实现刑事政策的人文关怀。[7]学者赵秉志、袁彬认为终身监禁制度本身存在着不人道、不公平、剥夺罪犯改造计划和浪费司法资源的缺陷,[8]学者张明楷教授认为终身监禁制度严重背离以教育改造为目的现代刑罚价值观,不应该成为死刑的替代刑。[9]终身监禁制度可能使犯罪者丧失对未来生活的希冀,增加犯罪人与国家和社会的对立,在高墙之下得过且过,惹是生非,或是惶惶不可终日,给监狱管教工作徒增困扰。
终身监禁制度有违刑法总则第五十条、第八十一条中“不得减刑、假释”的规定,刑法总则中并未明文规定“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腐败犯罪者,限制减刑”,因此终身监禁制度的设立难免有过于草率之嫌。减刑假释作为服刑人员的一种正常期待,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才能使其更好地融入社会。终身监禁制度的设立严重侵蚀司法正义的主题,被终身监禁者在无期徒刑执行期间因重大立功而具有“可以”甚至“应当”获得减刑的权利。
(四)体系性矛盾有待商榷
体系性思维强调组成法律体系的各类法律以及同一部法律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应当排列有序,在内容上做到协调一致,在目的上理应相互配合。《法律解释》在体系上、全局上存在考量欠妥的情形。
1.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二者呈现宽严失衡
《法律解释》第十一条规定“职务侵占罪中‘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受贿罪、贪污罪相对应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五倍执行。”那么职务侵占罪中“数额较大”的标准为“六万至四十万元”,“数额巨大”的标准为“一百至一千五百万元”,即职务侵占若不足六万元,则因未曾达到刑法的制裁标准,不会受到法律追究,职务侵占近百万元人民币,则最高判处五年有期徒刑,职务侵占的存在入罪标准过高的嫌疑,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综观《两高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盗窃入罪数额与量刑标准的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依次为“1 000元至3 000元以上”“3万元至10万元以上”“30万元至50万元以上”。因此,在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都无其他酌定情形时,盗窃一千元即可入刑,而职务侵占罪的入罪标准是六万元人民币;盗窃三万元可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盗窃三十万可能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职务侵占一百万元有可能仅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职务侵占罪和盗窃罪的关键区分在于行为人是否利用职务之便,公司、企业或单位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便利,将财物据有己有,定职务侵占罪。“法者,公天下持平之器。”[10]职务侵占和盗窃罪的数额标准明显存在不公,盗窃微小财物即可入刑,非法占有巨额公共财产,尚才入罪。从动用刑罚制裁的角度考量,职务侵占罪的入罪标准是盗窃罪的近六十倍。职务侵占的入罪门槛提高,岂不是给工作人员利用身份之便私吞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财物网开一面?
2.行贿罪和受贿罪之间的矛盾难以协调
(1)法定刑配置不合理
根据《法律解释》第七条的规定,行贿数额达到三万元的标准,或在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且具有特定情形,即可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依此类推,行贿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或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但具有特定情节,即可被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行贿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或二百五十万元不满五百万元,具有特定情节者,即可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相比之下,受贿罪与行贿罪的起点数额均为三万元,或特定情节下的“一万元至三万元”,但是行贿罪的最低量刑档次的最高刑罚为五年有期徒刑,受贿罪却仅为三年有期徒刑。如果没有其他量刑情节,行贿数额达到一百万元人民币即可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受贿满一百万元,则有可能只被判处三年徒刑;行贿数额满五十万元且具有特定情节,即可被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受贿满五十万元,尚且只判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行贿与受贿之间存在量刑不均衡的嫌疑。
贝卡里亚认为,犯罪行为的阶梯应该和刑罚的阶梯相符合,[11]根据罪行的恶劣程度配置轻重有别的刑罚标准。行贿罪和受贿罪互为对合犯,但二者犯罪数额与量刑标准之间却存在极大的不协调,犯罪数额作为行贿罪和受贿罪量刑时重要的参考标准,前者侵犯的法益为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而后者侵犯的法益为职务行为廉洁性和公私财产所有权,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要远远大于行贿罪,但面临同样的犯罪数额,行贿人可能较受贿人判处更为严重的处罚,依此看来,两罪的法定刑配置显得荒谬而不合常情。
(2)对情节的解释不利于查处对合犯
《法律解释》对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中行贿人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做出特殊规定,其中对“重大案件”和“对侦破案件起关键作用”界定较为严苛,“重大案件”在刑罚方面的衡量标准为“已经可能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另外,即使行贿人在被追诉前如实交代且犯罪较轻,对重大案件的侦破有关键作用属重大立功行为,也只是“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司法解释做出较为严厉的规定,行贿人若想获得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评判标准将会更为复杂,其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概率将会降低。
司法实践中大量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查处,依赖行贿人的投案自首,基于功利主义的价值考量,行贿人选择主动归案,是为谋求内心的踏实及刑罚的宽宥,而后者在风险与收益的衡量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贪污贿赂犯罪手段较为隐秘,且犯罪人之间利益关联密切,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信任基础,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出卖盟友。倘若不从犯罪人中寻找突破口,则很难获得确凿的证据,给司法机关查处案件徒增困难。今非昔比,对行贿人的减轻、免除情节做出如此苛刻的要求,难免会使许多愿意自动投案以求得刑罚宽宥的行贿者,面对即将到来的严厉惩处踌躇不前、望而却步,也使大量的受贿犯罪者侥幸脱于法网之外。
三、以刑事政策为导向对贪贿解释予以完善
社会日趋发展,刑法自应因势而变,但应在多大程度上回应变迁,又与刑事政策自然关联。“法律有时入睡,但决不死亡”。认为刑法典可以毫无遗漏,是荒唐的幻想,希望刑法典做到毫无缺憾,是苛刻的要求,承认刑法必有疏忽,才是明智的观点。[12]
(一)严格把控“自首”“退赃”等量刑情节
自由裁量权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将其限制在何种程度为宜的抉择。[13]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推行,以及刑法理论发展与实务界需求的变化,酌定量刑情节发挥着日渐重要的作用。
面对司法实践中各地法官对量刑情节评判不一的情况,可以选择将部分酌定量刑情节在刑法总则中法定化。如实供述、真诚悔罪、积极退赃等酌定量刑情节具有普适性,并非仅存于贪污受贿等少数个罪中,在侵财类犯罪、渎职类犯罪中也有体现,因而在分则个罪中规定酌定量刑情节既不合理,也无必要,可在刑法总则中以原则性或指导性的语句说明酌定量刑情节的作用。纵观刑法演进的历史可以发现,人们对量刑情节的认识和应用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粗到细、从少到多、由酌定向法定的渐进过程。[14]随着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发展,必然还会有更多酌定量刑情节被法定化。
可以把刑法典中的量刑情节看成是条随时有活水注入的溪流,已经存在但不合时宜的量刑情节,大自然会自动涤除,符合实践所需的新型情节如同源头活水般不断流入,从而实现整条溪流的空明澄澈。为了使量刑越来越公正和精细,司法工作人员在具体量刑时应写明退赃的具体情形,并尽可能找被害人或被害单位加以核实。另外,自首、坦白的时间早晚对于量刑也有重要的参考作用,犯罪分子尽早自首、坦白对于节省办案成本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因此,犯罪分子自首、坦白的时间早晚在量刑时也须适当考虑。
(二)引入保安处分,纾解追诉时效带来的隐忧
成文法律在一定时期内理应保持稳定,若是朝令夕改,将使普通民众感到无所适从。但是作为上层建筑,必然需要应时而变,在新法和旧法之间不可避免存在不被处罚的边缘地带,这亦是修法的代价。因为《法律解释》的出台,贪污、贿赂犯罪的入罪标准陡然增加数倍,综观司法实践,亦有诸多案件被判处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如何对曾经犯下的仅因新法出台就免予处罚的罪行合理惩处,做到法律的平止如水,也是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
我国《公务员法》虽然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务员,但是因为《法律解释》的横空出世,诸多触犯贪污、贿赂类犯罪的人员在其庇佑下免罪亦免刑,公务人员的任职标准对其并不适用。非刑事法律中类似于资格刑的规定,其实是“行资格刑之实,却无资格刑之名”。对基本权利的剥夺只能通过刑罚手段实现,刑罚只能通过法院的审判程序适用,在法院判决并未判处犯罪人资格刑的情况下,却以其他法律为名剥夺犯罪人的基本权利,实乃越俎代庖。在此可以考虑引入保安处分措施,使腐败犯罪者在一定时期内被隔离于可以运用职权贪占钱财的环境之外。
“保安处分”在《刑法修正案(九)》“职业禁止”中已有规定,*在第三十七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七条之一:“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职业禁止”在德国刑法中是指对那些滥用职业或行业、或者严重违反有关义务做出违法行为而被判处刑罚者,如其继续从事某一职业或行业部门的业务仍会引起违法行为危险的行为人,在一定期间或永久性禁止其从事某种职业或行业。[15]我国对免于刑事制裁的贪污、贿赂犯罪者,可以适当增设并合理运用腐败犯罪的资格刑,限制其一段时期内不得享有担任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利,来打击因为修法而逃脱法律制裁者。
首先,增设部分腐败犯罪尤其是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主要罪名的资格刑,明确规定对此类犯罪者可以单独或附加适用;其次,完善资格刑的内容,资格刑在我国现行刑法典中主要为剥夺政治权利,其中包括剥夺“担任国家机关职务”和“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在当前我国反腐败的严峻形势下,此种职务限定显得弱不禁风,应当考虑增设新的内容,诸如剥夺从事特定职业的权利,以及剥夺犯罪单位荣誉称号、一定期限内从业资格、限其停业整顿、宣告刑事破产等。[16]再次,也有必要实行资格刑分立制,规定此类刑种可以分解适用,即根据惩罚和预防犯罪的需要,剥夺罪犯一项或多项资格。最后,也有必要规定对于犯罪者可以单处或并处资格刑。[17]发挥资格刑在预防犯罪方面的特殊作用,使企图违法犯罪者因利益得失的考虑,谨慎行事。
(三)改良终身监禁制度
《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强调在惩治受贿案件时应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即根据刑法关于受贿罪的有关规定和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惩处少数,教育多数。现代刑罚不能重蹈重刑苛责的覆辙。虽然终身监禁制度的设立有诸多缺陷,但其已尘埃落定且成为整个刑事法律躯体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改良。立足国情,贯彻刑法的谦抑化思想,只有对极少数无法矫正、不堪改造的罪犯,才能切断其重归社会之路。
终身监禁与死刑立即执行的残酷性相当,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废除一种残酷刑罚的同时,增设另一种残酷程度相当的处遇,就意味着刑罚永远不能或者难以轻缓,不符合刑罚的发展趋势。[18]对于终身监禁的适用范围应当严格控制。
毋庸置疑,轻刑化是世界刑法发展的潮流,也是整个社会摆脱重刑束缚的折射,我国刑法理应顺势而行。美国司法控制死刑的模式,在立法保留死刑的条件下,加强对死刑的司法控制是减少死刑适用的有效途径。[19]依此类推,通过刑法的合理解释,在司法上寻求严格控制终身监禁制度的适用从而达到降低此种酷刑的适用频率是现实可行的选择和较为优化的路径。
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量刑“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仅有原则性的提示作用,具体操作还需要发挥司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由裁量权。《法律解释》第四条第三款中“犯罪情节等情况”太过抽象缺乏具体的衡量标准,在具体适用时极易掺入办案人员的主观判断,由于个人价值观、法律思维等方面的不同,这种主观评判难免存在差池,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犯罪情节等情况”的标准应从紧控制,对不是必须适用终身监禁制度的应当放宽标准,通过严格司法将此种极严酷刑罚的适用限制到极少数。[20]对贪污、贿赂犯罪者适用终身监禁的条件进行统一把握是司法控制的关键点,确保同类型的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在案件裁量时起到相同的量刑效果,只有对此种重刑的适用条件达成共识,才能制定统一适用的裁量规则,达到司法控制的目的,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兼优的公众期待。
(四)增设妥当举措,弥合法律之间的罅隙
1.适用“从一重罚”,缓和职务侵占与盗窃罪之间的冲突
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的差别在于主体、犯罪对象、是否“利用职务之便”方面存在差异,与盗窃罪相比,职务侵占罪存在更高的入罪门槛与更低的处罚刑期,但是两者都存在“非法侵吞公私财物”的客观行为,难免会出现竞合的可能。因此,对于非法侵占本公司、本企业、本单位财物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亦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当两种行为竞合时,因先因行为的不法性导致职务权源存在瑕疵,即便实行阶段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亦完全有可能成立其他类型的财产性犯罪。在对职务侵占罪理解适用的同时,对经济组织与其员工间的信赖利益予以保护也是题中之意,理应引起足够重视。因此,为了避免“监守自盗”情形的猖獗,可以规定如果同一行为符合职务侵占罪的特征,但同时契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选择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量刑,以实现罪刑均衡。
在日趋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对经济组织信赖法益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比财产法益更为迫切,因此对于“监守自盗”的行为,能否按照一般法条进行处置,司法实践中尚存争议。张明楷教授认为应当按照普通法条进行评价,刑法分则中存在特别法条原本应科处重刑实际上却规定轻刑的现象,所以不能照搬法条竞合原则,如果绝对地采取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适用标准,就会造成罪刑不均,因此,只要刑法没有禁止适用重法条,就应按照重法条优于轻法条的原则定罪量刑。[21]如对于诈骗犯罪如果没有达到金融诈骗的犯罪标准,则按照一般诈骗处理,此种类似规定,在我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中亦再现,佐证了在两种罪名竞合时,如果重罪处罚较轻,则按轻罪的重处罚论处的存在价值。
2.引入“囚徒困境”,构建行贿罪与受贿罪二者处罚的平衡
从刑事法律和司法实践可以看出,我国一贯坚持非对称性的刑事政策,即宽恕行贿,严惩受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和第八条的规定,特别自首制度的重点在于通过减轻对行贿行为的处罚以换取行贿行为人对受贿行为人的揭发,从而打击受贿行为。而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罪量(犯罪严重性程度)与刑量(法定刑严厉程度)是一致的,而行贿罪的刑量相对于其罪量是偏重的,显然不利于行贿者坦白犯罪事实。
行贿和受贿属密室犯罪,法律应当奖励行贿者,以打破事先构建的利益共同体。可根据“囚徒困境”*在著名的“囚徒困境”模型中,警方逮捕甲、乙两名犯罪嫌疑人,但无足够的证据证实二人入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分别和二人见面,并要求嫌疑犯检举对方。此时,两名嫌疑犯面临如下选择:若一人认罪并作证指控对方,而对方沉默,此人将被释放,沉默者将被判处10年监禁;若二人都保持沉默,则二人都将被判1年监禁;若二人都互相检举,则都将被判处8年监禁。两名囚徒若彼此合作,坚不吐实,可为全体带来最佳利益,但在资讯不明的情况下,出卖同伙可使自己缩短刑期,也因为同伙把自己招出来会为他带来利益,所以彼此出卖虽然违反最佳共同利益,但反而是自己最大利益之所在,坦白是任何一个犯罪嫌疑人的最佳选择。参见:曼昆.经济学原理[M].梁小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社,2009:78.模型重新设置行贿罪的特别自首制度,将刑法第三百九十条行贿人特别自首制度中“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改为“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不以犯罪论处”或“不追究刑事责任”,从而置贿赂者于囚徒困境,之前的信任关系亦不复存在。在犯罪行为实施之前,公职人员不敢轻易收受贿赂,行贿者即送贿无门;在犯罪行为达成之后,行贿者因担心身陷囹圄,会主动坦白罪行,使得贿赂犯罪案件数大大降低,受刑事追诉的概率亦随之提高,在实现公职人员不敢受贿的同时又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诚如柏拉图所言:“不管为着好事还是坏事,都不应当接受礼物”。[22]在《法律解释》中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既包括明示的行为,也容纳暗示的承诺。实际上,受贿罪中无论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还是“为他人谋取利益”等构成要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证明收受或索取财物与职务行为的对价关系。[23]“为他人谋取利益”之规定,徒增司法认定的难度,浪费大量的司法资源,应当予以取消。因此基于司法实践的高效便利角度考量,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就其职务行为索取或收受的财物,不是其依法应当取得的利益,就是其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侵犯了受贿罪的法益,即是受贿行为。[24]
我国当前允许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模式并行,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政府对资源配置的直接管理,使得部分行为人积极努力地“寻租”,追逐因政府对市场进行行政管制而产生的额外利润,从而造成行贿行为的泛滥。越来越多的例证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贿人多是自愿的“寻租者”,是“加害人”。[25]因此,对受贿者也可以设立特别自首制度,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中增加一条:“受贿者在被追诉前主动交行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情节较轻的,可以减轻处罚”,以实现对行贿行为的查处和惩治。多种手段并驾齐驱,成为预防和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有效措施。
四、结语
腐败犯罪是寄生于社会生活的毒瘤,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的一块绊脚石。随着经济的发展,此种犯罪呈现新的态势,《法律解释》在数亿人民满心期待中落下帷幕,也是顺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司法现实的产物,虽有部分疏漏,但仍然瑕不掩瑜。刑罚的谦抑主义价值观要求刑事制裁只有在穷尽其他手段时方可使用,因此应当严格量刑情节,尽量做到量刑的公正精细;降低酷刑如终身监禁制度的使用频率;坚持体系性思维,保持整部刑法典的协调一致,在打击犯罪时,考虑刑罚的经济性。毕竟,刑罚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剥夺生命自由等重大法益的极端措施,应当慎之又慎。任何新生事物都带着其自身的闪光之处和细微瑕疵降临尘世,作为法律人应当秉承理智的态度。对于《法律解释》的整体内容,仍然需要进行较深层次的反思与批判,使其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得以贯彻执行,将惩贪反腐引向深入,从而打造高效廉洁的社会。
[1] 解彬.现阶段我国腐败犯罪治理问题探[J].刑法论丛,2015(2):2.
[2] 大谷实.刑法讲义各论[M].成文堂,2013:641.
[3] 李希慧.贪污贿赂罪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203.
[4] 潘恩.潘恩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65.
[5] 陈洪兵.贪污贿赂渎职罪解释与判例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92.
[6] 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9.
[7] 卢建平.刑事政策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90.
[8] 赵秉志,袁彬.中国刑法立法改革的新思维——以〈刑法修正案(九)〉为中心[J].法学,2015(10):21.
[9] 张明楷.死刑的废止不需要终身刑替代[J].法学研究,2008(2):79.
[10] 王为国.新资治通鉴第二卷[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486.
[11] 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8.
[12] 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7.
[13] 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564.
[14] 卢建平,朱贺.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的路径选择及评析[J].政治与法律,2016(3):9.
[15] 赵秉志.外国刑法原理(大陆法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86.
[16] 赵秉志.论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完善[J].当代法学,2016(1):57-59.
[17] 刘晓梅,于阳.《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我国惩治贿赂犯罪刑事立法之完善[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9(2):21-26.
[18] 杰罗姆·科恩,赵秉志.死刑司法控制论及其替代措施[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477.
[19] 杨诚.死刑司法控制的美国模式之研究与借鉴[J].政治与法律,2008(11):28.
[20] 储槐植.死刑司法控制:完整解读刑法第四十八条[J].中外法学,2012(5):1014-1016.
[21] 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424-425.
[22]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7.
[23] 张明楷.刑法的私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41.
[24] 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064.
[25] 卢建平,张旭辉.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解读[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73.
(责任编校:杨 睿)
The Comment and Perfection on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emper Justice with Mercy Policy
CHEN Wei, SHI Ying
(LawSchool,Southwest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Chongqing401120,China)
Criminal policy midwifes the appearance of criminal legislation, criminal legislation in different period is also the representation adapting to the criminal policy. The criminal policy of tempering justice with mercy is not only the criterion of the guidance of criminal legislation but also the scale of estimating that the legislation is science and that judicature is justice. Comparing with the criminal policy,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 manifests its forethought, and also expose its defects, which may make the criminal judicature fall into the embarrassment of a dilemma. Under the guidance of criminal policy, based on the present problem and thinking under the rule of law, we should improve the collaboration when applying the law from the systematic perspective, strictly apply when it comes to the circumstance for sentencing, reasonably use life imprisonment without parole, introduce the system of security measures and so on, fully realize the benefit of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nd achieve the goals of punishing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 fairly.
justice with mercy policy; interpretation; criminal law; measurement of penalty
2016-09-25
2016年度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重点项目(16SKGH001)“刑法修订中的政策导向与前置化倾向研究——以9个刑法修正案为素材的清理与反思”;2016年度重庆市检察院课题(CY2016BO1)“适用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问题研究”
陈伟(1978—),男,湖北宜昌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刑法学、刑罚学研究。 石莹(1993—),女,河南南阳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刑法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刑法学、刑罚学研究。
10.3969/j.issn.1672- 0598.2017.02.001
D924.392
A
1672- 0598(2017)02- 0001-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