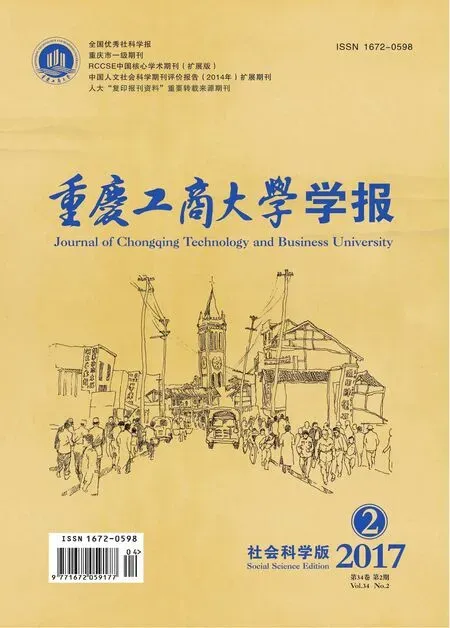“空间转向”之后“怎么办”
赵 斌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州 510275)
“空间转向”之后“怎么办”
赵 斌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州 510275)
“空间转向”之后的空间叙事学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显学”。但是,当前的空间叙事研究到了一个瓶颈阶段,原因多种。“空间转向”的这股后现代思潮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空间转向”的叙事推力功不可没,但后现代历史碎片化、随意切割时间历史的粗暴式学术批评也是不足取的。所以,首先,必须纠正“空间转向”等同于空间叙事研究的偏向。其次,必须区分出“形式化空间叙事”和“内容性空间叙事”,并且分别加以历史化——“空间再转向”,以结束当前空间叙事研究的破碎化、非历史化倾向。
“空间转向”;形式化空间叙事;内容性空间叙事;历史化
一、空间如何产生意义
空间叙事是一种重要的叙事模式,可以利用空间为人物活动提供一个舞台,可以利用空间来推动情节发展,也可以利用空间构置小说结构,等等。在传统的空间叙事诗学中,“空间常常是作为打断时间流的‘描述’,或作为情节的静态‘背景’,或作为小说事件在时间中展开的‘场景’而存在。”[1]为了突破传统诗学对空间的禁锢,“空间转向”后的空间叙事研究一直想方设法脱去空间“他者”的帽子。空间叙事研究一直关注小说空间是如何由静态向动态、由客观向主观、由具象向抽象转化的,也关注“空间怎样参与了小说叙事的建构,怎样影响了小说叙事的进程,在此基础上,还要研究小说里的空间在参与小说叙事建构过程中所使用的一些技巧,以及自身呈现出来的一些特点。”[2]而空间意义的产生是核心问题。
弗里德曼说:“空间并不是被动的、静止的或空洞的……‘叙事作为空间轨迹’的观念,将空间设想为积极的、能动的。”[3]那么,小说空间如何生产出意义呢?我们认为,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场域空间本身具有的基本意义。在小说中,同样是一座房子,可能具有卧室、客厅的叙事功能,也可能具有官场、欢场、酒店、旅馆的叙事功能;同样是书房空间,其摆设不同,意义也会有所不同。如小说《祝福》中的鲁四老爷的书房摆设就独具特色,符合人物的身份。
二是空间的历史表征意义。每一个小说空间都有自身的历史,而这个空间的历史在故事中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激活,从而获取意义。如老舍小说中多处描绘的“四合院”空间,就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意义。
三是空间的心理表征意义。大部分小说空间都具有心理表征意义,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心理表征意义能够增强小说空间的叙事功能,但同时也会给小说的阐释工作带来挑战。如,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小说《追忆逝水年华》。
四是空间的时代意义。“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从小说反映社会的角度看,小说对空间具有选择性,如,晚清小说对“官场”的酷爱;民初小说对“情场”的痴迷;五四小说对“家”空间的热衷等等,这些都有时代的烙印。
五是空间的流动意义。从宏观上看,空间的流动等同于时代的空间选择,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空间是不同的;从微观上看,也就是在一个文本的内部,空间往往会出现转换,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另外,即使小说在一个固定的空间发生,也会出现空间的流动,原因在于,单个的场域空间随着时间、人物思想的变化、空间人物的递减及人物关系的改变而会发生嬗变,衍生出不同的心理空间或关系空间,随之出现不同的空间意义。空间的流动是获得叙事意义的主要途径,因为,空间的流动往往与社会历史的变迁、人的命运及人物的成长是一致的。
二、“空间转向”之后“怎么办”
有一个有趣的研究现象,无论研究小说的时间叙事,还是空间叙事,在论文的开头都会说这个问题研究还很薄弱,并且有意思的是,在同一本书里,研究时间和空间的部分是都做同一种薄弱性强调,并且,受“空间转向”的影响,无论时间叙事研究还是空间叙事研究,经常把空间和时间对立起来加以研究。笔者不是说这种“空间转向”式的研究不可取,而是有点片面,会遮蔽一些东西,也似乎违背了“空间转向”的原意,“空间转向”的目的是打破形而上学,走向多元解读,结果却始料不及,走上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非时间化、非历史化。其实,就小说空间叙事研究而言,这几年的学术论文很宏富,早已实现了“空间转向”,这些成绩功不可没,但同时也暴露了不少问题。“空间转向与当代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的颠覆和历史主义的解构,有着内在直接的相互关联。”[4]也就是说,从“空间转向”的“出身”来看,其生来就是为了抗拒时间、抵御历史主义的。带着这样的神圣使命,也必然阻碍了学界对空间叙事研究的拓展。更进一步说,“空间转向”是后现代思潮推延下的一种学术现象,就文学批评而言,其追求的是一种形式化的空间叙事研究,必然带来“空间叙事研究的空间化”的弊端。什么是空间叙事研究的空间化?也就是空间叙事研究的破碎化,很少有系统化的空间叙事研究。就整个现当代小说的研究而言,横断面式的空间叙事研究不少,体系化的空间叙事研究凤毛麟角,晚清小说、民初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几乎没有涉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空间叙事研究的困境局面?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形式化空间叙事与内容性空间叙事没有进行区分;二是对空间没有进行历史化研究,所以必须“空间再转向”——回到时间、历史上来看空间。
按照后现代的空间理论,空间通过切割时间能够获取破碎、并置的空间,但破碎化不是空间叙事的最终目的,空间要回到时间、历史中才能获取真正的意义。空间怎样回到时间上,后现代的空间叙事需要读者做修缮工作,因而,后现代空间叙事更加丰富,因为可以对小说文本做多元解读。但值得注意的是,受“空间转向”思潮的影响,空间叙事,特别是后现代空间叙事,具有形式主义意味,一般只是强调“怎么写”,空间往往只是作为叙事的一种手段而已。这无形中就会对空间的内容叙事有所忽视,至少在研究思维中遮蔽了一些鲜活的内容性空间叙事。而实际上,空间叙事也注重“写什么”,空间形式固然不容忽视,空间内容更不可缺少,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不能顾此失彼。这一点,韦勒克做了很好的阐述,他认为,“若把形式作为一个积极的美学因素,而把内容作为一个与美学无关的因素加以区别,就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小说中讲述的事件是内容的部分,而把这些事件安排组织成为‘情节’的方式则是形式的部分。必须承认是形式的部分,这是无疑的。”[5]从中可以看到,内容和形式有很多交叉,但却可以做大致的区分。当然,把空间叙事区分为形式化空间叙事和内容性空间叙事还不够,还需要分别加以历史化。对这个复杂的空间理论问题,下面分别加以阐述。
三、形式化(结构化)空间叙事及其历史化
内容和形式的区分问题是一个美学问题,本身很复杂。小说空间本身又是混沌的,小说空间叙事的内容与形式的区分问题似乎显得更复杂。但笔者认为可以大致廓清,以此拓宽空间叙事的研究视野。按照韦勒克形式是“事件被安排组织为情节的方式”的说法,可以知道,后现代“空间转向”下的空间叙事研究是形式主义的研究,不能说这种研究不好,但需要加以处理——去破碎化。
笔者认为,形式化空间叙事是利用多种多样的空间组合、排列方式,形成空间叙事推力的一种空间叙事。形式化空间叙事是一种结构化空间叙事,这种空间叙事往往是参照小说的时间而组织、排列空间的。空间转换与空间并置是形式化空间叙事的两种基本方式。空间转换与空间并置,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都是空间的一种排列方式,只不过空间转换是递进式排列,空间并置是并列式排列。空间并置是一种特殊的空间转换。空间转换有两种类型,一是空间外转换,一是空间内转换。空间外转换是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转换,空间内转换是在同一个场域空间内,随着小说情节的推动,人物感情的迁移、人物关系的变化而发生的一种空间转换。这一点盛子潮和朱水涌两位学者提出的看法很实在,他们认为,“小说空间的结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有次序地展开空间移动过程,小说空间按线性的逻辑的关系而组合,时间维度起着维系空间结构的作用;另一种是非线性的排列小说的空间,各种空间成分横向摊开,或并列、复合,或对比、映衬,或犬齿交错,空间成分为各自的功能互为依存、互为作用,小说空间靠功能关系而结构成一个整体。”并且,他们认为,一部小说给人是“过程感”还是“围氛感”,这是判断作品是属于时间的小说还是空间的小说的重要标志。同时,判断的标准还要看“在最高层次上的情节段组合是时间性构成还是空间性构成,这是因为只有最高层次上的情节段组合,小说才产生整体的意义,在这之下的任何层次,情节段之间的组合都构不成一篇小说。”[6]当然,他们对“时间的小说”和“空间的小说”的划分看似合理,也是值得商榷的。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也在《空间故事》一文中,认为“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旅行的故事——一种空间经验。”对他来说,“叙事结构有着空间句法的地位”。就像公共汽车和火车一样,“它们每天穿过不同地方,将它们组织起来;它们选择了地方,将这些地方联系在一起;它们造出句子,从中分出行程路线。它们是空间的轨道”。[7]这种论述更形象,也更深刻。
笔者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不可分的,是永远纠缠在一起的。只不过空间性和时间性在不同小说中的呈现千差万别,以至于出现时间和空间的分野。但无论如何,空间叙事最终是指向时间的,这是不证自明的。而形式化空间叙事的历史化问题才是当前空间叙事研究的关键所在。这一点是学界一直忽视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提出容易,解决起来有点棘手。原因在于小说时间的复杂多变性和流动性。
小说的时间有不少类型,小说故事、情节和人物等都蕴含着时间。故事时间和情节时间非常明晰,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从叙事学的视野看,文本内所述事件长度被称作“故事时间”,文本外在长度被称作“叙事时间”(情节时间)。[8]并且,“叙事是一组有两个时间的序列……被讲述的事情的时间和叙事时间(‘所指’时间和‘能指’时间)……它要求我们确认叙事的功能之一是把一种时间兑换为另一种时间。”[9]而笔者更关心小说人物的时间,小说人物时间不同于故事时间和情节时间,但却与它们不可分割。按照巴赫金的理解,人物时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人物的生物学时间,一种是人物的历史时间,而人物是否获得历史时间是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标志。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那样,人与世界一同成长,“人的成长带有另一种性质。这已不是他的私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寓于他身上,通过他完成的。”[10]小说人物的历史时间是一个核心概念,对形式化空间叙事的历史化非常重要。
按照巴赫金人物的历史时间这一概念,从空间角度,很容易看到中国小说是如何从古典走向现代的。中国古代小说(部分的历史小说除外)中的人物是没有历史时间的,只有循环的宇宙时间或无时间。在这种时间下,古典小说的空间化倾向偏重。学者林岗说:“时间虽然在叙事的肌理中消失,但叙事所指向的故事‘段’与‘段’的组织安排展现了极为广阔的技巧施展空间。中国叙事艺术的精华可以说集中地体现为叙事空间化的努力。小说家在故事‘段’与‘段’组织安排的范围内,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技巧。”[11]这里的“段”就是小说的空间。罗钢在《叙事学导论》中也提道:“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结构特征却是所谓‘缀段性’,全书没有一个贯串始终的故事,只有若干较小规模故事的连缀,连缀的中介也不是时间的延续,而是空间的转换。”[12]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叙事空间是虚实相生的,且小说的空间化特点非常明显,原因在于,小说人物的历史时间阙如。
在这里,不是强调古典小说的空间排列有什么不同(古典小说也是按照故事时间或情节时间组织、构形的),也不是强调古典小说非常松弛的空间排列,而是重点突出古典小说偏重于故事情节的推进,而无意于人物的历史成长。换一句话说,“从近代小说发达的过程看来,结构是最先发展完成的,人物的发展较慢,环境为作家所注意亦为比较晚近的事。”[13]这一点在五四小说中得到了突破性进展。而这一点正是古典、现代分野的重要证据。如,即使在《水浒传》这样的古典历史小说中也很难找到人物的历史时间,那些梁山好汉“反贪官不反皇帝”,很难有历史进步意义。所以,古典小说的人物“出场定型”,是完全按照儒家的忠孝观念“灌注”而成的。而五四小说却表现出最多的异质性。按照评论家张均的“调节异质分布”的观念来看,五四小说“就是写作者对族群与社会的描写,都被要求脱离古典的忠孝节义等伦理想象而体现出历史发展的正确或反动本质,譬如新和旧、传统和现代等等。”[14]简言之,从空间来看,五四小说写出了从“家”空间到“社会”空间的时间性流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物获得了历史时间,人物从古代走向了现代。值得说明的是,这一离家空间叙事模式既是形式化的空间叙事,也是内容性空间叙事。
那么,如何阐释晚清、民初小说的形式化空间叙事呢?过渡性是它们的最大特点,它们往往会摇摆于古典和现代之间。非常有意思的是,晚清、民初小说都出现了思想与表达悖离的现象。具体地说,“作者,叙述的貌似万能的造物主,在他面前暴露出权力的边际,暴露出自己在历史进程中卑微的被动性。”“作者可能自以为是在领导新潮流,自诩革新派,小说中人物可能热衷于在全新的情节环境中冒险,而叙述者却只能够用旧的叙述秩序维持叙述世界的稳定。这样的小说中,新旧冲突在内容与形式两个层次同时展开。叙述者此时就会苦恼。”[15]学者赵毅衡从叙事学角度从创作者的心理挖掘出“思想”与“表达”的“苦恼”现象。王德威也注意到了晚清小说的这种“混杂性”,他说:“刻意求新者往往只落得换汤不换药,貌似故步自封者未必不能出奇制胜。重要的是,无论意识形态的守旧或维新,各路人马都已惊觉变局将至,而必须采取有别过去的叙写姿态。”[16]学者张均对此做了更透彻的阐释,他更清楚地揭示了这种“悖离”现象的根源,他认为,“‘新小说’家都是在严复、梁启超等一代启蒙巨子的影响下从事创作的,而这一代人对个人自由、民族国家的理论思考,根本并不比五四一代逊色。”并且,“如果尚未为这些理想找到一个恰当的来自文学自身的表达形式,那么文学离‘现代’就无疑还有一段不可能跨越的距离。晚清‘新小说’家们之所以不能抵达‘现代’,缺的不是理性、个人和民族等思想,缺的是恰当的文学表达方式。”[17]这一悖离现象从晚清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从空间叙事角度可以获得进一步的解释,小说的第一人称的使用,主人公的个人空间的成长经历与文本中占大部分社会空间中的“怪现状”的交织、混杂,给学界的阐释工作带来了不少障碍,也引起不少争议。但,在这里,用以证明晚清小说的形式化空间叙事的过渡性与背离性是非常充分的。民初小说《玉梨魂》也是如此,小说结局——主人公牺牲在革命战场——无论如何是牵强附会之笔,常常被评论家们所诟病,但能够确证小说的过渡性和作家创作的思想与表达的背离现象。
另外,从人物的角度来看,小说空间的转换主要有两种:空间的主动转换和空间的被动转换。空间的主动转换是指两个叙事空间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小说是按照人物的思想欲望来排列空间的。空间的被动转换则与之相反。当然两种空间也会有纠缠不清的时候。但大致可以看出,古典小说的空间转换是被动的,现代小说的空间转向是主动的。《水浒传》的“逼上梁山”就很能说明问题,每一个梁山好汉的“行程路线”不是由自己预设的,“落草为寇”都是无奈之举。而五四小说的人生路线图是由自己参与划定的,娜拉式的“我是我自己的”的“呐喊”为自我的人生路径抹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内容性空间叙事及其历史化
“空间转向”是当前热点,“空间转向”目的很明显,就是打破时间对叙事的垄断地位。在这种后现代理论的语境下,空间的“容器”功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贬抑(福柯持此种观点,也影响后来者)。其实,小说的空间首先是静态的“容器”(物理空间),其他一切意义都从这个“容器”生发出来的。从这个角度看,空间叙事不仅仅是形式的,也是内容的。形式化空间叙事强调的是空间的排列组合所形成的叙事推力,而内容性空间叙事却要回到空间自身,在自身中探求叙事的空间意义。所以,“人们在客厅里、厨房里、森林里或沙漠里说话或行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18]原因在于,小说家在作品中对于空间的选择和叙述与作家的主观意旨及作品的主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就是说,“所谓的‘风景’并不是这些东西,而是通过还原其背后的宗教、传说或者某种意义而被发现的风景。”[19]徐岱说得更实在,他认为,“在时间的绵延中,故事所给予我们的只是结局;而在空间的状态下,故事才真正成为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刺激着我们的感觉、激活了我们的想象,我们由此而到达那个经验的彼岸。”[20]这句话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按照时间的思路,形式化空间叙事能够取得一定的叙事推力,获得不错的叙事效果;一是内容性的空间叙事能够更好地呈现出流变历程,能够映射出一定的历史趋向和社会的变迁。后者就是内容性空间叙事的历史化过程。
福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权力空间,他认为,“一部完全的历史仍有待撰写成空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权力的历史——它包括从地缘政治学的重大策略到细微的居住策略。”[21]福柯在考察边沁于1787年设计的“圆形监狱”时,认为“圆形监狱”是现代权力统治技术空间化的一个特殊范型。当然,福柯没有止步于此,他更关注权力技术及其空间是如何实现的,“纪律”作为普适性的现代权力技术,其基本的实现路径是怎样的。带着这些问题,福柯对权力谱系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在对监狱、疯人院等边缘性的“异托邦”(heterotopias)空间进行历史化的考察的过程中,福柯发现了一个隐秘性的时代病症:“所谓的‘异托邦场所’……与危机、越轨、不兼容性、并置、补偿或连续性等较大些的文化结构联系在一起。”[22]这是一个现代性的悖论:人类作为空间的生产者,因自身的异化也必然导致空间的异化。
福柯所做的工作就是内容性空间叙事的历史化过程——知识考古。当然,福柯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进入历史的,但仍然有很多的借鉴意义。回到小说内容性空间叙事的问题上,我们可以从两个视域来阐释内容性空间叙事的历史化问题。一是从宏观视角来看,一是从微观视角来看(福柯就是此种角度)。
从宏观视角来看,即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每一个历史时段中的小说空间叙事。一般说来,社会历史在小说中的反映总会呈现出演进的阶段性。“在追随时代行进过程中,文学从与时代的生动联系中汲取活力,它回答历史的要求,不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23]具体地说,一个时代也就有一个时代之小说,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时代的空间叙事。换一句话说,每一个时代的小说对空间的选择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变迁有很大的关系。如晚清的“官场”充斥于小说中,其他时期也会有“官场”,但没有这么集中。更为重要的是,每一个时代的“官场”是不同的,而把不同时代的“官场”叙事连接起来,就形成了“官场叙事史”。五四小说中很少有“官场”空间,但“家”空间却大量出现。五四小说的“家”空间的构形与以前时代截然不同,呈现出明显的现代转向。格非有一段话能够把这一问题引向深入,他说,他的一位西方学者朋友“在阅读‘文革’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时候,感觉上更像是在阅读浪漫主义小说。”由此,格非得出一个结论:“就中国小说而言,它由于受到诗歌和绘画中写意传统的影响,现实主义的因素一直没有被置于首要地位,或者说,现实主义在一开始就显得“营养不良”。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聊斋志异》这类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因素,我们只能说,它不过是以一种曲折的隐喻方式表现了现实的某些征象,而不是再现现实,更不是对现实力求精确的复制。”并且他更关心的是,“被高度抽象化的‘现实’这一概念是以何种方式与作家的神圣使命联系在一起的。”[24]从格非的阐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五四小说的“家”空间是具象的,更是抽象的;同时,也揭开一直以来笼罩在五四小说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纷争迷雾,因为,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小说是现实的,也是浪漫的。而作为晚清与五四夹缝中的民初小说,其“情场”的空间构置同样适应了时代的选择,是与民国初年的社会现状息息相关的,与商业化、娱乐化的创作氛围一致的,这一点也一直成为五四小说家批判的焦点,由此导致学界对民初小说的研究不力的现象。
从微观视角来看内容性空间叙事的历史化问题,即是从每一个单个空间(如妓院、后花园等)来考察不同时期小说的空间叙事,以此来考察空间叙事的流变历程。这一点赵嘉鸿在《论中西古典小说的空间叙事》一文中做了一些可贵的尝试,他认为,“在中国,从早期叙述比较简单的庭园,如《世说新语》中顾辟疆的名园、唐代小说《李德裕》中的平泉庄,到《三国演义》中的凤仪亭、《水浒传》中的鸳鸯楼、《金瓶梅》中的西门花园、《红楼梦》的大观园……中国庭园叙事的笔墨越来越多,对小说文本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其叙事形式则日趋复杂和多样。”[25]当然,该文只是点到了这种历史化的趋势,没有对“庭园”空间的叙事流变进行历史性分析,似乎有点遗憾。如果把“庭园”空间叙事追溯到晚清、民初小说中的“庭园”空间,继而追溯到五四小说中的“公园”空间,形成中国小说“庭园”空间叙事流变史,似乎更有学术意义。
五、结论
“空间转向”之后的空间叙事学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显学”。但当前的空间叙事研究到了一个瓶颈阶段,原因有多种。“空间转向”的这股后现代思潮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空间转向”的叙事推力功不可没,但后现代历史碎片化、随意切割时间历史的粗暴式学术批评也是不足取的。所以,首先,必须纠正“空间转向”等同于空间叙事研究的偏向。其次,必须区分出“形式化空间叙事”和“内容性空间叙事”,并且分别加以历史化——“空间再转向”,以结束当前空间叙事研究的破碎化、非历史化倾向。
[1] [3] [7] [22] 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空间诗学与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A].JamesPhelan等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M].申丹,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05,209,215.
[2] 余新明.《呐喊》《彷徨》的空间叙事[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
[4] 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空间转向与当代文艺理论建构[J].王宁.文学理论前沿(第七辑)[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0.
[5] 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146-147.
[6] 盛子潮,朱水涌.小说空间与空间小说[J].小说评论,1989(2):54-55.
[8] 罗钢.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9]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2.
[10]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228.
[11] 林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52.
[12] 罗钢.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79.
[13] 沈雁冰.人物研究[J].小说月报(第16卷第3号),1925-3.
[14] 张均.现代之后我们往哪里去[J].小说评论,2006(2):50-51.
[15] 赵毅衡.苦恼的叙事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1-2.
[16]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M].北京:三联书店,1998:7.
[17] 张均.中国现代文学与儒家传统(1917-1976)[M].长沙:岳麓书社,2007:14-15.
[18] [20] 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93,297.
[19]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文版序[M].赵京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2.
[21] 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J].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39.
[23] 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3.
[24] 格非.小说叙事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4.
[25] 赵嘉鸿.论中西古典小说的空间叙事[J].文艺争鸣,2014(3):154.
(责任编校:朱德东)
After“Space Turn”,“How to Do”
ZHAO Bin
(ChineseDepartment,Sun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510275,China)
“Space narrative after space shift” has become a hot field. However, the current space narrative research comes to a bottleneck stage, there are many reasons. The post modern ideological trend of “space turn” has an inescapable responsibility. The so-called “success comes from it but the failure also comes from it”. “The narrative thrust of “space turn” has the contribution, but roughly academic criticism of the history of the post-modern history fragmentation and the randomly cutting time history is worthless. As a result, firstly, we must correct the deviation that the “spatial turn” is as the same as the spatial narrative study. Secondly, we must distinguish the form of spatial narrative from the content of spatial narrative, to let both of them be historical, “space and then turn”, so as to end the fragmentation and non-historical tendency in the current space narrative research.
“spatial turn”; formal narrative space; content of space narrative; history
2016-12-10
赵斌(1982—)男,安徽霍邱人;中山大学中文系2014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10.3969/j.issn.1672- 0598.2017.02.013
C91
A
1672- 0598(2017)02- 0097- 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