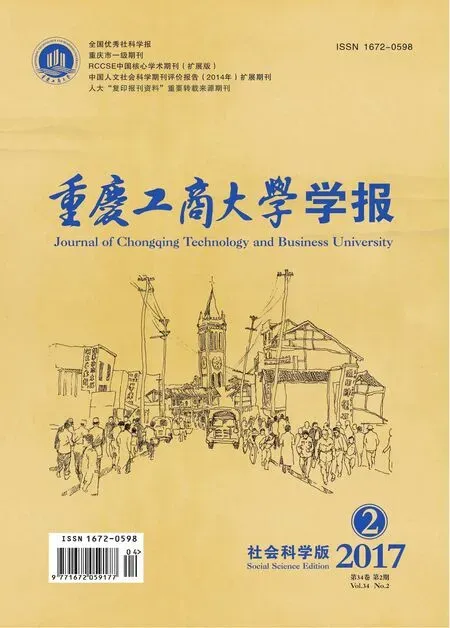破旧立新的文化身份建构途径
——对20世纪50—70年代民族小说的一种考察
朱 斌,徐小侠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 兰州 730070)
破旧立新的文化身份建构途径
——对20世纪50—70年代民族小说的一种考察
朱 斌,徐小侠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 兰州 730070)
50—70年代民族小说的文化身份建构主要是破旧立新,它形成了两条具体的实现途径:一是内在认知意识的“破旧立新”,二是外在实践行为的“破旧立新”。这有效更新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却消解了其传统的文化身份属性。理想的文化身份建构应该促成他者与自我之间的有机交融。
民族小说;文化身份;身份建构;文化属性
通常,文化身份建构是“在与他者不断的互动关系中所进行的一种自我身份与认同的设计、调整与改动过程”[1]58。我国20世纪50—70年代民族小说的文化身份建构,主要是少数民族“自我”的他者化过程:促使“自我”身份向作为“他者”的主流政治文化身份转化,具体言之,以主流政治文化身份力量,破除少数民族旧有的文化身份属性,从而在少数民族群体中孕育出符合当时主流政治文化要求的新文化身份特征,并让其成为主导性文化身份力量。其实质在于促成各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破旧立新。这主要包括两种途径:一是内在认知意识的“破旧立新”,二是外在实践行为的“破旧立新”。
一、文化身份认知意识的破旧立新
布尔迪厄曾指出:“文化需要是教养和教育的产物:诸多调查证明,一切文化实践以及文学、绘画或者音乐方面的偏好,都首先与教育水平密切相联”[2]。确实如此,文化身份的需要,也要依靠教育,因为“要将众多的,也许共享同一文化但缺乏彼此间认同感的人们凝聚为一个整体,并在他们当中建立一个统一的认同,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必须仰仗于宣传教育和思想动员[3]235。而且,文化本身就意味培养、教养,是人精神进步与完善的建构,唯有通过教育人们才能进入“文化状态”。据此,我们可以说,各种教育活动在文化身份的建构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文化身份建构离不开教育。
虽然,教育本身是一种实践行为,但其作用却主要体现在对受教育者认知意识的影响上,主要引起受教育者认知意识的变化。因而,在文化身份的建构中,教育侧重于内在认知意识的建构:影响受教育者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知。“认知是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对事物的认识是人类认同文化的依据。对某一事物有自己的认识,并且深信不疑,才导致对此的认同”[4]109。认知的变化往往为文化身份认同体系注入了新的因素,会促使其发生变更。所以,通过教育促成文化身份认知的变化,是有效建构文化身份意识的必要途径。50—70年代民族小说内在认知意识的他者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各种破旧立新的教育实现的。因此,对各种教育活动的描写,在当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仅以敖德斯尔(蒙古族)的两篇小说为例。在其《遥远的戈壁》(1957)中,八路军骑兵连连长孟和就常进行思想教育:他耐心教育蒙古族群众,毛主席领导的军队,是为贫苦老百姓的解放而打仗的;他还耐心教育战士,应该更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在《“老班长”的故事》(1959)中,作为党总支副书记的老班长,也一直在进行思想教育:他教育小娜布琪,存钱干什么?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可不能有爱钱观点啊!他还教育“我”,革命的人就要有革命的思想、革命的品德、革命的作风和行动,不然,算什么革命者、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呢?这些教育都属于典型的政治思想教育,主要是宣传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身份意识,以促使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破旧立新。因而,这种破旧立新的政治思想教育是更新人们文化身份意识的一种有效途径。
“回顾过去是解释现在的最常见的策略”[5]1。往事回顾主要是为了今天的文化身份建构。因此,当时民族小说“破旧”方面的文化身份意识教育,侧重于回顾性的反面教育:揭露旧社会、旧政权的反动性、腐朽性与必亡性,强调其带给各族人民的苦难,从而激励他们推翻旧社会、打倒旧政权、消灭剥削阶级。这往往形成了当时民族小说中的“忆苦”教育场景。譬如,《遥远的戈壁》(1957)就多次涉及“忆苦”教育:连长孟和把那位老妈妈年轻时悲惨的生活介绍了一番,引出了一场争相“诉苦”的场景。小战士查干夫,看见穷苦牧民家的孩子饿得直哭,便想起了过去挨饿的经历,因而进行了一次“忆苦”的自我教育。在《骑骆驼的人》(1973)中,阿巴干老汉对迷信的人进行了一次“忆苦”教育。相似的例子在当时民族小说中随处可见,譬如,在郝斯力汗(哈萨克)的《起点》(1957)中,在刘荣敏(侗族)的《忙大嫂盘龙灯》(1963)中,在伍略(苗族)的《收获的日子》(1975)里,我们都能看到忆苦教育的场景描写。这种忆苦教育,通过对旧社会、旧政权苦难的不断追忆与控诉,使各族群众不断重新体验过去的痛苦与不幸,从而加深了他们对“自我”过去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卑微身份的集体记忆,有效激发了他们摧毁它、废除它和摆脱它的文化身份建构意识。所以当时民族小说的“破旧”教育,主要是一种忆苦教育。
而当时民族小说“立新”方面的文化身份意识教育,则侧重于立足现实的教育:让各少数民族深切认知社会主义新社会、新政权的进步性、优越性,强调其带给各族人民群众的幸福与美好,突出各族劳苦大众作为新社会、新政权的被解放者、被拯救者的身份意识,也突出各族群众翻身得解放成为社会主人翁的身份意识,从而强化他们热爱新社会、保卫新政权的意识与激情。这往往形成了当时民族小说中的“思甜”和“展望美好未来”的教育场景。“思甜”教育,直接赞美新社会的新生活之幸福,而“展望美好未来”的教育,则关注新社会将来更幸福与更美好的理想生活,二者都在于激发各族人民新的文化身份意识,从而建构出符合当时主流政治文化要求的文化身份认知。
这种“思甜”和“展望美好未来”的教育场景,在当时民族小说中也随处可见。譬如,在安柯钦夫(蒙古族)的《草原之夜》(1953)中,老牧人单巴叔叔就对“我”进行过“思甜”和“展望美好未来”的教育:做梦也没有想到,这辈子能赶上这样一个美好的时代,人人平等,不许压迫,新政权还要继续引导我们使草原更加美丽繁荣。而在柯尤慕·图尔迪(维吾尔族)的《吾拉孜爷爷》(1958)中,吾拉孜爷爷则对海迪切妈妈进行了“展望美好未来”的教育:要修“青年渠”,还要修发电站,那时节啊,我们就有明亮的电灯啦,我们就会有更多更多的粮食了。这样,通过对新社会、新政权、新生活与新身份的不断赞美,通过对美好未来的不断展望,就使少数民族群众不断体验到现在的幸福与未来的美好,从而激发他们珍惜它、保护它和完善它的文化身份建构意识。
可见,经过“忆苦”或“诉苦”的反面教育以“破旧”,通过“思甜”与“展望未来”的正面教育以“立新”,各少数民族便在文化身份的认知意识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便慢慢更新了过去文化身份意识的旧观念,从而确立了符合主流政治文化身份要求的新观念。这样,当时的民族小说,不仅是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而且更是宣传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身份要求的一种思想教育形式,因而有效促使了少数民族文化身份认知意识的“破旧立新”。
二、文化身份实践行为的破旧立新
通常,认知意识的变革与更新,归根结底会反映到外在的实践行为上,从而促使外部实践行为的变革与更新。所以,文化身份的建构,仅有内在认知意识的破旧立新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仰仗于外在实践行为的破旧立新。因此,20世纪50—70年代民族小说的文化身份建构,除了依靠内在认知意识的他者化之外,还仰仗于外在实践行为的他者化,具体言之,更是依靠各种“破旧立新”的实践行为促成的。其“破旧”方面的实践,主要侧重于各种革命斗争活动,而其“立新”方面的实践,则主要侧重于各种生产建设活动。前者目的在于粉碎旧社会,推翻旧政权,消灭剥削者和压迫者,把各民族劳苦大众从苦难与不幸中解放、拯救出来,从而破除其旧有的文化身份关系。而后者目的则在于建设新社会,开创新生活,维护社会主义新政权,以巩固一种崭新的文化身份关系:各族人民平等互助,当家做主。
革命斗争活动,往往形成当时民族小说中“抗击敌人”的战斗场景以及“解放苦难者”的拯救场景。以几位蒙古族作家的作品为例,在敖德斯尔的《遥远的戈壁》(1957)中,八路军骑兵连追击土匪,与土匪展开战斗,最终消灭了土匪,并从土匪手中把牧民的骆驼队拯救了出来。在朋斯克的《金色兴安岭》(1953)中,解放军骑兵连经过多次战斗,歼灭了一群“反共游击队”,将受其蹂躏的蒙古群众解放、拯救了出来。相似的例子在当时其他少数民族作家笔下也极多,比如,在陆地(壮族)的《美丽的南方》(1960)中,通过抗击敌人的多次战斗,土改工作队拯救了安分守己、胆小怕事的韦延忠等壮族农民,使他们最终都成了挺起腰杆进行斗争的时代“新人”,而在胡奇(回族)的《绿色的远方》(1964)中,援藏老师李侠和草原民兵等通过抗击敌人的战斗,消灭了暗藏的阶级敌人,把扎西、阿江等“旧人”拯救了出来,使他们认识到了宗教迷信的罪恶本质,最终都成为西藏新牧民。这样,通过对各类阶级敌人的不断抗击,通过对各类苦难者的不断拯救,小说就以实践行为消灭了旧社会、旧政权对各民族劳苦大众的反动统治,破除了维系旧社会、旧政权的那套旧有的文化身份体系,从而开始建构一套文化身份新系统。所以,斗争活动是具有消灭性与摧毁性的实践行为,也是具有解放性与拯救性的实践行为。
生产建设活动,往往形成当时民族小说中改造自然的“战天斗地”场景,以及体现了崭新劳动关系的“集体劳动”场景。很多时候,这两类场景合二为一。在敖德斯尔(蒙古族)的《“老车夫”》(1960)中,盟长扎拉仓与全体牧民们一起“盖棚搭圈”,与暴风雨展开了一场殊死战斗,形成了“战天斗地”的集体劳动场景:村里一片人喊马嘶声和马鞍具的碰击声,四下闪着电筒的白光,到处是奔跑的黑影。柯尤慕·图尔迪(维吾尔族)的《吾拉孜爷爷》(1958),呈现了一场修渠青年们“战天斗地”与“魔鬼峡谷”搏斗的集体劳动场景:爆炸声、锄镐声、铁锨声,劳动的歌声在山谷里交杂成一片;“魔鬼峡谷”里人山人海,红旗飘扬。而在哈克宽(回族)的《金子》中,回族妇女队长白金子,也带领群众“战天斗地”,与洪水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将丰产麦田从洪水威胁中“拯救”了出来。这种“战天斗地”的生产斗争与集体劳动表明:在新社会与新政权中,各族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既呈现出战天斗地的豪迈精神风貌,又呈现出团结互助的高尚伦理品质,因而确立了一套崭新的文化身份行为系统。
而且,为了突出文化身份实践行为方面破旧立新的建构目的,无论革命斗争活动还是生产建设活动,在当时民族小说中,其最终结局往往都是以胜利而告终。这种最终胜利,常成为各少数民族新的文化身份关系得以确立的一种标志,因而,当时的民族小说往往也描绘了诸多庆贺最终胜利的庆典活动场景。敖德斯尔《遥远的戈壁》(1957),叙述了八路军骑兵歼灭土匪归来,受到牧民们热烈欢迎的胜利庆典场景。而安柯钦夫《金色的理想》(1965),则描绘了与山洪搏斗取得最终胜利后的欢庆场景。柯尤慕·图尔迪的《吾拉孜爷爷》(1958),在青年们与“魔鬼峡谷”的斗争取得最终胜利后,也描绘了一场庆典活动。这诸多欢庆胜利的庆典活动,既是各民族文化身份“破旧立新”活动取得胜利的一种标志,也是新文化身份行为系统得以确立的一种隐喻。
这样,经过各种抗击敌人与拯救群众的革命斗争活动以“破旧”,通过各种“战天斗地”与团结互助的生产建设活动以“立新”,还通过各种欢庆最终胜利的庆典活动以巩固“破旧立新”的成果,各少数民族便更新了旧的文化身份行为系统,从而确立了一套符合当时主流政治文化身份要求的新行为系统。因此,当时的民族小说,具有建构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实践功能,有效促成了各民族文化身份行为方式的“破旧立新”。可见,实践行为——尤其是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实践,也是当时民族小说建构他者化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因此,从文化身份建构角度看,当时几乎每一篇民族小说,都存在主流政治文化身份方面的实践者或行动者。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对各民族群众进行文化身份的实践改造,不断促使他们“破旧立新”,因而从实践行为上建立、维护了当时主流政治文化所要求的文化身份特征。
三、文化身份建构的简短反思
综上所述,20世纪50—70年代民族小说的文化身份建构,从本质上讲,是一个“破旧立新”的动态过程。其具体途径主要有二:一是内在认知意识的“破旧立新”,主要依靠各种政治思想教育;二是外在实践行为的“破旧立新”,主要依靠各种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活动。它们都有效促使了当时民族小说文化身份的他者化,使各少数民族都获得了现代意义的政治文化身份。然而,其本质是政治主导式的,强调民族文化意识对主流政治文化意识的服从。这剥夺了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多样性要求和丰富性表达,各民族文化身份因而变得单一而片面。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当时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过于严苛,而少数民族“自我”紧跟时代的更新意念又过于急迫,以致把他者与自我之间复杂的文化碰撞过程简单化了:简单地否定了自我,而全盘地接受了他者。
其实,理想地看,文化身份的有效建构,应维持他者与自我之间的必要张力:既吸收他者诸多合理的文化身份属性,又发扬自我诸多有益的传统文化优势。这必然要求维持反思他者与反思自我之间的必要张力:既批判、抵制他者的糟粕与不合理成分,又批判、祛除自我的落后与保守成分。据此,民族文化身份建构固然应“他者化”,但这并非是放弃自我,而是在立足自我的基础上,对他者的合理吸收与转化。因此,接受他者,“必须严格地从本民族的实际需要出发,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融会贯通”[6]25。可见,民族小说的文化身份建构,应摆脱50—70年代那种完全他者化的建构模式,而努力促成一种融双向反思与双向认同于一体的建构模式:既认同自我又反思自我,既认同他者又反思他者,从而孕育出民族文化身份的新特征。因此,当时民族小说在对主流文化的一体化认同中暗含了诸多自我认同的因素,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主流时代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交融,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认同他者与认同自我之间的必要张力”[8]。
[1]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98.
[2] 布尔迪厄.纯粹美学的社会条件[J].朱国华,译. 文化研究, 2005 (4).
[3] 何成洲. 跨学科视野下的文化身份认同[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4] 郑晓云.文化认同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5] 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 李琨,译. 北京:三联书店, 2003.
[6] 梁一儒.民族审美文化论[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
[7] 朱斌.50—70年代民族小说的自我认同原因探析[J].石河子大学学报,2013(4).
(责任编校:朱德东)
Construction Paths of Cultural Identity for Destroying the Old and Establishing the New
ZHU Bin, XU Xiao-xia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NorthwesternNormalUniversity,GansuLanzhou730070,China)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ethnic novels’ cultural identity during the 1950s-1970s is mainly destroying the old and establishing the new. It has two specific ways such as intrinsic cognition consciousness and the external practice behavior for “destroying the old and establishing the new”. This effectively updates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ethnic minorities, but digests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attributes. The ideal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should boost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between oneself and the others.
ethnic novel; cultural identity;identity construction;cultural attribute
2016-10-29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1BZW127)“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对文化身份的认同、建构与审美转化研究”;西北师大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骨干项目(SKQNGG12004)
朱斌(1968—),男,四川仁寿人;文学博士,西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 徐小侠(1989—),女,河南沈丘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0.3969/j.issn.1672- 0598.2017.02.012
B024.8
A
1672- 0598(2017)02- 0093- 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