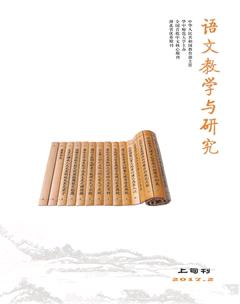基于语言分析的文本细读教学
王针桂
面对阅读材料时,文本言语的关键点究竟在哪里?教师如何抓住这些关键点引导学生进行文本细读呢?笔者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探索了以下几种基本策略。
一、从分析语言的空白化中细读文本
“空白化”原是国画创作中的一种构图方法,它以“计白当黑”的艺术手法使作品虚实相映、形神兼备,从而创造出一种“无画处皆成妙境”的艺术境界。对欣赏者而言,“空白”给人自由驰骋的空间,让他们充分地调动思维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去填补画面的空白内容,并在欣赏的过程中有一种自我参与感和创造感,从而得到再创作心理的满足。当然,作家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的故意留白与空缺,是为了克服语言的局限性所采用的技巧,使作品在有限的篇幅中表现出无限的内容,使本来难以言说的东西在读者的合作下得到较完善的表现。空白是文本中隐而不露的联结点,文本中没有说出来的地方,常常反而是至关重要的部分,如果没有读者的想象去加以补充、丰富,文本就无法在读者那里获得真正的反映和实现。
例如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中,写鲁四老爷的书房布置是极讲究的,书房壁上“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平和”。那么,作者为什么不连带把另一联内容也写出来呢?联语内容的空白应是作者有意之举。作者为突出这句联语,特意隐去了这幅对联的上联“品节深明德性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平和”是鲁四老爷这种所谓“理学家”所奉行的道德标语,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鲁四偏偏在对待祥林嫂的态度上表现出的“事不通理不达心不和气不平”:他无数次叱责祥林嫂是一个谬种!这幅只能用来自欺欺人、作遮羞幌子的对联无法掩盖鲁四虚伪冷酷的嘴脸。浸淫满身的根深蒂固的礼教思想如同他那幅无法舍弃的对联一样,它的阴影时时笼罩住鲁镇的上空。活在这样环境中的“祥林嫂”们是注定要往死路上走的!分析此处的语言空白并进行“补白”训练,便能更好体味鲁迅先生的良苦用心。
再如教学鲁迅《药》中分析华老栓的形象特征时,笔者注意到一处“可怕”的细节:作为小说主人公之一的华老栓在全篇小说中仅说了24个字,分别是:
⑴“唔”,老栓一面说,一面扣上衣服,伸手过去说,“你给我罢。”(5个)
⑵老栓待他平静下来,才低低地叫道,“小栓,……你不要起来,……店么?你娘会安排的。”(15个)
⑶“得了!”(2个)
⑷“没有。”(2个)
这样的一种言语空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华老栓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鲁迅为什么不让他多说两句话呢?与我们印象中的茶馆老板能言善辩相比,华老栓的木讷寡言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意义呢?”如果引导学生探析华老栓话语中出现的场合,不难发现,华老栓说话可理解为“主动式”和“被动式”两种情态,前两句是他主动说的:向华大妈索要买人血馒头的洋钱,临行前对儿子的叮嘱。后两句是华老栓对别人问话的被动回答,都很简短,但语调不同。“得了!”兴冲冲中极度欣喜,“没有。”轻飘飘地一语而过。这样一比较可以清晰看到:华老栓根本没有关心别人的兴趣,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儿子。从这点上来看,华老栓根本不会知道“革命者”,更不知道“革命者”会和自己还有什么关系。他在和自己的不幸命运作苦苦挣扎的同时,已变得愚昧麻木、极端无知。一个朴实本分、笃子情深的老父也是一个麻木迂讷、无知愚昧的农民。这样理解出来的华老栓形象在学生心中便会立体深刻了起来。
二、从分析语言的个人化中细读文本
在阅读实践中,我们常常会遇到看似不符合语法规范和逻辑事理却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的语言,这些语言不受常见的语法规范的限制和束缚,往往带有非常强烈的个人的、临时的感情色彩,正是在这种个人化的运用中,我们要能够辨认出作者和人物的个性及深层的、潜在的情感,要引导学生设身处地地从自己情感体验出发,主体投入地感性地阅读,以自己之心与作家之心、作品人物之心相会、交流、撞击,体会他们的境遇、真实的欢乐与痛苦,最终形成共鸣。
例如在《我与地坛》中,作家史铁生描绘荒芜而并不衰败的地坛,其中用了这样的句子:“它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我们在品读这几句时,不能仅仅品味“浮夸”与“炫耀”等词语的“反常规”运用,更应该去仔细品味在句式上的“反常规”。因为常规的句式往往是这样表述:它的琉璃剥蚀了,朱红淡褪了,高墙坍圮了,玉砌雕栏散落了。可在这里,作者却将“剥蚀”等词语都移到了句首,这是为什么呢?这些词语这样一移,给读者造成一种“个人化”的感觉,从而也就更能凸现这个古园的荒芜状态。如果我们再深味下去,我们也许还会发现并感悟另外一个问题:作者在这里连写了四种景象,为什么要将后两种景象连在一个分句中写?为什么不像写前两种那样分开,再加上与前两个分句相应的形容词,造一个由四个分句构成的排比句呢?在仔细的品读中,我们也可能体会到作者这样造句之妙:一连四个排比句,语言的气势增强了,但语言气势的增强,在这里却反而会冲淡古园荒芜的气氛,而到第三分句的忽然生变,在内容上,突出了古园高墙“坍圮”后的荒芜之景;在句式上,则既与前两个分句自然衔接,又生发出了新的变化,使整个句子显得整齐而富变化,摇曳而成新姿。
再如,“我真傻,真的”是《祝福》中最为典型独特的语言,出现在祥林嫂多次讲述“狼吃阿毛”的故事中。文中共写了祥林嫂三次讲故事:对四婶讲;对镇上的人们讲;自语阿毛故事。这每次讲的“狼吃阿毛”的故事,其开端是千篇一律的:“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考察这段“开场白”,我们会发现两点:一是从叙述角度看,叙述阿毛的故事,却从“我”开始,先叙“我”,再及阿毛,在故事中,“我”成了主角,成了线索,而非阿毛;第二是從叙述的语言结构看,开端的这一复句间总的关系是解说,其中心句是“我真傻,真的。”结合这两点看故事的叙述目的,可以看出,祥林嫂讲“狼吃阿毛”的故事,其意不在于渲染阿毛死得如何凄惨,以博得人们的同情,而在于表白自己是如何的“傻”,这是她在深深地自责,是她对阿毛的不可解脱的负罪的忏悔。所以,说祥林嫂的悲剧(寂然死去)的原因就在于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这仅是从行为发生的外因,也即社会环境而言。那么,其内因到底是什么?通过祥林嫂讲“狼吃阿毛”的故事来剖析,不难发现,祥林嫂的悲剧的发生,其内因是在于她内心的深深的负罪感(对她儿子的无法忘怀的负罪感)和对死的抹不去的恐惧感(即惧死情结)。
三、从分析语言的模糊化中细读文本
人的情感内容是最不确定,最难于捉摸的,这种情感的不确定性,不可能进行定量分析和逻辑规范。作家选定一个个词语组成一个语言单位时,其情绪的表现只能通过这些词的语义场的组合关系或清晰或模糊地表露出来。因此,它能产生出一种朦胧模糊的意味和体验,引发读者把阅读思考的重心转移到对文本整体聚合的言语风格、形态、情态的感受之上来,从而整体解读言语符号组合形态后面包容的生命情感。
例如教学朱自清先生《荷塘月色》中“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这一句孤零零地看,似乎难以确切把握其真正含义:作者觉得自由的人到底是要想还是不想?这样说不是有矛盾的吗?显然,弄清这些“模糊点”是感悟作者复杂深沉情感的关键。教学时我们似乎无法对这简短一句话进行语义剖析、词义索解,也没理由引经据典、知人论世去考证一番。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用心去品悟感受一番,稍有点生活经验的人便能体会到其间“没事偷着乐”的复杂情怀:对一个背负沉重生活负担、心理压抑的中年知识分子而言,“什么都可以想”意味着思想的无拘无束,“什么都可以不想”意味着生活的无忧无虑。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自由之境啊!
再如归有光《项脊轩志》后记部分: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这些文字乍看并不像正文那样富有诗意、充溢着情思,似乎平淡无味,且言语模糊。读者须充分设疑细读才能领会作者用最经济的笔墨传达的最丰富的内涵:作者为什么要写小妹们的话,这背后有什么故事? “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妻子从作者口中听到了不少精彩的历史典故,从南阁子的书籍中看到了大千世界,她的视野为之开阔,她的精神生活变得丰富充实,所以回到娘家,她充满自豪而又饶有兴味地向小妹们讲述阁子中的生活,引得小妹们油然而生羡慕之情,神往阁中的读书生活,这样便有了小妹们的问语:“且何谓阁子也?”以看似平静朴素的叙述包含了当日的夫妻情浓,而于今人去阁空,“吾妻死室坏不修”,寥寥数字,哀思尽在不言中。只余有庭院之中妻子亲手种植的枇杷树亭亭如盖,睹树思人,树在人亡,那种历久弥深的哀痛,无须张扬,学生只需想像此情境,亦能体会那种沉痛。
四、从分析语言的陌生化中细读文本
当代作家王安忆对“语言陌生化”概念有比较具体的阐述:“所谓陌生化,就是对常规常识的偏离,造成语言理解与感受上的陌生感。在指称上,要使那些现实生活中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化为一种具有新的意义、新的生命力的语言感觉;在语言结构上,要使那些日常语言中为人们司空见惯的语法规则化为一种具有新的形态、新的审美价值的语言艺术。”(《漂泊的语言》)这段话告诉我们,“陌生化”是文学艺术的一种技巧,从途径上说,就是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从方法上说,就是综合运用诸如移用、通感、新奇的比喻与拟人等修辞手法。通过熟练运用这些方法,化腐朽为神奇,变习见为新异,从而使读者获得意想不到的美感体验。
作家们也都十分注意综合运用各种修辞手法,使得语言陌生化,虽然增加了读者感知事物的难度,延长了感知时间,但却使人在反复品味中获得一种审美愉悦,充分显示了陌生化语言的独特魅力。例如“女人坐在小院子当中,手指缠绕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孙犁《荷花淀》)苇眉子也会“跳跃”,比拟手法化静为动,十分传神。“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睛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鲁迅《药》)“两把刀”“缩小了一半”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了康大叔的蛮横暴虐和华老栓的老实胆小。“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纺织着疲惫的歌”超常规的动宾词语搭配移用,“破旧的老水车”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与歌相对应,水车的外形与纺车相似,转动时给人的感觉也很有相似性,作者由此及彼展开联想,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仿佛歌是由纺车演奏出来。生动地抒写了表明了中国贫穷现状,数百年积贫积弱,百姓生活疲惫不堪,这种用法表面上看似乎有些用词不当,但却能产生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
再如鲁迅小说《孔乙己》中“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句话里“大约”与“的确”是矛盾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有的人说这是顺口说的,合乎说话的习惯;有的人说这是一个或然判断,本身就是模棱两可;有的人说这是儿童口吻,不顾及语法和逻辑等等。鲁迅用“大约”这个词,而不用“大概”“也许”等词,显然是经过比较、选择的,认为这个词比较符合小伙计的身份和口吻。本来,像孔乙己这样的人在旧时代是必死无疑的,为什么作者不采用肯定的語气呢?这不仅是因为小伙计没有亲眼看见孔乙己死去,更重要的是存在侥幸心理,或希望他不死,然而按照必然律推导,孔乙己已别无他路,只有死路一条,所以用“的确”一词,构成一个矛盾的判断,渲染了忧伤气氛。
参考文献:
[1]王尚文:语文教学对话论[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版。
[2]蒋成瑀:读解学引论[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孙绍振:名著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M],广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