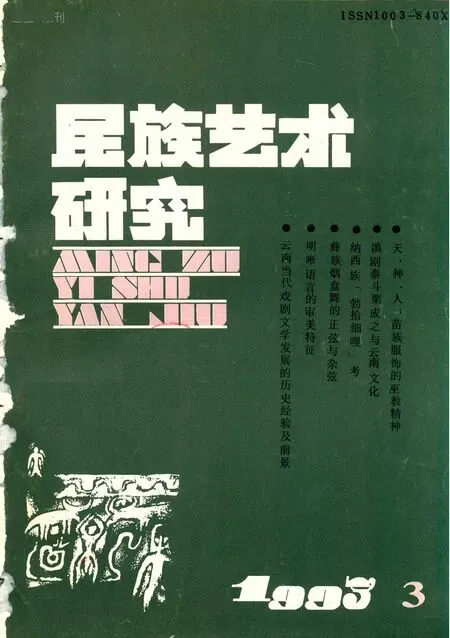神秘东方的诗性书写: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电影解读
崔 颖,朱丹华
神秘东方的诗性书写: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电影解读
崔 颖,朱丹华
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泰国电影已成为亚洲电影多样性发展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泰国电影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呈现,极具地域风情的影像书写,创造出风格独具的电影范式,成为继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伊朗之后又一代表性的亚洲电影新力量。在泰国电影创作群体中,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是引领泰国电影获得国际影响力的领袖人物,他的电影创作根植于泰国本土民族文化,用诗性的电影语言、非线性的叙事结构以及梦境、丛林、疾病等富含东方神秘色彩的意象表征,构建了一个极具个人气质的艺术电影世界,展开其丰富的民族想象,并收获本国族的自我认同。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也因此成为亚洲影坛最具个性的电影作者之一。
泰国电影;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诗性修辞;独立电影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是泰国电影新浪潮运动的代表性人物。与朗斯·尼美必达(Nonzee Nimibutr)、韦西·沙赞那庭(W isit Sasanatieng)和彭力·云旦拿域安(Pen-EkRatanaruang)等其他泰国新浪潮运动的领袖人物主要在商业电影领域进行创作不同,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一直游离于泰国主流电影工业体制之外,在艺术电影领域进行着独立的电影创作。2010年,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凭借《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Uncle Boonmee Who Can Recall His Past Lives)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阿彼察邦和他的电影也因此成为亚洲艺术电影的代表力量。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1970年出生于泰国曼谷的一个华人家庭,他的父母都是医生。1994年,阿彼察邦从孔敬大学(Khon KaenUniversity)毕业,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阿彼察邦上大学期间就开始了电影创作,1993年,他拍摄了第一部短片《子弹》(Bullet)。大学毕业后,他远赴美国,在芝加哥艺术学院(School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学习电影美术专业,并于1997年获得硕士学位。从美国毕业回到泰国后,阿彼察邦开始了自己的电影职业生涯。在拍摄了几部短片之后,1999年,他用16毫米胶片拍摄完成了第一部电影长片作品《正午显影》(Mysterious Objects At Noon)。2002年,阿彼察邦导演完成第二部长片作品《祝福》(Blissfully Yours,又译作《极乐森林》),这也是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此后,阿彼察邦以大约每两年一部的拍摄周期,开始了他的电影长片创作:2004年,其导演的《热带疾病》(Tropical Malady)问世,影片表现了两个青年男子含蓄的同性恋关系,获得2004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这是泰国电影在国际三大电影节上获得的最高奖项;2006年,导演完成《综合症与一百年》(Syndromes And A Century),影片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的竞赛单元;2010年,完成里程碑式作品《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该片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大奖——这是泰国电影乃至东南亚电影迄今为止在国际顶级电影节上获得的最高奖项;2012年,导演完成《湄公宾馆》(Mekong Hotel)。阿彼察邦的最新长片作品是2015年的《梦幻墓园》(Cemetery of Splendour)。
从2000年的《正午显影》到2015年的《梦幻墓园》,阿彼察邦一共导演了8部电影长片。除2003年的《铁制小猫的奇妙冒险》属于商业制作之外,其他7部影片都是独立制作的艺术电影。在这些影片中,阿彼察邦用他诗性的视觉修辞方法、个性化的影像书写以及对泰国民族文化的内在关照,在电影语言的创新、电影风格的探索和电影文化的呈现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实验,从而使自己成为亚洲影坛最具个性的电影作者之一。
一、诗性修辞和哲意表达
阿彼察邦电影创作最重要的艺术特色之一便是其独树一帜的电影修辞手法。电影修辞“是指如何更好地运用视听技巧和艺术手段去传情达意,以便更形象生动地表达影片的思想内涵;即如何艺术地使用电影语言,以达到自觉的语言审美目的。”[1](P21)在阿彼察邦的影片中,大量长镜头、空镜头的使用,以及对细节和环境的唯美呈现,使其形成了一种诗意的美感。
长镜头的大量使用是阿彼察邦电影诗性修辞的显著特征。作为一种重要的电影语言,长镜头是电影创作中进行意义建构的重要手法。长镜头原指景深镜头,是相对于蒙太奇剪辑中的分解镜头而言的。在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看来,长镜头“使画面更具真实性,更能激发观众的思考和参与,更能表达现实的模糊性和多义性……能保持电影时间与电影空间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表达人物动作和事件发展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因而能更真实地反映现实,符合纪实美学的特征。”[2](P155)长镜头是相对于“短镜头”而言的,一般分为固定长镜头、变焦长镜头、景深长镜头、运动长镜头四种。长镜头的拍摄可以使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得以保持,具有很强的时空真实感,呈现出独特的美学特征,成为电影史上很多作者电影导演钟爱的创作手段。
阿彼察邦也不例外。从早期实验性质的《正午显影》到新近创作的《梦幻墓园》,他一直偏爱用长镜头以旁观者的视角冷静地记录人物的活动,有时候这种镜头长达数分钟。比如《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中布米躺在床上接受治疗的镜头,就足足有三分钟。在这组镜头中,摄影机被固定在床的一侧,面对窗户,像监视器般记录下了医生给布米叔叔做透析的过程。相似的镜头出现在《综合症与一百年》中,同样是医生给病人看病,阿彼察邦用一个长达数分钟的景深镜头冷冷地记录下医生给病人诊疗的全过程。镜头中,只有寥寥数语的简单对白,画面干净纯粹。在医院长大的阿彼察邦试图用这种纪实风格的镜头语言把疾病中的人的真实状态呈现出来,就像巴赞所说的,“唯有这种冷眼旁观的镜头能够还世界以纯真的面貌。”[3](P13)而“纯真的面貌”正是阿彼察邦在他的电影中试图表达的主旨所在。
一般来说,电影修辞包括“叙述性修辞”和“表意性修辞”,前者停留在故事层面,而后者则是对前者的突破与超越,达到意义层面。[4](P80)阿彼察邦的影片大多没有完整的故事,也不喜欢采用线性叙事手法来讲述故事,其影片充满了独特的诗性意境,这种诗性的修辞就属于表意性修辞。因此,在他的影片中,有很多表意性的镜头,这些镜头需要置于上下文的语境中方能领会其真正的内涵。《热带疾病》中的片头部分,有一个裸体男子穿过画面的镜头。这个镜头和前后两个镜头没有任何衔接,人物也没有任何关联。如果不与影片下半部分关于人和动物的传说相联系,就无法理解这个镜头的含义。这种表意性的镜头在阿彼察邦的电影中,并不少见。
空镜头的使用也是阿彼察邦常用的诗性修辞手法。空镜头即景物镜头,也就是画面中没有人物的镜头。空镜头在提供电影银幕形象信息方面有重要作用,它与人物镜头可以互补而不能替代,“是导演阐明思想内容、叙事故事情节、抒发情感、形成意境的重要手段之一。在银幕时空的转换和调节影片节奏等方面也有独特作用”。[2](P149)在阿彼察邦的影片中,空镜头成为导演建构影片风格、营造情境意境和表达意义内涵的重要手段。在《综合症与一百年》中,影片的第一个镜头便是仰拍的随风摇曳的树林,这个持续十多秒的镜头与《热带疾病》最后一个黑夜里的丛林镜头相呼应,暗示两部影片有着相似的关于疾病、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内涵结构。《综合症与一百年》直到第8分钟才出现影片的片名,出现片名的画面是一个长达三分钟的空镜头,呈现给观众的是医院外开阔的丛林和草坪。除了交代环境之外,这种持续时间较长的空镜头的运用是形成阿彼察邦纪实美学风格的一种重要表现手法。
声音造型同样是阿彼察邦善用的修辞元素。在他的影片中,人物简单,对白简洁。在很多段落中,影片通过环境的自然声音而不是人物对白来渲染情绪。比如前面提到的布米叔叔透析的镜头,在医生为布米叔叔治疗的过程中,两人几乎没有对话,只有窗外传来的鸟鸣虫吟的大自然的声音。即将死去的布米,和窗外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形成了一种对比,这种对比不是通过画面,而是通过声音来实现的。
在阿彼察邦的影片中,远景、全景和中景是最为常用的景别,极少出现人物的特写镜头,也很少出现移动镜头。在阿彼察邦的镜头中,观众能感受到时间和情绪在画面中静静流淌。法国电影理论家马尔丹说过,“由于电影画面含有各种言外之意,又有各种思想延伸,因此我们倒是更应该将电影语言同诗的语言相比。”[5](P7)正是用诗意的语言、诗性的修辞手法,阿彼察邦将他的电影打造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品,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二、分段结构和散点叙事
一部影片要讲述什么样的故事,有何种意图指向与其选择的叙事结构和方式有密切关系。电影叙事结构“与通常所说的电影蒙太奇结构含义相当,它表明一部影片的总体架构方式,包括时间畸变、空间呈示、叙述方式等各个要素和方面在一个统一的整体结构中的分解、配置、对应与整合。”[6](P324)电影的叙事结构是确立一部影片的基本面貌和风格特征的最重要的方面,“一部影片之所以能给观众予某种新鲜的感受、心灵的触动或情感的激荡,除了其主题的深刻和人物形象的丰满充实之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其叙事结构的架构别出心裁,并恰当得体,富有叙述上的层次感、节奏感和艺术韵味。”[6](P325)因此,选择什么样的叙事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一部影片的整体美学特质。在电影史上,大多数商业影片采用的是线性的叙事结构,而艺术电影则更多使用非线性叙事结构。如彪炳史册的《公民凯恩》《罗生门》等经典影片,均是非线性叙事结构的代表作品。“非线性电影叙事结构的最大特征在于单一时间向度的打破和解除,时间成为不连贯的片段并产生前后颠倒。”[7](P76)
同样,作为独立制作的艺术电影,阿彼察邦的影片多为非线性叙事结构,时间和空间常常被打破。如早期的《正午显影》,影片中主人公所处时间和空间的界限非常模糊,观众很难分清故事时空的边界。时间跨度最大的《综合症与一百年》,影片前后两个时空中的故事有一定关联,但相对独立,在叙事上没有因果关系。《热带疾病》中,肯和东的同性恋故事也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讲述的;影片后半段,东神秘消失,只剩下肯在神秘丛林中寻找神秘的怪兽。这些非线性叙事结构的采用,使得阿彼察邦电影呈现出一种虽然略为晦涩但却独具韵味的美学特征。
在叙事段落的安排上,阿彼察邦的大部分影片都采用了前后两段式的结构,且上半部分的时空和下半部分的时空往往是割裂的。比如《祝福》的前半部分是城市的空间,以阿荣和奥恩带领阿明看病为主要叙事线,下半部分则是三人在森林里的活动,在上半部分长达40分钟的叙事结束后,影片才打出片名字幕,正式进入彰显主题的下半部分;《热带疾病》亦是如此,上半部分表现的是童和肯这两个年轻男子朦胧隐晦的同性恋关系,下半部分则进入丛林,演绎了人和动物的神秘传说;《综合症与一百年》上半段是20世纪70年代的泰国乡镇医生的故事,下半段的故事则发生在30年后的曼谷;《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是即将死去的布米和他前世梦境两部分的结合;《梦幻墓园》前半段,男主角士兵一直在沉睡,下半段则是他醒来后的“梦境”。
阿彼察邦通过这种两段式的蒙太奇结构,将影片分为两个看似割裂但却有关联的部分进行对比,以此来对现在与过去、现实与梦境、社会与自然等主题进行探讨和反思。比如《祝福》上半部分书写的是人在现代城市里的窘境,下半部分表现的则是人在大自然中恣意忘我的放纵;《综合症与一百年》的前半段是过去,后半段是现在,人物相同,身份相同,只是空间和时间已经发生位移。
在阿彼察邦“轻情节,重情境”的叙事逻辑中,电影的戏剧性、逻辑性被淡化和消解,只剩下随意的、散漫的情绪表达,用散点叙事代替了线性叙事,用心理线索代替了故事线索,在缓慢慵懒的节奏中,带给观众一种平淡而隽永的审美体验。
三、神秘意象和文化关照
富含东方韵味的神秘主义美学气质是阿彼察邦电影最为重要的特征,也是其获得西方顶级电影节青睐的重要原因。在亚洲作者电影导演中,可以说阿彼察邦是少有的没有刻意去以“东方想象”迎合西方世界的导演之一。身处第三世界,阿彼察邦的电影同样容易被置于所谓后殖民主义语境中进行考察和解读。但和许多其他的亚洲作者电影导演不同,阿彼察邦并未在他的电影中有意地通过一些符号性修辞手法的运用对本国的历史或现实进行隐晦的批判或反思,以构建一种符合以西方为中心的所谓“东方主义”的审美旨趣,从而获得更大范围的认可。相反,阿彼察邦只是通过自己个性化的诗性语言,把根植于泰国本土文化的民族特性、宗教传统和人文气质以客观而冷静的方式呈现出来,而这些他在电影中所表达和呈现的“能指”以及语义背后的“所指”,以“他者”尤其是西方世界的眼光来看,无疑具有浓厚的东方意蕴和神秘主义的审美特征。对阿彼察邦来说,他的电影就是基于自己儿时的生活体验,基于自己对世界的想象而构筑的梦。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我希望我的电影能让你飘入梦境。梦就像吃饭、看电影一样是我们的日常所需,梦把你从一成不变的生活和思考方式里解放出来。我们都是囚徒,都需要靠梦逃出牢房。”[8]
梦境在阿彼察邦的电影中,的确是重要的意象符号。《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中,即将不治的布米梦到了自己的前世——一条跟因丑陋而伤感的公主在水中交欢的鱼;《祝福》中,非法移民阿明和阿荣、奥恩在丛林中休憩的片段,更像是伊甸园般的梦境,而阿荣也的确在依偎着阿明,慢慢睡去;《梦幻墓园》里患病的士兵大部分时间处于昏睡状态,当他醒来时,所经历的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影片没有给出答案。在阿彼察邦的电影中,梦境和现实的边界往往是模糊的,在他散点叙事的语境中,观众有时候很难分辨出影片中哪些段落是现实,哪些段落是梦境。而这正是阿彼察邦要达到的审美效果。
万物有灵、业报轮回、因果报应等来自佛教的哲思也是阿彼察邦电影中神秘意象的彰显。在95%以上的国民信仰佛教的泰国,佛教文化对电影的影响无法回避。对泰国人而言,“佛教已深深地渗入到泰国人的心理和民族性格之中,成为泰国人判断是否和衡量伦理道德的准则,成为泰国人的精神寄托。”[9](P210)同样,对于精神世界外化形态的电影来说,佛教给予了泰国电影丰富的精神滋养,而电影也成为佛教传统的重要文化载体。因此,在泰国的文化传统中,对鬼神的敬仰,对自然的敬畏,对宗教的笃信,已经成为其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精神要素。阿彼察邦电影中,同样显现泰国文化中固有的宗教因素,体现了泰国人对神灵、鬼魂的超然态度。比如,在《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中,当布米在晚餐时看到显灵的妻子和成为鬼猴的儿子时,并没有感到恐惧或惊讶,而是像往常一样,和他们坐在一起平静地交流。《祝福》中,阿明带着阿荣和奥恩在丛林里闲逛,阿明和阿荣不经意地讨论起日本兵的鬼魂。在他们看来,只要自己上辈子不做亏心事,就不用害怕鬼魂。因此,哪怕在幽幽的密林里,他们也不会有太多的畏惧。可以说,在阿彼察邦的镜头中,没有对鬼魂、神灵、野兽这些灵异的形象进行刻意修饰,没有为他们营造常见的恐怖意向,而是以一种超然的态度,让他们自然地出现,然后自然地消失。
丛林是阿彼察邦电影中的重要符码。在他看来,茂密的、充满生机的丛林是人类的精神归宿。被现代工业社会物质化了的人类,只有在丛林中,才能找回自我。于是,《祝福》中的阿明、阿荣和奥恩在经历都市生活的苦恼后,来到森林中的伊甸园,享受着人的最本能的快乐;《热带疾病》中变成了人形的老虎最终回到森林回归本性;《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中布米则在丛林深处“子宫”一样的洞穴里找到了归宿。高楼林立的都市在阿彼察邦眼里,也是另外一种形态的丛林,只是,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丛林里,人们更多的是痛苦,只有在拥有灵性的大自然的丛林中,人们方能找到最元初的自我,获得真正的快乐。
或许在阿彼察邦看来,人类社会就是一个病态的有机体。福柯曾说,疾病是生命里的派生物。[10](P170)在阿彼察邦的影片中,生命与疾病成为重要的叙事要素。《祝福》中的阿明因为得了奇怪的皮疹,于是去看病,由于没有合法证明,医生因此拒绝给他开药,痛苦于是纷至沓来。《综合症与一百年》讲述的本就是医生和病人的故事;《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中,布米因为肾衰竭,逐渐走向死亡,因此回忆起自己的过去;《梦幻墓园》则是关于一个士兵患病沉睡不醒的故事。可以说,“疾病”在阿彼察邦电影中是一种独特的存在,这固然与阿彼察邦自幼和父母生活在医院里,因而对疾病以及疾病带给人的痛苦有独到的体验和理解有很大关系,但阿彼察邦影片中的疾病意象,显然并非只是儿时记忆的再现,而是对生命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层次的探讨。
四、民族想象与自我认同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他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太大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接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11](P6)对民族的想象意味着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这是人类深层的心理建构。电影无疑是这种想象建构的重要叙事载体,电影创作者和观众正是在创造和接受电影中的民族文化意象的过程中,共同完成了对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正如萨义德所说的,“人类身份不是自然形成的、稳定不变的,而是人为构建的,有时甚至是凭空生造的。”[12](P427)当然,对电影而言,这种人为的身份构建本身也是其艺术创作的主旨之一。
而在对身份认同的主体性建构过程中,“他者”是不可或缺的。萨义德说过,“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12](P426)在萨义德看来,每一时代和社会都会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对新时期的泰国电影来说,这一他者无疑是想象和发明了“东方”的西方。正是新时期泰国电影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让西方世界“发现”了从属于东方文化体系的泰国电影,并对泰国电影进行西方视角中的解读和阐释。而在与西方对话的过程中,以阿彼察邦电影为代表的泰国艺术电影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特性,充满异域风情的影像风格,重塑了西方对东方的想象,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他者”语境中的主体性。
民族电影是身份想象和主体建构的载体,集结了集体意识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努力。在阿彼察邦的电影中,泰国特有的民族和文化符号也时有出现,如《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中,与鱼在水中交欢的泰国公主,布米叔叔死后的充满宗教色彩的葬礼,成为僧侣的东,回来看望布米叔叔的珍的鬼魂,都是典型的意象化的泰国文化表征符号。而在多部影片中出现的村落、野兽、丛林等,也都是地处热带地区的泰国所特有的地域符号。通过这些符号化电影元素,在一定意义上建构了一种阿彼察邦眼中的当代泰国的社会生活图景,在一定程度上使导演和泰国观众完成了对本民族的身份想象和认同。
结 语
在丰富多元的亚洲艺术电影创作版图中,阿彼察邦用他个性化的诗性语言,散点式的叙事结构,民族化的主题表达,呈现给我们一个极富艺术魅力的电影世界。在电影创作一向注重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泰国,阿彼察邦电影像一颗熠熠发光的珍珠,在为泰国赢得世界级荣誉的同时,也带给世界观众独特的审美体验和思考。在他的引领下,泰国独立电影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越来越多的导演开始投入到艺术电影的创作中,并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2009年,狄也·阿萨拉(Aditya Assarat)导演的《奇妙小镇》(Wonderful Town)、2010年阿诺卡·苏维查库朋(Anocha Suwichakornpong)导演的《俗物人间》(Mundane History)、2011年西瓦罗·孔萨库(Sivaroj Kongsakul)导演的《永别》(E-ternity)以及2015年杰括瓦·尼坦隆(Jakrawal Nilthamrong)导演的《穿越消失点》(Vanishing Point)均获得了当年的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虎奖。在阿彼察邦的引领下,泰国独立电影已成为世界艺术电影领域的一道独特风景。
(责任编辑 彭慧媛)
[1]周斌.论电影语言与电影修辞[J].修辞学习,2004,(1).
Zhou Bin,On the Film Language and Film Rhetoric,Rhetoric Studies,No 1,2004.
[2]许南明,富澜,崔军衍.电影艺术辞典[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Xu Nanming,Fu Lan and Cui Junyan,Dictionary of Film Art,Beijing:China Film Press,2000.
[3][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崔君衍,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
Andre Bazin,What Film Is,trans.by Cui Junyan,Beijing:China Film Press,1987.
[4]郦苏元.袁牧之的电影修辞艺术[J].当代电影,2009,(2).
Li Suyuan,The Film Rhetoric Artof Yuan Muzhi,Contemporary Film,No 2,2009.
[5][法]马赛尔·马尔丹.电影语言[M].何振淦,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
Marcel Martin,Film Language,trans.by He Zhengan,Beijing:China Film Press,1980.
[6]李显杰.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Li Xianjie,Theory and Practice of Film Narration,Beijing:China Film Press,2000.
[7]游飞.电影叙事结构:线性与逻辑[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0,(2).
You Fei,Film Narrative Structure:Linear and Logic,Journal of Beijing Film Academy,No 2,2010.
[8]李宏宇.泰国导演阿彼察邦的电影修辞[N].南方周末,2012-02-09.
Li Hongyu,The Film Rhetoric of ThaiDirector Apichatpong,Southern Weekly,9 Feb.,2012.
[9]姜永仁,傅增有.东南亚宗教与社会[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2.
Jiang Yongren,Fu Zengyou,South-eastern Religion and Society,Beijing: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2012.
[10][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M].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Michel Foucault,The Birth of the Clinic,trans.by Liu Beicheng,Nanjing:Yilin Press,2001.
[1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trans.by Wu Rwei-ren,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5.
[12][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Edward Said,Orientalism,trans.by Wang Yugeng,Beijing:Sanlian Bookstore,1999
Poetic W riting of the M ysterious East:Interpretation of the Film s by Apichatpong W eerasethakul
CuiYing,Zhu Danhua
In recent years,Thai films have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iverse landscape of Asian films.Featured with unique ethnic culture and narrated in regional images,Thai films created a unique filming paradigm whichmakes Thailand a representative emerging power in Asia,following China,Japan,Korea,India and Iran.Among creators in Thailand,ApichatpongWeerasethakul is a leading figurewhomake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His film is rooted in the indigenous ethnic Thai culture and he uses poetic film language,non-linear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oriental imaginary representations,such as dream,forest and illness,to constructan artistic film world with his personal temperament.These films open a space of rich ethnic imagines and also are identified by Thai people.ApichatpongWeerasethakul is therefore regarded as one of themost unique film authors in Asian filmdom.
Thai film,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poetic rhetoric,independent film
J902
A
1003-840X(2017)03-0116-07
崔颖,昆明理工大学南亚东南亚新闻传播研究院研究员、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助理,博士;朱丹华,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昆明 650504
http://dx.doi.org/10.21004/issn.1003-840x.2017.03.116
2017-05-08
About the authors:Cui Ying,Researcher of th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for South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and Assistant-to-the-Dean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Media at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Zhu Danhua,Lecturer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Media at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Kunming 65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