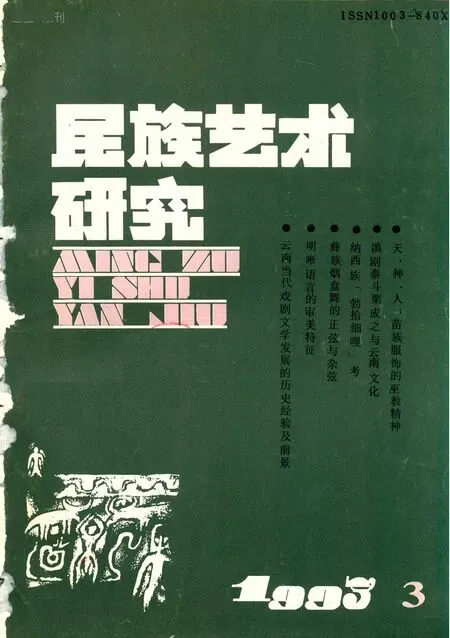戏曲音乐创作的古今变迁
路应昆
戏曲音乐创作的古今变迁
路应昆
近数十年来戏曲音乐的创作情况与过去时代有很大差异。在过去时代,艺人的创作以满足观众需求为第一目标,可归结为“观众主导”,作品是走通俗路线,创作自由度很大。文人的创作是为了“自见才情”,可归结为“创作者主导”,作品定位于高雅,不仅追求精致,而且注重格律,以致昆腔也走上“格律化”之路。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戏曲剧团由政府包办,创作首先是为完成上面交给的任务,故可说是“政府主导”。近三四十年来戏曲音乐创作成绩不理想,其中一个基本原因是对观众需求的忽视。要重新跟上时代,需要真正重视观众,调整创作定位,改进作品评价方式,加强人才培养,并给创作者以更大的自由空间。
戏曲音乐;新戏音乐创作;戏曲音乐传统与创新;戏曲观众
戏曲音乐的创作成就,最终是由创作者的自身状况、创作的目标、创作的具体方式以及相关社会环境等因素综合决定的。在过去时代,戏曲音乐的主要创作力量是艺人,同时也有一些文人,两种人的自身状况差异很大,他们在创作上的做法和所取得的成就也有很大不同。20世纪50年代以后,戏曲音乐的主要创作力量是国营剧团中的音乐人员和一些演员,同时在新的剧团体制下创作者与观众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而戏曲音乐的发展方向和所取得的成就也与过去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本文先对过去时代的戏曲音乐创作状况作一些简单回顾,再将近数十年来的戏曲音乐创作与过去时代的状况作一些简单对照,希望这样的对照有助于我们更自觉地把握当今戏曲音乐创作的方向。
一、过去时代艺人的创作:观众主导
过去时代艺人从事戏曲演唱和创作是为了谋生,他们的“上帝”是观众,他们必须把娱悦观众、满足观众需求作为第一目标,因此可以说他们的创作是“观众主导”(或者说是“市场主导”)。娱乐市场的竞争自然很“无情”,但既有“劣汰”,也有“优胜”,优秀艺人可以名利双收,这必然对艺术的发展形成强有力的刺激和推动。艺人创作的自由度也很大,最重要的只是让观众满意和不被市场抛弃。作品内容方面避免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统治者相冲突即可,如不违背“忠孝节义”等伦理原则、不“亵渎圣贤”、不鼓动“犯上作乱”等。艺术方面更没有什么约束。为了赢得市场,艺人的创作只能定位于“通俗”,即不走“曲高和寡”路线,而且艺术上很开放,时时自我更新,以不落后于时尚。例如清代的梆子、皮黄等俗腔俗戏,由于创作上自由不羁(一切以当时当地观众的喜恶为转移),竟被文人斥为“乱弹”。又如20世纪20~40年代在上海打拼的越剧,原本主腔是一唱众和、无管弦伴奏的“呤哦调”,进入上海后主腔出现一系列重要变化:先是去掉帮腔、加入胡琴伴奏创成“丝弦正调”,后又改变胡琴定弦变化出“四工调”,再后来胡琴定弦又变而形成“尺调”——短短20多年的时间越剧的主腔完成了一个漂亮的“三级跳”,前后几种主腔的音乐表现力完全不在同一个档次。如果不能紧跟市场需求而在艺术上作一而再、再而三的大步前进,就不可能打造出越剧这样一个极富生命力的剧种。正是这种一切以观众为转移、从不自我设限的创作意识,保证了数百年间艺人能在风云多变的市场上站稳脚跟,戏曲音乐的总体局面也由此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戏班的组织和活动形式,也完全根据市场卖艺的需要来设置。戏班与艺人的雇佣关系很灵活,戏班需要随时吸收对观众有号召力的艺人以增强竞争力,优秀艺人也总有用武之地。艺人在戏班之间的流动,成为戏班之间交流艺术的一种渠道。例如清代后期不少地区的昆腔班难以维持时,不少艺人流入乱弹班,乱弹班即得以吸收昆腔的很多东西。戏班还常常跨地区流动,繁华的城市常常成为戏曲的活动中心,戏曲因而能找到最适宜的生长土壤。戏班的自由流动意味着各地戏曲的自由“杂交”,这对于戏曲的整体发展来说十分有利。上面举到的越剧之例便很典型:出身于浙东嵊县的“小歌班”如果不打进上海等大城市,在既充满挑战,也充满机遇的环境中打拼,就不会有后来的越剧。又如清中叶后的北京如果不能海纳百川式地吸纳各地戏班和艺人,让徽调、汉调在北京扎根,后来的京剧也无从谈起。戏班的开放使得一个戏班可以兼容多种声腔,这对戏班的生存和发展也十分有利,因为自身手段丰富,才有随时根据观众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而自我调整的余地。例如清后期北京的徽班先主唱昆腔,后又主唱皮黄,如果不这样自我调整,也无法孕育出京剧。无数事实表明:在市场环境中,如果没有艺术上的高度开放和创作上的高度自由(包括艺人搭班自由、戏班流动自由、艺术上“杂交”和创新自由等),戏班连生存都会成问题,更遑论戏曲音乐在清代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繁荣。
当年艺人的创作又具有“大集体”的特征,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情况:其一,已有作品中的音乐材料(腔调、板式、器乐曲、锣鼓点等)都属于公共资源,不同戏班、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艺人在创作新作品时都可以自由搬用那些材料,这类可以“共享”的材料(包括它们的组织使用套路)用今天的话讲便是“程式”。其二,在利用既有程式进行自己的创作时,艺人们可以分别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程式进行各种各样的修改,艺人们当然也可以在程式之外另创新的音乐形式,但不论是艺人对程式的修改形式还是艺人新创的形式,马上又可以作为新的“共享”材料在别的作品中搬用(即又成为新的程式)。这种对音乐材料的共同使用、共同加工和共同创造,总体上便形成“大集体”式的创作。总体上看这样的“大集体”创作具有“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好处,而且一种程式在反复使用中经历各种修改加工的过程,就是千锤百炼和获得新的表现力的过程,新程式的陆续加入也使“程式库”的包容越来越大,戏曲音乐由此形成一种层层积累式的发展模式。
程式的共享显然是一种方便法门——过去时代的艺人(演员、琴师)无法得到专业的作曲训练,音乐创作能力不足,大量运用程式的做法则为他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例如新戏的唱词“套上”现成的腔调就唱(可根据需要作调整),当然是“轻车熟路”。本来一部新戏的音乐创作是一项浩繁的工程,但运用程式便可让整个创作过程“短平快”地完成。有大量程式可以利用,戏班便不需要设专职作曲,演员自己就可以利用程式来为一部部新戏编创唱腔(也常与琴师合作)。演员自编唱腔还有一种好处,便是可以随演随改,即随时根据观众的反馈来调整改进唱腔(包括随时得到琴师的帮助),以至每一场演出都可以成为一个再度加工和创造的机会。
当然程式的反复使用也容易带来重复之弊,例如同一种唱腔在不同的戏里一再搬用,听上去大同小异,新鲜感必然越来越抵,这与“艺术贵在独创”的原则是相冲突的。娱乐市场上的喜新厌旧倾向很突出,“通俗”艺术一旦跟不上时尚就会被市场抛弃,因此不仅程式不能一成不变地套用,而且程式之外的创造尤其显得重要。对程式进行加工的做法只能形成渐次积累式的变化,进步幅度小(近于今天所谓“移步不换形”),可说是一种“爬小坡”式的发展。在程式之外另创新腔和新形式的做法则进步跨度大,甚至可以促成剧种音乐的显著提升,又可说是“上台阶”式的发展。两种做法在戏曲音乐的历史上是混杂兼用、相辅相成的:普通情况下“爬小坡”的做法居多,显得相对平稳;到了一定关头又会出现“上台阶”式的跨越,由此开启的新局面。前一种做法较容易,一般艺人都能使用(只是水平不齐)。后一种做法则难度很大,不是随处可见,应该是由很有创造力的艺人在某种时刻“发明”。但那样的“发明”一旦推出,“后果”便非同寻常。前面说到的越剧的主腔在二十至四十年代经历的数度更替,便是连上几个台阶(可称为“三级跳”),后来的主腔尺调与最初的主腔呤哦调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又如在南北曲范畴内,明中叶水磨昆腔问世也是迈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南北曲音乐由此被推上了顶峰。从戏曲音乐的全局来看,历史上曾经跨过的几个最大台阶,包括从小曲小调一类发展到南北曲的曲牌体,从简单的上下句数唱发展到梆子、皮黄的板腔体,以及板腔体取代曲牌体成为唱腔主流体制,这几次跨越每一次都把戏曲音乐带上了新的高度。戏曲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后来居上者:宋元时才开始形成大戏(此前只有小戏),但明清时已成为中国音乐最高创作水准的代表,而只用“爬小坡”的做法当然无法达到那样的高度。就像越剧如果始终只是在呤哦调的格局内“爬小坡”,而不去打造尺调等新主腔,越剧音乐根本不可能有后来的成就。至于什么情况下“上台阶”,什么时候“爬小坡”,还是取决于具体的观众需求和创作者的情况——笼统讲:只有当观众需求有显著的提高,创作者也有适宜的条件施展其创造才能时,戏曲音乐才会跨上新高度,推出新境界。
以往一些研究者只强调以程式为基础的创作方式,对离开程式“上台阶”的做法缺乏认识,因而主张新戏的创作完全不能离开程式,只能“爬小坡”,这种认识当然不够全面。有一种看法认为沿用程式才是保存“传统”,离开程式就是丢弃或破坏“传统”,这种看法也不全面。艺人编创新戏时大量使用程式是为了创作上的需要(上面已说到),而不是为了保存传统。艺人自然会尊重和尽量延续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但具体到新戏创作,艺人最重要的考虑还是观众和市场,其他一切都要为营业的需要让路。艺人通常没有力量撇开市场专门承担保存传统的重任,正因为此过去时代戏曲大量的优秀成果无法保存下来。梅兰芳与一帮文界、财界的朋友兴办国剧学会在保存传统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舞台生活四十年》的记述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梅兰芳在编演新戏时首先考虑的还是观众的需求,他不会纯粹为了保存传统而不顾观众的需求在新戏里沿用程式。上面已说明艺人的做法是两手并用:一手是尽可能利用程式,一手是在必要时离开程式另辟新路——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传统”。
还有些研究者把艺人对程式的沿用解释为注重规范,即把程式当成了规范。这里需要注意区分的是:程式只是技术手段,只是为创作者预备的形式材料,程式自身的规格也只是技术层面的,而技术手段并不等于艺术,程式完成得中规中矩只是合乎技术标准,那样的“规范”还不等于艺术上的“好”。艺术当然离不开技术手段,一定的技术手段也可以赋予作品以某种形式感,但技术并非艺术的全部,技术要运用得好、变化得妙,才是真正的艺术,而且最好的创作总是要突破旧格,使作品焕发新的光彩。过去时代艺人大量沿用程式主要是为了手段处理上的便利(把前人的创造拿来作为自己的基础),而不是为了在艺术上约束自己。
在强调为观众服务的同时,艺人仍然有一定的“表现自我”的空间,优秀艺人还可以显得“游刃有余”。“大集体”协作和大量运用程式的创作方式很容易淹没个人的独特创造,但杰出的艺人仍然能够展现突出的艺术个性,例如京剧史上谭鑫培的“谭腔”、程砚秋的“程腔”,便都已成为个人品牌。但艺人的自我表现不能脱离观众的喜闻乐见,“谭腔”“程腔”都是在赢得大量观众喜爱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品牌,而不是撇开观众孤芳自赏的结果。优秀艺人追求个性表现并不是无视观众,而是为了满足观众的更高欣赏需求。
二、过去时代文人的创作:创作者主导
元杂剧和明清传奇都主要由文人创作,尽管文人主要是为曲牌填词和写剧本,很少直接创作音乐,但他们的创作追求和填词制曲的方式都对南北曲的音乐有很大影响。元杂剧的音乐留存资料甚少,音乐创作方面的情形已难于详知。明清传奇完全是以文人为创作主导,文人除了填词撰剧,也对音乐创作有深度参与,对场上演唱有重要指导,故文人很大程度上也是传奇音乐的创作主导。下面看看文人与传奇音乐创作的关联。
文人从事戏曲创作的目的和艺人很不一样。文人撰剧制曲不是为了取悦“广大观众”和在市场上获利,而是为了“自见才情”,即展露文才和寓托情志。文人作者也要寻求知音,但范围只在高雅之士的小圈子内,而不会去取悦小圈子之外的“俗人”。这样的创作显然是以创作者自我为中心,可说是创作者主导,而不同于艺人创作的观众(市场)主导。为了充分体现自己的创作追求和娱情悦性,一些文人除了填词撰剧,还要置办家乐,即自养歌儿舞女,悉心调教,以让自己的作品(也可以是其他文人的作品)能在“红氍毹”上完整展现,观演者自然也不超出亲朋好友的小圈子。这样的场上呈现当然也与艺人在公众舞台上的“卖艺”完全不是同一性质。文人能为自己的作品编配音乐(主要是谱曲配腔)的应该很少,他们常需聘用民间曲师来为其作品谱腔,有时也会聘用民间昆班来演唱自己的作品,但受聘为文人之作谱腔的曲师和为文人演唱的昆班,一定都是按照文人的意图和要求来处理作品。既然填词撰剧是文人的个人行为,作品的搬演也是由文人一手主持,传奇的创作便完全是以文人为主导,与市场和“广大观众”没有直接关联。文人也有一些着眼于“风世”和宣扬儒家伦理的作品(如《琵琶记》之类),该类作品自然也希望能为“广大观众”接受。但文人撰写该类作品的目的仍然不是取悦民众和卖钱,而且该类作品也并不是传奇的主流。
传奇(连同其音乐)的创作既然是以创作者自己为主导,创作的自由度便非常大。在思想内容方面,传奇也不会背离“忠孝节义”,不会亵渎圣贤,不会鼓动“犯上作乱”,但这些都是出自文人对儒家思想的信奉,而不是“被迫”。男女情爱是文人最热衷的题材(以至有“传奇十部九相思”之说),但描写男女突破礼教、自相爱恋的作品最后也要回到“奉旨成婚”之类轨道。在艺术方面,文人的创作更完全是自作主张,除了文人之间的互相评品,其他也不会有什么人来对创作者指手画脚。市场上普通观众是否欢迎文人之作,文人不会在意。文人普遍不屑“媚俗”,李渔的传奇创作常有在富贵之家“打秋风”的目的,以至有“一夫不笑是吾忧”之类说法,但很多文人看不起李的行为和创作,李的作品也不能代表传奇的主流。
文人的文化素养高,衡量艺术的尺度也高,他们的创作大力追求优雅精致,而不屑于“通俗”。为了炫示文才和品位,文人在创作上常常不避苛难,苦心孤诣,甚至可以“十年磨一剑”,这种做法与艺人在创作上的“短平快”形成鲜明对比。文人之作当然也有水平高低之别,但至少每一位文人作者期许的目标是很高的。传奇在填词撰曲方面的精益求精做法,也保证了传奇音乐的品位。魏良辅等曲家创制的水磨昆腔,便完全是根据文人在音乐方面的“阳春白雪”标准打造。该种唱法强调“字清为一绝,腔纯为二绝,板正为三绝”①“字清、腔纯、板正”可解释为演唱准确表达字音,腔调保持纯净,板拍对文词字句的处理遵循规范。[1](P7),而且演唱风范要求“闲雅整肃,清俊温润”,以“气无烟火”为最高境界,这些都是文人的曲乐理想的典型体现。当然为传奇作品配腔的曲师也有水平高低之分,一些优秀之作的唱腔精美而别致,达到了明代及清前期音乐创作的最高水准,也有一些作品的唱腔尽管“中规中矩”,却缺乏“意趣神色”。但总体上看水磨昆腔的品位是很高的,与民间戏曲的俗腔俗调完全不是同一种档次。
文人相互之间的作品评鉴,与音乐相关的话题通常只是曲牌填词是否合乎格律,文人对格律的看重又与昆腔的发展道路有重要关联。文人填词制曲不仅要求文词典雅华美,而且讲求格律,即遵守字句格式、平仄音韵等方面的一系列规定。在这种填词制曲注重形式规范的做法影响下,昆腔走上了“定腔定谱”之路:清代前中期宫廷编制的“曲谱”《南词定律》《九宫大成》为众多曲牌注上了工尺,后来的曲家便把那些工尺当成了每支曲牌的标准腔调样式。其后曲家在为新填词的作品谱腔时,便大都是以《九宫大成》中的工尺作为一支支曲牌的音乐框格(只作细部加工),而不再另创新腔。后来编昆腔曲谱的曲家和曲师们,也几乎都是采用旧谱“编订”的做法(称为“订谱”),即对前代留下的曲谱进行选编和作一些细部修订,而不另创新谱。这便是所谓“定腔定谱”。这种“定”意味着昆腔在《九宫大成》等曲谱问世之后,其音乐也被“格律化”了,而曲牌音乐的格律化正是曲牌文词格律化的一种延伸结果。但曲牌文词的格律化与音乐的格律化有一个重要差别:一支曲牌尽管词格固定,但填上不同文词后不会有很强的“重复感”,因为文词内容是千变万化的,只是词格的重复不容易让人觉得单调;一种腔调则比一种词格“感性”得多,因此同样的腔调一再反复,很容易失去新鲜感,甚至会显得乏味。昆腔的很多腔调材料又为诸多曲牌共用,这更会使腔调在总体上显得重复多而变化少。因此昆腔在音乐上的格律化,实际上意味着音乐的基本“止步”。本来同一曲牌用不同腔调配唱的情形在南北曲中相当普遍,而且昆腔的音乐直到《长生殿》依然颇有生气,但在音乐全面格律化后,昆腔的路子已变得很窄,音乐上已很难打开新的境界。文词强调“按律填词”暗含着抬高创作门槛的用意,填词由此成为一种“难处见才”的专门技能,音乐的格律化同样会让曲牌配腔成为只有熟谙“曲谱”的曲家才能掌握的特殊技能,一般艺人则难以措手。从后来的情况看,能按“曲谱”规范配腔的曲师数量很少,这也使得昆腔的音乐创作无法像乱弹那样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这对昆腔在音乐上的发展也相当不利。
贵溪冶炼厂的含铅物料中主要存在元素为:Cu、Fe、Sb、Sn、Se、Te、As、Ni等元素。各元素可能存在的最大量为:10%Cu,10%Fe、5%Sb、5%Sn、3%Se、3%Te、4%As、5%Ni。分取10.00 mL浓度为5 mg/mL铅标准溶液于300 mL烧杯中,分别加入上述元素的最大量,按分析步骤进行测定, 测定结果见表3。
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文人主导的创作既然与市场无关,其存活和发展便完全取决于主人自身的状况。明后期文人十分优游,纵情艺文声色者甚多,传奇创作在该时期即形成“彩笔如林”“词山曲海”的盛况。清康熙时传奇仍然盛行,作为传奇发展顶点的《长生殿》《桃花扇》两部杰作亦问世于其时。但雍正时突然官宦之家“禁蓄声伎”,家乐趋于销匿,政治高压也使本来热衷创作的文人几乎停笔,文人境况的转变,对传奇创作来讲可谓釜底抽薪,传奇从此一蹶不振。此后文人的处境再未恢复到明后期那样的状况,传奇也再未抬头(基本上不再推出新的佳作)。昆腔在音乐上的“止步”,也显然与传奇在整体上遭遇“断崖”的情形很有关系。
清代的民间昆班把不少传奇作品改造成一系列折子戏在公众戏场上演唱,传奇的部分成果得以在场上延续生命。昆班的演唱属于市场卖艺性质,因而折子戏里增入了大量的“通俗”成分(传奇原作中的“曲高和寡”部分相应被删除很多),但传奇的不少东西仍然被延续下来。昆班的演唱常常精致细腻,注重规范,更多固守经典和“规范”,很少创新开拓(尤其音乐方面),这些倾向便主要来自传奇,与形式粗放、创作上完全自由不羁的乱弹形成鲜明对照。例如道光时北京昆班的艺人情形:“所存多白发父老,不屑为新声以悦人。笙、笛、三弦,拍板声中,按度刌节。韵三字七,新生故死。吐纳之间,犹是先辈法度。……虽未敢高拟阳春白雪,然即欲自贬如巴人下里固不可得矣。”[2](P310-311)这种恪守“先辈法度”、不愿迈出新步的做法,意味着艺术上不再攀登新的高峰,加上对普通观众欣赏需求的漠视,昆班在市场上自然难以立足。清后期在乱弹繁盛、新戏新腔不断涌现的形势下,昆腔只能黯然走向消歇。
在清代“四大声腔”中,昆腔品位最高,但生存格局最小,可谓“峤峤者易折”;乱弹(以梆子、皮黄为主)最“通俗”,最能满足广大观众(其主体为普通民众)的需求,即最能对付市场,因而最兴盛,这样的反差很引人注目。文人的传奇创作以自我表现为中心,追求“阳春白雪”格调,努力打造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对戏曲提升高度做出了极重要的贡献。但该种路数的创作不仅对创作者的文才和精神境界有很高要求,对创作者的地位和相关社会环境也有很高要求,那样的主客观条件在很多时候都无法具备。戏曲(戏剧)从本性来讲是一种需要面向广大观众,需要“当场”实现价值交换的艺术,否则就会连基本的生存保障都没有,因此文人传奇尽管有很独到的成就,却不能成为戏曲发展推进的“主路”。
三、现今体制下的创作:政府主导
20世纪50年代后的戏曲创作,在一系列重要方面上都与过去时代大不相同。这六十多年来戏曲音乐的创作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尤其近三四十年来戏曲音乐的创作总体显得乏力,较之过去时代也有某些提升,但总体看离时代的要求越来越远。将这六十多年来的戏曲音乐创作与过去时代的情形作一些对照,对思考今天戏曲音乐的走向或许有一定帮助。
这一时期的戏曲音乐创作,首先与文艺体制的变革有重要关联。20世纪50年代起,全国主要戏曲剧团都变为“国营”,即由政府包办:剧团数量和规模由政府掌握,负责人由政府任命,经费主要由政府拨给,创作和演出任务由政府最终掌控,有关部门还以评奖、立项资助等方式对创作进行引导和鼓励。这种局面与过去时代的状况全然相异,最基本的一个不同便是艺人变成国营剧团的戏曲工作者后,他们的“上帝”已不再是广大观众。在这样的体制下,戏曲创作的首要目标既不是为广大观众提供娱乐品,也不是创作者的自我表现,而是完成“上面”交给的任务。因此这一时期的创作既不是“观众主导”(像过去时代的艺人创作那样),也不是“创作者主导”(像过去时代的文人创作那样),而可说是“政府主导”。剧团的这种归属和职能定位在过去时代未曾有过。例如明清时期宫廷也曾自养戏曲艺人,但那样的剧团是皇家独享,并不面向社会,与今天的国营剧团性质完全不同。
又因不同地区的剧团分别由当地政府掌管,剧团也不能像过去时代的戏班那样自由流动了,剧团可以赴外地演出,但不能在别的地方落户。在新戏创作中,保持“剧种特色”(主要体现在音乐上)也成为一项重要要求,各地政府部门常常是把当地剧种的新戏创作当成“文化政绩”来打造,相应也要求不同剧种各自保持其“剧种特色”(即不能“像”其他地方的剧种)。因而“京剧姓京”“川剧姓川”之类“剧种意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强。“剧种特色”又被认为都体现在声腔上,因此三百多个剧种之间声腔不再自由“杂交”,对戏曲之外的音乐的吸收也很有限,这种局面也与过去时代大不一样。
在“国营”体制下,戏曲从业者有基本生存保障,按理想状态讲可以专心从事艺术,编演新戏时也不必担心能否在市场上赢利。这样的体制尤其便于集中优质资源打造“高精尖”之作,民营剧团无法具备这样的优势。但要实现这些优势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如领导者是否懂行和有强烈责任心,制定的方针政策是否有偏差,用人是否得当等等。体制是双刃剑,发挥优势时戏曲会大大受益,反之戏曲也会严重受损。例如在“文革”时期,“样板戏”的打造取得突出成绩,同时“样板戏”之外的“万马齐喑”又对戏曲全局造成极大损害,两方面的情况都显示了体制力量的强大。
“文革”结束后“万马齐喑”局面不复存在,而且总体看政府在新戏创作方面有很大的投入。但近三四十年来戏曲音乐创作的总体成绩并不理想。一个突出问题是:在时代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而且变化速度越来越快)的情况下,戏曲音乐的发展创新落越来越落后于时代的需求。这种落后可以用两种尺度来衡量:一是观众数量的大小,一是艺术水准的高低。两项标准同时满足当然最好,但只满足其中一项标准也已是不落后于时代:简言之,“通俗”之作可以赢得很多观众,“高雅”之作可以达到很高艺术水准,“雅俗共赏”则可以同时满足两个方面的要求。下面分别看看这一时期的戏曲音乐创作在赢得观众和提升水准两方面的相关情况。
20世纪50年代后,很多剧团(尤其大剧团)都有了专职作曲人员,这无疑加强了戏曲音乐的创作力量,尤其有利于为戏曲音乐注入新的成分,同时也对新戏音乐与观众的关系有较大影响。50~60年代的普遍做法是作曲者与演员协同创腔,尤其老艺人与作曲者(多为上级派进剧团的新音乐工作者)的合作能互补长短,如此打造的不少唱段都能得到观众的喜爱。近些年来则几乎完全变为作曲者独力创腔,演员只是照谱唱,这种情况下作曲者表现“自我”(发挥个人创作才能)的成分常会增大,而且他们往往更愿意向“高精尖”努力,而不满足于“通俗”,这种状况很容易导致对观众需求的淡忘。再者,过去时代艺人自己创腔(常与琴师合作)时,一般不会形成“定腔定谱”的自我约束,演唱者可以随时根据观众的反应修改唱腔,反复调适,不仅可以灵活适合每一场观众的具体需求,而且随时有出新的可能。但在唱腔由专职作曲者编创的情况下,通行的是“定腔定谱”和一个版本打天下的做法,这意味着新戏唱腔一般不再有反复锤炼和根据观众反馈随时修改的可能,意味着作品很难“紧贴”每一场观众的具体需求。
再看新戏音乐创作的水准问题。新戏音乐创作达到的高度不够,首先与创作者的队伍(水平)和相关创作条件有关。政府掌管剧团、主导创作,也意味着创作人才的选汰与过去时代完全相异。过去时代观众是花钱看戏,对艺术的要求很苛严,市场的激烈竞争意味着优胜者可以得到很高的回报,不适者则会出局,这样的“自然淘汰”会对创作有极大的刺激和推动作用。在剧团由政府包办的情况下,创作人才也主要是靠体制来培养和选拔。近数十年来演员的培养很受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有显著成效,音乐创作人才的培养却未得到足够重视。戏曲音乐的创作无疑需要“特殊人才”,因为既要掌握一般作曲家的全套本领,又要吃透戏曲音乐(乃至整个民族音乐)的传统,这样的人才很需要发挥体制的“特事特办”长处提供特殊方式的培养,但此项工作一直未受到重视。时至今日戏曲音乐创作队伍的老化和的青黄不接已越来越严重,没有一流的创作力量,当然不可能有一流的创作。
新戏音乐创作达到的高度,也与创作中长期遵行的某些“指导思想”有重要关联。在新戏创作中,音乐的创新要求和剧本、导演、表演、舞美的创新要求很不一样:剧本等方面的出新幅度常常很大,早已与传统戏相去甚远(常常不听音乐便不知道是哪个剧种,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戏曲),创作者们的口头禅也常常是“现代性”“现代转型”乃至“国际化”之类,唯独音乐步履蹒跚,出新幅度大大低于其他方面。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差,主要是因为“保存剧种”“延续传统”的重担完全压在音乐身上,即由音乐独力承担延续剧种的责任,新戏唱腔一旦与老戏唱腔距离较大,便会招来“毁剧种”的指责。在剧本、导演、表演、舞美等方面都在努力实现“现代转型”,音乐却在努力维系“传统”的情况下,音乐拖新戏的后腿,以致被视为制约戏曲(整体)发展的“瓶颈”就完全不奇怪了。音乐的这种进退失据(新也不是,旧也不是)的处境,似乎提示我们在新戏中用音乐维系“剧种特色”的“指导思想”需要作必要的反思了。音乐必须固守“剧种特色”、不能脱离“程式”等理念(有时也被当成“方针政策”),主要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戏曲音乐的“传统”形式与当时观众的欣赏需求总体看还距离不远(1949年以前的东西都被视为“传统”)。但到现在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社会文化环境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戏曲音乐的“传统”与当今时代的距离已无疑增大了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半个世纪前的“指导思想”今天是否应该一成不变地照搬,自然会成为一个问题。
进一步思考,前面已说到过去时代艺人的创作是“爬小坡”和“上台阶”两种做法兼用,因此只用固守“剧种特色”和不离“程式”来概括过去时代戏曲音乐的发展道路显然不全面。在50~70年代的新戏(包括京剧“样板戏”)音乐创作中,其实也有“上台阶”的做法。例如在50年代的黄梅戏《天仙配》《女驸马》的音乐中,已有对老黄梅戏音乐的大跨度的变革。总体看黄梅戏音乐创作在当时是上了一个大台阶,而且直到今天很多人印象中的“黄梅戏特色”相当程度上是五六十年代新建的。但近三四十年来在戏曲唱腔创新方面迈出的步子,总体来看反而不如前面二三十年。在时代需求发生巨大变化,很需要音乐“上台阶”的时候,我们的创作还在一味“爬小坡”,其结果当然是与时代的距离越拉越大。从这样的事实来看,在音乐创作方面仍然被遵行的某些“指导思想”恐怕需要根据新的时代需求作必要调整了。“音乐语言”其实也有很鲜明的时代感,并不比剧本、表演、舞美的形式手段更能“超时代”。举例说吴梅在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教书时曾用昆腔曲牌〔锦缠道〕谱写过一首“北京大学校歌”①可阅陈均《吴梅昆曲写北大》一文的介绍,载《大公报》2012年9月2日。,板拍、腔调均依照昆腔传统规格——已无法知晓当时的北大有多少师生认可该首“校歌”,至少今天的北大是绝不可能把该曲作为“校歌”来唱的,四五百年前的“音乐语言”与当今学子的精神风貌实在相去太远。
还需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新戏艺术质量的监控。在剧团由政府包办而不是依赖观众和市场生存的情况下,新戏在艺术上的成败也不是由市场和观众来检验,而主要是由领导和评审专家评判。新戏的质量常常以评奖作为检验方式,评奖是由政府主持,评审专家的人数一般也不多,其中戏曲音乐的专家更是寥寥无几。近些年来获奖新戏总数已不少,但其中在音乐上很成功并广受观众欢迎的似乎举不出几部来,这种情况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现有作品评价方式存在的问题。关于评审专家的人数,可以对比的一个数字是美国电影奥斯卡奖现在每届的评委是六七千人(分为十多个专业评审团),评委人数的多少对评奖结果的“代表性”当然有重要影响。奥斯卡奖不是政府奖而是专业奖(由专业机构主办,评委全为专业人士),该奖在艺术上的说服力,以及评审结果所体现的专家眼光与观众口味的关系(也可说艺术与票房的关系),都值得我们注意。
总体看近数十年来戏曲音乐的创作情况颇为复杂,涉及问题较多,找到解决办法更不容易。但不管怎样,至少一些“常识”是应该明确的。首先从戏曲的社会生存来看,戏曲总要有观众,观众数量也不能太少,没有观众戏曲就成了无根之木,因此观众才是戏曲生命力的最终代表。尽管现今体制下观众已不再是戏曲主要的“衣食父母”,但对戏曲来讲不靠观众养活就不在乎观众是非常不明智的。很多剧团都已到了上面一旦“断奶”就没有活路的地步,因为它们早已丧失市场生存能力,可见有没有观众依然关乎戏曲的生死。从领导角度讲,“振兴戏曲”的口号已喊了30多年,如果始终没有观众,“振兴”就成了一句空话。而要赢得观众,创作者就一定要把观众作为最重要的服务对象,观众不一定是经济意义上的“上帝”,但至少应该还是艺术的“上帝”。政府作为戏曲事业的“主导”,一项重要职责便是引导和督促剧团真正为观众而创作,把重新赢得广大观众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并采取相应措施,这应该是对戏曲的一种最根本的指引。
再从戏曲自身发展来看,创作与观众脱节,作品表达的思想感情会不接地气,艺术上也会失去最可靠的试金石。事实上在不需要面对广大观众的情况下,创作的质量很难得到保证。没有观众的喝彩,创作也会失去最强有力的和刺激和推动。就像食物应该是为食客做的,食物做得如何也要由食客来评品,食客的喜爱无疑是对厨师的最大褒奖。如果好的创作得不到来自观众的激励,水平不够的创作不会被淘汰,这必然会导致创作者动力不足,并对创作质量产生根本影响。
要赢得更多观众,创作就必须走“通俗”之路,即充分重视“普通人”的欣赏需求。“雅俗共赏”当然更好,但那样的“共赏”只能是通俗的提高,故前提还是通俗——如果连通俗也做不到,雅俗共赏从何谈起?高不成低不就的东西也无法冒充雅俗共赏。通俗与低俗不能画等号,市场上的低俗之作一定情况下也能赢得不少观众,但总体看在市场上最风光、最有生命力的并不是低劣之作。例如当年京剧的“三鼎甲”“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等等在市场上立足都不是靠低俗,他们中的佼佼者还能走上雅俗共赏的高度。当然“阳春白雪”有高度,也应该努力争取,但阳春白雪的前提是艺术至上,就像明清时期的文人传奇,需要创作者完全自主,创作必须是纯粹的自我表达,而不是做应命文章,也不需要看任何人的“眼色”,那样的条件显然很难具备。还需要明确“和寡”不一定就是“曲高”,没有观众喜爱不一定就是“阳春白雪”,就是“高精尖”。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以赢得观众和跟上时代为目标,就应该给创作者更大的自由空间。创作者必须根据具体的观众需求来确定自己的做法,具体到哪个剧种、哪一部戏、哪一段唱腔以及需要什么样的出新等等,都应该由身处第一线的创作者自己审时度势并作相应处置。艺术创作本是高度复杂和需要有灵思妙想的智能活动,简单化、一刀切式的“指导思想”或“原则”之类并不能解决具体问题,外行在艺术上“指导”内行的做法应予避免。而要走“通俗”之路和强调跟上时代,就不能不高度重视创新,什么时候“上台阶”和什么时候“爬小坡”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此外创作成果的最终评判也要依靠观众——一方面创作者要树立真正为观众服务的意识,一方面要靠观众来严格检验作品,由此建立创作者与广大观众的良性互动机制。总之创作者是真正意义上的“责任人”,而且“责权利”(责任、决定权和回报)需要真正统一于创作者一身,这是创作取得实质性进步的必要前提。
(责任编辑 何婷婷)
[1]〔明〕魏良辅.曲律[A].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五集)[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Wei Liang fu,Qu Lyu,in Collection of Works of Chinese Classical Traditional Operas,Vol 5,China Drama Press,1959.
[2]〔清〕杨懋建.长安看花记[A].张次溪辑.清代燕都梨园史料[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
Yang Maojian,Looking at Flowers in Chang'an,in Zhang Cixi(ed.),Historical Materials of Liyuan(Opera Circle)in Yandu of Qing Dynasty,China Drama Press,1988.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the Creation of Opera M usic
Lu Yingkun
In the past decades,the creation of operamusic has changed a lot.In the past,the need of the audience was prioritized in the creation of the artists.Thatwas an“audience-led”one in which the work was on a popular route and the creation was free of restriction.In addition,the creation of the literatiwas for the“talents of themselves”and thiswas“creator-led”by which way thework was elegant and was emphasized on delicacy and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forms,leading Kunqu vocalization to be“standardized”. Since the 1950s,the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troupeswere organized by the government so that the creation was for the assigned tasks and its form was a kind of“government-led”.The achievementof the operamusic creation in the last three to four decades,however,was not satisfying and one of themain reasons is the disregard of audience's needs.In order to catch up with the times,therefore,it is needed to consider the audience,to re-orientate the creation,to improve the assessment of the works,to enhance the education of talents and to allow more freedom to the creators.
operamusic,creation of the new operamusic,the tradition and creation of operamusic,audience of the opera
J605
A
1003-840X(2017)03-0005-10
2017-05-10
路应昆,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 100024
http://dx.doi.org/10.21004/issn.1003-840x.2017.03.005
About the author:Lu Yingkun,Research Fellow and PhD Supervi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Arts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