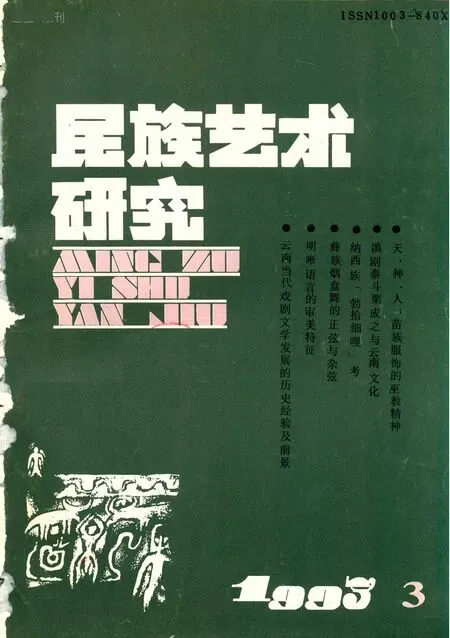比较美术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李倍雷
比较美术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李倍雷
比较美术学尽管没有成为一个学科建立,但是美术方面的比较研究在汉代就有了萌芽。作为比较美术学的实践研究与有关理论研究大概在明清之际就有了,明朝时利玛窦来华带来了西方宗教绘画艺术,他也曾对中国绘画进行了评价;中国明代的顾起元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教绘画也有过评述,这应该是较早的中西美术交流与比较美术学方面的实践研究。此后从清人邹一桂、外籍画家郎世宁伊始至21世纪,有关比较美术学方面的主体探讨几乎未有间断。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90年代以来是比较美术学主体研究的高峰期,出现了“美术比较”系列丛书的实践研究以及《比较美术教程》《中西比较美术学》等理论著作。时至今日,学者们提出了建构比较美术学学科的构想,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比较美术学的理论问题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比较美术学;发展;历程;实践研究
1581年(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Matteo Ricc)来到中国,将西方美术传入中国以降,中西美术的交流、碰撞就没有停止过,且愈来愈频繁。与此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的中西比较美术学的发轫时期。中国明代顾起元(1565-1628)在《客座赘语》中对西方美术这样评论:“脸上之凹凸处,正视与生人不殊。”清代画论家姜绍书的《无声诗史》评论了当时利玛窦带到中国的绘画作品:“眉目衣纹,如明镜涵影踽踽欲动。”这是中国较早的中西比较美术的观念意识。中国明清时期的这种美术评论,基本上是看到了西方异质文化背景下美术层面的技法和逼真的视觉效果。当然也有站在中国自己的文化立场上做出的某种判断和比较。如清代的邹一桂、松年等人尽管在某些方面延续了前面画论家的文化立场,但他们的中国文人画家立场更鲜明一些,因而做出了像西方美术史论家初始进行的美术比较的态度,做了中西美术形态价值高低、优劣的判断,提出了西方绘画“虽工亦匠,不入画品”的比较美术观点。松年的观点大致相同,认为“板板无奇”“无馀蕴矣”,这都是对西方美术做了价值判断层面的比较。无论怎样,这已成为中国比较美术学的开端。
一、比较美术学在中国的初始阶段
中国美术与外域的交流非常早。按照郑午昌的考证:“考域外画家之来中国,当以骞霄国人烈裔为始。”但是“其画与中国并不发生影响”。“汉室既东,印度佛画随佛教流入中国,吴人曹不兴,即以范写西国佛像为我国佛画祖。自是晋之卫协、顾恺之皆以善佛画名高一代。至南北朝时,中国画家之稍知名者,尤无不擅长佛画……明清之际,西洋教士布道中国者,如利玛窦、汤若望等,亦常以宗教画为宣传之具……于是中国画坛,于印度佛教美术宣告涅槃以后,又受西洋耶教美术之洗礼矣。”[1](P112)郑午昌描述了中国美术接受外来美术影响的一个历史的史实。作为中国与西方美术的交流,学术界都认同始于明末时期的利玛窦。这一点在明代的文人笔记和画论家的文献中评论了这一事实,并做了比较研究。譬如:明代文人顾起元在他的《客座赘语》笔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利玛窦,西洋欧罗巴国人也。面皙,虬须,深目而睛黄如猫。通中国语。来南京,居正阳门西营中。自言其国以崇奉天主为道。天主者,制匠天地万物者也。所画天主,乃一小儿,一妇人抱之,曰天母。画以铜板为帧,而涂五彩于上,其貌如生。身与臂手俨然隐起帧上,脸上之凹凸处,正视与生人不殊。[2](P1344)
顾起元的描述,是比较客观的视觉描述,没有比较高低、优劣,仅仅是感受到画的“与生人不殊”,认为西洋绘画非常逼真。明末清初的画家兼理论家姜绍书在《无声诗史》中,对当时利玛窦带到中国的绘画作品做了几乎相同的评论:
利玛窦携来西域天主像,乃一女人抱一婴儿,眉目衣纹,如明镜涵影,踽踽欲动。其端严娟秀,中国画工无由措手。[3](P133)
顾起元和姜绍书对西方绘画都是从“写实”的角度比较的,“与生人不殊”“如明镜涵影”就是这种比较的结论。并且姜绍书还把“如明镜涵影”作为绘画的一个写实的标准来看,认为“中国画工无由措手”,达不到西洋绘画那种写实的功夫。这个“标准”已经包含了中国画论家的形态研究的性质了。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自西方美术输入中国开始,比较美术学的比较意识和观念在中国就开始了。无论是文人笔记性的评述还是画论家的评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以自己的文化逻辑为基点,看待和评论西方美术,也把西方美术与中国美术作一些比较性的研究。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明清是中国的比较美术学的开端。
曾经在宫廷作画师的邹一桂,直接受到西洋传教士画师的影响。他对西方绘画的熟悉程度应该超过了顾起元与姜绍书,尽管他也认为西方绘画具有“令人几欲走进”的逼真视幻效果,但依然认为有工匠之气而“不入画品”。这完全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和以文人画为基本标准来看待西方绘画的形态和观念,还没有站在一个跨越中西文化视域的高度来认识和理解中西美术的深层不同特质,明显有如同利玛窦那样的在中西美术的比较中做高低、优劣的比较,也远远没有进入到通过比较研究达到深入了解不同文化和美术形态的层次。当然,任何不同性质的文化背景下的美术形态,在初次的接触、碰撞中,必然做出的本能反应就是高低、优劣的比较。
伴随中西美术的不断交流,清代的美术理论家们对中西美术的认识也有所加深。晚清的松年(1837—1906)在比较中西美术时,似乎不像邹一桂那样偏激。他在《颐圆论画》中云:
西洋画工细求酷肖,赋色真与天生无异。细细观之,纯以皴染烘托而成,所以分出阴阳,立见凹凸。不知底蕴,则喜其工妙。其实板板无奇,但能明乎阴阳起伏,则洋画无馀蕴矣。中国作画,专讲笔墨勾勒,全体以气运成;形态既肖,神自满足。古人画人物则取故事,画山水则取真境,无空作画图观者;西洋画皆取真境,尚有古意在也。[4](P839)
松年在这里抓住了中西美术各自的表现形态和文化特征,提出了中国画与西洋画“皆取真境”的观点,做了较为客观的分析和评论。应该说这是中国比较美术萌芽时期所采取的比较客观的应有的学术态度和所使用的有效的研究方法。我们也在这里看到了中国的比较美术学建构在某种程度上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变。
20世纪初期,比较美术学的方法逐渐被国人所重视,这与当时的文化革新派和新文化运动中主动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背景密不可分。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使国
人自觉接受西方的文化理念和科学精神,改良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主张。美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自然也在改良之列。最早提出改良中国画的当是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吕澂以及蔡元培等人。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文化态度恰恰与清朝时期的画论家们相反。康有为1904年在意大利看到了拉菲尔等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作品时,无不激动却又偏颇地认为:“吾国画疏浅,远不如之。”这自然与康有为不懂美术有关。康有为随即将西方绘画与中国传统文人画进行了高低、优劣的比较。他说:“基多利腻、拉飞尔与明之文征明、董其昌同时,皆为变画大家。但基、拉则变为油画,加以精深华妙。文、董则变为意笔,以清微淡远胜,而宋元写真之画反失。彼则求真,我求不真;以此相反,而我遂退化。若以宋元名家之画,比之欧人拉飞尔未出之前画家,则我中国之画,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故以画论,在四五百年前,吾中国几占第一矣,惜后不长进耳。”[5](P134)对于不懂美术的康有为来说,与其认为他是在说外行话,倒不如说是看到西方先进科技和强大的经济时,受到强烈冲击的文化心理的压迫感所致。对于力图维新的康有为来讲,看到中国绘画的“衰微”,他必然要把西方的美术与西方的科技经济优势联系在一起做文化上的思考。并且康有为的这种思考被陈独秀、吕澂用到了极致。陈独秀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西洋画写实精神。”[6](P10)康有为、陈独秀等提出的改良中国画的方法,都是趋同用西方的写实绘画的方法,在德国选修过美术和美学课程的蔡元培亦是这种思想。蔡元培说:“今世为东西方文化融合时代。西洋之所长,吾国自当采用……故望中国画家,亦采用西洋布景写实之法。……用科学方法移入美术。”[7](P226)他们异口同声地强调要用写实的方法植入和改良中国画,目的是要提倡科学的精神。西方的写实方法,包含了科学的元素。透视学、色彩学、结构学、解剖学以及光影明暗等,是与物理学、光学、医学等科学联系的结果。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带来丰富的物质文明,使贫穷落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进步的,绘画也不例外。在这种偏激的文化心理压迫下的中西美术的比较意识,自然会认为中国美术是落后的,必须是要改良或改革的。不难看出,文化心态的不平等,必然导致在中西比较美术上认识的不平等。
当然,我们也看到另一面。蔡元培毕竟是受到过美术教育和美学教育的中国学者。早在1916年蔡元培在《智育十篇》中作过较客观的中西美术的比较:“中国之画,与书法为缘,而多含文学之趣味。西人之画,与建筑、雕刻为缘,而佐以科学之观察、哲学之思想。故中国之画,以气韵取胜,善画者多工书而能诗。西人之画,以技能及意蕴胜,善画者或兼建筑、图画二术。”[8](P53)持这种平等的文化心理,所得出的比较研究结论,才是比较正确的,这给日后中国的比较美术学的正常发展,奠定了一个健康而良好的学术基础。
美术史家和美术家们看问题与当时的许多文人知识分子的心态有些不同。中国美术史学者郑午昌在1931年说:“若研究艺术者自认为是中国人,为中国民族之一分子,并和中国民族所以能永久巍然存在于世界之最伟大能力,使在文化,则于研究外国艺术之暇,亦宜注意民族的艺术,至少不可毫无根据,谩骂中国艺术为破产,为毫无意义。要知在表面武力经济竞争急烈的现世界,而其里面的文化竞争,或许更为急烈。”[1](P119)郑午昌站在了文化的高度来认识中西美术的关系问题,跳出了局限在科学技术、经济是否发达或先进的层面,并对高低、优劣的美术比较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认为那是毫无意义的。刘海粟在《石涛与后期印象派》一文中认为:“欧人所崇拜之塞尚诸人,被奉为一时之豪俊、溶发时代思潮之伟人而致其崇拜之城,而吾国所生塞尚之先辈,反能任其湮没乎。”[9](P69)显然,刘海粟把中国清代具有变革精神的石涛与法国具有变革精神的塞尚进行了比较研究,批判了那种动辄以西方美术为先进的思想的看法。稍后的中国画家兼美术史论家谢海燕面对西方绘画与中国绘画的关系时指出:“比较中西艺术之质量,就其盛衰之所当然,而知其所警励,努力以谋我国艺术之复兴。”[10](P48)总是还有一番中西美术之较量的感觉。画家兼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在1941年撰文《西洋美术对中国美术之影响》,主要反对西方现代主义野兽派为首的马蒂斯等,主张用古典的雕刻作为中国美术学习的样本。由于存在对西方现代主义流派认识的偏激,故此也影响到他对印象派的看法,难免还有一些认识上的错位和误区。如徐悲鸿在《中国艺术的贡献及其趋向》(1944年)说:“有如米芾的画,烟云幻变,点染自然,无须勾描轮廓,不啻法国近当代印象主义的作品。而米芾生在十一世纪,即已有此创见,早于欧洲印象派的产生达几百年,也可以算是奇迹了。”[11](P899)印象派主张对光的写实,强调视觉中阳光下的自然色彩的各种变化,而中国的米芾的“烟云”山水画并没有这种追求。
进入学术层面着力中西视域下美术关系研究的是向达。向达在《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的论文中,自觉地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对中西美术进行了比较研究,严密考证西方美术对中国明清美术的全面影响。作者从明代万历初年至清代乾隆末年二百年间,中国在接受西方美术过程中的态度以及西方美术的传播者、传播途径、传播范围、传播方式等,进行了充分的考证与钩沉,论证了上至宫廷下至民间的中国美术与西方美术的关系,从学术层面指出了中国明清绘画如何受到西洋绘画的影响。他通过比较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可见明、清之际,所谓参合中西之新画,其本身实呈一极怪特之形势:中国人既鄙为伧俗,西洋人复訾为妄诞,西画家本人亦不胜其强免悔恨之忱;则其不能于画坛中成新风气,而卒致殇亡,盖不待蓍龟而后知矣。”[12](P513)应该说,向达的这篇论文是中西比较美术走向自觉与成熟的标志。
如果说向达的比较美术学研究方法是运用影响研究的成功典范,那么稍后宗白华的研究便是形态研究的成功典范。他的《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西画法所表现的时空意识》是比较美术学中形态研究的两篇代表作。宗白华从中西方美术的发生学角度,客观地将中西方绘画渊源关系作了比较与研究,由此针对中西绘画的不同表达方式和文化心理,以形态研究为理论基础,展开了比较研究。宗白华用美学的理论,把中西绘画提升到境界层次的高度,分析、研究和比较了中西绘画形而上的构成形态与结构关系。宗先生认为:“因中、西画法所表现的‘境界层’根本不同:一为写实的,一为虚灵的;一为物我对立的,一为物我浑融的。”[13](P102)关于中西美术的空间问题,宗先生认为中国画基于“中国特有的书法空间表现力”,西方绘画“给予我们一种光影构成的明暗闪动茫昧深远空间(伦勃朗的画是典范)。”[14](P142-143)宗白华的形态研究方法和结论,真正地把握了中西美术的各种关系,寻求具有可比性的因素,而不是简单地、生硬地、作毫无关联地“拉郎配”式地的比较,跳出了刘海粟20世纪20年代《石涛与后期印象》的生硬比较,摆脱了其研究初期的那种不成熟的简单的“X加Y”的研究模式。宗白华的研究方法,是跨越中西文化视域下的形态研究的方法,在整体上寻求有比较基础的共同因素,也避免了高低、优劣的比较。可以认为,宗白华先生的研究方法,拓展并确立了比较美术学中的形态研究的方法。
由此以后,中国学者逐渐拓展比较美术学各种层面的研究。这表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跨中西视域的比较研究中。譬如台湾学者凌绍夔、张燕云、李霖灿、陈士文等的研究。凌绍夔的《中西绘画之本质基点器材与技法之同异》,提出了中西美术都有某种共同的因素:“置重于客观形象,并非绝无情意之内涵。置重于情意之表现,亦非绝对放弃客观物象。”[14](P2)就是说,中西美术的表现并不是把“情意”和“形象”决然对立起来的,而是都有顾及,只是各自的侧重不同而已。李霖灿《论中国山水画与西洋风景画》、陈士文《中西画学与画人》以及马白水《中西绘画特性》等都从不同视角讨论了中西美术的异同关系。值得关注的是,方豪的《嘉庆前西洋画流传我国的史略》、戎克的《万历、乾隆期间西方美术的输入》等,考证了明清历史中西方绘画的流传问题,主要对其传播者的路径做了研究,为影响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将比较美术学的方法向实证方面推进了一步。
纵观上述研究,明末清初以降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中国比较美术学发生转折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研究奠定了中国比较美术学的学术基础,尤其是向达和宗白华等人的研究,确立了中国比较美术学的“变迁研究”和“形态研究”的基本方向,中国比较美术学的实践研究开始走向成熟。由于历史的原因,此一时期的比较美术学,重点涉及范围在明清时期的中国美术与西方的写实主义的美术方面,讨论和研究跨文化视域的现代派美术的较少。
二、比较美术学在中国的发展阶段
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的比较美术学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伊始,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文化、思想、哲学、美学、艺术等思潮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西方美术思潮和美术作品成为当时中国艺术家追逐和模拟的样本。80年代初期,在中国画坛产生很大影响的油画作品,如罗中立的《父亲》和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前者受到西方超写实主义美术的影响,后者受到19世纪法国乡村现实主义美术影响,跳出了当时中国油画普遍受到苏联美术影响的局限。中国传统绘画同样受到西方各种美术思潮和流派的影响,走向了中国水墨试验的道路。最具标志性的是中国“8·5新潮”。这是一个受到西方美术形态、美术思潮、美术流派强大影响而产生的美术运动,它与中国其他现代文化诸如文学和哲学等,共同形成了中国文化艺术的“现代性”的开端。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开始了诸多“比较”研究:比较文学、比较美学、比较历史学、比较宗教学、比较法学、比较经济学等,在这种“比较”的学术潮流和文化语境中,中国的比较美术学实践研究也随之迅速地再次展开。
但是,对比较美术学本质的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依然比较混淆。由于80年代是中国美学热的年代,因此,一些学者或研究者把本该属于比较美术学的研究范畴混淆在“比较美学”的范围之内了。譬如当时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由曹顺庆编的《中西比较美学文学论文集》中,收集的有宗白华《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郑为《后期印象派与东方绘画》、邓福星《绘画的抽象性》、伍蠡甫《试论诗中有画》等。坦率地说,这些研究性的论文应该是“比较美术学”的研究成果,不属于“比较美学”的研究成果。这也许是由于形态研究中借用了美学理论,或者在比较美术学的讨论中涉及到美学的问题,编者就把这类比较美术学的研究成果作为比较美学的研究成果。当然在随后的“方法论”讨论的热潮中,大多数学者逐渐意识到方法的重要性,并且把方法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学者一方面梳理如何对待接受西方美术的问题,一方面又研究方法论的问题。以中西美术的“差异性”审视不同性质的美术形态和美术思潮,并以此作为比较研究的基础,以“异质性”延伸和发展了中国的比较美术学。在比较美术学的研究过程中,包含了“比较”的方法的运用。邓福星在《美术史、论研究方法刍议》中提到了“中外美术比较”“历史研究比较”和“综合比较”。其目的是:“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西艺术的异同,可以促进人们对我国的优秀艺术传统有更深入的认识。”[15](P58)“8·5新潮”是中国美术与西方美术大碰撞的重要标志,其中包含了中西美术思想理论和中西美术思潮的大碰撞。不少人在这个大碰撞中,注意到了比较美术学的重要价值与意义。这时期的美术刊物不断增加,纷纷刊登了不少比较中西美术的研究性文章。
比较美术学的一些实践研究,突出在对中西绘画方面的研究上,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热点。譬如郑为《后期印象派与东方绘画》(1981年)、齐凤阁《以形显神和以神统形——兼谈中西画家的审美意识》(1983年)、蔡祖武《试论中西艺术的本质差异》(1984年)、潘公凯《中西传统绘画的心理差异》(1985年)、徐书城《中西画法异同辨》(1985年)、杨成寅《中西绘画发展的历史规律性》(1985年)、李公明和李行远《艺术中的人与自然——中西方艺术传统的比较与反思》(1986年)、潘耀昌《西洋透视和中国界画——两种透视法的比较》(1986年)、陈池瑜《中西诗画中的时空艺术之比较》(1986年)、陈德胜《中国画与西方表现派绘画一议》(1987年)、伍蠡甫《国画之我与西方表现主义之我》(1987年)、罗培坤《中西表现说差异论》(1988年)、吴晶范《试谈中西美术创作中的“形似”与“神似”——兼论中西美术有关形似美的共同规律》(1989年)。这些比较美术学的实践研究,说明中国的比较美术学具有一定的深度走向。
我们还要注意到1984年10月24日至27日,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在湖北武汉举办了“中西美学与艺术比较讨论会”。尽管这是美学学会主办的中西美学与艺术方面的比较讨论会,但相关的一些论文涉及到比较美术学的问题。这个学术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比较美术学的深入发展,并由此从比较美术扩展到了比较艺术。80年代末期,比较艺术的概念也被提出,这大概是受到了美国艺术史论家罗伯特·沃夫曼《比较艺术理论》的影响。他的这篇文章在1988年被齐小新翻译介绍在《世界艺术与美学》刊物上,随后1989年李心峰的《比较艺术学的功能与视界》在《文艺研究》上刊登出来。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比较美术学,因为是在较多地吸收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展开比较美术学的研究,难免有一种情绪在里面,暗含了某种民族主义的心态。学术研究一旦有了情绪,必然会影响到学术的正常化发展。好在,这种“情绪”不在多数人,也并没有持续多久。
自1980年以后,中国的比较美术学逐渐深化。学者们在相对平和的心态下,认真对待中西方的美术问题,同时也逐渐意识到话语权和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也出现了明确的“比较美术学”的概念。袁宝林在1998年撰写《比较美术学教程》,首次提出了“比较美术学”的概念,同时做了系统的研究。总体来看,80年代以来中国的比较美术学有三种研究倾向:一是对中国明清时期美术与西方美术交流关系和影响程度与广度的再认识;二是西方现代与后现代艺术对中国当代美术的影响和相互阐释;三是有目的、有意识地构建比较美术学的体系。
我们不妨先看第一种研究倾向。对中国明清美术受到西方美术影响的史实,学者们一般从“放送者”“接受者”“路径”和“媒介”等方面入手研究。譬如傅乐治《中国的贸易画》(1984年)、沈康身《从〈视学〉看十八世纪东西方透视学知识的交融和影响》(1985年)、包遵信《山水·人物·时代精神:明清文人画和文艺复兴时期绘画比较》(1986年)、梁江《院画与清代美术思潮》(1986年)、潘耀昌《西法中国画的先行者——纪念朗世宁诞辰三百周年》(1987年)、洪再新《传统与归属——十八世纪欧洲与中国美术交流叙要》(1987年)、水天中《油画传入中国及其早期的发展》(1987年)、杨伯达《朗世宁在清内廷的创作活动及其艺术成就》(1988年)、阮荣春《西洋画在中国的“肇始期”汇考》(1989年)、吴甲丰《士大夫眼中的西方绘画》(1992年)、陈莹《清朝广州的外销画》(1992年)、谢文勇《十九世纪初广东西画的传入和外销画的盛衰》(1992年)、田毅鹏《西洋画入传中国始末》(1993年)、徐新《明清中西美术交流和朗世宁画派》(1994年)、聂崇正《清代外籍画家与宫廷画风之变》(1995年)、袁宝林《潜变中的中国绘画——关于明清之际西画传入对中国画坛的影响》(1995年)、莫小也《近年来传教士与西画东渐研究评述》(1996年)、逸弓《欧洲对远东艺术的欣赏:一个历史纲要》(1997年)、胡光华《西方绘画东渐中国“第二途径”研究之评述》(1998年)和《传教士与明清中西绘画的接触与传通》(1999年)、叶农《明清之际西画东来与传教士》(2000年)、周正平《明清之际西洋绘画在中国衰退的缘由》(2000年)、江莹河《乾隆御制诗中的西画观》(2001年)等。这些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美术与西方美术的交流和受其影响的比较美术研究成果,大多是从学术层面对中西方二者的接收者、放送者与途径作了史实性的考证。与此同时,中国台北故宫(1987年、1991年)、北京故宫(1988年)、香港艺术馆(1997年)、澳门艺术博物馆(2002年)等地举办了有关的明清人物画展,针对与明清时期相关的中国美术作品,举办了中西美术比较理论研讨会等,促进了比较美术学的发展。这一时期其相关的专著不断产生,譬如:聂崇正《清代宫廷绘画》(1992年),杨伯达《清代画院》(1993年),聂崇正《朗世宁》(1994年)和《宫廷艺术的光辉——清代宫廷绘画论丛》,莫小也《17-18世纪传教士与西画东渐》(2002年),李超《中国早期油画史》(2004年)等。在很多的讨论中,对高居翰的《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这部有关中西美术比较的专著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见解。其中对高居翰的“影响说”提出了较为尖锐的批判。郑培凯在《明末清初的绘画与中国思想文化——评高居翰的〈气势撼人〉》中指出:“作者对本土影响的可能性避而不谈,却长篇累牍讨论根本无法证实的西洋版画影响,这到底怎么回事?是作者认为本土影响不重要?还是作者之一心想着证明自己的‘风格及思想观念’理论,以开创新的研究方向,故此对本土影响也就视而不见了?”[16](P85)
总之,有关中国明清美术的比较研究成为中国比较美术学的一个重点研究范畴和一种突出的现象。
我们再看第二种研究倾向。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术界逐渐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现代与后现代二者的关系的认识和梳理也有了深度的进展,中国美术理论界对后现代艺术思潮也有了更多的认识。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波普艺术家伊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nberg,1925-)在中国北京等地相继表演了他的波普艺术以后,中国逐渐对西方的后现代的各种表现形态不断地进行挪用、模仿与移植。最突出的是1989年2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当代艺术展”,成为中国全面接受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公开化的标志。至此,中国的比较美术学关注的又一个热点便是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后现代艺术及其思潮关系的研究,并且形成了很多不同的观点和研究视域,其争论也颇大,同时研究的对象已经越过了传统美术概念。很多美术形态已经不是传统美术能够涵盖得了的。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和艺术思潮的影响,艺术的概念被拓展或被解构,流行艺术或称大众艺术的形态成为新的比较研究的对象。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的比较美术研究的一个基本走向。
在这个研究走向中,出现了较多有代表性的比较美术的研究成果。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外,还有朱青生《现代派与东方》(1985年)、齐凤阁《试论西方现代派绘画与中国文人画的异同》(1985年)、杭法基《后现代派和中国绘画》(1986年)、陈履生《西方现代派和中国文人画》(1986年)、王菊生《中国美术和当代西方“审美无利害关系”理论》(1987年)、陈德胜《中国画与西方表现派绘画一议》(1987年)、王以时《试谈西方现代派的“反传统”意识与中国古典美术的“同构性”》(1987年)、冯晓《宇宙观、美学致思与中西绘画》(1987年)、罗培坤《中西表现说差异论》(1988年)、陈伟利《中外绘画美学现象比较》(1989年)、高名潞《当代大陆新潮美术——新潮美术在中国当代美术格局中的地位及意义》(1991年)、邵大箴《写实主义和20世纪中国画》(1993年)、林木《对本世纪中国美术几个问题的检讨》(1999年)、沈亚洲《谈中国绘画的不同抽象方式》(1999年)、杨成寅《石涛画论与西方现代主义》(2000年)、邓福星《中西美术中象征形象与观念比较》(2002年)、章利国《中西画家的文化眼光与艺术观照》(2003年)、高千惠《当代艺术思路之旅》(2003年)、张朝晖《当叛逆沦为时尚》(2006年)、王南溟《观念之后:艺术与批评》、李倍雷《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的反思》(2008年)、漆澜和徐可《超越图像的中国新绘画》(2008年)、王洪义《从乌托邦到商品化——中国当代美术的复调结构》(2008年)、卫小乌《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从回溯历史开始》(2008年)、段炼《图像的堕落》(2009年)等。这些研究倾向中,有的研究者注意到了中西美术的不同表现形态特征,以及表现形态后面的审美形态和文化形态等的差异。这种对异质形态研究的方法,我们归纳为“形态研究”。当然形态研究不是孤立的,对复杂的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与中国当代艺术的碰撞与交流等关系的研究,仅仅使用形态研究的方法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的研究方法。因为关于现代与后现代艺术层面的比较美术学的实践研究成果,其比较研究范围有些已经超越了传统美术的概念,美术在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中,审美形态被解构,难以称为“美”的艺术。多数状况下使用的是“艺术”这个概念。在后现代知识体系中的美术,可以审美,也可以不审美,艺术成了反审美、泛审美或非审美的形态。这一动向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在第二种比较研究倾向中,本土话语、话语权、他者、中心主义等是关键词。从某种程度上说,与其说是在“比较”,还不如说是在“对话”。在现代艺术(美术)与后现代艺术(美术)语境中的我国的比较美术学研究,往往对“中心主义”的话语批判性较多,也是比较美术学中非常敏感的主题。以批判的姿态进行对话式的比较美术学研究,同时还对中西异质美术思潮、主义、流派等话语采取“互释”性的研究。当然,中国的比较美术学的互释研究,不同于西方的“阐释学”的方法研究。互释研究是要求不同文化圈美术互为主体的双向阐释,而不是单项阐释。“互释研究”的方式成为我国的比较美术学的一个新的研究方法,而“对话研究”则是中国比较美术学中对互释研究的重要补充。
第三种研究倾向。着力于建构比较美术学体系方面。如果说上述两种比较研究的倾向,重点在比较研究的实践工作中,那么第三种比较研究倾向是对比较美术学科建立的自觉认识。湖北出版的《美术思潮》杂志以及浙江美术学院的学报《新美术》等,在80年代中期辟出“比较美术”的栏目,刊登了一些有学术价值的有关比较美术的论文。譬如范景中《比较美术和美术比较》,明确提出了“比较美术”的概念。认为“比较美术要在各种人文学科之间促成‘伟大的对话’,要在各种艺术的外因史内因史中挖掘引力和斥力。”[17](P53)并且,范景中认为“民族性”是比较美术研究的核心。由于对比较美术的概念、范畴、本体、性质等认识方面的差异,故此,对比较美术的讨论也是非常激烈的。黄河清《为比较美术进言》就比较美术的定义以及中西比较美术的研究概况、方法等作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他提出:“比较美术的方法是中国当代美术崛起于世界艺坛的桥梁。用比较美术的方法创作,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嫁接’:将两种或三种美术传统的优势嫁接在一起,变成一种优于其‘父母’的新品种,从而达到世界性的成功。”[18](P17)相同的思考还有李公明、李行远的《比较艺术刍言》(实际上是比较美术),海源的《比较美术学》等。海源参考了比较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比较美术是一种跨国别、跨学科的学科,既属于现在也属于未来的新型学科[19](P34)。最系统的比较美术研究是袁宝林的《比较美术教程》(1998年),该成果从“‘世界文学’现象和比较美学研究”“有关比较美术方法论”“中外美术交流史要”“比较研究举隅”等四个方面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其中从世界文学现象、近现代中国文化艺术、世界性与民族性入手,进入到有关比较美术方法和探索中,利用阐释学、接受美学和文化研究的方法,探讨了建立比较美术的学科问题。另外,他还从中外美术史上最早的交流开始回溯,如佛教美术、南北朝隋唐美术中的萨珊波斯因素等一直到明清的西方美术的切入,包括西方现代艺术转型与东亚美术对我国的影响。这是目前将“比较美术学”作为一个学科建立最早的系统认识。我们还需注意的是在中西比较美术学学科认识下的一些实践研究成果。譬如孔新苗、张萍的《中西美术比较》以及邓福星主编的“中西美术比较十书”系列:廖阳《中西美术题材比较》、洪惠镇《中西绘画比较》、黄宗贤《中西雕塑比较》、郭小川《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等,不过该丛书因其他原因没有出版完。当然,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就是没有完全能够意识到“中西比较美术学”和“中西美术比较”的性质和区别。这是作为一门学科必须注意的问题。
三、中国比较美术学的特点
明清时期中国与西方美术的交流,首先在宫廷之内。最早接触到西方美术的是宫廷内的画家,这些画家具备中国传统文人画创作的基本素质和画院的审美趣味与立场,因而初次接受西方美术的态度显然是排异性的。现代研究者引用最多的就是宫廷画家邹一桂的“虽工亦匠,不入画品”,作为了解中国画家初次接触西方美术的态度和立场,并以此看待中国早期对待西方美术的基本评价和价值判断。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西美术思想上的初次交锋和比较研究的文化态度。清代另一位宫廷画家松年依然持与邹一桂相同的价值判断和评价立场,“则喜其工妙,其实板板无奇”,其学术层面的认识是一致的,都认为西方美术“匠气”,缺乏中国文人画的“气韵”。这显然是站在中国文化背景立场上的价值判断。这种比较的方法,重点放在了价值判断上,即比较异质文化背景下美术形态的高低、优劣等。看高自己、视别人低的比较方法,是中国的比较美术学初期的研究特征。这种偏见到了20世纪“五四运动”前后,西方科学、民主等观念意识以及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成果,使中国文化学者的先驱们开始反思中国传统绘画,并提出了改良主义和要革中国画的命等主张,这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总之,这一时期的比较美术学,是在高低、优劣的比较中形成的比较美术学。坦率地讲,这种比较如同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看到中国美术所做的价值判断,是没有太多的学术价值的,也是深入认识与了解中西美术特征、异同等的一大障碍。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们在比较美术学建立的自觉阶段中,纠正了比高低、比优劣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态度。其时,影响研究依然是中国的中西比较美术学研究的一大特征,影响研究的方法被有效地运用在比较美术研究的课题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向达的研究成果。他的影响研究方法和成果,不仅仅是简单地研究西方美术对中国美术的表层影响研究,而且是深入到了对影响的条件、路径的考证以及接受者和放送者的态度的研究,详尽地论证了西方美术对中国美术影响的事实根据以及广度和深度。后学们不断地将影响研究作为比较美术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取得了十分突出的研究成果。无论是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美术与西方美术的关系,还是研究中国当代美术与西方现代、后现代美术的关系,“影响研究”的方法都被运用在中国的比较美术研究工作中。因此,影响研究不仅是西方比较美术学研究方法运用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比较美术学的研究方法运用特征之一,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影响研究”的方法来自于比较文学,属于法国学派的研究方法。
“形态研究”是中国比较美术学研究方法运用的一大特征。尽管西方的比较美术学中曾运用形态研究方法,但相对来说,运用得不如中国比较美术学研究多,这与西方所持文化意识和意识形态等的观念有关。我国的比较美术学运用形态研究方法,主要是进行美术的构成形态与审美形态方面的比较研究。宗白华是最成功的代表人物之一。宗先生在形而上的层面中展开了中西美术结构层的时空意识和美学意识的比较研究。宗先生的《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和《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深入地讨论了中西美术各自异同关系和渊源基础关系,对时空表现特征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寻求中西美术不同形态的发生和各自的文化与美学特征。通过对中西美术不同形态特征的比较研究,深层次地揭示了中西美术不同文化的空间意识的基础,为充分理解和阐释中西美术的异同关系作了深入研究的基础工作,也提供了深入了解中西美术的异同性质的理论基础。同时期的研究者如李宝泉《中西山水画的古典主义与自然主义》(1935年)、孙福熙《西洋画中的风景——东方人富于自然美的感受》(1935年)、谢海燕《西洋山水画史的考察》(1935年)、尚其逵《中画与西画》(1936年)、陈之佛《略论近世西洋画论与中国美术思想的共同点》(1947年)等,这些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比较美术研究论文,基本上运用形态研究的方法研究中西美术的关系。70年代以后形态研究的方法被研究者普遍运用。譬如齐风阁《试论西方现代派绘画与中国文人画的异同》(1985年),陈池瑜《中西诗画中的时空艺术之比较》(1986年),罗培坤《中西表现说差异论》(1988年),胡素《陈洪绶——中西版画比较的一个视点》(1992年),王镛《凹凸与明暗——东西方立体画法比较》(1998年),沈亚丹《论中西绘画不同抽象方式》(1999年),邵大箴《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的同和异》(1999年),李一《品味与分析:中西美术批评方法比较谈》(1999年),李倍雷《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比较之方法与意义》(2002年)和《经验表述与视觉描述——论中西绘画的不同观念》(2005年)、《中国山水画与欧洲风景画的比较研究》(2006年),陈世宁《中西绘画形神观比较研究》(2007)等,这些研究成果中大量地使用了形态研究的方法。当然,对于研究者而言,他们在比较美术学研究中,并不局限在某一种研究方法上,同时也可能运用其他的方法,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
除此之外,中国比较美术学的研究方法还有互释研究以及作为补充的对话研究。中国的比较美术学中的互释研究,是基于中西当代的艺术、文化、思想、哲学、美学等观念的交流不断深入,彼此之间的碰撞也越来越激烈,双方需要深层次地了解对方,并把对方作为存在的他者来认识,既要消除二元的对立,又要互为主体地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场来认识他者。在这种语境中了解他者,必然就对他者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在对西方美术思潮、观念等不断深入认识以及对异质文化的深入了解过程中,可能有超越他者原有含义和意义的理解。这就需要对“他者”的原意义进行阐释。但阐释“他者”是站在跨视域的文化立场和学术视野中进行的一种比较研究,不是单向的阐释,需要互为主体的双向阐释。故此,我们称这种互为主体的双向阐释为“互释研究”。毛时安《中西表现美学及其影响下的绘画》(1985年),王以时《试谈西方现代派的“反传统”意识与中国古典美术的“同构性”》等采用了一些互释研究的方法,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主要美术形态、观念、思潮等作了一定的双向阐释,并将双向阐释的结果与中国或东方美术形态、观念等进行比较研究。邓福星《绘画的抽象性》(1983年)以及他的《中西美术中象征形象与观念比较》(2002年),某种程度上运用了互释研究的方法,双向阐释了西方美术中的“抽象”“形象”和“观念”等概念,通过对西方美术中的一些概念的互释,深化对异质美术的整体认识,从而达到研究的有效性。张灵聪《海德格尔艺术哲学与石涛画论之比较》(1999年),杨成寅《石涛画论与西方现代主义》(2000年),章利国《中西画家的文化眼光与艺术观照》(2003年),张绿江《试论中西方美术的观念》(2004年)等,其中也使用了互释研究的方法。互释研究的方法在当代中西美术碰撞中运用较多,也是对中西方当代美术比较研究的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譬如杨小彦《图像去魅化及其他》(2008年),运用了笛卡尔等的科学理论来互释中国当今的美术形态。漆澜、徐可《超越图像的中国新绘画》(2009年),同样是借用西方现代主义理论来解释受到西方美术思潮影响的中国当代绘画。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多数用互释研究方法的研究者,基本上用西方的现代与后现代理论和思潮来双向阐释中国自己当今的美术。也许是因为,中国当代美术受到西方当代的艺术理论影响较大,故此,借用西方的话语来阐释中国的美术形态及其观念。
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互释研究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构建中国自己的当代美术模式。譬如高名潞在《另类方法,另类现代》中做了这样一个对话研究的描述:“我们需要找到另一种解读中国艺术的现代性和前卫性的叙事模式和修辞方式。而这种新的方式本身就已经包含了某种不同于西方的新的美学经验、新的艺术创作方法论和艺术阐释方法论。只有通过建树这样一种新的话语标准,非西方的前卫和现代才能宣称它的平等存在价值。”于是高名潞用中国当代美术的“极多”绘画形式对话西方的“极少”的绘画形式:“‘极多主义’的形式观念与‘极少主义’不同,‘极多’的‘形式感’不是为娱悦观众的,而是为自己的生活或者艺术‘逻辑’负责。……因此,‘中国极多主义’既不把作品本身极端地看作自我精神的投射或宇宙精神的物质化形式,像西方的早期抽象绘画和中国80年代的‘理性绘画’那样,也不将艺术作品视为纯粹的物质客体。”[20](29,P51-52)艺术批评家吕澎就有关语境问题提出了看法:“不存在单一的语境,但也不存在平均值的历史要素,每一个时间段落,都有可能导致特殊语境概念的产生。……受西方艺术影响的中国艺术家被归纳到另一个文明系列,结果是,他们究竟是中国艺术家还是仅仅是黄皮肤的西方艺术家?”[21](P239)“语境”是对话的基本前提和条件,同时“语境”是不同国别艺术家创作的艺术的解读符码。中西当代美术包括传统美术都是在各自的语境中产生的,这种语境是民族与文化、社会等关系所构成的文化场。但这种语境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就是说语境不是单纯的某种文化场,受他者文化的影响是必然的。所以语境问题成为人们解读中西美术的节点,也是我们说的互释的基本前提和条件。段炼的《超越模仿:中国当代美术的焦虑》戏谑性地提出用模仿回应模仿来超越西方现代主义艺术:“面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和挑战,中国当代美术在20世纪80年代以模仿为主要应战方式,但后来这种模仿却出现了具有反讽意义的逆转。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渐渐深入到中国当代文化的肌体中,中国艺术家们洞熟了后现代的悖论之妙用,开始模仿后现代艺术的方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应对西方艺术的挑战,用模仿来超越模仿。”[22](P49)中国艺术理论家和批评家提出的构建模式,自然免不了有批评的文化态度。王天兵《西方现代艺术批判》以中国“文革”时期的那种“非黑即白”的“高、大、全、红、光、亮”的艺术“形象”,类比性地批评了西方后现代艺术的“丑、怪、病、碎、偏、脏”的“形象”,认为“它表面上和‘文革’形象是完全相反的,可实际上制造他们的却是同一类人……不管红卫兵的宣传画和后现代狂人的呕吐有多大的外观区别,它们本质上都是对人与自然同一体进行野蛮的概念化的简化。”[23](P78)这实际上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是一种批判式的互释研究方式,并作为构建自己模式的基础。栗宪庭的《同文异质与同文同质》《中国当代艺术缩影式艺术家:张晓刚和他的缩影式中国人的肖像》等,都是属于构建性的互释研究的探讨。栗宪庭以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作品为例指出:“这种在那个实验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标志——在就受西方现代和当代艺术影响的过程中寻找一种再创造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说,1993年至今的‘大家庭系列’,不但是张晓刚艺术的成熟期,也标志着中国当代艺术的某种成熟,这种成熟的含义是借鉴而不露痕迹。即在使用西方现代语言的模式,表达中国当代人的感觉过程中,成功地转换个人话语。”[24](P141)这表明了中国当代艺术家在借用西方现代艺术语言中,渐次成熟地表达了自己的美术问题和构建问题。
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比较美术学的跨学科研究也是一个突出的特征。其早在北宋苏轼就以唐代大诗人兼画家王维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论断,这应该是中国比较美术中跨学科研究自觉的开端。1928年梁实秋先生撰写了《诗与图画》,再次将中国这个诗的国度与中国特有的诗意性的绘画作了比较研究。与此同时,邓以蜇进行了雕塑与戏剧两门不同艺术种类的比较研究,他在《戏剧与雕塑》中比较两者在造型方面异同的性质特征。1934年艺术史论家滕固先生发表了《诗书画三种艺的联带关系》。钱钟书先生在40年代末期,研究了诗与画的关系问题,他写《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对中国诗画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是跨学科比较研究的经典之作。此后宗白华又在《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1949年)中,以独特的视角从形而上的层面探讨了中国诗画对空间的表达和处理特点,是具有代表性的跨学科研究成果。钱钟书先生在1962年,再次撰写了一篇有关美术与诗学的比较研究论文《读〈拉奥孔〉》,这是一个跨学科的比较美术研究型的成果,是钱钟书先生受到莱辛《拉奥孔》的启发而研究的。这些学术大师的跨学科研究为中国的比较美术学奠定了跨学科比较研究的坚实基础。此后有关跨学科比较研究的成果不断产生。譬如,伍蠡甫《试论画中有诗》(1983年),商伟《论中西方诗画比较说及其基础》(1986年),汪亚尘《绘画与音乐》(1990),邵彦《明清文人画与琴乐的几点比较》(1994年),张清治《吴派之画风与琴风——明清之际吴地琴画风格的地缘美学》(1994年),冯稷家《书画同源论》(2000年),王培娟《“诗画异质”与“诗画一律”——谈莱辛、苏轼诗画观的根源》(2004年)等。这些研究成果,完善了中国比较美术学的科学成果和研究体系的结构,也是中国比较美术学的一大特色。
结 语
从明清开始,至20世纪30年代以降,中国比较美术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向达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艺术学者开启了中西比较美术的自觉研究工作。他的《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今天依然是中国的中西比较美术学影响研究的经典范例之一。之后的宗白华的形态研究成果异常突出,他的《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最为经典,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中西比较美术学形态研究的最高成就,时至今日宗白华的观念仍然不断地被人们引证。至20世纪60年代以来,马白水、伍蠡甫、刘汝醴、杜学知、邓福星、范景中、王宏建、陈履生、潘耀昌、陈池瑜、袁宝林等,都做过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工作。袁宝林撰写了《比较美术教程》,立志于比较美术学的学科建立,邓福星主编了“中西美术比较十书”的案例实践研究系列丛书以及笔者的《中西比较美术学》等,都为比较美术学的学科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体现了中国比较美术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希望比较美术学最终成为一门学科。
(责任编辑 薛 雁)
[1]郑午昌.中国画之认识[J].东方杂志(28卷),1931(1).
Zheng Wuchang,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Painting,Dongfang Magazine,No 1,Vol 28,1931.
[2][明]顾起元.客座赘语[M].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Gu Qiyuan,Ke Zuo Zhui Yu,in Overview of Short Novels in the Ming Dynasty(Volume 2),Shanghai: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2003.
[3][明]姜绍书.无声诗史[M](卷6).于安澜编.画史丛书.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
Jiang Shaoshu,SilentHistory of Poetry(Volume6),in Yu An'lan(ed.),Series of History of Paintings,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1962.
[4][清]松年.颐圆论画[M].王伯敏,任道斌主编.画学集成(明-清).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
Song Nian,On Painting of Yiyuan,in Wang Bomin and Ren Daobing(eds.),Hua Xue Ji Cheng(Ming-Qing),Shijiazhuang:Hebei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2002.
[5]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M].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
Kang Youwei,Journey in 11 European Countries,in Zhong Shuhe(ed.),SiresofWalking into theWorld,Changsha:Yuelu Publishing House,1985.
[6]陈独秀.美术革命——答吕澂[C].美术论集(4).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
Chen Duxiu,Revolution of Fine Art:Answers to Lyu Cheng,Collection of Fine Arts,Beijing: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1986.
[7]蔡元培.在北大画法研究会之演说词[M].蔡元培美学文集.北京:文汇出版社,2003.
Cai Yuanpei,Speech in the painting Society of Peking University,in Collection of Papersof Cai Yuanpeion Aesthetics,Beijing:Wenhui Publishing House,2003
[8]蔡元培.智育十篇[M].蔡元培全集(4).北京:中华书局,1984.
Cai Yuanpei,Ten Papers on Intelligent Education,in Complete Works of Cai Yuanpei,Zhonghua Book Company,1984.
[9]刘海粟.石涛与后期印象派[M].朱金楼,袁志煌编.刘海粟艺术文选.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
Liu Haisu,Shi Tao and Post-impressionism,in Zhu Jinlou and Yuan Zhihuang(eds.),Selection of Liu Haisu's Papers on Arts,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Fine Art Publishing House,1987
[10]谢海燕.中国山水画思想专号发刊前谈[J].国画月刊(第1卷),1935(3).
Xie Haiyan,Preface of the First Issue of the Thoughts of Chinese Mountains and Waters Painting,Chinese Painting Monthly,No 3,Vol 1,1935.
[11]徐悲鸿.中国艺术的贡献及其趋向[C]//周积寅编.中国历代画论(下编).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
Xu Beihong,The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Arts and its Direction,in Zhou Jiyin(ed.),Chinese Paintings in the History(Volume 2),Nanjing:Jiangsu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2007.
[12]向达.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Xiang Da,Western Influences on Chinese Fine Art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Shijiazhuang:He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2002
[13]宗白华.宗白华全集(2)[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Zong Baihua,CompleteWorks of Zong Baihua(Volume 2),Hefei:An'hu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1994.
[14]凌绍夔.中国绘画之本质基点器材与技法之同异[J].大陆杂志(第7卷)(台湾),1953,(11).
Ling Shaokui,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the Basic Instrument and Techniques of Chinese Paintings,Mainland Magazine(Taiwan),No 11,Vol 7,1953.
[15]邓福星.美术史、论研究方法刍议[J].美术史论丛刊,1982(4).
Deng Fuxing,History of Fine Arts:On Methodology,Series of History of Fine Arts,No 4,1982.
[16]郑培凯.明末清初的绘画与中国思想文化——评高居翰的气势撼人[J].九州学刊(台湾),1986,(1).
Zheng Peikai,The Painting and Chinese Thoughts and Culture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On the Style of Gao Juhan,Jiuzhou Journal(Taiwan),No 1,1986.
[17]范景中.比较美术与美术比较[J].新美术,1985,(6).
Fan Jingzhong,Comparative Fine Arts and Fine Arts Comparison,New Fine Arts,No 6,1985
[18]黄河清.为比较美术进言[J].美术思潮,1985,(6).
Huang Heqing,For Comparative Fine Arts,Fine Arts Thoughts,No 6,1985
[19]海源.比较美术学[J].美术思潮,1985,(6).
Hai Yuan,Comparative Fine Arts,Fine Arts Thoughts,No 6,1985
[20]高名潞.另类方法,另类现代[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
Gao Minglu,Alternative Methods,Alternative Modernity,Shanghai:Shanghai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Publishing House,2006
[21]吕澎.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进程与市场化趋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Lyu Peng,The History and its Marketization Tren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s,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0
[22]段炼.超越模仿:中国当代美术的焦虑[J].批评家,2009(3).
Duan Lian,Surpassing Imitation,The Anxiet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ne Arts,Critics,No 3,2009.
[23]王天兵.西方现代艺术批判[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Wang Tianbing,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Modern Arts,Beijing: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03.
[24]栗宪庭.中国当代艺术缩影式艺术家:张晓刚和他的缩影式中国人肖像[J].东方艺术,2006(6).
Li Xianting,Contemporary Chinese Ministured Artist:Zhang Xiaogang and his Minitured Chinese Portraits,Oriental Arts,No 6,2006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 parative Fine Arts in China
Li Beilei
Although comparative fine arts is notan established subject,th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the field of fine arts appeared as early as in the Han Dynasty.Practical research and related theoretical studies of comparative fine arts emerged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Matteo Ricci brought Western religious painting art into China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nd he also critiqued Chinese paintings.Meanwhile,Gu Qiyuan in the Ming Dynasty also critiqued the religious paintings brought in by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which can be seen as an early practical research of China-West fine artexchange and comparative fine arts. From then on,the discussion on the subject in comparative fine artswas never suspended from Zou Yigui in the Qing Dynasty,Giuseppe Castiglione and other until the 21stcentury.A peak of the study of the subject in comparative fine artswas seen in the period between 1930s,1940s and 1990swhen practical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works appeared such as Tutorial of Comparative Fine Arts and China-West Comparative Fine Arts.At present,scholars suggest constructing the discipline of comparative fine arts,discussing the theoretical and inter-cultural issues in comparative studie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comparative fine arts,development,history,practical research
J0-03
A
1003-840X(2017)03-0051-14
李倍雷,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1189
http://dx.doi.org/10.21004/issn.1003-840x.2017.03.051
2017-05-20
About the author:Li Beilei,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Arts of 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211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