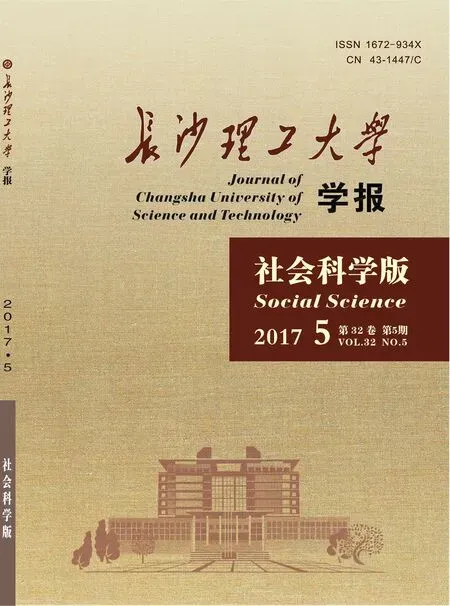法治进程中的话语分歧及法理反思
——基于影响性案例的分析
杨叶红
(中共湖南省委直属机关党校,湖南 长沙 410000)
法治进程中的话语分歧及法理反思
——基于影响性案例的分析
杨叶红
(中共湖南省委直属机关党校,湖南 长沙 410000)
当下中国法治发展进程中糅合了各种需求,交汇着各种声音,形成了多元话语的分歧与冲突,主要表现为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理论话语与实务话语、域外话语与本土话语之争。官方话语以“护道”为己任,而民间话语以“护权”为宗旨;理论话语追求法治的理想状态,而实务话语坚守传统与现实;域外话语注重制度的移植,而本土话语则强调法治的国情。中国法治发展需要减少法治话语的分歧与对立,整合各种话语中的优秀资源,形成法治观念的基本共识,这也是当前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话语分歧;影响性案件;法治共识
Abstract:Currently,the process of China's law-based governance has blended various needs,has met a variety of sounds,and has formed divergence and conflict of polybasic discourse,which has been demonstrated mainly with the disputes between official discourse and folk discourse,between theoretical discourse and practice discourse,and between extraterritorial discourse and local discourse.Official discourse owns its duty of"protecting direction",while folk one aims at"protecting rights";theoretical discourse pursues the ideal state during the process of governance by law,whereas practice adheres both tradition and reality;extraterritorial discourse focuses on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but local one emphasizes national condition during the process.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law-based governance expects to reduce divergence and oppositeness among law-based governance discourse,to integrate significant resources in discourse,and to form basic consensus of law-based government,three of which are the vital task in promoting law-based governance construction.
Key words:discourse divergence;influential cases;legal consensus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治国理念上,“要法治不要人治”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共识。人们普遍渴望在法律的规范下,社会公平正义,人们安居乐业,可以说,人们在要不要法治这个问题上已经达成一致。然而,由于法治内涵的复杂性,对于需要什么样的法治这一问题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于法治面相的复杂多样,在法治宣传与实践的过程当中,必然会碰到社会各个阶层对于法治的不同话语表达,这些法治话语的分歧与冲突具体表现在现实生活中诸多关于影响性案例的争论上。本文通过分析不同群体关于影响性案例的认识,深入解释其所展现的话语形式,分析各种冲突着的法治话语在该案例上的表现,并反思各种法治话语之间存在的重要差别,探讨其成因,希望整合各种法治话语中可能的内在价值共识因素,形成中国法治发展的推动力量。
一、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护道 ”与“护权”的二元进路
在很多政府官员看来,中国的法治发展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过程。尽管在民众当中有关于法治的初步认识,但是真正促使法治成为治国理念的首先是少数政治精英的科学决策,因政府的主动变革引发法治发展是中国法治进步的主要推动方式。也就是说,中国法治在推进过程中,尽管从道德上回应着民众的需要,但是从形式要件特别是操作要件来看,以政府官员为主体的官方话语实际上在决定着制度选取和制度安排,在主导着中国法治的具体走向。近年来,随着信息公开透明程度增高,话语表达空间和方式多元化,使得公共话语空间和话语秩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不仅官方话语传播速度加快,其它话语传播速度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齐头并进。民众参与中国法治建设并表达意见的渠道也越来越多,于是民间话语也逐渐开始显山露水,诸多“民间智库”中的民间高手在中国法治发展过程中也开始有了话语权。于是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关于法治的分歧与冲突显现在法治发展进程当中。
法治进程中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的分歧与冲突在“夏俊峰案”中得到集中表现。“夏俊峰案”的经过大致为:2009年5月16日,夏俊峰和妻子在马路上违法摆摊被沈阳市城管执法人员查处。在勤务室接受处罚时,夏俊峰与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刺死城管队员两名后又重伤一人。2009年6月12日被逮捕。2009年11月15日,夏俊峰一案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夏俊峰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夏俊峰还需要向原告赔偿约65.9万元。夏俊峰不服,提起上诉。2011年5月9日,辽宁省高级法院对夏俊峰刺死城管案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3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夏俊峰死刑,夏俊峰被依法执行注射死刑。“夏俊峰案”是普通的刑事案件,但是却又有值得思考的不普通之处。其普通之处在于,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和舆论的热烈讨论,这个案件就只是很多普通刑事案件当中的一个,“夏俊峰”也不会成为一个百度词条,一个中国法治进程中不能忽略的人物。但是正因为网络媒体因素的介入,民间话语的不断发酵,形成了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的严重分歧,使得这个案件变成了一个可以反思当前中国法治话语冲突的带有典型性的影响性案件。
“夏俊峰案”中的官方话语主要体现在一审、二审的刑事判决书以及代表官方立场的一些负责同志对此案的表态上。在法官看来,夏俊峰能否构成正当防卫需要具备法定条件,即需要针对正在进行中的不法侵害,对不法侵害人采取抵抗或反击行为,并且不能超越一定限度,方能不负刑事责任。在本案中已有的证据并不能支持正当防卫,而且从夏俊峰刺杀手段、程度和结果上,明显超出了法律的要求,构成故意杀人罪。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复核时认为,夏俊峰违规经营炸串,并且不服从城管执法人员的依法查处,与执法人员发生冲突后持刀行凶,造成2名城管执法人员死亡、1人重伤。犯罪情节极其恶劣,手段极其残忍,后果特别严重。被告人夏俊峰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应依法惩处。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故依法做出核准死刑的裁定。2014年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提及“夏俊峰案”时强调:“夏俊峰是一名摊贩,杀了两个城管,造成一人重伤。但是就因为夏俊峰是摊贩,对方是城管,大家对城管有偏见,所以有些人、甚至有些社会上的大V就鼓动说这人不能杀。但是这种人不杀就非常危险,就好像两个人关起门来吵了一架,你把人杀掉了,如果这样也是正当防卫,这个社会就会天下大乱。”[1]
法院的一审、二审判决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引起社会极大关注,许多网民对裁定提出质疑,夏俊峰杀死城管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性质,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这些争议,在网上引发极大关注。民间话语对“夏俊峰案”判决结果持异议的主要理由有:一是城管执法人员有没有打人,夏俊峰是不是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网民认为夏俊峰与城管执法人员没有积怨跟仇恨,如果城管执法人员没有打人,夏俊峰为什么要捅死两个、重伤一个呢?二是证人为何没有出庭,有6名证人证实夏俊峰在物品被扣押时被打,为什么未被获准出庭作证?三是对夏俊峰判刑过重,网民们指出曾经有贵州警察打死两名村民只判了8年,并且一些贪官一贪几亿甚至几十亿也没判死刑,而一个小摊贩被城管逼急了自卫捅死两个城管就判死刑,这很不公平。2013年9月25日,“夏俊峰被核准死刑”成为当天舆情热度最高的话题,至少有60万网友参与讨论,民众的态度出现一边倒的倾向,如有网民说:夏俊峰杀人,我对城管有些失望;裁定杀夏俊峰,我一定会对这个国家失望;他是被迫挥刀自卫!是谁把一个为生计奔波,原本朴实善良的社会底层民众变成了“恶人”?还有网民说:城管大庭广众都打人,把小贩带入自己大本营肯定打得更狠,小贩才被迫自卫。我们普通网民是不知道真相,但凡事发生都有起因,如果只是东西被没收,你敢不敢去捅死两个重伤一个?有时候法院简直是侮辱民众智商[2]!
在本案中,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在认识夏俊峰行为的方式上是不一样的。就官方而言,整齐划一地适用法律标准最为方便,此案中法官对夏俊峰行为进行考量的只有法律标准,所以法院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对夏俊峰进行处罚。然而,从民间话语的角度而言,社会舆论对“夏俊峰案”的判断是基于一般经验和普遍良知的基础之上,对于符合法律规定但却违背经验与良知的判决采取批判的态度。“夏俊峰案”经媒体报道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对作为社会底层人物代表的夏俊峰给予了同情和关怀,社会舆论把对弱势群体生存权的同情和对城管粗暴执法的愤怒带进了案件评价。按照法理学的语言说,官方是站在一种基于严格实证法学的立场,就法论事;而民众更多的是站在法律社会学的立场,就事论法。
由此,我们能够从中窥见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的核心态度:官方话语以“护道”为己任,而民间话语以“护权”为宗旨。所谓“护道”,即保护统治道统的权威性,指以国家机构为代表的官方人士坚持从严执行法律,以维护国家权威和国家利益为目的,关注法律适用的规范性、强制性甚于法律适用的合理性、适当性。这种官方法治话语背后所表达的实质就是权力,官方话语者接受的多为管理意义上的法治,将法律视为工具,希望运用法律强化权力与秩序。所谓“护权”,即保护公民权利的正当性,指民众坚持按照法治的目的固守对公民权利的尊重与保障,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问题上,倾向于严格地保护个人利益,关注法律适用的合理性、适当性甚于法律适用的规范性、强制性。城管与小摊贩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实质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一种冲突和较量,基于此发生了一系列类似的“小贩捅死城管”案件,如崔英杰案、侯钦志案。每当发生此类案件时,民间舆论总是呈现一边倒态势,同情小贩、抨击城管,这反映了民间话语对于公民权利的高度重视与维护。
我们需要看到,“护道”和“护权”都是必要的,通过二者的相互博弈,能够促使国家机关和民众更相信法律、依靠法律,维护法治。“护道”话语通过对国家权威和利益的维护,有利于增强国家管理能力。公民权利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政府积极的保护,需要政府的创设与实施。如果一个政府不能对国家进行有效管理,在公力救济缺失的条件下,每个普通公民就会陷入弱肉强食的丛林之中,基本权利的保障也就失去了依托。“护权”话语通过对公民权利的维护,有利于限制国家权力的肆意行使。权力产生的基础和服务的对象正在于公民的权利,在于对公民权利应有的敬畏和基本的保障。特别是在法治建设话语下,政府的一切行为必须是合法的,既要考虑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也要考虑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实无论是考虑维护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还是考虑维护公民基本权利,只要是合法维护,都是法治的表现形态。仍以保障城管权力和维护小贩权利进行分析,小贩们摆摊设点自谋生计是其基本的生存权利,摆摊行为是保障他们个人及其家庭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政府作为管理者,一方面要给予更多的宽容体谅和帮助扶持,另一方面也要划定范围加强管理和规范,通过提供各种诸如跳蚤市场、夜市、周末市场等场所给公民自由经营,同时通过严格执法规范管理实现城市整洁和交通畅通。但另一方面,“护道”和“护权”毕竟都是一种对己方利益的宣示。“护道”者因其掌握国家权力,话语优势较为明显,容易利用法律昭显和扩张权力,强势维护国家权威和国家利益。而“护权”者对权利的追求容易滑入权利片面化、绝对化的泥沼。
民间话语以批评性话语抑制权力的扩张,与官方话语相互制衡,有利于形成民间与官方的互动。民间话语的批评使得此前被隐蔽的东西显现出来,并以此对官方话语进行反驳,获得从以往的压制和支配之下的解放。因此,我们不应当将民间话语认定为官方话语的对抗,而应当认定为“牛虻”式的挑剔,是促进法治进步的重要力量。此案在成为公共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后,面对汹涌舆情,当事法官和城管部门却选择回避,没有对网民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及时澄清和解释,没有采取主动沟通的方式对舆论进行引导,使得质疑的声音不断放大。如何实现“护道”与 “护权”的融合,既需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也需要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交流与互动。正如美国学者霍尔姆斯所言,法治不是用来防止政府做它该做的事情,而是让政府对它的行为负责、作出解释[3]。
二、理论话语与实务话语:“理想”与“现实”的二元表达
法治是一种社会理想还是一种现实选择?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的回答相距很远。法学理论界在介绍和传播法治理念时将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让“法治”成为美好社会的符号。法律理想主义者在价值层面呼吁法治,强调对法律规范、原则与精神的坚守,但却忽略了对法治实施所依赖的现实环境的考察与分析。法律实务界并不把法治看成是一种抽象的社会理想,也不固守法律规范或法律原则,更注重运用法律解决现实问题,坚持法治实施要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注重对法治实施条件的考察[4]。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话语的分歧突出体现在“邱兴华案”这一影响性案件上。
邱兴华因对道观管理人员斥责其擅自移动道观内石碑不满,并怀疑道观主持有调戏其妻的行为,遂心生愤怒,为此连续残杀10人,作案后又放火焚烧道观,制造了轰动全国的陕西汉阴县铁瓦殿道观惨案,此后邱兴华在潜逃过程中再添血案,在湖北随州市又持刀抢劫杀人,杀死一人,重伤两人。邱兴华特大杀人案在媒体上公布后,著名精神病专家刘锡伟根据媒体披露的作案细节推断邱兴华患有精神病疾病,随后,另两名精神病学权威刘协和、纪术茂也表示赞同。这些精神病学专家为邱兴华积极奔走呼告,希望为其争取一个做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机会。当时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兵、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龙卫球、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何海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等五位法学专家发表联名公开信,请求司法部门为被告人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随后邱兴华的妻子何冉凤以邱兴华家属身份向陕西省高院提起了精神病司法鉴定申请。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如果邱兴华被鉴定为精神病人,那么根据现有刑法,邱兴华将被无罪释放。然而,无论是公安局、检察院还是法院都没有接受精神病专家和法学专家的建议,最终邱兴华以故意杀人罪被执行死刑。在此案中,理论话语输了,实务话语赢了。然而,这个案件中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分歧清晰显示出了理论话语和实务话语在法治发展进程中价值取向和方法的差异。
“普遍人权”“程序正义”是法学界理论的主流话语,法学专家们习惯于从纯粹法学理论来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将法律理想付诸实践作为自己的使命。法学精英们认为,如果邱兴华是一个精神病人,那么就应当保护他的程序性权利。精神病人是弱势群体,作案以后,就成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对可能患有精神疾病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做精神疾病鉴定是涉及到他有罪无罪及罪责轻重很重要的证据,从保障基本人权及被告人辩护权的角度来说,应当依法为他做鉴定,同时希望借助此案开创一个优先保护被告人抗辩权的典型判例。正如法学家们在联名公开信中所说:“我们认为,被告人依法享有辩护权,享有提供证据的权利。只要有合理怀疑,申请鉴定就应当是被告方的当然权利,尤其是死刑案件。人命关天,不可不慎。在精神病学家已经提出质疑的情况下,在邱兴华妻子已提出邱氏家族多人有精神病史的情况下,如果仍不对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判决将难以服众。这不仅严重损害了被告人的辩护权,也将严重损害司法之权威。”[5]
精神病学专家和法学专家为疑患精神病的“草民”邱兴华奔走,呼吁依法保障这个犯下“十恶不赦”大罪的“坏人”被鉴定的权利,应当说,精神病学专家和法学专家使用的“普遍人权”“程序正义”等理论话语与法治的价值追求是相一致的。然而,这种理论话语在实务话语者看来,实在是“轻如鸿毛”:一个连杀10多人的恶魔,不仅有计划有步骤的行凶,而且社会危害性极大。如果邱兴华经过司法鉴定确实患有精神病且不能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法院对其就只能做出无罪判决,而这意味着将“杀人恶魔”放回社会任其伤害更多人的生命。而据统计,我国重性精神病患者中有30%-40%有暴力倾向,而且80%的重性精神病人得不到有效治疗和监护。具有暴力倾向的重性精神病患者随时可能对他人或自己造成严重伤害[6]。这样的案例在中国已经发生过,即已经犯罪的精神病人被释放后因为监护人看管不严导致更大的社会伤害。如果从保护精神病人基本人权的角度出发免除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将其放回社会,那又如何保护潜在受害者的生命健康权利?所以对精神病人犯罪的惩罚在我国不是一个简单的程序权利问题,更可能是保护一个人的权利与保护一群人权利的现实选择问题。邱兴华案件中法院拒绝对邱兴华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正是基于上述利弊权衡之后作出的现实选择。
我们可以对理论话语和实务话语给予总结:理论话语者执着于法治的理想,而实务话语者坚守社会的现实。从邱兴华案看来,法学专家们往往是怀有法治理想信念的人士,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希望将自己的法治信仰实践于法律生活当中,他们坚持一些特定的法治信念,比如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遵循正当程序。法学专家关注的焦点并不在于邱兴华的个人生死,而在于建立健全精神病司法鉴定制度,培育法律实务界乃至整个社会对基本人权的尊重。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很多法学专家的人生经历都是从学校到学校,所以,他们对法治运行的生活场景了解并不够深入。就以法学专家主张的“普遍人权”而言,他们在主张保护某种权利的时候,通常只注重论证保护这种权利的正当性,却往往会忘记,在一些特定社会条件下,保护某种权利就会侵犯或阻碍另一种权利的实现。在关于邱兴华案的讨论中,法学家和精神病专家们只论证了精神病患者享有抗辩权和豁免权的正当性,却几乎没有谈及受害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也没有考虑和计算在现实社会条件下,保障精神病患者享有抗辩权和豁免权需要付出多少社会成本和代价以及国家和社会是否愿意承担[7]。
实务话语者则总会从权利保护的现实条件来看待法律。他们相校于程序正义更重视实体正义,注重考量法律适用的综合效果。他们坚守法治的现实基础,不追求某种固定的法治理想模式,而立足于具体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以权利保障为例,实务话语者注重权利实施的成本,反对以保障权利为名不计任何代价或后果的激进行为。任何权利的保障都需要付出代价承担成本,一项权利能否从法律权利成为实有权利,不仅取决于法律是否有规定、公民是否有维权意识、专家是否强烈呼吁,还取决于国家和社会是否愿意付出保障这项权利的代价,能否承担保障这项权利需要的成本。个体权利与自由能否实现受到现实条件的约束,每一项权利从法律权利成为实有权利的背后是政府的积极行动和公共支出,要受到政府能力的限制和财政预算的约束。政府在权衡彼此冲突的权利保障先后次序时要进行经济学上的成本核算,只有在具备相应的资源、成本或社会条件下才能将权利保障付诸实现。
三、域外话语与本土话语:“普适”与“本土”的二元分化
从学术基础和知识话语来看,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依然带有强烈的域外话语模式。西方法治理论对法治状态的描述已成为许多人的法治愿景,人们用对西方法治话语的推崇取代了对我国法治实践规律的思考,西方法治理论成为人们分析和考量社会问题的主要依据。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开始确立以法治建国开始,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入宪法,再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这其中有很多制度都是对域外的简单移植和模仿。然而,毕竟中国的法治发展有其自身的语境,中国的人民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传统未变,现代化却已经不知不觉来临,于是域外话语和本土话语之间产生了深刻对立,这一点在“李昌奎案”中得到反映。
云南农民李昌奎奸杀同村少女并杀害受害人3岁弟弟,一审被判死刑,随后云南省高院以李昌奎有“自首”情节,本着“少杀、慎杀”的刑事司法原则,将“死刑立即执行”改判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高院改判经由媒体的报道,最终引发一场轰动全国的舆论风暴。我们可以看到云南省高院负责人引用域外话语对于死刑问题的争辩:进入20世纪60年代,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了废除死刑观念,废除死刑是世界的主潮流,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死刑已经没有市场了,在中国还有死刑,是不人道的,是违背人权观念的。他认为网民对判决提出的异议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但杀人偿命的传统意识已经不符合现代司法理念。他呼吁社会舆论冷静面对案件的宣判,不要过度宣泄非理性情绪,坚持不会因为大家都喊杀,而草率地轻易地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并且向媒体宣称:“我们现在顶了这么大的压力,但这个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8]。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位法学精英人士胸怀废除死刑的志向,有志于并且能够在司法实践当中推行他个人的法律信仰,所具有的法治精神值得褒扬。只是,这位云南省高院负责人引用的域外话语并没有获得普遍认可。
废除死刑是域外话语中的流行词汇,但是在本土话语当中,并没有足够的市场。在普通大众看来,一个手段极其残忍的犯罪分子,凭什么就成为了“标杆”?一位如此凶残的杀人凶手,不顾邻里亲情,为何能够得到“免死”的照顾?一个罪大极恶的犯罪分子残忍的杀了两个人,非常严重地侵犯了别人的人权,而有些法官却还想着保护罪犯的人权,这是什么逻辑?在这里,域外话语关于法治的信念因为缺乏本土文化的支持,显得有些落寞和孤独。中国自古就有杀人偿命的思想,死刑在我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历史。特别是当网上调查以98%的高支持率支持李昌奎该死报道出来以后,废除死刑信念的孤独感“更上一层楼”!
由此,我们所看到的真实情况是,“李昌奎案”反映出了域外话语与本土话语的不同核心信念,即域外话语追求的是移植,而本土话语坚守的是实用。也就是说,在中国法治发展的进程当中,有许多受到过西方法治文明洗礼和熏陶的精英人士喜欢用一种简单移植的思维来考虑制度的安排和建设。与法律创制相较而言,法律移植简便易行。但是,“法律变革的任何主张,即使是以‘来自域外的法律制度’话语作为表现形式,也是时常包含了我们自身的一个法律变革的价值倾向”[9]。法律移植并不等于其他国家有什么我们就必须有什么,也不等于西方国家有什么我们就落后了。在我国的法治话语当中,域外话语还是处于强势地位的,不管是法学理论、立法理论还是许多的制度安排,绝大多数都是模仿了国外的,甚至是直接从国外移植过来的,当然也有一些是根据西方的法学理论设计出来的,很少有基于中国法治的需要设计的制度。甚至在很多域外话语主张者的眼中,如果一项制度没有经过国外制度的包装,其合法性和正当性就会受到质疑。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国外有,特别是西方人有,我们也必须有”的话语和思潮。实际上,法律作为特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的产物,必然受到这些因素的深刻影响。但是,一个国家需要什么制度,并不是根据国外有什么制度来决定的,而是根据这个国家的需要来决定的。这就是本土话语的核心主张和要求。本土话语所强调的“实用”,实际上就是认为任何制度都必须以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为前提,凡是华而不实的制度,凡是不能真正发生价值功用的制度,凡是不符合中国人民需要的制度,都是空中楼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刑观念正好区分了域外话语和本土话语。死刑是中国法律文化中传承的古老信仰,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都在遵循它。尽管现代法治理念流行以来,杀人偿命观念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松动,但是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对杀人放弃过惩罚,只是部分国家放弃了“以杀止杀”的惩罚,而且有一些国家曾经是死刑废除论者,到后来又变成了实施死刑的国家。可见,一意孤行的推行废除死刑观念,固然勇气可嘉,但是又实在让本土话语者难以苟同。基于域外话语提出废除死刑的观念深深刺痛了传统文化培育下人们的神经,所以人们的反应有点强烈。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当外国的法律规则遇到本国的法律文化……它并不被移入另一个肌体,而是起到刺激的作用,从而激发产生一系列新的和意想不到的事件。”[10]
四、法治话语分歧的反思:从分歧走向共识
随着中国法治的发展,话语传播途径也大幅度增加,所以,任何对中国法治发展有自己独立思考的人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都可以进行争鸣和反思,这就是法治的进步。然而,在这种进步当中,我们也必须看到,鉴于知识基础不同,对现实情况了解不同,对法治的价值追求不同,由此导致法治话语差别较大,我们必须对话语分歧背后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
首先需要反思的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话语分歧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分歧?是表层的知识差异,还是深层次的价值对立?实际上,这三种话语分歧体现出来的是表层的知识差异,而不是深层次的价值对立。法治作为治理模式的价值共识,在我国官方与民间、精英与大众中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当代中国出现的法治话语分歧,尽管没有对法治这一共识进行过否认,但是从分歧的内容来说,反映出我们对于法治的认识还很肤浅。就“夏俊峰案”来说,这是一个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出现冲突的话语对立案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却又是一个关于定罪量刑的法律方法问题。民间话语从实质正义的角度推论出了法官一审判决结果的不合理性,而官方话语却是因为在法律证据采用和证人出庭做证等审判程序上的瑕疵而失却了法律的权威,导致了话语的针锋相对。如果我们的法官有足够多的法律方式方法,有足够好的裁判理由和说服逻辑,那么这种对立显然很难发生。只有在出现知识匮乏、知识储备不足、说服理由不强的情况下,才出现这种基于个案的轩然大波。当然,对于民间话语而言,民众没有掌握基本的法律方法,往往依据直觉做出判断。尽管根据直觉的反应算不上科学和理性,但却能代表这个社会对公平和正义的朴素要求。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我们的法治国家建设尽管是由政府主导推进,但民众自下而上的参与力量显然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所以,官方话语的掌握者要提升法治能力与素质显然不是一句空话和套话。毕竟,法治发展的不断进步,使得我们已经度过了那种“只要是国家的就是权威”的时代,相反代表国家的行为已经越来越多的被放在了法治的显微镜下被人们品评、参详、反思和议论,只有掌握了全面的法律知识与正确的法律方法才能有效形成共识,维护司法权威。如果因为缺乏基本法律知识与法律方法而导致国家的司法权威受到损害,这样的司法行为值得认真反思。
其次需要反思的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话语对立反映出知识产出与社会需要之间的裂痕,导致“国情屏蔽”或者“现实屏蔽”。中国的法治建设主体必须是中国和中国人民。建设中国法治,也必须是在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语境中展开和运行。与西方发达国家法治发展进程相比,中国的法治建设是“后发赶超”式的发展,通过法治理论和法律制度的移植,我们快速地构建了法学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但西方发达国家法治话语与中国传统与现实的融合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突出难题。一些知识精英对西方法治理论的尊崇与坚持以及对域外法治话语的简单传播与直接运用已经遭遇现实的无情绞杀。“邱兴华案”,我们发现自己的程序正义、权利话语等诸多观点原来是如此理想;“李昌奎案”,在关于域外话语和本土话语的争论当中,我们也发现了所谓的死刑废除论只不过是将他人的观念引进到中国引发的争吵而已。在这种争吵背后,挑起争吵的一方,将域外的“先进”理念当成是自己的思想精华并四处替他人传播。当理论遭遇到现实绞杀之时,西方法治的理想图景就成为其行为的辩护之词。这些知识精英在仰望西方法治理想图景时却忘了低下头俯下身子面对“现实中国”,甚至是“传统中国”。因此,知识精英人士在传播法治理念和建立与执行法律制度时,要多问一声:我们中国与域外国家的法治根基差别在哪里?西方法治的理想能否适应和影响国情和现实?所以,我们的精英人士所阐述的观点不能因为借鉴了域外法治理论就理所当然地占据理论高地,甚至强迫使其成为社会“共识”,而应当是因为阐述了符合中国人现实生活需要的观点而使其成为社会“共识”。用一句话来说,我们必须要反思:我们提出的观点能否解决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重大问题?如何提升域外法治话语与本土法治话语的相融性?只有将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精神运用到法治实践中,才可能弥合知识产出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裂痕,才能达成社会关于法治的共识。
最后需要反思的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话语分歧反映出了我国已经进入利益分化与权利多元的时代,需要通过法治方式来整合利益需求和凝聚社会共识。伴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基于不同的机缘和不同的知识储备和能力,逐步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阶层之间基于各自利益有了话语之争,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常见的社会现象。但是,话语分歧并不意味着对立主体之间存在生死之争而使得“矛盾不可协调”,相反,我们可以通过法治找到协调的方法和进路,在多元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利益平衡与资源分配。从理论意义上说,民主政治条件下法律的本质是契约,法律是对社会共识的提炼和总结,法治就是契约之治。法律的制定是一种利益平衡,是分配社会资源、权利、利益等的制度性安排,只有经过多元利益主体的沟通、博弈、妥协后才能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所以说立法的本质是立约,在利益多元分化的当下,什么事情都得商量着来,商量的结果是相互承认对方的权利与利益,通过谈判协商制定契约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回顾我们国家重要法律的立法过程,也是一个多元利益主体参与讨论、不断凝聚共识的过程。开门立法是近些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的一个亮点,所谓“开门立法”,即在立法过程中坚持走群众路线,让群众积极参与,实现立法民主化。具体而言,就是采用公开征求立法建议、公布立法草案征求公众意见,举行立法听证等方式,让民众的意志从立法的最初就得到体现,从而提高立法的透明度,使立法更好地集中民智、体现民意、符合民心。在当前我国法治话语对立的情况下,需要加强法律凝聚价值共识的效果,实现多元利益的共性整合,促进法治更好地发展。
[1]周强谈夏俊峰案:如果这是正当防卫会天下大乱[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312/c70731-24607929.html,2017-03-06.
[2]今日舆情解读.夏俊峰案背后的质疑与期待[EB/OL].http://yuqing.people.com.cn/n/2013/0925/c212785-23035307.html,2017-03-07.
[3][美]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R.桑斯坦.权利的成本[M].毕竞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
[4]顾培东.当代中国法治共识的形成及法治再启蒙[J].法学研究,2017(1):3-23.
[5]法学家呼吁对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EB/OL].http://news.163.com/06/1212/09/324Q4IBK0001124J.html,2017-03-10.
[6]精神病抗辩的悖论[EB/OL].http://www.gmw.cn/02blqs/2007-06/07/content_650144.htm l,2017-03-10.
[7]桑本谦.反思中国法学界的“权利话语”[J].山东社会科学,2008(8):30-36.
[8]云南高院.“赛家鑫”案10年后将成标杆[EB/OL].http://news.qq.com/a/20110713/000001.htm,2017-03-12.
[9]刘星.重新理解法律移植[J].中国社会科学,2004(5):24-36.
[10]高鸿钧.法律移植:隐喻、范式与全球化时代的新趋向[J].中国社会科学,2007(4):116-129.
Discourse Divergence in the Process of Law-based Governance and Its Legal Reflection:A Case Study Based on influential Cases
YANG YE-hong
(Party School of Hu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Changsha,Hunan 410001,China)
D90
A
1672-934X(2017)05-0141-09
10.16573/j.cnki.1672-934x.2017.05.022
2017-06-16
杨叶红(1973—),女,湖南邵东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法理学、宪法行政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