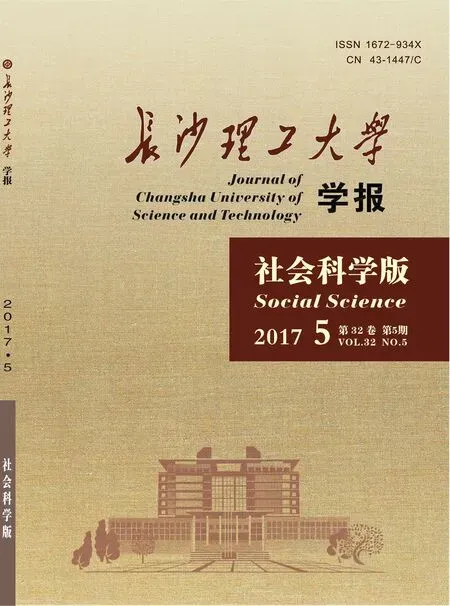教育管理伦理的主体建构及其策略
段佳丽,邹 华
(1.长沙医学院 管理系,湖南 长沙 410219;2.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部,湖南 长沙 410200)
教育管理伦理的主体建构及其策略
段佳丽1,邹 华2
(1.长沙医学院 管理系,湖南 长沙 410219;2.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部,湖南 长沙 410200)
教育管理是一种主体的伦理行为,教育管理伦理主体意指管理者作为“主体”的自我确认、对于“他者”的尊重以及关于“主体”与“他者”关系的科学处理。教育管理伦理的主体建构途径有教育管理伦理主体德性的建构、教育管理伦理主体德行的规范以及教育管理伦理主体美德的养成。其意义在于能够使价值性教育管理目标得以重估,实现民主化管理决策方式,并达成幸福型情感管理模式。
教育管理;伦理;主体;价值;道德
Abstract:Educational management is a kind of ethical behavior of the subject,which refers to the self-affirmation of the administrators as"subject",the respects to others,and the scientific treatment on relationships concerning"subject"and"the other".The ways to construct the subject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ethics consists of subjects'virtue construction,subjects'virtue regulation,and subjects'virtue'formation.The significance lies in these aspects:revaluating the target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realizing the way of the decision-making of the democratic management,and formulating the happy pattern of the emotional management.
Key words:educational management;ethics;subject;value;virtue
教育管理伦理,“是教育管理制度、管理关系、管理理念和管理行为的基本伦理规范与道德意义”[1]。在这些伦理规范和道德意义中,无论是教育管理的承担者、执行者,也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还是组织内部的激励、控制、资源分配、组织结构和文化形成,都是通过价值关系的调节功能予以实现的[2]。其中价值关系的调节,涉及到教育管理的理念、政策、制度和行为等方方面面,但是归根结底,作为一种管理行为,都是要通过对主体实施影响而实现,从而达成管理的伦理目标与实际效应[3]。教育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己任的,完善教育管理主体的伦理建构,从外来看,是教育的功用与人类社会发展在目标上的契合;从内来看,管理主体道德性的自我完善,亦是教育管理逐步完善并建构新的管理范式,也即主体与组织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从伦理的角度观之,教育管理要实现其目标,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就在于主体的形成以及建构,换言之,就是要在管理的过程中,实现主体德性建构,在管理实践中,与具体制度两相结合,使主体德行表现于教育行为中,使道德主体成为促进教育管理的重要因素。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主体的建构都需要教育管理伦理。
一、教育管理伦理的主体内涵
管理伦理是关于管理活动中具有善恶意义,能用来对管理活动进行道德评价的尺度和标准[4]。因此,管理伦理既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个实践范畴,管理伦理的确立,就是要通过伦理原则,来调节善恶、公正和合理与否等等,正如《管子·心术上》所说,“德者,得也”,有“德”,管理方能达成其目标。也就是说,伦理原则可以引导人们在管理活动中,哪些行为是正当的、善的,这样管理伦理成为价值引导和利益规范的引领者和协调者。于教育而言,通过“善”的完满,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价值的实现以及社会的发展,是其根本目的[5]。“众所周知,教育管理是一种为促进人类自身再生产从而使教育更好地为一定社会服务的特殊的人类实践活动。教育管理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目标的确定与达成同教育目的密切相关。”[6]在《荀子·劝学》中就曾指出“学”与“道德”之间的相互关系:“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道德之极”的实现,显然与教育管理主体的伦理特性密切相关,教育管理伦理主体的善恶标准、执行尺度,便成为教育管理以及教育活动本身能否实现组织目标,并在根本上自觉追求并有效促进人自由发展的一个前提性因素。
教育管理主体是高等教育系统目的实现过程中的调节者和控制者[7],无论是作为控制者还是调节者,作为教育管理者,其伦理主体角色的实现始终有一个“我”的存在、确认的过程。因此,教育管理伦理的主体内涵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教育管理伦理主体的自我确认。一方面,教育管理的主体是对自己所作用的对象有影响的人[8],作为教育活动的管理者,应对教师、学生所产生的影响,有明确的目标定位、清晰的工作思路和方法,以及合理的交流方式;另一方面,主体对道德之“善”的确认和运用。教育活动正是通过管理者所唤起的伦理法则,并结合教育的实际目标,使人摆脱物质和功利的个人幸福,从而使主体建构走出狭隘的个人观并培育济世情怀。康德曾说,如果物质生活的追求占据主导,那么道德生活就会无可挽救地萎靡下去[9]。因此,从教育活动开展伊始,便确认这一道德性主体的存在,并最终以此为其目标,那么教育的伦理价值,也就会得以保证。二是教育管理中对“他者”的尊重。“在具体个体看来,人群之道必然被分为‘我’与‘他者’两个视域。这两个视域相分且相对,往往表现为实践上的扬此抑彼乃至冲突斗争。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不能消除这种矛盾,伦理所追求的和谐就很有可能是且仅是一种理念。”[10]高贵的人性和完美的社会伦理追求人际的和谐,但在管理与被管理、施教与受教之间,这种人性高贵的理想状态,如没有必要的教育、调和或处理,很难达成。主体与他者之间,显然是不能被当作相互一致的东西并无条件等同起来的[11]。所以,讨论教育管理主体,不可能离开教育活动中的“他者”问题。三是教育管理伦理“主体”与“他者”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无所不能的、大写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象主体的消亡,从管理的角度来说,显然无法实现系统和组织的追求与目标,更是与教育促进人自由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在教育管理过程中,建构一种合理的与“他者”的伦理关系,也是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
二、教育管理伦理的主体建构策略
众所周知,伦理精神是教育人文精神的核心[12],事关教育的信念、使命和未来,以价值、伦理和道德性为基础的教育管理,理应广泛存在于教育领导实践之中[13]。作为一种在教育领域的系统活动,教育管理既是主体价值层面的追求,也是在实践层面主体对于教育资源、环境和其他主体要素的合理协调和道德引领,伦理主体的建构,便成为教育管理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
第一,教育管理伦理主体德性的建构。所谓德性,就是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人的内在信仰和准则的一种优良品质[14],也就是说,德性是一种尚未见诸于“行”的品性、禀赋与特质[15]。显然,德性的形成过程并不是天赋异禀,当然更不是后天的一种机械程序——它是一个生成性的建构过程。以人的自由发展为出发点的教育管理,不仅仅是技能、程序的设计和完善,以及纯粹的知性活动,而是一种以人为主导的、以人格完善和“善”的追求为出发点和目标的系统性伦理活动,从而摆脱教育管理中只见组织不见人的局面。这一过程中,伦理主体建构的意义便可见一斑。具体而言,教育管理伦理主体德性的建构途径有二:一是教育管理主体道德制度的完善与约束。教育管理依托于现代教育制度,通过制度道德化的方式,将教育管理行为中的人伦关系和道德活动方式明文化、正规化和异己化[16],教育制度在管理中发挥引领个体道德的作用。二是教育管理主体道德情感的认同与回应。以人的自由发展为目标的教育和管理,均需要以深厚的道德情感为基础和动力,教育管理过程中,“人从被关爱中成长、在自我价值感中关爱自己、在被关爱和关爱自己中自由关爱别人”[17],使管理者在面对教师、学生时,达成自我确认、实现情感交流,获得情感回应,从而实现管理之“善”。
第二,教育管理伦理主体德行的规范。关于何谓“德行”,孟子曾有“善为说辞”和“善言德行”之说,朱熹对此的解释是,所谓“善言德行”就是“得于心而见于行事者也”。东汉郑玄对此的解释比较到位,他说:“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18]。也就是说,如上文所述,“德行”更多是侧重于“行”。教育管理的主体德行的实现,就是“以高尚的个人品德和操守,影响和激励下属去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19],换言之,教育管理主体的德性规范其实就是个人品德和操守的建构过程。首先,这意味着教育管理伦理主体德行的自我限度。这就是教育管理主体德行的有限性问题,在教育管理实践中,德行的自我限度问题,并不是一个抽象问题,对教育管理善恶的判断,显然是置于具体情境之中的,因为“主体”问题一旦提出,就涉及与“他者”的问题。“日常的德行主体顾念有限肉身而在乎自我的现实存在,这种顾念与在乎自有其人性的根源和自然权利,它应得到理解与尊重,而不是蔑视,在此基础上的道德才是人道的。”[20]因此,教育管理主体德行的自我限度,就是教育管理者对自我受教育权益的充分实现,是对自我之“善”的充分引导,是对“他者”权益的充分尊重。从人格来说,是教育管理主体的仁厚诚挚;从工作与组织来说,是主体的正直、廉洁;从关系的角度来说,是主体间的相互关爱。其次,是道德共同体的培育。群体效应的道德践行,会密切影响群体组织成员的行为活动。教育管理者与教师和学生之间有着微妙的关联,当教育管理者能够以较好的善恶标准和道德风尚引领教师和学生群体时,便能形成两者的良性互动,反之则相反。正如卢梭所说,教育管理者如果能“以感情和良心为基础……当我可以说是把自己看成为他的时候,我希望他不受痛苦,也正是为了使我不受痛苦……自爱而产生的对他人的爱,是人类的正义”[21]。如此,在这道德共同体中,管理者的意志与集体意志和其他个体意志统一,管理者能够接纳每一个成员,并把自身以及全体成员作为管理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再次,是道德治理技艺的规范。这是教育管理主体在伦理道德实施过程中的一种品质与技巧,诸如正直、宽容、果断、简要、惠施等等。
第三,教育管理伦理主体美德的养成。主体德性和德行的完善,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美德,也就是“与其独特的社会身份和‘人伦位格’直接相关的道德行为领域或方面所达成的道德卓越或者优异的道德成就”[22]。美德管理的形成,是历史性的、现实性的,教育管理伦理主体的美德养成,同样也是置身于教育的现实语境之中的。教育管理中,主体的美德养成应是在如此几个维度:一是历史的维度上,自觉追随教育管理历史中道德文化共同体,实现教育管理主体的情感、心理和历史认同,以及一种归属感。二是教育管理主体的美德示范。具有典范性的教育管理主体通过在行政管理、教师和学生管理、教育教学管理方面所确立的价值权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公共影响力,而带来示范作用,并实现其社会公共影响力。三是将教育作为知识的传播手段与道德作为道德的感染相结合,培育美德氛围。道德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将其蕴含于教育的知识活动之中,通过合理的方式,使知识与道德均能超越“教”与“学”的简单关系,美育与美德结合,从而以道德共鸣、道德同感和道德互感的方式,实现美德建构,并达成教育管理的根本目标。
三、教育管理伦理的主体建构意义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说,管理者所追求的“既是一种 ‘人性’,一种 ‘道德哲学’,一种‘精神科学’,又是一种 ‘严谨的科学’”[22],毋庸讳言,在人的要素不断被重视及效能与价值不断被强调的现代教育管理中,在既遵循教育规律又遵循管理规律的情况下,促进教育管理主体及教育活动主体的建构、发展,并力求解决教育管理者伦理道德问题,其意义不言而喻。
第一,价值性教育管理目标的重估。伦理道德的指向是“善”,而以“善”为目标的道德追求则体现为一种价值追求。“作为人的存在的方式,道德的价值根据并不外在于人自身的存在;质言之,善的追求归根到底在于实现人存在的价值。”[23]显然,教育管理的实践目标,其实并不是“外在于人自身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教育管理中,主体定位的模糊与迷失,目标的含混与功利等诸多问题,就有待重估了。从价值目标的角度来说,教育管理伦理主体的建构,就是要通过教育管理活动及教育活动本身,实现主体之“善”,在自我主体的维度,也就是“自为”的角度,通过价值性的伦理目标引导,可以实现对管理者主体存在价值的自我确认。而从“他者”主体的角度来说,管理者是“为他”的一个组织者、服务者和引导者,价值目标的确立和实施,则充分体现了主体间个体价值和共同价值的相互尊重和确认。所以,这是改变传统教育管理中以管理者为中心的大写化主体模式的一种有效策略——既不是导向自我中心,亦不是对“他者”的否定——从而使教育管理者真正意义上成为实现教育体系中其他成员实现其目的的手段,尊重、肯定和理想得以实现,教育管理的伦理行为也就突破了狭隘的手段关系层面,而上升到“人”的自由发展层面。
第二,民主化管理决策方式的追求。传统教育管理视域下,管理者是“大写”的主体,占据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同时可以运用政府行政管理的方式和手段实现其目标,这一过程自然不可避免地存在有政府的督查干预、行政的强制手段以及管理者自身的个人意志甚至长官意志。毫无疑问,管理者的个人权威是一把双刃剑,存在着决策是否科学、影响力的大小甚至权威的误用等诸多问题。以德性的建构、德行的培育为契机,教育管理主体被置于主体之间,主体间性的教育管理关系得以形成,在这一背景下,教育主体的要素被激活,教育管理中民主化的管理决策模式便得以建构。一方面是基于伦理道德的主体精神得以培养,另一方面是在教育体系内形成了较好的民主意识环境,还有就是“他者”的监督成为可能。众所周知,独处者并不存在对与错的问题,其“善”也仅仅是满足于自身的精神追求,正是基于此,中国传统儒家教育才讲“独善其身”。教育管理是一种关系处理,换句话说,正是因为管理伦理主体的建构和确认,使调节性的管理关系成为可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便不再是一元性的,而成为一个主体间性问题。这样,以“主体”的存在为指向,教育管理便超越了工具性之维,管理过程也便具有了伦理意义上的民主化内涵。
第三,幸福型情感管理模式的达成。英国教育家约翰·怀特说过,受教育的人就是拓展他自己的幸福,然后把自己的幸福推己及人,并且把幸福生活于高尚的道德生活合二为一[24]。对教育来说,也就突破了唯知识论的局限,从而把美德与知识并举,把幸福情感作为管理模式的建构手段之一。道德情感的交流是基础,幸福的追求与感受是主体的目标,以在组织内部形成和谐融洽的工作氛围,“情感管理就是以真挚的情感来增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情感联系和思想沟通,以形成和谐融洽的工作氛围,为有效实现学校工作目标而进行的组织活动”[25],管理主体在信任、理解、关爱的教育管理过程中,打破个人私欲局限以及社会要素干扰等,达成对幸福教育生活的追求。
综上所述,“道德,是现代教育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26],教育管理伦理主体的建构,无疑是追求教育与管理、知识与道德、个人与组织的有效手段,教育管理伦理主体的建构与完善,也是教育管理境界提升的必由之路。
[1]郅庭瑾.教育管理伦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3):38-42.
[2]周祖城.管理与伦理结合:管理思想的深刻变革[J].南开学报,1999(3):77-83.
[3]戴木才.论管理与伦理结合的内在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02(3):24-33.
[4]杨伍栓.管理伦理与人本管理[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学报),2004(4):11-18.
[5]金保华.论教育管理的伦理性[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4):9-11.
[6]金保华.人的自由发展:教育管理的终极善[J].教育研究,2004(12):30-36.
[7]詹向阳.高等教育管理主体:一个新模式下的解读[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109-113.
[8]孙绵涛.关于教育管理活动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思考[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6(6):36-39.
[9][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96.
[10]朱武振.伦理的“主体性困境”探析[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19-23.
[11][法]雅克·马里坦.存在与存在者[M].龚同铮,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62.
[12]樊浩,田海平等.教育伦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6.
[13]Carol Campbell.Exploring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de-bates in education management[J].Education Policy,1999(6):656.
[14]丁秋玲.论公共行政主体的德性[J].湖北社会科学,2004(5):60-61.
[15]高国希.德性的结构[J].道德与文明,2008(3):37-42.
[16]王泽普,苟兆国.道德制度建设引论[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14-20.
[17]郑春燕.道德教育新取向:道德情感的疏通与回应[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91-96.
[18][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李学勤,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48.
[19]孙利平.企业组织德行领导的内容结构及其相关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08.
[20]余虹.有限德行与无限德行[J].河北学刊,2007(1):52-55.
[2][法]卢梭.爱弥尔(上卷)[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26.
[22][美]丹尼尔·贝尔,克里斯托尔,等.经济理论的危机[M].陈彪如,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29.[23]杨国荣.道德与价值[J].哲学研究,1999(5):62-69.
[24][英]约翰·怀特.再论教育目的[M].李永宏,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138-139.
[25]赵福庆,等.自主管理创新教育的制度建构[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114-115.
[26]黄兆龙.教育管理伦理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85.
The Main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Ethics and Its Strategies
DUAN Jia-li1;ZOU Hua2
(1.Department of Management,Changsha Medic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219,China;
2.Department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Hunan College of Information,Changsha,Hunan 410200,China)
G40-058
A
1672-934X(2017)05-0128-05
10.16573/j.cnki.1672-934x.2017.05.019
2017-07-28
段佳丽(1980-)女,湖南衡阳人,讲师,主要从事教育管理研究;邹 华(1983-),女,湖南衡阳人,讲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