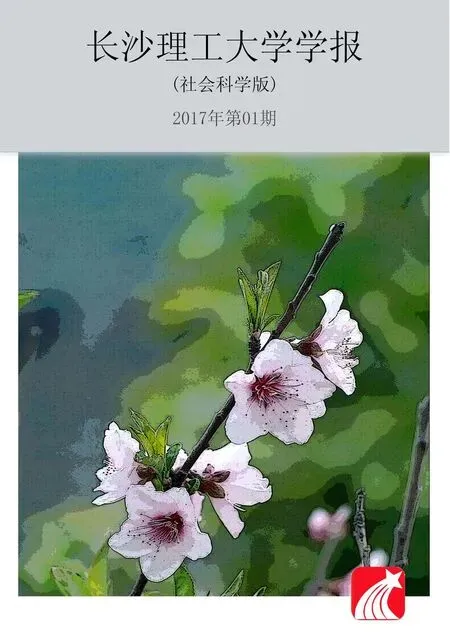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应对路径与困境
龚 超,王国豫
(1.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哲学系,湖南 湘潭 411201;2.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3.大连理工大学 哲学系,辽宁 大连 116024)
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应对路径与困境
(1.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哲学系,湖南 湘潭 411201;2.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3.大连理工大学 哲学系,辽宁 大连 116024)
进入21世纪以来,以纳米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问题日益突出,纳米技术已经走进并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世界, 纳米技术的不确定性成为其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为此,欧美学术界提出了应对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不同路径,如预防原则、亲行原则、“嵌入”道德的经验原则等,但在实践中这些路径或原则在可操作性方面还不够,也遭遇到了一定的困境。在不确定性无法消除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确立“与不确定性共存”新的理念,立足于可行性来思考我们应对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可能方案。
纳米技术;不确定性;预防原则;亲行原则;“嵌入”道德的经验原则
随着纳米伦理学、纳米毒理学等学科对纳米技术不确定性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我们开始认识到纳米技术的不确定性具有自身的特征并可能产生包括健康、环境、伦理社会等在内的诸多后果,这是纳米技术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技术评估作为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一环,强调在不确定性状态下纳米技术评估的实用性、可评估性和可认知性,但也忽视了纳米技术的非线性特征,忽视了技术演化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律,因此更重要的是需要考虑纳米技术不确定性应对的战略与路径。
纳米技术的发展不仅是技术演化的自然而然的结果,更是人类希望彻底摆脱自然束缚、超越自身有限性的诉求,但同时也无法摆脱技术发展的“科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s Dilemma)。这就是在技术的实现过程中,某项技术的社会后果是无法预测的,等到那些不好的结果开始显现的时候,技术已经成为了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中的重要部分,对它的控制几乎变得不可能[1]。由于纳米技术还处于发展的早期,关于纳米技术的信息、知识等的积累较少,纳米技术对人类健康和自然环境的影响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理等还不明确,使得不确定性问题进一步加剧,这意味着我们应当从技术实践活动的不同阶段和应用场景出发,去寻找应对不确定性的路径。欧美学术界对此有过一些有益的探索,但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需要我们在探讨引起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根本原因的基础上,进一步寻找应对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有效途径,为纳米技术的发展及其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建议和政策支持。
一、预防原则及其困境
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是在应对以纳米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时频繁被提及的一个原则。关于预防原则的定义,目前在国际上还没有达成一致认可或统一的意见。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预防原则可以应用于环境保护等领域,应当在考虑危害或威胁的概率的基础上事先采取措施避免这种危害或威胁发生。它要求通过系统而综合的协调研究,对环境的危害或威胁进行持续监测,查找其产生的原因。在科学尚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性意见的情况下,也应当采取预防措施[2]。1992年发布的《欧洲共同体条约》则认为,除了强调环境保护中应广泛采取预防原则,该原则也适用于其他有关健康的风险。在初步的科学证据己经显示有可能对环境、人类健康等构成潜在危险,即使科学信息还不确定、不充分,也适用该原则[3]。此外,在《里约宣言》《卡塔赫纳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等国际公约或条约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可以说,预防原则已经成为了许多国家乃至国际上制定有关环境保护政策的重要指导原则之一。面对纳米技术发展过程中所凸显的种种不确定性,将预防原则视作应对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一个路径选择,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
首先,从预防原则的定义来看,预防原则的提出本身就来源于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预防原则强调科学确定性的不足,不能成为推迟采取防止危害或威胁措施的理由。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不确定性问题也逐渐变得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为在科学研究和应用中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和随机性。对于纳米技术而言,它所研究的对象是在纳米尺度下物质,这是人类对自然世界认知的全新领域。由于纳米技术尚处于研究与发展的早期,学术界对如何应对不确定性还没有达成共识。纳米颗粒具有小尺寸、极易被人体吸收、在自然环境中极易扩散等特点,有研究显示,正常情况下没有危害的微米物质,一旦其材料尺寸达到纳米级别,就表现出毒性,这会对健康带来潜在的风险,其反应活性和毒性与颗粒尺寸有着密切的关系[4]。
也就是说,纳米技术对健康、环境等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影响和风险,而且这种影响很有可能是负面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当前的认识水平又远没有达到降低不确定性的要求,因此预防原则在应对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过程中才被提出来。2006年《自然》(Nature)杂志发表了由著名毒理学家梅纳德(Maynard A. D.)领衔的14位一流的纳米毒理学专家提出的研究纲要,提出要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揭示出纳米材料与人类健康及环境的关系,包括开发出监测大气与水中纳米材料的装置;评估纳米材料毒性的方法;从纳米材料的生产、使用及最终的处理等一系列过程的预测与评估等[5]。这些研究项目的实施必将有助于推动人们对纳米技术的认识,并促进整个纳米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从预防原则的实施目的来看,预防原则是为了有效规避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消极应对,等到因果关系确定了才去做决策,而应该从已有的观察和知识入手,去判断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影响,并提前采取应对措施[6]。因此,预防原则是一种积极应对不确定性的策略,即如果有证据表明,某项行动有可能会对健康或环境带来威胁或危害,在现有科学还不能明确这种行动和不良后果之间的联系的情况下,我们也应采取行动以防止危害的发生。
纳米技术在现代科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严格禁止纳米技术的发展,那么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无疑将处于全面落后的局面,这也就不难理解当今世界各主要科技强国无不将纳米技术的发展置于国家战略高度的原因了。在现阶段纳米技术的发展大部分还是在传统学科的框架之内。有学者认为,在当前纳米材料的实验室研究阶段,可以采用传统的防范未知毒性材料的相似措施来应对纳米材料的不确定毒性,如采取通风、佩戴手套等手段阻止纳米粒子的吸入与接触[7]。
虽然在应对纳米技术不确定性时,预防原则可能发挥较为积极的作用,但它也面临着一些局限。首先是预防原则的定义模糊,由此带来对它的不同解读。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关于预防原则的统一定义,尽管这一原则已在诸多国际公约、会议公报中广泛提出并采纳,但在不同的背景下,往往表述各有侧重和不同。对于不利影响,如“损害”“威胁”“危害”等都缺乏确切的描述,“科学信息不充分”“因果关系不明确”等表述也都带有极强的主观性。当预防原则运用于应对纳米技术的不确定性问题时,这种模糊性则进一步加剧,因为目前我们对纳米技术的认识远没有达到普遍公认的标准。除了前文所引述的美国国家纳米创新计划对纳米技术所下定义之外,不同组织或学者也都给出了自己的定义,这种双重的模糊性无疑将加剧预防原则在应对纳米技术不确定性中运用的难度。
最后,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很容易造成对于预防原则的运用带有选择性,表现出在某些领域严格,某些领域随意的混乱局面。对于纳米技术而言,由于与之相关的产品异常丰富,几乎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之相关的监管法规等也必将是多种多样的,例如针对纳米食品、化妆品、纺织品等特定领域的监管。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世界各国或国际组织间还没有专门针对纳米技术相关产品的监管法规出台。这种选择性运用的现象在纳米技术监管方面的表现将更为明显。
二、亲行原则及其困境
由于预防原则在实践中所带来的困惑,近年来,一种强调先行动并在行动中学习的“亲行原则”也受到学界关注。亲行原则(proactionary principle,或译作先行原则)最早是由未来主义和超人类主义哲学家摩尔(More M.)于2004年提出来的,亲行原则是作为预防原则的替代选择而设计的。摩尔认为,预防原则的运用阻碍了新技术的引进与进步,主要表现:往往假设了最坏打算的情景;低估了现有的对健康特别是自然已经存在的风险;假定监管的效应都是积极的或中性的,从来都不会是消极的;忽略了技术的潜在利益;将举证的任务不合理地转嫁到技术支持者一方;与应对风险和伤害的更为平衡和习惯性法律的路径相冲突[8]。摩尔指出,预防原则使得决策部门在面对现状时倾向于做出有偏见的决策,对技术的进展持一种过分悲观的观点[9]。
在对预防原则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摩尔提出的亲行原则是指决策者考虑技术活动的所有后果,部署预防的措施来应对我们实际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又重视技术创新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相信人类有能力去适应和补救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亲行意味着不仅要在行动前的预测,更强调通过行动来学习。特别是从历史的视角看,所有重要的技术创新以及它们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在其发展的初期也并不是为人们所完全理解,但如果我们因此而中断研究,我们不可能取得现在的科技进步。
亲行原则把人类在学习、创新和进步等方面的自由放在优先的地位,认为技术创新的自由对人类来说具有很高价值,甚至可以说对人类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是否和如何发展、展开或限制新技术都意味着与责任相关。我们应该在科学的基础上对风险和机会进行评估,制定客观且开放和综合而又简洁的决策,而不是依靠集体情感反应。对限制发展技术所付出的成本和机会的丧失也应作出充分解释。
将亲行原则运用到纳米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是希望纳米技术的创新与进步给人类带来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亲行原则也强调应该注意纳米技术潜在负面效应与风险的存在。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亲行原则包含以下要点:第一,保证纳米技术创新的自由。第二,保证纳米技术的决策过程是客观的,结构化的和清楚的。第三,全面性。考虑所有合理的可供选择的行动,包括不采取行动时的情形。第四,包含各方意见,考虑潜在受影响群体的利益,保持这种进程的开放以使得合法的代表都纳入进来。第五,简洁性。运用的方法不应当是比其他原则更为复杂的。第六,优先处理和分类原则,为了减少纳米技术的副作用,应当优先考虑纳米技术对人类健康带来的影响,再考虑其对环境的影响;优先考虑立即造成的影响,再考虑其远期影响;优先改善已知且已证明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风险,再考虑假设的风险。第七,采取有差别的应对措施。只有在某项活动的潜在负面效应具有极高的可能性与严重性时才采取限制措施。第八,尊重价值的多元化。第九,平衡的对待问题。同等的对待技术风险与自然风险,避免低估自然风险而高估人类技术风险。第十,重新审视与更新。当未来的条件发生明显变化时,决策者应及时对决策重新审视,尽快采取有效且能够承担的纠正方案[8]。通过这些具体的实施要点,摩尔希望能将亲行原则塑造成一个包容性和结构化的应对不确定性的路径。
在技术活动实践中,亲行原则也面临着诸多局限性。首先,亲行原则提出了对技术创新采取完全开放的政策,通过行动来学习而不是通过对于技术活动的事先思考。亲行原则将关注点过多的集中在简单的因果关系上,而忽视了其他方面发展的相互作用所带来的复杂结果。与此同时,通过行动来学习的逻辑将使得在实践中无视必须遵循的现有监管举措,使得技术发展没有任何限制。其次,亲行原则所强调的成本-利益分析的考虑不具有可行性,因为对利益的经济价值进行定量分析是非常困难的,新技术的风险和利益是未知的并具有不确定性,这使得在这方面的评估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远期风险的预测更加困难。虽然权衡风险和利益的重要性不能低估,但在实践中通常很有问题并且不能发挥作用。而且,有些利益如对环境或生物或健康等造成威胁,并不能仅仅通过经济价值来衡量,这还包括不同的社会价值或个体文化的观念等[10]。在缺乏充分的或确定的科学知识的情况下,我们几乎很难准确计算行动或不行动时的成本和收益。
对于纳米技术来说,这种测算的难度进一步加大。纳米毒理学的研究能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纳米材料对人类健康可能带来影响的诸多不确定性。已有研究表明,相同化学组成的材料,在纳米尺度和微米尺度上所表现出的毒理学效应通常具有较大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必须根据不同的材料进行分析。即使是相同化学组成和剂量的物质,它在不同纳米尺度下或不同纳米结构时,其毒理学结果也表现出新的不确定性结果[11]。由此可见,纳米材料对健康的潜在影响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我们很难通过对各种因素的量化分析,将可能带来的健康问题简化为成本和收益的计算问题。
三、“嵌入”道德的经验原则
除了预防原则与亲行原则,还有一种更加关注行动的经验原则,即“道德物化”(materializing morality)或“嵌入”的行动战略也成为应对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新路径。“道德物化”战略的基本思路是,按照技术中介论的观点,技术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起着中介调节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技术对人的认知和行为发挥着中介调节的作用。因此,技术设计活动必然负载着价值,成为一个包含伦理因素的活动。基于这种认识,荷兰技术哲学家维贝克(Verbeek P.)提出将道德“嵌入”到技术设计的新的理念。具体来说,“道德物化”是指在技术设计的过程中,将特定的道德观念、伦理因素等“嵌入”到技术人工物的功能和结构等属性之中,这样技术人工物的使用实际上就会引导和规范技术使用者的行为,甚至影响使用者的决策。“道德物化”从物的角度入手,通过“道德化的物”来迫使人们产生好的行为,这与传统的义务论伦理学和德性伦理学有着明显的区别。义务论伦理学强调通过内化于心的自我规范来获得真正的道德行为,而德性伦理学认为只有具备美德的人才能理解道德原则,二者都是从人的角度去达到幸福。“道德物化”思想从技术的外在环境出发,将道德规范、伦理因素外化到技术设计的过程中,体现在具体的技术人工物之中,可以看作是结果论伦理学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注重技术人工物所带来的实际功效,希望它能带来的最终的结果是大多数人的幸福。因此“道德物化”的思想在理论上是可以得到结果论伦理学的支持[12]的。
被“嵌入”道德的技术人工物具有的重要的伦理意义,它能对人的行为和认知产生影响,因此伦理责任成为了在技术使用和技术设计领域都需要面对的问题,而以往我们往往忽视了技术设计活动这一环节的重要性。“道德物化”思想更加强调技术设计者的责任,如果把技术设计活动看做是一种伦理活动,那么技术设计者实际上对技术伦理问题的产生和规避等都起到了原生性(seminal)的作用[13](P90)。这就要求设计者关注技术人工物与技术使用者的关系,同时也要关注技术人工物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塑造。可以说,技术的伦理意义就是由技术设计者、技术人工物以及技术使用者共同创造出来的。技术设计者实际上也是在从事伦理学(doing ethics)的活动,设计出来的技术人工物就是他们创造出来的一种“嵌入”了道德的物化形式(material form)[13](P91)。例如在荷兰“永恒的你”(eternally yours)的设计项目中,设计者就将生态保护理念贯穿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针对消费者长时间使用某一个产品而引起审美疲劳,从而在产品还可以使用时就遭到丢弃的问题,该项目设计的沙发就能在沙发长时间使用后由于磨损会呈现出新图案,有效地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14](P219-222)。通过将环境友好的理念嵌入到设计中,达到了影响消费者行为习惯并形成更好的生活方式。
在对“道德物化”思想的理论背景以及重要性做出论述以后,维贝克进一步对“道德物化”的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的分析。“道德物化”主要包括预测(Anticipating)、评估(Assessing)和设计(Designing)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预测,主要是对技术的中介作用进行预测。对于一个新技术而言,预测并非易事,这是由技术的“多元稳定性”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技术的本质与其具体的语境和使用者的理解有关[13](P97)。例如,互联网最初是用于军事领域,而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沟通的重要工具。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语境(context of design)和使用语境(context of use)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在重视技术产品功能的同时也要关注它可能具有的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做出合理的预测和伦理评价。维贝克认为可以通过设计人员的“道德想象力” (moral imagination) 、“扩展性的建构性评估”(augmenting constructive technology assessment)、“情景模拟”(scenarios and simulations)等三种方法来构建起“设计语境”和“使用语境”之间的联系。具体来说,设计人员的“道德想象力”就是通过设计师的想象去思考技术产品在未来使用中的任何可能性,特别是它对人的行为和感知的中介作用。“扩展性的建构性评估”就是强调评估过程应包括各个利益相关者,这样能弥补技术设计过程中设计师道德想象力的局限,从而提高对技术中介调节作用预测的准确性和完整性[13](P102-104)。“情景模拟”(scenarios and simulations)就是要考虑技术使用过程中的具体语境,通过虚拟现实模拟的方法可以对产品在未来被使用的方式等进行预先的考察,反过来促进设计的过程。
第二个阶段是评估,特别是伦理方面的评价。与“扩展性的建构性评估”类似,“道德物化”的评估也应该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从他们各自的立场出发,对某一个伦理问题发表意见,在权衡比较这些意见的基础上获得一个全面适中的评价结论[13](P106)。维贝克指出,从技术中介的视角来考虑,技术的伦理评价应重点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一是评价技术设计者有意嵌入的中介作用;二是评价技术人工物可能的中介作用,主要是评价通过“道德想象力”“扩展性的建构性评估”和“情景模拟”等方法获得的预测内容;三是评价技术中介作用所采取的形式,分析这些作用的“强制”(force)、“劝导”(persuade)或“诱发”(seduce)的性质;四是评价技术中介作用的最终实现结果,必须考虑预测的结果与实际的结果之间的差异[13](P107)。
第三个阶段是对中介作用的“设计”,或者说是对“设计”方案的选择。维贝克把这种选择看作是一种尝试,因为我们所嵌入的“道德内容”(moral content)并非就会我们所预测和评估的那样在使用过程中必然发挥作用,它还会受到许多不可预料的因素的影响。因此,道德嵌入技术设计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适度的和试探性的活动,而不是要对人类行为完全的操纵。
在纳米技术的实践中,维贝克的“道德物化”思想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纳米技术的治理就特别强调伦理学家的参与,这也使得纳米技术成为了新兴技术治理的典范。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费希尔就将关注点对准正在研究中的纳米技术项目,提出应该在自然科学家与伦理社会学家之间形成互动的“中游调节”模式。通过对项目参与者的前后两次的互动访谈,可以发现科学家者群体开始根据伦理社会因素等来调整研究决策过程,同时也使研究项目发生了变化。例如,对实验设置进行调整,改变处理方法,形成新的安全规则等[15]。此外,纳米技术的治理也特别重视公众作为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从纳米技术自身的不确定性来看,我们很难通过某个单一学科来应对其不确定性,而是需要构建多元的知识形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众参与所提供的是各种信息与经验的集合,也是多元知识的一种形式[16]。
四、结语
总的来看,目前学术界应对技术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所采取的路径方案,都是从增加人类福利的角度出发,但各自的侧重点相差较大。预防原则从保护人类、环境免遭伤害的角度出发,对技术发展持一种谨慎悲观的态度;而亲行原则从促进技术发展,鼓励技术创新的角度出发,对技术发展持一种乐观的态度。但在纳米技术具体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其在本体论、认识论、社会伦理影响等多层维度的不确定性存在,这两种原则在可行性方面遭遇到了困境。预防原则希望能在技术发展之前就能发现它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危害,从科学上来说不具有可行性;而亲行原则所倡导的等技术带来效益后再来对其进行风险评估,在政策上也很难实现。而道德“嵌入”的路径将视角转向技术的功能和使用的维度,重视对技术设计过程中对产品中介作用的预测、评估和设计,希望能借助技术来规范人们的行为,防范技术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但也面临着过高地赋予设计师权利的伦理风险。
这些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案或路径,都还是把不确定性看作是一种威胁或危险。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我们往往尽最大的努力去消除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带来的对未来不可控制的局面,这种技术的不可控性与技术后果的不可避免性、技术后果的不可预测性、技术的复杂性等多重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17]。而事实上,不确定性也意味着机遇和变化,它带来了我们生活世界的丰富多彩。在不确定性无法消除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确立“与不确定性共存”新的理念,意味着我们要接受不确定性的存在,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寻找确定性的解决方案。同时也意味着在面临多重可供选择的目标时,能够保证我们所做出的选择是最佳选择。
基于中国哲学面向行动的可行性评估,实际上是立足于可行性来思考我们应对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可能方案,特别是要通过挖掘中国哲学,例如《易经》中所蕴含的丰富思想与观念,旨在为纳米技术的发展提供一种引领性的行动框架原则。对于纳米技术来说,随着我们认识的深入,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会发生转化,要求我们在实践中采取“且行且看”的策略。对变化的应对可能又会引发新的变化,需要我们动态地制定纳米技术发展的政策和规范,不走极端,全面地看待纳米技术的风险与机遇。
[1]Collingridge D.The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M].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0:11.
[2]Percival R V. Who's afraid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J]. Pace Environmetal Law Review, 2006,23(1):21-81.
[3]Fisher E. Risk regul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constitutionalism[M]. Portland: Hart Publishing, 2007:39-45.[4]毕永红,胡征宇.纳米材料对环境和健康的潜在危害[J].上海环境科学, 2006(5):214-218.
[5]Maynard A D, Aitken R J, Butz T,et al. Safe handling of nanotechnology[J]. Nature, 2006, 444 (7117):267-269.
[6]胡丽.科技风险预防的综合机制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1.
[7]Hallock M F, Greenley P, DiBerardinis L,et al. Potential risks of nanomaterials and how to safely handle materials of uncertain toxicity[J].Journal of Chemical Health and Safety, 2009,16(1):16-23.
[8]http://www.maxmore.com/proactionary.html[EB/OL].
[9]Holbrook J B, Briggle A. Knowing and acting: The precautionary and proactionary principles in relation to policy making[J].Social Epistemology Review and Reply Collective, 2013,2(5):15-37.
[10]Colussi I A. The Role of Responsible Stewardship in Nanotechnology and Synthetic Biology[A]//Arnaldi S, Ferrari A, Magaudda P. Responsibility in Nanotechnology Development[M]. Dordrecht:Springer,2014:44-83.
[11]Gong C, Wang G. The Ethical Challenges of Uncertainty in Nanatechnology[A]//Wang Q.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Ethics and Applied Philospphy in East Asia[M]. Dalian: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2012:224-234.
[12]张卫,王前.道德可以被物化吗?——维贝克“道德物化”思想评介[J]. 哲学动态,2013(3):70-75.
[13]Verbeek P -P. Moralizing technology: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14]Verbeek P -P. What things do: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y,agency,and design[M]. University Park: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0.
[15]Fisher E, Mahajan R L, Mitcham C. Midstream modulation of technology:governance from within[J].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2006,26 (6):485-496.
[16]Stirling A. Risk, precaution and science: towards a more constructive policy debate[J].EMBO reports,2007,8(4):309-315.
[17]盛国荣.技术与控制:一个技术时代难以回避的问题[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2):22-27.
The Approaches and Dilemmas to Cope with the Uncertainty in Nanotechnology
GONGChao1,WangGuo-Yu2,3
(1.SchoolofHumanities,Hunan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Xiangtan,Hunan411201,China;2.SchoolofPhilosophy,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3.DepartmentofPhilosophy,Dal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Dalian,Liaoning116024,China)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uncertainty of the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nanotechnology becomes more and more outstanding. Nanotechnology had come into our life. Meanwhile, it is more and more deeply effecting our life world. The uncertainty of nanotechnology becomes an inevitable problem in the development of nanotechnology. So scholars in US and Europe proposed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deal with the issues, for instanc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proactionary principle; the empirical principle by "embedding"ethics. But these principles or approaches encounter some dilemmas in practice. In the cases that cannot eliminate the uncertainty, we should establish a new idea about "living with uncertainty". In this way, we may think about the possible solutions to deal with the uncertainty of nanotechnology based on the feasibility.
nanotechnology; uncertainty;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proactionary principle; the empirical principle by "embedding" ethics
2016-11-18
龚 超(1983-),男,湖南益阳人,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技术伦理学、技术哲学研究;王国豫(1962-),女,江苏盱眙人,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德国哲学、技术伦理学、科学技术与文化研究。
TB383.1
A
1672-934X(2017)01-0031-07
10.16573/j.cnki.1672-934x.2017.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