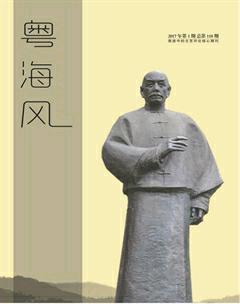赵元任先生与中国语言问题
胡龙霞
着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周有光老先生过了112岁生日去逝。周有光参加制订了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他曾经回忆:“到了50年代,我们要重新设计拼音方案,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的拼音方案就参考了国语罗马字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再走了一步。” (《周有光口述》,李健亚采写,《新京报》2007年1月23日)。这里说的是在中华民国成立的第二年,当时的政府公布了一套注音字母方案,这套方案由黎锦熙主持,赵元任参加,是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一套方案,国语罗马字是第二套方案,我们现在使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是第三套,1958年公布,至今已经使用59年,并于1982年通过ISO国际标准组织认定,成为汉语拼音的世界标准。这是汉语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的全球通用发音标准,也是汉语作为通用语言第一次拥有的通用发音标准。对此,周有光功不可没,赵元任有开拓之功。这篇文章,也算是对老先生们的一份纪念。
中华大地上距今7000年前已经有疑似汉语文字的图画、符号出现(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出土的113个符号),距今5000年前,系统完全的汉语文字出现(甲骨文),距今3000年前,完整的汉语书面文出现(先秦古籍),公元前217年,秦王朝颁布“书同文”法令。2200多年以来,汉语书面文从古文到骈文到文言文到白话文,同汉语口语相对独立地实现着自我发展变化,同时,汉语口语则始终保持着自身的语言发展规律,以地域、方言为特征实行着世代传承,直到1923年“国语筹备会”开始着手推行汉语通用语言:“国语”,中华大地上才开始出现一种统一通用的汉语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到1957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汉语通用语言“普通话”才开始普遍推广使用。60年来,普通话已经基本成为了汉语通用语言,但是,普通话的口語和书面语并不完全一致,汉语书面文也并没有完全同普通话保持一致,
更值得思考的是,在赵元任先生之前,有关汉语言的学术研究始终局限在文字、文字音韵、文字释义的范围内打转转,而且主要的眼光是紧紧盯着几百几千年前出现和使用的文字,两千多年时间里的中国语言学,实际上不过《尔雅》、《方言》、《说文解字》的颠来倒去,没完没了地谈论他们关于古文字,古音韵的解读,谈论汉语言的基本面貌特别是古汉语的表现状态,就是不去研究汉语的现在和未来如何发展,更不谈论汉语如何成为全民通用的语言,连汉语口语和文字的关系也或者避而不谈,或者浅尝辄止,似乎汉语就是那些早已经成为历史的古代文字,也就是胡适所说的死文字。
公元1914年夏天,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帮中国留学生闲谈起当时的中国严重缺乏科学知识的问题,谈出了一个中国科学社,并在上海出版了一份《科学》杂志。直到1949年,中国科学社成为当时中国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研究的主要力量。赵元任先生作为中国科学社的主要创办人和《科学》杂志的主要创办人,1921年之后,他的学术研究逐渐转向了汉语言,并利用《科学》杂志为学术阵地,在《中国语言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科学的研究汉语”,他的《官话字母译音法》、《中国言语字调的实验研究法》、《再论注音字母译法》、《电信号码根本改良的根本探讨》、《语音的物理成素》、《符号学大纲》等语言研究成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形成与发展,开创出了一条全新的科学道路。赵元任先生也因此成为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汉语言学家,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创性进行的汉语声调研究课题,后来由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完成为《汉语拼音方案》的四声标准;他创制的五度制汉语声调记调符号,恰如他设计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精确性强,但普及使用的难度大,加之他并未直接参与《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汉语声调最终被定型为四声,即与传统音韵存在关联,又符合当代汉语通用语言的发音习惯,“赵氏调符”尽管未被《汉语拼音方案》直接使用,却奠定了汉语声调的理论基础;他曾出任“国语筹备会统委员”,编写录制了《国语留声片》课本,推动了现代中国社会通用语言的形成和使用,设若没有“国语”的形成和使用,我们难以想象汉语通用语言“普通话”能够顺利推广使用。
尽管至今中国各地的大多数人们都更习惯使用自己从小就学会的地方语言进行口头交流,尽管普通话已经基本上能够全社会通用,按照赵元任先生的《语言问题》关于语言的描述,至今的汉语通用语并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语言体系。赵元任先生在《语言问题》中说:“一种通用语言,如果已经使用文字,它的口语词汇、文字词汇的表意一一对应,文字词汇的发音同口语一致,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共同构成这种通用语言的两种表达形式,两种表达形式为同一个语言系统。”
汉语普通话作为当代中国通用语言,与赵元任先生对于通用语言的描述还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普通话的语言描述不够科学(详见附文:《不伦不类的普通话》),这种不够科学的语言规定导致了普通话作为通用语言的先天缺陷。另一方面,中国当代的语言教育和语言运用长期厚古薄今,使得汉语通用语的运用标准表现得比较混乱。
在语言教育中,以2016年人教版9年级语文课本为例:25篇课文,超过100年的古文9篇,超过50年的6篇(其中一篇注明为1999年发表,但实际写作时间为50年前,而且也主要写100年前的内容),外国作品5篇半,当代的4篇半(两篇诗歌)。以篇数计量,当代的占18%,外国的占22%,超过50年的准古文占24%,超过100年的古文占36%。也就是古文和准古文占60%,当代文占40%。
古文和准古文中的一些词汇与当前的普通话词汇不一致,它们因此与当前使用的普通话并不属于同一个语言体系,它们属于汉语通用语言实行之前的汉语书面语体系,当前的普通话属于汉语通用语言体系,两者之间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两个语言体系并不一致,古文和准古文所使用的语言体系不仅同普通话大相庭径,其文字也与当代通用的汉语言文字存在千差万别。在当代汉语通用语言的教学中使用非当代汉语通用语言体系的语言教育课本,语言教育效果可想而知。这当然不便于人们完整、准确地学习使用汉语通用语言,使得汉语通用语言的使用出现混乱。
在书写方面,当代汉语书面文表现为互不相容的四大语言系统:中小学基础教育中的作文、不同的学术专业文章、官方公文、文学作品,由于各自的语言系统互不相容,各自书写而成的文章也就主要表现为本领域内通用。举例来说,中小学作文只流通于中小学,一旦高考完成,作文的使命也终止;学术专业文章只在各自的学术专业范围流通,非本专业或非学术人士难以阅读写作;官方公文为官方流通,在其他社会领域如读天书;文学作品相对于其他系统,基本上能够做到全社会流通,但一旦属于那种“纯文学”,也往往只在文学专业人士范围流通,其他社会领域难以问津。
早在1915年,胡适产生推广使用白话文的构想之初,赵元任先生也对白话文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大胆尝试,当时,胡适的文章往往夹杂着“文言”,常常需要赵元任先生帮忙修改,“你的白话文不够白”。赵元任先生取笑胡适的这句话背后,显示出他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更展示出赵元任先生的白话文水平在当时已经无人匹敌。最有力的证据是1922年用地道的白话文翻译出版的《爱丽丝漫游奇景记》,1922年出版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在赵元任先生的作品和课本里,白话成为唯一的语言标准,文字所表达的每个字每个词每句话都与当时人们通用的“国语”相对应,无论是发音还是表意,都严格保持与当时的“国语”为同一个语言系统。事实上,我们现在使用的汉语言通用语即普通话,尽管与赵元任先生当初设置的“国语”有明显区别,但我们无法否认,普通话的确大量承袭了“国语”的成分。
附文:不伦不类的普通话
中国当代使用的通用语言稱普通话,也称现代汉语,俗称官话,由汉语口语和汉语书面文两种形式构成。1951年,当时的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开始重视汉语汉字问题,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其主要内容是简化汉字,确立普通话为中国通用语言。根据这个指示,语言文字学家们确定了普通话的基本内容,这个内容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描述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描述至今为大家公认,所有关于汉语语言的学科、教科书,都使用这个描述。
我们使用的汉语通用语竟如此不伦不类。
方言的意思是不同地方所使用的不同语言(口语,或口语加书面文),当一种方言被选定为通用语言,这种方言就变成了通用语言, “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解释,并没有确认北方话的通用语言身份,只是将它提升到了“基础方言”的地位,还是方言,比其他方言的用场多一点点。
“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哪些著作被称为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这种确认以什么为依据?由谁确认?就算用不着告诉大家确认的依据和机构,从使用角度来说,公布出来这些被当成“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目录,人们才有样板可学,可模仿,不然,这个语法规范究竟是怎样的,谁能说得清楚呢?还有, 如果这些“典型的现代白话文”与北方话的语言习惯不一致,怎么办?如果不同的“典型的现代白话文”作品出现不同的语法规范,以哪篇为规范?
任何一种语言都经过了长期的使用、演变、传承,是庞大的人群共同使用的结果。一种语言的消亡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够出现,使用这种语言的人越来越少,直到再也没有人使用。而一种语言的产生,那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情,从那以后,人类世界的语言只有一种种消亡,从来没有新冒出一种语言。而某种语言的兴旺,则只是使用它的人数越来越多的结果,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原因。
汉语通用语言的描述(其实是官方规定),看上去是选择了北方方言,实际上是幻想着打造出一种新的语言,北方方言只是它的基础方言,混搭上北京语音,典型著作的语法,这边要一点,那边借一点,而且还是一些不明不白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混搭成的语言,不伦不类是次要的,实际上只能是一种幻觉,一种臆想,无法成为事实。这也许就是汉语通用语言和书面文至今难以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致命原因。
如果说当初确定北方方言作为中国社会通用语言的时候,人们对语言的认识有限,难以认识清楚方言与通用语言之间的关系,只能将普通话描述成这样一种不伦不类的语言,当属可以理解。而选定通用语言,推广普通话已经过去了60多年,至今的汉语标准、教学标准依旧使用这种描述,毫无进展,不能明确、完善汉语语言的内容,不知道是显示汉语认识能力低下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让人费解。
既然选定了北方话为通用语,就应当明确这种方言的通用身份。
事实上,2000多年来,汉语通用语言一会被称作官话,一会被称作雅言,一会被称作普通话,名称换来换去,语言始终没有脱离北方方言,它已经被使用那么多年,使用的人数越来越多,绝非谁想改变、谁想灭绝它就能够做到。
因此,汉语通用语言,也就是普通话,并非异想天开的新造语言,而是选择已经存在了多年的汉语北方方言,将这种方言进行直接的描述,用作汉语通用语言并不困难,也不存在任何障碍,唯一的阻碍是某种愚蠢的自以为是的权威。
是抛弃那种愚蠢的自以为是的权威的时候了,是时候让汉语通用语回归真实,回归到它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它就是以北方方言的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语言,以北方方言的语言习惯为语法规范的汉语通用语言,也可称普通话、官话、国语、白话,它有口语和书面文两种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