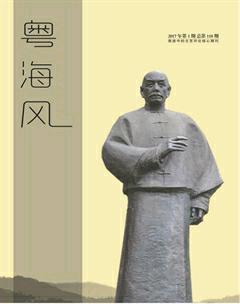现实主义与文化自信 (上编)
陈实+罗宏+谭运长
从《骡子和金子》说起
陈实(以下简称陈):今天我提议谈一个话题,“现实主义与文化自信”。这个话题的起因,是从罗宏新近创作的小说《骡子和金子》,以及由这部小说所引发的系列文化现象说起的。我感觉到,我们广东,至少是文学理論界、文学评论界,对于这样一个创作现象,以及这现象所隐含的某种趋势,不够敏感,没有从理论上来认识它。《骡子和金子》的热度,在广东似乎还不如在江苏、浙江,他们是 小说一出来就知道了,就给予高度重视,我们这里实际上是不太重视的。《骡子和金子》这个小说出来以后,第一,它在读者和阅读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其实反映了一种新的情况,这个小说是写长征的,属于我们一般所说的主旋律的作品。在这之前,所谓主旋律的作品,是从来不怎么受欢迎的,所谓叫好不叫座,大家不太喜欢。
谭运长(以下简称谭):就是能得“五个一工程奖”。其实“五个一工程奖”的评奖标准里面,是有对票房与发行量的要求的,但是实际上大多数都达不到。
陈:达不到嘛。这情形很普遍了,像电影,小说,都是这个样子。甚至就是茅盾奖、鲁迅奖,在这些具有官方色彩,体现国家意识形态要求的体系里面,一般来讲就容易出现这种“叫好不叫座”的情况。也就是说,主旋律写作是一个大问题。而这个《骡子和金子》写主旋律,写得在网上票选都能成为第一,这个很了不起。这本书放在购书中心销售,开始是排在后面的,后来排名逐渐靠前,再后来排到畅销书的名单里去了,完全是在市场里面受欢迎,读者喜欢,才会这个样子,对不对?第二个,它所引发的文化现象。这个作品卖了五六个版权,一个作品带动了一群相关的文化产业,这也是过去少有过的现象。第三个,从我个人来讲,我喜欢小说里边对于中国革命,对于长征的这种思考,尤其是书中“二号首长”这个人物。现在听说这个书准备翻译到国外去,我估计到了国外,人家不一定看重的是骡子这个人物和故事,说不定人家更看重的是“二号首长”所代表的这种思想,说明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对长期以来所奉行的马列主义,有了新的认识。这个东西,是当时的革命者为后人,为后边的时代所提供的、很新颖的思想,我觉得这部小说的贡献,最主要的是这个。以上三点,我是从现实主义创作这个角度来看的,而且罗宏本人有一个发言特别好,他解释了现实主义创作现在碰上的挑战,是在哪个地方的发言?
罗宏(以下简称罗):长安论坛上。
陈:就可以谈谈这个。所以我就觉得,第一,他这个作品对于现实主义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经验,比如说,罗宏没有参加过长征,也没有当过农民,是不是?他这里面写农民,写长征、革命,都不是他经历过的。这个作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来说,就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话题。第二个,我们这个文学,从1980年代,就是我们叫做改革开放以来,受到外来文化各种思潮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学创作中,实际上是变成了东不东西不西的一个东西了,诗歌也出现问题,小说也出现问题,各种体裁都在出现问题。而在这个《骡子和金子》里边,起码有一条,我感觉它基本上是把中国文学创作里边的一些传统类型的东西给复活了,比如说这种类型化、扁平人物。我们从1980年代以来都在批评类型化,批评“扁平人物”,要典型化,写复杂人物,性格二重组合,等等。实际上也没怎么写出来,我看除了路遥的高加林,就没有人能够写出多么复杂的人物来。这是一个。又比如说里边的误会法、巧合法,这都是很典型的中国小说的手法,中国古典的传奇、话本,以及以“三言两拍”为代表的,都是用的传奇的手法,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主旋律,现实主义的作品,我们正儿巴经的这种精英文学,怎么和大众文学结合的问题。《骡子和金子》能改编成电影电视,而且在电影电视里面它又那么受到欢迎,电影电视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大众文化的一个骨干性的组成部分,为什么这个主旋律的作品能够受到大众的欢迎,这是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值得总结和探讨的东西的。我们现在的很多小说,老讲到人民性、人民性。人民性,说白了就是人民欢迎,是不是?人民都不欢迎你,你还说有多少人民性在里边,也就是你自己说说而已。所有这些,我觉得都是与现实主义话题有关的,就我看来都可以归入到关于现实主义创作的讨论,或者是现实主义创作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的某种新探索、新经验的讨论里面。
另一个大问题,就是文化自信。为什么要谈文化自信呢?对此可以扩广一些来说。我觉得,习近平发表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在文艺界里面,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表面上看学习会开了很多,可是从文艺实践来看,并不十分的理想。我思考其中的原因。我觉得,习总书记在讲话里面,是已经看到了至少未来十年,甚至未来三十年,中国文艺应该走到哪一条路上去,我觉得他心里是知道的。但是文艺界也好,理论界也好,在解释这些东西的时候,所能够运用的理论武器太少。基本的理论,我们能够用上的文艺理论,还是以前的那种文艺理论。我们大学学文科的,尤其是学中文的,那时的文艺理论教材,和现在大学里用的,基本上都是相同的一套。
罗:在这个体系下还是有一些变化,但是变化不大。
陈:没有本质的变化,在我来看。我认为,我们现在是叫做中国共产党的新一代,它确实在文学艺术、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应该有创新的地方,这样才不愧为现在的新一代。重要的是,各个方面的建设,能够拿出一套东西来,至少应该像建国初那样,有一个《新民主主义论》来指导,对不对?我觉得习总书记他是看到了这一点,而且他可能心目中也有这些东西,但是给他提供阐释的这个理论,缺乏力度。我简单的说,我们现在应该运用现代武器了,但我们的理论,还处在一个扛麻袋的时代,那不行。这个文学、艺术,它一般在文化里面是属于最敏感的部分,它是看新东西看得最快的,连它都提供不了新的东西,那就不行。我们搞一个文艺座谈会,那起码要有给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新东西,才能够指导下面。
回过头来说,我们平时谈文化自信,嘴巴上是自信了,骨子里还不够自信,就是因为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一些新的东西出来。你看,好像是1962年,陈毅和周总理到广州来开文艺座谈会,直接就带动了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这才出现了六十年代中期的那种全国性的文化繁荣,特别是广东,什么《三家巷》、《香飘四季》啊,以及军区的那些创作,等等。包括中南戏剧会演,许多优秀的作品,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1962年在广州搞的文艺座谈会,一下把大家的思想照亮了。那个时候的文艺界人士,的确是足够自信的。
讲文化自信,还可以说一下所谓粤派,所谓岭南文化的自信问题。前段时间讨论“粤派批评”,我注意到,这个话题的发起人之一陈剑晖教授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认为广东人从不参与全国性的前沿问题讨论,这说法明显是不对的,可见即使在讨论“粤派批评”的时候,岭南文化也还是不够自信。我觉得别的不说,就是两个世纪之交的文艺思想,广东都是处在全国前沿的。1992年在广东开了一个理论研讨会,那个会议很小,但是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艺创作,可以说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其中出现的许多理论认识,在当时无疑都是前沿性的。那么,近年来,很多人认为广东的文艺创造有点落后了,可是你看罗宏的这个《骡子和金子》,那就是一个新的东西,值得进行理论总结的。我的总体的感觉,实际上就是,广东啊,每当有变化的时候,它都会把握到变化的脉搏,产生第一线的东西,这才是广东的文艺界,或者广东的理论界,应该提供给全国的贡献,这才叫做文化自信。
谭:我插一句,我们讲现实主义与文化自信,不一定是指对现实主义的自信,是不是,你的意思?
陈:首先是就提出文化自信的本意来讲的,我个人认为。
谭:那就是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包括你刚才也提到对岭南文化的自信,都是大题目。
陈:题目大,但我们可以从小处谈起。比如说,在文艺观念与文艺理论上,对一些比较适应中国国情,为中国大众喜闻乐见的,同时也是我们的文艺家运用得比较得心应手、行之有效的一些文艺手法,要有自信,不要轻易丢弃。
现实主义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谭:话题是从《骡子和金子》引发的,切入这个题目的话,我觉得可以請作者罗宏说一下,《骡子和金子》是不是现实主义?或者认为是现实主义在一种新的时代变化下,在面临某种挑战与问题的时候,所出现的一种新篇章、新经验?
罗:可以这么说吧。去年8月份,我去参加中国文联在西安和陕西省委宣传部一起做的一个长安论坛。长安论坛的主题就是文化自信,一个大主题,分了三个组,中间有一个组就是讨论现实主义的文化自信,我就被分到了这个小组里面。大概有20几个人参加讨论,只有半天时间,所以每个人发言限定五分钟,很仓促。在现场我也看到一种“学界现象”,谈现实主义,开始从库尔贝讲起,讲到后来不断地有人敲桌子打断,但是他还是收不住,情愿他真正要讲的东西讲不完,也要把库尔贝讲完。最后他的主题还没出来,就不得不结束了。我感觉这个学界的先生比较迂腐,好像他不从库尔贝讲起就讲不下去了。于是到我发言,我就吸取前面发言人的教训,讲得比较直接。第一个,我说现在我们讨论现实主义的概念以及它的源流,没什么意思,应该直接地讲:现实主义在中国是什么状态。我们不要讲它是怎么来怎么去的,那是另外一个话题。第一,现实主义在当下中国,它是主流创作形态,这是一个事实,为什么是这么个事实我们先不说了,不管是官方的倡导还是作家自觉的选择,总之它是一个主流形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就讲现实主义的基本价值,就是真理承诺。真理承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作者要告诉人们生活是怎么样的,什么生活是应该的,什么生活是不应该的,历史是什么样的,什么才是历史的本质,什么是历史的假象。要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生活,同时用这种真实的生活去感染人,教化人,引导人,用真理承诺去告诉人们生活的道理,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基本功能。现实主义不是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所谓的艺术形式,也是为了加强它的功能,而不是相反,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就讲现实主义它有一个艺术上的原则,就是仿真性,你写这个东西呢,你要写出比较符合我们的经验状态中的生活来,比如说《红楼梦》,就是属于经验状态的,那《西游记》就不是。就是要求按照生活的逻辑去写生活,写得像生活,不是说不可以虚构,但要虚构出日常经验生活的这种状态来。然后再加上一个什么东西呢,恩格斯所说的,就是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要以点带面,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生活状态,折射出种整体性的时代本质来,前提就是要真实,所谓的真实,当然是指仿真性意义上的真实,因为文艺作品本质上还是虚构的。我说这三点,目前都在面临挑战。第一个,现实主义作为主流创作形态,这个认识受到挑战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可以实现文艺作品的功能,很难说将其定于一尊了。第二个,我觉得所谓的真理承诺,也受到考验,现在我们的文艺作品,很大一部分功能不是让人去受教育,去读生活的教科书,而是当做生活的调剂品、娱乐品,是这样去看待文艺生活的,很多很多的人在进行阅读的时候,是把娱乐性、消遣性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上来诉求的,而那种受教化的功能诉求减弱了。第三个,现实主义作品的仿真性,它也受到了很大的挑战。比如说现在有很多抗日剧,从大的方面看好像也是仿真的,但是裤裆里掏雷啊什么的,显然并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它有点传奇性,但是总体上感觉在真真假假中间,还是以真为主。总而言之,现在说现实主义,就会遇到很大的尴尬,这三点都受到挑战。原因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把文艺创作当作产业了,一旦产业化,它的逻辑马上就变了。如果我们把它当事业的话,脑子里就会坚持一个指导作用和揭示作用,现在变成产业,等于是读者和创作者之间是甲方和乙方的关系,一种契约关系,中心地位没有了。包括对真理承诺的看法,也并不是说真理只有一个,真理的相对性加强了,而真理的绝对性减弱了,所以你的真理承诺,大概只能承诺一个有限的真理,是不是?真理性的东西,其普遍性、唯一性,大大的削弱了。而契约性强化了,对真理的看法,也要得到对方的认可才行。于是现实主义本体的那些东西,就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这就导致现实主义很尴尬,通常的情况就是,你要是坚守现实主义,那你就全靠领导的支持,领导下行政命令买书、订报、包场,然后领导给你评奖,用这种办法去支撑现实主义。这当然不是现实主义的长久之计。我说现实主义要突围,要靠自己来救自己。第一个,我认为,就是调整观念,现实主义在今后的创作中间,不应成为唯一的创作现象,甚至也不一定非得自认是主流。人们用不是现实主义的方法、态度创作,我没意见,是吧?但是我如果愿意拥抱现实主义,那我就要用现实主义的创作魅力去吸引人,我不是唯一,但我终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百花齐放,我是一朵花,而且我这朵花有人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怎么解决呢?就是这种真理承诺,我认为我们也要考虑。就是说,可能需要放弃那种对于真理的唯一性、普遍性、绝对性的看法,承认多元真理、局部真理、相对真理的存在。你只是写你看到的生活,中间的那种所谓的道理的确定性,不要把它放大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程度,在这个前提下缔结与受众的契约关系,我认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谈到第三点,就是说这种仿真性。我们怎么样吸纳很多很多的的民间元素,调动受众喜闻乐见的手段,让他具有真实感。于是我就拿出我这个《骡子和金子》的文本。这个《骡子和金子》,从它后面产生的社会效果来讲,起码可以说比传统的一些文本更受到读者的欢迎。我就讲我在这里面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手段,我向江湖靠拢,向底层靠拢,向老百姓的心态靠拢,就是找出了老百姓喜欢一些什么。比如说传奇,说悬念。悬念的话,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吸引读者的东西。而生活中处处是悬念,它是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我就以悬念为核心来结构我的故事。这是可信的,也是仿真的,这里面还有一些巧合、传奇等等的元素。我找到了这样一些元素,它既符合现实主义的规矩,也符合我们现在大众的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能会超出一些传统认为的现实主义的范围,但是如果你拿捏那个度拿捏得好,它就不犯现实主义的规。后来一位解放军政治部的文艺局局长,叫汪成德,他就说我们有些题材很真的东西,却感觉很假,而你这个东西一看就知道是编的,但是却觉得很真。他这个说法大家也可以体会。我在这个文本里面,主要就是在一些技术上,在一些形态上,观众心理上,还有一个,就是从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学手法中间,找到一些行之有效,一些经久不衰的招数。把这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比较好的效果。所以我认为,当然我不能说我这个东西就是现实主义了,但是应该给现实主义创作起到一定的启迪作用,或者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一种可能性。
现实主义的各种可能
谭:听你们俩刚才所讲,关于现实主义,总的来说,就是说传统的、本体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概念,受到了挑战,《骡子和金子》,是因应这种挑战所产生的这么一种具有探索意义的、新的文本,而这种探索,特别在当下这个处在各种变化之中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一定的趋势性、启示性的作用。从理论上对这一新的经验进行总结、概括,其实涉及到与文化自信有关的问题。大概是这个意思。
首先,我觉得罗宏对现实主义问题总结的三个要点,很有意思。
罗:我不是讲现实主义的源流、演化,我是讲在中国的现实主义。
谭:中国的现实主义,我觉得有些地方可以讨论。比如说在当代中国,或者说整个社会主义中国吧,现实主义是不是主流创作形态。当然从主流意识形态,从官方文件上看,我同意你的看法,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进入到实际情形上看,我觉得里面的问题还非常复杂,许多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理论关键,到现在都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比如说,我们建国以来对各种标榜为现实主义的文艺观念,批判是不断的,而不管是批判者还是被批判者,都同样标榜为现实主义。我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从感觉上一直认为现实主义是主流。你比如说文革时候的文艺,那时候现实主义口号应該是叫得很响的,但是八个样板戏,是不是属于现实主义的作品?我从艺术上看,不认为八个样板戏是坏作品,也不认为在现实主义与好作品之间可以划等号,好作品不一定非是现实主义的。八个样板戏,我认为从艺术上看,不失为艺术的精品,但是它并不适用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论来讨论,当时的说法,是声称为经过改造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又有说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是这样的。
现实主义概念,应该说它基本上是在十九世纪,在工业化,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散文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然后到了别车杜那里,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就已经非常成熟了。后面经过普列汉诺夫、卢卡契等等,进一步把它完善。到我们红色中国以后,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就产生了。但是这里面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具体地说,胡风这一派的现实主义,它跟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形成的,后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其实冲突得非常厉害,后来甚至演变成了很大的政治事件。胡风的现实主义,是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于原始的、本体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他的理论的体系性、学术性,相对比较强,包括后面“向着真实”这一类的发展,都是他这套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的结果,并且与十九世纪那种批判现实主义,写真实的这一类概念,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延安文艺座谈会所形成的理论,它的实用性比较强,特别强调的是功能性,它首先要求的是对现实发生作用,而且是很明显很快的作用。延安当时因为它是战争时期的文艺,像街头剧一样,要的是对革命有利的效果,是不是?所以首先从功能的角度来要求它。它不像胡风的那一套,是有很具体的方法论为基础,并且是与传统的本体的现实主义理论相联系的。方法论跟功能没关系,功能就是达到一个目的,所以当时特别强调为工农兵群众喜闻乐见,这些都是从功能的角度来考虑的。所以你讲到在中国的现实主义,我想至少也存在两种现实主义的概念,一种是从方法论出发的现实主义,一种是从功能性出发的现实主义。应该说,这两种在中国的文艺实践中都是广泛地存在,但不管是就其内容本身,还是就其为官方意识形态所接受的状况而言,都是有区别,甚至有冲突的,不能笼统地说现实主义是主流创作形态。
另外还要说到一种现实主义概念,就是想要调和以上说到的两种现实主义,抹平其中的矛盾、冲突的地方,这就是也曾遭到批判的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这种理论,是把现实主义看成一种总的精神,一种原则、态度,而不去管具体的观念、方法的区别。这其实也并不是完全中国特色的,法国的罗兰·迦洛蒂的“无边的现实主义”观点,就是这样的。罗兰·迦洛蒂的现实主义观,实际上是现实主义理论进入二十世纪,面对现代派文艺的挑战,所作出的调整。他就是要把毕加索、卡夫卡这样公认的大师,统括到现实主义中来。卡夫卡说“文学是现实生活的避难所”,但迦洛蒂认为他也是现实主义的。
我1988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论文,就叫《现实主义是一种自信》,所以接到你这个题目,“现实主义与文化自信”的时候,我觉得很是亲切。当时参加全国文艺理论学会的年会,这篇论文收进到年会的论文集里了。我主要就是从某种精神、原则、态度的角度,来理解现实主义的概念的,我把这种精神、原则、态度,概括为“自信”。主要观点,大致就是你刚才说到的第二点,就是现实主义承诺给读者提供真理,那是何等的自信,是不是?这具体的讲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在人和自然的关系当中,人的自信。现实主义相信人类是主体,人类是中心,人能够认识自然并且改造自然,这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哲学思维。这个就是马克思讲的主观能动性,人是万物之灵长,莎士比亚是马克思最欣赏的,这就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的态度。现实主义要提供时代精神,人相信自己能够把握住时代精神的脉搏。当然再具体地说,实际上还有一个方法论和功能论的区别的问题,否则的话席勒化也是现实主义,就不需要强调莎士比亚化了,是不是?但我没有细致地涉及这些更复杂的问题,只从态度上讲,所以大体这篇论文的意思还是属于“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在人和人的关系中,在人类社会内部,在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中,文艺的自信。现实主义认为我提供的文艺作品,它能够改造生活,参与生活,介入生活,就是说我的作品能够使生活变得更好,不管你是批判的也好,你歌颂的也好,你塑造美,让人们向真善美的生活看齐,是吧。它就是真正认为文艺作品能掌握善,掌握真,掌握美,然后提供给读者。就是这样。我当时说现实主义有很多人讨论,它有很多很具体的世界观,方法论,但是我觉得在这些之外它有一个总体的精神,就是认为人有能力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认为文艺作品有能力来使生活变得更美好,这个就是现实主义的基本态度。到现在已经快三十年了,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现实主义的概念,并不过时。这既带有一点方法论现实主义的因素,跟传统的、本体现实主义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另外它也强调功能的角度,是一种调和派、折中派。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包括全世界的现实主义理论,在对现实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上,一直都在不断的争论当中,到现在都没有定论。从无边的现实主义,或者现实主义广阔道路的说法看,那就是卡夫卡都算现实主义,因为它是从现实生活当中产生的,反映现实生活并且最终要对现实生活产生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现实主义,那就几乎没有一部好的文艺作品不是现实主义的。当然也许作者的目的不是对现实生活发生作用,但是如果这个作品产生了影响,它一定会对现实生活发生作用。对现实生活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就是只从文本本身的内容来看,比如说你这个《骡子和金子》,一定对现实生活发生了作用,它不可能对长征发生作用,但是他对受长征影响的人以及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发生了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是属于无边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那不是一条道路,很多很多道路都可以通向现实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八个样板戏也可以说是属于那种无边的现实主义。它里边的内容,编造很明显,人物高大全,但是如果这个作品最后能够成立的话,我觉得它还是遵循一定的生活逻辑的,可能它的编造比较偏重于审美的逻辑,政治的逻辑,但是它还是有生活逻辑的基础。我觉得从无边的现实主义或者说现实主义广阔道路的角度来讲,它与“向着真实”的这种提法,那有区别。这就涉及到你讲的仿真性。从功能的角度来讲,传统现实主义强调的具体性、形象化,也许并不是唯一的,它就不排除一种抽象的真实性。就是亚里士多德讲的,他对真实有一个定义,他用效果来讲,用心理效果来讲,真实就是相信。文艺作品一定是虚构的,不可能是真正的真实,你去判断它的时候,建立在对真实的一种经验把握的基础上,对吧。所以真实性一定是仿真性,它不可能是真实本身。所以亚里士多德关于真实的提法,我们可以称之为真实的幻觉。要给你的文艺作品营造一个环境、气氛,让整体的真实感立起来。所以传统现实主义理论讲典型人物以外,还要讲典型环境,营造整个的真实的环境,真实的气氛。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峰,就是在这方面最高明的,他是不厌其烦的从现象到本质,从局部到整体,把那种整个的真实感,真实的气氛营造出来了。但是,这种具体的、形象的方法,我想并不是唯一的,比如样板戏,他用舞美、灯光、舞台调度等等综合性的手段,以及与内容相配合的意识形态宣传,让观众相信舞台上表现的东西是真实的,这种以阶级斗争为基本哲学的对现实的认识,指向的大概只能说是一种抽象的真实,但也许也并不违反现实主义所强调的仿真性。据说当时《白毛女》上演的时候,有观众中的战士举枪要向舞台上的黄世仁射击,可见其在营造真实的幻觉这一点上,是挺成功的。
罗:这里我先插一下,就是我写东西,对于你说的“真实的幻觉”,我喜欢造成它所谓的质感。故事嘛肯定是编造的,但是我就把它放在历史的框架上,使这故事有质感。那什么叫历史框架呢,它有一个技术,比如现在有很多作家、编剧,他写抗日战争,他写日本人是坏人,中国人是好人,他就觉得真实了。但是具体地写,比如写大扫荡,日本人为什么扫荡,扫荡的背景是五一大扫荡呢,还是别的什么,他不计较这个东西,然后就一味地打。我基本上是这样:这次扫荡,它是平原的扫荡,还是山区的什么扫荡,这个扫荡的指挥官是谁,部队番号是什么,打的时候,和他发生接触战的是谁,是120师还是135师,是林彪的部队还是贺龙的部队,我觉得有必要说清楚。而我们现在好多抗日剧,开打的是哪个部队,他不讲究。我就比较讲究这样的东西,我认为做仿真感,营造真实的气氛嘛,必须要有历史的框架在。再比如说我最近写的一个小说涉及朝鲜战场上的一次谍战。为什么出现谍战?就是因为谈判陷入僵局,陷入僵局的时候,李承晚和美国人,想的不一样。李承晚是希望打,美国人希望谈,于是李承晚希望把这个事情搅大,让美国谈不成,谈不成就打。于是志愿军的部队,针对的间谍就应该是李承晚派出的间谍,而不应该是美国的间谍。我们很多人是不会编的,他就说是美国派来间谍,要暗杀李克农。那我说是,暗杀李克农,把他干掉了,谈判就谈不下去了,就只能打了。但这个绝对不能是美国远东情报局干的活,一定是李承晚干的活,我把我的故事放在这个历史框架里面去编,就有特殊的质感,好多人不讲这个。
谭:你说的这个,可以把仿真性这一块的讨论,引向深入。刚才陈实讲到,罗宏没有经历过长征,但《骡子和金子》,大家觉得很真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就我所知道的,比如我们广东的作曲家刘长安写的一首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这么传唱经久,具有无限魅力,而且真实到令人神往的,对于海南岛风物的塑造,大概许多人都想不到:刘长安当时根本就没去过海南岛。谈现实主义,这可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跟真实性相关的,亲历性的问题。我以前与人讨论文化散文。写散文,大多数都是讲真情实感的,对不对?散文最基本的要素,就是真情实感,但是历史散文、文化散文,大家都没经历过历史,作者的真情实感从哪里来?所以我讲亲历性,有一种可以称之为感受的亲历性,就是你的感受是真实的。那么你的这个感受的真实性从哪里来呢?你是真正进入了那个真实的历史氛围,你在读历史资料的时候,或者你在历史古迹面前的时候,其实是把自己代入到了那个历史资料、古迹所代表的环境里面,这种感受是亲历的。我想刘长安写《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的时候,一定是把自己代入到了海南岛的山水环境里了,这样他才能想象出五指山万泉河的形象,并表现出其中的热爱。谈现实主义,特别是谈主旋律这一类“主题先行”的创作的时候,我认为“感受的亲历性”,这一从一般的真实性概念中分离出来的、更为深入一点的认识,很重要。所谓“想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只有自己亲口尝一尝”,记得读书的时候我们讨论现实主义,有人说:那陀思妥耶夫斯基写杀人犯,他必须要自己去杀人吗?感受的亲历性,某种代入式的亲历,可以解决这一疑问。
陈:这是怎么搞好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些技术活,我更关心的,就是你们刚才发言所及现实主义的各种可能性的问题。比如你说胡风式的现实主义和其他的现实主义,包括和延安的现实主义,它是不一样的。其实胡风也好,延安文艺座谈会也好,它们都不是卢卡契的现实主义,实际上都还是以日丹诺夫这一类为主的。真正来讲的话,相比胡风,延安文艺座谈会里的东西,更多地把中国本土的许多成分加了进去,可以算是中国的现实主义。另外它在当时的文艺界看来,具有不少新的思想、新的发现,让人眼前一亮。至少有一点,延安和西安比,它的文艺观是不一样的,它是有新的东西在里边的。你比如说国统区的新生活运动,比较提倡风花雪月,那是从周作人就开始了。这种闲适文学,也是现实生活,而毛泽东那个时候强调的就是劳动大众的生活,而且是革命的生活,而且是抗战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新生活。所以我觉得现实主义至少有三种区别。第一是有不同时代的现实主义,你比如说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那种现实主义,和十九世纪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肯定是不一样的,到苏联那时代,《静静的顿河》,又跟十九世纪的那个不一样了。这里有个时代的差别。所以我们真正应该讨论的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现实主义,这是一个。第二个区别是什么呢?中国的现实主义和外国的现实主义,它也是有差别的。包括浪漫主义,你比如说我们中国一讲浪漫主义,就是《西游记》,是不是?这种东西和雨果式的浪漫主义是两码事。所以中国式的现实主义和外国式的现实主义,我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中国的现实主义,我认为基本上应该就是《诗经》的传统,风雅颂的现实主义。第三个呢,还有一个生活的现实主义和心理的现实主义的差别,的确是有差别的。比如刚刚讲的“感受的亲历性”的问题,似乎也与此有关。所以我说,纯粹的从理论上去讨论,不是我们现在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真正所要解决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什么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现实主义。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现实主义和延安时期的现实主义一样不一样,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中间经历了那么多的讨论、争论,甚至批判、斗争,真正收获的可以上升为现实主义理论的成果少之又少。我觉得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分歧,之所以到现在还这么争论不休,就是因为理论界没有对这个现实主义下一个大家相对认可的定义,有一些基本的理論问题没有解决。
谭:具体一点说,比如现实主义和主旋律的问题,现实主义和生活阴暗面的问题,就是歌颂与暴露的问题,这些都困扰了几十年,但到现在都还没有真正解决。
陈:理论上没有解决。往往是一出现大的争论,就用行政命令给压了下去。这样争论是平息了,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本应产生的理论收获一点也没有。我们的理论很滞后,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应该骂读书人偷懒的。傅斯年1949年到台湾之前,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失败不在于什么别的东西,就是读书人太懒,不读书。理论家们太懒,在新的理论上缺少敏感性,这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以你看习近平想把文艺搞好,但理论界来来去去提不出好的东西。
谭:比如刚才提到的现实主义和生活阴暗面的问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曾经有人写过一篇文章《歌德与缺德》,反对写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后来到电影《人到中年》出来,又有人以其揭露了阴暗面而反对给予授奖,就使这问题的争论更趋激烈了。就此王元化写了一篇长文:《论知性的分析方法》,这其实是对此一问题的极有价值的理论收获了。可是没有人对此进行梳理、总结,形成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系统表述。后来《人到中年》得奖了,要不要和能不能揭露阴暗面的问题也不争了。但问题并不是王元化的文章解决的,而是有关方面打电话、发通知来解决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