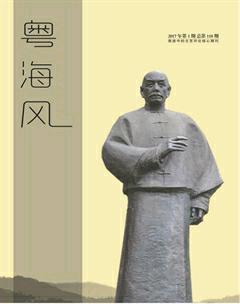人可貌相
苏福忠
1
听说秦颖积攒了许多名人的照片,要配上文字结集出版,我便成了一个远方的推手,不失时机地催问。因此,他的书的出版过程,我知道得比较清楚,连《貌相集》这个书名,他都极早告知我了。书终于出版后,秦颖等样书心焦,就在网上购买了几本,先给我寄来一本,也算是聊解我的心焦了。全书收集了四十五个人的貌相,我先把书目浏览一下,发现其中十二个人是我熟悉或者相当熟悉的,十八个人是通过文章或者电视节目知道的,剩下的十五个人是全然陌生的。相片的好处有点类似见面如见人,端详一番照片,陌生人也就成了熟人了。一本书可以让你不出家门就认识几十个社会名人,谁还会拒绝读它呢?这还只是相对读者而言。对那些自己的照片永远被收藏在一本书里而得长存的人而言,用亚当·斯密的话说,就是到了“所有的人都渴望能够一睹尊颜”的份儿上了。然而,对于摄影迷秦颖而言,按他们湖南的一句谚语说,我以为,这是一次“草鞋没样边打边像”的尝试。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拥有“一架凤凰205”,到今天的《貌相集》,从胶片到数码,记录的是他一个有心人的锲而不舍。我想,他一开始玩相机就是有些心胸的。他拥有凤凰的时候,我也拥有了一台华夏,但我只是给孩子和妻子照相,我想留下的只是孩子成长的迹象和生命的年轮。秦颖不同,他走出了家庭,抱定“我的视角、我的想法”,加之兴趣和爱好的驱使,去和陌生人打交道,去捕捉“最有创造力的一群人”的相貌。从秦颖谦谦君子的性格看,他需要克服相当的障碍,拿出加倍的勇气。我目睹过他给牛汉、绿云和高健拍摄,他一边抓拍,一边像被什么东西拉扯着,总带着一些犹疑。记得给高健先生拍照后,回到旅馆我忍不住跟他说:“秦颖,你拍照片子很辛苦,总怕麻烦别人。”
他笑笑说:“是的。也有好的一面,我会更加冷静地观察对象。”
2
秦颖是学历史的,影像只是表层,他的专业要求他往深层走去,他服从了专业。这是他的幸运,更是他的眼光。比如他选定了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可以深入历史,“分子”可以研究问题。他可以从貌相入手,琢磨相貌下的真人。多么可取的关系,多么犀利的角度。于是,就有了每个相貌下的文字。一般说来,一本摄影集,照片下的文字无非是时间、地点、和谁在一起等等;在这点上,摄影迷秦颖交代的文字有限却实话实说,指出了数帧他的得意之作。在我看来,他的说明还挺到位。可贵的是他不满足于摄影迷,他要通过相貌,成为作者。在写作相貌们的传记上,秦颖似乎也遵循了“草鞋没样边打边像”的法子。这法子不土,是伟人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另一种实践。首先是他有心,每次给相貌们摄了相貌,他必会写下一些会面的记录。《貌相集》一书中的许多文章,都能看到他那些现场感很强的笔记,如“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还是清,但没有那么清了。”又如“你的境界高,你追求的是大我,可追求大我的人都不是人”,又如“现在大家对一些普通的道理都糊涂得很。”等等。
阅读秦颖的零散笔记变身为成篇的文章,我感觉他是循序渐进地有了主观色彩、有了自己的看法、有了自己的选择的。在这点上,秦颖所遵循的还是他一贯的谦谦君子之风,分明有他自己的观点和选择的倾向,他却利用开列提纲和提问的方式,让传主亲口说出来,这招很厉害,又实用又巧妙。其实,他拍摄下的大量相貌,我以为,都是这一大妙招的显性表达。秦颖在快递书时打来一个电话,希望我看过书有所感的话,写一个书评。我没有丝毫犹豫便一口答应了。岂知《貌相集》翻阅过几遍,怎么都写不出一个满意的开头,更别说长篇幅的文字;直到我又一次翻看到王养冲先生的相貌并凝视过后,写作点一下子丰富了,笔下流利起来。关于这帧貌相,秦颖说:“这目光、这眼神一以贯之,坚韧、自信、沉着。”有了这个标杆,我再次翻阅《貌相集》,认真辨认一个个貌相,不管生人还是熟人,最后发现让我感到一下子成了老熟人的却分别是王元化、王养冲、李普、严秀、张思之、何兆武、何满子、陈乐民、周有光、杨宪益、贾植芳和黄裳等十几位,几乎全都是我不认识或不太熟悉的。他们的貌相的眼光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沉静,专注,自我。想来不可思议,其实,这里与我和知识分子的交往有些关系。
大學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个名叫国家版本图书馆的地方。这里新成立了一个编译室,除了我们新分配来的十几个“小年轻”,其余三十多个老人,都是有“政治问题”的“地富反坏右”,是原单位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后重建红彤彤的新出版社,拒绝他们回去的。猛地和一群老知识分子在一起工作,他们有知识,我们只学了三年半英语,尊敬油然而生是情理之中的。我觉得应该像在学校里一样,叫他们老师才得体,可事无巨细的领导告诉我们,叫老某就行。我们起步做翻译,生词多得招架不住,把生词查明白了,连起来的意思又弄不大明白,请教老某们就是情理之中了。但是,领导会很策略地告诉我:你们可不是只搞业务,还有政治任务呢。我很晚才知道所谓政治任务就是要我们掺沙子,第一次感受到距离权力中心越近,人身越容易受到播弄,所谓皇宫着火殃及鱼池也。那是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时不时组织我们去清华和北大参观大字报,回来进行政治学习,成了常态。奇怪的是,尽管政治气候黑压压,但是几乎每个老同志却都在邀请我们去他们家看看,而且还有接二连三邀请的。一个叫冯金辛的老同志家只有老两口,女儿去插队,换煤气有困难,接二连三地要我去帮忙换煤气。干了这点活儿,他们老俩一定要请我吃他们亲手包的馄饨。其实,人与人的关系最容易通过具体的事情建立牢固。好像第二次,记不得什么话题引起的,我后来一直称之为“老冯”的,突然很动情地跟我说:
“小苏啊,你不知道每次搞运动,我们有多么害怕。不管你怎么表现,你都是一个旧知识分子,总有新知识分子在帮助你,斗争你。那是真难受啊,因为你怎么都说不清楚你为什么给旧政权干事;这次你说清楚了,下次你还是没有说清楚……。”除了特殊场合,平常和人说话,我是不习惯观察对方的,但这次我定定地看了老冯半天。他消瘦的脸,短发向上立着,脖子前倾,后背微微弓起,两眼直视着我,一脸的真诚,好像在说:我已是这样一个人,怎么办呢?后来我们都分回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他是出版社老职工,可据我观察,他并没有回归的高兴,见谁都是点头哈腰的客气。有一次我跟我以为有些头脑可以交流的老王说起我这种感觉,他竟然这样回答我:
“嗨,他们呀,没法说。那时开批斗会,两个人最有意思:一个萧乾,最喜欢打小报告;一个绿云,最爱给自己上纲上线,我们都跟不上。嘻嘻嘻——”
老王比老冯小二十来岁,大约上世纪三十年代中生人,学俄语的,口碑不错,可这话完全牛头不对马嘴,让我费解了好一阵子。我当时正在看杨绛的《洗澡》,看到解放后的新知识分子帮助老知识分子洗澡的文字,我意识到新旧知识分子很早就形成了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了。我对老冯的为人处世以及老王信口而出的话感到好奇,那是因为我是七十年代末才闯进了知识分子堆儿里,对他们几十年来明里暗里的积怨一点不了解。因此,新老知识分子的是非问题,至今仍是我的一个命题。秦颖笔下,王养冲先生一生诸多不顺,却精神不倒,还能说出“他著作等身,而我连等鞋也等不了”这样心酸却幽默的话;而我的老同事冯金辛,却唯唯诺诺,再难挺直身板了。但是,在我看来,在他们沧桑的脸上,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无奈。大约上世纪末八十年代中,我就职的出版社分了几次房子,其中小范围的一次,我被推选到了分房委员会;因为做通了几个闹情绪的老职工的搬迁工作,居然委托我出台一个分配方案,得到领导认可,一手解决那次的分房问题。说来有趣,也算想帮帮老冯吧,辗转腾挪一番,终于给他分了一套楼房,厨房厕所都配套,生活方便多了。辗转腾挪的条件是他必须把他原来的两间住房腾出来,但他搬进新分的住房后,让自己的女儿住进旧房,耍了一个赖。这种事情在各单位的分房过程时有发生,但是谁都没有想到老冯这样一个唯唯诺诺的老人,会来这一手。我被搞得十分被动,一开始十分恼火,但转念一想,像老冯这样受了一辈子冷眼的老派知识分子,耍这点赖恐怕也是最后的稻草,他还能怎么样呢?总不会像会闹的人找领导闹,坐在人家沙发上不走,撒尿也在沙发上解决吧?我学老冯,和头头们也耍點赖,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公家就是大家的意思,全看谁的手伸的长,谁就多拿罢了。老冯毕竟是老实人,后来总是躲着我,我们延续了十多年的交情也就渐渐地淡化了。
然而,这事常在我心头萦绕,感觉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新时期以来首先应该弄清楚改造与被改造的恶果,也就是所谓新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的是与非;因为这种自古以来不曾有过的分裂知识分子的做法,使得新老知识分子都发生了严重的性格裂变,而且只往坏处变不往好处变。所谓旧知识分子多数都还有自己的道德底线,所谓新知识分子则很少知道自己的道德底线在哪里了;如果没有从内心的认识和忏悔,所谓新知识分子是不能称其为知识分子的。
3
在秦颖的《貌相集》里,他选择的人物,没有可以和新知识分子对上号的;从年代生人上看,三十年代出生的人,尤其一九三五年之后,如果大学毕业,正好赶上新时期就业,就成了所谓的新中国的大学生,一般说来都成了改造人的人。自己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因为跟着时代的政治气候而变,到后来都变得不伦不类了。《貌相集》里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是“地富反坏右”之类,如朱正先生,作者所写都是他的苦难以及受难之后的作为:“他(朱正)经历的磨难常人难以想象,这张照片表现出了他为什么能走过来的性格特点。”朱正先生貌相下的文字是全书中最长的篇什之一,内容基本上是朱正先生所受不公正待遇的重点记述以及他的性格与为人,像周有光、何兆武、杨宪益、黄裳那样开口就有观点的话语却不多见,至少不鲜明。当然,例外也是有的,例如邵燕祥,从自己的苦难和不公正待遇出发,往往能有个性鲜明的话。所以,我感觉,写苦难,应该是受苦受难的人自己写,别人写来只是片段或者角度,写长了就成了故事了。更要紧的是,由自己的苦难引发的思考,与从国难引发的思考,无论深度和长度都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在《随笔》上读到过邵燕祥先生的一篇文章,由别人的经历而感慨道:如果我没有被打成右派,照我这种性格,上蹿下跳整别人,是难免的。这种深刻,只能由当事人自己说,属于一种反省。
不知道秦颖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把最长和比较长的篇幅,都慷慨地赐予年龄更长的人,比如说《貌相集》最长的一篇是写中国文字改革泰斗周有光老先生的。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文字,读者看到的不只是传主一辈子超强的工作效率和独一无二的贡献、豁达平和的性格和不屈不挠的坚守,更有他窥探世界和社会的纵深视野和自由思想。这篇似乎是作者唯一事先提出访谈提纲的文字,因此作者记录下来的内容准确而多面,例如这样珍贵的文字:
苏联的教育制度应当说是错误的,我们目前已经改变不少了,但是还是没有完全脱离它的影响,这是我们教育改革中必须要做的工作。
他们完全不了解地主不完全是剥削农民啊,地主是农业生产的组织者、投资者、设计者、指导者、管理者,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动力。
三民主义在当时被认为是非常进步的原理,日本也学了这两个原理(即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把它们订在宪法里面。美国人一看,不行,这两个原理美国都否定了。日本人不能理解啊:三民主义是进步的东西,我们学三民主义为什么是错误的呢?美国说三民主义早已过时了。平均地权,就是将土地平均分配嘛,分成一块块的,农业就完了。美国是鼓励土地合并的,要大农业、机械化、科学化。美国鼓励大资本吃掉小资本,这样才能有力量来发展新的技术。这个故事中国人很少知道。
“一百零八岁的生日,多么充实啊。”秦颖感叹道。我以为,周老先生不只是因高龄而充实,更是因高龄而积累了独到的见识;还有青少年时形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能够坚守一辈子,内心超常的强大。掐指算来,老先生生于一九零五年。这个生年比民国诞生还早了几年,在这乱世里形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肯定不会是任何主流意识形态灌输和洗脑的结果。国家不幸诗人幸。周老先生对中华民族可以居高临下地审视、观察、思考,得出难能可贵的结论,令今人望尘莫及。
另一篇长文则是写何兆武先生的,文中的细节最多,也最生动,如家常聊天,所聊的内容却事关大是大非:
我翻译的古希腊哲学,那时资本主义还没有出现呢,怎么就给资本主义招魂了呢!当然没有理由可讲。招魂就招魂呗,我也没有争辩。被关进了牛棚,好在牛棚里的‘反革命分子很多,一点都不寂寞。呵呵!
问题并不在于某个学校出了几个诺贝尔奖(或者其他什么奖)的得主,而在于它是否能培养出一批人才,能否开创并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学风。
秦颖2014年去拜访何老先生,我随他而去,因为我已读过何老口述的《上学记》,认定是新时期以来为数不多的鼎鼎好书之一,自然有心看望一下传主了。何老说他“九十三岁了,已经不写东西,只看看闲书。”我这厢一算,老先生是一九二一年生人。我在他的《上学记》里读到:“一个人的性格或者思想大多初步觉醒于十二三岁,到十四五岁思想定型,形成比较成熟、确定的人生观、世界观,此后或许能有纵深的发展或者细节上的改变,若是有本质的改变,我想是非常罕见的。”我很想和老先生请教这个说法,连带听听老先生的思想成熟过程,但终未敢造次。在这点上,我远不如秦颖有韧性。不过,想到何老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前已经是一个求知上进的青年,人生观和世界观应该很成熟了。美国的十九世纪的思想家亨利戴维·梭罗说过:人是很难改变的,但却必须改变。何老先生说“这一辈子都在打杂”,是他的“必须改变”的具体表现,但是何兆武这个“人是很难改变的”了,否则他口述不出来《上学记》这样顶尖的好书。仔细阅读秦颖的这些长文,作者记录得详细固然重要,但传主有话说似乎更重要,因为传主要做到有话说,他必须有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做支撑才有底气,才能滔滔不绝而掷地有声。靠别人灌输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多会儿说话都是鹦鹉学舌,其实自己并不真正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4
有的貌相的文字不长,但是秦颖的笔记很密,比如写黄裳先生的,基本上以他的笔记为线索而写成,而且还多是关于《随笔》杂志怎么办得更好而发表的看法。有看法就有做法。我在《随笔》上看过黄裳先生的一篇文章,那才叫精彩。他写一个在当下很张扬很牛气却不过一个糠心柴萝卜的所谓学术带头人,年纪不算老却摆臭架子,在一次聚会前迟迟不露面,让别人干等着,待到他露面时老远就嚷嚷: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让什么什么事情绊住了,等等,等等。黄老先生用如此简单的情节让读者看见一个浅薄之人,可见笔端的功夫修炼之深。有人说这样的老先生個性很足,其实这是他们的人生观很足。个性只能在个人身上表现,用来看穿别人的形状,则难免一孔之见;但是你有了一个很足的人生观,别人的一举一动就难逃你的眼界了。
有时候,秦颖又能把摄影迷和记录者两重身份不偏不倚地都担负起来。张思之先生的貌相“从容而自然,沉静的眼神里有一种力量”,但是比起秦颖记录下来的话,我倒觉得张思之先生的眼神只有沉静:沉静到冷静,冷静到思考,思考到语出惊人:
自由的基础一定是个人的利益,东海西海同心同理。
仅是思考出这样一句话,张思之先生就没有白活一辈子,然而这样的话如今恐怕多数人都听不懂啰。随便一提的是,我在小书《文革的起源——公有制启示录》的前言里说:“至于民主和自由,没有私有制,一切都谈不上,因为‘民主和自由这样的概念,是私有制的意识形态。”几位朋友看了这样的话,纷纷责问我:“这叫什么话?”有责问还算好的,更多的人已经麻痹到根本就注意不到这样的话。小书是在台湾出版的,我纳闷台湾的出版商也是棒槌一个,因为我的书名本是《我的父老乡亲——公有制启示录》,他非要改成《文革的起源》,否则书卖不了!一个政治,一个商业,把人类逼到了很难转身的窄道上,令个体十分无奈。
5
秦颖是幸运的,赶上了时代相对开放的时代,否则他的这个爱好完全会被人家用“假公济私”的帽子给打压下去。《貌相集》里很多篇章都告诉我们,《随笔》带动了影像,影像促进了《随笔》,是双赢的举措。这点在关于王元化先生的文字里,最能感受到。关于王元化先生貌相的文字,大概是作者兼摄影者的秦颖写下的最多的,约一百多个字,而当时的主编秦颖则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乃至一直持续到世纪末的思想启蒙,王元化是不能绕过的人物”,便“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请他再为我们写稿”;文中王元化先生关于《随笔》所见,几乎贯穿了全篇,又因为《随笔》是思想性很强的杂志,作者特意地录用了《王元化谈话录》的一段话:
人的认识是一种真实的反映论吗?我怀疑。我觉得人类认识,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这是我最根本的一个命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启蒙学派,把他认识到的就认为是一个绝对真理,他认为就是他掌握了。他一旦掌握了绝对真理,他就非常大胆和独断,因为他不是为了个人的一个东西,他是为了真理,做出很残暴的事情。
一本书靠什么流传?靠它传达的内容和特色。《貌相集》的特色是照片,而这样的文字是它的命脉,图文并举,注定可以收藏和长存了。
6
秦颖的编辑生涯发轫于家乡长沙,关于上世纪八十年湖南出版业的辉煌,他也记下来珍贵的文字。
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每天晚上不熬到深夜一两点睡不着,于是就尽量给自己找点事做。既然是找事做,就不能讲究那么多条件,只要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行。那时读英国大智若愚的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上瘾,忍不住把他最重要的作品《巴塞特记事》翻译出来,七十多万字,打问了多家出版社无人接手,我写信给湖南人民出版社,很快接到编译室主任唐荫荪的信,让我把稿子立即寄去了。唐荫荪先生和我的所有通信都是用毛笔写成,传统的竖条红格子信笺,毛笔字遒劲有力,给我印象极深,心想哪里藏匿着这样的人才,突然间就在湖南出版界冒了出来,形成了一股一往无前的势头,令我们这些死气沉沉的中央出版社望尘莫及。在接受了拙译的当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就在《光明日报》占用一整版,做新书预告,其中就有拙译。我正惊叹出版界异军突起的湘军来势汹涌澎拜之际,突然听说湖南人民出版社犯事儿了,要被取消!2001年我去湘潭大学参加英国文学年会,回来时去长沙看望老同学,顺便去了却一桩心事,那就是去和唐荫荪先生坐坐。找到湖南出版社,才知道老先生去世几年了。
秦颖是个稳重之人,尽管在朱正、李冰封、钟叔河等貌相里都写到了这件事儿,但下笔客观、叙事不惊的笔调令我钦佩,因为我当时对一个堂堂的人民系列的出版社,说取消就取消,这种小孩子玩家家般的把戏,哪像是一个共和国在建设自己的文化?在京城对此事的热议中,我听说湖南人民出版社之所以被吊销,真实的原因不只是因为出版了《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还因为出版了台湾国民党一个要人的传记。不是色情问题,是政治问题。时过境迁,回头看看,什么色情,什么政治,一切都扯淡,耽误并摧残的只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
然而,摄影迷和作者一身二职的秦颖,我行我素,把他几十年来的摄影积累和笔记积累,经过整理和辛勤的写作,合二为一,固定了一种图文并举的力量,真的值得庆贺。秦颖在快递给我的书中写了短信,说:“做编辑近三十年,平常写东西很少,这次算是集中写作,感觉是上了两个台阶,初步体会了写作的愉悦。”这是一个谦谦君子的真心话,作为长秦颖整整一轮的我,只有高兴的份儿。要说建议呢,既然周有光老仙人说,我们的教育制度照搬了苏联,误入歧途,那么我们这些在新体制下受教育的人,人生观和世界观被搞乱是必然的,需要自觉的深刻的“拨乱反正”也是必然的。我这老朽,谨希望和正当年的秦颖共勉,争取做个明白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