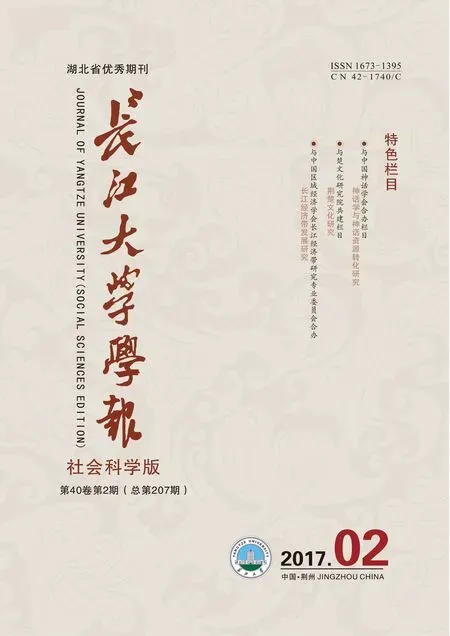《白鹿原》中婚丧民俗的文化内涵及艺术价值
郭海峰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系,安徽 淮北 235000)
《白鹿原》中婚丧民俗的文化内涵及艺术价值
郭海峰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系,安徽 淮北 235000)
《白鹿原》描写了几乎所有主要人物的婚礼或葬礼。这些婚丧民俗描写,不仅为我们呈现了彼时关中人们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女大男小的婚配需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程式,以及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轻死重生的生命意识,同时也推动了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与可读性,强化了小说的地域特色,为小说带来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白鹿原;婚丧民俗;文化内涵;艺术价值
民俗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的较为稳定的文化事项。《白鹿原》中的民俗描写丰富多彩,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主要关注其中有关婚丧习俗的描写。
一、婚嫁民俗
《白鹿原》是在主人公白嘉轩的七次婚姻中拉开序幕的。小说一开始就说:“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1](P3)在小说中,作者先后描写了多人的订婚及婚礼。这些婚俗礼仪,无不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里,婚配双方是否门当户对,是衡量一门亲事是否合适的重要标准。所谓门当户对,指的是男女双方包括各自的家庭,在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等方面不相上下,情况相当。小说中,无论是老一辈如白嘉轩等人的婚姻,还是新一辈如白孝文、黑娃等人的婚姻,都以门当户对为准绳。在介绍白嘉轩前三次所娶的媳妇时,作者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了她们的出身——殷实人家的女儿。在选择儿媳妇时,白嘉轩也恪守了这一准则。描写白嘉轩的长子白孝文的婚礼时,作者一面详细地描写了婚礼中的各种习俗,如新媳妇进祠堂叩拜祖先仪式,一面又始终强调:女方与男方一样,同样出身于殷实人家,这门亲事是门当户对的。此外,白嘉轩之所以没有将冷先生的二女子许给孝文而是许给了孝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受了门当户对思想的影响,因为冷先生的大女子许给了鹿子霖做儿媳,所以,如果他的大儿子娶其二女子,在他看来就是门不当户不对了。门当户对婚姻观支配下的婚姻,已然与情感无关,而只是维护家族尊严,扩大家族势力的重要手段。
白鹿原的传统婚俗,除了要求男女双方门当户对外,还要求女子要比男方大几岁。小说中的白家人丁不旺,为了早得子孙,白家的男人都是很早就结婚了,而他们所选的结婚对象,也都是比自己大几岁的女子。白嘉轩“娶头房媳妇时他刚刚过十六岁生日。那是西原上巩家村大户巩增荣的头生女,比他大两岁”[1](P3)。白孝文的媳妇也比他大三岁。这样的婚配需求无疑是务实的,因为这样的媳妇一进家门后,不仅能洗衣做饭,纺纱织布,侍候公婆,操持家务,且比同龄男子早熟,对男女之事有所了解,能在婚姻中起性启蒙者作用。更重要的是,女大男小的婚姻观背后,折射出了关中人的生殖崇拜观。“这个村子的住户……人口冒不过一千。”[1]62这使得白鹿原上的人们在男女婚配问题上,首要考虑的并非两人是否情投意合,而只是能否传宗接代。正如白嘉轩在娶第七个媳妇时所说:“只要能给我白家传宗接代就行了!”[1](P41)其实,这种繁衍后代的焦虑,早在他娶第五位媳妇时就已经存在。小说中说:“这个女子是一个穷家女子,门不当户不对已经无从顾忌。”[1](P4)由此可见,在白鹿原上人们的婚姻中,一旦涉及到传宗接代这一重大问题时,门当户对的婚姻观便退居其次了。白嘉轩对自己的婚姻是如此要求,为长子白孝文选媳妇也同样出于这一目的:“我想给孝文订娶个大点的闺女。咱屋里急着用人(不便出口的一层意思是早抱孙子)。”[1](P113)正因为这样,在得知三儿媳不能生孩子的事实后,即便这个儿媳妇其他方面做得再好,身为封建家长的白嘉轩也绝难容忍,所以他便有了休掉再娶的打算。
在中国的传统婚俗中,父母与媒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无论缺少了那一项,男女婚姻都可说是无效的,难以获得社会的认可。一桩婚事能否成功,取决于两家父母的意见及媒人在其中的沟通,男女双方在成婚之前基本上很少见过面,更别说交流和相处了。白嘉轩所娶的七个老婆中,只有仙草是他唯一在婚礼前见过面的一个。白鹿原是中国旧社会的缩影。在这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具有绝对的合理性和强制性。老一辈的封建家长如白嘉轩、鹿子霖、冷先生等,都强烈且顽固地维护着这一婚姻习俗。他们眼中的婚姻,只不过是性与孝的结合体。在他们看来,男女双方的结合,很多时候并非出于爱的冲动,而是孝的虔诚,因此,一旦有人违反了这一习俗,便意味着对父母的极大不孝。这自然是他们强烈反对的。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宗法社会里,始终处于权利绝对中心的男性,在两性关系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在这样的背景下,白鹿原上看似喜庆的婚俗背后,实则蕴藏着无数的悲剧。旧时的关中平原,男女之间的婚姻多由包办买卖而成,很多男方家庭会因娶媳妇而倾家荡产。白鹿原上便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女,花轿娶,十个布,半斤礼,银货不全不得娶。买来的媳妇是骡马,任我用来任我打。”在白鹿原,女人只是男人泄欲的工具与生育机器。她们是可以买卖的商品,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小说中的仙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在流言横飞的环境下,仙草冒死嫁给白嘉轩,为他生儿育女,彻底改变了白家几代单传的命运;但即便这样一个为家族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女人,在这个家族中却既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定权,因为在人们看来,她只是完成了她本应承担的传宗接代的分内事而已,谈不上什么伟大,甚至根本不值一提。鹿兆鹏的媳妇冷家大小姐,也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冷家大小姐虽是鹿家明媒正娶的媳妇,但由于鹿兆鹏并不接受她,而只是被三记耳光打着才举行完了婚礼,因此,婚后鹿兆鹏便一走了之,撇下冷小姐一人,任其在传统的贞洁观与现实生活中苦苦挣扎。在欲望与理性的双重折磨下,冷小姐最终得了淫疯病。面对婚姻如此不幸的女儿,冷先生并没有表露出一个父亲应有的关心与爱护,而只是在乎自己的颜面,最终他亲手毒死了自己的女儿。顺从封建礼教的仙草、冷小姐的婚姻,最终都以悲剧收场,反抗者如田小娥的婚姻,则更无法逃脱悲剧命运。田小娥与郭举人的结合,虽然极其病态,但在那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时代里,只要有了明媒正娶这一冠冕堂皇的外衣,人们便会视为理所当然。惟其如此,田小娥即便与黑娃真心相爱,但两人的结合,仍会招致家人及周围人的极力反对,最终无以逃脱悲剧结局。
二、丧葬民俗
除丰富的婚嫁民俗外,《白鹿原》还呈现了众多关中丧葬民俗。这些丧葬民俗,也无不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小说一开始描写的就是主人公白嘉轩的六娶六丧。此后,作者又写到了秉德老汉、仙草、白赵氏、鹿兆海、朱先生等人的一系列葬礼。在众多的葬礼描写中,我们可以发现,与男性死者相比,女性死者的葬礼往往显得十分寒酸。这在死者所用的器物——棺材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在葬礼中,富人家一般会选择柏木或松木做棺材,至不济也会选择楸木,棺材大多板材较厚;而穷人家则因为没钱,多选择杨木做棺材,板材比较薄。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棺材,除了取决于死者的身份地位外,还取决于死者的死因。封建社会的女性地位一向较低,故其死后大多用薄棺材入殓,即便小康人家也不例外。白嘉轩的二房媳妇死时,便是用“一具薄板棺材抬出了这个门楼”[1](P3)。直到埋葬第五房媳妇时,白家才“用杨木板割了一副棺材,穿了五件衣服,前边四个都只穿了三件……年轻女人死亡做到这一步已经算是十分宽厚仁慈了”[1](P12)。这一变化,并非白嘉轩念及夫妻感情,而仅仅只是他对这个女人有一种负罪感。对于他最应该感谢的女人仙草,他并没有任何特殊照顾。临死前的仙草“想见的亲人一个也见不着”[1](P458)。出于对瘟疫的恐惧,仙草死后,白嘉轩不仅没有报丧,而且连仙草的娘家人也不曾告知,只是草草地打了个墓坑,就把她埋葬了。仙草的葬礼之所以如此草率,如果还可以说是因为仙草死不逢时的话;那么,白嘉轩对前几房女人葬礼的从简,就从骨子里体现出了他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在那个时代,对于那些未曾给夫家留下一男半女的女性而言,即便其娘家家境不错,当其死去时,最终也不过是躺进一副薄板棺材里,草草下葬了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白鹿原上男性死者的葬礼。秉德老汉死去时,适逢白嘉轩娶妻。在这一特殊背景下,其葬礼不得不从简;但即便如此,其葬礼的复杂和隆重程度,也远远超过了白鹿原上女性死者的葬仪。至于鹿兆海和朱先生等人的葬礼,则更为隆重。鹿兆海的灵柩是“漆成黑色的棺枋”,其葬礼是“白鹿原绝无仅有的一次隆重的葬礼”。[2](P549)朱先生的离世,更是引起了全城轰动。从这些描写中,我们不难见出,在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关中地区,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是何等深厚。
与此相关的,是白鹿原上人们的轻死重生观。“每逢祭日,白嘉轩跪在主祭坛位上祭祀祖宗的时候,总是由不得心里发慌尻子发松。”[1]63这种恐慌,在他有了儿子之后竟不治而愈了。长子诞生时,他举行了热闹隆重的庆祝仪式,“所有重要亲戚朋友都通知到了,许多年已经断绝往来的亲戚也闻讯赶来了。嘉轩杀了一头猪,满心欢喜地待承亲朋乡友……嘉轩听着众人不断重复着的恭维新生儿子的套话——再没有比这些套话叫人心里更快活的事了”[1](P53)。有了三个儿子的白嘉轩,其女儿出生时的喜悦之情发自肺腑:“为女儿灵灵满月所举行的庆祝仪式相当隆重,热烈欢悦的喜庆气氛与头生儿子的满月不相上下。”[1](P81)为了让女儿健康成长,白嘉轩还找来鹿三做她的干大,以保佑她趋利避害,身强体健。所有这些描写,都呈现出关中人对生命的重视。与庆生的热闹隆重相比,《白鹿原》中的葬礼则呈现出简单悲凉的一面。在养生与送死的问题上,对养生的重视,明显占据了白鹿原人们意识的上风。这从秉德老汉葬礼上一位伯伯的话语中,便能得到充分的印证:“人说‘瞻前顾后’,前后总是不能兼顾,就只能是先瞻前而后顾后;生死不能同时顾全,那就先顾生而后顾死。”[1](P10)一代大儒朱先生在评价白嘉轩修祠堂办学的这件事上,说了这样一句话:“祖宗该敬该祭,不敬不祭是为不孝,敬了祭了也仅只尽了一份孝心,兴办学堂才是万代子孙的大事;往后的世事靠活人不靠死人呀。”[1](P66)当此之时,重生轻死的意识,与儒家入世观便有了紧密的联系。白鹿原上的人们之所以轻死重生,用小说里的话说,虽是源自“一个诅咒”;但事实上,这一生命意识的背后,更多地折射出白鹿原上自古以来生存条件的不乐观,以及生命存活之不易。白鹿原上出生的婴儿,半数以上在幼儿时就夭折了,而艰难存活下来的人门,也很少有长寿的。这便使得白鹿原上的人更加重视生命。陈忠实以其生动的描写,再现了我们民族在生存过程中的种种挣扎与抗争,以及在这一抗争过程中所彰显出的顽强的原始生命力。
三、婚丧民俗描写的艺术价值
作者让主人公一出场就不停地忙于操办红白之事,这样的开头,看似与主题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正是因为陷入操办红白之事的困境之中,白嘉轩才会在大雪天出门去请风水先生,并在机缘巧合之下发现白鹿,由此才引出了接下来的换地、娶仙草、种罂粟,以及随之而来的发家致富、人丁兴旺等一系列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小说中的婚丧民俗描写,虽然说不上处处匠心独运,但都是小说情节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对营造故事氛围,推进情节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白鹿原》几乎描写了所有重要人物的婚礼或葬礼。作者不仅把这些内容安排得错落有致,且藉此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如描写白嘉轩与仙草新婚之夜时,作者一改白嘉轩娶前几房媳妇时新婚之夜的血腥与恐怖描写,饶有兴趣地描写了“桃木棒槌打鬼”“百日忌讳”等乡野民俗,以至于后来仙草拿这个桃木棒槌打趣时,读者都会发出会心的一笑。与婚俗描写相比,小说中的丧俗描写虽然少了许多欢乐,但其细节描写如关中习俗骑马坠灵等,均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
不同的民俗,源自不同的地理环境及特定地域民众的社会生活。鲁迅先生指出:“地方色彩,也能增画的美和力,自己生长其地,看惯了,或者不觉得什么,但在别地方人,看起来是觉得非常开阔眼界,增加知识的。”[2]《白鹿原》中所涉及的丰富的民俗内容,与白鹿原的环境、风情、世态、习惯、语言等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使得作品带有浓郁的乡土风味与地域特色,具有厚重的沧桑美。
[1]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2017-01-16
安徽省高校省级教研重点项目(2013jyxm343)
郭海峰(1981-),女,安徽淮北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
I247.5
A
1673-1395 (2017)02-005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