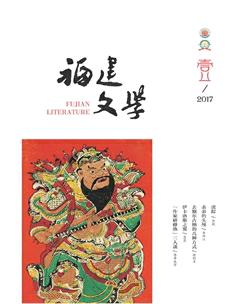“作家研修热”三人谈
陈希我 何同彬 南宋
“教”写作还是“带”写作,该不该“带”
陈希我(小说家、教授)
写作能不能教?技术可以教,但技术不是很重要。“文无定法”,所谓能够作为硬件的技术,不过是遣词造句。而即使是这个,也各有标准。什么是好的词句?修辞需要不需要?简洁好还是拉杂好?我就认为莫言语言的拉杂挺好。什么叫通顺?我就觉得鲁迅的文句改通顺了会失去其崎岖的力量。至于内容如何剪裁,线索如何设置,结构如何布局,只能依作者表达需要而定。我说的是表达需要,而不是内容需要,也就是说,差异性是非常大的,几乎没有标准。
但即使这些能教,也仍是次要的,一个作品好还是一般,拼的是境界,境界是绝对不能教的。某种意义上说,写作靠天生才华,后天补拙是补不出好作家的;而一个天生是好作家的人,即使打压他,不让他写作,他也会因写作而疯的。一个天生的写作者,他有着无法改变的语言风格、设计偏好、思维方式,归根结底是洞察力、感受力和思维力,让他换一种方式,他可能十分低能,十分蹩脚。从这点上说,作家天生的素质就像科学一样,是可以证伪的。不能证伪的,什么都能操弄的,肯定不是好作家。
当然创意写作可以录取有慧根的学生来教,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怎么教?“教”是需要系统的,逻辑自洽的,很难想象教学者在讲台上讲得支离破碎自相矛盾。要不自相矛盾,要不支离破碎,就必须敷衍出一个圆来。而写作者应该相信世界是复杂而丰富的,写作者应该相信自己并没有穷尽所写的物事。另一方面,写作是无拘无束的,甚至写作者的精神状态必须是疯狂的。那么,一切的自圆其说都是非文学的,一切的教育都是束缚。如果一定要培养写作者,那么也只能是“带”。“带”与“教”不同,“带”是即时点拨,像孔子教学,学生则像《歌德谈话录》的记录者爱克曼那样,听取片断(当然爱克曼并无心成为作家)。写作和教写作的人应该都熟悉福楼拜教莫泊桑写作的故事,但那其实是“带”。“当你走过一个坐在自己店门前的杂货商面前,走过一个吸着烟斗的守门人面前,走过一个马车站面前时,请你给我描绘一下这个杂货商和这个守门人,他们的姿态,他们整个的身体外貌,要用画家那样的手腕传达出他们全部的精神本质,使我不至于把他们同任何别的杂货商人、任何别的守门人混同起来。还请你只用一句话就让我知道马车站有一匹马同它前前后后五十来匹是不一样的。”这样的教法,只是指点,显然不成系统。
还有个更极端的例子:据说陈寅恪教诗,就是把诗吟一遍,又吟一遍,再吟一遍,结束。看似荒谬,实为正确。虽然这不是教写作,但对诗的讲解尚且如此不能,何况教写诗?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培养的是艺术创作硕士。我实在想不出“创作”跟“硕士”在价值取向上怎么统一起来。“硕士”“博士”的养成是一个以理性为主导的系统工程(混硕士博士的除外),我想只要读过硕士博士的都应该有所体会。我本人读博时,就深切感受到其与写作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甚至互相冲突。“创作”而“硕士”是个莫名其妙的怪物,明白地说,“创作硕士”是个伪概念。
接着讲“带”。“带”的人甚至可以只是处在顿悟状态,他自己也没有很明确的意见,他只是让学生感受到他的思维方式,甚至是瞬间思想闪现。很多时候,“带”的人成了反例,成为靶子,当然,“带”的人也可以反击。这样,到头来培养者和被培养的关系倒成了“泡”的关系。学写作,就是跟大作家“泡”。你如果有更高的领悟,那么你可以爬到大作家肩膀上,践踏上位。
有人也许会说,我也不求当大作家。但这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我还可以承认:创意写作课程能教,且一定会教出老鼠。
有人会说,国外不少作家在大学教创意写作。这样说的人,多少有“挟洋自重”的意思。搞“挟洋自重”,我们只客观探讨,作家在大学教创意,一,究竟是教创意,还是当“天鹅”?我记得王蒙曾经有个很妙的比喻:驻校作家就好比大学校园里养了只天鹅。天鹅好看,但只能用来观赏。二,即使教创意,是否有成果?培养出作家或者写作人才了没有?三,即使有这人才,有多少程度是教出来的?
所谓“带”,还包括人格的潜移默化,归根结底,写作写的就是人格。而文学人格的形成,是要经过磨难的。那么,另一个问题就出来了,而且是更重要的问题:文学的伦理。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不重要,但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可能有人会觉得,我们是在谈文学的培养,但文学不是技术,作家不是作匠。可能有人会认为,我们这里谈的是教学,但教学恰恰是最具有伦理意义的行为。那么,我们的教育的目标应该是让学生成为常态人,而文学写作会使人狷介乃至疯狂。从这点上说,文学教育是否必要都是问题。如果“文”只是“纹”,那没问题,还可以让人“诗意栖居”。问题在于文学写作者到头来并不满足于“纹”,形式会冲进内容,修辞最终酿成思想,而对普通人来说,思想就是苦难的根源。
有一句话:作家就是殉道者。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把稚嫩的学生、别人家的孩子“带”到殉道的火坑里?哪怕是孩子不懂事,作为教师,也应该为孩子的幸福着想,担当起父母的责任来,阻止他们。钱理群先生反思他自己毕生热衷的“启蒙”事业时,引了鲁迅一句话:自己做不到的牺牲,就绝不鼓励别人牺牲。但钱先生还反思得不够,如果自己做得到的牺牲呢?我觉得就是自己做得到牺牲,也不能绑架别人去牺牲。前者是虚伪,后者是不负责任。我就对我的学生们说:当我站在讲台上时,我是作为你们老师的,我应当尽老师的职责。我甚至可以将你们当作我的儿子,但我深知我也并没这个资格。我没有给你们喂一口飯、擦一次屁股,我没有养你们一天,我凭什么鼓动你们去当牺牲者?哪怕是我所给予生命的儿子,我也没有这个权利。我至今庆幸我的儿子不爱文学,压根就没写作这根筋。
不仅如此,写作有害还因为,写作者连殉道者都可能当不成。作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我指的是真正的作家。巴尔扎克手杖里还铭刻着“我能粉碎一切障碍”,到了卡夫卡,成了“一切障碍能粉碎我”。这样的人自然担当不了重任,而且还会成为“现世宝”,这是上帝的恶意安排,同时也是善意的安排,有了这些“现世宝”,其他人才能得以在对“现世宝”的笑声中正常生活。
作为一种症候的“作家研修热”
何同彬(评论家)
当我们在讨论“作家研修热”的现象时,必然会遇到如下一些亦旧亦新的话题:作家是否会在各种形式的研修中受益?大学或中文系是否能够培养作家?大学和相关机构为什么努力推动这种热潮?回应这些话题的方式也已基本形成惯例,比如历史性地回顾“作家研修”的形态,如何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央文学研究所、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发展到后来的作家班、文学写作本科、文学写作硕士、创意写作、MFA等;在这一过程中莫言、王安忆、余华、虹影及不同时代的年轻写作者们又是如何受益,并最终提高了自己的写作水平;或者从美国写作课的历史传统和文学效应、从王安忆在复旦大学文学写作教育上的成功实践等角度,论证当下“作家研修”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因此,在中国当下,“作家研修热”有无必要继续推广其实根本不需要讨论,某种意义上讲,其价值、正当性和必要性是预设的、“先验的”。在当代文学行为、文学实践的意义诠释制度化之后,没有任何文学活动是无意义、无价值的。当然,最终的解释权归制度和权力所有,而对于“作家研修热”而言,其制度和权力主要归属于作家协会和大学。
在“作家研修”的制度运转中,大学和作家协会始终是通力合作、互相依存的,因为它们拥有着共同的渴望、诉求和“梦想”,这一切维系着中国文学基本的动力、活力、生产能力和自我认同。而参与其中的作家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他们与大学、作家协会之间既是合谋的关系,也是形塑与被形塑的关系。“作家研修热”和中国文学场域中诸多的“文学热”(诸如网络文学热、诗歌热、活动热、奖项热、会议热等)一脉相承,均是依赖于一整套陈旧的、有制度保障的文学观念或文学意识形态,后者经由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基本完成,一直到现在仍旧牢固地掌控着中国文学场主要的制度逻辑和话语、权力的运行、生产模式。这样一种旧的、强势的文学观念,与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新月异的文学变革之间的错位和矛盾早已“昭然若揭”,但因为前者拥有制度提供的权力依赖和源源不断的各种形态的“扶持”,因此得以把各种错位、矛盾修正为恰当、合适,这就导致各种彼此无法融合的文学观念忽而相互对立、冲突,忽而又缠绕、混杂,乃至最终一起汇入一股同样的汹涌奔腾的浊流。
不仅仅是“作家研修热”,中国文学场域中的任何现象、事件或者所谓的“热”都是症候式的,而且这些症候的根源是同一的。吕西安·戈德曼在《论小说的社会学》中认为:“文学创作的集体性来自于如下事实:作品宇宙的结构同某些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是同源(相似)的,或者说它们之间有着明白易懂的关系。”文学文本尚且如此,那就更遑论“作家研修”这样的文学社会学层面的现象了。当大学和作家协会广受质疑或诟病的时候,“作家研修热”将如何成为一种症候,其实并不需要做更多的解释、举证,它“同某些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是同源的”,“或者说它们之间有着明白易懂的关系”。这里并不是简单、粗暴地否定“作家研修”对于写作和作家成长的积极作用,而是强调如果以中国当前的文学制度作为基本前提,那任何看似合理的文学举措、文学实践在生产积极性的同时,往往会同时滋生出数倍的消极性。比如在“作家研修”的各种形态的空间和模式中,显而易见的功利性驱动机制、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文学权力的传承和转移、意识形态的训诫和改造、主体的溃散与重塑、盲目而狭隘的文学生产等负面效应是必然相伴相生的,而且没有任何良性的機制可以避免这些症候的显现。
“作家研修”被赋予过多抽象的、高蹈的价值和功能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比如培养所谓的“学院派作家”就是一种奇怪的理想,或者把系统的高等教育作为一个作家成熟、成功的必要前提,显然高估了积弊丛生、丑态百出的中国大学,也忘了大学不仅培养智者,更培养各种各样的“蠢货”。而作家协会系统很多的作家班、培训班和读书班,也基本上依赖于高校体制,加上自身体制的弊端,因此往往表现出双重的症候性,其以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为表征的无效与荒诞更是自不待言。至于迅速勃兴的创意写作,其主要功能是围绕着影视娱乐业、网络文学引发的必要的职业分工展开的,有极强的功利性和显著的职业特征,属于“泛文学化”之后的文学现象,与我们经常讨论的文学之间是有距离的。简而言之,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如果不清除制度的积弊,那么任何所谓的创新、创意最后都沦为庸俗社会学、新闻学意义上的“事件”,我们在论争和标榜其有限的、局部的合理性的时候,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其“黑暗”的一面,乐此不疲地踵事增华、随波逐流。而这种习常性的“忽视”也就阻隔了我们的文学主体成为阿甘本意义上的“当代人”:“他将这种黑暗视为与己相关之物,视为永远吸引自己的某种事物。与任何光相比,黑暗更是直接而异乎寻常地指向他的某种事物。当代人是那些双眸被源自他们生活时代的黑暗光束吸引的人。”
创作可以教,关键看怎么教
南宋(小说家、媒体人)
近年来,继复旦大学成立全国第一个创意写作的艺术硕士点、中国人民大学开办首届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之后,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也重启20世纪80年代的做法,准备联合招收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文学创作方向的研究生,多地高校开办“作家研修班”已然成为一种风气。
我以为,这是一种纠偏。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大学不培养作家”几乎成为一种共识。更早以前,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就曾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后来,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晦、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东润也说过类似的话。在这些著名的学者眼中,中文系就是培养文学研究人才的,打好文学基础更重要。这些年来,写学术论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成为师生共同关心的头等大事。至于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不能得学分,更不能评职称,在师生眼中,是可有可无的事。你可以研究作家作品获得硕士博士文凭,但如果你在《收获》《十月》上发表一篇小说,至多挣得一些稿费和一点虚名而已。打个比方,钱钟书研究宋诗可以得博士学位,但如果他仅仅写出《围城》,对不起,你还是一名清华大学的本科生。在我的记忆里,20世纪80年代,似乎只有华东师大中文系曾有“吃螃蟹”的精神,本科生可以以小说或散文当毕业论文,只因当时中文系终身教授钱谷融是一位开明的、有创作才能的学者,他知道创作与研究同等重要,两者都可以衡量一个人的文才。华东师大当年拥有格非、李洱等一批作家,其来有自。
学术论文受到推崇,创作备受冷落,后果就是我们培养出大量千篇一律只会写西式论文的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连一篇文从字顺的散文都写不好,遑论写出有一定难度的小说和诗歌了。工作后,大部分时间不需要论文,而“散文”需求却纷至沓来,许多人经历了痛苦的再学习过程,这时,主要靠自学了,青春已逝,师友不在身边,学习效果大打折扣,有的人学会了,有的人则永远学不会。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一位在媒体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只有个别记者的文字有点文采,大多数记者的文字干巴巴的,又缺乏文学的描写能力,报道极为枯燥。遇到有点文采的报道,就像捡到宝似的额手相庆。
所以,我看好多地高校开办“作家研修班”或招收创意写硕士的做法。知错能改,这是教育界的一种“拨乱反正”。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说过一段很有启发意义的话:“大学中文系本身就担负了文学教育的义务,除了培养专业方面的研究人才以外,进行文学审美教育,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并且通过文学阅读来提高学生理解人生社会、历史现象的能力,以及通过文学实践来培养更多的文学创作人才,都是中文系的教育任务和培养目标。尤其在今天大学教育越来越趋向大众化(非精英化)和实用性(非专业性),大学中文系本科的培养目标,除了为一部分人进一步的专业研究打基础外,大多数的学生将在本科毕业后从事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工作,只有少数人才会继续从事专业研究。因此从教育的功能看,培养健全而美好的人格也许比给予高深的专业知识更为重要。”真希望各地高校的中文系主任都能有此认识并大胆加以实践。
当今社会,会写好文章,利人利己。那么,创作可以教吗?美国的创意写作传统源远流长,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著名作家、《大教堂》的作者雷蒙德·卡佛能够成长才,就得益于这一传统。很难想象,没有参加创意写作班,他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小说家。美国的创意写作班,有教材,有练习,有课外实践,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据说,一位有中等才华的人,几年写作班学习下来,基本可以熟练地写出及格线以上的小说。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有几位懂得教写作的好老师。在自传《火》里,卡佛提到一位写作小说入门课的老师对他的帮助,他就是约翰·加德纳。加德纳说,作家既是后天造就的也是天生的。卡佛的理解是,音乐、作曲、视觉艺术都可以有学徒,写作为什么就不可以有?加德纳说,要当一名真正的作家,必须要有心灵之火。加德纳推荐有点价值的小刊物给学生,告诉他们哪些作家应该读。他会拿过卡佛一篇小说的初稿,跟他一起仔细地读。一遍遍告诉他,用准确的语言表达自己想表达的意思是多么重要。他不断敲打卡佛,使用平常的、正常说话用的、我们用来互相交谈的那种语言是多么重要。卡佛动情地写道:“他教我在写作中怎么缩短词语,教给我怎么用最少的词语说我想说的话。他让我明白一篇短篇小说所有的一切都是重要的,就连逗号和句号往哪儿放也不例外。他给我这样那样的帮助,他把办公室的钥匙给我,让我周末有地方写作,他容忍我的莽撞和寻常的胡说八道,为此我将永远感激他。”
无独有偶。在中国,也产生过一位会教写作的好老师,那就是小说家沈从文。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里,深情记录下年轻时沈从文在写作上给他的教导和帮助。汪曾祺写道:“创作也不是绝对不能教。沈先生的學生现在能算是作家的,也还有那么几个。问题是由什么样的人来教,用什么方法教。现在的大学里很少开创作课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偶尔有大学开这门课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沈从文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题目都非常具体。一次出的题目是“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还有一次出的题目是“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沈从文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汪曾祺有一次写了一篇小说,竭力把对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从文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汪曾祺从此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沈从文还有一种方法,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让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从文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汪曾祺说,沈先生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写作是一场马拉松,沈从文对学生说,凡事要耐烦,意思是,锲而不舍,不怕费劲。
约翰·加德纳和沈从文会教创作,这与他们都是作家知道个中甘苦密切相关。我欣赏各地高校开办“作家研修班”的做法,但我更希望这些班级多教出一些优秀的作家。那么,请谁来,怎么教,至关重要。如果只是高校自己的老师教,特别是只会研究作家作品自己却无创作实绩的老师,教学效果一定不会好,这就需要引进外面有创作成绩的作家了。我想,这就是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招生的目的所在,双方优势互补。复旦大学引进王安忆、中国人民大学引进阎连科、刘震云,都是很有眼光的。有了好老师,再用写出一定数量的好作品来要求学生,而不是泛泛地听课,这才能有实际效果。招来的学生,大都有一定的基础,有的甚至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作家了,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招的张楚、郑小驴、双雪涛等。我想,他们也不必囿于学生的身份,完全可以不定期在校园里开办文学沙龙,出版文学内刊,带动全校形成尊重写作热爱写作的风气,让校园生活变得更有趣更有余味。这些作家学生也可以利用私人关系,把自己认识的作家介绍给其他同学,畅谈文学与人生。正如陈思和在《文学会使校园变得更美好》一文里所说,我很支持作家进校园,如果我们的知名作家都经常到校园走走,即使不上课,能够让同学在教室里、操场上甚至食堂里经常见到,也是一道非常靓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