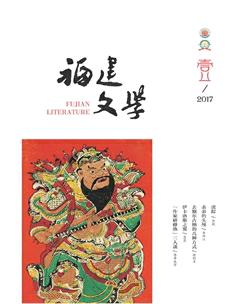人兽之间
郑国庆
虽然《虎踪》具有写实的外形,叙述人的身份——“黑砖窑”逃离者也容易让人联想到主流文坛的 “底层文学”。但小说的走向很快就逸出了底层文学的社会写实路线,笼罩着浓厚的象征色彩与某种程度的神秘韵味。
小说的叙述遵循着两条线索,一条是叙述者“我”的心理动作,另一条则是叙述者“我”眼中所见的老郑。所谓“虎踪”,讲的就是老郑追踪老虎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位“一根筋”山民的执念。老郑在野山里目睹一只四十年不遇的老虎,回村讲述时却无人相信。为了争口气,老郑头脑发热,刻了木质的老虎脚掌,在山上布下老虎的伪脚印,以资证明他的真所见。而后事件开始失控,媒体、政府、专家的介入,使得伪造事件发酵升级,事态裹挟着老郑,以至“骑虎难下”,最后因为伪造老虎的照片而进了班房。故事讲述的,就是出狱的老郑怀着难以下咽的“冤屈”,一心要找到他确曾亲见的老虎。小说将这位朴实又颟顸,仗义、执着中带一点农民式狡黠的人物刻画得相当生动,是当代小说创作中一个新的人物形象。
小说的材料很容易让关心社会新闻的读者联想到周正龙假老虎事件。事实上,这一起假老虎事件与地方政府的角色、媒体时代浮躁、功利的氛围等,大有小说家可以挖掘之处,但作者显然志不在此。这篇小说并没打算往问题小说的方向发展,而是将笔触探入到一种人兽之间意味深长的关系中去。老郑出狱后将全部生活孤注一掷在寻觅虎踪上,证实老虎的存在成为老郑生命存在的证明,老虎在某种意义上升华为一种神圣对象,是老郑生命中所有热烈与冒险的黄金誓言。在小说的结尾,老郑在老虎的召唤下循虎而去,不知所终,“老郑迎着落日的方向,敏捷地奔跑着,蹦跳着,背影看上去就像一只羚羊,他的动作似乎带着一种极大快乐的韵律,如同一个游子,奔跑在通往久别的家的最后一段山路上。”人与兽、人与自然在此达到了一种神秘的融合。小说也特别安排了一组寻猎老虎的人员,他们与老郑形成对照。与这批人对待动物及大自然那种征服、捕获的心态相反,老郑对老虎则具有一种前现代式敬畏、向往的精神。“在他和那只野兽之间,似乎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心灵感应”——老郑与老虎之间所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共生共存,既相互敌对又相互依赖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更阔大的整体观。对生态文学、动物书写感兴趣的研究者,当可从这篇小说解读出更多相关的意涵。
小说的另一条线索与假老虎事件一样,同样具有社会新闻的来源——“黑煤窑”事件,然而文学不仅是社会学,小说家的关注点在人,作者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有力地以内视角展现出这个叙述者兼人物的“我”在逃亡过程中向兽蜕化/退化的过程。从睡梦中不时听到的兽性号叫,到在山林中听到真正的老虎嘶吼,再到在高烧发热的睡梦中化身为走投无路的愤怒“困兽”,即被仇恨压倒的老虎,小说细致入微地写出了这位逃亡者如何在黑煤窑毫无人道的环境中被残酷地压榨、折磨后,如何被恐惧吞噬,被仇恨吞噬,而逐渐向非人/兽退行的心理动作与幻觉。
小说中写虎之梦的那一章甚为精彩,颇有几分康拉德《黑暗之心》的精髓。作者从青苔与藤草的气味开始写起,写这些阴湿的植物如何渗透进“我”的皮肤,在“我”的身体中慢慢长成一个活物,活物一点点地吞没“我”的意识,直到“我”的眼睛变成兽的眼睛在观看“我”仅剩的人形,最后没入黑暗,“那意识的转移一刻不断,一直到那个视角完全转移到那双非人的野兽的眼睛背后,而它也在那最后的这一刻里,完全长成,猛然间撕开一直滋养着它却又牢牢束缚住它的肉体,站起来,用力地甩着身上的鲜血,就像甩着细毛上被沾湿的雨水。它用冰冷的眼神看着这具躺在地上的伤痕累累的瘦弱男人的身体,有些迷惘、快意,还有一丝畏惧。最后,它扭转过身体,一跃而起,从火堆上跳过,冲入到山洞外那无边无际的丛林黑暗之中去。”虎在这里,不再是老郑那条叙述线索里神明一般的存在,而是象征地狱一样的深渊。人类潜伏的兽性永远隐藏在人形外衣底下,在适当的时机就会伺机而出,反噬人类。
所谓虎踪,一方面指的是老郑对于老虎的追踪,而在叙述者这条线索,则又暗示着老虎对于人类的追踪。老虎在小说中因此具有了双重的象征意义:一层是老郑故事中,自然对于人类永恒的引力;另一层则是人类与兽性之间永无休止的纠缠。这就是所谓人类文明的苦恼了:那广袤的原始山林,那伟大的山林之王,既是我们渴望復返的自由与伟力,又是我们需要小心防范的黑暗之心。
这是一篇主题含义相当丰富的小说,探讨的是人类与原始的关系。而老虎所代表的“原始”的象征意义,在这篇小说又可再具体分为自然/兽性这两个层次,由于这两个层次的内容、指向、价值并不完全一致,作者的两条叙述线索因此有一些强行扭接之嫌。但作者作为文学家,这篇小说的好处并不在对于人类文明的复杂思辨,而是富于艺术感觉的叙述。整篇小说通过切分小节营造出一种人类在人兽边界徘徊的紧张气氛,作者尤擅于通过延伸比喻来传达一种幽微的心理感觉。例如,“我总能看到身体上那些留下的痕迹,那就像是煤炭的黑色渗透到交错的伤痕里,深深地渗透进去,无论怎么清洗也无法洗掉,最后慢慢形成兽皮斑纹一样的纹理,它从那个时刻开始发芽生长,一直不断地生长到心里深处。”或者,“一道重击打在我耳朵下方的脖子上,就像原来还低伏在草丛中的阴影,在一瞬间突然上涨起来,一下子淹没整个视野整个身躯,而且从稀薄的状态,一下子变成浓稠的黑暗,浓稠得就像几乎无法搅拌的泥浆,就像突然炸开的煤炭粉尘。”这些比喻都没有在给出喻体之后结束,而是继续延伸意象的状态、动作,从而将人物的心理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的艺术感觉与叙述才能由此可见一斑。
关注当代中国文学的人或许会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期,福建文坛曾经突然冒出一位天才少年,一位名叫俞帆的高中生在《福建文学》上发表小说《阉猫纪事》《隐秘的水仙》,笔法老练,叙述精当,一点也不像出自初出茅庐的写作者之手。两篇小说先后被《小说月报》连续转载,一时间令彼时被视为小说弱省的福建文坛颇为惊喜。然而这位普遍被看好的文学新星在几年后却转投商界,逐渐逸出了文坛的视线,终没能充分发挥他无可限量的潜力。个人的人生选择旁人自然无可置喙,然而正如挖掘了这位天才少年的著名作家、彼时《福建文学》的编辑北村在为俞帆唯一的小说集《余温如诉》的序言里殷殷所言,俞帆写得太少,没有真正地完成他应该完成的“任务”。就个人职业来说,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职业方向的自由,然而,就造物主的恩赐而言,他希望俞帆不要辜负了造物主赐予他的写作才能,不要辜负这个恩赐里所包含的重托与使命。如今,疏离文坛二十余年的俞帆重出江湖,仍宝刀未老。让我们祝愿他在未来的创作道路上善尽才华,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出更多精美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