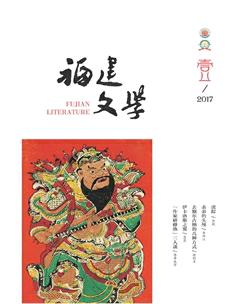吴钧尧小品文
吴钧尧

默
最怀念的互动,是与孩子,一起移动了岁月。那时光点点滴滴,孩子的方寸,我的世界,我与孩子镇守客厅、房间,有时候,或抱或推,到屈臣氏跟顶好,指陈尚待命名的一切。
最爱单臂抱他。一个娃儿、一种柔软,他仿佛自知,紧拎我衣领,以免这世界变得过度坚硬。抱他上顶楼,常在黄昏前。蚊虫还没肆虐,胳臂不需要遮掩;太阳已经揉皱,宛如穿旧的毛线。孩子与我齐高,当时盆地在,一衣淡水,映山带楼,缓缓流海口。而今盆地在,楼之外还有楼、高之外还有高,淡水流域不曾撤离,只是城市长高,显得它变矮。
诗人吴晟与歌手吴志宁,发表《野餐诗歌》,父亲的诗、孩子的曲。這在华山,但不论剑,而抒亲情的招法。若说亲情有招,吴晟肯定反对,只能说我们勤练心法,不过在于描绘出父母亲的一两句话,如同吴晟的母亲说,我们用不了这么多,食不了这么厚,何必汲汲赚取?
如果亲情有招,一练几百式,最终不过归于一。不一统江湖与江山,而召唤往者的行谊。那些个幽幽,我们一旦气足,便召唤为神。尽管只是一个人的神。想起我跟孩子的顶楼,那一刻,我恐怕比落日更像落日,我是他完整的一天,从开始到结束。而今吴晟父子一起登台,招式各自练了,再又融合。我若说,这是一个各自为神的世界,吴晟又要反对了,当一个人,就该渐渐消解人与人、人与物的界线,哪能允许睥睨,虎视眈眈,以为三人成虎。
其实三百人、三百万人,也不能把人变成老虎。只是人选择相信,他是虎。
吴晟盖了书屋,我还没去过,痖弦纪录片、文友照片,都让我得以围观:书屋也是树屋,屋外头有树,树的视角有屋。吴晟与土地的移动,是不移动它们,是练一口真气,立桩,成为一棵树。他的孩子,无论社运、唱歌或学医,农忙时一律卷高裤管,弯着腰,凝视着默默大地,一株株草翠。
什么时候呢,拎我衣襟的孩子,不仅能与我同台,还可以一块弯腰,掬露水、迎朝阳?这时候,我不会比日出更像日出。这只是一天的,两种开始。
后来,我们的眉目,都是等待别人再来发现。犹如这一天的华山与吴晟。我们一起跑回了童年。若吴晟能偷听我心声,势必又要反对,他年长我几个世代,哪肯占我便宜。文字是神、音乐也是,我一路跑回去,奇怪的是我甚么也没有逗留,只记得割高粱,必须左手握高粱秆,右手使镰刀,角度需斜、力量得巧。红土田埂中掏花生,双手持梗头,一起施力。否则,有的拔了出来、有的还在土堆里,必将遗落更多的收成。晒干的玉米土红土红,以平口起子犁出几道缝,双手得扭,才能一口气卸了玉米。
每一种作物的收获,都有接取它们的方式。正如每一种谷物,都长着不同的毛毛虫。如果说,对待作物也必须出招,我跟吴晟会一起反对,这人间,人的声音着实多了,也杂了、乱了,这时候,该是不去移动的时刻,我们可以静静静地老,静静静地,躺成“一”。
“一”,就够了,而不是“三”。
飞
那些年,很多人到台北逛花博。我也去。带父母与孩子,看花朵开在室内与户外。父亲不爱游旅,说:花朵这款,开在哪里都一样。我们指着东南亚区,几只大象与锦簇花园,说:台北不生大象,以及得翻看说明,才得知道的花种。
父亲说,知或者不知,又干卿底事?不能与父亲争论一朵花、一枝草,至于玉山与石头,说到底,又干卿底事了?在孩子撒娇下,父母站上魁儡立像的后头,往前,透出他们的脸。花,把他们的白发都遮花了,他们站得拘谨,跟花闹的立像衣裳,形成两个世界。
我想起斗牛场景。斗牛士招展手上的红旗,瞪着它们的黑眼睛,则兴奋咆哮。一个静,一个非常动;一个帅,另一个非常暴。这是一场以“静”为核心的暴动,我看着牛、看着父母,很明白这是一场时间的战争。
我们都会败,这是逛花博的一层意义。所以要拼一口气,争夺这一季,不该开与不能开的,我们用温室、用药剂,让百花都一一开了。
我们都会败,这是一个朋友说的。她还说,再聪明的人,没有为感情做过傻事,也是遗憾的。
飞啊飞。是的。我的联想很无端,所以当不了诗人。年少上过诗人白灵的新诗讲座,一个即席的测验是,给你“天空”,请发想十个有关的意象。像是给你十条路,让你找到自己的天空,但我找啊找,天空不见了,只有自己飞啊飞。
不一定能飞,就更靠近天空?君不见,飞蛾怎么飞?尤其穷夜孤灯,都隔着玻璃了,窗外不时传来,针灸般的冲击。啪咧,脆弱与刚硬;啪裂,其实没裂,而是渐渐碎了。
所以,谁能不败,允许自己一身弱翅,继续与火拼搏?
这即是你说的,没有遗憾,不要万事聪明,而选择一个葬场,葬蚀聪明。
尽管我们都将败北,但还是很怕很怕,怕一个不留神,牛从西班牙那头跑来。糟糕的是手上没有招展的红旗,糟糕的是,空荡的人生地盘上,就一个自己,身着红衣?牛啊,它很兴奋,它看见战场上,总是以死亡延续新生。于是它疯狂奔跑了。所谓啊,人生只有一回,不单是人,牛也是;不单是愚蠢之徒,聪明之辈亦然。
当年的我,没在白灵的课程上,找到发现天空的十种法门,到今天,岁月的尘埃更重了,灵性已不开,剩肉性、顽性、还一些傻性,继续在我心底争执?争,该由哪一个,带领我飞?
我很佩服一个电蚊香品牌,它是“灭飞”。这是聪明人的产物,凡飞行的害虫,都该灭绝。它,指蚊子,一个能飞而且能飞得很高很高的昆虫,却没有人歌颂它的飞。一只聪明的蚊子只能烟它、熏它,使之头昏脑涨,静静而死。灭的,不单是蚊子,而是飞啊飞,关于那个题目:给你十个词汇,请你走进天空来。
来掉个书袋。孟子曾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我跟朋友说,意思是笨蛋,更容易打败聪明人,拥有爱情?如果我有惑,而续问父亲爱情,他肯定说,爱,爱甚么呀?爱情这玩意,能吃呀、能饭呀?
多可怕呀,父亲突然能说京片子了呀!
对
西部,离现在很远了,除了那是另一个国度,还因为那款君子之战,久不见矣。克林伊斯威特、保罗纽曼、劳勃瑞福等,与对手背身而走,十、九、八……快速扭身鸣枪击发。或者不背转,直接对峙。风萧萧兮壮士寒,尘烟起兮傲骨胆。黄土大街上,一扇被吹歪的酒吧门闩,不停地哎呀。然后你看着我,哎呀地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