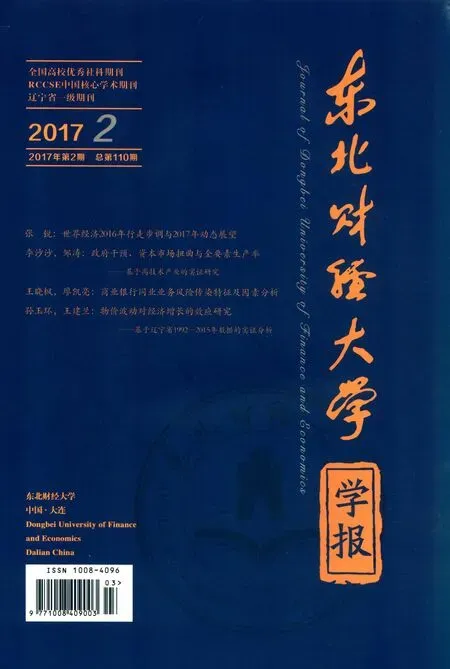中国预算思想演进刍议
舒丽娟,付志宇(.上海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上海 00;.西南交通大学 财税研究中心,四川 峨眉山 640)
中国预算思想演进刍议
舒丽娟1,付志宇2
(1.上海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上海 210021;2.西南交通大学 财税研究中心,四川 峨眉山 614202)
预算在中国已有千年的历史,其间大量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关于如何编制、执行和监督预算提出过许多独到的观点。他们的思想多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熏陶,但由于实际情况的差异,又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气息。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和西方先进思想的进入,传统的预算思想在变革中得以发展。本文着眼于历代先贤关于预算原则的讨论以及预算实践中体现的思想,探讨中国古代预算思想演进的轨迹和规律,为当前的预算工作提出良好的借鉴,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国家财政;预算思想;预算原则;预算实践;量入为出;量出制入
一、从预算原则看预算思想
(一)“黜奢崇俭”论的发展与批评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自然经济国家,百姓财富积累十分不易,因此从先秦起勤俭持家的观点就被大多数人所认可,这个“家”不仅仅是指家庭,还指国家。《周礼·天官·小宰》载:“以官府之六职,辨邦治:一曰治职,以平邦国,以均万民,以节财用……”,“节财用”就是限制天子开销。当时的人认为,夏桀商纣之所以会灭亡,就是因为生活奢靡没有节制,所以周天子在制定国策时就师前事之鉴,厉行节俭。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军力和财力都有所提升,奢靡之风开始抬头,思想家如孔子、晏子等提出了限制君王支出的观点。孔子以周朝的礼制作为评判奢俭的标准,认为治国要“节用而爱人”①。孔子最看重的礼也应节俭:“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②晏子也认为,人追求财富的欲望是无穷的,因此他主张“幅利”,也就是限制财富:“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使无迁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无黜嫚,谓之幅利。利过则为败。吾不敢贪多,所谓幅也。”③如果说春秋时期思想家的观点还多是从个人和家庭出发的话,自战国开始,节制支出的观点就更加有针对性地指向了国家财政。荀子发展了孔子的观点,提出“节用以礼,裕民以政”④,明确提出了国家应该以“礼”作为用度依据,以百姓富足作为财政工作的第一要义。秦统一中国后,始皇帝大兴土木使得民不聊生。秦亡后,汉初采取休养生息的黄老之道。刘安提出了“安民足用”的思想,“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⑤这样的观点一直延续了数千年,每当一个朝代走向没落之时,或者君王有骄奢淫逸之欲,都有黜奢崇俭的观点对其进行批驳。后世典型的如朱熹、张居正和海瑞等,都提倡节俭、反对统治阶层挥霍民财以追求过度的物质享受。张居正以历史为鉴,提出了富贵节欲论:“以天下之大,奉一人之身而常苦其不足,口厌甘脆,而天下始有藜藿不饱者矣;身厌纨绮,而天下始有短褐不完者矣;居厌广丽,而天下始有宵啼露处者矣。其弊至于离志解体而不可收拾,则汉、唐、宋之季世是已。”⑥
尽管黜奢崇俭一直受思想家和政客们所推崇,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明中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产生,消费主义思想对传统的积累主义产生冲击。思想家陆楫认为节俭只能使一人一家“免于贫”,但如果要让整个国家富裕就不能崇尚节俭,在他看来“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生者也。”⑦陆楫认为之所以节俭反而造成贫穷的原因在于节俭不能创造消费的动力,也就没有办法刺激生产。明末郭子章将陆楫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并引申至财政支出上来,在他看来“奢俭”不是绝对的支出多少,而是国家财政不该开支的开支了,该开少支的多开支了,就是“奢”;该开支的没有开支,该多开支的少开支了,就是“俭”,而这两种“奢俭”都是对国家不利的。他尤其批评“俭”,认为“俭”会造成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缺位,使得社会不稳定,“阴以酿国家他日之忧”。维新变法时期谭嗣同、梁启超都对黜奢崇俭进行了批评。谭嗣同主要是从市场的角度说明黜奢崇俭会使人们安于生活停滞落后,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并以此抨击封建制度。梁启超从政府理财的角度,赞成政府的赤字财政,认为政府应该大力“兴工程,拓商务”,“而后之颂善政者,以大官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谓为美谈。抑何与计然之言相剌谬耶?善夫西人之政也,国家设银行,借国债,民有财贷之于官,官藉之以兴工程,拓商务,以流通之于民,而国之富强遂莫与京。”⑧
(二)“量入为出”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黜奢崇俭的观念延续了上千年,与之相应的量入为出思想也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礼记》最早提出“量入以为出”,此后一直被奉为圭臬,直至唐德宗年间杨炎提出“量出以制入”的理财原则并实施两税法,撼动了延续数千年的经典思想。当时反对量出制入最强烈的便是陆贽。他所提出的量入为出是建立在两税法实行十余年后,政府不断摊派加码造成百姓税负大幅增加的基础上,“今既总收极甚之数,定为两税矣;所定别献之类,复在数外矣;间缘军用不给,已尝加征矣;近属折纳价钱,则又多获矣。比于大历极甚之数,殆将再益其倍焉。”⑨所以他针砭时弊地指出:“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⑩后来的研究者褒杨贬陆,认为陆贽思想过于保守迂腐,实际是没有客观看待两税法这个“先进的”生产关系脱离当时生产力而对百姓生活以及国家财政造成的不利影响。
南宋时期,朱熹和陆九渊兄弟也倡导财政应量入为出。朱熹针对自北宋遗留下来的严重的三冗问题,提出“撙节财用”的基本方针,除老生常谈的“去冗兵”“汰浮费”之外,他结合“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思想,要求统治阶层“正心”。他认为“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同时,朱熹对“量入”进一步解释,“量入”不仅仅要准确计量财政收入,还应该与各地区的经济情况、百姓的实际负担能力相匹配。陆九渊兄弟的观点与朱熹近似,却也有独到之处。陆九韶的治生之学里提出“用度有准,丰俭得中”,并定量地举例来进行说明:“今以田畴所收,除租税,及种盖粪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为水旱不测之备,一分为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数,约为三十分,日用取其一,可余而不可尽用。至七分为得中,不及五分为啬。其所余者,别置薄收管,以为伏腊、裘葛、修葺、墙屋、医药、宾客、吊丧、问疾、时节馈送;又有余,则以周给邻族之贫弱者、贤士之困穷者、佃人之饥寒者、过往之无聊者。”上述观点虽然没有上升到国家的高度,但不可不谓是量入为出思想的直接体现。
不同于先代理财者,明代的丘浚非常直接地主张“国家之所最急者,财用也”,并且提出了最接近现代财政预算的思想。丘浚也以量入为出为基本原则,但是他并不是根据当年所收到的财政收入“现收现付”地去安排财政支出,而是根据今年的收入情况,安排来年的财政支出。由于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于田赋,而农业生产在当时受天时的影响很大,在缺乏科学技术进行合理预测的情况下,预计来年的收入情况是很困难的,“财生于地,而成于天,所以致其用者人也。天地岁岁有所生,人生岁岁有所用,岁用之数不可少,而岁生之物或不给。”因此丘浚提出根据本年的收入安排来年的支出,具有操作上的可行性,并能够对国家财政支出进行限制,即来年支出的上限就是本年的收入,“至十二月终旬,本部通具内外新旧储积之数,约会执政大臣通行计算嗣岁一年之间所用几何,所存几何,用之之余,尚有几年只蓄,具有总数,以达上知。不足则取之何所以补数,有余则储之何所以待用。岁何不足,何事可以减省,何事可以暂已。如此国家用度有所稽考,得以预为之备,而亦俾上之人知岁用之多寡,国计之盈缩,蓄积之有无云。”这种预算思想相较以前“勒紧裤腰带”式的量入为出更加科学,实际的财政工作也更加易于管理。
明末清初,黄宗羲总结了历朝历代的兴盛衰亡,把当时的赋税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概括为“三害”,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改革建议。关于财政管理原则,黄宗羲强烈反对杨炎的量出制入,认为这是统治阶层任意加赋的根源。从现代财政理论的角度来看,量出制入更加先进、民主、科学,但若以今人之智度古人,难免有失公允。黄宗羲反对量出制入而提倡量入为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首先,他提出“反积累以前而为之制”,也就是提倡复古,恢复到三代的贡、助、彻制度。周天子在中国历来都是被视为解救万民于水火中的君王,加上传统的儒家将周礼奉为一切行事之基本准则,因而历代的鸿儒们都对周朝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抱有乌托邦式的幻想。一旦土地兼并问题严重了,就有人提出“复井田”;一旦君王的开销显得铺张,“义主利从”的观点便再次兴盛。同样,量入为出属于周制之一,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使国家财政健康稳定的最优解,以食古不化来批评是不恰当的。其次,量出制入的预算原则虽然先进,但是需要以严谨的支出计划、严格的征收管理,最重要的是以充分的权力制衡为前提,而在当时这些条件都是不具备的。中国古代君权与相权之争自朱元璋撤相后就已经白热化了,而黄宗羲所处的时代距离下一次权力回归君主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因此,与其任统治阶层随心所欲地制定开销计划并让百姓埋单,不如先锁定财政收入,使得财政支出不至于失控。
(三)“量出制入”思想的出现与演变
汉武帝时桑弘羊主管国家财政,其财政管理方面的言论不多,仅在《盐铁论》中有“计委量入,虽急用之,宜无乏绝之时”的说法。关于“计委量入”,先前有学者将其理解为根据支出来确定收入,笔者认为是过度引申原意了。在“计委量入”之前,桑弘羊说:“兵甲不休,战伐不乏,军旅外奉,仓库内实。今以天下之富,海内之财,百郡之贡,非特齐、楚之畜,赵、魏之库也。”此处桑弘羊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连年征战而没有出现财政亏空,而汉初国库充裕但财政工作开展步履维艰,因而应该根据国库储备的实际情况来度量财政收入。此处“计委量入”的“委”是积累的意思,“委之则聚”,而非支出之意。尽管如此,桑弘羊提出的根据国库的充裕程度来确定财政收入,亦体现出量出制入的思想,是对周朝以来量入为出思想的一个大胆的挑战。
唐中叶时杨炎提出以财产为基础的赋税征收办法,“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侥利。”杨炎之所以要以“量出以制入”作为两税法实行的前提,实际上正是为了克服后世思想家所言的两税法之弊病。杨炎在谈及租庸调制失败时,除了战乱导致人丁脱离土地外,官员的肆意盘剥加码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他说:“权臣猾吏,因缘为奸,或公托进献,私为赃盗者动万万计。”所以,新的税制要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也要保证税负的稳定。有研究者将以支定收的财政管理原则分为“量出制入”和“量出为入”,此二者大意是相同的,但细究起来确有区别。“量出制入”指的是根据支出来限制、控制收入,而“量出为入”则是根据支出来安排、确定收入。据此判断,杨炎所提倡的是“量出制入”,因为他指定的政策目的是限制政府过多地收取税收,减轻“有形的手”对生产生活造成的负外部性。此外,杨炎在之前谈及皇室支出时,也提出“度宫中经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的观点,表明其量出制入的财政管理思想并非是专为两税法而特别提出的。
杨炎之后,王安石、李鸿章等人都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采取过类似量出制入的管理模式,但均未明确提出量出制入的思想,及至清末从欧美国家考察回国的学者、官员以量出制入为原则编制财政预算才被公开提出。王韬在访问英国之后,对英国采取的财政体制大加赞扬,“所征田赋之外,商税为重。其所抽虽若繁琐,而每岁量出以为入,一切善堂经费以及桥梁道路,悉皆拨自官库,借以养民而便民,故取诸民而民不怨,奉诸君而君无私焉。”同样是向西方学习,黄遵宪考察了日本的财政之后,明确地提出应实行预算制度。他说:“余考泰西理财之法,豫计一岁之入,某物课税若干、某事课税若干、一一普告于众,名曰豫算……其征敛有制,其出纳有程,其支销各有实数,于豫计之数无所增,于实用之数不能滥,取之于民,布之于民,既公且明,上下孚信。自欧罗巴逮于米利坚,国无小大,所以制国用之法莫不如此。”在预算原则方面,“泰西诸国必预计一岁出入之款,量出为入。”也就是说,黄遵宪提出效仿西方建立量出制入的财政预算。并且,他还认识到,在量出制入原则的指导下,非经常性财政支出可能会导致财政运作困难,因而需要以国债作为补充,“国家一旦有大兵革、大政事,乃大开议院,议加征重赋。重赋加征之不足,于是议借债。”不过,黄遵宪对举国债的态度相对谨慎,认为“外国债则利在一时而害贻于他日,且利在邻国而害中于本邦。”但总的来说,黄遵宪还是赞同量出制入的原则。此时期以后,由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量出制入的财政预算原则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宋子文主持国家财政工作时曾希望建立量入为出的预算,“先定收数,次为支配,以收统一财政之实效”[1],但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军费、基础建设等支出剧增,量入为出的预算被破坏。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时,改“量入为出”为“量出制入”,他认为战时理财“应以达到增加国家财富为目的”,同时加大征税力度并大量举债。由于国民党本身的腐败和战时财政管理工作的缺位,量出制入的预算反而助纣为虐,加深民众的苦痛,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然而,无论是量入为出还是量出制入,都需要建立在政府权力能够被有效制约的基础上。王韬认为这是“君无私”的结果,他的思想是典型的奴隶、封建社会中渴望“明君”、“弥赛亚”的思想。从今人的实践中可知,民主政治是制约政府权力的一个有效途径,量入为出和量出制入的预算原则对民主政治的一种支持,二者各有利弊,在民主的基础上因具体形势的不同而又在实践中所取舍,方能达到最优的财政和预算管理效果。
二、从预算实践看预算思想
在量入为出和量出制入的预算原则的指导下,历代的财政官员在编制财政预算、制定政府收支政策的具体实践中,也有值得当代学习和借鉴的思想。
(一)强调财政平衡、收支有度
自古以来,儒生便把《礼记》中的“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作为管理国家的先行条件,治国之道亦是从治生之学中演化而来。孟子的恒产论开辟了治生之学中“平衡、有度”的理论先河,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按照孟子的设想,每一家都有刚好能够使每个家庭成员“无饥”的财产,就能够使君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当每家每户都能有稳定的收入,则“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国家财政就有了稳定的保证。
秦汉之后,治国思想逐渐从治生思想中独立出来,才有了相对成形的财政观念。汉成帝时期,刘向针对当时赋敛繁多的问题,以“楚人献鱼”的典故表明国家不应一味追求国库充盈,而应使财政平衡、让利于民。他引用楚王的话:“盖闻囷仓粟有余者,国有饿民;后宫多幽女者,下民多旷夫;余衍之蓄,聚于府库者,境内多贫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庖有肥鱼,厩有肥马,民有饿色,是以亡国之君,藏于府库”,劝解皇帝要轻徭薄赋,使财政张弛有度。东汉末年,曹操提出了“他不得擅兴发”,亦是对财政的度的控制。
魏晋时期,傅玄对于财政平衡、收支有度的问题,提出了“有常”“至平”和“积俭趋公”三个基本原则[2]。其中,“有常”指的是“上不兴非常之赋,下不进非常之贡”,也就是说,财政收入应该是按照计划好的数量去征收,中央不额外增添附加税费,地方也不能在定额以外另行征收。并且应效仿周朝订立“典”来规范国家财政,“役简赋轻则奉上之礼宜崇,国家之制宜备,此周公所以定六典也。”从预算的角度来看,傅玄的这种“有常”的思想与现代的增量预算较为相似,都是强调财政预算的稳定,使经济平稳发展。
元初,耶律楚材在财政问题上提倡收支有度、抵制任意摊派。由于统一中原后财政机构机制尚不健全,出现了“州郡长吏,生杀任情,至孥人妻女,取货财,兼土田,燕蓟留后长官石抹咸得卜尤贪暴,杀人盈市”的现象,耶律楚材“即入奏,请禁州郡,非奉玺书,不得擅征发”,从而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贪暴之风”。元太宗即位后,一些大臣认为蒙古国应以牧业作为主要产业,“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认为中原保持其原有经济结构才能够给国家创造稳定的收入,“财用所出,宜存恤其民”,不允许“擅行科差”。耶律楚材的财政思想,不仅仅因地制宜,并且还体现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具有时代的先进性。
(二)区别国家财政和皇室财政
西汉初,政府的经费收支与皇室的经费收支实行“分灶吃饭”,其目的在于保证国民经济的运行免受皇权的干预,实质是限制皇权。虽然在实际操作中二者很难区分,但思想家和官员们通过财政来限制王权的努力是不可被否认的。
唐初国家财政由太府主管,贮于左藏库,尚书比部负责稽核,而皇室财政则由中官管理,贮于大盈内库。杨炎之前,由于皇帝私欲膨胀和宦官乱政,原贮于左藏库的国家财政收入被归入大盈内库,国家财政完全由皇帝及宦官掌控。杨炎出任宰相后上书唐德宗:“夫财赋,邦国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焉。是以前代历选重臣主之,犹惧不集,往往覆败,大计一失,则天下动摇。先朝权制,中人领其职,以五尺宦竖操邦之本,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则无以计天下利害,……请出之以归有司。”他痛陈利害得到唐德宗批准,此后“凡财赋皆归左藏库,一用旧式,每岁于数中量进三五十万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数闻。”
丘浚也提出了限制皇室开支的措施。他主张将财政收支管理分为内外二府,“外府贮常赋所入,如秋粮、夏税及折粮、银钞、绢帛之属以待军国之用,岁终计其用度之余别为贮处,以备水旱兵火不测之需;内府则贮凡天下坑冶、赃罚、门摊之属以待宫室、衣车、赐予、燕好之费,岁终则计其有余者别储,以备他年之不足,及外府或有不给则以济之。”内外二府的库藏不仅用途各异,流通路径也不一致,“夫外府有不足则可取之于内,内府则常为撙节,使不至于不足,虽有不足亦不可取之于外。”丘浚认为,国家的财政支出需求应该被放在第一位,“军国之需决不可无”,而皇室开支是满足私欲的,是“可以有可以无故也”,因而“断不可以军国之储以为私奉之用。”丘浚的思想,不再是单纯的以国家来供养皇室,而是区分了轻重先后,即先有国家后有皇室,无论是从财政管理的角度,还是限制皇权的角度,较之过往的思想家都更加先进。
(三)决算思想
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总结。在近代以前,由于预算体系本身不健全,因而也谈不上有科学的决算制度。但是,财政并不是一个定性的政府行为,而是由实实在在的数字所反映的,因而古时虽无决算之名,但已有决算之实。一如预算起于周,会计制度也始于周。此时的决算有两种职能:一是作为官员绩效考核的依据,如《周礼》记载:“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致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二是作为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总结,由“司会”下辖的“职币”掌管,“职币掌式法,以敛官府、都鄙与凡用邦财者之币。振掌事者之余财,皆辨其物而奠其录,以书楬之,以诏上之小用赐予。岁终,则会其出。”每月、每年都要进行结算,“以周知四国之治”,范围很宽泛,包括“膳夫”、“庖人”、“酒正”、“外府”、“司裘”等,通常是“岁终则会”,但是也有例外,就是“唯王及后、世子不会”。
秦时,商鞅将决算涵盖的信息进一步细化,他认为“强国知十三数: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这里的十三数不仅仅包括了财政所直接管理的收支之数,还包括了统计经济信息。商鞅的观点不仅推动了决算事项的发展,也使中国古代的统计制度有了理论基础。
西汉初年,张苍出任“计相”,主管上计事务。张苍将算术思想应用于上计之中,史载“苍明习天下图书,善用算术,故命以列侯居相府主郡国上计也。”可以推断出,此时的决算就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登记造册,而是可以通过计算使财政绩效指标化。约七百年后,刘晏将财政决算从思想和实践上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刘晏推行的常平法,实际是建立一个经济情报网,亦可称为经济信息系统。
南宋时,郑伯谦所著的《太平经国之书》主张“不独考其国之财,亦将以并考天下之财”,以决算“计用度之当否”,郑伯谦提出“职内掌邦之赋入”“职岁掌邦之赋出”,由“职内”和“职岁”分别管理财政收入和支出的账务,而由“职币”负责掌管“币”。他认为如果财政收支由同一个部门管理,“不惟不免于奸欺,而内外参差不齐,出入之变交错差并,薄书会计之繁多委轧,亦必将有敝其精神,而络其思虑者。”收支分离则可以防止舞弊,并提高效率。“纠察钩考之势得以行于诸府之中,事不至于欺伪,用不至于没,数不至于亏耗。”郑伯谦对财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洞若观火,对于当世的财政工作亦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明清时期,丘浚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首先,丘浚指出明朝废相后“以户部掌天下户口、田土、钱粮,然散属诸司”,导致“兼厘众务,事多端而职不专”,所以提出“如古计相制,于户部卿、佐之外添设尚书一员专总国计,凡内外仓库之储、远近漕挽之宜咸在所司,稽岁计之出入,审物产之丰约,权货币之轻重,敛散支,调通融,干转一切。”丘浚察觉到户部在专制制度下无法独立行使监督和限制财政收支的职能,必须设置专门的预决算机构,严格限制财政开支,“凡所以用度取予一付于九式之成法,故虽一尺之帛、一束之刍、一饮食之微、一燕好之私而皆不得以过差焉,是以上之人侈心有所惮而不生,欲心有所节而不纵。”其次,丘浚还提出了具体的财政预决算对象,“凡天下秋粮、夏税、户口、盐钞及商税、门摊、茶盐、抽分、坑冶之类租额年课,每岁起运存留及供给边方数目一一开具,与夫每岁祭祀、修造、供给等费,通以一年岁计出入最多者为准,总计其数凡有几何,一年之内所出之数比所入之数或有余或不足或适均称。”最后,丘浚也强调财政与审计职务相分离,“司会掌钩考、司书掌书记,二者之职交相参互”,这样便能够“防有司之奸欺也。”后来民国卫挺生所提出的超然主计制度最核心的思想也是审计对财政收支进行稽查审核,“明清以降,计政与财政和而不分,故虽严刑峻法,而仍不能防止官吏之贪污私营。……为防止超然主计人员之玩忽职掌,或串通机关长官或其所属人员共同舞弊起见,并应采用就地审计制度。”
黄遵宪在将日本预算制度引入中国的同时,相应地也引入了决算制度。他给决算的定义是“及其支用已毕,又计一岁之出,某项费若干、某款费若干、亦一一普告于众,名曰决算”。为了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更需要对财政精打细算,故“通筹统计势不得不尔”。具体而言,首先应完善审计制度,“分别朝廷之上计,州县之留支,核需用之额明取之,即举应用之款实销之”。为了使决算被百姓所接受,政府应该做到财政公开透明,“列所用之数公布之,以惰庶政,以普美利,以昭大信,……书其贰行,悬之象魏,使庶民咸知。”财政透明可以提高百姓对财政的参与度,“深信吾君吾上无聚敛之患,凡所以取吾财者举以衣食我,安宅我,干城我,则争先恐后以纳租税矣”,最终“君民相亲,上下和乐”,实现周朝时的太平盛世。
三、结 论
中国预算制度起于先人创立国家之时在财政活动中的实践摸索,其后的思想家和执政者不断总结,并在理论上进行创新,再在实践中进行检验。这样反复的试验最终形成了一套与中国传统哲学及现实生产力相匹配的财政预算思想体系。
中国古代预算思想的核心是“礼”,“礼”要求政府和君王的行为要符合社会的道德准则、遵守社会的运行秩序,因而不可以进行奢靡的消费,也不可以过度征税、剥夺百姓的生产生活权利。无论是量入为出思想还是量出制入思想,其根本的出发点都是限制君王支出,实现轻徭薄赋。
相比西方以“法”为核心的预算思想,中国的预算思想更强调道德。与其用君王制定的法律来约束君王自己,使用道德手段更能限制君王的行为。因为如果君王违背社会公认的道德,铺张浪费、奢靡享受,百姓就会失去对他的尊重和敬畏,就必然会被推翻。这种反对铺张浪费的道德准则,是由中国农业社会的生产积累慢、劳动收获少、百姓生活不易的性质决定的。当代执政者在编制和执行国家预算时,应坚持传统思想中的精华,每一分财政支出都应实实在在地作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民生,并在注重效益的同时兼顾节俭。此外,预算不能对没有效益的空头账户置之不理,亦不能助长政府敛财行为,而应以监督控制财政为目的,以保障民生为根本,让政府真正成为“守夜人”。
但是,基于“礼”的预算思想也有其本身的不足。一方面,君王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其权力远大于道德的软约束,只有自身具有杰出道德修养的贤君、明君才会接受以“礼”为基础的预算,昏君、暴君则完全可以突破道德约束、践踏财政预算。因此,唯有更强有力的约束,也就是以民主政治为制成的“法”,才能够制约君主权力、限制君主行为。另一方面,传统预算的编制受限于落后的科学技术,上下级之间、区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且由于统计手段原始,预算编制的精确性也较差。先人虽提出了一些改进的观点,也有过相应的尝试,但多没有能够延续下去。因此,当代政府在开展财政预算工作时,首先,应制定完善的预算法律,更重要的是在编制和执行预算以及进行决算时,须一切在法律的规范下进行,绝不能跨过法律的红线。其次,预算应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编制,不仅仅是采用科技手段,还应树立严谨、科学的预算工作作风,杜绝经验主义。最后,预算需对百姓公开,接受百姓和媒体的监督。公开不能只是一个形式,而应该在不损害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将预算公开细节化、可理解化,并明确相关责任人,使预算的全过程在阳光下执行。
注释:
①《论语·学而第一》。
② 《论语·八佾第三》。
③ 《左传·襄公二十八》。
④ 《荀子·富国》。
⑤ 《淮南子·诠言训》。
⑥ 《张太岳文集·卷十五》。
⑦ 《蒹葭堂杂著摘抄》。
⑧ 《史记货殖列传今义》。
⑨ 《均节赋税恤百姓·其二》。
⑩ 《均节赋税恤百姓·其二》。
[1] 江苏省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编写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一辑上册)[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183.
[2] 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二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902.
[3] 孙文学.中国财政思想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4] 刑铁.我国古代专制集权体制下的财政预算和决算[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4):92-100.
[5] 陈光焱.中国预算制度的历史变迁与现今改革[J].地方财政研究,2008,(5):59-63.
[6] 王军.中国财政制度变迁与思想演进[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兰桂杰)
2016-11-06
舒丽娟(1976-),女,贵州开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研究。E-mail:shulijuan@sina.com付志宇(1977-),男,贵州遵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后,主要从事财政税收学与经济思想史研究。E-mail:fuzhiyu1234@263.net
F092
A
1008-4096(2017)02-0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