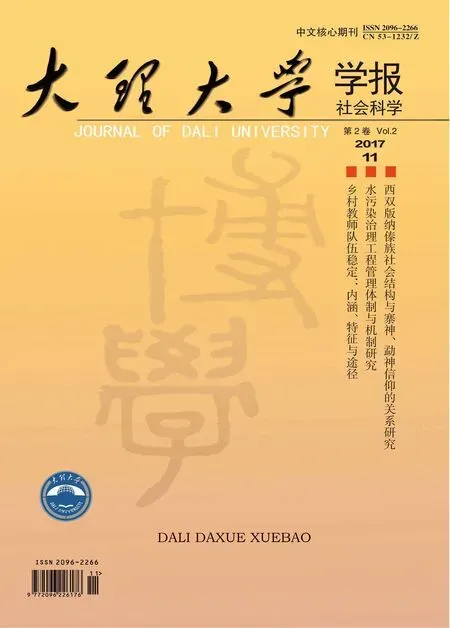清中叶知识分子的寂寞与骚动
戴红宇
(三明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福建三明 365007)
清中叶知识分子的寂寞与骚动
戴红宇
(三明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福建三明 365007)
清中叶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总结期,这一时期的学界、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学问都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清王朝在君权专制上的登峰造极必然影响到知识分子对学问的态度,此外,明清之际的实学运动也对此时的学界影响深刻。在那个时代,思想家已然淡出,经历着历史上的低谷,学问家正在崛起,构筑历史上的巅峰。曾经鼎盛一时的乾嘉学派必然有其特殊之处,然而它的迅速覆灭也不得不引起知识界的深思。
道统;知识分子;义理
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与西方学术界所认定的具有特殊涵义的中国传统概念则是“士”。笔者之所以没有用“士”,而用“知识分子”的概念,是清中叶大部分的学者并没有达到传统意义上的“士”的境界;相反的,随着宋朝以后“智识主义”的兴起,清中叶的学者们更具有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些特征。乃至有人认为,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就是脱胎于清中叶的学者〔1〕。暂且不论这个观点的确切与否,清朝中叶确实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一段历史。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这个时期都是我国古代一切传统的积淀,这种积淀要么登峰造极,要么尘埃落定。
一、君权与绅权
中国的封建史同时也是一个君权不断集中膨胀的过程,相对于处于直接对抗、矛盾激烈的君权与相权的争斗而言,君权与绅权的斗争则处于较为隐蔽和柔和的状态下。并且在事实上,力图打压地方士绅豪强以达到中央集权的努力,往往以失败告终。传统的文官制度必然意味着王朝权利无法触及到各个方面,民间社会的实际权利往往掌控在地方士绅手中。清朝定鼎中原后,一度极力地打压士绅阶层,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尽管学术界普遍承认缙绅阶层作为一个独立阶层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但是对于缙绅阶层的主要构成却存在较大的争议。这种争议的存在,就不得不对清朝,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以前的清朝士绅作一番探讨。换言之,清朝中前期的缙绅构成与其他封建王朝的缙绅构成有着较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的确是存在的,其显著特征就是清朝的缙绅是以是否取得行政职务为标准〔2〕。以知识或功名作为主要标准的士在这个时期已然被排除在缙绅阶层之外,除非他获得了行政职务。韦伯曾说:“中国的社会阶级决定于任官资格者,远较于财富者为多。”事实上,尽管这个时候的读书人仍然接受的是获得官职的训练,但是相较于严格而不封闭的官僚系统,数目庞大的读书人能够获得官职的实在少之又少。高中进士,仍无法担任实际官职的读书人不乏其数;同时清朝中前期严苛的政治制度也使得许多获得官职的读书人或革职或革名或流放或被杀;而愈演愈烈的“文字狱”更是将数以万计的读书人牵扯其中。然而,或多或少地受到明末知识分子党争影响的读书人,已然无法团结起来——也无法与掌握经济优势的地主团结起来,去争取原有的地位。雍正皇帝的一些改革措施,也大大地打击了传统士绅阶级——其中包括明太祖朱元璋给予士绅免于参加徭役的特权。事实上,中国历史一直有着打击士绅与拥护士绅的两大政治派系的反复斗争,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等都在抑制士绅问题上遇到了巨大挑战。在封建王权高度集中的清朝中叶,雍正皇帝的这一举措虽然也遭到了部分士绅官员(大致等同于士大夫)和地方士绅的反对,但结果无疑是君权获得了胜利。宋明两朝风起云涌的士绅阶层,在此时已销声匿迹;教化权利被官僚政治和长老政治瓜分殆尽〔3〕。可以说,在这一场争斗中,君权取得了绝对的胜利。
在“有其一以慢其二”(《孟子·公孙丑下》)清朝中上层社会,读书人自然不可能再有“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上》)他们在失去政治上的便利的同时,也失去了其作为平民阶层道德标杆的士绅功能——暂且不论这种道德标杆的真实性。然而,与其说是被清政府剥夺了,还不如说是读书人自己放弃了自己跻身于士绅阶层的社会地位。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特权后,读书人已经不能等同于士,也不能等同于士绅了。他们要么匍匐在新政权的脚下,要么逐渐地适应冷板凳。清中叶学者的一个显著特征——为学术而学术开始显现出来,就如同当时的教育是为了科举一样。为学术而学术固然可以看作是在追求学术的内在目的,同时也是个自我教育的过程,然则换言之就是,当时的学者不再以教育他人为目的——教育局限于有限的师生关系中,而不再承担社会教育的重任。
士绅阶层的衰弱固然是政府愿意看到的局面,却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同时,士绅的社会功能包括行政的、文化的、道义的衰微,也对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社会风气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从今天来看,这种影响在较大层面上具有积极意义,譬如打破了文化垄断、解放了社会观念,在这一过程中,清政府将原来属于士绅的社会教育权利也剥夺过来。然而对于当时的社会,尤其是市民社会而言,则是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生产方式相表里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肆意发展。譬如“人欲”在当时受到的普遍讨论和一定程度上的肯定,就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当时知识分子对不断膨胀的“人欲”的一种省思。
二、政统与道统
王夫之有言:“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4〕治统亦即政统。春秋战国时期,道与政出现分野;秦王朝明火执仗地打压“道”,最终二世而亡。承嗣了大一统格局的汉王朝不得不改变文教政策,于是树立了一个道统,并且试图给道统一个次于政统的官方地位——尽管代表道统的士阶层没有承认。此后历代王朝相因沿革,政统与道统也一直处于相互利用、若即若离的态势。因此,士依然“根据‘道’的标准来批评政治、社会”〔5〕;帝王可以给予孔子、孟子等人封号,却不能代表道统。事实上,也很少有帝王乐衷于将政统与道统紧密地结合在自己的手中,亦即帝王本身代表了政统与道统。第一个这么做的,是没读过几本书的朱元璋。然而明朝后继的君王,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去使得自己以代表政统与道统的结合体出现,因此终明一朝,道统的发言权依然掌握在或在庙堂或在乡野的士(知识分子、读书人)手中〔6〕,掌握着道统发言权的士人或明或暗地向统治核心表达着不满与抗议。道统依然借助着它的代言人与政统龃龉。无论是西汉的讳谶之学、魏晋的玄学,还是两宋的理学,事实上都是通过“道统”反抗、制约日益膨胀的政治权威的努力。
当然,明朝并非没有道统之争,亦即士人内部对掌握发言权的争斗——而这种争斗最终的反应形式是掌权派的士人与非掌权派的士人(包括在野及非权力中心的官员)之间的争斗。显然,这种争斗的影响是负面的,学术上明末理学、心学都流于清谈、狂禅;政治上则争权误国。因此,明末清初之际才会出现顾炎武所说的“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实学”运动,也在此时开启了新一轮的古文运动。事实上,清朝中前期学术界的风气都是在此时奠定的。然则,顾炎武等人提出的“实学”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丰富的内涵,而清朝中叶学术界的“实学”仅仅是实证方法的不断发展,乃至登峰造极,而忽略了“实学”面向实际的这一点〔7〕。
清朝是少数民族入关,对中原文化既景仰又恐惧、既利用又防范。在政权巩固之后,清王朝的统治者们开始着手将政统与道统都收归自己所有。无论是以“理学大师”自居的清圣祖、热衷于佛学的清世宗、还是学术不精却屡批程朱的清高宗〔8〕9,都牢牢把握着道统代言人的地位。学术与教育,都不得不受政治的摆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失去了自由,学术和教育失去了自由,道统也失去了自由。换言之,这个时期的政统与道统处于高度、紧密集中的状态。诚然,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除了封建王朝一贯的利益诱惑之外,在迫使汉族士人交出“道统”的过程中,清王朝通过一场一场的“文字狱”,让汉族士人不敢对清王朝的统治加以议论。甚至在乾隆中期,由于感觉到知识分子的势力有所抬头,乾隆皇帝族杀李光地一个官至广西巡抚的学生以杀鸡儆猴①此例笔者曾在相关书籍见过,仅凭记忆,不知具体姓名。诚望告知。。事实上,是政治权威大大地压过了道德权威,正如清世宗所说:“使孔、孟当日得位行道,惟自尽其臣子之常经,岂有韦布儒生要自做皇帝之理。”(《大义觉迷录》卷二)
的确,历史上也少有要“自做皇帝”的儒生,然而“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呻吟语·卷一》)的优渥似乎也在此时荡然无存了。相对于明朝理学与心学之间的“道统”之争,清中叶由于哲学上的停滞与消极,也没有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过较大的争论。尽管还有“宋学”与“汉学”之争,“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但已经离我们所说的相对于“政统”而言的“道统”很远了。不再代表“道”的知识分子,其著述内容是十分有限的,教育内容也是十分有限的。普通民众显然无法理解,也不需要他们此时的一些教育;另一方面,也很难说清中叶的学者们在教育民众上下过多少工夫。故而,道统在这段时间里既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也没有以其应有的形式存在;道统与政统之争在此时告一段落了。
三、一个阶层的解体与一个群体的形成
严苛的科考制度、按部就班的官员升迁、庞杂的八旗贵戚功勋,使得读书与任官之间的联系不再如以往那么紧密;与此同时,绅权的削弱和捐官制度的日益公开,也使得读书人的社会地位逐渐下降。另一方面,随着以实证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汉学(考据学)鼎盛一时,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者,事也”的形象相去甚远。大约在康熙年间,出现了以阎若璩、毛奇龄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为学问而学问的专门人才。这几乎成了整个清中叶学界的基调。在这个时期仅有的几次较大的学术辩论,不是儒家素来争论的义利、华夷、心性,而是集中在对古书的辨伪、对典籍中字词的解释等等。这样的讨论现实意义显然没有那么大,相反的,更具有现当代学术讨论的意味。对于纯粹学术的讨论,可以在学术上越来越深入,却也可能离现实越来越远。中国素来没有两个世界,只有一个世界;所以中国的士人一开始便是这个世界的“公共知识分子”,即便在更多的时候,是寄生于政治的,不过那样只是为了更好地面向现实生活的公共领域,从而依据自己对圣贤提出的理想社会的理解而改造现实社会。唯有此时的知识分子不是。
如果说李光地、陈梦雷等人进入政坛还能说明清初知识分子与现世生活有着较紧密的联系,那么在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积淀后,乾隆朝已经可以大胆地不依靠汉族士绅、极力排斥汉族知识分子了;如果说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还是或明或暗地向以《大禹谟》为理论依据的心学提出挑战,那么由于在理论上的空虚,钱大昕等人在哲学上的造诣已然执迷于末流。在清中叶,大部分学者都把毕生的精力放在对典籍疏注的整理、辨析、解释上,这诚然对古代典籍的保护和恢复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也使得中国传统的哲学在这一时期出现断层。另一方面,“禁书”自秦始皇开始则有,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愈演愈烈,在清朝中叶登峰造极。《四库全书》的编纂,同时也是“寓禁于征”,在对古代书籍进行整理、分类、保存的过程中,也毁禁了许多有“违碍字迹”的书籍〔8〕35。
我们不能不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上,士人要获得个体人格的自由和批判精神的突显往往要从统治阶级中剥离出来;另一方面,士人在统治阶级中获得的物质与精神赏赐往往是以牺牲独立性而获得的。在清中叶时,汉学已经全面战胜了宋学,然而也仅仅止步于此。此时的官方已有对汉学、宋学进行调和式的评判。当然,这种评判仍然是以宋明理学为主,因为宋明理学是统治阶级赖以维持统治秩序的工具,而汉学仅仅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的一种学术范式。这种缺乏坚厚的理论基础的学术研究范式,自然不可能有太大的影响力——既不足以影响君主的统治,也不足以影响百姓的生活。在所谓的太平盛世,他们不得不“既明且哲”地缄口默言。
周作人尝言,中国人在思想上只有一个阶级①语见周作人《爆竹》。。尽管我们一直理解当时的知识分子十年寒窗、冷板凳、故纸堆,事实上,他们也同时享受着俗世的安逸生活。最为典型的,要数袁枚的随园;次者,纪昀、钱大昕、章学诚等人也是生活优越;即便是戴震这样的,家无余财、又未能金榜题名者,不过他因为能够践行“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的教诲,也不至于穷困潦倒。经过明代的熏染,人们普遍认为甘于清苦往往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操守,一个要走向“公共知识分子”的人必须要经历物质上的贫匮〔9〕。当时的很多学者不能做到,今天就更少了。生活上的差异,包括学术思想上的冲突,必然导致当时的知识分子不能形成所谓的“场域”,事实上笔者认为,中国的士人从来没有形成过“场域”,尽管他们可能沿袭着某几种固有的思维模式和道德理想,却缺乏共事的可能。
知识分子远离现世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既有统治阶级的排斥,也有自身能力的欠缺,更因为自我意识的衰退。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都有人对这一阶段执迷于书斋冷板凳,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代替了“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尖刻的批评。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已经不能称之为士大夫了。他们既没有“士者,事也”,也没有切实地争取好好地做一个“大夫”。与政治生活的远离,标明着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在此时不复存在。代之而兴的,是知识分子这一群体。近来人们喜欢用“学人集团”这个词,笔者觉得并不确切。相对于汉朝的李固之党②具体参看《汉书·党锢列传》。、宋朝的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党争、明朝的东林书院,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普遍性,即实证方法的流行,然而不仅没有在政治上形成力量,也没有在社会风气上形成力量。相反地,知识分子只是以三三两两的形式互相探讨学术,或者排挤其他知识分子。因此,笔者更倾向于称之为知识分子群体。虽然其中绝大部分还是儒家学者,但是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家,因为儒家是要求士人积极投身现实社会,通过教化改造现世生活的。
愈发走向故纸堆的清中叶的学者们,离具体的事就越远,而离传统意义上的士也越远。与此同时,被排斥在统治中心之外的学者们,也远不能冠以大夫的头衔。文化上的辉煌与政治上的辉煌,并不像大家所理解的那样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政府的行政人员有较大部分是通过科举而获得官职的,但是科举的成功绝不等同于文化的高度;反之亦然。
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对我国传统学术的总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固然,乾嘉学人的工作不能看作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开端,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乾嘉学人标志着我国纯粹学者的出现,即不以“仕”和“事”为主要目的,而是以学术而学术的治学态度。但是由于没有同一的期许,因此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被社会广泛接受。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学人的研究侧重于方法、在哲学上缺乏坚实的基础——尽管在学术上对后世,尤其是民国初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它也在19世纪前期迅速走向衰落。
四、谁是“轿中人”
戴震曾言:“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升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余英时曾对这句话有过很精彩的演绎〔10〕。学界尽管对戴震的研究不多,但是对这句话也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见解,即“轿中人”是指他的《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书。东原曾在其给弟子段玉裁的信中说道:“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做。”〔11〕
显然,《疏证》所要论述的正是当时学界匮乏的“义理”之学。在戴震的书中,他一再强调“血气心知”和“遂欲达情”,并以此抨击当时作为统治基础的“理”。这本身就是对现实生活中,随着生产日益繁荣而普遍流行的“人欲”的肯定。袁枚对于“人欲”也有过相当丰富的论述,他和戴震一样,都试图从价值观念方面对当时桎梏人的思想行为的“礼教”进行反抗。然而在“朴学”盛行的乾嘉年间,“义理”之学却是被鄙弃的。袁枚的“千秋万世必有知我者”固然可以理解为其对自身学问的自信,但也无不包含着当时的寂寞。戴震又何尝不是呢?
仅仅从学术上来说,中国自汉至清,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一言以蔽之,经学而已。只不过各朝各代对“经”的态度、治“经”的方法、用“经”的手段各有侧重、互为长短罢了。两汉重视古文经学,强调其微言大义;魏晋则侃侃清谈,儒道贯通;唐朝则注疏、集注,正式奠定“十三经”的官学地位;宋明则理学、心学大盛,强调养心、持静、无欲;清代则以训诂、考据来反对宋儒、重振汉学。然而,维系这些的“义理”之学才是中国文化真正的精髓所在,并且才是使得一直以来中国士人(知识分子)的地位普遍较高的关键所在。这种社会地位不正是来源于范仲淹笔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不正是来源于对现实世界的关怀和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吗?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程朱的“理”、陆王的“心”、乃至顾炎武的“经学济理学之穷”,都是在“义理”上进行阐述。“义理”上的论述,虽然往往是纯粹哲学的,但却有着更为深刻和长远的现实意义。它所表明的,是士人对理想社会的认识,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它既是知识的生命力,也是士人的生命力,更是中华文化的生命力。
教育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再生,或多或少地承载着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同时也承载着“义理”的生命力。相应的,“义理”往往是最能体现教育的活力和教育的精神。失去了“义理”的学术,变得黯淡;同样的,失去了“义理”的教育,流于空疏。在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变革,无不是以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变革为先驱;而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往往要比政治、经济上的发展更为深刻和久远。义理之学不仅仅是戴震学问中的“轿中人”,也是中国文化中的“轿中人”。然而在那个时代,思想家已然淡出、经历着历史上的低谷,学问家正在崛起、构筑历史上的巅峰。
显然,“博杂而无系统的学问”“不在道术本身下手,而在著作及解经方面挑剔”〔12〕的乾嘉汉学缺乏义理上的支撑——既缺乏对现世生活的深刻认识,也缺乏对理想世界的执着追求。虽然当时的知识分子参与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以及其他丰富的论述对于纯粹学术的发展和古典书籍的整理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他们在全力打压“宋学”的过程中的确将“汉学”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便他们在享受社会上的骚动时也忍受着文化上的寂寞,但是他们的一页终究还是无可避免地翻过去了。当他们无不得意地在《明史》上只留下《儒林传》,而不再并列《道学传》的时候,或许不曾想到他们的学问和清王朝一样,迅速地衰落了……
〔1〕山口久和.中国近世末期城市知识分子的变貌:探求中国近代学术知识的萌芽〔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6(1):8-17.
〔2〕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9.
〔3〕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13.
〔4〕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479.
〔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07.
〔6〕王家范.晚明江南士大夫的历史命运〔J〕.史林,1987(2):29-39.
〔7〕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08.
〔8〕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派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9〕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1.
〔10〕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生活〔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03.
〔11〕戴震.孟子字义疏证〔M〕.何文光,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2:4.
〔12〕梁启超.儒家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97.
(责任编辑 杨朝霞)
The Loneliness and Disturbance of Intelligentsia in Mid-Qing Dynasty
Dai Hongyu
(College of Artistic Designing,Sanming University,Sanming,Fujian 365007,China)
Mid-Qing dynastyis a summary stage of Chinese ancient culture.During this period,scholars,intellectuals,and their works showed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from the past.The peak of monarchical tyranny in the Qing Dynasty inevitably impacted on the intellectuals'attitudes towards knowledge.Besides,the campaign of practical knowledg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scholars as well.At that time,thinkers faded out and reached their low ebb in history,whereas the scholars were on the rise and reached their peak.Qian-Jia School which had a period of prime must had been extraordinary,but its complete and sudden collapse should cause deep reflection among intelligentsia.
Confucian orthodoxy;intelligentsia;doctrine
G40-09
A
2096-2266(2017)11-0067-06
10.3969 ∕j.issn.2096-2266.2017.11.013
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明清实学的教育内涵研究”(JAS170470);三明学院科学研究发展基金项目“明清实学的教育内涵研究”(A201718)
2017-05-19
2017-09-15
戴红宇,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