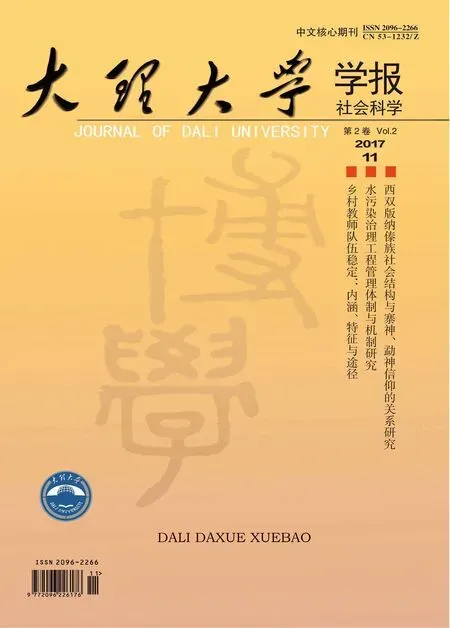历史人类学视野下拉祜族“阔塔节”仪式的融合与变迁
——以班利村和撒拉科小寨为例
项露林,寸锡彦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昆明 650000)
历史人类学视野下拉祜族“阔塔节”仪式的融合与变迁
——以班利村和撒拉科小寨为例
项露林,寸锡彦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昆明 650000)
从历史人类学角度来看,拉祜族“阔塔节”仪式经历了长时期的融合与变迁。在分析班利村和撒拉科小寨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揭示了如下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与撒拉科小寨一直笃信山神“厄莎”不同,班利村在20世纪完成了外来基督教信仰与“厄莎”信仰的融合,并由此导致二者在祭神仪式及文化象征上的显著差别;第二,“洗手擦脸”仪式凸显了以孝善价值观为主体的社会文化意义,而“抢新水”仪式的消失则证实社会经济发展对传统文化象征的破坏性作用,并且随着时代发展这种破坏将日益扩大。
拉祜族;阔塔节;仪式;融合变迁;文化象征
节日被人类学家认为是展示族群社会生活和文化意义的集中时刻,嵌入其中的一系列或简或繁的仪式,则是分析和解读族群权利组织运行方式、社会性别关系和宗教信仰等重要问题的最佳视角之一。受特纳和范·盖内普影响,象征—结构分析法似乎成为人类学界理解仪式的固定范式,即认为仪式是结构性和反结构性行为,强调完成仪式的人们获得了某种文化意义上的身份“过渡”,并由此开始崭新的生活。人类学家的兴趣多是研究族群中已然成型的仪式,然而一个明显却未被多数人注意的事实是:族群仪式一直处在发展变化中。在漫长的仪式演变过程中,经常受到外来文化和内在传统的双重影响,在博弈与内化中最终成型,跨境边疆民族尤其如此。本文以云南省澜沧县班利村和孟连县撒拉科小寨拉祜族“阔塔节”仪式在20世纪初以来近一百年时间的演变为基础,以口述史资料为依据①笔者及调查团队在班利村的田野调查时间为2016年2月6日至20日。调查期间,通过访谈工作组掌握了当地大量的口述史资料,成为本文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探讨跨境边疆民族传统节日仪式的融合与变迁,及由此体现的文化象征和社会意义。
一、拉祜族“阔塔节”基本程序
拉祜族是典型的跨境民族,目前集中分布在云南和东南亚泰国、缅甸等地区,在云南主要集中生活在靠近边境的澜沧、双江两县。笔者调研的主要田野点班利村即位于澜沧县东回乡,村中拉祜族群众占主体,另有少量的佤族、哈尼族和汉族群众。拉祜族有其本民族图腾——葫芦,认为祖先是从葫芦中孕育而生〔1〕。在班利村拉祜族特色民居中,屋檐下最显著的地方均能见到金色葫芦的标记。泰勒认为图腾崇拜是祖先崇拜的一种特殊形式,一般认为,就文明程度而言,祖先崇拜高于图腾崇拜,拉祜族的“葫芦”图腾即糅杂了祖先崇拜的文化象征意义,是拉祜族对祖先的集体历史记忆。传统拉祜族村寨信仰山神“厄莎”,而班利村较早受西方传教士影响,据本村牧师段三妹介绍,班利村传入基督教的时间是在1927年。经过长期演化,“厄莎”与基督信仰合而为一,主宰了班利村拉祜族民众的精神世界。具有显著特色的本民族图腾、原始民间信仰和外来基督教的融合,使班利村呈现出区别于一般拉祜族村寨的特色节日风俗,“阔塔节”就是其中的代表。阔塔节,部分学者亦称“扩塔节”,指拉祜族传统新年。拉祜族“阔塔节”的特色之处是分“大年”和“小年”,大年又称“女人年”,时间为正月初一至初四,小年又称“男人年”,时间从正月初九到十一。在拉祜族的族源传说中,由于男人外出狩猎,过年时仍未回村寨,等男人们返回村寨时年已过完,女人们为犒劳男人的辛劳,决定重新给男人们过个年。这就是拉祜族历史记忆里大年(女人年)、小年(男人年)的来历,共同的历史记忆会强化人们对族群的认同。
在调查组对班利村“阔塔节”的全时段观察和采访调查基础上,我们选取拜年活动为重点研究对象,其基本程序的叙述以报告人杨云青一家活动为主线索,附带补充其他村民的活动内容。
(一)拜年活动的准备工作
2016年2月6日(腊月二十八)晚上8时:杨云青妻子李二妹开始冲洗、浸泡糯米,糯米分白糯米、红糯米两种,为第二天舂粑粑作准备。
2月7日(腊月二十九)早上9时:杨云青、李二妹在火塘上蒸糯米,糯米熟后二人开始协作舂粑粑。粑粑舂好后分别被捏成圆形和长条形,平放于垫了松针的簸箕中。采访李二妹获悉:“圆形代表女人,长条形代表男人”;而杨云青则告之:“圆形代表太阳,长条形代表月亮”①访谈对象:杨云青、李二妹。访谈时间:2016年2月6日,访谈地点:班利村杨云青家。访谈人:项露林。。腊月二十九是舂粑粑的时间节点,调查组就这一问题采访了许多村民,发现男人、女人各有一套说辞,且与杨氏夫妻别无二致。可见拉祜族男人、女人关于粑粑形状意义的说法是经过长期沉淀之后约定俗成的,其原因可能是男人、女人不同的性别及承担的社会角色差异导致的。中午12时,杨云青、李二妹驱车前往邻县孟连年货市场采购一批年货,晚上6时回班利村。
(二)拜年活动的进行过程
2月8日(正月初一)早上7时:李二妹凌晨起床打开自来水龙头接了新年第一壶水,放在火塘上面烧开灌入暖瓶存好。此时天微微亮,然而不少村民已经出门,只见一家老小,浩浩荡荡七八人,手提暖水瓶,带有毛巾、脸盆、肥皂,径直往前。一行人走到一户拉祜族民居前,为首一人掷出一串点燃的鞭炮,顿时“噼啪“作响,大家走入屋中,一对老年夫妇已坐于火塘边烤火,见人来眉开眼笑。进屋的中年妇女放下脸盆,倒入暖水瓶中热水,兑入适量冷水,给老人手上打上肥皂,洗手;打湿毛巾,擦脸。双方握手寒暄一阵,老人说了些祝福话语并以粑粑相送,如此即告结束,一行人又前往另一家。天已大亮,村中一波一波行人穿梭,均是如此。“拜年”活动中晚辈向长辈拜年占多数,他们之间的关系或为本家亲戚,亦或是村邻。在村中百岁老人家里,前来为老人洗手擦脸之晚辈络绎不绝。老人孙女说:“村民们普遍认为,给年长的老人拜年能够给自己带来福气”②访谈对象:百岁老人孙女。访谈时间:2016年2月13日,访谈地点:班利村百岁老人家。访谈人:项露林。。而在老人自身看来,“过年来拜年的,表示得到丰收,来感谢老人”③访谈对象:百岁老人。访谈时间:2016年2月14日,访谈地点:班利村百岁老人家。访谈人:张锦鹏。。
上午9时左右,杨云青携妻儿驱车前往位于孟连县景信乡撒拉科小寨的岳父家,车上装有粑粑、雪碧等礼物,还有早晨灌满热水的开水瓶和毛巾等。撒拉科小寨是一座位于半山腰的传统拉祜族村寨。李二妹到家后,以同样的方式为父亲洗手擦脸。该村寨拉祜族笃信山神“厄莎”,与信仰基督教的班利村有较大差别,且初一正午村民将举行祭祀山神“厄莎”的仪式。正午12时,一队队的村民吹着芦笙、敲着铜镲、拍打着象脚鼓往村后山上走去,到达山腰一处用竹篱笆隔开的祭祀地。祭祀台上供奉着堆成小山的粑粑,一位慈祥长者(即卡些)手执葫芦,用所盛之水为前来的村民将手中的纱线打湿,村民将纱线缠绕在手臂上④据了解,初一早晨晚辈为长辈“洗手擦脸”后,长辈将纱线系于晚辈手腕处表达祝福。,后每位朝拜山神“厄莎”的村民都会喝一口葫芦中的清水。据卡些说:“这是‘厄莎’充满爱心的福水,喝了之后能得到‘厄莎’的保护,消灾避祸,百事顺心。”⑤访谈对象:撒拉科小寨长老。访谈时间:2016年2月8日,访谈地点:撒拉科小寨祭祀场地。访谈人:项露林。与此同时,村民们吹着芦笙、敲着铜镲、拍打着象脚鼓一圈一圈地在祭祀台前跳着,庆祝着新年的到来,祈祷“厄莎”给他们带来好运。
2月9日(正月初二)早上8时:班利村村民打着富有节奏的象脚鼓,敲着铜镲,吹着芦笙,一部分人手提暖水壶、脸盆、毛巾,扶老携幼,浩浩荡荡朝村公所进发。到达村公所大院,村委会工作人员和教会牧师段三妹已排成一列,村民们排成长队依次与他们握手祝福,长至弯腰驼背的老者,幼至襁褓怀抱中的婴孩,无一遗漏。仪式结束后,村民们转场至离村公所不远的临时教堂(正式教堂在重建),在临时教堂前的大操场上,举行基督教的新年庆祝仪式。村民每户带来两个粑粑,有的还携带整箱饮料,粑粑和饮料堆在场地中央,数量甚多。在段三妹和卡些张福等人的一系列讲话仪式后,年轻村民将带来的脸盆摆在操场中央,倒上暖壶中热水,给坐成一排的老年人洗手并用毛巾擦干。随后握手祝福仪式开始。教会人员立于一侧,村中公职人员立于另一侧,以握手的形式接受村民的祝福并同样给予村民们祝福。现场班利村上千人同时行动起来,场面十分宏大和热闹。持续近一小时的仪式结束之后,村民们慢慢散去。
2月10日(正月初三)下午两点半:每年澜沧县轮流组织两个乡到县城葫芦广场拜年。调查组跟随杨云青驱车从班利村赶至澜沧县城,发现今年轮到木戛乡和雪林佤族乡派出代表队。他们穿着节日盛装,前几排打着富有节奏的象脚鼓,敲着铜镲,吹着芦笙,热闹欢腾,后几排抬着象征丰收的巨型粑粑、茶饼、年猪以及甘蔗等入场,最后数排跳着本民族的舞蹈,喊着振奋人心的号子步入葫芦广场。入场仪式结束后,按照惯例由县领导讲话,之后为献礼环节,粑粑、茶叶、年猪等被抬上舞台,随后由两个乡的代表讲话,代表各自乡向全县人民拜年。仪式结束后两个乡分成两个片区,各自在葫芦广场举行富有本民族特色的庆祝活动。
二、“阔塔节”仪式关键性节点的象征—结构分析兼历史人类学解读
总体来看,班利村拉祜族“阔塔节”拜年活动持续时间为正月初一至初三,初一村民给长辈拜年,初二村民在村公所、教堂跟村委会干部和教会人员相互拜年,初三由县里轮流组织两个乡村民在县葫芦广场举行拜年活动。在持续三天的拜年活动中,一些关键性的仪式是具有深厚的文化象征和社会意义的。
(一)祭神仪式:山神“厄莎”与耶稣信仰的融合
1927年基督教传入之前,班利村与撒拉科小寨都是传统的拉祜族村寨,信仰山神“厄莎”。“厄莎”信仰的形成是由于生存环境导致的,传统拉祜族多生活于西南边疆的连绵群山之中,村寨多位于山顶或半山腰,大山的雄伟壮丽震撼了人们的大脑,山神“厄莎”被抽象出来成为神灵,受到拉祜族膜拜。人类学家王铭铭认为民间宗教是流行在一般民众尤其是农民中间的神、祖先、鬼的信仰,庙祭、年度祭祀和生命周期仪式,血源性的家族和地域性庙宇的仪式组织,世界观和宇宙观的象征体系〔2〕。“厄莎”属于“神”的类别,是主宰拉祜族精神世界的最高神祇。撒拉科小寨半山腰的“厄莎”祭祀,成为传统拉祜族进行民间宗教活动的独特仪式,文化象征意义浓厚,此类仪式在班利村已不能见到,因此更显得弥足珍贵。一方面,小寨村民们认为“厄莎”掌管着人的生老病死一切大事,他们用浸润着“厄莎”爱心的福水打湿手腕纱线并饮用福水,吹着芦笙跳着芦笙舞,随着象脚鼓和铜镲的节奏摆动着身体,通过这些方式期望得到山神“厄莎”的保佑。另一方面,祭祀山神“厄莎”的仪式显示出极强的社会意义,仪式中卡些实现了人与“厄莎”的沟通,隐喻着其在村民中的权威和力量,展示出卡些在维护村民团结,恪守传统习俗中的作用。同时,祭祀活动以村落为单位,赋予了村落成员在行为和仪式上的权利,体现了村落作为社会互助和认同的共同体。班利村因为基督教的传入,使得“厄莎”与耶稣信仰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对这一问题,有学者认为:拉祜族在“厄莎”信仰的前提下接受了基督信仰,“厄莎”神是耶稣的父亲,“厄莎”与上帝的拉祜族化的过程中被视为同一概念,具有同等地位〔3〕。这一点在班利村三天的拜年活动中表现得很明显。在与班利村卡些张福及村民的访谈中,“厄莎”的话语位置基本被耶稣替代,与此相对应的是班利村卡些的权威也远逊于撒拉科小寨。
(二)“洗手擦脸”仪式:文化象征与社会意义的集中凸显
“洗手擦脸”,是拉祜族拜年活动中最具特色的仪式环节。前述程序中,初一村民自带暖壶、毛巾和肥皂为长辈“洗手擦脸”,初二在教堂临时操场,年轻村民也要自备上述工具为在场的老年人“洗手擦脸”。笔者在初一早上偶然光顾村中“老湖南”商店时,注意到也有村民来给店里湖南老板“洗手擦脸”,经询问老板,其表示:人家尊敬你才来给你拜年的。可见,拉祜族拜年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长辈老人。“洗手擦脸”仪式是拉祜族很久以来就有的传统,这一传统的形成早于20世纪初期基督教的传入。然而在基督信仰传入班利村后,“洗手擦脸”仪式就逐渐被基督教化了,并在圣经故事里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圣经《约翰福音》第13章1~17节有“耶稣为门徒洗脚”故事,藉此表示耶稣对信徒的关爱和劝其向善的宗旨,这与拉祜族为长敬者“洗手擦脸”形式相似,传教士便将二者结合起来,演化为拉祜族祖先给长辈“洗手擦脸”仪式实际上是上帝教导的,传承了耶稣为信徒洗脚的精神,这一解读被班利村拉祜族信徒普遍接受。“洗手擦脸”仪式的文化象征被耶稣故事的有力阐释,体现了基督教信仰与拉祜族传统的融合,并且展现出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的包容和善于本土化的特点。
比较之下,“洗手擦脸”仪式的社会意义更值得我们挖掘和重视。这一仪式是随着拉祜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孝”“善”文化发展而自然形成的。孝善观念一直为传统社会所标榜,也为当前社会大力提倡和推行。“孝老爱亲”和“友善待人”是近年来国家层面大力倡行的社会道德准则。全国、各省市和地区每年都会组织评选“孝老爱亲模范”,树立为全社会学习的榜样。“友善”更是被列入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国家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拉祜族“阔塔节”为长敬者“洗手擦脸”仪式,是对孝善价值观的最好表达和阐释。苏翠薇指出:“扩塔节是拉祜族倡导勤劳、孝道的美育场所。”〔4〕中华民族“孝道”文化源远流长,以儒家为主的“孝”文化传播也曾深入国人的骨髓。然而如今人们的价值观中“孝文化”已不似古代社会那样浓郁,且呈现出日趋淡化的势头。人们对于孝道表现出“言”重于“行”,只“言”不“行”,甚至不“言”不“行”的消极态度。究其原因只能归结为教育的缺位和榜样的缺失。俗话说:上行下效。作为个人,孝之“言、行”从小耳濡目染,父母“孝道”之表现潜移默化埋藏于子女心中,对其日后所作所为影响颇大。拉祜族为长敬者“洗手擦脸”仪式是“行”重于“言”,而且是大年初一、初二全家出动,儿孙辈群体在这场仪式中所受教益当为最大,“孝文化”如此代代相传,经久不息。关于“友善”,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也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上均是协调家庭以外人际关系的准则,通行于生人社会,影响传统社会达千年之久。近来,“老人倒地扶与不扶”社会大辩论和层出不穷的各类“碰瓷”事件,都深刻地折射出了中国当代社会百姓在道德层面的焦虑和不安。苏翠薇认为:“扩塔节是拉祜族参与聚合,团结和谐的象征。”〔4〕班利村和撒拉科小寨拉祜族对陌生人的友善是调查组在田野调查中所能够深切体会的。每至一户人家调查采访,主人会用玻璃杯倒水,搬凳子,围着火塘烤火,我们则回以几句简单的拉祜感谢话,尽管言语交流不甚通畅,但彼此间的善意仍可轻易捕捉。访谈结束,主人会用方便袋装上数个粑粑让客人带走,以此表达祝福。反观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导致危急时刻袖手旁观,对人性“本善论”的质疑体现为“怕被讹”的现实考量,是“友善”价值观在当下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这种形势下,拉祜族百姓的“孝善”行止和所体现的价值观展示出弥足珍贵的社会意义。
(三)“抢新水”仪式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解读
以班利村为例,由于地处边疆,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沿边开发开放政策影响下,村中面貌获得了极大的改观。班利村在1998年接通了自来水,村民取水难、用水安全难以保障的问题得以解决。但自来水的接通,直接对拉祜族“阔塔节”的“抢新水”仪式产生了影响。“抢新水”是拉祜族“阔塔节”庆祝的重头戏,“新水”是拜年仪式中为长敬者洗手擦脸所用之水,作为重要的准备环节,文化象征意义浓厚。村民们普遍认为,哪家接到第一桶新水,那么这一家在新的一年就会有好福气,遂有“抢新水”一说。因为村寨坐落于山腰或山顶,而水源地一般位于山谷地区,自来水接通前村民取水十分困难。调查过程中,村民为我们演示了传统“抢新水”的过程。凌晨五时左右,村中拉祜族姑娘或携葫芦,或背竹筒,开始向山谷水源地出发。山路蜿蜒曲折,坡度甚大,在一片坡地边缘,大家开始搀扶着下到坡底,辗转来到位于谷底的一眼顺竹管流淌的山泉前。姑娘们挨个用葫芦或竹筒接满水,开始往回走,顺山路返回,这一往返过程要花费大约一个小时。自来水接通前,村民每家每户都要在初一凌晨赶到山谷接取新年第一桶水,返回家中后在火塘上烧开,准备早晨给长敬者“洗手擦脸”仪式之用。苏翠薇认为:“扩塔节是拉祜族划分旧岁和新岁的节点”,也是“拉祜族追求美好事物的节点”〔4〕。“抢新水”活动正是新旧交替的重要仪式。然而,自来水的引入打破了拉祜族群众沿袭了数百年的“抢新水”传统,村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跋涉数里山路去山谷抢接新水,他们只需在大年初一的早晨拧开自家水龙头,里面流出的水即是所谓的“新水”了,并且大部分村民都认可接受了这种取水的新方式。这是典型的经济社会发展对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仪式变迁的影响个案。
三、“阔塔节”仪式和文化象征消失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前,班利村拉祜族村民务农居多,人员流动性不强。即使因婚嫁等原因发生远距离迁移,也多局限在澜沧、孟连、双江等边疆县份,因此“阔塔节”拜年仪式一般都能面对面进行。然而改革开放后,边疆地区人员流动加大,他们或在省内城市务工,亦或远赴外省,甚至与外省籍青年恋爱后婚嫁于当地,这些情况在我们的调查中较为普遍。如报告人杨云青的大儿子,年龄17岁,经朋友介绍已赴江苏无锡务工一年,过完“阔塔节”后,其还将外出务工。另外百岁老人的孙女也是因为外出务工远嫁山东,隔几年才回家过一次“阔塔节”。采访对象七组组长李扎迫,53岁,家有两儿一女,女儿已远嫁安徽十多年,基本三四年才回娘家一次。在采访十组组长时,一位自称河南南阳籍中年男子表示娶了班利村一姑娘,这次是从河南随老婆回娘家过节,因为相隔较远也是几年才来一次。由此可见,地处边疆的班利村嫁入内地省份的女青年绝不是个例,而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些身处外地的拉祜族人如何给在老家的亲戚长辈拜年也成了一个实际问题。一般而言,身在外地的拉祜族青年是隔几年回家过一次“阔塔节”,如果过节时身处外地,会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来给长辈亲友拜年。调查亦发现,班利村的座机和移动电话普及率也在逐年提升。人员的远距离流动和通信工具的现代化使得古老的拉祜族已经开始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然而电话拜年的兴起,并不能弥补时空距离造成的传统文化缺失。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元素的不断注入,班利村人员外流将不断加大,年轻人逐渐析出后势必造成古老村寨拉祜文化的断层,届时“祭神”“洗手擦脸”等等“阔塔节”仪式都将如“抢新水”一样消失不见,这些仪式所表达的文化象征也将一并不复存在。
〔1〕李进参.拉祜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27-29.
〔2〕王铭铭.社会人类学和中国研究〔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39.
〔3〕苏翠薇,刘劲荣.拉祜族厄莎信仰与基督教的互动整合〔J〕.云南社会科学,2006(1):86-89.
〔4〕苏翠薇.拉祜族扩塔节的文化内涵和当代意义〔J〕.云南社会科学,2012(5):25-28.
(责任编辑 张玉皎)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huquot;Kuotaquot;Festival from the View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Village Banli and Salake as an Example
Xiang Lulin,Cun Xiy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Archive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650000,China)
From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ical point of view,the Lahuquot;Kuotaquot;Festival has undergone a long period of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After analyzing the survey data of the villages of Banliand Salake,the following two basic facts are revealed.Firstly,different from village Salake which has a devout faith in the mountain god Esha,village Banli has perfectly integrated the worship of Esha and foreign Christian faith in the 20th century.This has led t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religious ceremonies and cultural symbols between the two villages.Secondly,the ritual ofquot;washing hands and facequot;highlight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filial piety,whereas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quot;new year waterquot;ceremony demonstrates the destructive effect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raditional cultural symbols,and this destruction will grow over time.
Lahu;quot;Kuotaquot;Festival;ceremony;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cultural symbol
C95
A
2096-2266(2017)11-0006-05
10.3969 ∕j.issn.2096-2266.2017.11.002
文化部少数民族节日志课题“阔塔节”(YXZ2015010)
2017-05-12
2017-05-31
项露林,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民族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