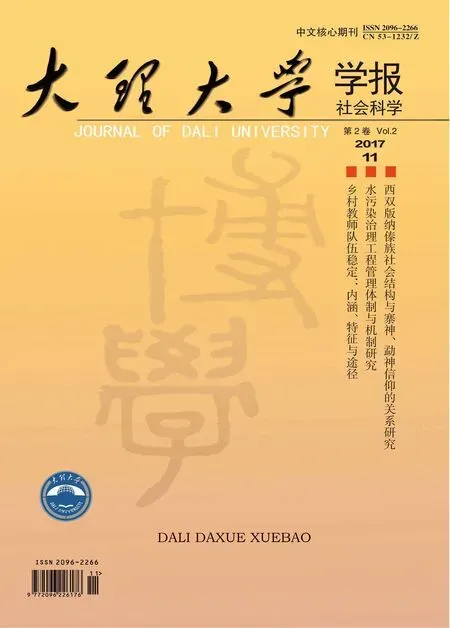家庭承包制的演变及其对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启示
王廷勇,王雪苇,王 珊,林忠舒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贵州都匀 558000)
家庭承包制的演变及其对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启示
王廷勇,王雪苇,王 珊,林忠舒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贵州都匀 558000)
家庭承包制经历了“三起三落”的曲折过程,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正式得到确认和推广。家庭承包制的创新实践贯穿了党中央向农民放权让利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农民自觉选择的一个渐进式过程,党中央尊重群众实践的决策过程推动了制度变迁。当前及未来的土地制度改革试验,必须坚持实践的标准,以维护农民利益为根本目标,充分发挥农民在土地制度创新中的根本作用,正确认识和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力争实现纵向延续与横向扩展的统一、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联动及政策过程与法制过程的协同推进。
家庭承包制;演变;土地制度改革
一、问题的提出
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1〕,农村土地问题与当下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转型紧密相关〔2〕。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每次重大的经济、社会制度变革,几乎无不与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土地制度的嬗变相关。这是因为土地制度改革涉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重大利益调整,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改革的重大难点和国家重大制度的调整;不仅具有历史性、现实性,而且更具有未来性。同时,土地作为一种基础性的自然资源,是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依赖和利用的经济资源,承载着多种社会功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的要求。因此,对作为国家基础性制度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任重道远,意义非凡,必须对重大现实问题作出回应。
历史经验表明,土地制度变革常常成为引发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动因和前导〔3〕。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始终贯穿于革命、建设和发展的全过程。就起始于农村土地利用模式突破创新的中国农村改革而言,家庭承包制的形成和推广集中体现和反映了土地制度突破创新的整个过程;就直接影响和决定我国土地制度改革进程而言,家庭承包制的整个实践过程具有其独特性,涌现出许多新的规律性元素,为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土地制度积累了有益的经验。特别是在近年来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不断加速的情况下,面对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的全面推进,家庭承包制历史演变的意义和价值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从大量有关文献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家庭承包制变革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研究,得到了学界的持续关注,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对家庭承包制历史发展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改革开放后的农地制度,缺乏前后相继的系统性、规范性考察,缺乏较长时间的历史性研究〔4〕。同时,对家庭承包制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深入认识不够,许多演变过程中的新的规律性元素也并未被学界充分认识。
二、家庭承包制演变的历史脉络
(一)1921年至1948年的土地革命与土地改革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土地制度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所有权与极其分散的租佃关系并存的格局,长期维持着土地私有制的基本形态〔5〕。封建土地制度造成旧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力发展。因此,土地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上缺乏必要的可以借鉴的实践经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具体条件、情况千差万别。在这一背景下,为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只能紧紧依靠基层党组织领导农民群众在实践中充分发挥首创精神来为全局性工作积累必要的经验,并根据实践制定正确的政策。
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土地革命与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发布了一系列的土地法令。其主要核心内容是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没收地主土地,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并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公平,这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按人口、按土地等级“分田、均田”家庭承包朴素思想的继承发展,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在遵循马克思土地革命理论和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科学结论。1921年至1948年,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土地革命,以家庭为单位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不仅获得了土地所有权,而且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封建土地所有制也相应转变为土地农民所有制。这种由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土地农民所有制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初。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家庭承包制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农业合作化的推行,土地农民所有制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形成了“公有公营”的土地利用模式。建国初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依靠政权的强制力量,没收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的土地无偿平均分配给农民。1953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由于个体劳动增产有限、部分农民希望向富农发展、农村阶级分化导致互助合作难以巩固等原因,建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随之展开。合作化运动初期,加入互助组的农民仅在生产过程中相互合作,仍然拥有相对完整统一的土地产权;初级社中的农民已不再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集体所有权开始萌芽;农业合作化后期,高级社则明确规定土地所有权集体所有,所有权主体突破了初级社以熟人社会为特征的农村社区界限〔6〕。土地农民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土地集体所有制,“公有公营”土地利用模式基本形成。
农业合作化初期,党的主要领导人主观认为农业合作化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越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农民对合作化也抱有美好憧憬,期待能够通过合作化更好地改善生活。但在辽阔分散的土地上进行集体生产经营劳动,监督管理难度较大,加之农业生产的季节性较强,劳动与收益的直接相关性与工业生产相比又有较大的时间差,农民出工不出力普遍盛行,出现了“大锅饭”和农业产出率下降。由于粮食紧张,农民的口粮得不到保障、农村多种经营受到限制、政府对多种产品的定价又难以反映地区和品种差价等原因,政府、集体与农民关系紧张,农民并没有如期所愿。部分地方干部和群众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生产自救式的地方试验开始出现。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最初的地方承包试验是从生产队以包工形式承包农业社土地(包工到队)经营开始的,但在包工到队的一些地方实践中发现,包工到生产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合作化经营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出现了作业组向生产队包产(包产到组)的形式。如安徽芜湖地区的生产组向农业社包工包产,这一形式与合作化经营形式相比较,更具有效率。1956年初,一些对农业合作化不满意的地方,直接出现了农民“拉牛退社”的现象,这是包产到户的最初萌芽。如广西环江县出现了“大集体下的小自由”的退社现象,四川江津地区、浙江永嘉县、江苏江阴、广东中山、河南沁阳等地推行包产到户,山东榆次县海燕农业社实行“个人责任地制度”(责任田)、安徽埠阳县推广“分户田间管理”〔7〕。但中央对各地的做法并不认可,“责任田”和“包产到户”被指责为“单干风”〔8〕,连发文件予以制止。1957年“反右”以后,“包产到户”受到批判,全国开展了一场关于“包产到户”的大辩论,最终理论界和中央政策将包产到户定性为“资本主义的主张”,被划为禁区和被批判叫停。
农业合作化进入高级社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下,经营土地的农民基本没有自由权利,低下的农业产出率不仅加重了农村的贫困程度,而且导致了城市商品供给严重不足(当然,这与当时的“大跃进”和自然灾害也有一定关系)。人民公社体制既没有解决贫困区的脱贫问题,也没有满足先进队的致富要求。对于经济状况好一点的地区,国家为保证城市居民和贫困区人口的口粮,加重粮食征购任务,农民收入不升反降。处于中间状态的地区,逐渐滑向贫困地区。处于生存危机中的广大农民逐渐产生了对家庭经营的留念(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农民留有小块自留地)。自留地经营与集体经营相比,经济效益大不一样,增产效应明显,如能够推广自留地的公有私营模式,或许能使农村经济走出共同贫困的困境。于是,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进行了被动式经营模式创新,允许田间包工包产,生产队有了独立的经营权,基层干部和社员自发谋求生产自救的出路和形式又不断出现,农民要求改革的愿望日益增强。
人民公社主要是通过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合并,对土地加以集中,实行土地公社集体所有。“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特别是“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使得整个农村经济几乎停滞不前。为扭转当时困境,1959年的中央八届七中全会规定小生产队也应有部分所有制和享有一定的管理权。1960年11月,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制度。在政策微调过程中,1959年,包产到户在江苏、甘肃、河南、湖南、贵州等部分地方生产队再度出现,但中央有关部门同样认为,这是从集体退回单干的“右倾歪风”,随即发文纠正和制止。《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还发文对个别包产到户的地方进行批评。“庐山会议”后,包产到户又被彻底禁止。但60年代初,为了改变农村生产面貌,广东清远县凤凰大队将低产田按出产量标准划分到户,增产效果显著,解决了口粮不足的问题,在全县很快得到推广;安徽在全省范围内把高产田包给社员耕种,推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增加了粮食产量。1961年,广西龙胜县近一半的生产队也搞包产到户,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州70%的生产队推行包产到户。1962年初,中央又开始对各种形式的包产形式予以纠正。“七千人大会”后,包产到户又被全面叫停。此后,包工包产改革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又出现。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家庭承包制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农业集体化仍存在“学大寨”“穷过渡”等问题。“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农业投入严重不足,简单再生产式的手工劳动并不能提供满足工业发展的生活必需品,供给制的分配并不能满足城市人口快速增加的需求,“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堵塞了劳动力的合理自由流动,限制了家庭副业和多种经营的发展。农民负担过重,行政瞎指挥、农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农民与城市居民的食品供应严重不足。农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不高,国民经济发展困难,引发了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加重了人们对集体经济优越性的怀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实践标准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制度创新的闸门。农村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左”的思想。当时,政策处于大转变时期,“包产到户”属于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包产到户”仍然属于政策的禁区。但中央高层对“包产到户”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有的观望。在“包产到组”还是“包产到户”的争论中,主张根据地方已有的经验,反对“包产到户”,逐步试行“包产到组”仍然是主流思想。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背景下,尽管当时中央高层一些主要领导仍然认为集体化是大方向,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但也同意放宽贫困地区的农村政策,对群众搞包产到户不搞批判斗争,也不勉强纠正。允许边远山区单家独户的农户搞包产到户,允许部分地方对“包产到户”进行试验。在此背景下,安徽省委在肥西县山南公社实行了包括包产到户的多种责任制形式试点。安徽试验结果表明:包产到队比大集体好、包产到组比包产到队好、包产到户比包产到组好。包产到户增产效果明显,群众评价较好,值得推广。这为进一步转变党的农村政策奠定了实践基础。
“公有私营”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得到正式确立及推广。20世纪70年代末,农民为了解决自己的基本生活保障,把目光聚焦在了土地制度的变革上。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1978年,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生命危险以“托孤”方式立下“生死契约”①1978年11月24日,安徽小岗18个农民的“生死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再次搞“包产到户”的“公有私营”承包责任制,创造了“小岗精神”。“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9〕,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在小岗村大包干等农业生产责任制基础上形成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政策的重要基石〔10〕。实践反复证明,这次由农民自发进行的土地制度经营模式创新,不仅带来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而且还带动了我国整个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但由于存在政策不配套、不稳定和法制不健全等问题,农民的担忧和顾虑较多。在地方多次自发创新的基础上,国家逐渐认识到,确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赋予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和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在确认和扩散“公有私营”家庭承包制的过程中,政策调整对家庭承包制的正式确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为推动土地家庭承包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实行奠定了初步基础;1979年底,包产到户也仅在个别地方(贫困地区)试行,其他地区自由选择。但因包产到户有旺盛的生命力,另一些地区自发效仿,数量不断增加。1980年初,农村政策进一步放宽,经济落后、地广人稀的甘肃、云南、贵州等生活贫困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生产生活变化很快。1980年,中央高层和地方的一些领导在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上,仍然不同意在贫困地区以外的地方搞包产到户,但文件最终还是确定为贫困地区可以“先行先试”,其他地方可以因地制宜,尊重群众选择。邓小平也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1982年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将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确定为解决温饱的必要措施和农民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强调不能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强迫群众,明确了要改革人民公社体制。1982年底,全国86.7%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已有93.0%的生产队实行了家庭承包制,标志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体制初步形成。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颁发了关于“三农”的五个“一号文件”,确立并推广家庭承包制是其主要内容,确定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家庭承包制在改革中不断得到坚持和完善。1986年的《土地管理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家庭承包制的地位。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明确了要把家庭承包制为主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的任务。1993年又提出承包期延长至30年,实现了政策的长期化和稳定化。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自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农村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验。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肯定了家庭承包制的广泛适应性和旺盛生命力、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同时,家庭承包制作为农村的一项基本经营制度正式入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的《土地管理法》,使土地承包关系的管理逐步过渡到法治轨道,对抑制农村土地的过快非农化、更好地保护耕地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时期,家庭承包制的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改革,土地承包期限从15年到30年,再到“长久不变”,都是建立在稳定家庭承包关系和不改变家庭承包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的。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逐步确立了“三权分置”的改革方向是农村生产关系应然和必然的反映〔11〕。尽管土地流转权利保障的相关制度和配套措施还不够完善和健全〔12〕,但以各种形式的土地流转为基本特征的土地制度改革不断全面向纵深推进,家庭承包制仍然体现出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三、家庭承包制的演变特点
家庭承包制创新实践的曲折演变过程,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一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总体上呈现出从纵向延续到横向扩展、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从政策过程到法律过程的三大特点。
(一)内容变化从纵向延续到横向扩展
纵向延续是按事物发生的时间顺序来说明该事物在不同时代发生的变化和发展。纵向变化和发展是事物发展的时间序列,是指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由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而引起的不同形态的更迭和变化。事物在纵向变化和发展过程中,无论方式和形态如何变化,其本质内容都具有历史延续性。就家庭承包制的纵向演进而言,自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保持着纵向发展的延续性。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短暂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后,由于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速度过快和中央反对各种形式的土地承包,土地家庭承包仅仅时断时续、反反复复地在地方实践中出现。尽管每一次出现都很快被中央制止、叫停,但总体而言,土地家庭承包虽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但还是得以延续下来。
横向扩展是按事物发生的空间顺序来说明该事物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变化和发展。事物横向变化和发展是相对于相互封闭、彼此分散的客观过程而言的,其本质内容的各要素具有整体联系的扩展性。在改革开放前纵向延续的基础上,家庭承包制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横向扩展趋势。自家庭承包制得到党中央的确认和推广以来,在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中不断得到坚持和完善,不仅得到政策支持,而且有了法律保障。随着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内容的扩展,改革试点内容出现了重点突破与多头并举的整体推进局面,许多内容都呈现出关联性、整体性。家庭承包制在新的改革形势下也面临承包经营权市场化流转、“两权抵押”、承包经营权期限设置和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等亟待完善的问题。
(二)改革过程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的改革指社会各阶层面对社会问题或社会危机,在某一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实践,这与革命方式进行的社会变革有根本性不同。自下而上土地制度改革探索是在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指导下,由地方部门、社会团体或基层群众在实践中先解决局部问题,然后得到中央的鼓励、支持而得以推广、效仿。改革开放前的家庭承包制演变,更多体现为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如前所述,家庭承包制的群众创新实践经历了“三起三落”的曲折过程,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央主要领导人同意并通过多个政策文件予以确认才最终得以迅速推广和入宪,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才逐步实现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相协调。
自上而下的改革指执政者面对社会问题或统治危机,在不触动统治阶级执政地位和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主动制度变革。就我国自上而下土地制度改革“试点试验”而言,党中央、国务院针对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先勾勒出解决问题的大纲,然后根据大纲把问题分解,有计划、有组织地解决问题。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在不断积累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日趋成熟的基础上,党中央全面推进土地制度改革试点的主动性增强,家庭承包制的坚持、完善和发展更多体现了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合。当前,中央注重“顶层设计”的土地制度改革与改革开放前过分夸大主观能动性指导下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有根本区别。
(三)制度变迁从政策过程到法律过程
政策过程是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的相关形成机制和作用体系,包括政策主体、政策客体与政策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这使得政策系统呈现一系列的动态过程。科学的政策过程机制和作用体系离不开民主决策。改革开放前,由于法制不健全,中央政策文件主要鼓励发展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因此,反复出现的家庭承包制被屡次叫停,有时还给家庭承包制扣上了“单干风”“资本主义歪风”等帽子。但是,无论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的推行还是对家庭承包制的反复制止,都缺乏政策过程的真正民主决策程序,更多的体现出人治特征。由于各种人为因素的干扰,家庭承包制没有在土地制度改革中一以贯之。
改革开放后,在对商品经济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明确了要把家庭承包制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的任务。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将“农村改革”确定为支撑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厦的重要内容之一;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了要长期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长期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双层经营体制,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农村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验,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肯定了家庭承包制的广泛适应性和旺盛生命力、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随着家庭承包制实践的深入发展,家庭承包制的法律过程进一步加快发展。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国家机关在推动经济及社会协调发展中的作用与管理手段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家庭承包制不仅获得了政策的支持,而且随着相关法律规定逐步完善,其法律地位不断提高,实践中得到了中央与地方的真正坚持和完善。多个行政法规以及《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等对家庭承包制都进行了详细具体的规定。特别是《宪法》第八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标志着家庭承包制在农村经济体制中最高法律地位的确立。
四、结论和启示
(一)家庭承包制经营模式创新适应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要求
土地家庭自主经营在中国农村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中居于基础地位,由此演变而来的家庭承包制是中国农民结合实际的伟大创造。家庭承包制使农民从人民公社体制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创新了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体制,既发挥了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大发展和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家庭承包制的实践,同时也为深化农村改革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这种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所有权同使用权分离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适应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要求。伴随着家庭承包制的产生、形成、确立和创新,农业增长速度加快,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也满足了城市居民制度变迁后对农产品的极大需求,这种帕累托最优的制度变迁赢得城乡居民的大力支持和拥护。
(二)家庭承包制经营模式创新贯穿了放权让利的基本价值取向
家庭承包制的制度变迁过程,始终贯穿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保障农民的自主权、尊重农民群众首创精神、依靠群众推进改革的基本思想;始终贯穿土地公有制、市场化改革、放权让利的基本价值取向。这一制度变迁过程充分说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群众创新实践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实践的深化和认识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艰难曲折的过程,解决包产到户这类敏感政治、经济问题根本上离不开基层群众实践的深化,关键在于最高决策层能否突破思维定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使用权同所有权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始终以市场为改革取向,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适应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要求。农民的自主权得到有效保障、首创精神得以充分激活、群众力量得以充分释放,把保障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根本落脚点和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作为改革的首要出发点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
(三)制度创新是一个渐进式过程,农民是土地制度创新的根本力量
任何一项制度创新,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都有一个准备、酝酿的过程,新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创新也自然如此。从家庭承包制演变的过程不难看出,家庭经营土地的思想和历史源远流长,家庭与土地历来密不可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指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家庭承包制创新实践,1959年、1961年又再度反复出现,经历了“三起三落”的曲折过程。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正式得到确认和推广,其间经历了“包工到队”“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在地方实践与中央政策的博弈过程中,家庭承包制也经历了从“彻底禁止”“全面叫停”到“不许”“不要”,再到政策“肯定”、法律“明确”下来的过程。这说明:新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主要是一场农民的自觉行动,农民是土地制度创新的根本力量,加之具有超前意识的地方官员的首肯和推动,中央决策层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了农民的首创精神,最后将制度创新成果推向全国。这一过程不是中央制定好方案,然后自上而下层层传达再组织群众来推动的。
(四)尊重群众实践的决策过程推动了制度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农村的好政策是我国农村面貌改变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并由此而凝集了人心、形成了政策依赖性。李景鹏指出,在中国,社会的一切重大变化都是以党的政策的变化为开端的,政策的变化是中国一切社会变化的原始推动力〔12〕。王绍光指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倡导者利用实践和试验进行学习,获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以调整政策目标,回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这正是中国体制的活力所在〔13〕。也就是说,善于学习,从不相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这种“不唯上、不唯书”的学习能力和实践精神是中国体制活力的来源〔14〕。中国仍然是政府主导型社会,政府的政策对于社会的影响十分巨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决策实践,“地方试点、中央推广”的决策过程为“政策对头”提供了保障。中国政策发展中,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政策调整方法,具有渐变性特征,避免了因政策变动过大造成的社会冲击。实践的策略方法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是这一渐变过程的集中体现。从政策发展角度看,政策实践有了一段较充足的调试时间,用以纠正政策内容的偏差和有针对性地解决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待政策完全成熟后,总结实践经验再立法,更能够体现法制的严肃、科学态度。政策主导着制度变迁。一般来说,制度结构是社会长期变迁的结果,具有相对稳定性。制度基本稳定的国家,政策变量对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影响十分有限。如在一个法律制度比较稳定的国家,受到短期政策的影响就较小。但从家庭承包制的发展历史看,新中国的情况却与此不同。建国近70年来,我们始终处于制度变革、制度创新的改革之中。在制度不稳定的情况下,政府在各个领域的管理和决策上起着关键性作用。不过,随着制度性障碍的减少,政策主导制度变迁的空间也在随之收窄。因此,政策法制化的“先政策、后法律”模式也必须转变〔15〕。
总之,当前及未来的土地制度改革,必须在坚持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坚持实践的标准,以维护农民利益为根本目标,正确认识和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力争实现纵向延续与横向扩展相互统一、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互联动、政策过程与法制过程协同推进,探索和完善农村土地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1〕前无古人的创新:深改组审议农村“三块地”改革意见〔EB∕OL〕.(2014-12-10).http:∕∕news.sohu.com∕20141202∕n406594546.shtml.
〔2〕王敬尧,魏来.当代中国农地制度的存续与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2016(2):73-92.
〔3〕王景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30年回眸与展望〔J〕.现代经济探讨,2008(6):5-11.
〔4〕丁军,刘爱军.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述评〔J〕.江汉论坛,2010(7):46-51.
〔5〕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7.
〔6〕赵阳.共有与私用: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58.
〔7〕杜润生.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85-86.
〔8〕张占斌.中国式崛起:渐进改革与政府公共政策选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66.
〔9〕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考察时的谈话〔EB∕OL〕.(2016-04-29).http:∕∕news.sina.com.cn∕c∕2016-04-25∕.
〔10〕习近平.加大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力度〔EB∕OL〕.(2016-04-29).http:∕∕news.sina.com.cn∕c∕2016-04-28∕.
〔11〕王廷勇,杨遂全.承包经营权再分离的继承问题研究〔J〕.农村经济,2017(1):35-42.
〔12〕李景鹏.权力政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82.
〔13〕王绍光.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变迁的启示〔J〕.中国社会科学,2008(6):111-133,207.
〔14〕王廷勇.中国土地制度“试点试验”机制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17.
〔15〕王廷勇,程靖淇,陆玲.我国集体土地产权抽象化与具体化研究〔J〕.大理大学学报,2017,2(5):74-78.
(责任编辑 刘英玲)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Evolution of Household Contract System to China's Land Reform
Wang Tingyong,Wang Xuewei,Wang Shan,Lin Zhongsh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Qiannan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Duyun,Guizhou 558000,China)
Household contract system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quot;three ups and three downsquot;,and was officially confirmed and promoted in the early 1980s.The innovations and practices of household contract system is a symbol of delegating powers to peasants and a process of getting conscious selections by peasants.With respect for all the people,the Central Party has greatly propelled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In current and future land reform experiments,we must adhere to the practice standard,take peasants'interests as the fundamental target,bring the main role of the peasantry into full play,properly understand and handl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strive to integrate vertical continuity and horizontal expansion,and collaboratively promote policy and legal process both in bottom-up and top-down ways.
household contract system;evolution;land institution reform
F321.1
A
2096-2266(2017)11-0035-08
10.3969 ∕j.issn.2096-2266.2017.11.007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农村房地产权城乡间流转与遗产继承”(13AJY013);黔南民族师范学院重点学科项目“农林经济管理重点学科”(QNSYXK20170604)
2017-06-28
2017-09-01
王廷勇,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商制度、土地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