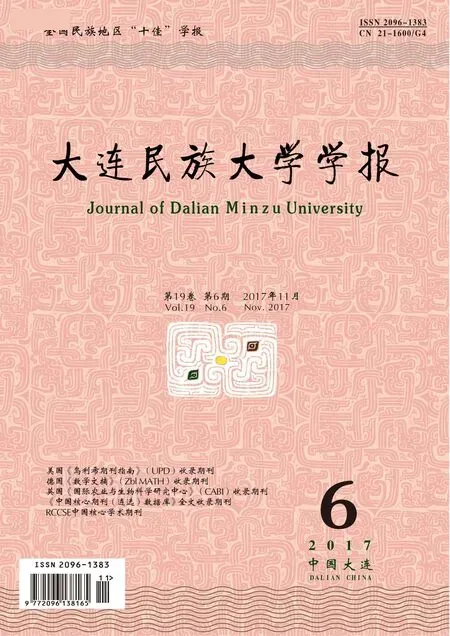从新世纪女性影视作品看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建构
——以《我的前半生》和《七月与安生》为例
贾 琼,于桂敏,马 虹,韩 松(大连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工会, 辽宁 大连 116605)
从新世纪女性影视作品看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建构
——以《我的前半生》和《七月与安生》为例
贾 琼a,于桂敏,马 虹,韩 松b
(大连民族大学 a.外国语学院;b.工会, 辽宁 大连 116605)
运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语境下“他者”思想和拉康的镜像理论,以时下关注度颇高的两部女性影视作品——《我的前半生》和《七月与安生》为例,深入解读了女主人公的命运,明确阐释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内涵和“他者”理论,探讨了新世纪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建构进程,并提出了理想的女性自我构建理论。
女性;镜像;“他者”;主体建构
古今中外,关于女性的想象与构建似乎都充斥着男性的欲望和父权的霸道。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女人的思想、语言、经历、命运以及痛苦与悲伤,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一种阳性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centric)的话语所构造的。然而,自从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自己的房间》(1928)发表以来,具有女权主义思想的作家和艺术家已经对这个话语提出了挑战,甚至开始对它进行重新改写[1]。
20世纪传统女性主义先锋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到灯塔去》中塑造了“房中的天使”形象。“天使”生活在男权社会里,心甘情愿演绎没有独立思想的攀附人生。伍尔夫讽刺其为女性自我意识消亡的产物,认为要解放女性,应该杀死“房中的天使”。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代表作《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拉,是典型的“房中天使”。直到看清丈夫的市侩和无情,娜拉才毅然选择出走。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会怎样”的讲稿中推断娜拉出走后只有两条路:一是堕落,二是回来。1925年鲁迅先生在短篇小说《伤逝》中,塑造了一个类似娜拉的角色,子君。鲁迅在《伤逝》中安排子君“天使”死亡的结局和伍尔夫在1927年创作的《到灯塔去》中所提倡的女性解放意识无疑是一种跨越空间的呼应。
香港女性作家亦舒怀着对女性主体的全新认识,续写《伤逝》,在小说《我的前半生》中,赋予女主人公子君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2017年夏天,电视连续剧《我的前半生》将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香港的故事搬到21世纪的上海,聚焦子君面对人生困境后的逆袭,倡导女性独立自强。在《我的前半生》和《七月与安生》这两部改编自女性作家原著小说的影视作品中,女性被压抑的自我得到挖掘,她们逃离了男性桎梏,走向了自我发现与建构的道路。
一、《我的前半生》:传统女性主义的“他者”之觉醒
女性主体意识是女性对其生存困境的探究和思考,对个性自由解放的追求。
长久以来,西方哲学被二元论思维所局限。二元论认为一方拥有超越另一方的权威,比如天/地,主观/客观,男性/女性等。男性是主体/自我,女性是客体/他者,自然地将女性置于男性的附属地位,女性沦为主体的他者。法国传统女性主义先锋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指出在男权文化视域下,男人的存在处境被认为是正当合理的,而女人只能作为男人的附属财产,成为非“人”的存在,即“第二性”或者“他者”。波伏娃在书中所涉及到的“他者”即为女性。于是建构主体性成为波伏娃理论的出发点。波伏娃指出,在父权制文化中,“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他是主体(the Subject), 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2]。 波伏娃强调女人只有摆脱“他者”状态,成为自由的主体,实现自己的价值,才能获得解放。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罗子君是典型的波伏娃笔下的“他者”,即男性主体的附庸,将取悦丈夫预设为自我存在的价值导向。在丈夫出轨,自己被迫离婚后,已经习惯了男权制度下被当做花瓶观赏的“他者”失去了生活的基本来源,开始面对人生最为现实的问题:如何生存。长期守在家中的女人如同笼中的鸟儿,失去了飞翔的本领,已经丧失独立生存的能力。
子君面对类似娜拉的生存困境,没有向丈夫乞怜(回去),也没有就此消沉(堕落),而是选择洞悉自我的存在价值,不再局限于家庭角色,不再认同“他者”的身份。当罗子君拒绝扮演“天使”,摆脱“他者”状态,开始正视其生存困境时,主体意识便开始觉醒。《我的前半生》从根本上与 “他者”决裂的是袁泉饰演的角色唐晶。唐晶与子君有着迥异的人生观和爱情观。她从开始就认识到爱情与婚姻的本质不是相互依附,所以日夜兼程追求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独立。她不急于也不屑于通过婚姻寻求一劳永逸的避风港,反而坚信女人可以因独立而卓越,因卓越而在爱与婚姻中拥有主动权。有别于子君作为附属“他者”的如履薄冰,唐晶在爱情面前拒绝从属,骄傲而洒脱。唐晶的角色充分演绎了颠覆“他者”地位的当代女性的典型形象。
鲁迅说:“妇女的解放,在于人格的独立与经济的独立。舍此,女性说不上真正的解放。”[3]亦舒非常强调女性在爱情中的独立性,女性不应该依靠男性,这不仅在经济上,更重要在精神上。无论哪个时代的女性,当她丧失女性主体意识和自主精神,只求在家庭内部追求有限的情爱满足和价值体现时,最终她们的希望会落空[4]。在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爱情和婚姻是女人生命的主旋律,然而失去主体意识的女性只会飞蛾扑火般迷失自我和方向,最终遍体鳞伤。
《我的前半生》中罗子君是新世纪中国已婚女性的一种形象。她婚前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文化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婚后在履行家庭角色的过程中完全忽视自我的社会角色,将所有的热情与希望投入到婚姻与家庭中,照顾孩子支持丈夫。这样的角色设定是在扮演“房中的天使”,付出丧失独立人格的代价。子君的失败在于经济的依附和自我的迷失。“爱情确实是一种激人奋发的力量,而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激发的则是牺牲自我多于确立和肯定自我 , 女人在爱情中发现的是作为妻子 , 情人的自我 , 而非真正自立的自我。”[4]传统女性主义认为女性经常错误地将男人的凝视内化为自我的主体意识[5]。如果罗子君没有被离婚,没有被逼到人生的绝境,她依然会生活在男权社会的幻想里,追求被丈夫凝视的愉悦,过着房中天使般的生活。这种被凝视被观赏被供养的主妇式生活方式曾经,甚至当下仍然是中国社会一些青年女性的理想。
《我的前半生》喝令混沌而不自知的女性洞见现实,自我觉醒。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是女性发展、改变男主女从的性别认知,从根本上取得男女平等的关键。《我的前半生》中,子君的主体觉醒与蜕变,给出走后的娜拉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同时告诫爱情中迷途的女性只有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独立才能够保障女性人格的尊严,摆脱“他者”的身份,成为命运的主宰。
二、《七月与安生》:于“他者”中建构自我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提出的镜像理论阐述的是个体的生命体验,是主体形成的最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婴儿从镜中认出自己,同时将光影幻象当成了真实存在。婴儿通过将“我”投射到镜像中,获得了对“我”的认知,而这种认知或者说主体的建构,从一开始就指向了一个虚拟的方向,所以这个阶段,也被拉康称作想象界(The Imaginary)。在对真实与虚构的混淆中,人对自己的镜像开始了终生的迷恋[6]。于是在镜像阶段,一个关乎自恋与自卑的生命历程被启动。这个生命历程在2016年由陈可辛监制的影片《七月与安生》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现。《七月与安生》改编自内地女作家安妮宝贝1998年的短篇小说集《告别薇安》中的同名短篇《七月与安生》。电影版讲述了七月和安生两个女孩从13岁开始相识相知,后因爱上同一个男孩子家明而分道扬镳,又在各自迥异却始终交织的人生轨迹中发现和审视彼此,最终成长为彼此的故事。
拉康认为,自我的建构离不开自身也离不开自我的对应物,即来自于镜中自我的影像,自我通过与这个影像的认同而实现,因此,自我并不是自己的主宰[7]。人们苦苦寻找自我,而当找到它时,它却外在于我们,总是以“他者”的姿态存在。影片中安生向往七月的安稳,七月渴望安生的自由。然而安生并不安生,她代表着一个不羁的自由世界,这对从小循规蹈矩的七月和家明有着不可名状的吸引力。七月则恰如其名,稳定得就像每年的七月都会如期而至,她衣着传统,举止端庄,大学专业选择听从父母的建议,毕业后有体面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子拥有美满的家庭,这是七月被预设好的人生,她在这条轨道上匀速运行,一方面享受着可以预见的安稳,一方面深感被束缚和囚禁。安生,圆了七月叛逆的梦,周游世界,居无定所;七月,则给漂泊的安生带来衣食无忧的安定感。七月与安生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缺失和匮乏。她们互为彼此的“他者”,在看与被看中共同成长,同时渴望着成为对方。
拉康认为“匮乏”是镜像阶段的前提条件,主体在“他者”身上凝视到自我的匮乏。凝视(gaze),使凝视者逃逸自身的匮乏,进入某种欲望的想象关系之中。七月与安生彼此凝视,在彼此身上看到缺失的自己,并对虚拟的镜像产生终生的迷恋。安生曾问家明:“你喜欢七月什么?”家明回答:“我喜欢七月的一切。”安生接道:“我喜欢七月喜欢的一切。”甚至在二者对家明的爱打破了往日的亲密无间之后,因妒恨嫌隙而激烈争吵之时,七月与安生也没有停止对彼此的迷恋,直至生命的终结。正如拉康所说,一切爱的动机,在于维护自己眼中的另一个自己。七月与安生,是彼此的“他者”,是眼中的对方。影片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山洞的庙里,当家明与安生第一次表现出对彼此的情愫时,躲在岩石背后的七月看到了,却跑到山洞外装作若无其事的等待。那一幕好似卞之琳在《断章》中所写“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家明凝视中的安生如一道风景,七月看着凝视安生的家明,家明装饰了安生的人生,安生始终是七月和家明的梦,而七月,是安生匮乏的现世安稳。
那一幕三者的凝视过后,安生选择把幸福留给七月,自己去流浪颠沛流离,七月去大学深造,两个影子带着彼此的缺失与欲望在人世第一次背离。而家明作为影片的男主角,却是一个经常缺席的在场。影片中他的存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体去界定和塑造女性角色,而只是作为一种见证和催化剂,促使两位女性角色意识到自我的欲望和匮乏并由此推进建构。
按既定轨道生活的七月一直与漂泊中的安生保持通信。七月说安生走后,日子变得很平淡,她和家明定好了26岁结婚,30岁生小孩,好像一眼就看得到一生。在安生不在的日子里,七月越发意识到自己的“匮乏”。长久压抑自我的七月,最终决定让家明逃婚,这样才有足够的理由离开既定的轨道,追逐渴望的自由。婚礼早上,家明没有出现,七月对妈妈抱歉说不能再过长辈们期望的生活。
从此,七月挣脱束缚,减掉长发,浪迹天涯,寻找渴望成为的自我。影片旁白说“七月曾经赖以生存的稳定的生活,像陆地一样离她越来越远了,她才发现其实自己特别习惯摇晃和漂流。”七月丢弃了从前的自我,通过对安生“他者”身份的认可,确立自由的新自我,最终找到其身份的真正归属。而一直流浪的安生却始终渴望一个家。
在影片尾声,安生住在高档社区,有体面的工作,独自抚养七月和家明的孩子,仿佛变成了安稳的七月。安生把自己和七月的故事写成小说在网上连载,笔名“七月”,让七月在安生的语言中得以永生。影片即将结束时,曾经不羁的安生穿着高跟鞋,在玻璃橱窗中照见七月, 两人相视而笑。安生眼前的镜像是想念中的七月,或者说安生真的成了七月,并续写着七月的人生。
“在拉康的表述中,主体并不等同于自我,而是自我形成过程中建构性的产物。主体建构过程就是把自我想象成他人,把他人指认为自我的过程。”[6]至此,七月与安生在影片中完成了主体的建构,活出了曾经匮乏的、渴望中的自我。
三、女性影视作品中新世纪中国女性之自我觉醒
在《我的前半生》和《七月与安生》两部近期的女性影视作品中,女性主体意识使女性摆脱充当男性凝视的客体对象的地位,反映出中国当代女性不再关注自己是否是男性理想的观看对象,而将注意力转向自我的情感诉求、生存境遇和价值定位。这两部影视作品中的女性角色不再作为男性角色和观众凝视的花瓶,而是处在主体和看的位置,是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主动者。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天,世界范围内的女性运动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在大多数国家地区女性不再是传统女性主义理解的男性主体的“他者”,也不再满足于充当伍尔夫笔下“房中的天使”。这种变化在新世纪的女性影视作品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优秀的女性作家和女性导演用文字和光影书写着新时代女性成长与蜕变的故事。这些故事折射出当代新女性的生存现状:她们可能是《北京遇上西雅图》(2013年)中走出国门的单亲妈妈文佳佳,在文化的碰撞与对自我的审视中看淡荣华回归本真,冷静而坚强地独立负担起养育孩子的责任和自我发展的使命;她们可能有着超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2005年)中女主人公的爱情观,勇敢承担自己的选择,说出“我爱你,与你无关”的独立爱情宣言;她们也可能就是徐静蕾这样的新女性本身,敢于对媒体问出曾经是离经叛道的问题“我为什么要结婚” ?是的,越来越多的新世纪中国女性受过良好的教育,对自我有清醒而理性的认知,当她们的生存需求已然依靠自己得以满足,当她们获得了社会归属感并得到尊重,她们不再依赖男性的光芒来照亮自我,她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的顶点,不再是男性主体的专属,自我实现,同样是女性选择攀登的精神高峰。
四、结 语
女性主体意识觉醒是个跨越时空的话题,它不局限在某个世纪某个地域。鲁迅笔下20年代的悲剧可能会在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上演,也可能在21世纪的内地重现;女性的生存困境本质上仍是家庭角色、社会角色和自我认知之间的永恒矛盾,然而在面对困境的思考和抉择上,新世纪的中国女性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是众多女性问题的核心。主体觉醒是一个寻找缺失自我的过程,一个自我探究自我发现自我成长的生命体验。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21世纪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意识到自我成长的必要,经历着自我觉醒的阵痛。这些阵痛与成长在《我的前半生》和《七月与安生》等众多优秀女性影视作品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现和探究。
女性究竟该如何建构理想的自我?传统女性主义先锋波伏娃告诫我们女性不是“第二性”;拉康认为自我建构可以建立在想象界中对“他者”的认同;海德格尔强调人被抛至世间的境遇,人要反抗没有预设的命运就要勇敢承担筹划的责任,于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说是懦夫选择成为了懦夫,英雄选择成为了英雄,意即人生而自由,人生在于选择。女人,活成自己选择成为的样子,应该就是理想的建构。正如伍尔夫所言“人不应该是插在花瓶里供人观赏的静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韵律。”[8]
[1] 常芳,郭海霞.从禁忌的打破看《无名女人》女性的自我重塑[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12):81.
[2]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 》[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11.
[3]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M]//鲁迅文集·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8.
[4] 黄敏.比较鲁迅《伤逝》与亦舒《我的前半生》女性观之异同[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3):89.
[5] 李希萍.从凝视理论分析苏珊的悲剧成因[J].语文学刊,2014(1):50.
[6] 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83.
[7] 刘文.拉康的镜像理论与自我的建构[J].学术交流,2006(7):24.
[8] 弗吉尼亚·伍尔夫.飞蛾之死[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95.
(责任编辑 王莉)
OntheWakeningProcessandConstructionofSubjectivityofChineseWomenfromthe21stCenturyFilmandTelevisionWorks——Based onTheFirstHalfofmyLifeandSoulmate
JIAQionga,YUGui-min,MAHong,HANSongb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Minzu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605, China)
Based on the two highly concerned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TheFirstHalfofmyLifeandSoulmate, by applying the understandings of “Other” under the context of western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and Lacan’s Mirror theory,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fate of the classic female characters. With these studies, the connotation of women’ subjectivity and the theory of “the Other” are clearly expounded. Through the explorations of the wakening process and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21stcentury, it proposes the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women’s ideal self-construction.
woman; mirror image; “the Other”;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2017-09-25;
2017-09-28
大连市妇女联合会项目(2017dlfn072)。
贾琼(1975-),女, 辽宁新民人,讲师,主要从事西方文学和中西方文学比较研究。
2096-1383(2017)06-0603-04
I206.7
A
——评电影《七月与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