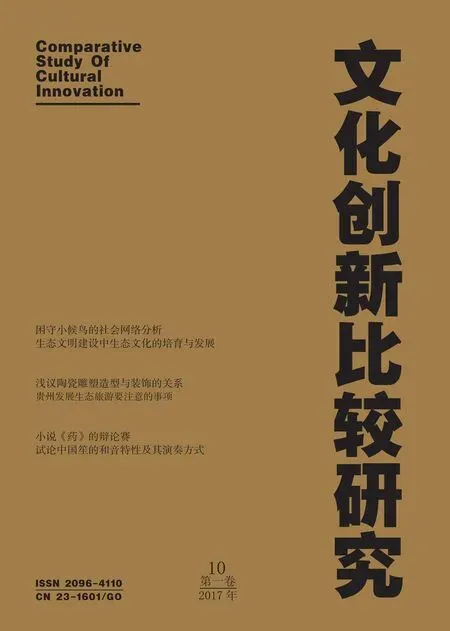泸县宋代石刻分类浅谈
周健
(四川省泸县文物局,四川泸州 646100)
泸县宋代石刻分类浅谈
周健
(四川省泸县文物局,四川泸州 646100)
泸县宋墓是继南宋安丙墓之后,四川地区宋代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自2002年泸县宋墓考古发掘工作以来,泸县又陆续抢救征集了大批宋代石刻,目前拥有国家级珍贵文物高达五百余件,是四川省拥有宋代石刻文物等级最高,藏量最为丰富的地方。
文物;考古;石刻
泸县宋代石刻有多种分类方法。我们根据研究需要,以及石刻上雕刻的人物、建筑、家具、以及各种花鸟灵兽等图案内容,通常把它们分为四灵、武士、伎乐、侍仆、综合、墓志等以下六个类别,以供参考。
1 四灵类
四灵,也叫作四象,即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在泸县宋代石室墓中几乎都有四灵图案雕刻,在墓室内的位置分别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它们形态各异,造型别致,雕刻精湛,构思高妙,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考古学价值。青龙,亦作“苍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传说中,青龙身似长蛇、麒麟首、鲤鱼尾、面有长须、犄角似鹿、有五爪、相貌威武,在四灵中最为高贵。它在泸县宋墓中的主要作用是镇慑邪魔,保卫墓主的灵魂安定。白虎,为百兽之长,是西方之神。它常常跟着龙一起出动,民间有“云从龙,风从虎”之说,它和青龙一起是降服鬼怪的最佳拍档。泸县宋墓中出土的白虎石刻,其形态多为呈行走状或踏于祥云之上呈飞奔状。朱雀,也叫“朱鸟”,是南方之神。朱雀有引导死者灵魂的作用,刻画在墓门上,有引魂升天的象征意义。南宋墓葬中的朱雀形象多为昂首挺胸,做行走状或站立状,显得雄健有力,给人以高昂、威武的感觉。玄武是一种由龟和蛇组合成的一种灵物。玄武以龟蛇合体的形状出现,也被古人看作雌雄交配、生殖繁衍的标志。泸县宋墓出土的玄武石刻一般都雕刻在墓室的横梁部位。在出土的石刻中,它有以下几种形象呈现:一是蛇头与龟头对视;二是蛇缠绕龟身一圈,蛇头与龟头对视;三是蛇缠绕龟身两圈,蛇头与龟头均平视前方。
2 武士类
在泸县出土的宋代人物石刻中,武士类石刻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它们一般都雕刻在墓室门柱两侧,两两面对面站立,共同守护墓主人。目前泸县发掘的镇墓武士石刻除了男武士以外,还出现了四件国内罕见的女武士。男武士面部丰满,多为大耳、瞠目、阔口。它们神态各异,有的面部表情严肃,有的表情温和,也有的怒目圆睁,面目狰狞。有的头部稍上仰,有的平视前方。男武士一般高102~195cm,宽45~69cm。女武士脸庞丰腴,柳眉杏眼,身着戎装,手执兵器,面部表情刚烈,有凛然不可侵犯之感。女武士的具体高度相差不多,最低的连脚座1.42m,最高的连脚座1.6m。泸县出土的武士石刻均系高浮雕或浅浮雕,其大小规格视墓葬规模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它们均身披铠甲,手执兵刃,全副武装。人物的动态、表情、衣甲、服饰精雕细刻,形象栩栩如生,异常精美。这些武士石刻再现了宋元时期部分战争情景,为研究宋元时期四川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汉蒙两族的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和考古价值。
3 侍仆类
宋代社会,等级森严,尊卑分明、贵贱有等、长幼有差,等级观念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泸县宋代石刻中,清楚地看到南宋时期地位卑微的侍仆形象。泸县所出土的侍仆类石刻又分为女侍、男侍、仆从三种类型。女侍类型石刻形象大多梳髻或戴软脚花冠,脸庞圆润,身穿窄袖长袍、半臂和背心,手或执壶,或执团扇,或持铜镜,或捧奁盒,或捧果盘,或倚门而立,姿态万千。表情或含蓄端庄或温顺妩媚。女侍“妇人启门”造型较为常见。女侍所穿服饰风格简朴、淡雅、实用,以便劳作,这与宋代女侍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以及时代审美风尚有着一定的联系。男侍类型石刻形象多为听差、跑腿的杂役。他们头戴幞头或挽高髻,低眉垂目,表情恭敬,手或捧器物,或作叉手施礼状,站立于座椅一侧。仆从类型石刻形象多为头戴幞头,浓眉大眼,脸形方圆,或持书、或扛椅的男仆。他们极有可能是深得主人宠信并掌握有一定权限的贴身侍者,地位应当比男侍稍高。泸县宋代石刻中的侍仆造型各异,生动逼真,服饰种类丰富,雕刻手法细腻,为我们了解南宋时期四川低层百姓的精神面貌与生活状况的提供了重要资料,是南宋时期理学思想所倡导的等级观念、审美意识的具体反映。
4 伎乐类
宋承唐制,宋代时期的上层社会或贵族官僚仍存在家里蓄养舞女或乐伎的情况。目前,泸县境内共出土伎乐类石刻了14件,这些石刻多为高浮雕,分为舞蹈、乐官、器乐演奏、勾栏表演四种形式。舞蹈形式表现为灵动妩媚的女子采莲舞。舞者均头戴软脚花冠,身着圆领窄袖上衣,圆领上露出内衣衣领,下穿及地长裙,跷尖鞋,系有腰带。舞者脸庞圆润,面部表情含蓄端庄。她们手持荷花、荷叶、蒲草及弯曲状饰物扎成舞具,背于身后,并作重心前移,搓袖起舞动作,优美的舞姿跃然于石刻之上。采莲舞的出现,说明宋代风靡一时的宫廷队舞——采莲队舞于南宋时期曾在四川流传,且深受人们的喜爱。
乐官形式表现为两个头戴软脚幞头,身穿圆领袍衫,束腰革带、眉清目秀的男子双手搓袖在翩翩起舞。从身穿官服的舞人形态分析,似为乐舞伎人的领班,即"乐官"之类的人物。石刻中,乐官衣袖的形态以及舞姿与《韩熙载夜晏图》中王屋山的舞姿十分相似。据重庆大学张春新教授考证,这极有可能就是失传已久的六幺舞,也就是民间俗称的甩袖舞。器乐演奏形式为乐伎头戴软脚花冠,上穿圆领窄袖短襦,圆领内露出内衣衣领,下面身穿长裙,束腰,扎腰带。演奏所涉及的器乐种类有齐鼓、扁鼓、横笛、拍板等。
泸县出土的勾栏表演形式石刻,它们真实地还原了伎乐者和舞者在勾栏之上的身形绰约。宋代时期的“勾栏”相当于现在的戏院,系供民间艺人们表演的场所,也是中国最早的演艺场。泸县宋墓“勾栏”的位置是在正墓室门的上方,下面便是墓主人埋葬的地方。从位置分布来看,墓主人是按照生前观看“勾栏”表演最佳位置进行设置的。由此可见,当时的“勾栏”文化已经在四川地区存在了。伎乐们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表演,还原了当时乐声飘飘,歌舞升平的景象,展现了宋代人们的精神娱乐的风貌,也为我们对南宋时期音乐舞蹈、服饰文化等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实物资料。
5 综合类
儒家哲学在南宋思想上占主导地位,而民间的丧葬风俗并未受大传统的制约,佛教、道教及习俗观念始终对人们的生死观产生影响,“灵魂不死”就是活人对死者的期望。而泸县出土的宋代综合类石刻,更是映证了宋人的这一观点。泸县宋代综合类石刻,包含的内容有花鸟灵兽、建筑构建、飞天、人物故事等。它们一般都位于墓室两侧壁或作壁龛内装饰。花鸟灵兽在泸县宋墓中一般都是作为门饰内容出现,雕刻手法多为浅浮雕与线雕。雕刻的花卉有:牡丹、荷花、菊花、芙蓉、月季等;禽鸟类有:凤凰、孔雀、仙鹤、小鸟等;兽类有:狮、鹿、兔、虎等;这些花鸟灵兽图案主要分布在门的上格眼或障水板、墓室壁龛、屏风、建筑横梁与台基等位置。泸县出土的建筑构建主要有仿木结构的斗拱和门。斗拱是中国古代传统建筑中独具特色的构件系统。它位于宋墓的横梁部位,主要作用是承重且兼有装饰效果。出土的门分为单扇门和双扇门。门饰大多雕刻精美、大气,也有少量的素面门。飞天,是佛教中乾闼婆和紧那
罗的化身,原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娱乐神的歌舞神。飞天艺术在东汉时期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与道教文化互相交流、融合,最终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飞天。两宋时期,随着佛教文化的盛极而衰,中国飞天也逐渐走向衰退。但在我们的宋代石刻中,却非常有幸能见到南宋时期飞天的倩影,虽然数量不多,却对研究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人物故事石刻中的“四子折桂”、“花好月圆”图案,则是我国文化隐喻的表现,它是民俗文化、社会心理的图像呈现。折射出宋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南宋高浮雕四虎二俑石刻,极有可能是反映高道郑思远的传说典故。“仙人骑虎图”出现在泸县宋墓中,不但反映了墓主希望死后成仙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宋代道教在四川的传播及其影响,为我们研究道教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宋代综合类石刻反映了宋人希望人生能够永恒延续和升华。精湛雕刻出鲜活、生机盎然的世界,为我们对宋代丧葬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考古价值。
6 墓志
墓志是存放于墓中载有死者传记的石刻。它把死者在世时,持家、德行、学业功名等方面内容,浓缩为个人档案,是断代的确证。泸县宋墓出土的几通墓志,大多因早年被盗墓者破坏,碑文残缺多字。
墓志代表“古德骏墓志铭”,记载了南宋乡绅古德骏在南宋绍兴年间至乾道八年在泸川县的生活经历。通过它可以了解到南宋政治最稳定、经济最发展的一段时期内泸州地区人民的生活状况。
泸县宋代石刻构图巧妙、雕刻细腻精美,丰富的内容充分反映了南宋时期西南的世俗生活和社会文化状况。这些宋代石刻是当时南宋社会生活的再现,是一幅南宋社会历史画卷,给后人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实物资料,堪称中国石刻艺术的瑰宝。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泸县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2]张春新.南宋川南墓葬石刻艺术[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TU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17)04(a)-0017-02
周健,女,汉族,四川泸县人,本科,文物博物助理馆员,研究方向:泸县宋代石刻、泸县龙桥研究、馆藏文物信息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