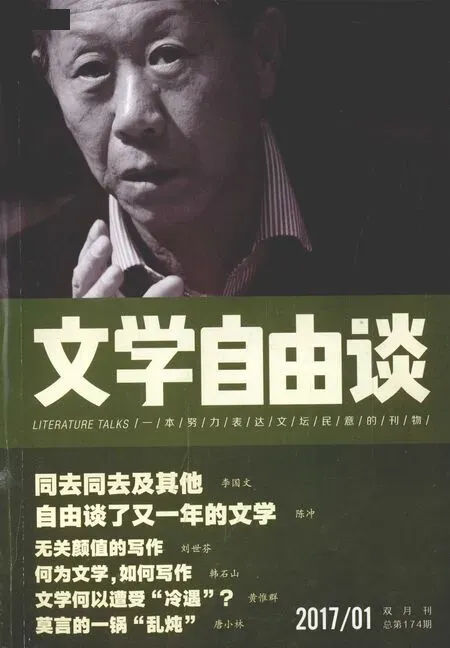一座真正的文学高峰
李建军
一座真正的文学高峰
李建军
天降鞠凶,歼我良人。2016 年 4 月 29 日,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陈忠实溘然长逝。
事后,媒体和出版社的朋友,或发邮件,或打电话,约我写一点怀念他的文字。 我与他交往二十多年,也算得上过从甚密,写起来自然不会无话可讲。 长夜纵谈,海阔天空,依稀往事,都在心头,然而,我却实在没有将它们写下来的心情和冲动。 更何况,那些可以写的,未必值得写;而值得写下的,又未必可以写。 回忆也有语境的限制。 那些不疼不痒的话,不咸不淡的事,不写也罢;其他种种,无妨俟诸他日。
那么,就来谈谈他的作品。 事实上,谈作品也就是谈它的作者。要知道,无论有多少例外,“文如其人”都是一个可靠的真理。 作品包含着作者的人格密码,是他的气质、趣味、才华和道德情调最清晰的折射体。
是的,《白鹿原》是值得经常谈论的。
如果说,时间是文学品质和价值最可靠的试金石和显影剂,那么,《白鹿原》就是一部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杰作。 即使隔着二十多年的时间回头看,它仍然是令人震撼的文学奇迹,依然是一部伟大的文学杰作。
陕西人常用“咥冷活”来形容一个人干了件出人意外的事情。然而,谁也没有想到,陈忠实会“咥”这么大一个“冷活”,会写出这样一部金声玉振、不同凡响的长篇小说。
《白鹿原》注定是一部要改变当代文学史叙事结构的作品。 它不仅彻底改变了陈忠实自己的作家形象和文学地位,而且也在很多方面,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写作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1
《白鹿原》是一部亦因亦革、继往开来的现实主义巨著。它以多方面的成功,证明了现实主义文学不仅具有自我更新的活力,而且还拥有无限广阔的前景。
就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来看,陈忠实像路遥一样,没有被甚嚣尘上的文学“新风潮”所迷惑和裹挟,也从来没有丧失对现实主义文学的信心。创作这样一部小说,既需要成熟的文学意识和文学经验,也需要不为时风所移的冷静和清醒。
陈忠实的成功,首先决定于他能“转益多师”,虔诚而虚心地学习多种模式和风格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经验。他始终珍惜并学习柳青的文学经验,先后买过好多本《创业史》,无数次研读这部艺术性很高的杰作。
对柳青来讲,观察先于想象,身历目见则是小说家必须跨过去的铁门槛;他更相信自己眼睛,更注重对生活和人物的深入而细致的观察,而不是关起门来,凭着一点才气任意挥洒,凭着天马行空的想象随意杜撰。观察需要付出切实的努力,来不得半点马马虎虎的偷懒,所以,柳青才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 陈忠实像柳青一样,按照最老实的方式来写小说。如果说,路遥从柳青那里学来了抒情化的叙述方式,那么,陈忠实则掌握了柳青细致、准确、传神的描写技巧。 像柳青一样,陈忠实笔下的人物,也是用錾子在生活的石头上,一下一下凿出来的,几乎个个都给人一种雕塑般的坚实感。
陈忠实还从巴尔扎克和哈代的长篇小说中,从契诃夫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中,从《静静的顿河》《愤怒的葡萄》《碧血黄沙》《百年孤独》和《假如明天来临》等多种样态的外国现实主义小说作品中,理解了人与历史的关系,吸纳了新鲜的叙事技巧,领悟到了解决可读性的方法,从而使《白鹿原》成为一部既传统又现代、既庄严又亲切、既有思想性又有可读性的伟大作品。
2
小说是人类生活的别样形态的历史。 然而,历史感的丧失,却是当代小说叙事的一大危机。一些小说家的叙事是封闭而苍白的,是没有背景的——既没有现实背景,也没有历史背景。他们笔下的人物与故事,皆如飘忽的影子,忽焉而来,忽焉而去,仿佛无本之木,只有枝叶,没有根系,缺乏清晰的来路和内在的深度。
然而,陈忠实认识到了历史与小说的密切关联。没有历史的生活是不完整的,没有历史的人物是不真实的。 他将小说理解为“民族的秘史”。 这是一种更真实的历史,是小说家需要深入理解和叙述的历史。 他通过阅读、调查和思考,深刻地理解了他所叙写的历史生活,理解了处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人。
在他的理解中,历史不再是僵硬的公式化的表述,人也不再是历史的干巴巴的填充物,而是有血有肉的复杂的生命体。他写出了真实的历史,也塑造出了真实的人物形象。他们有爱恨与情仇,有冲突与和解。 因而,《白鹿原》中的历史,就是真正属于人的历史;其中的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冲突,是丰富的人性以及复杂的关系引发的冲突,而不再是某种虚假观念的教条而抽象的冲突。
《白鹿原》在人性的意义上,超越了非人性叙事的狭隘性;在真实性的意义上,克服了教条的历史意识的虚假性。我们从他的叙事中看到了真实的历史,看见了有欲望和痛苦的人,看见了人物眼中流出的泪和心中流出的血。
3
文学既是美学现象,也是伦理现象。伦理精神是人们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的重要尺度。伟大的作品,首先是指那种在伦理精神上达到很高境界的作品。美好的道德诗意和伦理光辉,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最能吸引人和打动人的内在力量。
一个作家的伟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对善的正确理解和深刻表达上。如果说路遥的写作充满了青春的激情,表现了他个人的经验以及时代的经验,彰显了陷入逆境的个人应该具有的美好德性、坚韧意志和奋斗精神;那么,陈忠实就凭着自己成熟的理性,表现了我们民族漫长历史中的苦难,以及摆脱这种苦难应该选择的方向、应该有的道德精神。 就此而言,《白鹿原》属于伦理现实主义文学的范畴。
陈忠实写出了我们民族道德和伦理中永远不灭的善。《白鹿原》在伦理精神上真正吸引我们、打动我们的东西,就是这种善。 在白鹿原》里面,人的内心充满了道德痛苦和道德焦虑,而整个小说就在两种伦理文化的冲突中展开:一种新的文化进来了,它有理想,有激情,对生活要有新的安排;而旧的文化、道德精神则处于守势,面临被新的文化和道德解构掉的命运。
《白鹿原》打动我们的,就是那些将要失去精神家园、失去未来的人物身上的道德光辉和道德激情。无论是一心向学问道的乡贤朱先生,还是总是严正凛然的族长白嘉轩、永远忠诚厚道的鹿三,都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超人。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犯一些常人都犯的错误。 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良心之火从未熄灭,人性之光从未黯淡。 他们有情有义,敢于担当。 陈忠实怀着非常强烈的感伤,写出了这样的悲剧结局:原上最后一个好先生、最后一个好长工、最后一个好地主,都无奈地死灭了,消失了。 这表现着他站在现在的基点上回望历史时的感受,也表现着他在历史中观照现实的焦虑。
4
就艺术性来看,《白鹿原》 足以代表当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准和最高成就。 几十年来,没有哪部长篇小说能给人们带来如此强烈的美学震撼和如此丰富的艺术享受。
叙事是小说的重要技巧,但不是小说价值构成的主体部分。叙事的最终目的在于塑造人物。是的,塑造人物,这才是小说艺术的根本任务。一部小说倘若没有塑造出能让人记住甚至让人迷恋的人物,那它就很难说是一部够格的好小说。
现代小说的危机,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人物被叙事的话语淹没了,被作者自己的形象遮蔽了。众所周知,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经验的排斥和对“现代主义”的认同,小说作者的主观和任性,被当作一种先锋姿态;小说写作陷入了叙事压垮描写、作者遮蔽人物的误区里;小说中充满了花样翻新的技巧实验和话语狂欢,但缺乏真实可信的细节描写和个性饱满的人物塑造。
《白鹿原》拨乱而反之正,既吸纳了现代小说的叙事技巧,也用心追求现实主义小说在细节描写上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并将人物置于小说文本世界的中心位置。它调动了隐喻、象征等多种修辞技巧,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 他给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贡献了一系列崭新的人物形象:朱先生、白嘉轩、鹿子霖、田小娥、白孝文、鹿三、黑娃,个个都是过去未曾有过的人物,个个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气质和个性。
如何塑造女性形象,是检验一个作家精神高度的尺度。在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上,陈忠实的作品表现出一种现代性的教养。他写到了她们的不幸,同情她们的悲惨遭遇,并代她们发出了抗议的声音。陈忠实对她们的悲剧命运的表现是深刻的,充满了现代的启蒙意识和批判精神。尤其是田小娥这一形象,蕴含着丰富的人性内容和文化内容,也具有丰富的象征意味。美国著名批评家威尔逊将日瓦戈医生》中的拉拉当作俄罗斯民族的象征,某种程度上,田小娥也可以被当作中华民族命运的象征。
5
小说家在小说中塑造人物,也塑造自己。作者形象是小说的形象谱系构成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与人物形象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人与文是相通的,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小说。小说是一个作家秘密的人格档案,而且是他非常可靠的人格镜像。一个伟大的小说家都会在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时,塑造一个真实的自我形象。人们透过小说作品,可以看到作者自己的情感态度、人格状况和思想境界。
《白鹿原》中的作者形象,是一个颖悟的智者,一个慈悲的仁者。 他危惧悲呻,凄凉在念,内心充满了对人间不幸的同情和怜悯,对美好事物和美好德性的真诚热爱和赞美。他的小说是白鹿原上种种人物的苦难史,但也是作者献给那些逝者的安魂曲,献给生者的充满善意和智慧的启示录。他希望自己的同胞们能从自己的作品里获得积极的生存智慧,在未来活得更理性,更道德,更幸福。我们从《白鹿原》中,看到了陈忠实健全的人格和善良的心性——他塑造了一个真实而美好的自我形象。
总之,无论从作品的美学价值和艺术趣旨上看,还是从它所表现的作者的伦理自觉和人格境界上看,《白鹿原》都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代表着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是一座真正的文学高峰。
2016 年 12 月 27 日,岭南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