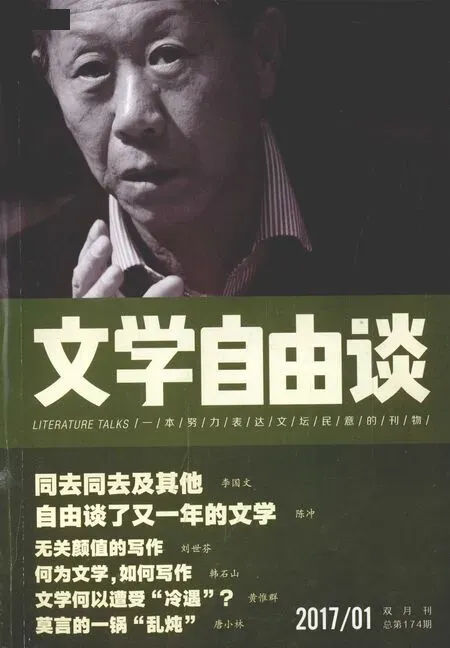毕飞宇,你实在不应该这样做
曹澍
毕飞宇,你实在不应该这样做
曹澍
老曹有个习惯,每年年底都要“扫荡”积压的没有看完的报刊。 浏览剩余的 2016 年《文学报》时,忽然看到一篇奇文:11 月0 日第 4 版,江苏作家荆歌的《两个周洁茹》。 老曹不知周洁茹为何人,荆歌在文章开头说她是咱国 70 后美女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个。 不但是美女还是作家,那就看看吧。
文章的前半部分,荆歌重点写了一件事:十多年前,江苏省作家协会在连云港搞了个笔会。某天晚上,大家来到荆歌和毕飞宇住的房间,先聊天,后来玩摸牌的游戏,游戏的结果“必然是有一男一女摸到同一种花色的牌,然后,这对男女当晚就要住在一起”。结果接连两次,都是荆歌和周洁茹摸到。第一次摸到时,“大家一片欢腾,我自然内心窃喜。 但是周洁茹不干,她表示她其实并没有弄清规则,所以不算。 于是有人重复了一遍游戏规则,于是重摸。然而结果竟然还是这样!”这时,老曹要批评的主要人物正式出场了——荆歌接着说:
周洁茹骂骂咧咧地转身要离开我们房间,但是毕飞宇不让她走。毕飞宇说:“周洁茹,你知不知愿赌服输这句话? ”她显然认理,不加反驳,但她就是要走。 毕飞宇当然不让她走。老毕其实并不想怎样,他只是扮演一个主持正义的角色,他觉得既然认可了游戏规则,违约是一件很无趣,也是无耻的举动。 一个要走,一个不让走。而我,却似乎始终反倒没事人似地坐在床上看热闹。夜已深,客散去,周洁茹则始终没有走成,因为毕飞宇坚决不让她走。眼看无法打破僵局,周洁茹说:“那到底要我怎么样? ”毕飞宇说:“我走啊,你留下来! ”我觉得如此拉锯战,到天亮也不会有个结果,也是乏味,于是我说,这样吧,周洁茹,既然是你输了,你又不肯,那你就写个欠条,欠我一夜,怎么样?
《两个周洁茹》 中还有一点关于此事在文坛发酵的叙述,老曹就不引了;老曹重点讨论的是毕飞宇在此事中扮演的角色(恐怕不是像荆歌所说的“主持正义”那么简单、那么“高大上”吧),捎带说说荆歌对此事的态度。
为了写作这篇小文,老曹特意在网上搜了搜:周洁茹,1976年出生,2000 年旅居美国 (她参加笔会应该是去美国之前,所以,她当时可能不到 24 岁),后定居香港;荆歌 1960 年出生;毕飞宇 1964 年出生。 荆比周大 16 岁,若也来个四舍五入,二人勉强算是差了一代人——年龄差距这么大,难怪荆“内心窃喜”,自以为“运气特别好”。 毕飞宇比周大 12 岁,应该还在兄长的年龄范围之内;但此事中,他却没有一丝兄长的样子。 兄长在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难道不是保护小妹妹不受欺负吗? 怎么反而会起哄架秧子——荆认为这是在“主持正义”——呢?
通常来说,玩这样的游戏,最多是闹个高兴、逗个乐子,结果出来,大家哈哈一笑,然后作鸟兽散,没有谁会当真。让两个既不是夫妻也不是恋人的人当晚“住在一起”,这毕竟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而是人伦道德的大事,那是万万使不得的。而且,笔会乃社会之公器,是作家协会组织的,不是私人性质的聚会,弄了出格的事情,作协是要负责任的;这是任何一个头脑稍微冷静的人都会想到的。
毕飞宇却反其道而行之。本来此事和他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他只是众多围观起哄者之一,但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却出来主持正义”了。 毕之所以如此行事,我猜,可能是因为他是江苏中青年作家的“大哥大”,用金圣叹的说法,是“上上人物”。 尽管 2000年以前,他还没有写出牛气冲天的《玉米》《平原》等,但已经写出非常精彩的《青衣》;他不可限量的逼人才华,已得到江苏文坛的公认——笔会时,大家都到他住的房间聊天玩游戏,他不让周洁茹走而她竟然就不敢走(看文中对周的描述,她应该不是一个温顺的“乖乖女”),可做旁证。
五年前, 老曹读过毕飞宇一篇很棒的演讲稿:《文学的拐杖——从〈半夜鸡叫〉说起》。在演讲中,他大谈特谈“世态人情”,说“世态人情”里有“日常的规则,生活的规则,生活的逻辑,文化的形态,这个文化形态是标准的东方式的”。他还说,“世态人情”是“小说的底子,小说的呼吸”。 老曹理解,生活中我们谁也绕不开用“世态人情”思考问题、处理问题,故而他才如此强调。那么,老曹就以“世态人情”来讨论此事。
老曹不知道周洁茹当时结婚没有。倘若没结婚,这样的事儿如果成了,你让她将来如何面对自己的恋人? 父母知道了,会袖手不管吗?他们是去找作协还是找荆歌算账?倘若她已经结婚,她回家怎么跟丈夫交代?她能对丈夫说是她“愿赌服输”吗?她丈夫能饶了荆歌吗?这事很可能导致他们的婚姻终结吧?——这是站在周洁茹的立场上说话,或者说从她这一方说。
再从另一方来说——玩这个游戏时, 荆歌已经 40岁上下,在正常情况下,应是已婚状态。 如果他的妻子知道了这事,会怎么想?是暴跳如雷臭骂他是“什么氓”呢,还是横眉冷对马上提出离婚?或者闯到周洁茹的单位大闹一场?她会既大度又自私地四处吹嘘她家老荆占了个大便宜,跟个美女作家“住了一夜”吗?
请问毕飞宇, 老曹这样揣测, 符合不符合你那个 “世态人情”?符合不符合你说的“日常的规则,生活的规则”?你说会不会出现这些后果?生活中这样的事,我们听的见的难道还少吗?倘若周是你妻子或者妹妹,别人这样对待她,你愿意吗? 你还会劝她“愿赌服输”吗? 或者,她是你好朋友的妻子或恋人,你还会要求她这样做吗?你就不考虑你朋友的感受和反应吗?一个大男人,好意思让一个姑娘陷于如此境地吗? 违背了这样的“约”,是一个姑娘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怎么能说是“很无趣,也是无耻的举动”? 这是什么标准、什么逻辑? (老曹以为,对这种“契约”,“践约”才是无耻的举动。 )老曹还想请教毕飞宇:你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推拿》,不是把帮助弟弟赖赌账的王大夫当成一个英雄,浓墨重彩地描写歌颂吗? 怎么到了周女士这里,就祭出“愿赌服输”的法宝来怪其失信? 这不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吗?
至于荆歌,老曹想提醒你,即使你的小说远远没有毕飞宇写得好,可你究竟比他大四岁,比他多吃了四年盐。 就算毕飞宇在为你争取“权益”,但你如果主动放弃这个“权益”,开门放周女士走人,不就什么事情都完了吗? 你怎么能“似乎始终反倒没事人似地坐在床上看热闹”? ——且慢! 你是真的在“看”热闹吗? 你为什么要让周女士写那个奇葩欠条呢?真的像你事后安慰周所说的那样——“人们都知道你写了一个欠条, 那就很明白地证明,咱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是不是? 只要欠条还在,清白就在,是不是? ”——是为了证明什么“清白”吗?
这篇文章中还说,2014 年,荆到香港公干,有和已在香港定居的周见面的机会。他猜想:“十多年过去了,她还是那副玩世不恭的问题少女样子吗? ”老曹教了一辈子书,知道“问题少女”这个词可是分量很重的贬语——写到这里,老曹突然警觉和觉醒:原来,当年荆、毕等人是把周当成“玩世不恭的问题少女”来对待啊!回过来再看文章开头:“二十多岁时候的周洁茹,有一种反叛的妖艳,那股新鲜而又莽撞的劲儿,在一个年轻姑娘的身上闪耀,既是发光的才华,又是另类的吸引。我记得她喜欢皱眉头,时不时还爆个粗口。”“反叛”,“妖艳”,“新鲜而又莽撞”,“另类的吸引”,“爆个粗口”——把这些词语密集地加到一个“问题少女”的身上,是不是没有任何“违和感”?
不知道荆先生写作此文,跟毕飞宇打招呼没有;这毕竟是十多年前一件最起码具有闹剧色彩的旧事。如今,毕飞宇也已五十出头,更是排名非常靠前的咱国著名作家,如此孟浪的事情,大概不会再去做了,当然也应该不愿意让人再写出来公告天下。荆先生此文并没有达到给毕飞宇脸上“贴金”的效果,反而把毕很便宜地“出卖”了,让他丢人现眼。 ——其实,我宁愿相信“欠我一夜”的故事纯属作者的“小说家言”,仅是个有趣有料的段子,这样,前面我对他们三人的各种议论就可作废,他们在我心目中的高大形象便会满血复活。
老曹不是清教徒,更不是道学家,读书写作之余还要挤出时间,每天站在马路边,欣赏半个钟头的时尚美女,以养我浩然之气。老曹不想也不配挥舞道德大棒击打谁,更不想搞伪高尚的道德飙车。老曹只是觉得这样的玩笑可以开,但是这样的事绝不能做,更不能把它当作乐事趣事写出来。这是底线。超过这个底线,就可能真应了王朔上世纪 90 年代的那句“胡说八道”:
哪有作家啊,流氓集体转业呗。
——哦,对了,作家对此事的看法,或许是别有逻辑的吧。老曹不是什么作家,不懂作家们对“欠我一夜”这种事是不是根本就不像我这样当回事,更缺乏对流氓与作家之间身份转换的真切体验,只是觉得,无论是写了件真事,还是编了个段子,《两个周洁茹》都是老曹 2016 年看到的最无聊的文章。 没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