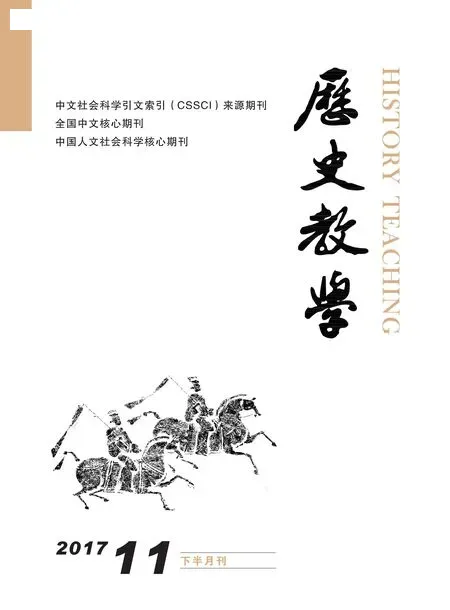从枢臣、全权大臣、东南督抚的互动看《辛丑条约》的形成*
王 刚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400715)
《辛丑条约》是晚清史上最为重要的外交条约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清政府的覆亡。得益于前辈学者的研究,其订约过程已大致清楚,但有些侧面仍值得深入探讨。在笔者看来,此次议约与以往议约的一个重要不同在于政务程序。其时,中央政府颠沛流离,用人、行政皆不能自主,因此在议和人选问题上做出了十分特殊的安排:庆亲王和李鸿章授为“全权大臣”在京议和,刘坤一、张之洞二督则留在原任函电会商。双方步调不尽一致,意见也常有分歧。行在处理议和问题,需要兼顾双方立场,意见往来形成“三角”格局。同时,作为决策中枢的军机处此时人员不整,多数时间仅有荣禄等三名大臣,办事体制多有变通,权势较平常膨胀,但他们却不谙交涉,难以驾驭庆、李和刘、张之间的纷争,为照顾双方感受,不惜牺牲某些条款上的利益,这不能不影响到条约文本的定案。对此,马忠文、戴海斌等先生已有所揭示,但尚未见专题申论。①参见戴海斌:《〈辛丑条约〉议定过程中的一个关节问题——从“惩董”交涉看清政府内部多种力量的互动》,《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98页;另,韩策:《行在朝廷·全权大臣·东南督抚:辛丑议和与清廷“三角政治”》作为通俗读物对该问题也有讨论,载《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11期。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枢臣、全权大臣和刘、张二督的三方关系演变作为考察该时期政治与外交变局的主线,揭示《辛丑条约》何以代价巨大的另一种原因。
一、开议前枢臣、议和大臣的人选纷争
晚清时期,军机处为实际的行政中枢,其人员构成格外为中外关注。庚子前期,军机处共有六名大臣,分别是世铎、荣禄、刚毅、王文韶、启秀、赵舒翘。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4日)“西巡”之际,世铎、启秀滞留京城、荣禄逃往保定,随扈者仅刚、王、赵三人。八月初七日,经刚毅奏请,慈禧添派端郡王载漪执掌中枢。这一安排引起列强极大不满,各国纷纷施压。八月二十一日,在东南斡旋和局的李鸿章(全权大臣)、刘坤一(江督)、张之洞(鄂督)、袁世凯(东抚)四人联衔上奏,以列强“必欲先办主持拳党之人而后开议”为由,请将载漪、刚毅、赵舒翘等六名“祸首”革职查办。②《大学士李鸿章等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90页。慈禧虽不情愿,但非此不能“开议”,拖至闰八月初二日,只好下诏撤去载漪一切差事,刚、赵二人交部议处,新增鹿传霖入枢。经此之变,行在保守势力大衰。消息传出,李鸿章和刘坤一、张之洞等决定抓住这一时机,运动主和派枢臣荣禄入值,以进一步坚定慈禧立场、及早促成开议。①李与刘、张等人合谋荣禄入值一事,可参看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7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24~329页。闰八月初九日,李鸿章为此出奏。此时中枢人手严重不足,慈禧接奏后没有太多犹豫,即于十四日允荣禄入值。九月二十一日,荣禄到西安与两宫会合。此事为庚子政局一道重要分水岭。其一,荣禄到后,中枢人员才稳定下来,由他和王文韶、鹿传霖组成的枢臣阵容与议和相始终,支配着该时期的内政与外交。②荣禄到西安时,刚毅已病死、赵舒翘称病不出,故枢臣只有他和王、鹿三人。至来年四月议和尾声又添派瞿鸿禨入枢。其二,荣禄因深得慈禧宠信,在政体上得到特殊眷顾。比如,承平时期,军国政令皆由皇帝裁决,枢臣系备顾问。但该时期慈禧既信任荣禄之忠,并不事事躬亲,若干事务允其放手去做。③随扈军机章京王彦威编《西巡大事记》收录有辛丑(1901年)三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奏片一道,内容是“汇举连日各处电商偿款大致情形撮要恭呈御览”。其中文字表明,当时外臣发来的电报,慈禧并不逐一过目并批示,有些电奏是由军机大臣事先处理,事后将电文大意择要恭呈御览。这一奏片提示出驻跸西安时期中枢政务程序的异常,值得注意。参见李育民等点校:《清季外交史料》(9),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860页。再如,为防止枢臣权势坐大,清代定制严格限制枢臣与外臣之联络。凡外臣奏事皆需直达御前而不得事先关会军机处;军机处以皇帝名义传达政令,“不得独立行使权力”。④刘子扬:《清代军机处》,《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但荣禄主政后,枢臣从幕后走到台前。他们发出的政令,除了以皇帝名义行文的“谕旨”外,还有以军机处名义行文的“枢电”;外臣发给行在的电报公文,除了致皇帝的“电奏”外,还有给枢臣的“致军机处公电”。⑤枢臣以军机处名义发出的“枢电”和外臣致军机大臣的“致军机处公电”在《义和团档案史料》《李鸿章全集》《愚斋存稿》等文献中收录不少,本文后面也有引用,可参看。简言之,枢臣与外臣(尤其是议和大臣)的联络已经常态化,这是考察该时期政局需特别注意的一点。
与枢臣情形相似,“开议”之前议和大臣人选也在不断变动。七月十三日,当联军逼近京城之际,慈禧谕令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向各国商请停战。但因李的“亲俄”背景,这一人选没有得到列强普遍接受。以此,李一直滞留沪上,其发出的求和电文,列强大多反应冷淡。与此同时,主持“东南互保”的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等人虽无议和大臣之名,却深得各国(尤其英、日两国)好感,私下策划过一系列缓和局势的举动。京陷之后,慈禧七月二十五日以六百里加急谕令李鸿章“迅筹办法”,继续视李鸿章为议和的唯一人选。⑥《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248页。但此时英、德等国仍强烈抵制李,拒绝承认其“全权”资格,转而提出“专恃刘、张二人主议”。⑦刘坤一:《寄张制军》(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刘坤一遗集》(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86页。日本则折中立论,接受李鸿章的“全权”地位,但须另添刘、张、庆(王)、荣(禄)四人为“全权”。由于当时日本在停战开议方面态度最好,李鸿章只好按该方案出奏(时在八月初一日)。慈禧此时虽成惊弓之鸟,却并未爽快答应,其八月初七日批复仅同意添派庆王、刘、张三人议和,却未派给“全权”身份,又强调刘、张二人须留在原任“函电会商”。⑧《军机处寄全权大臣李鸿章电旨》(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七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530页。这表明,在议和人选上,慈禧有其特殊顾虑。此番“添派”未达到英、德等国满意,僵局仍在继续。八月初九日,李鸿章再次按日本方案出奏。十四日,慈禧无奈在人选问题上再次妥协:全盘接受日本的人选提议,刘、张、庆、荣悉数添派议和,但四人未加“全权”头衔。⑨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9页。这次调整得到列强的部分谅解。十七日,态度最为强硬的英国表示:除荣禄外,不对其它议和人选的资格持异议。这一表态后,李鸿章于二十一日由沪北上,而奕劻也在稍早前回到北京斡旋。至此,议和人选问题才初步解决。不过,英德等国依然对“亲俄”的李鸿章心存不满,继续为刘、张的“全权”地位施压。闰八月初十日,庆王转达在京公使的立场,奏请加派刘、张为“全权”。⑩《庆亲王又片》(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十),《义和团档案史料》(下),第668页。慈禧批复时做出两个调整:添派庆王为“全权大臣”;加刘、张二人“便宜行事”之权。但对原奏所请“全权”一事置之不论。这已经是慈禧第三次拒绝派给刘、张“全权”头衔。何以她在这一问题上如此坚持?细味谕旨原文,似能看出一些奥妙:
庆亲王奕劻着授为全权大臣,会同李鸿章妥商应议事宜。刘坤一、张之洞均着仍遵前旨、会商办理,并准便宜行事。该亲王等务当往还筹商,折衷一是,勿得内外两歧,致多周折。是为至要。①《军机处字寄庆亲王等电旨》(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第689页。
其中最可注意者为“内外两歧、致多周折”一句。这背后既包含着慈禧对日后政务程序的担心,也包含着对日后权力分配的警惕。质言之:若加派刘、张为“全权”,则刘、张之地位与庆、李完全相同。将来政局中会出现权力相等、但又不在一处的两套议和班子。当行在处理议和问题时,既要与北京的班子联络,又要与东南的班子联络,政令往来必成“三角”局面,所谓“致多周折”既指此意。更重要的是,在“西巡”之前,朝廷已失去对东南督抚的有效控制,许多政令不被执行。将来议和事关慈禧的政治命运,如果不对这些督抚的权力有所约束,可能会导致无法收拾的后果。所以在人选安排上,慈禧不能不有十二分的小心。其亲信奕劻授为全权大臣,可对李鸿章有所监督和牵制;但刘、张两人远离北京,又在本省有强大势力,驾驭更难。所以,慈禧无论如何不愿给以等量的“全权”地位,她要竭力维持一种“一主一从”“一高一低”的局面,且强调双方意见要整合为一。这样既可以得函电往来之便,又可以让北京制约东南。慈禧的这一安排虽费尽心机,但在当时动荡混乱的局势下不过是一厢情愿,其后的政情变化并未按照她的算盘展开。
庆、李与刘、张同属主和阵营,双方在“西巡”之前有过不少合作。七月间李鸿章被授为全权,即是刘、张联衔奏请;八月间添派刘、张议和,李鸿章也非常积极。英、德不承认李鸿章全权,刘、张四处为之斡旋。该时期双方遇事互商,大有水乳之势。但八月底李鸿章北上之后,情形大变。由于当时南北电报线路多遭破坏,局势又瞬息万变,遇事来不及电商。另外,李到天津后主要依靠俄方进行斡旋,需要与亲英日的刘、张二人保持距离。所以,从这时起,李并不将交涉进展通知刘、张,更不用说“会商”。闰八月二十日慈禧强调“会商”后,李依然如此。所以,李鸿章一方首先破坏了慈禧期望的“往还筹商、折衷一是”安排。此时,刘、张一方也有觉察,但反应十分温和。他们十分敬重李的“全权”地位,遇事注意分寸,起初并无怨言。②刘坤一闰八月二十三电张之洞、盛宣怀谓:“京沪电不易通,随时会商恐多延误。此后仍宜听邸、相议行为妥。”(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2页)这等于是接受了李鸿章“不会商”的局面,此时并无抵触情绪。不过,此时之大环境毕竟险恶,刘、张救时心切、不甘袖手旁观,渐渐对李的做法产生不满。这一苗头出现于九月初。其时因慈禧迟迟不愿重办“祸首”,列强发起新一轮军事攻击,先后有夺保定、杀廷雍、占西陵之举。此时,刘、张心急如焚,切盼早日解决“祸首”问题。但该问题的症结在于“拟议”环节。慈禧也有心重办,不过,她是想知道列强的底牌后再行惩办,所以曾多次谕令李鸿章先“拟议”一个惩办方案。③慈禧最早谕令李鸿章“拟议”是在闰八月二十六,此后九月初四、初七等日又多次催促。参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下),第712、730、734页。但此时并未“开议”,李无从得知列强底牌,所以迟迟不曾“拟议”。事情就这样陷入僵局。此间,刘、张跃跃欲试,设想过若干破局之法,但因有“分际”所在,不便绕开“全权”独立行事。另一方面,局势日益糜烂,他们又不甘心坐视。在这种两难境地下,两人对李鸿章由“盼”生“怨”。九月十八日,张之洞致刘、袁、盛电文中,批评李就“祸首”问题的具奏“自紧自松”“老笔亦有疏漏”。二十八日,张致刘电更抱怨李鸿章“向不愿与商外间”,如此下去,江鄂“徒有会议之责,而无会议之实”。④张之洞两电分别见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386、8408页。这样,半是出于对局势的焦虑,半是出于对李的不满,九月二十日前后,他们决定另换思路,从“枢臣”一方打开僵局。当时,荣禄即将到达行在,刘、张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机会。如果荣到后能说服慈禧重办、而李鸿章又恰好在此时“拟议”,则内外必能形成合力、一举解决“祸首”问题。为此,他们一方面电促李鸿章迅速“拟议”,另一方面又电嘱荣禄在中枢接应,同时还请出盛宣怀、袁世凯一同用力。⑤参见《愚斋存稿》卷44(民国刻本)中九月十五至二十二日刘、张、盛、袁四人之间的往来电文。刘、张的本意虽系助力李鸿章打破议和僵局,但结果却事与愿违。首先,在这一计划中,刘、张是主导者,李鸿章成了配合者,“全权”和“会商”的角色颠倒过来。李虽未必因此心生不满,但难点在于他无法配合——此时仍未开议,无从了解列强底牌。所以,李始终未按刘、张的期望“拟议”。其次,荣禄到后,虽促成慈禧于二十二日加重处分,但尺度太小,远达不到列强的预期。李鸿章闻讯后不但毫无喜色,而且在复盛宣怀电文中大骂荣禄:“二十函抄各电,苦口忠言,乃荣一到,竟明发定案,颇自居功,圆媚可鄙。”①《寄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419页。在李看来,“祸首”问题不该在这个时候“定案”,更不该由行在一方单独定案(所谓“颇自居功”即此指)。此次惩办不到位,再请就更难。归根到底是打乱了他的计划。这样,刘、张的计划以失败告终。此事不但没有解决“祸首”问题僵局,而且对中枢、全权大臣与刘、张二督的三方关系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其一,在李鸿章一方,由于他对荣禄严重不满,此后与枢臣的关系较为疏远,除不得已的公务联络外,私下的函电互商十分少见。同时,李鸿章对运动此事的刘、张二人也有意见。自北上之后,李鸿章就抱有一种看法:刘、张远在东南,对一系列交涉不知底蕴,意见多有隔膜。②参见九月初三日《盛宣怀致刘坤一函》所引李鸿章言论,《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第339页。经此之事,李鸿章更认为刘、张的想法不切实际,无互商之必要。所以,其后的议和进展,李仍不告知刘、张二人。刘、张时而主动相商,李亦十分排斥,十月间他明告盛宣怀:“电费每月巨万……刘、张空论长电,弟务于转电时删冗摘要,以免虚糜。”③《寄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455页。由于缺乏互商渠道,日后议和中出现了北京自北京、东南自东南的局面。二者步调不尽一致、立场也常有分歧。行在决策要兼顾与双方的联络。当初慈禧所担心的“三角”格局最终还是形成。
其二,在刘、张一方,他们由于难以同李鸿章进行合作,日后更注意利用枢臣来表达意见、影响政局。在这方面,他们本有“裙带关系”之便(刘坤一与荣禄系多年密友,张之洞则是鹿传霖妻弟),荣禄入值后,又从体制上扫清了联络障碍。所以从这时开始,刘、张一方(以及关系密切的袁世凯、盛宣怀等东南大员)一直与枢臣保持着频繁的公、私联络,其意见可以不经过李鸿章而直达行在。另需注意的是,庆、李与刘、张虽有“全权”“会商”之别,但由于局势特殊,二者的实际权势相差不大。庆、李系“全权”,但这时期两宫及中枢并不在京,其意见往来也要通过函电,速度上并无优势。刘、张虽无“全权”之名、也不在议和一线,但他们与列强驻沪领事、清政府驻外公使有良好的公、私交情,通过这两个群体,他们可以与列强外交部门直接联络。另外,李鸿章虽不告、不商议和进展,但其电奏要通过盛宣怀转发行在,刘、张通过盛也可以对京中政情了解到七七八八。④盛宣怀由于维护“东南互保”,庚子前期就与刘、张保持着密切关系;李鸿章北上后,盛宣怀能感觉到李对刘、张有所排斥。但他想竭力调和双方、共同推动议和,所以常将李电转发给刘、张。因此,南北议和大臣实际权势本就接近平衡,如今枢臣的因素又在刘、张一方增添了一颗砝码,二者更加旗鼓相当。若江鄂有心对抗北京,权势上是够用的。只不过,在九、十月间,李与刘、张的关系余温尚存,双方对彼此虽有不满,但都注意着分寸,矛盾并未公开。十一月“开议”之后,情形就大不一样。
二、议和期间关键条款背后的意见往来
(一)“大纲”问题交涉阶段
十月间,列强的军事进攻暂告停止,局势走向缓和。十一月初二日(1900年12月23日),列强将“议和大纲”交予中方。次日,李鸿章电奏行在,主张速允。⑤参见《寄西安行在军机处》,《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473页。初六日,中外双方在北京“开议”。行在当日电谕庆、李:“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⑥《盛京堂转西安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七日午刻到),《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482页。据此,“大纲”已得到批准,只待李鸿章画押。但就在这一天,张之洞两次致电枢臣,对禁运军火等条款提出异议。荣禄等人非常认同,初八日,他们以“军机处”名义回复:
两电已面陈,上意甚以为然,并谕令转电。趁此开议之际,但有所见,即电商庆、李酌议……贵督与江督本系奉有会商条议之旨,此电并祈转电江督为要。荣等。⑦《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470页。
初九日,军机处电寄庆、李,要求其按照张之洞意见将有关条款删改。随后张之洞又接连两次电奏,对“大纲”中的其他条款表示异议,相应提出两个重要请求:一是“暂缓回銮”;二是删除“大纲”中“尊奉内廷谕旨”等字眼。对此,行在的处理态度一如之前,均电谕庆、李,参照张之洞意见办理。初九日谕旨还强调:
该督与刘坤一均奉有会商便宜行事之旨,但有所见,即著径电该亲王等商酌,以期妥速。奕劻、李鸿章现议条款,如有应行参酌之处,亦随时电商该督等。①《军机处寄湖广总督张之洞等电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第859页。
据此可知,行在对当时意见往来方式十分不满:张有异议不直接商于庆、李,却让朝廷在中间转达,这正是闰八月二十日谕旨所警惕的“周折”局面。故该谕旨重申二者应直接会商。从谕旨的措辞看,行在对李与江鄂之间的微妙关系并不知情。由此,中枢在处理张的电奏时没有很好拿捏双方感受。特别是十三日谕旨,竟要求庆、李“随时电商刘坤一、张之洞,互相妥酌,切勿草率画押”。②《军机处寄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电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第863页。黑体为笔者所加。若此,庆、李作为“全权”却没有画押的权力,反倒需要等待江鄂的意见才能定夺。这毫无疑问是对李鸿章权力的严重冒犯。因此,尽管谕旨的本意是敦促双方和衷商办,却无意间点燃了南北第一次公开冲突的导火索。十四日,李在电奏中发起全面反击,逐一否定张之前的各项所请,最后还狠狠挖苦:“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十六日,李在另电中又称:“刘、张等相距太远,情形未能周知,若随时电商,恐误事机。”③《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十六日),《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494、496页。公开拒绝了行在要求其“会商”江鄂的指令。稍早前,张之洞在十一日致鹿传霖私电中也将矛盾揭破:“合肥从不来商,但电奏后转知。昨见合肥电有‘定约画押’之语,万分焦急,故请电旨饬下全权,并请枢廷电告之也。”④《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474页。
对于主持全局的枢臣来说,这是一道突然而又棘手的难题。李不愿“会商”的表态不仅是对张之洞权力的否定,也是对历次谕旨的公开违抗。放在往常,必然会给予一定警告,但在当时的局势下,慈禧也好、荣禄也好,都未如此处理。查“西巡”期间慈禧的有关言论可知,在她心目中,李鸿章“威望为外人所信服”,“别人不能向洋人说话”。⑤《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213页;第28册,第305页。基于这种认识,李鸿章在议和中的地位无可取代。此时“祸首”问题仍悬而未决,慈禧、荣禄也很可能被追责,这有赖于李鸿章在议和中的斡旋。所以,尽管李的上述做法近于跋扈,但慈禧和中枢选择了隐忍不发,随后的谕旨连一句警告措辞都没有。另一方面,从内心来讲,行在君臣不可能认同李鸿章的做法。从前引十一月初八等日“枢电”“上谕”来看,慈禧和中枢十分重视刘、张二人意见,也十分清楚他们与英、日等国的关系。最好的局面当然是双方都能参与议和、和衷办事。为解决这一难题,慈禧与中枢曾经酝酿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将下一阶段的谈判由北京移往上海,这样李与江鄂不再天各一方,或许双方能够和衷。十一月十五日,中枢由鹿传霖出面对江鄂进行试探。但刘、张均担心列强不肯配合,事情最终不了了之。⑥参见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张香帅来电兼致岘帅》及十八日《刘岘帅来电兼致香帅》,《愚斋存稿》卷49,民国刻本。
“移沪”计划流产后,行在未再想出新办法来缓和双方关系。所以在这次政争中,行在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是引爆了李与江鄂的矛盾,又没能收拾好这个烂摊子。其后,江鄂之意见更难商于李鸿章,遇有重要谋划,往往是先运动枢臣、再由枢臣说服慈禧。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江鄂通过这种方式合谋的一个重大成果即促成“新政诏书”,限于篇幅,笔者拟另文述之。
(二)“祸首”问题交涉阶段
庚子十一月底(1901年1月)“大纲”画押后,“祸首”问题再次凸显,成为时局中最棘手的难题。对此,行在和李鸿章虽然都未曾怠慢,但处理的方法又落入了之前的怪圈:行在同意加重,但要求李鸿章先行“拟议”;⑦参见荣禄等十一月二十九、十二月初八日致李鸿章“枢电”。《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518、538页。李对列强的底牌不确定,迟迟不复,倒怀疑朝廷“袒护”。⑧《致李经方》(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李鸿章全集》(第36册),第264页。双方你来我往,终把问题拖入绝境:由于一直不见中方主动惩办,列强于十二月十八日联合照会,要求将载漪等11人一律处死。李鸿章随即奏报行在,主张速允。⑨《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556页。中枢断不相信这是列强的真实要价,怀疑是部分国家故意刁难,遂求助于刘、张一方。十九日,中枢以“枢电”行文刘、张、盛三人核实列强是何居心,并请三人“从旁解救”。⑩《寄江督刘岘帅、鄂督张香帅》(十二月十九日),《愚斋存稿》卷50,民国刻本。在刘、张等回复之前,行在未按李鸿章要求迅速下旨。这让李在京如坐针毡:其时列强武力威胁不断升级,多次宣称要攻取山西。
为避免决裂,李鸿章二十三日再次敦促朝廷决断,否则“危在旦夕”。出于安抚李的需要,二十五日(2月13日),行在颁布一道“加重”谕旨,但对英年、赵舒翘、启秀、徐承煜等四人未处死罪。之所以如此下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刘坤一、盛宣怀在回复十九日“枢电”时称东南正在设法,英、赵等人有望“议减”。①刘坤一:《覆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602页;盛宣怀:《寄行在军机大臣》(十二月二十二日),《愚斋存稿》卷50,民国刻本。 盛宣怀:《寄西安荣中堂》(正月初八日),《愚斋存稿》卷51,民国刻本。二十五日谕旨下发后,列强不满意,李鸿章也不满意。故二十六至二十八日局势更紧,眼看联军西进已箭在弦上。二十九这天,李鸿章接连三次急电行在,要求朝廷速按列强要求照办,“勿为局外摇惑”。②《致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581页。 分别参见《杨儒庚辛存稿》,第77、240页所录正月初九日电旨。对照上一注释中盛宣怀初八日来电可知,这两道电旨是荣禄采纳盛宣怀建议的结果。这里的“局外”无疑就是影射刘、张。二人虽有心继续挽救,但也担心拖延生变、更不愿因此激怒李,所以只做了少许努力之后便回复中枢:无可挽回。③《两江总督刘坤一等电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第954页。正月初三日(1901年2月21日),行在下旨将英、赵等四人一律处死。至此,“祸首”问题才算了结。
回顾“祸首”问题的前前后后,中枢、北京、江鄂三方根本立场并无不同。意见分歧在于时机、轻重等细节。即便如此,三方仍无法做到步调一致、密切配合,是以九月二十二日之后再没有颁布过一道“加重”上谕,直到把问题拖入绝境。④此间,清政府曾有过一次“加重”做法,即把九月二十二日谕旨漏掉的董福祥“革职”,但是以“密旨”字寄北京,仅供谈判时向列强出示。参见盛宣怀:《寄北京庆亲王、李中堂》(十二月初八日),《愚斋存稿》卷50,民国刻本。“祸首”问题告结之际,“俄约”问题已经棘手,北京与江鄂的关系又遇考验。
(三)“俄约”问题交涉阶段
议和之前,俄国已占领了东三省。为达到独霸目的,俄企图在北京“公约”之外单独立约。“俄约”问题由此出现。十一月十一日(1901年1月1日),行在据李鸿章提议,授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方展开秘密谈判。
十二月二十八日,谈判告一段落,俄方提出一个条约文本(12条),要求中方批准画押。辛丑正月初五日,该条约递达行在。此时,慈禧和中枢已经知道这是一块烫手山芋。原来,“俄约”谈判虽极为秘密,但早在庚子十一月底(1901年1月)日本就获得了情报,迅即向清政府提出交涉。十二月间,英、美、德、奥等国也闻风而动,均以“俄约”有碍“公约”为由,要挟中方不得签约。⑤各国的干涉情形可参见李鸿章正月初九日电奏,《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29页。东南得知这些消息后极为焦虑。初五条约到后,张之洞、盛宣怀等人或私电荣禄、或公电军机处,切嘱“万不可允”。⑥参见正月初五日《刘坤一电枢垣》、初六日《张之洞电枢垣》,《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杨儒庚辛存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38页;按:该书将两电日期误为初六、初七日,今据电码改正;又参见盛宣怀:《寄西安荣中堂》(正月初八、初十日),《愚斋存稿》卷51,民国刻本。刘坤一还亲电李鸿章解说利害,劝其从缓。⑦《盛宗丞转江督刘来电》(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四日到),《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40页。
李呈递“俄约”时,也主张继续磋磨后再行画押。⑧正月初六日李鸿章电奏提议:“令杨探询(俄)各部口气若何,再与从容议约,急脉缓受为宜。”(《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20页)但是面对英日等国干涉及江鄂的反对,为免节外生枝,转而主张速签。其正月初九日电奏攻击刘、张“素昵英日”,敦促“早定”。⑨《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29页。因此,在“俄约”问题上,李和江鄂早早处于对立状态。随后,为达到“画押”或“拒约”目的,俄方施压李鸿章,英日则运动江鄂,极尽明争暗斗。⑩分别参见《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29~62页;《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602~2606页;《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07~8512页。而所有压力最终都汇总到中枢处,让荣禄等人举棋不定。画,可能激各国之怒,导致瓜分;不画,可能激俄之怒,霸占东三省永不归还。万般无奈之际,荣禄采取了盛宣怀正月初八日的提议,从李和刘、张两方入手,“将(俄约)必不可允者责成李相、杨使竭力减除;并由刘、张覆日本等国请其设法帮助”。①刘坤一:《覆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602页;盛宣怀:《寄行在军机大臣》(十二月二十二日),《愚斋存稿》卷50,民国刻本。 盛宣怀:《寄西安荣中堂》(正月初八日),《愚斋存稿》卷51,民国刻本。据此,中枢初九日寄出两道电旨:一是谕令李鸿章恳求俄国删改部分条款;二是谕令刘、张请英、日等国直接向俄国施压、迫使俄方让步。②《致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581页。 分别参见《杨儒庚辛存稿》,第77、240页所录正月初九日电旨。对照上一注释中盛宣怀初八日来电可知,这两道电旨是荣禄采纳盛宣怀建议的结果。对此,李鸿章十分不满。他先后于正月十六、十八、二十等日接连电奏,或批评江鄂所言不可信,或渲染俄将“决裂”,均催促早日画押。①《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46、49、50、56页。 《岑中丞来电并致刘岘帅、张香帅等》,(辛丑)二月初四日,《愚斋存稿》卷53,民国刻本。中枢则坚持从两面入手,俄方答应“改约”之前不画押。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对李极尽安抚,去电中百般解释朝廷为难。
中枢的坚持取得了部分效果:正月二十三日(1901年3月13日),俄方在英日等国的干涉下,删除少许“刺目”条款。但为了逼迫中方早日画押,此次以最后通牒形式交约:“允”或“不允”限两周内答复(二月初七日之前)。正月二十六日,新约由李鸿章转达行在。②《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发),《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64页。 王文韶记初五日决策内幕称:“东三省俄约,东南各督抚力争不宜画押,上为所动,今日全权奏请画押,坚不允准。”见袁英光等整理:《王文韶日记》(下),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19页。此时,画与不画更难决断:其一,俄已让步,若不画,更易激成武力冲突。其二,刘、张求助英日已有成效,英方同意设法、嘱中方暂时不得画押。③《刘岘帅来电并致香帅、慰帅》(正月二十八日到),《愚斋存稿》卷52,民国刻本。 参见《李鸿章全集》(第28册),二月初六等日电,第97~104页。故此时画押,也更易激英日之怒。起初几天,中枢冀望于央求俄方“展限”,好有更多时间补救,但遭到严厉拒绝。④参见军机处二十七、二十八日致李鸿章电旨及其覆电,《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73、77、79页。 参见二月初五日《安庆王府台来电》中某军机章京密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辛丑第9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号:182-147。时间一分分流逝,而各方都未传来转机。二月初一日这天,画与不画到了最后决断关头。荣禄的焦虑达到极点:李鸿章的来电一味催促画押,刘、张的来电则一味劝告不画,两方均不见有缓解局势的切实办法。王、鹿二枢臣也各主一方,更添其乱。万般无奈之下,荣禄干脆把责任推给李鸿章,让李自行决断。某军机章京致王之春(皖抚)密电记载当时内幕甚详:“鹿见同各帅(刘、张等督抚)。王见同李(鸿章)。荣要李担利害。”⑤《安庆王抚台来电》(二月初五日申刻发),《张之洞存各处来电》(辛丑第9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号:182-147。所谓“荣要李担利害”,不是支持李画押,只是不阻止李画押,不让中枢站到李的对立面。抱着这一态度,荣禄等人初二日以“军机处”名义电告:“惟有请全权定计,朝廷实不能遥断也。”⑥《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82、85页。消息传来,刘、张等人大为惊慌:按这道电文,李鸿章势必画押(李鸿章接电后确实据此指示杨儒画押)。为在有限时间内做最后挽救,初二、初三日,刘、张等人动用了一切可能的途径运动中枢:既有致荣禄私电,也有“致军机处公电”,还有致慈禧“电奏”。⑦参见二月初二日盛宣怀《寄江鄂督帅、山东抚帅》、二月初三日《袁慰帅来电》《寄行在军机处》《刘岘帅来电》等,《愚斋存稿》卷53,民国刻本。同时,王之春、李盛铎等督抚(公使)亦出而声援。⑧参见《李盛铎电信》《皖抚王之春电信》(二月初四日到),收入王彦威编:《西巡大事记》,李育民等点校:《清季外交史料》(9),第4807~4808页。一番急电下来,中枢风向出现反转。初三日,军机处急电盛宣怀核实:若俄霸占东三省不还,其它各国是否会效尤?顺天、直隶能否退还?而“退还顺直”一语,正是盛宣怀昨日“电枢”时所述。⑨参见二月初三日《行在军机处来电》《寄江鄂督帅山东抚帅》,《愚斋存稿》卷53,民国刻本。从中可知,此时中枢已经着重考虑“不画押”的后果。果然,第二天上谕即电告李:俄约“自难轻率画押”。⑩《盛宗丞转西安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到),《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87页。陕抚岑春煊当天也密告张之洞等:“廷意初七决不画押!”①《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46、49、50、56页。 《岑中丞来电并致刘岘帅、张香帅等》,(辛丑)二月初四日,《愚斋存稿》卷53,民国刻本。至此,朝廷风向确定已变。细味前后原委,不难看出江鄂与枢臣的联络优势在行在决策中的微妙作用。
二月初四、初五两天,更多督抚、公使的反对声音到达行在,慈禧遂亮明“不画押”立场。②《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发),《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64页。 王文韶记初五日决策内幕称:“东三省俄约,东南各督抚力争不宜画押,上为所动,今日全权奏请画押,坚不允准。”见袁英光等整理:《王文韶日记》(下),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19页。所以,尽管初四之后李鸿章怒气冲冲地反复电奏,但再也没能把局面扭转回来。③《刘岘帅来电并致香帅、慰帅》(正月二十八日到),《愚斋存稿》卷52,民国刻本。 参见《李鸿章全集》(第28册),二月初六等日电,第97~104页。在这一轮政争中,江鄂的意志压倒了李的意志。不过,考察中枢初四日之后的做法可知,他们对“不画押”的决定处理得小心翼翼,尽一切可能对李进行安抚:其一,初四日谕旨极尽婉转,并未直言“不画押”,字里行间为“画押”留有分寸。其二,随同初四日谕旨,中枢还把刘、张等人反对画押的电文抄录给李。④参见军机处二十七、二十八日致李鸿章电旨及其覆电,《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73、77、79页。 参见二月初五日《安庆王府台来电》中某军机章京密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辛丑第9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号:182-147。这种做法就是拿刘、张等人做挡箭牌来解释朝廷的“苦衷”,无疑会恶化刘、张与李的关系。但是,假如不这样做,李鸿章和俄国的怒气将全部发泄在朝廷身上。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保住自身,中枢已经顾不得刘、张等人。枢臣、“全权大臣”与东南督抚的三角关系,在这个时刻体现得最为真切。尽管荣禄等人用心良苦,但经此之事,李鸿章与中枢的关系还是不可避免地恶化,李在私电中抨击“枢、疆皆隔壁账”,又借俄使之言指责中枢“偏听疆吏”。①《覆盛宗丞》(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五巳刻、戌刻发),《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91、92页。 《寄上海盛宗丞》(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四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87页。故“俄约”危机之后,李鸿章既与刘、张公开反目,也对中枢的指令(甚至电旨)心存抵触。这对其后的议和进程影响甚大。
二月初七日的期限到后,俄方并未如此前所扬言“决裂”,反而主动照会各国将东三省问题搁置。时局走向缓和。但出乎各方意料的是,李鸿章二月十二日致电俄国吴王,承诺北京“公约”定后,会将俄约“再行画押”。②《覆彼得堡吴克托》,《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109页。这一事关全局的表态,李鸿章事先并未征得朝廷同意,江鄂一方更不知情。二月十七日,李鸿章才将这层意思电奏行在。③《寄西安行在军机处》,《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120页。刘、张听说后,其焦灼愤恨,至此已极!二十七日至三月初一日,刘坤一先是私电荣禄,继而请出袁世凯一同电荣,接着与张之洞会衔电奏,严词痛斥李鸿章偏执成性,又控诉李从不相商。④参见《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615~2617页。相应提出一个重要请求:
请枢廷密电庆邸,遇俄事亦密商英日各使。至现议赔款情形及有关全局重要事件,亦请饬下全权电知江鄂。或可稍效愚者之虑。⑤刘坤一、张之洞:《致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三十日卯刻发),许同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电奏10,民国刻本。
这一表态是庚子时期李与刘、张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在此之前,半是出于对李鸿章的敬重,半是出于在“大纲”“祸首”等问题上立场相近,刘、张默认了李不“会商”、不告知的局面。但从此开始,二人已顾不得分寸,公开要求在重大问题上有知情权和发言权,以分庭抗礼的姿态站到李的对面。
在“俄约”交涉中,中枢对李鸿章的做法同样多有不满。其一是李“意涉偏重”,独与俄密而与其它公使疏远;其二是李不受商量,连中枢的意见也“不以为然”。二月初,中枢曾经背着李鸿章密电庆王:叮嘱他注意纠正李的“亲俄”路线。⑥《军机处致庆亲王电信》(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一日),《西巡大事记》卷6,李育民等点校:《清季外交史料》(9),第4798页。本段中的引文,除另作注明外,均来自此电。在这一背景下,行在对刘、张的要求表示了支持。三月初一日上谕重申“刘坤一、张之洞本系派令会议之大臣”,着庆、李“将应行筹议事宜随时电知,互相参酌”。⑦《盛宗丞转西安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二日到),《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149页。同日,荣禄又单独致电奕劻:
江鄂两督,皆经奉旨会商和议,据云数月以来全权从无相商之事,虽欲献议,亦苦于后时不及。本日电旨已令将赔款及禁运军火各事会同妥商,并望婉劝合肥,勿过执己见为要。将来关系俄约之事,并可会尊处密商英日各使,以资补救。⑧《西安荣中堂致北京庆亲王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辛丑第10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号:182~148。
这一表态改变了上年以来朝廷对李鸿章不受商量的默认态度,敦促其与江鄂会商。尽管上谕拿出了几分威严,但其实质无非是对朝廷本意的再一次重复,对李谈不上有约束力。至于荣托庆王婉劝李“勿过执己见”,更属徒劳。所以,三月之后,李与刘、张的关系依然紧张,继而还波及另一个重要人物——盛宣怀。盛与刘、张因共同酝酿“互保”而感情升温,他又系李鸿章门生,故之前总以调和双方的姿态出现。在“俄约”问题上,盛宣怀奉行的也是调和路线。⑨郑孝胥二月初九日记各方对“俄约”的态度,称“盛(宣怀)执两端”。见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89页。但这一做法却两面不讨好。刘、张认为盛对一些重要电文未曾转发、替李鸿章掩盖政情。⑩二月二十七日刘坤一致荣禄电中曾抨击盛:“近来全权电奏及电旨,盛均不转江、鄂,非受李嘱,即系护李。”(《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616页)而李鸿章则责怪盛总是与刘、张谋划,“扬其波而逐其流,都喜为隔壁谈”。①《覆盛宗丞》(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五巳刻、戌刻发),《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91、92页。 《寄上海盛宗丞》(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四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87页。所以,经过“俄约”危机,双方与盛宣怀的关系均有恶化。在失去盛的缓冲作用后,李与刘、张呈现直接对立之势。这种更糟糕的关系带给议和更消极的影响。
(四)“赔款”问题交涉阶段
“俄约”交涉的同时,“公约”谈判也在进行。二月下旬(1901年4月初)“俄约”问题暂时平息,“公约”中的“赔款”问题成为政局的焦点。围绕该问题,东南一方入手很早,庚子九、十月间,刘、张、盛等人就开始往返筹议。在此期间,他们和荣禄等枢臣有交流,与列强也有直接联络。①参见《行在军机处王中堂、鹿尚书来电》(十月二十二日),《愚斋存稿》卷47,民国刻本。又见《寄刘岘帅、张香帅》(十一月二十一日),《寄荣中堂》(辛丑正月初八日),《愚斋存稿》卷49、卷51,民国刻本。又见《致西安行在军机处、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丑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56页。所以,在李鸿章与北京公使团进行“赔款”谈判之前,江鄂已先行介入“赔款”问题的交涉。
因“俄约”问题,英日等国对李鸿章十分不满,对刘、张则更添好感。加之各国在赔款总数、利息、还款方式等细节上矛盾重重,所以,进入“赔款”谈判之后,部分国家绕开李鸿章,直接与刘、张商议。德国外交部三月中旬电告张之洞,对“赔款”问题若有实在办法,可以电达该部,德国愿“格外迁就”。②《盛宗丞转驻德吕使致江督刘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到),《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184页。美国驻宁领事三月下旬拜会刘坤一,听取刘对赔款问题的看法。英国公使四月初派参赞杰弥逊专程赴南京、武昌,就赔款问题与刘、张面商。其间,刘、张所了解到的各国态度,均比李鸿章在京所了解到的乐观;刘、张等据此提出的赔款方案,也比李鸿章提出的方案见优。比如,关于赔款总数,李鸿章在三月十九日(5月7日)与公使团第一次谈判中了解到的数字是4.5亿两,而刘坤一与美领事会晤时了解到有望减至3.1亿两,并且美国愿意“向各国劝减”。③《盛宗丞转西安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到),《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195页。关于赔款利息,李鸿章通过公使团了解到的数字是“四厘息”,而刘、张与杰弥逊会晤时,对方表示有望减至“三厘半”。④《张之洞电信》(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八日到),《西巡大事记》卷8,李育民等点校:《清季外交史料》(9),第871页。关于分期还款方案,李鸿章据北京的谈判结果,向行在提出的方案是44年、本息共计10.75亿两;江鄂据与英方的会晤结果,提出的方案是36年,本息共计7.8亿两。⑤分别参见李鸿章:《致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三日),《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282页;刘坤一、张之洞:《致西安行在军机处》(五月初八日),《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电奏11,民国刻本。两相对比,利害无需多言。所以,当这些意见到达行在,中枢明显期望以江鄂意见定案。但是,江鄂与外方的接触,只是与部分国家的接触。能否据此订约,还要看其它国家是否同意,这就需要李鸿章在京进行接应。
中枢切盼李能够如此配合,或以“上谕”或以“枢电”方式将刘、张来电陆续转告,反复叮嘱李一同用力。⑥参见《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195、302页。但是考察李的覆电可知,他对中枢的做法十分反感,对刘、张意见更强烈排斥。先是在赔款总数上,李指责美国是“借此讨好”,“并无把握”,主张迅速按照4.5亿两定议。接着在赔款利息上,李指责杰弥逊没有“议事之权”,所说“断不可信”,主张按“四厘息”速了。最后,在还款方案上,李又指责刘、张所筹36年方案没有足够“抵款”,列强不会答应。⑦分别见《致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七日、十一日、五月十二日,《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214、228、301页。
在李拒绝配合的情况下,中枢的态度至关重要。倘若中枢不予批准,坚持让李继续磋磨,或有办法缓和李对刘、张意见的排斥,仍有望减少损失。但这一时期,中枢对李的态度仍是妥协基调。中枢转述江鄂意见时,无论是以“上谕”还是“枢电”,大多是商量或嘱托口气,极尽婉转,以此表明朝廷无意偏重江鄂。这种做法相比江鄂直接电李并无太多不同。另外,进入三月之后,美、奥等国陆续撤军,议和进入尾声,李鸿章从速了结的态度对中枢而言颇具诱惑。为了早日订约,荣禄等人已不惜在赔款问题上多出点儿高价,总数、利息均按李鸿章“速了”的原则,接受了公使团的要价。
由于李鸿章和中枢的态度,刘、张的意见在“赔款”阶段均未能成为最后定论。但是他们的坚持还是挽回了一些损失,因为其激烈反对李鸿章所主的44年方案,“分期”问题久拖不决。当年六月(1901年8月),列强为了解决这一悬案主动妥协,转而提出39年、本息共计9.8亿方案,最后即以此签约。⑧参见《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375页中六月二十日辰刻致中枢电。
“赔款”问题即将定议之际,李和刘、张又爆发了第三轮冲突。当时刘坤一提出,赔款当中俄国所得最多,俄既获得赔款就应该和其它国家同时撤兵。为此,他五月间数次致电行在,请电谕李鸿章照会领袖公使,借“公论”迫使俄撤兵。在刘的反复要求下,五月底中枢电李鸿章设法。⑨《盛宗丞转西安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到),《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315页。李接电后怒斥不已。在他看来,当初就是由于江鄂的反对才导致“俄约”成为僵局,如今刘、张又让他来收拾这一摊子。盛怒之下,李不但拒绝照会列强公使,而且在回电中抨击江鄂“为日本所愚”。①《致枢垣》(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325页。刘、张迅即反击,指斥李“为俄所愚”,“置国事于不顾”。②《刘坤一电信》《张之洞电信》,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五、六月十二日到,分别收入李育民等点校:《西巡大事记》卷8、卷9,《清季外交史料》(9),第 4900、4906页。面对这一轮政争,慈禧和枢臣以和事佬面目出现,称“李鸿章身处其难,原多委曲,然时有不受商量之失;刘坤一、张之洞虑事固深,而发言太易,亦未免责人无已”。③《盛宗丞转西安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到),《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371页。言辞上极尽公允,但实质上对李妥协,对迫俄撤兵一事搁置不论。由于行在的这一立场,“俄约”问题直至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画押仍悬而未决,成了随后政局中一个火药桶。
“祸首”“俄约”和“赔款”问题是议和中最棘手的三大难题,对后世的影响也最为深远。考察这三大问题的决策内幕可知,李鸿章和刘、张先是因时机问题而意见不一,随后又因根本立场相左而势成水火,矛盾呈愈演愈烈之势,自始至终未能形成合力,实质上是各行其是。中枢虽属政务总汇之区、有朝廷名义可用,但该时期朝廷权威本就大打折扣,荣禄等枢臣又才力有限,无法驾驭许多棘手难题,是以面对二者纷争,不敢做大胆纠正、只能勉强调和。为此,条款本身的利害、国家利益的得失都成了可以“折衷”的因素,误国不可谓不深。若三方真能做到清政府所期望的“和衷”,《辛丑条约》的许多内容都会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