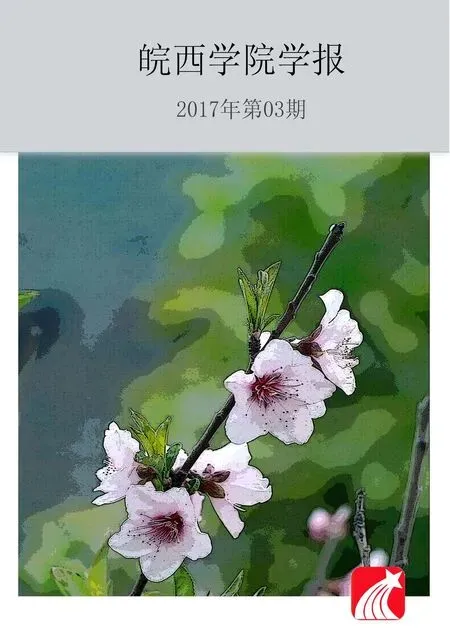重构女性主体性
——拜厄特笔下的三位女艺术家
朱永玲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重构女性主体性
——拜厄特笔下的三位女艺术家
朱永玲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在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中,男性不光主导政治经济,而且统治艺术界。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女性知识分子特别是女艺术家艰难跋涉,凭借心中坚定的信念和手中智慧的武器不断挑战男权话语。英国作家A.S.拜厄特在其小说《占有》和《孩子们的书》中颠覆传统的性别角色,猛烈抨击了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对小说中三位女艺术家主体意识和重构主体性的过程加以研究,有助于探索如何实现女性在艺术领域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机会,进而促进两性平等和谐发展。
男权话语;性别角色;女艺术家;主体意识;重构女性主体性
当代英国小说家A.S.拜厄特以其丰富的想象与博大的智慧创作了一部又一部惊人的作品,其中《占有》(1990)和《孩子们的书》(2009)最引人入胜。前者将欧洲古老神话传奇、维多利亚诗人爱情故事和当代学者的探寻之旅巧妙并置,揭示历史演进中女性知识分子命运的一致性与发展性;后者以厚重精深的华美语言书写儿童的“黄金时代”、少年的“白银时代”以及成年后的“灰铅时代”,再现维多利亚-爱德华时代儿童文学作家实现自我历程中的困境。无论《占有》中的诗人拉莫特和画家布兰奇,还是《孩子们的书》中的作家奥利弗,都反映女性知识分子在男权文化中被歪曲和贬低的本质特性,说明她们在重新界定自我特征和走进主流文化过程中遇到的艰难险阻。然而由于所处时代不同,所属阶级有别,三位女性自我实现的方式和结果也迥然有异。后现代女性主义批判男权话语对女性的定义,提倡女性在言说自我特质时拥有话语权,并重构女性的主体性,进而彻底解放女性,实现两性平等,促进人类和谐发展。
一、男权话语中的女艺术家——“他者”
正如罗伊斯·泰森所言:“传统性别角色赋予男人以理智、力量、保护作用和决断力,而女性则是情绪化、脆弱、哺育和顺服的代名词”[1](P85)。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中都没有话语权,女性的性别角色被贬低和歪曲为男性的反面。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说:“他是主体,他是绝对——她是他者”[2](P35)。男性作为父权制文化的中心是主体,是绝对的权威,是统治者;而女性是这个主体的客体,被男性构建为“他者”,沦落为“第二性”。在父权文化中,作为客体和他者的“第二性”——女性只能接受男性强加的性别角色。也就是说,“女性并非天生是女性,而是由社会建构的”[1](P86)。拜厄特笔下的三位女艺术家的命运反映男权话语中女性的“他者”身份。
拉莫特沦为“隐形人”,布兰奇成为“溺水者”①,奥利弗不过是又一位讲故事的“鹅妈妈”②,说明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实际上不能成为真正的主体,只是被压制被边缘化的客体,而女艺术家作为女性和创作者的主体性在男性话语中不被认可。男权文化压制了女艺术家的主体性,剥夺其自主创作的权利,并扼杀其创造力,将其排挤在主流文化之外,而追求自我和自由的女性不能善终,不能幸福。
(一)拉莫特——维多利亚时代的“隐形人”
《占有》中维多利亚女诗人拉莫特才华横溢、志向远大、内心独立。出身书香世家的拉莫特深谙西欧神话,并将这些融入诗歌创作,“笔落惊风雨”;然而终其一生她不过是一个“隐形人”。在维多利亚的文学主流中,她是“看不见的”;作为一个未婚妈妈,一生只能把孩子寄养在别人家,而且孩子并不知道母亲的存在;对于当代艾什研究派的多数学者们来说,她更是无足轻重的;当代女性主义学者并未意识到她诗中表现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而把焦点放在其诗中同性恋倾向以及“性”隐喻。
拉莫特原本不仅理智过人而且坚强果决,丝毫没有传统女性的柔弱和安分。她勇敢地追逐心中所爱——诗人艾什,一个有妇之夫,并且为之生下孩子。这在父权制根深蒂固的维多利亚社会是遭人唾弃的,最后她只能选择妥协——放弃爱情和孩子。拉莫特曾把自己的几首短诗寄给一个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诗人评价:“这些称得上是诗吗?我可以表达——心声吗?”[3](P197)那位伟大的诗人认为拉莫特的诗“写得还凑合,就是不大符合常规,不成体统”[3](P197),显然,他所谓的“常规”和“体统”不过是男性制定的社会准则,女性只有遵守这个准则才能被认为得体。最后,这位诗人还诚恳地建议拉莫特将来要承担一些“sweeter and weightier”责任以获得生活的乐趣。那既甜蜜又有分量的责任正是男权社会赋予女性的天职——结婚生子。女性因此成为伍尔夫所说的“房间里的天使”。拉莫特诗歌中表达的追求自由的心声和对传统女性角色的摒弃不符合父权制社会的期待,自然得不到主流文化的认可。
研究维多利亚诗人艾什的罗兰无意中发现拉莫特存在,便开启漫长的探索之旅。他之所以关注拉莫特也是为更好地研究诗人艾什,而通过整个小说的叙述,读者不难认识到拉莫特创作诗歌的才能毫不逊色于艾什。经过一个世纪之久,人们对于拉莫特的了解微乎其微,罗兰在大英图书馆里所能找到的关于拉莫特资料寥寥无几。自认为对拉莫特有所研究的费格斯·沃尔夫是一个维护男权社会的典型。沃尔夫把拉莫特称为“伊西多尔之女”,认为她的史诗充斥着“怪诞的淫荡”。沃尔夫对拉莫特的介绍和解读体现当代学术圈仍然存在对女性的成见和蔑视,有些学者仍旧企图维持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传统。与此同时,研究拉莫特的女性主义学者沉迷于其诗歌和童话故事里的隐喻,比如水、孔穴、山洞、手套和喷泉[4](P3)。他们认为这些意象实际上是“女性语言”,表达诗人对“以男性为中心的文本”的批判。
(二)布兰奇——泰晤士河中的“溺水者”
《占有》中另外一位女性——画家布兰奇同样处在边缘地带,崇高的艺术抱负与一贫如洗的经济状况最终把她推进奔腾的泰晤士急流,成为无数绝望的“溺水者”之一,自由的呼声只能封存在画作之中。
出身贫寒的布兰奇热爱画画,但她的作品在维多利亚时代不被认可。没有经济来源,又拥有高贵的自尊,还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更不会寻求“婚姻”的办法谋生,她只能寄人篱下,暂居在朋友家。艺术方面的抱负无处施展,甚至不能养活自己,进而选择跳入水流湍急的泰晤士河。最后,布兰奇在遗书中写道:“的确,我已痛苦地感觉到自己是个多余人了。”[3](P335)布兰奇最终绝望自杀,究其原因就是她的边缘化处境,而被边缘化正是男权社会扼杀她的主体性的一个表现。为保持最后的尊严和体面,布兰奇在遗书中悲哀地交代好友帮她卖掉“四幅非常漂亮的花卉图形”以便支付葬礼的费用。而这几幅可能卖出去的油画便是她向男权社会做出的妥协。在男性主导的文化中,女性仿如花朵,是男人生活和房屋的点缀,女性存在的意义在于取悦男性。布兰奇提到的克莱希先生便是当时艺术界审美的权威代表。布兰奇断定权威人士克莱希先生会喜欢这些“漂亮的花卉”,为什么这位先生不喜欢布兰奇的其他画作呢?因为父权制的维护者们界定的女性是温柔的、隐忍的、谦卑的、顺从的。而布兰奇的其他画作如“梅林和薇薇安”则是要颠覆男权社会贬低的女性形象,她的反叛精神自然要被“克莱希们”压制的;但是以“漂亮的花卉”为主题的油画符合“闺秀”的身份,更迎合男性对女性的期待。为迎合男权文化审美,布兰奇被迫放弃艺术自主。
(三)奥利弗——爱德华时代的“鹅妈妈”
与拉莫特和布兰奇不同,《孩子们的书》中奥利弗身处爱德华时代。历史发展到这个时期,女权主义运动已取得初步胜利,女性在政治、经济和教育方面已获得部分权利。奥利弗靠写作为生,获得经济独立;关心政治,积极参与社交活动;读过书,出过国,有一定的见识和思想。乍一看,俨然一个“新女性”,但是读者只要深入到奥利弗家庭生活内部以及她的灵魂深处,就不难发现无论作为女性还是作家,她都身处困境,没有真正获得自主。
奥利弗的困境主要由她的“母亲”身份所致。奥利弗成名后,在一次采访中被记者戏谑为“现代版的鹅妈妈”。作为多个孩子的母亲,奥利弗虽然从孩子身上获得创作灵感,但这也束缚了她的写作。奥利弗写自己孩子的故事,也为自己的孩子编故事,她的作品中表现出“母亲”身份对她的困扰[5],她似乎永远摆脱不掉作为母亲的恐慌与焦虑,她认为孩子让她无法正常写作,阻碍她实现自我价值,所以努力克服,埋头创作。奥利弗一边总被“怀孩子”“养孩子”的使命束缚着,一边又被读者难以满足的阅读欲望追赶着,最终丧失写作的创造力和乐趣,不能正常写作,而迷失自我。讲故事的欲望驱使这位“鹅妈妈”不断从自己的孩子身上挖取素材,不顾孩子心灵感受,走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最后“迷失自我”。她的作品把孩子们带入别样的世界,却也无情“杀死”了一些孩子,虽然构筑了自己的主体性,却没有处理好女性主体性中强调的与子女的关系,这是女艺术家在实现主体性时难以逃脱的厄运。
二、主体意识觉醒后的女艺术家——重构女性主体性
拜厄特在多部小说中探讨了女性知识分子[6],特别是女性作家的身份问题。在其小说《占有》和《孩子们的书》中,拜厄特书写三位女艺术家主体意识觉醒并寻求自由和独立的故事。《占有》中女诗人拉莫特改写传统神话故事,重新定义女性的性别特征;女画家布拉奇颠覆男权文化,反客为主,赋予女性绝对权威和自由;《孩子们的书》中女作家奥利弗以写作为生,获得经济独立,但是艺术领域却完全屈从于男权社会,在重构女性主体性的道路上陷入困境。
(一)诗人拉莫特改写神话故事,否定男权话语中女性形象,重构女性特征
拉莫特“改写”神话,赋予女性“理智”“坚强”“智慧”“勇敢”“创造力”和“保护能力”这类特征,是对男权社会的直接挑战。拉莫特对女性特征的重构集中表现在她对大湖神话和梅林希娜神话的改写上。大湖原是法国布列塔尼神话中的女巫,她的母亲是女法师莫尔葛温,父亲则是国王葛兰隆德。拉莫特把她的故事改写成叙事诗《黎城》,故事中大湖因反叛父权制社会而遭到灭顶之灾,她和整个黎城的人都被大水淹没而沉入海底,从此与外界隔离[7]。在拉莫特笔下,大湖和她的追随者坠入海底之后变成透明物,她们从此不得不忍受外界的窥视,但他们始终都保持“坚不可摧的高傲”[3](P149)。这些叛逆的女性隐蔽于海底并建立一个神秘的母系社会,从此水下的黎城便于与水上的男权社会巴黎(Paris)城形成对峙。拉莫特改写大湖不仅表达她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维多利亚社会的深恶痛绝,而且说明她认为男女两性是平等的,女性同样具备男性拥有的能力。她在节选自《黎城》的短诗“被淹没的城”中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大湖和她的丈夫在海水淹没城池之时迥然不同的表现。大难临头时,大湖泰然自若,从容不迫;而她的爱人惊慌失措,畏畏缩缩。“他吓得魂飞魄散,哀号不断:/‘海水来啦!我们快逃吧!’”[1](P358)男人胆小怕事的模样跃然纸上。相反,大湖却行若无事:“来,乖乖地躲在我的怀里吧,/海水有什么好怕的?/我能魔力征服它!”[3](P359),女性的自信潇洒和坚强勇敢表现得淋漓尽致。拉莫特用幽默的笔触讽刺了男权社会对两性角色的定义。男性所谓的“理智、坚强、保护能力和果断力”荡然无存。这些特质可以同样归属女性。
传统的神话叙事是由男性主导,仙女梅林希娜的形象也是男性刻画并用以维护男权文化。拉莫特颠覆以男性为中心的叙事,在长诗《梅林希娜》中让女主角自己发言,赋予她倾诉内心的权利,她不再是“Men say”的宾语。梅林希娜故事的叙述因此有了女性的参与:“The old nurse says”“I read”“a lady sang to herself”“she said”[3](P314-322)。通过梅林希娜,拉莫特重构了女性三个方面的主体性。首先,女性拥有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无限创造力和博大智慧。梅林希娜原是一个兼具人形和蛇形的美丽女神,咒语说她只有同凡人结婚才能解脱,婚后的梅林希娜生下十个孩子,而且为丈夫修建城池,为国家繁荣昌盛贡献极大力量。梅林希娜实际就是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化身,女性拥有实现自我价值的能力。其次,女性不仅可以承担家庭责任,而且能够走进社会。梅林希娜克服艰难险阻哺育十个孩子,竭力扮演母亲的角色,为丈夫分忧解难,承担妻子的责任;同样,梅林希娜参与社会活动,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我社会价值。最后,女性是具有欲望的主体。梅林希娜在追求爱情和婚姻的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
(二)画家布兰奇颠覆男权文化,反客为主,重建女性的主体身份
布兰奇通过画作“颠覆”父权社会,让女性主宰世界,虽有些极端,但表现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并表达了重建主体身份的渴望。布兰奇通过画作“利奥兰面前的克里斯特贝拉”表达她对男性的敌对情绪,拒绝与男性的婚姻,这实际上就是对男权文化中女性角色的反抗。画中杰拉丁和克里斯特贝拉的姐妹情谊映射现实中拉莫特与布兰奇的关系。布兰奇希望与拉莫特建立一个“世外桃源”,没有男性的干扰,然而艾什的介入打破了她的梦幻。
布兰奇的另外一幅作品“梅林和薇薇安”完全颠覆父权社会中男女两性的地位,赋予女性薇薇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男性梅林完全被薇薇安掌控。由此可见,布兰奇不仅排斥婚姻,希望与女性拉莫特建设一个没有男性的独立世界,而且在画作中表达控制男性的意图。她意识到女性被边缘化的处境,并通过艺术和实践揭露女性的生存状况,颠覆男权文化,然而,她的主体性是极端的,不可取的。作家拜厄特这样构思说明她反对男女两性处于敌对状态。人类文明的延续,既需要男性也需要女性,男女双方也不应该是一方钳制另一方,而是保持差异的前提下和平共处,相互促进。但布兰奇的创作中体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发出内心渴望自由的呐喊,创作成为她寻求独立、重构主体性的一种途径。
(三)奥利弗以写作为生,获得经济独立,却失去艺术上的自主,在重构主体性的道路上陷入困境
男权文化压制女性的声音,写作也被认为是“男性事业”,即便女性从事写作,也得在男性接受的范围内操作[8](P45)。奥利弗通过写作成为言说的主体,讲述女性自己的故事,实现自我价值,重构自己的主体性。奥利弗凭借写作为生,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经济的独立,并且拥有托德福莱特庄园,实现“自主”,但最终受困于母亲和妻子的角色,走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
弗吉尼亚·伍尔夫说:“女人要写小说得有钱和一间自己的房间”[9](P2)。女性要想在创作方面实现自主,就必须经济独立,而且要有自己的空间。奥利弗为拥有更多的“钱”和“房间”不断编写儿童故事,以迎合主流文化。她用自己赚来的钱为丈夫支付账单时获得一种奇妙的快感,这感觉源于独立能力[10](P178)。渐渐这种独立的快感加上鹊起的声名驱使她创作更多作品。她的作品之所以受欢迎,并非源于她的创造性,而正如小说中那位知名记者评论的——“她平静的母爱”和吸引孩子的“神秘刺激的想象力”。可见,奥利弗的作品实际上迎合当时主流文化——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对女性角色的界定,她依然在用男性话语写作,虽然经济独立,但艺术上并未实现真正自主。为获得现实生活的自主,奥利弗放弃艺术领域的自主,选择屈服男权文化。总之,写作虽让奥利弗获得经济独立和自主,写作的欲望或表达的欲望却让她走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最后甚至为达到某种艺术效果,不顾孩子们的感受,自作主张地安排他们在故事里的命运。
三、结论
三位女艺术家以创作来颠覆男权文化歪曲的女性形象,重新定义了女性特征。拉莫特在“改写”神话中重构女性主体性,在追求爱情和艺术时都表现出极大的果敢,但终究没有获得幸福;布兰奇在画中掌控男性,但现实中却以自杀作无力反抗。通过拉莫特和布兰奇,拜厄特一方面肯定女性的创造力和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她也批判了她们割裂艺术和现实的错误。女性在重构主体性、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如果与男性隔绝或是企图统治男性,必然走向极端,不利于两性和谐发展。而奥利弗在重构主体性过程中和其他两位女性不同。作为作家,她获得经济独立,然而为迎合主流文化审美,她牺牲艺术自主,最后丧失创作能力;作为妻子和母亲,她拒绝承担责任,认为这两种角色是对作家的束缚。这种为彻底的自由而忘记自己还是“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做法,使她走向自我中心主义的极端。由此可见,拜厄特赞同女性艺术家首先要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政治、经济方面的独立,然后才能于艺术中真正实现其主体性;另外,女艺术家同所有追求自主和幸福的女性一样,需要处理好自我与外界的关系,这个外界对于女艺术家来说,不仅包括家庭而且包括艺术领域。
注释:
① Elaine Showalter(伊莱恩·肖瓦尔特)认为Halmet中的Ophelia 是父权社会中典型的女性形象——代表着软弱、被动、缺失、轻浮和疯癫,最后成为父权社会的牺牲品——溺死在河流中。
② Mother Goose,会讲故事的村妇,被认为是《鹅妈妈童谣》的原作者。源自17世纪法国作家 Charles Perrault写的故事集Contes de ma mère l’Oye (《鹅妈妈童谣》)。
[1]Tyson, Lois.Critical Theory Today — A User-Friendly Guide[M].New York: Routledge, 2006.
[2]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3]Byatt, A.S.Possession: A Romance[M].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Limited, 1990.
[4]梁晓冬.身份的识别与重构——论拜厄特早期小说女性人物的神话性塑[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5]魏兰.拜厄特:从“理念小说”《占有》到《儿童书》[J].外国文学动态,2010(2):40-41.
[6]徐蕾.神话·历史·语言·现实:A.S.拜厄特访谈录[J].当代外国文学,2013(1):158-165.
[7]朱海燕.析《占有》中神话故事的女性主义内涵[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0(1):24-25.
[8]Butler, Judith.Gender Trouble[M].New York: Routledge, 1999.
[9]Woolf, Virginia.A Room of One’s Own[M].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89.
[10]Byatt, A.S.The Children’s Book[M].London: Vintage, 2009.
Reconstruction of Females’ Subjectivity— The Three Female Artists in A.S. Byatt’sPossessionandTheChildren’sBook
ZHU Yongling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HuaibeiNormalUniversity,Huaibei235000,China)
In the long history of human society, males are dominant in not only politics and economy but also arts. Female intellectuals, especially female artists, striving for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continuously challenge the patriarchal discourse with their firm beliefs and wise weapons. British writer A.S. Byatt subverts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women’s images in her novels, namely,PossessionandTheChildren’sBook, thus criticizing the male-centric culture. Probing in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female artists’ subjectivity and their consciousness of subject will be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artistic area as well as other fields.
patriarchal discourse; gender role; female artists; consciousness of subject; reconstruction of females’ subjectivity
2017-03-01
朱永玲(1988-),女,河南信阳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I561.065
A
1009-9735(2017)03-009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