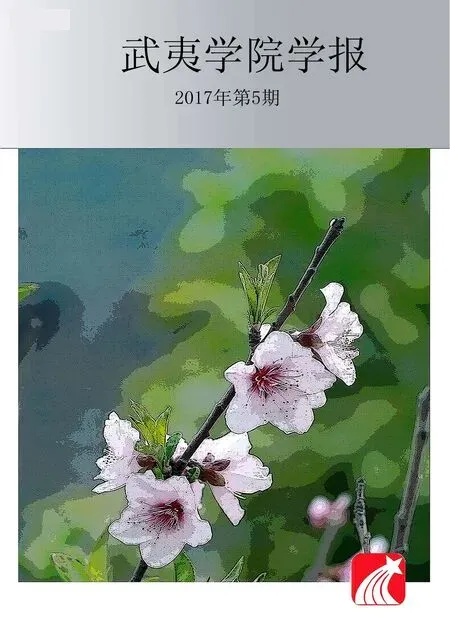认知隐喻理论视域下古汉语诗歌意象翻译探究
刘 譞
(四川外国语大学 翻译学院,重庆 400031)
认知隐喻理论视域下古汉语诗歌意象翻译探究
刘 譞
(四川外国语大学 翻译学院,重庆 400031)
传统理论关注隐喻的修辞学研究,莱考夫和约翰逊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对其进行了解释,主张隐喻是深入人们头脑的思维方式,而非单纯的语言现象,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意象是一首诗歌的核心成分,一篇优秀的诗歌译作必须处理好诗中意象隐喻的翻译。阐释了认知隐喻与诗歌意象的关系,并结合具体译作,从认知视角分析了古汉语诗歌意象隐喻的英译方法。
认知隐喻;意象;诗歌;翻译
有关隐喻的研究历史悠久,可以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时代,但传统语言理论认为隐喻属于单纯的语言现象,与思维无关,并且只起到点缀装饰的作用,与日常规约化的语言背道而驰。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认知语言学的发展,有关隐喻的研究逐渐转向认知层面,不同于传统上只把隐喻看作一种修辞技巧,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认为隐喻是人类认知与思维的本质,具有普遍性,此观点开启了隐喻研究的新篇章。
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理论,不可否认的是,诗歌这种特殊体裁的文学特点决定了其与隐喻之间不可分割。传统理论中,“‘隐喻’被定义为新奇的或诗歌的语言表达,即用一个概念的单词来表达其正常的规约化意义之外的另一个‘相似的’概念”[1],现代理论中,认知视角涵盖之广泛也必定会将隐喻与诗歌联系在一起。作为诗歌的灵魂,意象是诗人选择寄托情感的媒介,体现着其对世界的认识,意象的表达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隐喻的方式完成的。古汉语诗歌对意象的运用尤其丰富和广泛,所以,在古汉语诗歌的翻译中,意象隐喻的翻译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是决定翻译成败的关键。
一、认知视角下的隐喻概念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用语中,并非文学语言所特有,它不仅是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思维现象。“概念隐喻”是认知隐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莱考夫和约翰逊的合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的发表标志着概念隐喻理论的问世”[2]。他们认为隐喻是人们通过其他事物来认识和表达当前事物,是概念性的。“我们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本身是以隐喻为基础”[3],概念以隐喻的方式建构。隐喻的本质是源域 (source domain)到目标域 (target domain)的映射(mapping),即两个概念域之间的互动。比如,我们熟知的“TIME ISMONEY(时间就是金钱)”就是一个概念隐喻,其中,“TIME”是目标域,“MONEY”是源域,该隐喻通过从源域“MONEY”映射到目标域“TIME”上而实现。
一般来说,作为源域的概念域较具体,易于理解,且为人们所熟悉,目标域概念较抽象、难以理解。这是因为人们在认知世界时,由于类别概念和抽象概念语言的缺乏,导致只能用已知事物的具体意象表达新事物,将二者联系起来。比如“She is a block of ice.”这句话中,“ice(冰)”是我们熟悉的事物,很容易从头脑中提取对该意象的认知,进一步把“人的感情”与“冰”的特点相联系,便获得这句话中“她像冰一样冷漠”的隐含义。因此“隐喻是我们对抽象范畴进行概念化时有利的认知工具”[4]。
隐喻具有系统性,一个隐喻概念能够生发出大量相关语言表达,而不同的隐喻概念又组成了一个网络体系,影响着人们的语言和思维。仍以前面“TIME IS MONEY”为例,这一概念隐喻可以衍生出多种相关表达:
You are wasting time.(你在浪费时间。)
Thismethod can save you much time.(这个方法可以为你节省不少时间。)
Ispent hours repairing the radio.(我花费好几个小时修收音机。)
It cost her two days to get there.(她花了两天时间到达那里。)
Themanager has invested a lot of time in the project.(经理为这个项目投入了很多时间。)
由这些句子中可以看出,“金钱”这个概念网络的一部分构成了“时间”概念的特征,语言也遵循此模式,因此,我们从概念上用描述金钱的相关词语(浪费、节省、花费、花了、留出、投入)来表述时间,系统地影响了时间的表达方式。
如此一来,我们发现隐喻在生活中比比皆是,非隐喻概念的存在并非无限,故非隐喻的表达也相当有限,只是由于许多隐喻已经深入我们的思维,因此常常被人们忽视。隐喻“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是新的语言语义产生的根源”[5],它具有概念性、跨概念域的结构映射性、体验性和系统性的基本特征。
二、基于认知隐喻理论的古汉语诗歌意象翻译
隐喻的普遍存在决定其必然会成为翻译研究的对象,“在认知语义学中,翻译被认为是概念隐喻的最好说明。在翻译时目标语言的概念结构被映现到原材料,便于目标语读者理解”[6]。但同时,隐喻自身的特点导致 “隐喻的翻译就成为翻译中最复杂的问题”[7],且中国古代诗歌中的隐喻性意象俯拾皆是,意味深远,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古汉语诗歌意象翻译自然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认知隐喻与诗歌意象翻译
隐喻在文学作品中大量存在,与诗歌的联系尤为紧密。隐喻是诗歌魅力的源泉,隐喻的使用避免了单调平淡的平铺直叙,令诗歌更新奇、生动,吸引读者。当本体难于理解时,恰当的隐喻能够清晰地展现其内涵,更好地传达诗人的感情和用意,使诗歌富有感染力。隐喻可以折射出诗人对世界的体验与认知,体现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诗歌阐释的根本任务是对诗歌隐喻的把握”[8]。
“诗歌语言是一种旨在唤起或引发意象的语言游戏”[9],可见意象是诗歌中的核心要素,古典文学专家袁行霈先生对其做出了如下定义:“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10],由此我们得知,意象的使用是诗人的一种思维方式,体现了诗人对世界的认知。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来讲,诗歌意象和概念隐喻的认知机理相同,二者均由联想的方式生成:“隐喻形成的基础就是发现互相联系的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把本来看似完全属于不同范畴领域的两种事物联系起来。”[11],而意象的产生是由诗人经过大脑的联想加工,对已知的客观物象产生新的理解,融合自己的感情后,赋予其以新的内涵而得出的。因此二者的产生过程都可以用“映射”的概念来解读。诗人将熟知的具体物象映射到抽象事物上,从而形成对抽象事物新的认识。比如,“竹子”是古汉语诗中常出现的一个意象,具有坚韧挺拔的特点,诗歌中“竹子”这一具体意象被映射到目标域“人类的品格”这一抽象事物上,使得人们生动形象地理解了目标域。所以,诗歌意象本质上是一种概念隐喻。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古汉语诗歌翻译中,对意象隐喻的把握成为译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意象隐喻翻译并非仅仅是修辞层面的语言符号转换,更为重要的是隐喻背后的深层含义和情感,译者需要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以合适的方式用英语表述出来,这一过程既涉及语言的运用,更有认知的过程,而二者都离不开文化的影响。人类生理构造和生活经验的相似性决定了汉英两民族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具有共通性,自然会产生许多相同的隐喻概念和语言表达。但不同民族的文化又各具特色,认知体验不可能全部一致,这些差异表现在语言之中,于是隐喻便打上了特定的文化烙印。比如,“狗(dog)”这一意象在汉语里常用作贬义:狐朋狗友、狼心狗肺,而在英语中恰恰相反,“lucky dog”是形容幸运者的说法。
正是由于意象隐喻的文化特异性,在古诗意象汉译英时就难免会遇到障碍,由于意象隐喻集中体现诗歌的特色,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因此如何处理此类翻译便成为一项重要内容。
汉译英意象隐喻翻译要求译者首先确定隐喻中本体和喻体的联系,然后在英语文化中找到与原作相契合的意象,进行转换,恰当地表达出来。既然意象隐喻是一种映射过程,那么我们可以把汉英语言中的两个喻体之间也看成是映射的关系,即汉语中的喻体是源域,英语中的喻体为目标域,翻译就是找出二者之间的相似点,进行对应。这就要求译者具备较高的认知能力,全面把握英汉文化中的概念,选择能够引起两种语言读者相似反应的、高度契合的意象。此外,这也检验了译者的双语水平,不仅要自己理解,还需能用语言完全展现给读者。在选择英语喻体时,应为多数读者熟悉的事物,否则引发读者对本体的理解困难,就违背了隐喻的初衷。
(二)古汉语诗歌意象翻译方法
纽马克(Newmark)指出:“隐喻翻译是一切语言翻译的缩影,因为隐喻翻译给译者呈现多种选择方式:要么传递其意义,要么重塑其现象,要么对其进行修改,要么对其现象进行完美结合”[12],针对这些不同的目的,我们在翻译古汉语诗歌中的隐喻时应采取不同方法。通过分析不同译作,并根据喻体在原语和目的语间的不同对应关系,笔者总结出四种翻译方法:保留喻体直译法、转换喻体法、隐喻移植法和省略隐喻法。
1.保留喻体直译法。前面说过,同处于客观世界的人类具有相似的认知体验,因而存在隐喻思维的共性,不同民族分享着许多相同的隐喻概念和表达方式,汉语诗歌意象隐喻英译最理想的情况是在英语中保留原诗的隐喻特征,包括完整无缺的隐喻意象,做到既完全忠实于原作,再现原文的隐喻含义,又展现出诗歌的艺术感染力。例如,许渊冲将《长恨歌》中的著名诗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直译为“On high,we’d be two lovebirds flying wing to wing;/On earth,two trees with branches twined from spring to spring”,原诗用“比翼鸟”和“连理枝”作为意象,都是成双成对的事物,隐喻夫妻恩爱,永不分离,这种映射在英语中同样存在,因此保留原喻体直译即可,如果抛弃原意象进行翻译,如Fletcher译本“We swore that in the heaven above/We never would disport/One tomb on earth enclose of us/The frail and mortal part”,则剥夺了读者的想象权利,无法体会原诗含蓄的美感。再比如,《诗经·周南》第六篇《桃夭》是一首祝贺新娘出嫁的诗,开篇即运用隐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源域是盛开的桃花,映射至目标域女子的美丽上,用鲜艳的花朵比作少女的美丽,西方同样也有类似的意象隐喻: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的著名诗歌 A Red,Red Rose(《一朵红红的玫瑰》)中写到“O,my luve's like a red,red rose”,将自己的爱人比作美丽的玫瑰。所以,汪榕培保留原诗意象,将《桃夭》第一句译为“The peach tree stands wayside,/With blossom glowing pink./Iwish the pretty bride,/Affluence in food and drink.”,传神逼真,让英语读者产生相似的认知过程,品味原作的韵味。
2.转换喻体法。中西方民族认知体验的差异同样通过语言反映出来,很多情况下,同一隐喻概念在汉英两种语言里借助不同的喻体体现,即用不同的源域概念来映射相同的目标域概念,此时,译者可以在英语中寻找等效的喻体,传达与原诗一致的喻义,让中西方读者产生相似的认知效果。仍以《诗经》为例,《关雎》首行写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雎鸠”是中国特产的珍惜鸟类,汉文化中常用来隐喻爱情,西方世界不存在这一物象。但英语也有用鸟类隐喻爱情的情况,“turtledoves(斑鸠)”就隐含“情人、爱人”的含义,因此在翻译这句诗时,可将“turtledoves”作为替换喻体,使英文读者能够顺利获得与汉语读者相似的认知。类似地,“鸳鸯”因其出双入对的习性,也成为汉语诗歌中象征爱情的意象,《长安古意》中就有“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在西方,“lovebirds(情侣鹦鹉)”也因与伴侣形影不离而用来指恋爱中的人,所以,此处用它来替换“鸳鸯”的喻体意象,能使两文化读者间产生相似的映射。
3.隐喻移植法。若原诗中的隐喻框架为汉语所独有,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因而无法在英语中找到同样或相似的喻体,则译者可以将汉语中的整个隐喻框架移植到英语中,为便于读者理解,必要时还可以添加注释,点明喻义。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能够让英语读者更多地体会汉语的文化特色,丰富认知思维,扩大英语的语言表达。例如,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用“豆子”和“豆萁”的意象来比喻兄弟,英文中没有此种隐喻,该意象又贯穿全诗,若将其全部替换为其他意象则完全改变了原诗的风貌,因此,许渊冲采取了直译加注的方法,题目 “WritingWhile Taking Seven Paces*(星号表示后文有注释)”,全文为“Pods burned to cook peas,/Peas weep in the pot:/ ‘Grown from same root,please,/Why boil us so hot?’”另附注释“*The poetwon the favor of his father for his literary talent and lost that of his eldest brother,who later became the first emperor ofWei and ordered him,under pain of death,to compose this poem within the time of taking seven paces.”如此便完整地保留了原作的意象隐喻,也不会造成读者的理解困难。
4.省略隐喻法。当英语中既没有与原诗中对等或相似的隐喻,移植隐喻也不能被读者接受时,译者只好舍弃原作中的隐喻,将其意义翻译出来即可。比如,“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中的“牵牛织女星”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由中国古典神话传说而来,代表了缠绵悱恻的感人爱情。翻译时,在英语中找不到相同或相似的源域概念,因此无法直译或转换喻体。添加注释进行隐喻移植虽是一种方法,但在这里若想要清楚地阐释意象,注释未免会太过冗长,影响读者阅读体验,所以许渊冲将这句诗译作“The steps seem steeped in water when cold grows the night,/She sits to watch two stars in lovemeet in the skies.”舍弃了原诗的隐喻,直接译作“two stars in love”,将喻义译出,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翻译古汉语诗歌中的意象隐喻时,首先应明确汉语隐喻中的文化内涵,而后努力在英语中寻求对应的喻体,力求实现汉语意象和英文意象的“映射对等”。一般情况下,应尽力照原形象保留隐喻,不宜通过解释的方法淡化诗的形象,减弱艺术感染力。
三、结语
隐喻全面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媒介,纽马克甚至指出,英语中四分之三使用的是隐喻语言[13]。以语言取胜的诗歌当然更离不开隐喻,隐喻意象是传达诗歌韵味的核心,其翻译的好坏决定着汉语诗歌英译的成败,但同时隐喻意象富含丰富的文化内涵,想要做出准确恰当的解读并进行翻译,并非易事。概念隐喻理论从认知语言学角度阐释隐喻现象,为我们理解诗歌内涵和研究英诗翻译提供了新思路。我们总结出多种汉语诗歌意象隐喻的翻译方法,译者在翻译古汉语诗时,需要对诗歌隐喻进行全面、立体的解读,只有在透彻理解诗中的意象隐喻、掌握其深层内涵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方法加以灵活运用,才可能在译作中再现原诗风采。
[1]乔治·莱考夫.隐喻的现代理论[A]∥德克·盖拉茨.认知语言学基础.邵军航,杨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98.
[2]孙毅.认知隐喻学多维跨域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8.
[3]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1.
[4]UNGERER F,SCHMID J.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114.
[5]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696.
[6]胡壮麟.认知隐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4.
[7]于莹.认知理论关照下的隐喻翻译策略[J].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8(3):39-42.
[8]云虹.隐喻:诗歌的家园--论中英诗歌隐喻及其理解[J].当代文坛,2008(6):89-91.
[9]束定芳.论隐喻的诗歌功能[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6):12-16.
[10]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63.
[11]刘冰泉,张磊.英汉互译中的认知隐喻翻译[J].中国翻译,2009(4):71-75.
[12]NEWMARKP.Approachesto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a:112-113.
[13]NEWMARK P.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b:85.
(责任编辑:江 玲)
On Image Trans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Metaphor Theory
LIU Xuan
(School of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1)
Traditionalmetaphor studies had focused on its rhetorical features until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explained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They proposed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holding that instead of being amerematter of language,metaphor is also amatter of thought,which sheds new light onmetaphor translation study.As images are a key part of poetry,special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them in poetry translation.This paper explains the relation between cognitive metaphor and poetic image and comes up with some generalmethods ofmetaphorical image translation for ancient Chinese poetr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pecific examples.
cognitivemetaphor;image;poetry;translation
H059
:A
:1674-2109(2017)05-0031-05
2016-11-03
刘譞(1991-),女,汉族,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