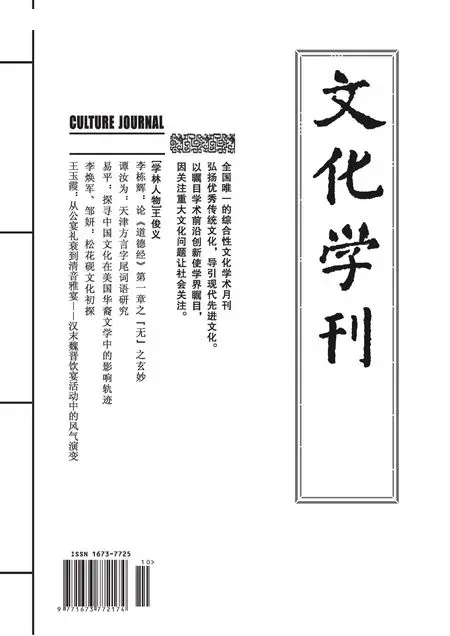儒教的衰亡
——重读《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朱渊博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广东 珠海 519087)
【责任编辑:周丹】
【文化纵横·文化书评】
儒教的衰亡
——重读《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朱渊博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广东 珠海 519087)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洞悉了儒教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和发展本质,并预示了儒教中国的衰亡。本文通过对比多方著作,并根据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的根本矛盾,结合共产主义作为新价值观的兴起和君主制的覆亡,分析儒教在中国衰亡的必然原因及不可逆的事实。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儒教;共产主义;相对主义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阐述了儒教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其以一种社会结构和思想统治的存在形式,以及独特的与君主共生的生存方式,使得在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得不在废除封建君主专制的同时,将与其依存的儒教连根拔除,而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处于当时“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动荡局势下所爆发的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的矛盾,导致了儒教崩塌之后价值空心化,并急需新兴价值和思想体系填补这一空白,而这一被人民所选择的新兴价值便是共产主义。对内,君主制的崩溃,以及难以与历史相协调的落后,致使自身发展深陷泥潭;对外,现实环境的紧迫,新兴价值和思想体系的出现与取代,在西方文化的大力倾轧下,儒教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放弃。当代,其建立的根本已经被打破,儒教失去了卷土重来的思想基础与物质基础,它的衰亡是不可逆的。
一、儒教衰亡的自身原因
儒教衰亡的发端并非是传统所认为的源自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作为一种社会的伦理构架,其思想的核心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然陷入了困境。列文森称儒教中国仅仅具有历史的意义,在现代已成死物,他认为“历史超越了儒教”。[1]从前的儒家常常研究过去,这是由于他们确信过去的经典思想具有内在的同时代性和普遍的联系性,确信其固定的价值标准是绝对普遍适用的,而在比较阅读《展望永恒帝国》《历史上的理学》和《从理学到朴学》等著作后,可以看到从春秋时期对于圣王的无限崇拜,到汉唐对于圣人再现的期待与推崇,再到宋明对于传统经典的反复斟酌和阐发新论,知识分子所期望达到的目标逐渐降低,对于儒教的传承,也渐渐跟不上时代历史变迁的步伐。到清朝,考据学派甚至怀疑汉以来经典的真实性,被长久认为真理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也被放到了讨论的会议室。当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出版,剑锋既毁灭了古文经,也未建立可信的今文经,经典在唯物主义历史学家手中成为了研究历史的史料。现代的儒家又相对主义地认为,儒教仅适用于中国的历史,现代的反儒家人士更进一步认为,儒教仅适用于中国早期的历史,对于当今社会发展失去了普适性。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展望永恒帝国》中曾讨论过的君主与儒教的关系,那便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可离其一。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君主既明白儒家士人对于君主的理论要求与限制,同时也不得不通过儒教这一系统来为其巩固统治、输送人才,而儒家士人亦需要且只能通过君主来追求出将入相,从而实现“齐家、治国平、平天下”的圣人使命,并承担监督君主的重大责任,因此,君主与儒教构成了亦敌亦友的共生之态,但在清末,君主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从湘军捻军的兴起,到东南互保条约的签订,最后到民国的诞生,在民主的呼声中,君主制已被瓦解,而与君主制相共生的儒教则遭遇了历史的淘汰,衰亡在所难免。
二、儒教中国衰亡的外部原因
(一)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利用文人画为我们展现了儒教中国的文人理想。中国官僚士大夫具有明显的非职业化倾向,作为官员,他们并非依托强力的行政能力登上天子堂,而是通过本质具有审美化的、是目的而非手段的科举考试,即所谓的“学而优则仕”。中国官僚士大夫凭借文化涵养获得政治权力,其在为官的同时,还要掌握甚至精通琴棋书画等技艺,这样一种社会现象恰恰反映了孔子“君子不器”的教诲,“器”为专家,而“君子”为非职业化的士人,那么非职业化在列文森教授眼中就成为了儒教中国精神理念中最重要的特征,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西方所树立的是职业神圣化和专业化的社会理念,因而儒教中国的非职业化与西方社会的专业化是天然的反义词,具有对立性。于是列文森教授便将儒教中国称为传统,将西方称为现代。
当鸦片战争爆发,传统与现代便发生了战式的碰撞,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境地,随着民族主义兴起,求富求强成为知识分子的追求目标。处于传统和现代夹缝中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中体西用的折中主义,或是梁启超的物质精神二分法,还是严复对于“孝道”的固守,都是一种精神上的挣扎,他们希望利用调和主义来使传统、现代和谐相处,但是在列文森看来,传统与现代是对立的,西用恰恰为传统敲响了丧钟。传统与现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可调和的,在《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中,无论这些知识分子是保守派或是激进派,都陷入历史与价值的抉择,即感性上倾向历史,理性上又重于价值。面对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的割裂,“文化认同”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这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兴起预埋了伏笔。
(二)儒教中国与共产主义中国
1.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共产主义填补了儒教衰亡的精神空白。在德里克先生的《革命与历史》中提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普世化的进化论假定,即“一个所有人类社会都要逐级爬升的阶梯,尽管速度有异,但最终都会到达共同的顶端”。[2]共产主义在坚定富强信念的同时,也为处于两难境地的知识分子起到了历史与价值之间缓冲的作用,更关键的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蕴含着相对主义,解释了世界是处于不断发展中的,这也就为儒教的衰亡奠定了理论基础,因为在这个理论的支持下,有兴盛便会有衰亡,儒教的衰亡理所当然,而对新价值的需求也是正常不过。同时,在共产主义者们看来,儒教文化具有相对性,儒教只是属于符合古代中国那一段特定的时期,它的意义存在于过去,在现代历史中,许多革命主义者在探讨中国的历史分期时,能够在相对的历史分期中注入绝对的历史意义,以抚慰传统衰亡对心理的创伤,而这又是反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所无法做到的,反传统这一行为虽然使社会不得不做出转型,但是对于自由主义者则是损失,是一次替别人作嫁衣的行动,因为他们损害了知识分子在矛盾中的痛苦情感,并迫使他们转而投向共产主义的怀抱。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已是大势所趋。
2.儒教中国衰亡的不可逆
1949年共产主义中国成立,与儒教中国不同的是,它的兴盛不是中国传统的“天命”轮替,也不再称之为道统的转换,而是建立于革命和解放战争。德里克曾说到,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就在于使中国人意识到思想与价值不是超历史的永恒存在,而是特定的社会经济存在的产物,并使其深入到民间,成为大众的思考习惯。这种特殊的相对主义,将儒教尘封在过去特定的社会经济中,新中国等同于儒教中国已是无稽之谈,当代修缮孔庙、修复文化遗迹并不是要重新恢复儒教的荣光,而是真正的把儒教放入历史,放入陈列馆,放入博物馆,让人们缅怀历史,绝不会再重蹈儒教的覆辙,真正地把儒教当作被审美的目标。尤其在如今不断向现代意识潮流靠近而解读经典的过程中,经典本身已经作为了被审美的对象,而审美产生距离,传统与现代已经被割裂了。要求专一与永恒的儒教与普遍怀疑的现代思考习惯相遇,其注定不会再一次成为构建社会的理论体系,由整体回到部分,儒教的衰亡是不可逆的,但是儒教不同于儒学,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对于新的符合国情的文明面貌的精神要求,儒学这一蕴含着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历史馈赠,既是时代的潮流,也是无可反驳的选择,儒学精神必然会以塑造人性、培养社会道德文明的一种形式重新繁盛,但儒教中国的荣光一去不复返。
“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同样会全球化,当某一天,世界主义真的成真,也就是国家的博物馆成为了世界的陈列馆,孔子将同苏格拉底一般作为世界人的祖先,多元文化的混合,儒教中国已难以再复兴了。”[3]
[1][3]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郑大华,任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5.
[2]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3)[M].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
【责任编辑:王崇】
B712
A
1673-7725(2017)10-0237-03
2017-08-01
朱渊博(1996-),男,山西太原人,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