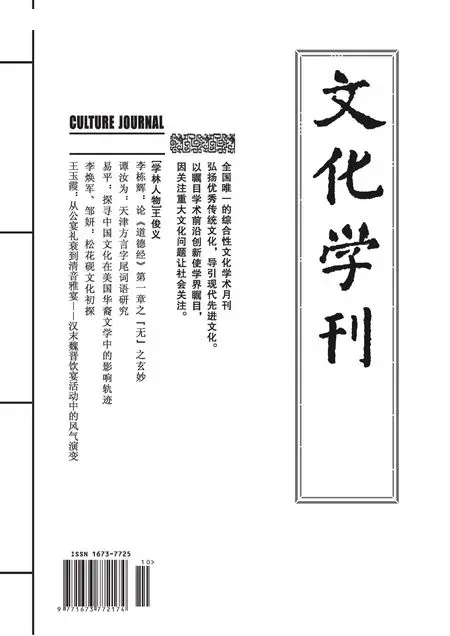京剧何以成“样板”?
——探究京剧艺术成为文革宣传工具的原因
李 萌
(天津体育学院运动与文化艺术学院,天津 301900)
【责任编辑:董丽娟】
【文史论苑】
京剧何以成“样板”?
——探究京剧艺术成为文革宣传工具的原因
李 萌
(天津体育学院运动与文化艺术学院,天津 301900)
“样板戏”诞生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年代,作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选择以京剧这种传统艺术形式承载其“革命”的宣传内容,必然有其深刻的原因与内在逻辑。本文旨在讨论京剧艺术本身的特征,对于文革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内在要求所具备的适应性。从表现形式上的符合需要、创作原则上的相互吻合、受众群的广泛庞大三方面,加以具体论证。
京剧;样板戏;意识形态;程式性;三突出;受众群
绪论
“样板戏”*这里有必要首先理清一个概念。“样板戏”一词源于《人民日报》1967年5月31日的评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而被确定为样板戏的文艺作品只有8个,它们是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后来陆续出现的京剧《平原作战》《龙江颂》等9部作品,不在“样板戏”之列,而被称为“样板作品”。文革中流行的小说、诗歌、舞蹈、故事片都已伴随文革的结束而被观众抛弃;样板戏与“样板作品”中的舞剧、交响乐、钢琴曲,囿于技术与市场的限制条件,也渐渐湮没。不论在文革中还是文革后,在数量上还是影响力上,样板戏中的京剧作品都远胜于其他艺术形式,基于此,本文所探讨“样板戏”概念,主要指代的是8个样板戏中的京剧作品,以及之后陆续出现的“样板作品”中的京剧;既包括它们的舞台版本,也包括以之为对象所拍摄的电影,而这也是大众对于“样板戏”的直观概念。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无疑是为了实现政治宣教功能而产生出现的。然而对于试图建立全新社会图景的“文化大革命”而言,为何选择依照文革话语属于“腐朽文化”的京剧,作为其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承载形式?京剧现代戏最终成为“革命文艺”的样板,这一看似有违常理的重要决策,背后必定蕴含着经过深刻推敲的合理性。
本文旨在讨论京剧艺术本身的特征,对于文革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内在要求所具备的适应性。从表现形式的契合、创作原则的吻合、受众群广泛庞大三方面,加以具体论证。
一、“形式的意识形态”:样板戏与京剧“写意性”追求上的契合
王元化在阐述东西方艺术传统的特点时,曾经提出“模仿说”与“比兴说”的概念,即西方艺术侧重模仿自然,中国艺术则重于比兴。“模仿说以物为主,而心必须服从于物。比兴说则重想象。表现自然时,可以不受身观限制,不据守于自然原型,而取其神髓,从而唤起读者或观众以自己的想象去补充那些笔墨之外的空白。”[1]依照这一理论,讲求留白的中国书画艺术是典型的“空白艺术”,而上马没有马、开门没有门的京剧,显然也属此类。
京剧界与京剧研究界,经过长期的探讨总结,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即京剧艺术具有“虚拟性、程式性、写意性”三大基本特征,而深究这三大特征的内部关系,可以概括为京剧是以“虚拟性”为核心,通过“程式性”构建起的“写意性”的艺术体系。
基于这一论断,京剧艺术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它的高度写意性。所谓“写意”,体现在京剧艺术从不执著于模仿现实,不为观众制造——甚至拒绝制造——舞台幻觉;而是将生活虚拟化,从而契合“以意为主”的审美原则,使之符合主体(其中既包括创造者,也包括欣赏者)的意志和愿望。但这并不意味着京剧脱离了生活之源,而是指其放弃了对生活真实的“还原”,转向追求一种“神似”,“出之贵实,用之贵虚”[2]。这种写意品格,决定了京剧有着更高的理想化视野,与受“模仿说”支配的写实艺术的存在区别,自然也就不能以后者的批评理论来衡量前者。
强调这种以“虚拟性”为核心的“写意”是通过“程式”建构起来的,是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并不能直接看到写意性,如果我们将“写意性”比作灵魂,那么它无疑附着于程式的肌体之上,一方面指导着“程式肌体”的形成、发展,另一方面又必须借助这一肌体实现传达。
“程式”一词最早出自《荀子·致仕》,其解释为“物之准也”,即事物的规程、规范、法式。就京剧艺术而言,依照一整套人为设立的标准,使表演规范化的形式便称作程式。京剧是程式化发展到巅峰的代表性艺术,京剧表演即是一种“程式思维”(阿甲语)。“京剧舞台上不允许有纯属自然形态的事物原貌出现,一切生活的自然形态,都需要按美的原则予以提炼、概括、夸张、美化,使之成为节奏鲜明,格律严整的技术格式(即程式),才可以在舞台上表现出来。”[3]京剧将角色分为生、旦、净、丑四类行当,又运用特征鲜明的面部化妆、服饰搭配,来帮助观众辨别这些行当角色的忠奸善恶。最典型的面部化妆的例子,就是净、丑两行当的脸谱(生、旦两行基本是没有脸谱的,但譬如生行角色所挂的“髯口”,也部分的体现人物性格特征)。京剧脸谱包含颜色和图案两大元素,蕴含着褒贬强烈的是非观。就脸谱颜色而言,红、黄、黑、白、蓝(绿)几种基本色调,各被界定为一类抽象化、典型化的性格(也是命运)特征。在此基础上,人物的行为举动,都按照这一既定的性格特征发展,好人绝对的好,坏人绝对的坏,而京剧服饰也是程式化的,“宁穿破,不穿错”的行头起到了标志人物身份、注明人物性格或者品评人物善恶美丑的作用,从而强化脸谱化的角色面貌。
规范性是“程式”的基础,经过一定的强化训练,就会形成一种在演员和观众之间可以默契交流的“语言”。从人物的第一次出场开始,观众就可以通过外观判断其忠奸善恶,甚至进行人物命运(也就是故事走向)的预知。有了这样普遍存在的艺术实践作为基础,京剧的“程式性”特征已不仅流于形式层面,而是上升到了内容层面。按照美国文艺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提出的说法:“形式是作为内容来理解的。”形式里蕴含着“政治无意识”,即所谓“形式的意识形态”[4]
这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可以被理解为是原本属于内容的意识形态,外化成为一种形式,并通过形式的固定性得以确立,最终形成了一种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形式。
如前所述,在我们指出京剧具有“虚拟性、程式性、写意性”这些形式化的特征倾向的同时,绝不意味着它没有内容,但实际上,基于“表演艺术体系一旦成熟,而且能够独立时,便必然限制和排斥文学性”[5]的艺术规律,表演体系高度成熟的京剧,所强调的又正是重形式审美而轻内容欣赏。我们发现京剧传统剧目在内容上呈现出主题的浅显单一化、情节的简单化、语言的俚俗化的特点;而内容背后,又包含着“忠孝廉节”“君臣父子”这类简单、抽象的道德观念和伦理标准作为主题内核。用技巧高超、形式完美的外壳包裹道德原则,以程式化的方式反复灌输,观众的心理接受从不自然到自然。到后来,内容模糊为形式,程式变成了“形式的意识形态”。顺着这一思路推导可以发现,京剧的脸谱、服装、音乐,这些原本属于形式范畴的元素,无一不显示出具有内容高度的价值判断意义。当观众沉迷于对京剧形式的欣赏时,早已潜移默化的接受了形式之下的价值观。
作为虚拟性、写意性在舞台上的体现方式,程式的创立、形成遵循“不受身观限制,不据守于自然原型,而取其神髓”的美学原则,在处理生活材料时,诗化生活而非还原生活本身。戏剧理论家阿甲强调程式来自生活,“但不是生活的摹仿放大”,它是“在对生活进行概括、夸张、装饰、想象的基础上变形的结果”[6]。因此,程式从最初的创立,就蕴藏着一种浪漫倾向,必然的走向一条远离甚至拒绝再现生活的艺术方向,这是一种符合东方传统审美观的“重比兴”的表现精神,“形式的意识形态”特征也是在这种浪漫倾向下催生的。抽象道德原则只有借助“浪漫化”的程式外衣能实现价值观灌输。因此,当我们发现并归纳出京剧程式具有“形式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同时,等于找到了一种不必追求还原生活,摆脱了现实的拘束,完全主观化、自我化的艺术表达方式。
因此,京剧这一中国传统戏曲的典型,与“无产阶级新文艺”之间具备一种根本性的精神契合。官方意识选择将“无产阶级新文艺”的“新酒”装入京剧的“旧瓶”,所依循的是相当坚实的内在逻辑,而绝非随意的个人好恶。
这种逻辑的深层根源,在于无产阶级新文艺所要表现(或曰营造)的“行当化”的社会模式。所谓“行当化”的社会模式,是对1949年以后对于中国社会的阶级划分在文革中达到顶峰状态的一种描述。
一方面,“工农兵”“无产阶级”成为一个符号,成为一种光荣、神圣且富于感召力的新国民典范;另一方面,通过抽象的阶级划分对全社会重新命名,复杂的社会身份和个体的多样性被简单的标签替代,并且非“我”即“敌”——如果你不是无产阶级范畴的同志,就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敌人——善恶两分法的定位方式,“人”的内涵被抽象化、简单化为一个脸谱的颜色。
在“亲不亲”要靠“阶级分”的年代里,“行当化”成为人们看待、理解和掌握世界的最基本的文化方式之一。也许在现实生活中,个体人还在以具体的面貌出现,但“无产阶级新文艺”所要反映的社会包括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则与高度程式化的京剧舞台暗相契合。这种契合体现在两者都将自己的抽象理念付诸于规范固定的符号。按照这一思路,我们甚至可以将“文化大革命”本身视作一部超级大型的“广场京剧”,整个社会变成巨大的舞台,全体民众按阶级本质论划分行当(红卫兵、革命群众、反革命分子、走资派、修正主义者),依据官方流意识形态规范扮上不同的脸谱行头(袖章、军服、大高帽),通过固定的唱念做表(集会、游行),上演着关于阶级斗争的戏剧冲突。
如果我们从上面这个角度看待那个年代,那么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官方意识形态意图打造的“无产阶级新文艺”,期望为各阶级分别勾勒特征鲜明的脸谱,绘制一幅“阶级立场鲜明”“政治站队准确”的社会图景,因而“虚拟生活”的写意艺术,才是理想的负载“无产阶级新文艺”的体裁样式。所以,江青和她的样板戏创作团队在艺术形式上对传统京剧所进行的重要改造,虽然自称拒绝“旧瓶装新酒”,强调符合“无产阶级美学观”且“革命化”,但依然是在按照京剧的章法反映生活,即程式化的基本规范和内在属性(夸张性、鲜明性、稳定性)。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解读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打进匪巢”一幕对英雄杨子荣的艺术设计:匪首座山雕坐于威虎厅侧边,大厅气氛阴森,伴随强烈的阳光和雄壮的音乐,以智取为目的打进威虎山的杨子荣昂然出场,并始终居于舞台中心;而后通过载歌载舞的形式,舞台的主动权完全由杨子荣掌握,座山雕和群匪被牵着鼻子满台乱转;结尾,杨子荣手持联络图,脚踏虎皮交椅,群匪恭恭敬敬、俯首接图。按照写实原则看待这场戏,是完全经不住推敲的。然而,样板戏的创作者却偏要通过调度、布光、音乐等方面的非写实安排,专意突显英雄形象的高大英武、正气凛然。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智取威虎山》一部作品塑造英雄的特殊修辞,而是所有样板戏普遍呈露的艺术追求。
这些调度、布光、音乐,乃至具体人物在扮相、动作、服饰等各方面所体现出的固定特征,可以清晰看出创作者对于正、反两派的符号化区分。如果从艺术体裁的角度进行审视,就不难发现这些正是京剧程式化的某些表现。
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由于其“主题内容的形式化”,样板戏的主题本身也变成了一种程式——即样板戏中的领袖(英雄)崇拜。一方面,毛主席、共产党化身为万物生长依赖的对象──太阳(或曙光、朝霞、黎明、春风、雨露等与太阳有关的自然现象),在唱词、念白、舞美等方面反复出现。《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胸有朝阳”上威虎山会见土匪。《红色娘子军》里, 面对枪口的洪长青引吭高歌: “洒热血迎黎明, 我无限欢畅, 望东方已见那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找到了红军的吴清华以泪洗面:“想不到今天哪, 春风引我到这里, 找见了救星,看见了红旗。”另一方面,英雄人物除了依靠自身的机智勇敢之外,他们的成功更是因为有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与教诲,这就把英雄崇拜与领袖崇拜联系在了一起。例如, 《沙家浜》中阿庆嫂身陷窘境、徘徊无计的紧急关头, 耳边仿佛听到《东方红》的乐曲, 顿时信心倍增、计上心头, 唱道: “毛主席!有您的教导, 有群众的智慧, 我定能战胜顽敌度难关。”《奇袭白虎团》中严伟才在接到任务之后唱道: “毛泽东思想把我的心照亮。浑身是胆斗志昂。出敌不意从天降, 定教它白虎团马翻人仰。”需要看到的是,“‘样板戏’的领袖崇拜其崇敬的神并不是只是毛泽东, 而是他所象征的绝对性的神圣力量[7]”。这种通过造神来解决问题的叙事方式和其中蕴含的崇圣心态,都是典型的京剧化特征。
由此可见,这些不惜违背生活真实的音乐、调度和布光,脸谱化特征明显的扮相、动作及服饰,包括简单故事与直白的主题,都可以被理解为京剧的程式。因为它们完全符合程式夸张性、鲜明性、稳定性的特质。在程式的规定之下,样板戏对于人物的善恶预设性评判,又与传统京剧刻画人物时的创作原则吻合。费正清认为京剧是表现符码化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良好媒介,“它可以极大地减少对人物的心理刻画,而观赏起来仍饶有兴味。因为京剧中有传统的说唱、音乐、高度程式化手势和动作,功夫表演和惊险情节”[8]。
源于样板戏处理形式与内容关系时的内在要求,创作中的惊人“形式主义”标准——上至“三突出”原则,下至规定出服装上补丁的数量、位置——就都不难从京剧中找到解释。
二、“三突出”与“立主脑”“写一人”:样板戏与京剧在创作原则上的契合
尽管自诞生起就带着强大的政治基因,但样板戏毕竟首先是作为一种戏剧存在的,关于它的学术性探讨,不能仅仅局限于政治范畴之内。时隔近半个世纪,样板戏仍在舞台上受到观众的欢迎,证明了荒谬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艺术作品,在剥去政治外衣之后,仍然存在的艺术本体上的合理性。
近年来大量的关于样板戏的研究、评论,指向了样板戏对于传统京剧的发展、出新;而本文重在讨论样板戏对于京剧样式的选择,因此本章节探讨样板戏与传统京剧的在创作原则上的契合,以及样板戏对于京剧创作在符合艺术原则前提下所做的探索、发展。
关于样板戏创作原则“三突出”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1968年5月于会泳在《文汇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在其中,他提出了“三个突出”的说法。[9]而在以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的名义创作,发表于1969年第11期的红旗杂志,名为《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的文章中,“三突出”被正式提出。文中这样说道:“用反面人物的陪衬、其他正面人物的烘托和环境的渲染以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是无产阶级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10]文章进一步作出解释:“我们的经验是需要注意‘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11]自此“三突出”正式被提升至“创作原则”的理论高度,不仅成为所有样板戏尊奉的创作经验和原则,还被推广到其他艺术领域,成为当时一切文艺创作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
戏曲理论界一般把江青在1964年7月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后座谈会上的讲话《谈京剧革命》,视作是这位“文革旗手”第一次正式而且系统的表达自己的戏剧观,作为样板戏创作的领导者,江青在这篇讲话中谈到:“……剧本还是要主题明确,结构严谨,人物突出,不要为了几个主要演员每个人来一段戏而把整个戏搞得稀稀拉拉的。京剧艺术是夸张的,同时,一向又是表现旧时代旧人物的,因此,表现反面人物比较容易,也有人对此很欣赏。要树立正面人物却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树立起先进的革命英雄人物来。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干瘪瘪。领导上亲自抓……把杨子荣和少剑波突出起来了,反面人物相形失色了。”[12]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三突出”原则的一些初始理念。如果把其中一些诸如“树立革命英雄人物”之类的政治话语去掉,其实江青讲出了京剧,乃至所有戏曲创作中的一条基本原则:写戏要突出重点,不能太“散”。这是一句谈不上什么创见性的基本剧作法则,但透过它,却可以使人联想到中国戏曲的基本创作原则“立主脑”。
清初著名剧作家、戏剧理论家李渔,是这样提出“立主脑”的概念的:“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如一部《琵琶记》,只为蔡伯喈一人,又只为重婚牛府一事……“重婚牛府”四字,即作《琵琶记》之主脑也。”[13]
依照这条理论去套任何一部样板戏的剧情与主题,会收到很奇妙的效果。把蔡伯喈换作杨子荣或者严伟才,把剧名写成《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将主题易为“智取”“奇袭”,我们发现这段话依旧成立,毫无违和感。
由此看来,“三突出”与“立主脑”之间的确具有关联性,存在相似之处。这种关联与相似体现在对于“剧作的首要任务,应当突出主要人物”这一点上的高度共识,但仔细比较不难发现,“三突出”与“立主脑”又有很大不同,李渔所说的“主脑”除了主要人物之外,还包含主要事件,二者地位同等重要,而作为创作原则的“三突出”,则只强调了突出主要人物。
这种现象的根源,同样可以上溯到江青的另一戏剧理论“根本任务论”,她强调:“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14]从这一“根本任务”以及样板戏创作过程中的具体过程来看,我们发现,虽然这一创作原则被概括为“三突出”,但最后一条“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才是核心关键。《红旗》杂志上的文章本身,对此也表述得相当明确。
“三突出”原则与“立主脑”在强调突出主要人物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大到整个中国古典戏曲理论范畴,则不难发现,“立主脑”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说法。金圣叹在评点《西厢记》时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西厢记》只写得三个人,一个是双文,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其余如夫人,如法本,如白马将军……他俱不曾著一笔半笔写……若更仔细算时,《西厢记》亦止写得一个人。一个人者,双文是也……《西厢记》止为要写此一个人,便不得不又写一个人。一个人者,红娘是也。若使不写红娘,却如何写双文……”[15]
如果相较于“三突出”对于突出主要人物的强调,“立主脑”还关注主要事件的话,那么金圣叹的“写一人”则与“三突出”原则更为相似、接近了。
虽然无法断定“三突出”原则的提出直接来自于“立主脑”“写一人”,但它们在理念上的相似性,绝不只是一种巧合。李渔和金圣叹的见解,是基于他们对于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的大量观摩、实践所获得的体悟和总结,是对于中国传统审美意识和戏曲艺术规律的凝练的概括;反之又由于他们的见地和影响力,使得他们的见解影响了戏曲艺术的创作,进而植根于中国人的审美意识,而作为当时中国最为优秀的一批艺术工作者(包括作为京剧内行的江青本人),样板戏的创作者们显然也深刻的了解这种戏曲创作规律与中国传统的审美观。所以,不论“三突出”的提出者们如何高呼破旧立新,他们都无法摆脱传统戏曲审美意识与戏曲艺术创作规律对于他们的影响与制约。
由此可见,作为文革中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样板文艺”,之所以会选择京剧这种艺术样式,是有其深刻而必然的原因与逻辑的。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京剧的创作理念,对于样板戏所追求艺术表现目标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对于非红即黑、非善即恶的文革思维,以及在这种思维下形成的艺术理念而言,只有非写实的、夸张变形的京剧,才有可能在“三突出”原则的指导下进行较为合理的艺术展现,而当这种艺术理念和创作原则强行地加诸电影、小说或者话剧时,我们只需要去简单的审视一下文革时期诞生的其他形式的艺术作品,就会对那种荒诞的效果了然于心。
三、“最易动人耳目者,最易动人之心”:庞大受众群所具有的宣传效果最大化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事”是否可以做到“善”、做到什么程度的“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器”的合用与否。作为宣传意识形态的工具,为了追求效果的最大化,“样板”究竟要以什么“戏”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而京剧艺术之所以作为一种“利器”最终被选中,除了前面所说的京剧艺术本身的规律和特点对于样板戏这种政治宣传工具的要求具有内在的契合之外,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京剧广泛的受众群、巨大的影响力和庞大的演出队伍远超其他艺术形式。
这种状况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与内在逻辑的。
历史的看,古老的自然经济社会聚落分散、交通阻隔,观看戏曲演出不仅是广大民众的娱乐方式,更是一种公众聚集环境下的社会交往,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参与公共生活的渠道。一段关于清初江南乡村演戏时盛景的记载:“观者方圆数十里,男女杂沓而至,男子有黎而老者,童而孺者,有扶杖者,有牵衣裾者,有衣冠甚伟者,有竖褐不完者,有躇步者,有蹀足者,有于众中挡拨挨枕以示雄者,约而计之,殆不下数千人焉。”[16]可见,戏曲在漫长历史中已经超出了我们通常理解审美的功能,具有了更加丰富的社会意义。
戏曲之所以具有这样巨大的社会影响力,重要的原因在于其通俗易懂的特点适合于缺少文化教育的庶民百姓。同时,由于戏曲并不追求过分复杂的故事情节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所以,浅显直白的主题,往往更容易在喧闹的表演环境中,被数量巨大的观众理解和接受。戏曲艺术在形成、发展、兴盛的过程中,以几百年的时间,完成了为适应中国社会各阶层审美需要而进行的自我改造,并以自身的艺术形态、风格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意识,而京剧作为戏曲艺术中高度成熟、典范、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最大剧种,自然成为一种最为深入国人之心、影响力最大的艺术形式。
自清末以来,京剧的鼎盛期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仍未出现明显的衰落。建国后,虽然仿效苏联,在大城市建立了专门的话剧、音乐、舞蹈院团,但由于艺术水平和观众欣赏习惯等原因,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戏曲艺术依然是影响力最大,观众人数最多、观众层最复杂的艺术形式。
解放之初,由于戏班本身及其内部人员的高度流动性,对于戏曲从业人员的数量,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我们从两份当时的戏改运动中,关于组织艺人学习的报告中,得窥全豹:“截止1950年12月,全国除老解放区及东北外,已有17个省开展了这种学习,参与学习的100余个剧种的艺人达3万人,含老区及东北共约5万人。”[17]可见,在老区、东北及这17个省份中,就至少存在100余个戏曲剧种,而仅参与学习的艺人,就高达5万。马彦祥在1951年9月撰写的一篇文章,也指向了这个巨大的数目:“……东北全区9000余艺人中有5600余人参加了文化学习,……华东区,经过一次或数次以上学习的艺人,上海9000余人(包括前台职工),占全部艺人80%左右;南京约750人,占全部艺人60%;浙江1900人左右,占全部艺人45%;山东1000余人,占全部艺人30%;苏南1900余人,占全部艺人50%;苏北约1100人,占全部艺人45%;皖北900人左右,占全部艺人45%……全区经过学习的约17000人,约占艺人总数的45%。”[18]
从以上两则数据中,我们可以约略的看到建国初期戏曲剧团、演员的巨大数量。而在之后的剧团改革、登记后,戏曲院团的数目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伴随着大跃进不断激增,在1958年达到了一个峰值。随后,虽然由于国家的紧缩措施,剧团(这里主要指国营剧团)的数目有所缩减,但截至文革前的1965年,由文化部门管理国营剧团仍有753个。[19]
在这些庞大的戏曲剧团中,占有最大比例的是京剧剧团。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以及诸多的地区、市、县都建立了当地的京剧院团。我们可以从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的几个数据中,管窥京剧相较于其他戏曲剧种,无论在数量还是水平上的压倒性优势。这次会演共有全国23个剧种的30多个表演团体、1600多名演员参加,其中京剧占五个演出代表团,演员约380人;在88个演出剧目中,有17出是京剧;在获得个人最高奖项荣誉奖的七位演员中,五位是京剧演员;在获得演员奖的名单中,京剧演员更是占多数。
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20]正如俞樾在为余治的《庶几堂今乐》所做的序言中,对此所做的极为清晰的阐述:“天下之物最易动人耳目者,最易动人之心。是故老师巨儒,坐皋比而讲学,不如里巷歌谣之感人深也;官府教令,张布于通衢,不如院本平话之移人速也。君子观于此,可以得化民成俗之道也。《管子》曰:‘论卑易行。’”[21]
因此,戏曲的宣传、教化作用被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京剧具有最为庞大的演出团队和观众数量,以它作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使样板戏以京剧的形式演出,天然的就获得了最为广泛的受众群。
样板戏被拍摄为电影,可以通过拷贝大量传播;另一方面,一出样板戏剧目一旦成型,对于唱腔、身段、调度、伴奏等等,也就都有了相应的严格规范,京剧由于自身高度的程式化特点,非常便利于规范化、标准化的搬演、复制这些剧目,从而实现了样板戏在全国范围内的剧场(舞台)演出,而众多的京剧院团和京剧从业者,正是这种剧场(舞台)演出的根本保障。
综上可见,在上世纪60年代,相比于其他艺术形式而言,京剧具有影响广泛、易于接受、从业者与受众数量众多、覆盖社会层面广泛等优势,将其作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显然在形式上更易为人接受,从而收到效果的最大化。
结语
通过以上论证,可以看到文革中京剧艺术成为意识形态宣传的形式,所具有的深层原因和内在逻辑。从另一个角度也看到了京剧艺术自身特征所能达到的一种可能、一种效果。这种研究对于我们更加深入的理解京剧艺术、研究样板戏,以至于探讨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京剧在合乎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是否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由于水平和篇幅所限,加之掌握资料较少,本文还存在很多问题,作者乐于就此抛砖引玉,得到更多专家学者的批评指导。
[1]王元化.京剧与传统文化[A].翁思再主编.京剧丛谈百年录(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1.5.
[2]王骥德.曲律(杂论第三十九上)[M].
[3]吴同宾,周亚勋主编.京剧知识词典[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10.
[4]杰姆逊.政治无意识[A].[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59.
[5]黄仕忠.中国戏曲之宏观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87.
[6]林真,李春熹.实践中产生的真知灼见———评介阿甲戏曲理论的主要成就[J].戏剧论丛,1983,(1).
[7]李松.“样板戏”的领袖崇拜[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02):84.
[8]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9]于会泳.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N].文汇报,1968-05-23.
[10][11]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对塑造杨子荣等英雄形象的一些体会[J].红旗,1969,(11):128.
[12]江青.谈京剧革命——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67-05-10.
[13]李渔.闲情偶寄[A].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七册)[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4.
[14]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A].林道立.文学灾难的背后[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22.
[15]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A].品书四绝[M].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7.8.
[16][清]王应奎.柳南文钞[M].乾隆刊本.
[17]张庚主编.当代中国戏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32.
[18]马彦祥.1951年的戏曲改革工作和存在的问题[A].中国戏曲志·北京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338.
[19]傅谨.新中国戏剧史[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166.
[20]周敦颐.通书(列传第三十一)[M].
[21]俞樾.余莲村劝善杂剧序[A].春在堂全集之春在堂杂文(续编三)[M].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名誉社长:耿相新 社长:王刘纯 总编辑:董中山 主编:郑强胜★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双月刊邮发代号:36-10■《寻根》是由大象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化期刊。16开,144页,图文并茂,装帧精美,每双月10日出版,全年6期72元,全国各邮局均可订阅,邮发代号:36-10,您亦可直接汇款至本刊邮购。为答谢读者的厚爱,本刊特推出真情大回报活动:1.凡向本刊邮购2015年全年6期者,只要您寄72元(60元书款及12元挂号邮寄费),可获赠2014年《寻根》一套;2.凡向本刊邮购2016年《寻根》的读者,可享受8折优惠。(优惠价58元)☉特别关注 004 “许昌人”研究取得突破性进李占扬………………☉百家纵横 010 福隆堤与宋元以来岭南的水利建设谌小灵………015 明清时期黄运地区的“大王”和“将军”胡梦飞……022 太平天国起义对江南学术共同体的影响———以锡山秦氏家族为例梁秀坤…………………☉东西风 030 李凤苞笔下的柏林王室图书馆中文藏书及其与汉学家之交往李雪涛………………………☉民间文化 036 灵宝道情陆小燕……………………………………039 饮酒掌故吴正格……………………………………☉寻根扫描 044 两方墓志再现拓跋鲜卑“魂人”习俗段锐超………048 赣闽粤边区客家锡器探考李 聪…………………077 河南博物院藏三彩调鸟俑研究熊丽萍……………☉艺文杂谈 051 苏东坡四子之名与《易经》韩立平…………………055 “半”字入诗妙无穷牛 锐…………………………085 《赵氏孤儿》舞出忠义诚信苏 翔…………………☉寻根情结 088 夏鼐的“故乡情怀”及温州地方民俗王 兴………097 曾宏父与凤山书院李宗江…………………………☉田野调查 065 卢氏史家大院初探贾 鹏…………………………103 红庙高孝祠考察记张艳丽 齐立森………………☉旧刊寻踪 058 “一柳二罗”与《人生与文学》凌 夫………………☉序与跋 114 题跋与解印(《石韵卮言》代序)初国卿……………☉姓氏谈 111 邹平“西张氏”盛衰录卢兴国………………………118 赤心木与朱襄氏朱国林……………………………☉移民寻踪 121 夏威夷早期华人移民史张 岩……………………☉家族史 070 新城王氏家规家训的形成与发展王焕文…………124 《鄞东冰厂跟余氏宗谱》概述应芳舟………………130 明清歙县桂林洪氏家族科举研究陈淳子…………☉乡土影像 136 江西龙南的关西新围张文锋………………………☉文化遗产 140 留住乡愁的金昌木偶戏肖永辉………………
J821
A
1673-7725(2017)10-0190-08
2017-07-05
李萌(1989- ),男,辽宁抚顺人,主要从事文化产业、影视文化、戏曲艺术等研究。
——评张丽军《“样板戏”在乡土中国的接受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