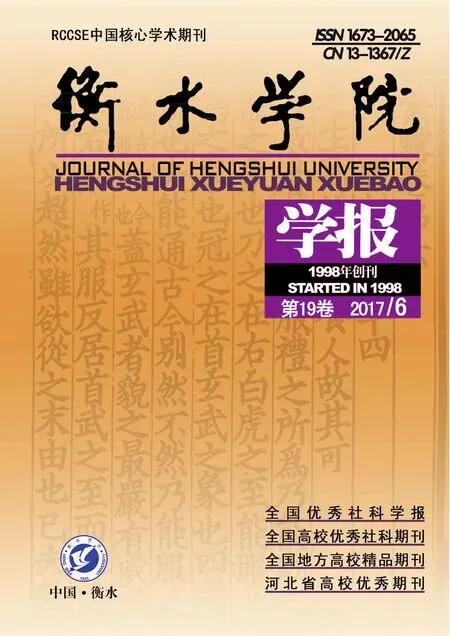佛教中国化第一人——释道安
王其谭
佛教中国化第一人——释道安
王其谭
(衡水道安文化研究会,河北 冀州 053200)
道安既不以中国既有的思想去桎梏佛学,也不原封不动地照抄印度佛教,而是在不违背佛教义理的情况下,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去诠释佛学,使佛学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道安统一“释”姓,改变服饰,使僧人生活中国化;建寺修塔,创规立制,规范僧人修行的中国化;组建译场,创建译论,注经作序,使佛教义理中国化;创宗立派,依玄解佛,使佛教信仰中国化;首倡爱国爱教、佛法不离世间,创政教关系的中国化。正是由于道安奠定了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的根基,才有了后来佛教在华夏大地的大发展,故被誉为“佛教中国化第一人”。
道安;佛教;中国化;冀州
释道安(312-385年),东晋冀州安平扶柳(今衡水市冀州区扶柳城村)人①。7岁开始读书,12岁出家,一生为佛教的中国化做出巨大贡献,被称为“东方圣人”。
佛教中国化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依据魏晋玄学而创立的“六家七宗”,最有影响的、正宗的,正是道安大师创建的“本无宗”。道安大师以玄解佛,以佛释玄,既不是以中国既有的思想去桎梏佛学,也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抄印度佛教,而是在不违背佛教义理的情况下,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去诠释佛学,使佛学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道安是开端,也是首创。他钻研经典、编撰经录、规范僧团、严持戒律,倡导实修实证,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开了先例,正是由于道安奠定了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的根基,才有了后来佛教在华夏大地的大发展,故被古今高僧学者誉为“佛教中国化第一人”、佛教中国化的奠基者。
李富华教授指出:“东晋时代道安和鸠摩罗什创造性的译经和著述活动是中国佛教宗派创立的最直接的源头,也是佛教中国化的真正开始。由道安开创的,由鸠摩罗什及其门徒们推广起来的中国佛教义理之学,实实在在地为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可以这样说……自道安、罗什始,中国佛教才有了自己独立的形态,这种形态就是南北朝时期在中国的南北广为发展的佛教义理之学。”[1]
一、统一“释”姓,改变服饰,使僧人生活中国化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开始只是一些印度和西域僧人,传教方式主要是翻译一些佛教经典,由于当时人们还不认识佛教,所以“佛教在汉代纯为一种祭祀。其特殊学说为鬼神报应。……佛教或其一也。祭祀既为方术,则佛徒与方士最初当常并行也。……汉代佛教依附道术,中国人士如襄楷辈,因而视之与黄老为一家”[2]37-41。到后赵石虎时,虽然佛教已从黄老中独立出来,但人们还弄不清什么是佛法。石虎问佛图澄什么是佛法,佛图澄答“佛法不杀”。石虎是历代皇帝第一个明令汉人可以出家的君主。由于他打破了汉人不得出家的禁令,鼓励汉人可以信佛教,一时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竟出家,佛教几乎成为后赵的国教。由此可见后赵是佛教真正在中国兴起的开端。
道安大师是佛图澄最得意的弟子,但是他不是像其师佛图澄靠神通传教,而是努力学习研讨佛教义理,以义理弘教。佛图澄圆寂后,道安大师离开邺都,在北岳恒山建寺立塔。由于他学识广博,声望甚高,因此名声远扬,信众极多。“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他的信众达到了河北人口的一半,跟随他身边的弟子达500多人,成为北方的佛教领袖。道安僧团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由汉人领导的第一个僧团,他为佛教的中国化开辟了道路,创立了榜样。由于他们生活在深山之中,地理环境、生活条件都不同于印度,所以穿衣、吃饭、住宿、修行都要打破印度僧人修行的习惯,得根据中国僧人的实际情况予以改变。这样也就促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转型,使中国僧人按照中国的地理、气候、人文等条件对印度佛教的要求予以调整,使印度佛教开始了走向中国化的道路。
1.僧伽服饰的中国化
佛陀在世时,为了使出家僧人安心修道,对僧人的衣食住行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对衣着的要求就是其中之一。为了使僧人断除一切贪欲,超越凡心,僧人的衣着达到御寒、遮体就可以了,穿衣要穿“粪扫衣”,即被世人遗弃的衣服,被火烧坏、牛嚼过、鼠咬过、女人的月经布、产妇血污布及死人的衣服等,经过洗涤而用之。而且衣服的颜色要求用染色,不能用正色。因此,僧伽服装又称“染衣”。具体说,僧衣又分三种,这就是“三衣”:僧伽梨、郁多罗僧、安陀会。为了让僧人表示与世间割断贪欲的决心,僧伽的服装是用剪刀将整块布料剪成许多零碎的小块,再缝合起来,称福田衣,亦称田相衣。
三衣是古代印度佛陀在当时特定环境下形成的,能适应印度的热带气候。但在中国夏季还可以,到春秋冬季显然不能御寒。特别是道安大师的僧团,住在恒山,夏季三衣也难以御早晚之寒冷,其他三季就不用说了,穿棉衣薄了都不行,更不用说赤脚,只有穿棉衣、棉袜、棉鞋,改变了印度僧人赤脚的要求,不然就不能维持僧人的生活,僧人的服饰中国化了。三衣只有遇到法事活动,作为法衣而用了。
2.僧伽饮食方法的中国化
在印度佛陀时代,为了让僧人安下心来修道,不动土伤害生命,僧人是不参加劳动的。根据印度的风俗习惯,在家人对出家人是非常尊敬的,这样出家人的吃喝由在家人供养。
佛教把僧人的饮食也分成了三种形式:“受请食”“众僧食”“常乞食”。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规定,那就是“过午不食”。总的说就是除信众请僧人到家吃饭外,其他方法就是托钵乞食。
道安僧团在恒山有500多人,当时的冀州由于战乱不断,大部分居民已南逃,没逃走的也因兵役灾害死伤无数,平原都人烟稀少,山中人烟就更少了,生活相当困难,出家人一个乞食还有乞到的可能,500人的僧团去哪里托钵乞食。他们只有依靠野果野菜、自种自食,或者很少的一部分布施。《高僧传》载:“复渡河依陆浑,山栖木食,修学。”[3]这样就改变了印度僧人不劳动,靠托钵乞食的方式,再加上修寺建塔,每天劳动,日中一食也就不能坚持了,僧伽饮食方式中国化了。
3.僧伽姓氏的中国化
佛教初传中国,到汉地传法的僧人的姓氏多以国名为姓,后来,有的以“佛、法、僧”三字为姓,还有的以师姓为姓。僧人姓氏的不同,对中国佛教之一体化发展极为不利,如依师为姓,往往造成小宗派观念,增加分别心,这样既不利于僧团的管理,也不利于僧人的修行。
道安俗姓“卫”,出家后第一个师父给起的法姓没有记载,拜佛图澄后姓竺。面对三个姓氏,自己收的徒弟姓什么,道安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想到了佛祖释迦牟尼,“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此“遂为永式”。道安的创举,开创了佛教僧伽统一“释”姓的先例,使僧人的姓氏中国化,一直延续至今,并影响到韩国、日本、越南等。
道安为僧人统一“释”姓,是一个创造,也为佛教的中国化打下了基础。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僧人统一姓氏为“释”,可以视为佛教与中国文化相契合的开始,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
二、建寺修塔,创规立制,规范僧人修行的中国化
1.僧伽道场的中国化
印度原始佛教对比丘个人而言,只要有一席之地即可安住,所以佛陀对比丘开始的要求是:“若树下起不碍头,枝叶足荫一坐。”因此,树下也就成为简易可求的住所;树下坐也就成为佛陀最初对比丘住所的规定。头陀行对住处的要求则是阿兰若、冢间、树下、露坐、随坐等更为苦行的五种形式。树下坐是最初之制法,后因瓶沙王施房舍之因缘,佛陀允许比丘接受檀越的布施。从此,树下坐及檀越布施成为比丘住处的两种来源。
中国不同于印度,印度处于热带,而恒山处于中国北部,平常季节山中气候都非常寒冷,到秋冬春季更是寒气逼人,不用说在树下,就是在屋内,穿得薄了,都难以御寒。因此,道安僧团在恒山就需要找山洞、盖房子、建寺修塔。要说在坟间修行,就更不可能了,因为中国的风俗人和鬼是不能在一起的。至于接受檀越的布施,当时正是五胡乱华,兵荒马乱,人们自己的住处、生命还不能保障,对刚刚入华的佛教还不了解,布施供养就不用谈了。这样道安僧团的住处道场就和佛陀要求的印度僧人的方法不一样了。他只有按照中国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人文习惯予以调整,这样僧人的住处、道场就中国化了。如道安大师在恒山现可考的有恒山寺、金龙寺,道安大师住过的两个洞穴还存在,有一个叫恒山寺伏虎堂;慧远在其家乡建的楼烦寺、白仁岩寺等。道安僧团每到一地都建寺修塔、弘法布教。据胡中才先生和释贵明先生考证,道安僧团到襄阳后15年间,修建寺庙有十几所。
2.僧伽仪轨的中国化
佛教传入东土,到道安大师时已300多年,但是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戒律。而僧人的行为要靠戒律来轨范。在恒山,道安大师面对500多人的僧团,僧人成分参差不齐,有为逃避徭役和兵役而出家的;有家庭困难,生活无以为计而出家的;还有因人生的不顺而出家的,真正为解脱出家的可能不是很多。这就为僧团的管理增加了难度。加上恒山的偏僻,吃、住、修行的困难,没有一个严明的纪律约束,管理这么大的僧团确实困难。为了整饬僧人纪律,他四方寻找戒律,道安曾派人去武遂法潜处得一部戒,并且采取制订《僧尼轨范》替代没有戒律的措施。道安400多人的僧团到达襄阳后,习凿齿与谢安书云:“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伎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从习凿齿向谢安推荐,可以看出道安僧团管理有方,不然,就不会出现习凿齿所看到的景象。
道安大师创造的适应中国国情的《僧尼轨范》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这个《僧尼轨范》是中国僧人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的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个僧人仪轨,因为适宜中国国情,所以,“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宋明以来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寺院普遍奉行的朝暮课诵,逐渐统一为每日“五堂功课”“两遍殿”,并且有钟、鼓、盘、木鱼等法器伴奏。早晚殿课诵成为汉传佛教寺院修行的重要宗教活动之一[4]。
三例的开始首先讲到道安大师创造的行香之法。“行香”原是法会仪式之一,法会开始时,先要行香,行是施与之义;香能解秽流芬,令人乐闻;法师主持法会,升座说法时,向他燃香礼敬。也泛指燃香、上香、拈香。
定座就是指讲经者的坐法。从南北朝以来的讲经记载,讲经之时必须为讲经师搭高座,座高二丈,这样一是显示讲经者身份,二是能让听经者都能看到讲经者,三是高处宜传音,能让听经者听到。讲经时一人转读、赞呗,一人解说。前者称都讲,后者称法师。为都讲所设之座叫唱经座或经座,为法师所设之座叫法座或讲座,二者统称高座。法师坐北面朝南面为主座,都讲坐南面朝北面为次座,听众一律就地而坐。
上经或上讲经之法。上经是指向高座递上经本、唱导文等书卷而言。上讲,指如何讲经之法,包括讲经的具体过程、讲经者的身份和职能等等。
现存最早的山东文登市清宁乡赤山院的讲经仪式是日本僧人日记留下来的。道安所制讲经仪轨与唐代讲经仪式大体相似,赤山院的讲经仪式应该就是道安所创的讲经仪轨,后经不断实践和完善逐步形成了一种讲经制度。
道安拟定该制度,上承其师高僧佛图澄,下启弟子释慧远,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深远。为现代讲经仪式奠定了基础。
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食法。讲的都是僧人日常生活与修持的一些轨范。它包括两个内容: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
六时行道。印度把一日一夜分为六时,即晨朝、日中、黄昏、初夜、中夜、后夜。虔诚的教徒一般在这六时都要举行念佛、诵经、礼忏等修持活动,称为“六时行道”。在印度传来的经典中,行道最主要的是指诵经和坐禅。佛教传入中国后,行道的内涵发生很大变化,到道安时代,他所谓的行道应该是从广义方面来讲的,泛指早晚课、过堂、诵经、坐禅、经行、绕佛、礼忏等各种修持方法。
不同宗派对修行内容的要求不一样。从道安“三例”可知,起码在道安时代,六时行道已经在中国流行。这种修持历代在中国各个宗派都十分流行。敦煌遗书中也保存不少六时礼忏文。
饮食唱时法。在用早午二斋前,举行上香、供佛和唱诵“供养偈”和“结斋偈”。以不忘报佛之恩,不忘施主之恩,僧众每天唱诵,以示不忘,从而能激发积极向道的信心。实际上早午二斋也是一种修行方法,是道安大师《僧尼轨范》三例中的一种修行方法。
道安大师所创的饮食唱时法,详细内容已不可考,经过逐步发展和完善,形成了后来寺院丛林的过堂(用斋)仪轨和二时临斋仪,一直沿袭到现在。
道安大师还首创了斋堂供宾头卢罗汉像。道安大师三例的第三条就是:布萨、差使、悔过等法。所讲的都是佛教僧团关于戒律生活的一些制度。
布萨,译为我对说,就是比丘之间相向说罪的意思,或者翻译为净住、长养、和合等。布萨法,又名为布萨犍度,就是诵戒仪轨。每半月大众集合在一起诵戒,诵戒时,自己检举或者他人帮助检举所犯戒条,然后依照所犯轻重进行忏悔,以使整个僧团保持完全的清净。
差使是指僧团差使一位比丘代表僧团去办某件事情,如差使教诫比丘尼,当僧团的知事人,处理僧团的事务等。《四分律》卷第四十四说,比丘具有八法,可以受僧团的差使,到质多罗居士家,为他做白二羯磨忏悔。八法者,闻、能善说、已自解、能解人意、受人语、能忆持、无阙失、解善恶言义。
悔过就是对自己所犯过失进行忏悔,和一般的忏悔不同,这里的悔过是专指僧团中的一种羯磨。根据所犯戒律的轻重不同,忏悔的方法也不同。布萨差使悔过法,都是属于僧团戒律的内容,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羯磨法,才能保持僧团的清净、健康运转[5]。
三例最早出现在《高僧传》中,道安的僧尼轨范三例,具体是何时制定的,史料上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我们只能依据道安的行迹,做一大胆的猜测。道安在恒山就讲般若经,直到襄阳,和后来到长安,还是每年讲《放光经》,所以行香定座上经上讲法形成最早。佛图澄去世后,道安开始成为一方佛教的领袖,几百人的僧人吃住行道在一起,必须要有较为完善的日常生活及修道准则,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应该在这段时间之内完成的。因此笔者认为,道安制定的僧尼轨范、佛法宪章之三例,是根据道安在不同时期的经历、不同的需要而产生的,并非出于一时。当然,有可能道安在他晚年,对这三例做了一次总结。
道安制定的僧尼轨范对僧人的修行提出了比较全面的要求。从僧团管理来看,僧尼轨范的制定使僧众的行为有了制度上的宗依,僧团的统一也才有了制度上的保障。虽然佛教僧团是以佛陀制定的戒律为准则,但是在戒律尚未完备的道安时代,“僧尼轨范三例”对于完善僧团规制、促进僧团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才会“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凿空开荒,则道安为僧制之始也”。可以说《僧尼轨范》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部僧尼清轨。
3.佛教礼仪的中国化
赞宁指出:“今出家者,以华情学梵事耳,所谓半华半梵,亦是亦非。寻其所起,皆道安之遗法是。”[6]这充分反映出当时佛教制度初传中土时相互交融的情形,也说明了道安大师对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的方方面面,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中国化了。
赞宁又说:“西域之法礼有多种,如传所明。礼拜者屈己也。旋绕者恋慕也。偏袒者亦肉袒也。脱革屣者不敢安也。和南者先意问讯也。避路者尚齿也。诸例常闻不烦多述。若尼礼于僧,自传八法。比丘奉上接足至三莫不尽恭。如事令长也,近以开坐具,便为礼者,得以论之。昔梵僧到此,皆展舒尼师坛,就上作礼。后世避烦。尊者方见开尼师坛。即止之。便通叙暄凉。又展犹再拜也。尊者还止之。由此只将展尼师坛拟礼,为礼之数,所谓蓌拜也,如此设恭无乃大简乎。然随方为清净者,不得不行也。又如比丘相见,曲躬合掌口云不审者何。此三业归仰也(曲躬合掌身也。发言不审口也。心若不生崇重,岂能动身口乎)谓之问讯。其或卑问尊,则不审少病少恼,起居轻利不,上慰不,则不审无病恼,乞食易得,住处无恶伴。水陆无细虫不。后人省其辞,止云不审也。大如歇后语乎。又临去辞云珍重者何,此则相见既毕,情意已通,嘱云珍重。犹言善加保重,请加自爱。好将息宜保惜同也。若西域相见则合掌云和南,或云盘茶味,久不见乃设礼。若尊严师匠,则一见一礼。今出家者以华情学梵事耳,所谓半华半梵,亦是亦非,寻其所起,皆道安之遗法是。则住既与俗不同,律行条然自别也。或云,僧上表疏,宜去顿首,以其涉祝宗之九拜者。余观庐山远公太山朗公答王臣之作,皆名下称顿首。远公讲礼,讲贤釆义,岂滥用哉。且顿首者,头委顿而拜也。今文云顿首,而身不躬折,何为拜乎。又道流相见,交手叩头,而云稽首亦同也。然秉笔者避之为敏矣。”[6]可以看出印度的佛教礼仪传到中国以后,有些不适宜中国的国情,道安大师为了让中国人容易接受,就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改革,既有印度佛教的礼仪形态,又不失印度佛教的礼仪原貌,看时半梵半华,如印度佛教的偏袒右肩、赤脚、礼拜等,因印度气候与中国不同,到中国就不适应了。到赞宁时,即公元1001年,距离道安时代已600多年,佛教礼仪还是半华半梵,还是道安所创造之法,至今如此。
4.禅定修行的中国化
印度原始佛教修行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听经闻法,二是修习禅定。佛教传入中土,禅法也同时传入。按史料记载,汉魏时入华的禅法,主流有二:一是安世高所传,一是支娄迦谶所传。安世高所译禅经均为小乘禅法,支娄迦谶所译均为大乘禅经。但实际发生影响的是以小乘禅为主,他们偏重对理论与方法的介绍,所以这一时期中土习禅之风并不盛行。又受中土盛行神仙方术的影响,此时的禅学颇重神通,认为“禅用为显,属在神通”。
道安大师是安世高以来小乘禅数学的重要传人,是当时的般若学大家。但是道安早年在注安世高所出禅经时屡发叹息:“于斯晋土,禅观弛废。”“每惜兹邦,禅业替废。”因此道安大师对印度佛教的禅定修持,也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这一改造,不是全盘否定印度传来的原始禅法,而是在理解真正禅法的过程中,做了适合中国文化的选择。
道安在中国首创弥勒念佛之法,并对西方极乐世界也大力宣传。据《乐邦文集》载遵式《往生西方略传序》称安公有《往生论》六卷,唐怀感亦引及道安《净土论》。在襄阳道安造铜制丈六无量寿佛像,均证实他对弥勒净土和西方弥陀净土的弘传。他把念佛修行引入到禅修当中,以念佛往生兜率、往生极乐,以念佛这简而易行的禅修方法,解决了中国人对印度传来的门类繁多、不易修行的禅法的畏惧。虽然属于五门禅中念佛法门,但仍不脱离禅定原意,乃是佛教修持中国化的一次创新。
他用自己独到理解的般若学来推进、发挥禅数之学,自禅观趣般若,以般若解禅观,肯定并突出“心”的本然状态与真如实相的契合,融会了大乘般若学与小乘禅学两大系的思想,是这两大系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禅修必须以般若智慧为指导,“执寂以御有,崇本以动末”是禅修的根本原则,“安般守意,止观双运”是禅修的基本方法。就是以“本无”去统摄,消融末有,归于虚无,而这又是心的作用。通过禅法,当人的心清净了,根绝了一切欲望,就会体会到“本无”,体会现实世界是虚妄的,也就进入了最高境界。他的禅学既是南北朝时期“毗昙师”学派先驱,也是唐代“俱舍宗”乃至“唯识宗”理论的滥觞。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系宣方教授对道安在中国禅学史上的贡献做了精辟的阐述:“道安在中国禅学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禅学的独立品格,从而开创了以对禅学系统性的追求和对禅学的宗教之维的自觉实践为标志的禅学本色化进程。在中国禅学史上,明确意识到禅学与中国本土化在精神特质上的差异,并因而强调在佛教思想自身的整体框架内追求禅学的独立品格,道安可以说是第一人。”[7]
5.像教弘法的中国化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佛教造像也同时传入中国。道安法师在弘法中除译经、讲经、注经外,也重视像教弘法。他的方法一是“每讲会法众,辄罗列尊像,布置幢幡,珠珮迭晖,烟华乱发。使夫昇阶履闼者,莫不肃焉尽敬矣”,即讲经法会先要悬挂佛像、幢幡,使会场庄严肃穆;二是造像弘法。《高僧传》载:“有一外国铜像,形制古異,时众不甚恭重。”从此看来,佛教东传的佛像,形式上也是印度及中亚的佛像,不论服饰、发髻和动态都是印度及中亚人的形象。直到北魏早期佛教造像有的还是如此。这些以外国人形象所造佛像,中国人显然不能适应。道安在襄阳造丈六无量寿佛像,“每夕放光,徹照堂殿”。造像改梵为华,使佛教像教弘法中国化。
道安的像教弘法和弥勒信仰在中国影响很大,到唐朝以前弥勒造像盛行,这和道安有很大关系。
杨惠南先生指出:“南北魏和南北朝之间,云岗、龙门等地所雕塑之佛菩萨像的数目,主要的有:释迦 112 尊,弥勒115尊,弥陀29尊,观音82尊。可见这一时期弥勒信仰之盛行。”[8]由于弥勒信仰的兴起,南北朝后期至盛唐时期,出现了大型摩崖弥勒佛造像,如山西太原63米的蒙山大佛、河南浚县22米的大坯山大佛、莫高窟第96窟35.5米的北大像、莫高窟第130窟26米的南大像、宁夏固原须弥山20.6米的大佛、甘肃炳灵寺27米的大佛、四川乐山71米的大佛等。
弥勒菩萨从佛教神谱中独立出来,被单独造像膜拜,是中国佛教艺术的一大特色。为弥勒造像之风的兴起,得力于两方面的条件:一是教义上弥勒信仰的建立,二是艺术造型上的某种特殊的表现手段,即交脚坐相被固定地用在弥勒形象的塑造上[9]。这样可以看出道安的弥勒信仰和弥勒造像对中国之影响。
麦积山石窟研究所研究员项一峰讲道:“道安学识、德行、传教、弘法,在中国各地教内外影响广大,他一生特崇弥勒、宣传弥陀、立寺造像、讲经法会时陈设尊像等净土信仰及像教弘法,也无疑会随之而影响广传……总而言之,道安本人及其弟子门人,在弥勒净土信仰(也包括弥陀)和像教弘法方面,开创了佛教史上的先河,掀起并带动东晋十六国时的第一高峰,而影响着后代。”[10]
三、组建译场,创建译论,注经作序,使佛教义理中国化
佛教初传中国,这一时期主要是对传来的佛教经典进行翻译和理解。由于国人对此还未认识,在汉代被视为道术的一种,到魏晋时代,佛教脱离黄老而独立,近而与高谈清静无为的玄学相融合。传来的佛经虽然已初具规模,但对佛经经义的理解还只是一种比符《老》《庄》格义的学问,它虽然走出了神仙方术之流,却又被纳入中国玄学的范畴。这种情况一直到东晋道安时期才有了转机。而引起这一势态发生变化的,东方圣人释道安也。
可以这样说,在道安、罗什之前,佛教真正的义理还没有被中国僧人所阐释,佛教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学术思潮;自道安、罗什始,中国佛教才有了自己独立的形态。……正是道安、鸠摩罗什和他们的弟子们把佛教经典的翻译和著述推向了高潮,并掀动了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深远的“义学”之风,为中国佛教鼎盛时代的到来,即隋唐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奠定了基石。……中国佛教史家所以推崇道安,说到底是他开创了对中国佛教具有深远影响的义理之学。如果没有道安,中国佛教可能还要在朦胧中摸索许久。这也正是印顺大师说道安是“确树此一代之风者”的原因[1]。
1.组织大规模译场,创建翻译理论,使佛经翻译中国化
公元379年,道安离开襄阳来到长安,在前秦皇帝苻坚的支持下,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由皇权支持的大型译场,可以说依靠皇权支持组建大规模译场是从道安大师开始的。翻译人员有几千人,道安作为译场的领导人,凭他佛教领袖地位,在长安的7年当中,主要任务是组织译经,并为译经写序。经过长期的翻译实践,他总结出“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原则,是要告诫时人,在翻译佛经的时候,肯定要遇到很多困难,很不容易解决,所以要慎之又慎,千万不可草率行事。即要把印度人的佛教理论翻译得不失原意,又要让中国人能够看懂,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道安大师的翻译理论,不但为翻译佛经指明了方向,使佛经翻译中国化,也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奠定了基础。其弟子僧叡承其衣钵,“执笔之际,三惟亡师‘五失本,三不易’之诲”,盛赞根据其原则翻译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为“出八地之由路,登十阶之龙津”。隋代彦悰非常推崇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对其赞美说:“余观道安法师,独禀神慧,高振天才,领袖先贤,开通后学,修经录,则法藏逾阐,理众仪,则僧宝弥盛。世称印手菩萨,岂虚也哉!详梵典之难易,论译人之得失,可谓洞入幽微,能究深隐。”梁启超论及“五失本,三不易”时指出:“后世谈译学者,咸征引焉。要之翻译文学程式,成为学界一问题,自安公始也。”钱钟书说:“五失本,三不易,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曹明伦认为:“道安此序之重要性非同一般,‘五失本’乃佛经翻译之指导性原则。”道安的翻译原则标志着我国佛经翻译理论从此步入成熟阶段。
2.诠释佛经,为经作序,创佛经注疏的中国化
道安大师的一生,志在弘法,除用心讲经外,更对其读过的佛经注疏做解。他看到当时的佛经虽然已流传较广,但旧译颇多错误,往往自相矛盾,难解深义,对此道安大师博览群经,苦心钻研,以求深解其意,并采取了为经作序、注疏的方法,让人们了解佛经深义。因此梁启超说:“前此讲经,惟循文转读,安精意通会,弘阐微言,注经十余种,自是佛教界始有疏钞之学。”[11]由此可以看出道安大师开创了佛经注疏的中国化。
据方广锠博士对道安大师一生的著作包括对各种佛经的注序进行了考释。他认为:道安一生勤于著述,撰写过不少著作。遗憾的是这些著作绝大部分已经亡佚。不过,不少典籍对道安的著作有所著录或叙述,我们可以借此窥见关于道安著作的基本情况。13种资料共提及道安著作102种,除去相互重复的,还有66种。这66种著作大部分已经亡佚。保存到现在的有25种。这25种著作可以分为3类:注疏、经序、书信。
除方广锠博士总结的以上著述外,笔者在这几年当中又发现了道安法师的16种著作。另据《出三藏记集》记载,还有11部,“先在安公注经录末”。
以上11部,道安放在他的注经目末,理应理解为道安的注经篇目。但道安对前19部经注经目后都附有释言,而此11部无一字释言。因此释僧祐在其11部后注“凡十一部,先在安公注经录末,寻其间出,或是晚集所得”。这11部是否是道安注经,有待专家考证。从以上11部篇目来看,前5篇可能是经注,后6篇可能是道安的作品。博士研究生潘慧琼、王琪、周杨、覃勤等均考证《悉昙慕》可能是道安的作品。从《悉昙慕》以下6篇文章看,《吉法验》也属悉昙类,《口传劫起盡》应属道安的“科分”或“科判”。《打犍椎法》应属道安“三例”中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之法器使用方法。《律解》应为道安为戒律的注解。由此推断这11部应为道安的作品。
方广锠博士总结的66种,再加上新发现的16种,和《出三藏记集》记载的11部,道安的著作就有93种。
道安注释经典,就是希望通过佛法中的智慧和自己的实践体会,能够摸索出一条佛教本土化之路,让人们认识佛教、了解佛教,通过佛教得到解脱。自道安开始,佛教界有了一整套完全符合中国人的民风习惯的道场规则和佛学修学方法,由此从理论上、思想上、制度上使中国佛教理论自成一体,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本土化,从而使佛教在中国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3.编纂经录,甄别真伪,创佛教经录的中国化
从两汉到东晋,佛经经过西域源源不断地传到中国,但是由于当时人们对佛教还没认识,所以佛经也不被重视。针对当时译经都是手抄,佛经散失各地,目录混乱不堪,佛经原义难以明白这一状况,整理佛经成为当时刻不容缓的大事。道安曾经派出一批又一批弟子到各地搜集佛经,如派弟子慧常、慧辩等数人千里迢迢去天竺取经。他盼望能够通过一代人的努力,汇编出一套最完整的佛经,以供后世四众弟子修学佛法。正是出于这一发心,加上无数人数年不懈的努力,道安带领徒众终于在公元374年完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部佛经目录——《众理众经目录》,简称《经录》或《安录》。这部《经录》包括了东汉灵帝到东晋孝武帝将近200年间的译经记录,是当时汉地能见到的所有佛经,是第一部最系统的佛经目录书。
道安原著已佚,大部分内容保留在僧祐著《出三藏记集》卷三、卷五当中。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安录》大概分为以下9个部分:经律论录、古异经录、失译经录、凉异经录、关中异经录、疑经录、注经及杂经志录、诸天录、杂经志录,以上总计著录各类典籍599部。
这部《经录》,为研究中国佛教的译经史提供了可信的史料,更为后人学习佛法、整理佛教典籍提供了极大方便。在印度佛经没有统一的记载,更没有经录,道安大师的这一创举,无疑也是佛教经录中国化的尝试。
4.整理传译佛经,谨慎科判,使佛经宣讲中国化
在对佛教经卷的整理传译过程中,将佛经判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大部分,每部分又层次井然地分为若干小段。这种严谨的科判治学态度从道安开始。
“震旦诸师开分科门,实始于释道安,而道安则称‘科分’为‘起尽’”[2]377。所谓“为起尽之义”,即区分章段。吉藏《仁王般若经疏》卷上一云:“然诸佛说经,本无章段。始自道安法师,分经以为三段:第一序说,第二正说,第三流通说。序说者,由序义,说经之由序也。正说者,不偏义,一教之宗旨也。流通者,流者宣布义,通者不拥义,欲使法音远布无壅也。”良贲《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卷上一云:“解本文者,先总判科,后随文释经。……昔有晋朝道安法师,科判诸经以为三分,序分、正宗、流通分。故至今巨唐慈恩三藏译《佛地论》,亲光菩萨释《佛地经》,科判彼经,以为三分。然则东夏西天,处虽悬旷,圣心潜契,妙旨冥符。”
科判之说是为了更好地诠解经文而兴起的一种注释方法。运用科判的方式,可以使段落清晰,经义豁然,也更便于初学者把握。科判之学兴盛以后,一般佛教徒在研习或解释经论时皆用此方法。这种区分章段的注释方法,也影响到了儒家的经典义疏和文学典籍的注释。可见佛经科判影响之广大深远。
四、创宗立派,依玄解佛,使佛教信仰中国化
1.潜心创立本无宗,刻意阐发般若学
道安大师对般若学情有独钟,从恒山开始讲般若经,到达襄阳以后,更注重对般若学的研究和阐发。道安在襄阳的弘法活动中,根据东晋朝野崇尚玄学的风气,刻意宣讲在思想上与玄学有着某些相似之处的大乘般若学,把当时玄学的一些争论引入般若学研究。到长安还是继续讲解般若经,他的一生很多著述都与般若学有关,他建立的“本无宗”的般若学理论,成为魏晋时期“六家七宗”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是佛学般若学的正宗。
由于时代久远,道安《本无论》已佚失,内容无从查考,但在一些高僧著作中的引用可见一斑。慧达《肇论疏》云:“第三解本无者,弥天释道安法师《本无论》云:‘明本无者,称如来兴世,以本无弘教,故方等深经,皆云五阴本无。本无之论,由来尚矣。’须得彼义,为是本无。明如来兴世,只以本无化物。若能苟解本无,即异想息矣。但不能悟诸法本来是无,所以名本无为真,末有为俗耳。”隋代吉藏《中观论疏》卷二末云:“一者释道安明本无义,谓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夫人之所滞,滞在末有,若宅心本无,则异想便息。……详此意,安公明本无者,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这两段引文,从内容、观点乃至文字都基本相同,可以说是道安“本无宗”的基本思想。它强调了释迦牟尼佛来于世间弘扬佛教,从早期弘法到大乘佛教,本无思想就是佛教的基本教义。
道安认为,如来是以“本无”的思想弘教的。世间万物在产生之前,“无”为本体或依据,而“空”则是有形有象事物的始原。一直到出现元气之后,才由元气分化出万物,万物因禀受元气才有各自的形状。万物虽凭借元气而演化,但演化的依据根本,则是出于自然。自然而然,没有什么造物主。由此而言,可以说“无”在元气演化万物之先,“空”是众多有形事物的始原。所以称之为本无。
汤用彤先生指出:“而道安之学,六朝常推为斯教之重心。”“盖在此时代,中国学术实生一大变动,而般若学为其主力之一也。吾称此时代为释道安代者,盖安公用力最勤,后世推为正宗也。”[2]157
道安法师“本无宗”的本无思想与般若经中的本无思想有一定关系,“有人认为,‘本无’一词系来自玄学,这固然是违背历史的说法;有人认为是借用《老子》,也不完全”“考察一下早期的《小品般若》,不论哪个译本,贯穿全篇的核心概念都是‘本无’”[12]237。实际上本无来自般若,本无也是性空、真如、法性的意思。
道安的本无就是性空,性空就是实相。因此说,道安的本无宗(性空宗)与鸠摩罗什的实相宗暗合,从而驳斥了比附于老庄的其他六家的宗旨,使佛教走上了独立纯正的道路[13]。
汤用彤先生指出:“僧睿称其师之说曰性空宗。昙济《六家七宗论》则称为本无宗。而僧睿以后,梁朝武帝、陈时慧达以至隋唐吉藏均认安公为般若学之重镇。吉藏之时,尚无定祖之说。假使有之,可断言道安必被推为三论宗之一祖也。……道安时代,《般若》本无,异计繁兴,学士辈出,是佛学在中夏之始盛。西方教理登东土学术之林,其中关键,亦在乎兹。”[2]168
吉藏《中观论疏》云:“一者释道安明本无义,谓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夫人之所滞,滞在末有,若宅心本无,则异想便息。……详此意,安公明本无者,一切诸法,本来空寂,故云本无。此与方等经论,什、肇山门义无异也。”吉藏大师更是把道安的本无宗排在了和罗什大师、僧肇法师理论并行。
道安对佛教般若思想的理解,对现代人们认识佛教的本原思想以及佛教的中国化,依然有着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2.首倡净土信仰,率众往生兜率
道安大师率弟子等8人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净土,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深远。导致了一系列思想的重大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杜继文教授指出:“第一,传统上,佛教是以‘众生’为本位的,现在改为以‘国土’即众生的生存环境为本位,促使佛教的全部教理和践行,也从纯粹众生的个体出发,转向从改善众生生活条件与生活质量的群体性活动着眼;第二,传统上,佛教把个人解脱的涅槃,即与现实人生彻底割断联系,定为终极归宿,现在则完全撇开了涅槃的观念,展现出一种为现实人生普遍想望的,充满幸福欢乐的全新世界作为最高目标。这两大转变,也带动了整个佛教人生观的变革,使传统上之厌恶人生、讴歌出世,变得珍贵人生、赞美世间;由对现实生活的绝望,给出未来美好的希望。”[12]105
道安大师以前,大量弥陀净土经典已经译出,并广为流传。弥陀净土类经典译出那么多,为什么道安大师选择弥勒净土而没选弥陀净土呢?实际上道安大师是两种净土都选择了,道安大师在襄阳就造了丈八无量寿佛像,还写过《往生论》和《净土论》。据敦煌莫高窟有关资料记载,唐朝以前弥勒净土和弥陀净土分辨不是太清楚,很多都是并提,不过记载道安大师弥勒净土的事迹多些,也可能在两种净土中更注重弥勒净土。
道安大师在中土首创弥勒净土信仰之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后来历代高僧争相仿效,如北齐的昙衍,陈隋时代的智者,唐代的玄奘、窥基、灌顶,后唐的令湮,后周的道丕,明代的憨山,近代的虚云、太虚等。这是佛教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此历代高僧大德、专家、学者都给予了很高评价。
道安大师不仅自己向信徒弘扬弥勒净土思想,而且还带领弟子一起修持弥勒法门,推动弥勒信仰的传播。在道安大师及其弟子的努力弘扬下,弥勒信仰在中国受到四众弟子的普遍欢迎。从东晋到建国初期,虽有兴衰,但始终没有间断,它不仅影响了中国,后来又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对世界的弥勒信仰都有卓越的贡献。
五、首倡爱国爱教、佛法不离世间,创政教关系的中国化
首次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著名论断,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原则。
新野分徒前历尽坎坷的传教实践使道安大师深有感悟,认识到如果违背王权的意愿,不和王权的意图趋向一致,脱离世俗,单凭佛教徒的努力,要使佛法弘扬四方,根本不可能。由此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的著名论断。对此有很多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他所指的“不依国主”不是指依靠国主,也不是依附国主,不要片面认为只有依靠国主才能弘扬佛法,这样就丧失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的独立性,也就违背了佛教的价值观,而是要想弘扬佛法,不要违背国主的意愿,使佛教与世俗政权相协调,要把弘扬佛法和政治保持一致姓,不然“则法事难立”。这也改变了印度神权大于皇权的观念,使佛教在正确处理政教关系中中国化。
道安在以后的传教活动中,不仅要求其弟子遵循此原则,而且他本人也身体力行。如他在其师圆寂后,9次迁徙避难,一生经过六国四朝二十一帝,就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没有一次去投靠某位帝王,而是在避难之中讲经、注经,弘法不辍。又如他在襄阳传教15 年,主要精力放在讲经、译经、注经和搜寻诸经编撰《经录》,修建寺院等。
虽然此时他也与东晋的一些政要以及北方前秦政权有来往,但已不似其师佛图澄那样参与朝议,而是更多地与士族中的信佛人士交往,其中有襄阳的士族精英习凿齿、高平的名族居士郗超、凉州刺史杨弘忠、襄阳朱序、荆州刺史桓豁等等。和他们保持着融洽的关系,利用这些名人权贵扩大佛教影响,弘扬佛法。
对道安大师的弘法思想,吕瀓先生有个公正的评价:“他不像支道林那样,与名士们混在一起,走清淡的路子;也不像竺法汰那样,逢迎权臣贵族,奔走于权贵之门;更不像支敏度那样,把学问当成儿戏,随便立宗。道安是作风踏实,为着寻求他心目中的真理而孜孜不倦的学者。”[14]吕徵先生对道安大师的评价,可以说明道安大师的“不依国主”不是依附于国主,更不是依靠国主。后来其弟子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也说明了师徒传承思想的一致性。这句至理名言,既是道安大师对自己长期传教活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佛教传播发展一般原则画龙点睛的高度概括,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原则。
道安大师为佛教所提出的这个“定位原则”,深刻说明了政治对佛教生死攸关的重要作用和佛教必须采取的协调立场。妥善处理佛教与王权的关系,是佛教在中国获得生存与发展的首要条件。这个原则不仅影响了他那个时代的中国僧团,也影响了以后历代历朝的佛教信徒,从一般的护法居士到僧团,从高僧佛教到民俗佛教,从寺院的清众到佛门龙象领袖,无不遵从、推崇、谨守这个“定位原则”,中国佛教史上此类例子可谓俯首皆是[15]。
[1] 李富华.佛教典籍的传译与中国佛教宗派[J].中华佛学学报,1999(12):97-112.
[2]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3] 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4:178.
[4] 王晓朝,李磊.宗教学导论[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
[5] 通了法师.道安法师与佛教戒律[EB/OL].[2017-10-11].www.zgfxy.cn/ztjj/zgfx/fy/zdesq2002n/2012/04/11/15053 1985.html.
[6] 赞宁.大宋僧史略[EB/OL].[2017-10-11].http://www.nanputuo.com/nptlib/html/200911/2514562173499.html.
[7] 宣方.从神异禅到玄学禅再到本色禅——中国早期禅学话语的演变[EB/OL].[2017-10-12].http://www.foyuan. net/article-105200-1.html.
[8] 杨惠南.汉译佛经中的弥勒信仰[J].文史哲学报,1987(2):119-181.
[9] 朱刚.中土弥勒造像源流及艺术阐述[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4):71-75.
[10] 项一峰.论道安大师弥勒净土信仰及像教弘法[G]//印顺.第一届襄阳道安论坛论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413-420.
[11]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118.
[12] 杜继文.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13] 崔正森.五台山佛教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74.
[14] 吕徵.中国佛学源流略讲[M].北京:中华书局,2013:55.
[15] 金易明.以巨赞法师生平为由对中国僧侣与政治之探究[EB/OL].[2017-10-12].http://www.docin.com/p-775836 541.html.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①道安的出生地,《高僧传·道安》称之为“常安扶柳”,诸多学者也一直认可这一记载,然而根据《晋书·地理志》所载,晋时共设十三州,州下设郡国。时冀州统郡国十三个,包括安平国和常山郡。其中常山郡“统县八”,即:真定、石邑、井阱、上曲阳、蒲吾、南行唐、灵寿、九门,八县之中并无扶柳;而安平国“统县八”,即:信都、下博、武邑、武遂、观津、扶柳、广宗、经,八县之中有扶柳。从地域上看,信都(今冀州旧城)与常山郡中间还隔着一个赵国,根本不连片。而信都自曹魏文帝黄初年间至晋代,就是冀州、安平国、信都县三级治所。自西汉至东晋,治所设在信都的郡国,或称信都,或称安平。虽名称几经更移,但其所辖之县均含“扶柳”。西晋末年道安出生之时,治所在信都的郡国为安平国。所以说道安出生地为“常山扶柳”是错误的,应为“安平扶柳”。
Shi Daoan: The First Man Who Sinicizes Buddhism
WANG Qitan
(Hengshui Institute of Daoan Culture, Jizhou, Hebei 053200, China)
Daoan neither shackles Buddhism with the existing Chinese thought nor copies the Indian Buddhism exactly. He interprets Buddhism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out violating the tenets of Buddhism so that Buddhism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e unifies the surname of “shi” and changes the clothes of the monks to sinicize their life; He builds temples and pagodas, establishes rules and regulations to sinicize the monks’ practice; He arranges places of translation, creates translation theories, interprets scriptures and writes prefaces to sinicize the tenets of Buddhism; He creates schools of Buddhism and interprets Buddhism based on the profound theory to sinicize the belief of Buddhism; He advocates the ideas of patriotism and love for religion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inks that the Buddhist doctrine should guide people to sinic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It is because Daoan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ini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Buddhism that it has developed greatly in China, and for this reason he is praised as the “the first man who sinicizes Buddhism”.
Daoan; Buddhism; sinicization; Jizhou
10.3969/j.issn.1673-2065.2017.06.008
王其谭(1947-),男,河北冀州人,衡水道安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冀州道安文化研究会会长。
G127.223HS
A
1673-2065(2017)06-0048-11
2017-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