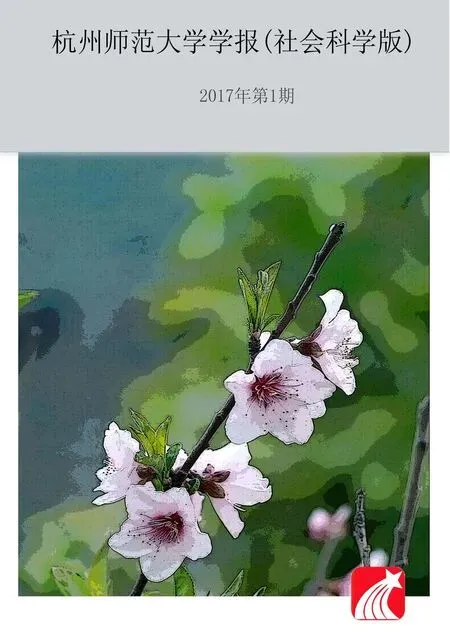新文学“国民性改造”脉络中的沈从文
迟 蕊
(沈阳大学 文法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44)
新文学“国民性改造”脉络中的沈从文
迟 蕊
(沈阳大学 文法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44)
从沈从文的作品、书信,尤其是发表于三四十年代的大量杂文和文论可以看出沈从文虽然留恋乡村,厌恶都市,但他的国民性改造思路却并不是想要复归传统,也不是反对现代性,而只是希望用乡村的自然、淳朴和淋漓的生气来警醒现代性发展中所隐含的弊端,用它们所蕴藏的真、美以及生命的热度来进行国民精神的重建。
国民性;沈从文;新文学
提起沈从文对“重造民族品德”[1](P.160)的关注和表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国民性改造问题,而且也有不少研究者直接从这个角度解读过他的作品[2]。不过,需要留意的是,他本人在晚年却明确交代过,对于“下层人民的雄强、犷悍等品质”的歌颂与“当时国民性改造思想”“毫无什么共通处”[3](P.522);另外,翻阅《沈从文全集》也会发现,他几乎不怎么使用“国民性”一词。所以,能否从这个角度解读他的作品,还需作必要的辨析和论证。为此,本文通过对他的作品、书信,尤其是发表于三四十年代的大量杂文和文论的全面考察辨析了这个问题,并对他的国民性书写进行了一番新的解读。
事实上,沈从文的创作,就其出发点和整体思路来看,的确是属于清末民初出现的“现代国民国家——国民性改造——文学启蒙”这条大的思想脉络的;而且,就其表现的具体内容而言,也是统一于他对中国国民精神的整体观察和思考中的。一方面,凭借一己独特的生命感悟,沈从文从湘西和都市两种生活的对比中,发现了国人普遍存在的精神病灶,即乡村虽然古朴淳厚,却充满了愚昧与野蛮;都市虽然意味着进步和未来,却充斥着虚伪和巧滑;更可怕的是,在政治扰攘和商业文明的侵蚀下,乡村的古朴与淳厚正逐渐在丧失,整个国民精神都在恶化,变得更加的堕落。另一方面,他从重造国民品德的文学观念出发,自觉思考着重建国民精神的命题,并以殉道般的情怀,力图通过文字从湘西世界里挖掘可以疗救国人的精神资源。也就是说,沈从文虽然留恋乡村,厌恶都市,但他的国民性改造思路却并不是想要复归传统,也不是反对现代性[4],而只是希望用乡村的自然、淳朴和淋漓的生气来警醒现代性发展中所隐含的弊端,用它们所蕴藏的真、美以及生命的热度来进行国民精神的重建。
一、与“国民性改造”思想脉络的关联
据张新颖考察,1935年左右至1949年底的沈从文是一位“思想者”,这段时期对他来说是一个“从文学到思想的阶段”,而且“越是往后去,思想的成分越重”。[5](P.4)对此,笔者十分赞同,并且进一步认为,沈从文在这段时间内对于自己创作的梳理以及对社会人生的诸多思考,包含着许多可以用来解读其作品的重要线索。比如,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就可从中找到很多线索。
首先,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说明和强调有了“国民”才有“国家”的道理,表现出对现代国民国家理念的强烈认同和对改造国民精神的迫切愿望。比如,在《中国人的病》中写道:“事实上国民毛病在旧观念不能应对新世界,因此一团糟。目前最需要的,还是……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6](PP.88-89);在《变变作风》中说:“国家忧患那么深,国民责任那么重,如我们不能在普遍国民中(尤其是智识阶级中)造成一种坚韧朴实的人生观,恐怕是不能应付将来的!”[7](P.159)此外,在《应声虫》《性与政治》《五四》《一种新希望》《明日的文学作家》《美与爱》《从现实学习》等文章中,提及“国家重造”或“社会重造”的地方,也比比皆是。显然,沈从文的这种观念典型地体现了“五四”前后中国知识人有关现代国民国家政治理念下国民性改造的普遍认知。当时,西方世界早已经进入了现代国民国家时代,在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中有关国民性的研究不仅为这种国家组织形式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在德国、日本的崛起中,国民精神作为一种整合民族力量的理念在实践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当中国人逐渐觉醒的时候,面对需要尽力追赶的强大西方,就将国民精神的改造看成了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必须完成的非常重要的一课。身处那样的时代,沈从文作为一个敏感的、渴望有所抱负的文人,国民国家、国民性改造这些理念自然成了他思想和事业选择的一个原点。
而且,他也清楚地交代了正是这种强烈的认同,直接促成了他的文学自觉以及重造国民观念的文学观的形成。在《从现实学习》一文中他讲道,当年之所以从湘西跑出来,就是因为痛感到“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想来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救救国家”。于是“依照《新青年》《新潮》《改造》等等刊物所提出的文学运动社会运动原则意见……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并且“相信人类热忱和正义终必抬头,爱能重新黏合人的关系,这一点明天的新文学也必须勇敢担当”。[8](PP.374-375)在《我的学习》中也写道:他那时“深信通过文学,注入社会重造观念于读者,是一个必然有效方式”。[9](P.365)另外,晚年时他在一次演讲中也再次追述了这个心路历程:“当时追求的理想,就是五四运动提出来的文学革命的理想。我深信这种文学理想对国家的贡献。”[10](P.384)
其次,沈从文不仅提倡过有助于改善国民性的文学创作,还表达过与国民性改造思想极为相似的言论。1932年他针对文坛上所出现的新礼拜六派现象,在《小说月刊》上发表了《上海作家》一文。细读此文就会发现,在他向各大报社副刊所提出的六条建议中,有四条都与改善国民精神有关,而且其中还有一条直接提到了“应该奖励征求能使国民性增加强悍结实的一切文学作品”。[11](P.44)此外,在《定和是个音乐迷》和《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中也都涉及到了国民性改造的话题,即“三十年来虽明白社会重造和人的重造,文学永不至于失去其应有作用”[12](P.213);“也许把这个民族的弱点与优点同时提出,好像大不利于目前抗战,事实上我们要建国,便必需从这种作品中注意,有勇气将民族弱点加以修正,方能说到建国!”[13](P.52)
由此可见,沈从文的创作,就其出发点和总体思路而言,明显是与清末民初所出现的“现代国民国家—国民性改造—文学启蒙”这条大的思想脉络密切相关的。众所周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而后,中国为了救亡图存,也不得不力图通过变革尽快走上现代国民国家的道路。在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层面的一系列改革之后,种种失败的教训却使国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和精神上的危机才是中国最大的危机。在此背景下,正流行于日本的国民性改造理论便引起了国人的关注,被逐渐地输入了进来。1902年梁启超最先借鉴了这个理论,并在其基础上提出了“新民说”,于是国民性改造遂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之后到了“五四”时期,由于鲁迅在文学领域对它的成功表现,这个话题不仅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还逐渐演变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主题。沈从文的创作正是在这样一条脉络上起步和发展起来的。
不仅如此,他由此而形成的这种重造国民观念的文学观,在其整个写作生涯中,还从未被动摇过。尤其是到了30年代中期,当他力拒政治和商业的干扰,再度高扬五四的旗帜,提出“重造文坛”之后,这种文学信念则变得愈加的坚定。他在《关于学习》中写道:“一切意义都失去其本来应有意义时,一群有头脑的文学家,还能够用文字粘合破碎,重铸抽象,进而将一个民族的新的憧憬,装入一切后来统治者和多数人民头脑中,形成一种新的信仰,新的势能,重造一个新的时代一种新的历史”[14](P.349);在《欢迎林语堂先生》中指出:“可以从文学作品中来作有关人生一切抽象原则重造的工作。”[15](P.171);他倡导“建设一个新的文学运动”,“在作品中输入健康雄强的人生观”。[13](P.50)[16]另外,他甚至还认为在推动人类精神向上发展方面,“文学作品实在比较别的东西更其相宜”,“到近代,这件事别的工具都已办不了时,惟有小说还能担当”。[17](PP.66-67)
可见,沈从文的创作,就其出发点和整体的思想脉络而言,是完全可以将其纳入到“国民性改造”的视野中来考察的。那么,就其所表现的具体内容来说,能否采用这个视角呢?
二、对整个国民精神的审视
以往,许多研究者都谈到了沈从文对“野性”与“生气”的张扬*持这种观点的文章在沈从文研究中俯拾即是。,这是颇有价值的。但由此而引申出他崇拜野蛮、厌恶文明、甚至是主张绝圣弃智,皈依自然等结论[4],却值得讨论。
首先,从前文的梳理可以看出沈从文对现代性的发展方向是赞同的。其次,从他对湘西人的分析和对湘西地区发展的建议,则能更加清楚地感受到他的这种态度。在《湘西·题记》一文中,他劝告湘西的年青人不该借口地瘠民贫就不思进取,认为“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不仅仅对一切进步的理想加以拒绝,便是一切进步的事实,也不大放在眼里”。他还指出了湘西在商业、企业和教育发展方面所存在的各种问题,譬如商业“无不操控在江西帮,汉口帮商人手里,湘西人是从不过问的”[18](PP.330-331);军校阶级支配了凤凰,只“知道管理群众,不大知道教育群众”。[19](P.394)另外,他还批评“负责者对于湘西茫然无知,既从不作过当前社会各方面的调查,也从不作过历史上民族性的分析”,进而建议:“湘西必重新交给湘西人负责,领导者又乐于将责任与湘西优秀分子共同担负”;“知道尊重知识,需要人来开发地面,征服地面,与组织群众,教育群众。”[20](P.409)从中可见,沈从文并不崇拜什么野蛮、也不主张什么反智,而是将包括商业文明在内的现代性的发展视为未来民族的发展方向。
当然,尽管沈从文赞同这种方向,但同时对它所带来的弊端,却有着极为清醒而深刻的认识。1923年当他义无反顾地逃离湘西,奔赴北京后,就逐渐发现都市虽然少了家乡那种残暴的杀戮和可怕的愚蛮,但整个社会在政治的愚弄和商业的熏染下,却到处充斥着功利、虚伪、狡诈、浅薄、四平八稳的市侩气。据他观察,“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然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以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21](P.4)“许多人一眼看去,样子都差不多……无信心、无目的,无理想。”[22](P.283)而且,即便是“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在外表上称绅士淑女的,事实上这种人的生活兴趣,不过同虫蚁一样,在庸俗的污泥里滚爬罢了”。[23](P.37)此外,更令他大为失望的是,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们,也都堕落得不成样子了,一个个如同“阉鸡、懦夫,与狡猾狐鬼,愚人妄人,在白日下吃、喝、听戏、说谎、开会、著书、批评攻击与打闹!”[24](P.199)总之,在沈从文看来,“对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政治、学术、文学、美术,背面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23](P.39)
于是,在都市和湘西两种生活的对比中,他清醒地认识到都市虽然有比乡村进步的一面,但实际上那里的人们也同样过着一种无目的、无意义的生活,充满了愚昧。只不过,是另一种愚昧而已。如果说乡村的愚昧是因为缺乏教育,是值得同情的;那么都市的愚昧则更多是由于人们自身的虚伪和浅薄,因此格外令人憎恶。而且,更加可怕的是,在政治扰攘和商业文明的侵蚀下,乡村的古朴正逐渐在丧失,整个国民精神都在恶化,变得更加的堕落。因此,当他重新审视湘西世界时,豁然发觉那里原来蕴涵着那么多宝贵的东西,既有淳朴、善良、诚实、厚道、热情、轻利重义这些美好的品质,又有清新、恬淡、令人陶醉的自然环境。于是,他在自己的小说中除了揭露和嘲讽都市人的种种病象之外,便极力去渲染乡村的美好,希望能给堕落中的人们“一种对照的机会”,使其对现代性发展所带来的弊端有所警醒。比如,他的代表作《边城》(1933)就是意在让读者“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25](P.59)此外,诸如《月下小景》《三三》《丈夫》《柏子》《萧萧》《菜园》《阿黑小史》等作品,也都是如此。
后来,他的这些认识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深化。1934年初,当他重游故乡时,不仅重温了沅水一带的美丽风景,还从中获得了对于自然、历史、命运以及人生的前所未有的领悟。一路上他情不自禁地赞叹到那里“满眼是诗”,领略到“生命另一形式的表现,即人与自然契合”[26](P.376),透过眼前的种种情景,他的内心还产生了一次强烈的震动。他先是感到自然是那么美,而人类社会与之相比却显得如此的不协调;而后又猛然间彻悟到,尽管时间、历史和宿命都在无情地束缚和摧残着人类,使其一代又一代始终都在艰难里苦苦地挣扎,然而就是在这挣扎中竟有着一种求生的庄严,实在是令人感动、敬佩不已。他在《湘西书简·历史是一条河》中这样记录:
我心中忽然好像彻悟了一些……得到了许多智慧,不是知识。……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而异常爱他们。……我错了。这些人不需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你瞧我眼睛湿到什么样子
这是异常复杂的一种人生体味:既有无限的怅惘,又有巨大的悲悯;既有彻悟的狂喜,又有受难的悲壮。眼前的自然景物愈是美丽,就愈加反衬出人事的毫无章次[28](P.170);尽管乡村有着人与自然的契合,充满了诗意,但人类终究不可能退回到那种原始古朴的生活中。于是,他写道:湘西人若不想法改造,“将不免与自然同一命运,被另一种强悍有训练的外来者征服制驭,终于衰亡消灭”[26](P.376);“我们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一种‘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改造这些人狂热到一件新的竞争方面去?”[29](P.281)这再次说明,沈从文的生命理想并不是想要归复自然,而是主张主动去迎接现代性发展的潮流,去开创新的历史。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因为参悟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选择消极无为,而是恰恰相反“因为明白人类在某种方式下生存,受时代陶冶,会发生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悲悯心和责任心必同时油然而生,转觉隐遁之可羞,振作之必要。目睹山川美秀如此,‘爱’与‘不忍’会使人不敢堕落,不能堕落”。[26](P.376)
因而,至此以后,沈从文从改造国民观念的文学观出发,就更加自觉地思考着国民精神重建的问题。他不仅立志要“用文字来重新安排一次”[30](P.104)这个世界,还将其作为一种坚定的文学信念来实践着,充满了“殉道”般的情怀。关于这一志向,他在很多文章中多次清清楚楚地表达过。比如,在《白话文问题》中说道:“伟大作品不易产生,写作的动力,还有待于作者从两者以外选一条新路,即由人类求生的庄严景象出发……活一世,写一世,到应当死去,倒下完事。……他本身一生实应当如一篇宏大庄严而同时又极精美的诗歌。”[31](PP.62-63)在《我的学习》中说道:“要有许多人,各自带着殉道者精神,披荆斩棘来开发工作中不同的道路。”[9](P.365)此外,在他的散文《水云》《白魇》《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诗歌《一个人的自述》以及致亲友的书信[32](PP.409,521)等文字中也都有所表白。
由此可见,沈从文对于国民精神的重建,不仅是在认同现代性发展方向的前提下来思考的,而且他所针对的也不仅仅是都市性问题,而是对包括乡村和都市在内的整个国家的精神病灶的审视。实际上,他并不是想要复归传统,也不是反对现代性,而只是希望用乡村的自然、淳朴和淋漓的生气来警醒现代性发展中所隐含的弊端而已。因此,他所思考的国民精神的重建从客观上看,其实就是国民性改造的问题。那么,他所提供的具体方案又是什么呢?
三、以真、美与生命的热度来重建
关于这个问题以往已有很多的阐释,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认为,沈从文是希望用湘西的朴野来挽救患有“阉寺性”[33](P.43)的都市人,使衰老的民族重新焕发活力。这也就是苏雪林早在1934年就提出的,她说沈从文的理想“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34](P.38)这种理解,当然不错,但笔者认为还有进一步加深理解的必要。因为,实际上沈从文真正的意图或许并不是,或者不仅仅是想要使国人变得野性、悍犷、单纯起来,而是更看重其背后所蕴藏我们民族本有的,可以用来重塑国民品格的良方。
首先,他发现野性虽然常常表现为粗鲁、野蛮和无知,却包涵着来自生命的真与热度。比如,他从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身上,就惊异地发现这个人虽然爱说野话,行为粗鲁,却是个“绝顶的妙人”——他对字画的品评总能“揉合了雅兴与俗趣”;他说的“即便是荤话野话,也莫不各有出处,言之成章”;“有人称他为豪杰,也有人称他为坏蛋”,但合起来看“才真是一个活鲜鲜的人!”[35](P.227,226,230,228)又如,1934年当他路过沅水上游几个县分时了解到,当地“民性强直,二十年前乡下人上场决斗时,尚有手携着手,用分量同等的刀相砍的公平习惯……一个商人的十八岁闺女死了,入土三天后,居然还有一个卖豆腐的青年男子,把这女子从土中刨除,背到山洞中去睡她三夜的热情”。虽然这些奇闻异事也令他惊诧不已,但从中他却感到了一种早已消失殆尽的“生命洋溢的性情”[28](P.385)。以至使他不禁感叹到城里人,“即或有学问,有知识,有礼貌,有地位”,却总好像他们“实实在在缺少了点人的味儿”。[36](P.171)这里所谓的“人的味儿”,其实指的就是来自生命的“真”与热度,或者说就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为此,他不无悲凉地写道:“和尚,道士,会员……人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存,为一切名词的迎拒取舍而生存。……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37](P.14)也就是说,沈从文发现正是由于背离了这种自然本性,再加上缺乏生命的热度,人们才会变得异常的虚伪和麻木。
此外,还有浅薄。这是沈从文从许多日常生活中所洞察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比如,在《烛虚》中就记载了这样一桩小事情对他的启发。有一天傍晚,他骑着马路过一处风景可人的田埂,可是正当他为夕阳下的山野风光所陶醉的时候,却忽然来了两个非常无礼的女大学生。她们边吃零食,边相互打闹,后来竟然把梨骨抛到他的身上,她们不仅没道歉,还笑嘻嘻地跑掉了。这件事尽管很小,但当他“把眼前自然景物和人事情形两相对照”后,却产生了“一种极其痛苦的印象”,以至“许多日以来不能去掉”。[37](P.10)这让他不仅感到现代教育的失败,竟然教育出如此浅薄的人,而且认识到现代教育虽然先进,但如果所灌输的知识和思想,不能与受教育者生命发生关系,那么书本上的东西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堆空空洞洞、毫无意义的名词和口号而已,不但很有可能起不到正面的作用,反而会使他们的认识流于皮毛,甚至是陷入到另一种愚昧中。
可是,与此完全不同的是,湘西的孩子们虽然没有接受过现代教育,但他们在与大自然的密切接触中,在古老的各种游戏中,却真正获得了许多的知识,增长了许多的勇气和智慧。比如,他在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中就借阿丽思小姐的一封信,讲述了一个关于乡村孩子们是怎样从花样繁多的赌博游戏中,获取知识、变得勇敢聪明的故事。他写道:“赌博有五十种或五百种……其中全得用一种学问,一种很好的经验,一种努力,且同时在这种赌博上,明了这行为与其关系之种种常识,才能够站在胜利一方面。……比如说用湿沙作圆宝,应如何方能不轻易破裂?到挖一长坑,同其他沙球相碰时,又应如何滚下,才不致失败?有了裂痕后,再如何吃水?全是有学问的——一个工程师建筑一堵三合土桥,所下的考究不至于比这个为多……”[38](PP.225-226)
他在《从文自传》中也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好多与此类似的故事。他经常逃学,早上一出门就南辕北辙,到街上到处游荡,一路看看针线铺、豆腐坊、染房、铁匠铺……又一会儿下河泅水,再到血腥的河滩上看宰牛……沈从文从中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可见,在他看来,唯有融入了生命体验才可能获得真的知识和智慧,否则即便被灌输的再多也都是空洞浅薄、毫无价值的。这也又一次说明,他并不反智,而只是反对“假”的智慧而已。甚至,他还认为:“新来的便是无个性无特性的庸碌人生观,养成这种人生观就是使人去掉那点勇气而代替一点诈气的普通教育。”[28](P.385)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他之所以总是强调自己“乡下人”的身份、“带着一把乡下人的尺子”的原因之一。实际上,这把尺子就代表了一种融进生命的真与热度方式,即他所说的,一种“‘乡下人’实证生命的方式”,一种对生命的“信仰”。[30](P.94,124,128)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强调这个姿态,但并不是要反对现代教育,而只是希望以此来警醒和避免这些弊端而已。可见,他的这些认识是非常深刻又富有远见的。试想,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可是为什么人们还总是被时风所左右,被各种名词所欺骗呢?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不正是因为没有将知识和思想融进自己的生命体验,才无法使其在生命中生根发芽的么?
此外,从他对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品评以及择友的标准中,也能明显地感受到对“真”与生命热度的推崇。比如,他说:“一个人生命若没有深度,思想上无深度可言……一时之间得到多数读者,这种人的成就,是会受时间来清算,不可避免要随生随灭的”[17](P.74);又如,他在一封家信中谈道:《史记》之所以成功,最主要的是由于“作者生命是有分量的,是成熟的”;它“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的东西”,就是“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39][40](PP.318-319)再如,在评论“五四”时说道,其“特点是‘天真’和‘勇敢’,如就文学言,即大无畏的高谈革命之外,还用天真和勇敢的热情去尝试。”[41](P.81)另外,在《萧乾小说集题记》中还说道:“我崇拜朝气,欢喜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一个人行为或精神上有朝气,不在小利小害上打算计较,不拘于物质攫取与人世毁誉……他所学的或同我所学的完全是两样东西,他的政治思想或与我的极其相反,他的宗教信仰或与我的十分冲突,那不碍事,我仍然觉得这是个朋友,这是个人。我爱这种人也尊敬这种人。因为这种人有气魄,有力量。这种人也许野一点,粗一点,但一切伟大事业伟大作品就只这类人有分。”[42](P.324)
其次,沈从文还从湘西的山水光影间、从农人们毫无做作的表情里、从再平常不过的什物中发现了美,并认为这种美对于扩大和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极具教化作用。关于这个发现的过程及其美妙的体验,他在许多文章中都浓墨重彩地描述过,比如《烛虚》《水云》《泸溪黄昏》《过新田湾》《鸭窠围的夜》等。限于篇幅,这里仅摘引《烛虚》中的几个片段,略尽说明:
在有生中我发现了“美”,那本身形与线即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统制,受它的处治。人的智慧无不由此影响而来。这种美或上帝造物之手所产生,一片铜,一块石头,一把线,一组声音,其物虽小,可以见世界之大,并见世界之全。或即“造物”,最直接最简便那个“人”。流星闪电刹那即逝,即从此显示一种美丽的圣境,人亦相同。一微笑,一皱眉,无不同样可以显出那种圣境。一个人的手足眉发在此一闪即逝更缥缈的印象中,既无不可以见出造物者手艺之无比精巧。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捕捉住这种美丽神气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中即终生不灭。……即一刹那间被美丽所照耀,所征服,所教育是也。[37](PP.23-24)
于是,沈从文由这种切身的体验出发便觉悟到,身为作家是有责任引导那些已经“被种种名词所阉割”的读者们,去体会这个“神”,不断地“增加其神性”的。他认为不仅对于作家自己而言,首先应该忘掉“一切书本所留下的观念或概念”,“用各种官能向自然中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向社会中注意各种人事”;“脱去一切陈腐的拘束,学会把一支笔运用自然,在执笔时且如何训练一个人的耳朵、鼻子、眼睛,在现实里以至于在回忆同想象里驰骋”[43](P.331),而且整个新文学也应该“从娱乐方式上来教育铸造一个新的人格,如何向博大、深厚、高尚、优美方面去发展”。[44](P.507)这样,有了来自生命的真与热度,再经过美的熏陶和教化,人们就能更加懂得爱与悲悯,就能真正获得抵抗世俗的力量,进而避免现代性发展所带来的弊端。这就是沈从文所提供的国民性改造的方案。
可是,由于他所找到的这个药方是蕴藏在各种现象和事物背后的,因而总要通过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1](P.5)才能呈现出来。因此,他就建造了一个美丽又满蕴的忧愁的湘西世界。不过,当他将这样一个桃花源展现到读者面前时,却又发现虽然有不少人喜爱他的作品,但大多数读者实际上却“近于买椟还珠”[21](P.4),不能与他会心。所以,他只好无奈地说道:“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殊不知,沈从文真正所期待的是使读者们能够“越过那条间隔城乡的深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健康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这种感情且居然能刺激你们,引起你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的怀疑”。[21](P.5,6)可见,在沈从文的笔下,无论是对湘西自然景物、人情土俗的描绘也好,还是对农民们粗犷豪放、热情淳朴的歌颂也好,其实都是与国民精神的重建,或者说国民性改造这个总体目标紧密相关的。然而,沈从文后来却为什么要完全否认这一点呢?
四、一种独具特色的“国民性”书写
1979年,凌宇以书信的形式向沈从文请教了23个问题,沈从文对每个问题都做了简要的回答,国民性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细读这份记录会发现,沈从文的回答在态度和方式上表现出一种极为鲜明的倾向性,就是极力想消解其作品的创作意图。或者声称只是为了维持生计,或者解释为不过是练笔而已,或者强调对其作品仅做欣赏足矣,总之是反对任何观念式的解读。比如,当被问到“是否含有提倡返归自然、回复野蛮的创作意图”时,他写道:“一切都是在学习用笔中完成的。不可能一面写什么,一面还联想到什么。当时最主要企图,还是能维持最低生活,作品能发表就成了。”又如,他对于“关于城市中绅士阶级的生活描写”的解答是:“你应当从欣赏出发,能得到的是什么。不宜从此外去找原因。特别不宜把这些去问作者,作者在作品中已回答了一切。”因此,他对“国民性改造”这个问题的处理,也是如此,不仅断然予以否认,还补充到自己“是试图用不同方法用笔,并不有什么一定主张”。[3](P.552,553)
当然,沈从文的这种说法也可能是一种“文本批评观”使然。但如果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也不能不说还极有可能是出于对建国后自己的作品长期被误读、批评和忽视的不满,对那种用政治观念图解文学作品、独尊鲁迅的做法的反感。如果查沈从文1957年至1981年的书信就会明显地体味到这一点。如他在1957年6月2日致吕德申的信中写:“学生只看王瑶教授《现代文学史》,习于相信一种混合谎言和诽谤的批评,而并未看过我的作品。访问我虽出于好意,也近于猎奇,并无基本认识。”[45](P.179)在1972年6月30日致张兆和的信中说:“那些写现代文学史的人,自然更会有意回避,从来没有把我在某一时期和别的作家在同一时期写的作作比较,总是先作结论,而忽略实际。”[46](P.185)此外,还有在其它9封信*参看沈从文:《19790514致沈虎雏、张之佩》,《沈从文全集》(第25卷),第319页;《19800115(1)复柯原》《19800127致沈虎雏、张之佩》《19800313复马逢华》《19800406(1)致王渝》《19800823复萧成资》《198009上旬复陈越》《19810922复苏仲湘》《19810926复李孝华、吕洪年》,《沈从文全集》(第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4、25、57、72-73、143、147、267-268、269页。中提到此事。这里他所提到的这部教材,指的是王瑶于五十年代初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在这部教材中涉及沈从文作品的篇幅仅有七百余字,主要观点是认为他专在猎奇、鼓吹原始野蛮的力量,而无社会意义。[47](PP.160-161)显然,这种评价的确是不科学的。另外,从他劝阻邵华强、汪挺等青年学生以他为研究对象的书信中也能看出这种不满。他说:“易犯时忌”[48](P.180);莫不如搞鲁迅研究“既容易有出路,更不至于出差错”[49](P.257);“至于研究旧一代作家,也以研究业已完全得到肯定的第一流大作家,如鲁迅、茅盾、老舍、巴金、丁玲……论文即或不免抄来抄去,只要像篇文章,到毕业分配工作时,就见出十分具体现实效果”[50](P.291)。再者,他还多次在书信中表达了对独尊鲁迅、只学样板戏等思想控制的强烈不满。在1974年9月28日致徐盈、彭子冈的信中说:“听到北大国文系一个教‘现代文学’的教授说,上面已肯定,商讨近五十年文学成就时,只教鲁迅,作为代表。其中又只教《阿Q正传》和此外一二短篇,和《野草》中几个小杂文。此外即主席的诗,和八个样板戏。倒也简便省事!”[51](P.189)又如,在1977年8月16日致沈虎雏、张之佩的信中说:“在廿年凡是独占情形下,大多数新作家都以为五四只有一个鲁迅,鲁迅最伟大,作品又是《阿Q正传》,别的什么通见不到,听不着,在这种一切独占认识基础上谈‘百花齐放’,能作到的努力,亦可想而知。稍出界线,就犯错误。”[52](PP.117-118)因此,当被问到自己的作品与国民性改造思想是否有相通之处时,他自然会特别反感,以至断然予以否认。更何况,他还与鲁迅有过一些过节,而鲁迅建国后一再被神话,因此他就更不愿意与鲁迅扯上任何关系了。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他对国民性改造思潮的特殊理解。查沈从文的文章,共有两处出现“国民性”一词。一处是在《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一文中,在介绍《莽原》杂志时说:鲁迅是这本杂志的负责人,对于上面的作者“假若是我们对文艺还抱有欣赏文艺醇化以外的使国民性趋于非微温的地方去的愿望,我们当然得同情他们!”[53](P.15)一处是前文已引用过他《上海作家》一文中所提到的:“应该奖励征求能使国民性增加强悍结实的一切文学作品。”[11](P.44)尽管这里所提供的信息不多,但仍能从中窥见沈从文对国民性改造的基本认识:第一,他所提倡国民性改造的思路与鲁迅的不尽相同;第二,他将鲁迅的思路等同于当年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思路。关于第一点,从本文前面所阐释的内容来看,二者之间的差异的确非常明显。他们对国民性的观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所凭借的思想资源也不同。如果说鲁迅借助西方个人主义思想,所揭示主要是在异族奴役和传统文化束缚下所形成的国民劣根性的话,那么沈从文则是凭借来自湘西生活的一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侧重于对现代文明给国人所带来异化的反思。
至于第二点,沈从文这种理解也不无道理,但他的这些认识却比较狭隘。尽管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和表现,的确最能代表这一范畴的基本内涵,即站在精英式的启蒙立场上,以西方个人主义思想为理论支撑,以日本、德国等国的国民性为参照,揭露并对中国国民性的种种弱点加以改造。然而,事实上,“国民性改造”却从来都不是这样一个狭隘、凝固的范畴,而是包涵着许多种视角、思考路径和表现方式。比如,与鲁迅同时代的周作人、林语堂就与他的思考不尽相同,更偏于学理性;又如,与沈从文几乎同时登上文坛的老舍,他对国民性的认识和表现与鲁迅之间差异则更加显著。他从市民主义角度,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开辟了另一条路径。[54]另外,如果放眼中国当代文学,则会发现它始终是一个不断被丰富的范畴,诸如余华、莫言、韩少功等作家都从各个角度思考和表现过这个主题。也就是说,从客观上讲,只要是希望通过揭示中国国民性的特点进行民族反省,向读者传达一种改变和完善国民性的思考的作品,都可以被纳入到“国民性书写”这个范畴里。至于通过哪种路径和方式,借助何种思想资源去书写,其实都是可以的,甚至连是否使用到“国民性”一词,是否谈论到国民性改造这个提法,也是无关紧要的。
更何况,何谓“国民性”,历来对它的界定就说法不一,在不同作家笔下其内涵也不尽相同,而且常常与另外一些词语混用,比如“国民精神”、“国民气质”、“民族性”、“民性”、“种性”等。关于这一点,从1919年《新青年(第二卷)》上光升发表的《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中的这段解释,就可窥见当年这个话语处于流行时的基本涵义。他说:“一国之政治状态,一国人民精神之摄影也。……无以名之,名之曰国民之精神。政治学者,或别称之曰国民性,即一国民之思想也。”[55](P.348)可见,所谓的“国民性”,也可称作“国民精神”,二者是通用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沈从文笔下反复宣扬的国民精神其实就是国民性,只不过不是那种狭义的国民性而已。
当然,比起国民性问题,更引人关注的是,沈从文对“人性”,尤其是对其中的神性的“供奉”。[21](P.2)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两个问题,沈从文本人对此也没有清晰地说明过,但无论是从人性与国民性之间的关系,还是从沈从文从事文学创作的具体动因、志向以及实践来看,这两者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完全可以说是一致的。因为,实际上国民性本身就是人性的状态和表现,只不过它在对人性的认识的角度上,侧重的是地域差异、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等方面而已。也就是说,其实对国民性的批判,也就是对人性的批判,对国民性的改造,也就是对人性的改造。相反,倘若从沈从文的文学观,即重造国民观念的角度来看,他对健全人性的思考和表现,实际上也就是对改造国民性的思考和表现。另外,如果说国民性改造是一个包涵着多种视角、思考路径和表现方式的范畴的话,那么沈从文对于国民精神重建的思考和表现,无疑也构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国民性书写”。
[1]沈从文:《白魇》,《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2]曹林红:《“国民性”主题的流变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知网博士论文库,2007年。
[3]沈从文:《答凌宇问》,《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4]杨联芬:《沈从文的“反现代性”——沈从文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
[5]张新颖:《沈从文九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6]沈从文:《中国人的病》,《沈从文全集》第1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7]沈从文:《变变作风》,《沈从文全集》第1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8]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9]沈从文:《我的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10]沈从文:《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11]沈从文:《上海作家》,《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12]沈从文:《定和是个音乐迷》,《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13]沈从文:《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14]沈从文:《关于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15]沈从文:《欢迎林语堂先生》,《沈从文全集》第1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16]沈从文:《一个传奇的本事》,《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17]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18]沈从文:《湘西·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19]沈从文:《凤凰》,《沈从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20]沈从文:《苗民问题》,《沈从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21]沈从文:《写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22]沈从文:《北平的印象和感想》,《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23]沈从文:《长庚》,《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24]沈从文:《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25]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全集》第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26]沈从文:《泸溪·浦市·箱子岩》,《沈从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27]沈从文:《历史是一条河》,《沈从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28]沈从文:《沅水上游几个县分》,《沈从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29]沈从文:《箱子岩》,《沈从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30]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31]沈从文:《白话文问题》,《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32]沈从文:《致沈云麓19420908》,《沈从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33]沈从文:《生命》,《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34]苏雪林:《沈从文论》,《沈从文研究资料》上,邵华强主编,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
[35]沈从文:《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沈从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36]沈从文:《滩上挣扎》,《沈从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37]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38]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沈从文全集》第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39]沈从文:《鲁迅的战斗》,《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40]沈从文:《19520125致张兆和、沈龙珠、沈虎雏》,《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41]沈从文:《文运的重建》,《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42]沈从文:《萧乾小说集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43]沈从文:《〈幽僻的陈庄〉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44]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45]沈从文:《19570606致吕德申》,《沈从文全集》第2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46]沈从文:《19720630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2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47]王瑶:《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中国新文学史稿〉节录》,《沈从文研究资料》上,邵华强主编,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
[48]沈从文:《19801026复邵华强》,《沈从文全集》第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49]沈从文:《19810905复汪挺》,《沈从文全集》第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50]沈从文:《19811020复两位同学》,《沈从文全集》第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51]沈从文:《19740928致徐盈、彭子冈》,《沈从文全集》第2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52]沈从文:《19770816致沈虎雏、张之佩》,《沈从文全集》第2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53]沈从文:《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
[54]迟蕊:《老舍对“国民性”书写的思考及与鲁迅的差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7期。
[55]光升:《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第2卷,杨宏峰主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
(责任编辑:吴 芳)
Shen Congwen in the Metamorphosis of Domestic New Literature
CHI Ru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Shenya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44, China)
The work of Shen Congwen has once been included in the thought of “national character transformation” proposed by Lu Xun, which lacks sufficient analysis. On the basis of his essays in 1930’s and 1940’s, it is discovered in this paper that despite his attachment to the countryside and resentment to the city, Shen Congwen is neither in favor of tradition-reversion or oppos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As a matter of fact, his wishes, on one hand, to warn the public against the disadvantage of modernity in terms of the naturalness, simplicity and the vigorous vitality of the rural area; on the other hand, to reconstruct the national spirit with truth, beauty and passion of life.
National character; Shen Congwen; New Literature
2016-11-12
辽宁省高等学校杰出青年学者成长计划(WJQ2013033)、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新文学中的‘人民性’历史脉络研究”(L14BZW007)的研究成果。
迟蕊,沈阳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
I206.6
A
1674-2338(2017)01-0120-10
10.3969/j.issn.1674-2338.2017.0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