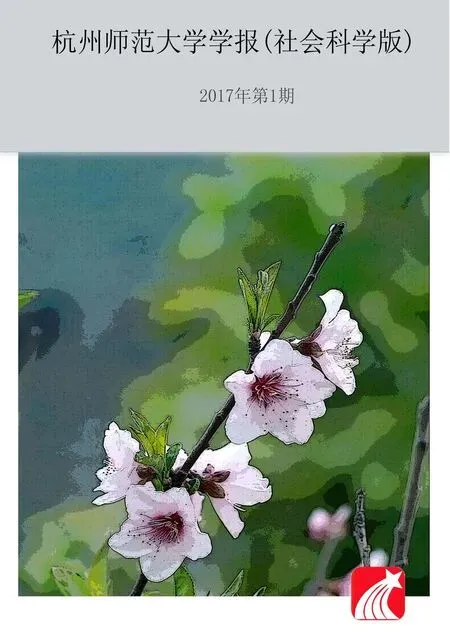辽宋之争:论真宗朝意识形态层面的角力
——兼论宋代的秦朝观之转变
段 宇
(学习院大学 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 日本 东京 1710031)
辽宋之争:论真宗朝意识形态层面的角力
——兼论宋代的秦朝观之转变
段 宇
(学习院大学 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 日本 东京 1710031)
宋真宗在位期间兴起的大规模“东封西祀”运动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澶渊之盟以后辽政权试图通过宣扬自身对秦汉正统的继承来建构自身合法性,这使得外觉威压内生紧张的宋政权在对内宣传中做出了针锋相对的行为。其措施包括对秦汉进行污名化,并最终在舆论场中形成了政治正确。这最终推动了文化和思想上中华史观的重新建构,并使得此后学术发生转向。
宋真宗;意识形态;秦朝观;辽
北宋真宗时期的政治是宋史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话题。从澶渊之盟的缔结到封祀闹剧的上演,引人瞩目的政治事件接连不断;而真宗本人主导的礼制改革的挫折和士大夫势力抬头在有宋一朝的制度建设方面都留下了浓重的印记。这些都极大地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其意义虽极言而不为过。
澶渊之盟的缔结对于封祀闹剧的最终上演,两次重大政治事件之间具有深刻的关联,这已经由诸多前辈学者充分地论述了。①如张其凡:《宋真宗“天书封祀”闹剧之剖析——真宗朝政治研究之二》(收入氏著《宋初政治探研》,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葛剑雄:《十一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读书》,1995年第11期)、刘静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们的权力》第3章(稻乡出版社,1996年)、汪圣铎:《宋真宗》第4、5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第4章(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等,均持此种观点。王瑞来对此的阐述包括,封祀决策的出台并非真宗皇帝凭私意操弄皇权所达到的结果,而是体现为皇帝在得到士大夫势力妥协和支持后,权力层所做的共同行为;同时,举办封祀的根源在于澶渊之盟缔结后,“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一元的中华天下观受到的强烈冲击。[1](P.300)《宋史》卷二八二《王旦传》中的记载可以印证上述判断。
契丹既受盟,寇准以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钦若忌准,欲倾之,从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诸侯犹耻之,而陛下以为功,臣窃不取。”帝愀然曰:“为之奈何?”钦若度帝厌兵,即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涤耻。”帝曰:“河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能为此?可思其次。”钦若曰:“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然后可尔。”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惮旦,曰:“王旦得无不可乎?”钦若曰:“臣得以圣意喻之,宜无不可。”乘间为旦言,旦黽勉而从。帝犹尤豫,莫与筹之者。会幸秘阁,骤问杜镐曰:“古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耶?”镐老儒,不测其旨,漫应之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尔。”帝由此意决,遂召旦饮,欢甚,赐以尊酒,曰:“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既归发之,皆珠也。由是凡天书、封禅等事,旦不复异议。
小岛毅的评价是“为了恢复和宣扬业已坠地的(真宗自己觉得)皇帝权威”的“系列国家级仪礼”。[2](P.71)而何平立在此基础上注意到,“‘东封西祀’运动,并非仅仅是以往史论所言对‘澶渊之盟’的涤耻洗辱事件。该运动的目的,不仅在于以盛大规模的封祀礼仪来证明赵宋皇权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而且也是礼治社会整合和调适统治阶级政治秩序、强化意识形态和构建精神信仰的一场思想运动。”[3]
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转述苏颂的话,更加详尽地谈到了兴起封祀的政治决策是如何出台的:
苏子容曰:王冀公既以城下之盟短寇莱公于真宗,真宗曰:“然则如何可以洗此耻?”冀公曰:“今国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为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闻之,庶几不敢轻中国。”上疑未决,因幸秘阁,见杜镐,问之曰:“卿博通《坟》《典》,所谓《河图》《洛书》者,果有之乎?”镐曰:“此盖圣人神道设教耳。”上遂决冀公之策,作天书等事。故世言符瑞之事始于冀公成于杜镐云。晚年,王烧金以幻术宠贵,京师妖妄繁炽,遂有席帽精事,闾里惊扰,严刑禁之乃止。
但是,仅仅对史料做出解读,不加辨别地继承史料中对于真宗的封祀行为的观点,这样形成的对于“封祀”决策的起因的认识是有局限的。固然,由于王钦若的进言,真宗皇帝对宋政权面临的意识形态危机有了确切了解,甚至可以说是因此而深受刺激,他对于宋政权此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需求有着清晰认识当无异议;同时,君臣双方都对宋辽间的武力对比和宋朝面临的形势有所了解,并基于此做出了谨慎的判断,因此通过对辽进行战略进攻,以达成军事胜利来凝聚人心、确保意识形态的做法并未被提上选项。常识上来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举办国家级的典礼的意义能够与发动战争并带回战果相提并论;可是,这仍然不意味着国家在直面意识形态危机的时候,举办盛大的典礼会是顺理成章的选择。解释真宗选择了通过这种国家层面的礼仪行为的思想背景何在,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史料梳理,从中寻找线索;而在厘清这一政治事件内在的逻辑如何演生的同时,在政治史以外的维度来重新解读这一历史事件及其影响同样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一、论澶渊体系下辽的文化竞争行为
关于真宗的封祀行为,早在元代脱脱修《宋史》的时候,就已细致地观察到其与辽政权之间的关系。
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践位,相臣李沆虑其聪明,必多作为,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见也。及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辽史》,见契丹故俗而后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然不思修本以制敌,又效尤焉,计亦末矣。仁宗以天书殉葬山陵,呜呼贤哉!(卷八《真宗本纪》)
“契丹故俗”既包含了辽政权继承了以天命为尊、以得天命为夸耀的天命观,也包括了礼重游幸这一特点。元人修《辽史》,作《游幸表》,明言“今援司马迁别书封禅例,列于表”,正是基于对游幸的礼仪作用有所认识。根据上述史料能够看出,辽政权通过游幸来夸示天命所在、在树立自身政权合法性方面起到作用。将真宗一手导演的东封西祀和辽政权夸示天命的政治行为两相比照,二者拥有形式和目的的双重相似性。这对于辽宋间的“文化竞争”的实态确是明确的提醒。
胡小伟提出了用“文化竞争”一词来描述这一时期宋辽之间意识形态层面的特殊关系。其研究显示,宋真宗以封祀的礼仪“夸示外国”拥有充分的证据。一例是景德四年初次举办迎接天书的系列典礼时,恰有两个契丹使节团进驻东京,分别对应着“降神”和“酌献三清天书”仪式的时机。另一例是举办泰山封禅典礼之前,“命都官员外郎孙至辽境上,告以将有事于泰山”。尽力做到了对辽的展示。[4]然而,关于宋辽两国之间的文化竞争是如何进行的,这一点还需要在利用史料时,在超越宋朝中心观的前提下做出进一步的分析来显示。
张耒写道:“为今中国之患者,西北二虏也……自北方罢兵,中国直信而不问,君臣不以挂于口而虑于心者,数十年矣。”[5](P.1293)点出了对于宋朝廷而言所谓的外患长期存在,并且即使是在军事敌对行动依照盟约平息以后依然如此。此处“外患”的真实含义,除了一个与“中央政权”平起平坐的政权出现在“卧榻之侧”,造成意识里的中华秩序内在的紧张以外,外在的以文化竞争为形式的压力也始终存在,不可忽视。长期以来被视作野蛮民族的契丹,在建立辽政权后又是如何在文化领域挑起竞争、让宋朝君臣花费重大代价迎战,这是问题所在。
辽太祖接受“中国之王无代立者”的成规,推行帝制,并诏建孔子庙,保留幽州诸制度。随着辽太宗灭晋,唐代礼器北归,宗庙制度也得以完善。“始置太祖庙,岁时祭祀。”宋朝士大夫对此有着较为清楚的了解。《宋史》卷三四〇《苏颂传》言辽朝“颇窃典章礼义”。而《辽史》卷五八《仪卫志》里写道:
王通氏言,舜岁遍四岳,民不告劳,营卫省、征求寡耳。辽太祖匹马一麾,斥地万里,经营四方,未尝宁居,所至乐从,用此道也。太宗兼制中国,秦皇、汉武之仪文日至,后嗣因之。旄头豹尾,驰驱五京之间,终岁勤动,辙迹相寻。民劳财匮,此之故欤。
这说明了辽逐步制定典礼的过程。辽太祖建国时期戎马倥偬,未得集中精力进行国家礼仪方面的建设,被附会为舜一般的行为;而太宗时期开始将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正规化,并被后代帝王继承了下来,其意识形态的内容则是“秦皇、汉武之仪文”。
仅仅过了一代,到了辽太宗时期以后,辽国方面的上述工作已取得了高度成效:
至于太宗,立晋以要册礼,入汴而收法物,然后累世之所愿欲者,一举而得之。太原擅命,力非不敌,席卷法物,先致中京,蹝弃山河,不少顾虑,志可知矣。于是秦、汉以来帝王文物尽入于辽;周、宋按图更制,乃非故物。辽之所重,此其大端,故特著焉。
即使以现在的学术眼光来审视,也应当承认辽政权所做的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建设在内涵上与秦汉立国时期所做的意识形态建设有着相当的共通性。“帝号”在统一之初执政合法性宣传中的重要意义得到了充分重视,领导者的武略和德行方面也作为赢得社会认可的手段加以了宣扬,制造和展开了统一国家的热望等方面的舆论、还有试图通过“宗庙”的建设取得对执政权力的认可,[6]这些秦汉开国时期的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受到重视的因素,在此时依旧发挥着影响。
另外,本处对于王通言论的引用亦有可玩味之处。王通自称“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主张以“天命”来判定正统所在,其尊元魏为正统之说饱受争议。其所提倡固与辽“北朝”地位相匹配,又与作为“契丹故俗”的天命观相合。有学者指出王通思想在此期间的传播,可分南北两大支。[7](P.119)而北方政权对王通思想更为重视,将其视作官方意识形态。宋朝诸儒亦重王通,视为道统中人而张挞伐于史论,如欧阳修作《原正统论》,斥王通之说为“不至之论”。张沛文中有“宋以积弱偏安之国而如此推重帝元魏之王通,岂非咄咄怪事”,[8](P.56)既注意到了现象又觉察了现象包含的理论矛盾,而解释这种现象归因为王通《中说》的理论坚实性。隋唐五代释氏大盛,及宋儒学不免与之争,为赓续此间儒家道统而不得不重王通,本不足为怪。而从宋儒对于王通的评价来看——部分肯定其学术地位却做低于以往的人物评价,论短其史论,一意批判——正可推测宋人对于王通的批判态度也有否定辽金正统性的警觉心在起作用。
二、正统观念层面的抵抗与传国玺神话破灭
辽所得“帝王文物”里,最有意义的莫过于汉传国玉玺。《辽史》卷五七《仪卫志》有如下记载:
会同九年,太宗伐晋,末帝表上传国宝一、金印三,天子符瑞于是归辽。
传国宝,秦始皇作,用蓝玉,螭纽,六面,其正面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鱼鸟篆,子婴以上汉高祖。王莽篡汉,平皇后投玺殿阶,螭角微玷。献帝失之,孙坚得于井中,传至孙权,以归于魏。魏文帝隶刻肩际曰“大魏受汉传国之宝”。唐更名“受命宝”。晋亡归辽。自三国以来,僭伪诸国往往模拟私制,历代府库所藏不一,莫辨真伪。圣宗开泰十年,驰驿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
兴宗重熙七年,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
玉印,太宗破晋北归,得于汴宫,藏随驾库。
《辽史》的文字对于汉传国玺的来源、授受交代甚详,可以在这段叙述看出辽政权以自己拥有传国玺这一礼器的名义,将自身紧密地归入了因玺而得统的历史王朝之列。于时人影响之深刻自不待言,对外足值夸耀。郝经指出“天下之人,遂以为帝王之统不在于道而在于玺,以玺之得失为天命之绝续,或以之纪年、或假之建号”[9],可以为证。此处“玺之得失”指的是哲宗绍圣五年改元元符。到辽兴宗重熙七年,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为题试进士。一者可以明白地看出拥有汉传国玉玺乃是辽朝主张自身政权合法性的依据;二者可以看出,辽通过表现对传国玺的重视来主张自身合法性来源于秦汉,这一主张的提出不晚于圣宗开泰十年,即宋真宗天禧五年;三者可以看出辽政权试图以主张该项依据来建立政权认同感的对象是知识人,亦即参与科举的士人。
刘浦江注意到了赵宋时期围绕政权合法性问题的政治文化中传国玺的地位最终走向“沦落”。[10](P.184)但是关于传国玺在这一漫长时期是如何沦落,传国玺被否定的逻辑何在的论述依然有待明晰。解读宋治下的士人们“集体性地、自觉地”在意识形态领域解构由传国玺所象征的传统正统观这一行为,通过类比西欧史来归结为这一时期存在一场启蒙运动的确难免质疑。拙论也正是有意于沿用刘浦江提出的关于政治伦理方面的视角来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
截至真宗朝,辽政权借由宣称对传国玺的掌握,在传统秦汉型正统观语境下无疑处在优势,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了绝对高地。辽政权通过宣传战强化这一优势,并且与其他针对汉人的诸如经济方面的优惠相结合,营造了契丹国治下尊儒盛世的景象。这与当时多起士人越境奔辽很可能存在着直接的关系;而非如同之前的研究一样,把这一时期士人的越境和投效辽政权单纯当作宋国在军事上失败的结果。[11](P.99)
不断越境的士人在向宋政权表明着这场起源于澶渊之盟前的意识形态危机的深刻性。而这一时期进行忠节方面的文化建设因刻不容缓而上马,举行封祀也被认为是确有提升臣民忠诚的效用。[12]封禅一事最大的效用当在于,彰显北宋对于圣地泰山的统治,来表明赵宋政权的合法性。这依然可以看作是针对王通思想语境下“中国”定义的行为,意即针对强调“中国之道”的北方政权,宋作为“居中国之地”的政权,具备自身合法性。在辽政权咄咄逼人的宣传攻势面前,宋真宗如此做出了强烈而有效的反击。
士人们对这种大费周章的礼仪表示了抵触与困惑,表现出一种外在的“天人关系的紧张”,这可能也包括对于陷入对方思想语境的忧虑。同时,面对最初由真宗本人主导的显露出支绌的国家宣传,士人们展现出他们在思想上的更多独立。绍圣改元元符之际,士人们对于所谓传国玺真伪的否定已经展现了他们对于围绕着传国玺、以及其所代表的“天命说”正统观有了抵触。李心传、赵彦卫等人都认为“汉以前玺”毁于汉末董卓之乱正是其例。[13][14]宋金石学大兴,围绕金石相关的研究使得士大夫们形成了全新的关系,他们在国家礼仪方面的话语权得以提升,同时营造了围绕文物的共同舆论场。围绕着传世史料的文本记载和来历不明的《玉玺图》等资料,南宋士人对所谓传国玺传世系谱做出了共同的解构。
可是真宗不惜强行推动封祀典礼的举办,这除了预期在上述意义上能起到瓦解辽国正统性宣传的用途,也同样可以解释为这是试图在一般民众之间获得影响,保持地位——所谓“神道设教”。即使面临士人们所在的思想界难以被这种表演打动的情状,真宗并未放弃沿用自身逻辑,坚持在天命归属方面在思想界做出全面反击的姿态,这一期间形成的儒释道三教的文本都能够显示这一点。*典型的研究有山田俊:《北宋·真宗の三教思想について——〈天書〉と〈清静〉——》、東北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報告》第二十八集(第169~191页)和中嶋隆蔵:《〈軒轅本紀〉と〈翊聖保徳真君伝〉——北宋真宗時代、読書人層における道教思想的一側面——》,《東北大学文学研究科研究年報》第五十一号(第57~87页)。久保田和男:《玉清昭応宮の建造とその炎上:宋真宗から仁宗(劉太后)時代の政治文化の変化によせて》,《都市文化研究》Vol.12(第139-152页)也有提及。一些时候,真宗皇帝亲自布置。秦汉的正统性也是在这场宣传反击战里受到怀疑和打击。这场反击的思路在于,如果推翻了秦王朝的所谓的正统,那么北方的对手就算如同他们自己所声称的那样继承其“正统”,也将毫无意义。如果说对于辽国通过传国玺构建自身合法性这一事态,宋真宗的态度尚是停留在否定传国玺真伪性,并未否定其价值的话,比较而言,对于初创玉玺的秦王朝,真宗的态度则是彻底否定其正统性,却并不在意于否定辽声称对其正统性做出继承这一方面。
三、政治正确下的秦汉观演变
景德二年,奉宋真宗皇帝敕命,类书《册府元龟》的编纂工作开始,由王钦若和杨亿负责,耗时八年完成。在其中,关于帝王正统性的论述值得注意。该书体例,将历史上称帝的人物分为帝王、闰位、僭伪三类,在王朝正统以外详细地品评了帝王正统。在《帝王部总序》之中,论及秦朝的部分意义深刻:
秦兼天下,独推五胜,不当正统。
因而将秦王朝与蜀汉、孙吴、南朝宋齐梁陈、东魏、北齐、五代梁一起,置于“闰位”部。该意见的意义不仅在于否定秦王朝的正统地位,还提示了以五行说来标榜正统乃是对于秦朝话语体系的继承。鉴于该书“区别善恶,垂之后世,俾君臣父子有所鉴戒”的性质,这代表真宗时期关于历朝正统问题的官方意见。其意义不仅仅提示了超越历史的语言窠臼,抛弃五行说来进行正统评判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是为欧阳修的“古今一大文字”[15](P.39)《正统论》的面世铺平了道路。宋真宗并没有直接否定五行德运说。实际上在他在位期间,对于宋朝德运的检讨一直不曾衰落,有大中祥符三年张君房进言事、天禧四年谢绛上书事载于史籍,[16](P.2130)其结果是真宗先后以“岂敢骤改”的意见和借两制议“兹事体大,非容轻议。二臣所请,难以施行”驳回。直接对德运说进行否定有违他的不轻言利害更革的施政原则。
但是改变对于秦王朝的观念正是所谓另外一个层次上的关怀,换言之这“使得某种政治语言成为可能”,对于秦朝乃至“承秦制”的汉朝做出否定都因此箭在弦上。不仅仅是通过《册府元龟》的编纂来表明态度,真宗皇帝本人还在咸平四年四月颁布的《论贤良方正制策》中,提到“秦非正统,奚所发明”*见《宋会要辑稿》第一百十一册《选举》一〇之七,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4415页。原文照录如下:汉诏贤良,垂三百余载;唐策俊造,悬四十余科。得士者昌,于斯为盛。用能佐佑帝业,焜耀儒风。历代已来,其道中废。皇朝开国,复举而行。朕奉祖宗,不敢失坠,思得天下方闻之士,习先王之法,明当世之务者,以辅朕之不逮。传曰:“三皇步,五帝骤;三王驰,五霸骛。”斯则皇帝王霸之异世,其号奚分;步骤驰骛之殊途,其义安在。称诏之旨,临御之方,必有始终,存诸典故。加以姬周始之三十六王,刘氏承之二十五帝,受授之端,治理之要,咸当铨次,务究本原。而又周有乱臣,孰为等级;秦非正统,奚所发明。勒燕然之石者,属于何官?剪阴山之虏者,指于何帅?十代之兴亡足数,九州之风俗宜陈。辨六相之后先,论三杰之优劣。渊、骞事业,何以首于四科?卫、霍功名,何以显于诸将?究元凯之本系,叙周召之世家,述九流之指归,议五礼之沿革。六经为教,何者急于时?百氏为书,何者合于道?汉朝丞相,孰为社稷之臣?晋室公卿,孰是廊庙之器?天策府之学士,升辅弼者谓谁?凌云阁之功臣,保富贵者有几?须自李唐既往,朱梁已还,经五代之乱离,见历朝之陵替。岂以时运之所系,教化之未孚耶?或者为皇家之驱除,开我朝之基祚耶?是宜考载籍之旧说,稽前史之遗文,务释群疑,咸以书对。。考核该文文体,“秦非正统”作为陈述的交代出现,能反映出真宗皇帝本人在秦是否正统方面直截了当的意见。
受到了权力支撑、由君主提出的这条意见在通过权力编织的毛细管般的网络向下渗透,发挥着对于言论和思想的规范作用。在福柯看来,这种体现在日常的社会活动中的“规训性”权力甚至比暴力、酷刑、国家机构、法律制度等更为有效,能让权力下的每个人都在“权力的注视”下自我审查。[17](P.193)关于“秦非正统”的话语如何贯彻,这在一些事例方面有所体现,似可资参照。
例如此后宋庠写出《纪年通谱》十二卷,意在区别王朝正闰,其事载《宋史》卷二八四《宋庠传》,《纪年通谱》书目收入《宋史》卷二百三《艺文二》。原书已佚,考《直斋书录解题》可以得其大概,其书将帝王的性质分为“正”、“闰”、“伪”、“贼”、“蛮夷”类,起自汉文帝,并未回答秦的正统问题。
另外,秦字在相当多的场合,特别是与仪礼相关的场合相当于被抹去。前述“汉以前玺”[18]的措辞采用是为一例。这与当时秦国=秦代在意义上成为了北方政权的暗喻指代也有关系。
如北宋更早一些的时期成书的《太平御览》就记载了如下的故事:
《风俗通》曰:秦始皇遣蒙恬筑长城。徒士犯罪,止依鲜卑山,后遂繁息。今皆髡头衣赭,亡徒之明效也。
将契丹民族的形象与秦代刑徒联系在了一起。按《太平御览》,其出典作《风俗通义》。《风俗通义》汉应劭著,原有二十三卷,今残十卷。卢文弨、钱大昕、严可均等皆有考证。钱大昕《风俗通义逸文》将这条辑为佚文第十六条,乃辑佚中的直录手法,因其出处唯一而直录原文。其真实所出似有讨论之余地,或仍为宋儒杜撰,而在政治正确以外又反映一种真实的心态。
被暂时放下的秦正统问题最终在此后的正统论论争中发展为中心问题之一。围绕这个正统争议双方因而可以分为两派,代表人物分别为欧阳修和章望之。充分的辩论后正统论的学术成果由朱熹集大成,内藤湖南以“朱子纲目出,正统大势定”来概括。[19](P.308)这可以看作是北宋真宗时代的诸象在思想界最后的波澜。
四、结语
学术上与“汉学”相对立的“宋学”在东亚思想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宋学肇因于当时政治情势的紧张,源自宋代的学者们对汉学进行批判的思潮,在当时形成的政治正确下注目实际问题。这使得学术范式发生了转换,最终确立了独成体系的全新学问。
长期以来,这一变化的过程被视作作为整体的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部分,其思想上的渊源被认为是上承隋唐时期,并强调了这样一个所谓的长期的学风转变过程中社会的变革和士大夫精神的觉醒的共同作用。如此理解的话,从汉唐以来学风到宋学这一儒学的范式转换虽源自对实际社会的关心,但是视野依然只是局限在国家的内部和士大夫本人的周围空间,“内因”被当成了唯一解释。这对于宋代士大夫的世界观来说未必不是一种曲解。另外,固然这种解读如溯“道统”而上,然而道统的建构就是放在宋学的全盛期也未曾自洽。关于唐宋之间学术系谱的解构仍存在着相当的研究盲点。
众所周知,儒学学术的发展与政治史接触紧密,在宋开国以来做出了崇文尊儒的表率后更是如此,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来说地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与之相对应,儒学者为政治行为寻求理论支持的自觉也同步高涨。澶渊之盟以来,赵宋政权追求像汉唐那样建立世界帝国的政治目标事实上破产,宋国朝野面临全新的东亚世界,以及随之加深的意识形态危机。澶渊之盟以前,辽国所做的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努力造成的影响作为外部因素长期以来被忽视,辽政权以继承了秦汉的正统来建构自身的合法性,在宣传战中处于攻势,这让宋国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正是意识形态方面遭遇的危机推动了宋国国内的知识人群体对史观进行重新建构。除了引人注目的正统论争以外,一些对于历史朝代和人物的重新评价也显示了这场文化转变的彻底性。作为意识形态斗争中的政治行为发酵的结果,北宋时期的思想与学术此后也随着政治上对于“至大无外”的世界帝国路线被抛弃,走向提倡内省的道路。
[1]王瑞来:《君臣——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
[2]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何晓毅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3]何平立:《宋真宗“东封西祀”略论》,《学术月刊》,2015年第2期。
[4]胡小伟:《“天书降神”新议——北宋与契丹的文化竞争》,《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5]吕祖谦:《宋文鉴》卷九一,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6]王子今:《秦始皇议定“帝号”与执政合法性宣传》,《人文杂志》,2016年第2期。
[7]张博泉:《略论金代的儒家思想》,《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5期。
[8]张沛:《“中国”之义——文中子的立身与存心》,Tiziana Lippiello、陈跃红、Maddalena Barenghi编:LinkingAncientandContemporary:ContinuitiesandDiscontinuitiesinChineseLiterature, Venezia: Ca’ Foscari,2016年。
[9]郝经:《传国玺论》,《陵川集》卷一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11]崔瑞德等:《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史卫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2]路育松:《从天书封祀看宋真宗时期的忠节文化建设》,《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13]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14]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五,《全宋笔记》第六编第四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
[15]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16]徐松:《宋会要辑稿》第五十三册运历一之五,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17]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1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六元符元年三月乙丑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内藤湖南:《支那史学史》第一册,东京:平凡社,1992年。
(责任编辑:吴 芳)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Liao and Song: On the Ideological Wrestling during Zhenzong Reign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A Concurrent Discussion on the Transition of the Perception towards Qin Dynasty in Song Dynasty
DUAN Yu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Gakushuin University, Tokyo 171-0031, Japan)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ideology of the massed sacrificial rites of “Dong Feng Xi Si” movement, which took place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Zhenzong in Song Dynasty. After the treaty of Chanyuan, the Great Liao tried to claim its legitimacy by preaching its succession to Qin and Han, the heir of original Chinese. This policy triggered a series of corresponding and a drastic reaction from Northern Song to curb the hostile spreading even Song was already suffering various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oblems. Countermeasures concentrated on stigmatizing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forming the political correctness in the field of public opinion. This controversy ultimately promoted the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history, and made a paradigm shift to the academy.
Emperor Zhenzong in Song Dynasty; ideology; the perception towards Qin; Liao Dynasty
2016-12-21
段宇,日本学习院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宋代学术史、10-13世纪中国思想与国际关系史研究。
K244
A
1674-2338(2017)01-0084-07
10.3969/j.issn.1674-2338.2017.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