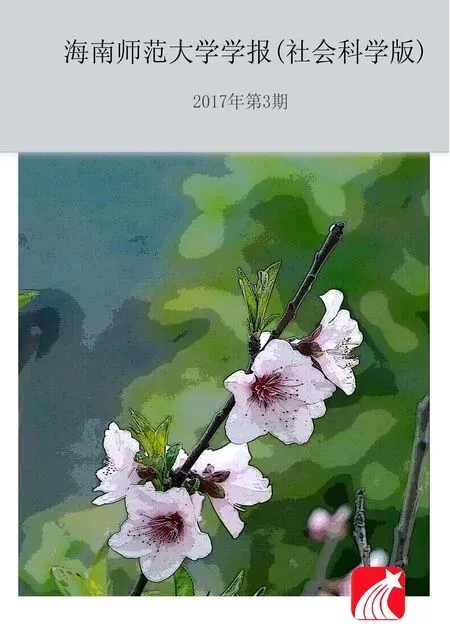重返缄默历史
——论笛安小说《南方有令秧》
蔡郁婉
(中国艺术研究院 《艺术评论》杂志社,北京 100029)
重返缄默历史
——论笛安小说《南方有令秧》
蔡郁婉
(中国艺术研究院 《艺术评论》杂志社,北京 100029)
《南方有令秧》是对女性缄默历史的一次重返。小说首先以丈夫的死亡赋予令秧言说自我的可能性,再借助于对秩序话语的利用与播弄,使令秧宣扬了节烈之名。令秧言说的实现是因为节烈本身所具有的秩序合法性,而对节烈的宣扬也造成了令秧对秩序的规训的自杀性内化。因此,小说只能突兀地转向性与身体抵达令秧生命的自由与完满,而这一转向恰恰意味着超越的最终失效。
《南方有令秧》;女性;秩序;言说;历史
笛安在长篇小说《南方有令秧》中讲述了明朝万历年间寡妇令秧的故事:令秧十六岁嫁与年长她三十岁的唐简为继室,不久成为孀妇。为换得一座贞节牌坊,族中长老逼迫令秧自尽殉夫。守祠堂的门婆子以令秧已有身孕的谎言保住其性命。令秧在家人的谋划下与继子川少爷生下一女,开始了她漫长而艰难的守节岁月。在失意文人谢舜珲的帮助下,令秧如愿获得了贞节牌坊。但在守节的过程中,令秧却与族中九叔唐璞有了私情。在贞节牌坊落成的时候,令秧带着腹中唐璞的孩子自杀身亡。小说将此视为令秧生命完满境界的趋归。显然,《南方有令秧》是对女性历史的一次重返。笛安试图于女性的缄默之中描摹生命与秩序搏杀的痕迹,并探讨女性超越秩序的可能性。这也是本文论述的起点。
一、谋杀亲子——言说的可能性
《南方有令秧》的主线故事似乎是一个“节妇不节,贞妇不贞”的老故事,但笛安却从这一故事模式之中翻出了新意。用笛安自己的话说,《南方有令秧》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失意男人塑造了一个节妇的故事”,是“经纪人如何运作女明星的故事”*笛安:《令秧与我》,《东吴学术》2015第2期。——令秧能够在守寡十多年后便取得贞节牌坊,主要是由于失意文人谢舜珲的帮助。后者对令秧的运作就是一个不断扩大其贞节之名的过程。这是一个令秧不断彰显自我、言说自我的过程,也是秩序话语不断被利用与播弄的过程。
在令秧所处的父权宗法制社会之中,女性作为被拘禁与被贬抑的亚文化群体,被要求顺从与沉默。中国传统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身份地位和言行举止有明确的规定,是“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女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女诫·女行》);也是“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礼记·曲礼》)。在这谨言慎行的规定之下,女性被压入缄默的处境之中。如小说对令秧出嫁之前生活的描述:年年岁岁只能守在绣楼里缝补与刺绣。令秧为其侄女制作过分精细的襦裙实际意味着刺绣是令秧所被允许从事的、仅有的可以发挥其创造力的事。然而,这些倾注令秧创造力的刺绣却又是可有可无之物——随着侄女的成长,这一精细的刺绣终将被抛弃。编织与刺绣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女性的言说;而这些造物的被无视便意指这种言说的无人倾听,因此编织与刺绣便与女性失去权威的命运关系密切。*参见 [美]桑德拉·吉尔伯特、[美]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66-667页。而绣楼这一被限制的空间更直观地显示了女性命运与其的同质性,凸显了父权宗法制对女性所实施的囚禁和扼杀。与这一空间形成呼应的是未出阁的令秧对已出嫁的姐姐海棠的羡慕。海棠的“牡丹髻”或许并不仅仅意味着出嫁的她已经成为一个有历史的女人,而更显示了一种自由的获得,尽管只是相对而言的自由——活动范围从绣楼之内扩大到仍是封闭的深宅大院。但对于被要求成为节妇的令秧来说,这种相对的“自由”背后实际潜藏着更多对于保持缄默的要求。这不仅表现在守节之后,令秧一年里只有正月十五、清明上坟两次出门的机会,偶尔的例外是在祭祖之时听劝人向善、孀妇听之亦不算逾礼的目连戏;当监视与流言呈灭顶之势袭来时,令秧只能以斫伤手臂的行动而非言语来自证清白。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获得贞节牌坊,成为秩序颂扬的节烈楷模,实际是女性在秩序之中显影的一种方式。在这一裂隙之中,女性沉默的处境被有限地打破了。值得注意的是,是丈夫唐简的死亡使令秧获得了争取贞节牌坊的资格。换而言之,是男性家长的死亡,使令秧具有了撕破被迫沉默的层层屏障,并言说自我的可能性。有趣的是,小说中唐简之死与其说是一场意外,不如说是一次有意为之的谋杀。唐简是在元宵观灯时被疯病发作的母亲唐老夫人自二楼撞下,缠绵病榻数月之后身亡。唐老夫人在小说中是一个颇有意味的存在。与令秧相似的是,唐老夫人也曾是青春守寡的孀妇。唐简辞官返家后,唐老夫人与账房先生之间的私情败露。最终,账房先生被迫自尽,唐老夫人也因此而疯狂。这一疯狂显示了女性在父权宗法制之中可能的结果——如果不曾以惨烈的方式结束生命而成为被标举的烈妇,便将以疯狂的形象隐身于制度之中。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女性生命的被扼杀。尽管疯狂看似为唐老夫人制造了某种程度的自由空间,使她获得随意言说的可能。但唐老夫人显示的是一种以言说的形式呈现的沉默。以一种置身制度边缘而获得的洞明,唐老夫人一早窥见了令秧有孕的真相。然而唐老夫人对这一真相的每一次叙说都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疯言疯语,最终形同缄默。以一种悖论的形式,唐老夫人的言说再度指向了女性的沉默。另一方面,唐老夫人这一“阁楼上的疯女人”实际是令秧的一个投影。不仅是“孀妇”这一相同的身份使她们承受来自制度共同的审查、监视和压力;如果说父权体制对节妇的要求与坊间关于“不贞”的流言使令秧遭受的压制是相对无形的,那么唐老夫人在发病时往往被几个身强力壮的婆子合力捆绑,则可被视为这种压制的显形。也是在此意义上,唐老夫人的“疯病”既是父权制实行压抑的结果,也是对压抑的反抗。面对制度规则与自我生命的急剧冲突,如果说令秧的反抗以自残与自杀的形式呈现,是一种“向内”的反抗;那么唐老夫人则借助疯狂的掩饰而使这种冲突成为一种外化和实在的愤怒与攻击,并最终在疯狂间将唐简自二楼推落,以谋杀亲子的方式实施了对制度的反抗。尽管唐简的死将令秧推入青春守寡的可悲命运之中,但同时也确实为令秧制造了打破沉默的机会。以杀子或曰杀夫的方式,笛安探讨了女性在父权制度之中显影与言说的途径——尽管这一处理显得悲观,并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男女两性间的二元对立。
二、节妇令秧——播弄秩序
正如小说所显示的,要取得贞节牌坊最重要的是节妇的事迹能为皇帝所知悉。谢舜珲为令秧谋划而采取的一系列“运作”,都是为了使令秧能够从一群普通的寡妇/节妇之中脱颖而出,从而令她“节烈”的名声“上达天听”,缩短取得牌坊的时间。也正是在此,父权秩序的话语显示出了某种悖谬的性质。一方面,秩序对令秧等守节的寡妇实施严密的监控和规训;另一方面,秩序的话语也暴露出了可被利用的破绽。可以说,对令秧而言,“节妇”这一身份既对她进行了压制,也对她进行了“赋权”——言说与彰显自我的权利。
小说中,谢舜珲为令秧的筹划包括举办“百孀宴”,建议她收留被东林党人攻击而受伤的宦官杨琛等。这些筹划一步步地扩大了令秧节烈的名声,从而为天子所知。而这些策划都是在秩序对节妇的监视与训诫之下完成的。然而女儿唐溦的身世却在根本上否定令秧作为节妇的合法性。这一讳莫如深的秘密也确实给令秧带来了守节岁月中最大的一次危机。在令秧与三姑娘丈夫的争执中,三姑爷当众道出了有关唐溦身世的流言,使令秧无法对这一早已在坊间流传甚广的流言继续视而不见。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流言实际道出了真相。这不仅将使令秧失却获得贞节牌坊的资格,更令她性命堪虞。但这次的危机却为令秧制造了最为有效地利用秩序话语的机会。在谢舜珲的暗示下,令秧借口手臂在争执中被三姑爷所碰触,而用柴刀斫伤了自己的左臂。这一行为是对“贞烈的妇人因被陌生男子拉一下手臂便将其砍下”这一传说的借鉴和实践。当令秧自残这件事流传开来之后,不仅流言平息,舆论更将令秧确认为贞女烈妇的榜样。父权宗法制社会的舆论在此显示某种可被引导和被利用的可能,使令秧得以在秩序之中借以反抗秩序的压迫。不仅如此,节妇“断臂”这一行为被谢舜珲写进自己的戏《绣玉阁》之中。随着《绣玉阁》的上演和流行,令秧自断其臂的贞烈进一步得到宣传。同时,《绣玉阁》所讲述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孀妇守节的故事,戏中的文绣与现实中的令秧本就具有一种互文性,《绣玉阁》的流行便成为对令秧的宣传和彰显。可以说,谢舜珲对令秧的“经营运作”实际是利用秩序的某些裂隙,使一个并非“纯白”的女人重归“纯白”,并塑造传奇。
不仅如此,这一行为也使得令秧能够真正有效地撕裂沉默的遮蔽。借助《绣玉阁》,本应缄默的令秧获得了某种公开性。当戏台上的文绣以柴刀断臂时,文绣背后的令秧借此而显影,从而使整个徽州乃至京城都知道休宁有一位与文绣一样贞烈的节妇。面对禁锢与压抑,令秧借助对自我肉体的伤害劈开了一道裂缝,使呈现自我成为可能。但事实上,令秧对贞烈之名的自我宣扬本就与女性被迫沉默的处境形成对比,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一种对自我的言说。同时,在宣扬贞烈的前提下,令秧的某些“逾越”行为也被允许为合法。东林党人如川少爷等反对宦官征税一事原本属于闺阁之外的、“受命于家”的女子不应参与的“男人的事”。但令秧收留在围攻税监府中被书生与民众殴打致伤的宦官杨琛,不仅使她介入闺阁之外的事端之中,实际也在无意中反对甚至冒犯唐家名义上的家长川少爷。而这一“僭越”不仅未使令秧遭受惩罚,相反的,它不仅使令秧的节烈通过杨琛之口“上达天听”,还导致在川少爷金榜题名进宫面圣时,天子与他谈论的主要内容也是令秧的节烈。在此,令秧/女性的事迹取代了男性的满腔热血、家国抱负,更进一步地显示了一种“僭越”。另一方面,小说的叙述实际还有另一条线索,即账房先生之子侯武的为父报仇。事实上,作为复仇计划的一部分,有关唐溦身世的“谣言”也是由侯武散播出去的,但是令秧斫伤左臂的自戕行为很快使侯武在愧疚之中放弃了整个复仇计划,而成为唐府忠心的管家。节烈不仅使令秧得以显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梗阻于君/臣、父/子的秩序话语之中。借助秩序话语来拆解秩序本身,小说由此显示了某种颠覆的意义。
三、贞节牌坊——自杀式的内化
从另一角度来看,令秧言说行为的合法性其实来自于其言说内容的合法性——其对节烈名声的宣扬,实际上与父权宗法制对女性贞节的要求是一致的,并满足秩序对一个三贞九烈的女性楷模的需求。令秧对贞节牌坊的强烈渴望最初是来自于族中长老的要求,在漫漫岁月之中却逐渐被令秧指认为自我唯一的人生目标,而这意味着对牌坊的渴求正是令秧对父权宗法制规训的内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为使自己成为“纯白”从而获得贞节牌坊,令秧正自杀性地内化父权宗法制对自己的拘禁与扼杀。这正如令秧斫伤手臂这一事件的结果所显示的,在身体上,令秧往往不自觉地将重伤而萎缩的左臂藏于袖中;身体则为了保持平衡而显得倾斜佝偻,身体上的重创使令秧显得更加自我封闭,长时间将自己关闭于房中,不与人作过多交流,对家中事务更加漠不关心。在使令秧的节妇形象彰显的同时,她在身体与精神上都显示了某种程度的残疾。如果说少女时期的囚禁是一种被迫,那么节妇令秧则表现了内化规训之后的自愿。换言之,令秧取得牌坊的过程实际是一个沉默而缓慢的自杀行为。她既是父权宗法制所需要的神话,也是这一秩序话语的牺牲品。如果小说借助宣传贞节之名、获得贞节牌坊来使令秧得以自我言说和显影,那么这一途径却同时通往对自我的扼杀——这也正是小说的悖谬之处。
这种对规训的自杀性内化在小说对令秧与唐溦这一母女关系的描述中也呈现了出来。作为同性,更作为同属父权宗法制社会之中被贬抑的性别群体,母亲与女儿分享着共同的内囿经验;未出嫁的女儿更具有逃脱母亲命运的可能性。在这一基础上,母亲的经验意图为女儿提供参照和指导。因此,令秧为唐溦选中的丈夫是谢舜珲幼子。令秧所看重的是作为边缘文人的谢舜珲并非秩序的代言人和父权家长。这样的家庭将给予唐溦相对的自由。即使成为孀妇,女儿也不必如自己一般被迫守节,为一座贞节牌坊承受十几载空心岁月。这是令秧审视自己的人生后为女儿所寻找的出路——尽管并非真正的自由,但在面对铁板一块的父权秩序时,它至少应允了有限的周全。然而在谢舜珲的幼子夭亡之后,令秧仍然坚持这一婚约的有效性。这使得母亲为女儿寻找的出路转变为对女儿未来的病态扼杀,这一行为坚持的理由之一是令秧认为贞节的女子不能被许配两次。与谢舜珲允诺的周全相比,唐溦首先要承受青春守寡这一更为深刻和沉重的绝望。已被秩序收编的母亲成为秩序规训女儿的直接执行者,母亲的疼爱与关怀实际执行了秩序的规训,从而更牢固地将女儿绑缚在被秩序辗压的位置之上。令秧不仅自己严守诫条,也强迫女儿接受相似的命运,这正是自杀式内化规训所导致的结果。
令秧对唐溦婚事的坚持也致使她与云巧之间同性情谊的破灭,令云巧最终向族长告发了唐溦的身世秘密。这一决裂表面上看是云巧背叛了同性情谊,但事实上令秧才是真正的背叛者。如上所述,令秧已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规训的执行者,显示了一个从同性联盟向内化秩序的转向。而云巧告发的结果则更进一步将令秧指认为真正的背叛者。由于真相的败露将是欺君的大罪,族长只能将云巧对真相的揭穿斥为疯妇的胡言。于是随着令秧臣服于秩序,并成为秩序旌表的节妇楷模,秩序既然认可了她的纯白,便将维护她的纯白。另一方面,秩序的维护者将说出真相的云巧指认为疯妇,则再一次证明了女性的言说在秩序之中的位置——当女性所言说的不再是秩序所允许的内容时,她的言说将被视为对秩序的攻击而遭受惩罚。这也从另一角度将令秧对秩序话语的利用和播弄指认为一种隐晦的臣服。唯有成为秩序的一部分,女性才有显影的可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令秧对话语的拨弄与利用最终只得到了一座贞节牌坊——为沉默个体树立的高大墓碑。
四、身体或性——悬置的道路
在此悖谬的意义上,为了赋予令秧所谓自由与成全,小说不得不转向性与情欲。小说铺陈了令秧与唐璞的一段私情,意图在身体的欢愉之中显示女性个体的苏醒,并以此完成反抗秩序的目的。但笛安在此选择的其实是一条“捷径”。诚然,当令秧最终走向“贞节”的规训最不能容忍的通奸与肉体的欢愉时,小说确实借此传达了对秩序的嘲讽与蔑视。但是,当小说借助性爱与身体去抵达反抗时,历史境遇之中的真正困境却被悬置了。随着小说对“性”的聚焦,叙事所关注的空间相对地缩小了。身体之外,真实而广阔的生活与历史境遇被忽视了。正如令秧的自我封闭与自杀是对真正生活的拒绝,小说对身体的关注实际是一种逃避。这样,性与情欲的反抗意义反而将令秧更稳固地被束缚于内囿的处境中——小说意图借助性/身体这一途径来完成令秧遁逃,却暗示了其精神追求与超越的最终失效;而对性的沉迷更进一步地显示了对精神超越的放弃。事实上,在书写着“节妇不节”故事的同时,令秧仍常常闭门不出不问家事,呈现出一种自我放弃的形象;另一方面,她也确实从未怀疑与放弃她对贞节牌坊的等待。正如波伏娃对通奸的探讨:“这只是虚假的回避,根本不能让女人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法]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II》,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393页。,“性”实际是一条悬置了解决的遁逃之途。因此,性与其说是令秧对父权宗法制社会中内囿处境的反抗,毋宁说突出了这一内囿处境,并再度延宕了对秩序规训的质疑。同时,为了完成“性”这一抵抗途径,小说对这段私情的引入相当生硬。令秧与唐璞仅在唐简去世之时有过短暂的会面。以何来维系这场见面寥寥却又持续数年的爱恋,铺垫的欠缺使得这一情节的铺设显得极为突兀,影响了叙事的流畅。
但是小说同时也透露出令秧的道路并非女性在父权宗法制社会中唯一的超越途径。作为唐简的妾,同为孀妇的蕙娘并不具有获得贞节牌坊的资格。这反而给予了蕙娘免受秩序严密的监视的相对自由。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唐简生前死后,蕙娘都是唐府内大小事务的真正“管家”。不容忽视的是蕙娘的出身,其作为犯臣之女而沦落风尘,反而获得了拓展视野的机会。这与作为闺秀而被拘禁于绣楼的令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令秧将川少爷等书生与宦官之间的争斗视为自己不懂也不必懂的“男人的事”时,蕙娘却可就此侃侃而谈,甚至还借助自己在教坊司里积攒的人脉,挽救了唐府捉襟见肘的财务。蕙娘利用父权宗法制的赋权,达到某种程度的超越,并暗示了女性一旦突破父权宗法制的秩序拘禁之后可能的作为。但当小说着重呈现令秧的命运,而对蕙娘却少正面而详细的论述时,实际上在无形中将有关女性遁逃的可能讨论封闭了。从这点来看,笛安在叙事上对令秧与蕙娘的处理,显示了某种保守性。
五、结语
如果说杀子/杀夫赋予了女性突破缄默处境的可能性,那么作为节妇的令秧则利用了秩序的压制与赋权的悖谬性,在缄默处境中打开了一个缺口。由此可见,《南方有令秧》确实显示了某种激进的姿态。然而,作为节妇的令秧最终所能言说的其实仍是秩序允许的内容,她所显示的形象则是秩序表彰的节妇楷模。为使令秧抵达超越与自由,小说不得不转向性的途径。这使小说的关注被局限在身体之中,而女性所面临的真实而广阔的生活与历史被忽视。通过性与身体去抵达超越成为一条被悬置的途径。在此意义上,小说所给予令秧的实际是一种狭隘的自由与完满。换而言之,通过对“节妇不节”故事的重新讲述,笛安并未为令秧寻找到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完满”。在这里,突破沉默并未允诺对秩序的超越,反而以突破的姿势重复了对秩序的驯服。
(责任编辑:晏 洁)
On Di An’s NovelAStoryofLingYanginSouthChina
CAI Yu-wan
(Periodical Office of Art Review,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29, China)
AStoryofLingYanginSouthChina, a return to the history of female silence, starts with providing Ling Yang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self-narration by virtue of her husband’s death and proceeds to make Ling Yang publicize her fame of a female in readiness to die for preserving her chastity by means of using and manipulating the order discourse. The realization of Ling Yang’s discourse is resultant from the order legitimacy of the act of readiness to die for preserving chastity itself; while the publicity of such an act has also led to Ling Yang’s suicidal internaliza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order. Therefore, the novel has to abruptly pursue the freedom and completion of Ling Ynag’s life by resorting to sex and body, thus having given rise to the ultimate failure in its transcendence.
AStoryofLingYanginSouthChina;females; order; discourse; history
2017-01-20
蔡郁婉(1987- ),女,福建莆田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杂志社编辑,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6.7
A
1674-5310(2017)03-005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