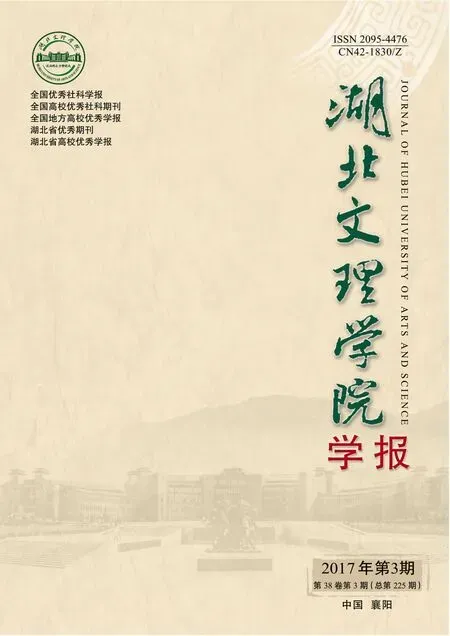王蒙文学作品中的公园、外国文学、音乐及语言
——以《仉仉》为例
赵 露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王蒙文学作品中的公园、外国文学、音乐及语言
——以《仉仉》为例
赵 露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从《青春万岁》到《奇葩奇葩处处哀》(内含《仉仉》),再到刚刚发表的《女神》,“文坛常青树”王蒙一直保持着绵延不息的创造力与创作力。虽然年过八旬,但王蒙仍是那个“青春万岁”“生活万岁”“爱情万岁”的“年轻人”,他的创作不仅承接着过去,更“试验”着未来。在《仉仉》中,从其公园、外国文学、音乐及语言等审美质素的运用皆可察见王蒙文学作品的承接性与超越性。
王蒙;《仉仉》;审美质素
20世纪80年代,《夜的眼》《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作为“集束手榴弹”接连发表。30多年后,《奇葩奇葩处处哀》《仉仉》《我愿乘风登上蓝色的月亮》作为又一波的“集束手榴弹”更是几乎同时写就,同时发表。耄耋之年的王蒙活力依旧、精彩依旧、青春依旧!
从《青春万岁》到《蝴蝶》再到《奇葩奇葩处处哀》,60多年来,王蒙笔耕不辍、孳孳不倦,一直葆有着绵延不息的创作感觉和创作活力。最新文集《奇葩奇葩处处哀》既承接了过去,更“试验”着未来。本文以《仉仉》为例,从王蒙文学作品中的公园、外国文学、音乐及语言等审美质素着手,以期探讨王蒙文学作品的承接性与超越性。
一、公园:纪实与虚拟
“公园”是王蒙人生中“有意味”的场所,更是其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审美质素,“游园”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场景。童庆炳曾言明童年经验对于作家的重要影响:童年经验基本上是一种心理效应,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一个人在青年还是老年回顾自己的童年其感觉和印象可能是很不一样的,这意味着一个作家可以不断地吸收童年经验永不枯竭的资源。[1]《王蒙自传》中详细记录了作者幼时“游园”的经历:父亲和好友傅吾康联合在北海公园买了一条游艇,我们去北海公园划船,吃小窝头、芸豆卷、豌豆黄,“傅吾康叔叔曾经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去北海公园,我有记忆。”[2]王蒙和已故的妻子崔瑞芳第一次相见是在北海公园,“初恋似乎还意味着北海公园。……我们首次在北海公园见的面,此后也多次来北海公园。我们在北海公园碰过雨、雷和风。”[2]王蒙的青春时代也与颐和园密切相关,“六十二年前,当我动笔《青春万岁》的时候,十九岁的小王蒙就那么钟情于颐和园了”。颐和园是杨蔷云、郑波、张世群们青春的徜徉与张扬。公园是张思远和海云爱情的生发地。湖边长堤是鹿长思和郑梅泠寻梦、圆梦与怅惘的追忆。“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耄耋之年的王蒙再一次徜徉在大风中的颐和园,站在十七孔桥上看“波涛汹涌,石桥山丘,长廊庭院,漫天落叶”,记忆蔓延在眼前,情思涌动在心头,“我每去一次颐和园,都要欣赏昆明湖的碧波,惊叹于湖水的美丽与自身的渺小。”[3]再加上老友的一通电话,“我们都老了”(王蒙曾坦言自己很喜欢“我们都老了”,认为这句话特别有感情,特别人性化),《仉仉》便应风景与情思而生了。
开头便是主人公李文采游园的见闻与随想,紧接着的不是情节的顺延,而是追溯到早晨的梦境: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人头和形状与数目不确定的书;然后又追溯到更早的时间:少年时代的红缨枪与文学、月光与青纱帐、地瓜与大黄米地头,青年时代的外国文学书与外国语大学、卷舌音与小舌音、老革命身份与党委工作,还有“崇拜得五迷三道”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复活》《悲惨世界》《红与黑》《双城记》《青年近卫军》和外国文学书籍“特殊的刺活鼻孔的”气息。由气息引出了仉仉,因为仉仉深谙外国文学的味道。接着追忆了与仉仉的相处与自己的万分痛苦和“被帮助”,然后是50多年后的离休、游维也纳与老同学聚会,又一次的游大湖公园以及和仉仉的相遇,仉仉的离世与仉仉寄还的笔记本,到最后的“其实挺好”。在这其中,有王蒙自己真实的经历:共青团的工作经验、外国文学的阅读、被打成“右派”的无奈、2012年旧稿《这边风景》的发现……然而,在你觉得李文采是王蒙的同时,你又有深深的怀疑:王蒙对妻子崔瑞芳是始终如一深爱的,在危难之时妻子也决不会搞揭发,这从其对王蒙小学老师的态度上即可看出。这就是小说家的纪实与虚构了。小说家的天才之一就是让读者觉得这是他又不是他。这到底是不是王蒙呢?在你心里产生这个疑问的时候,说不定王蒙这时候会会心一笑。王蒙曾多次谈到对小说纪实与虚构的看法,见解十分精到:“结构小说的一个基本手段,是虚构。虚构这个词我还不十分喜爱它,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词叫虚拟。小说是虚拟的生活。”[4]“小说之吸引人,首先在于它的真实,其次(或者不是其次而是同时),也因为它是虚构的。如果真实到你一推开窗子就能看到一模一样的图景的程度,那么我们只需要推开窗子就可以看到小说了,何必还购买小说来读呢?如果虚假到令人摇头,又令人作呕的程度,又怎能被一篇小说感动呢?”王蒙进而提出,作家一方面要从实际生活出发,发现别人所未发现之物,用生活实际提供的种种因子进行奇妙的排列组合,用其他方面的经验补充某一方面的有限的经验;另一方面,他(她)也可以设想生活发展的种种可能性,那些从未发生过但有可能发生,或者为某些人所向往又为另一些人所恐惧的尚不存在的事情,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来带动、启发、推进读者的想象,使读者进入一个既是充分现实的又是充分虚构的,既是令人信服的又是莫须有的世界。[5]小说应当求“真”,写现实,写生活,还有真实的内在感受与情感,但不一定要太写实,有虚拟,有虚构,有生发,小说才能更灵活,更生动,更加有情味。另外,《仉仉》中不仅有个人经历和个人命运的浮沉,还有历史、时代与社会的风云变幻,也有白日梦与反思,是个人、历史、命运的万花筒,政治、爱情与性别的纠结激荡,是“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是风雨与阳光兼程的一生,这是王蒙一贯的笔法。更有梦境与现实的交织,时间和空间的交错,情感与思想的火花,不仅有现实感和厚重的哲理色彩,还有梦的浪漫与自然的诗情。“公园”的加入不仅诗意了故事发生的场景,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且与主人公的心境交相辉映,情景交融,相得益彰。相比早期创作中景物主要提供情节生发的环境,后期作品中景与情与境与人更加内在地浑然一体,诗意盎然,情致宛然,更加有韵味与余味。这固然是由于彼时中国当代文学的风景“禁忌”,也可见作者文艺创作的精到与圆熟。王蒙确实深谙小说纪实与虚构的奥妙,诗与真在这里更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二、外国文学与音乐:触动与灵感
王蒙的老朋友刘绍棠说,王蒙属于城市,更注重引进、借鉴、吸收外国文学的表现手法。“在我当时所工作的共青团委会的院落外面,是一个新华书店门市部,我常常到那里去吸吮油墨的香味。我徘徊徜徉于书林,流连忘返。”[5]60多年前的青春记忆在写《仉仉》的时候奔涌而出。王蒙极爱读书,“前四十年,周末的主要活动是读书。”[6]有会背诵千家诗的姥姥和爱背唐诗、爱读文学的二姨相伴,儿童时期的小王蒙热衷于阅读《唐诗三百首》《千家诗》《道德经》《庄子》,青春时代更是阅读了大量的左翼文学、苏联文学与欧美文学。“我开始走上创作道路时喜欢读的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爱伦堡。”[7]可以说,王蒙的青春时代是与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互为一体的,“苏联文学构成了王蒙文艺思想的重要精神资源,也成为王蒙文学创作的一种重要特点,并在相当本质的意义上影响了王蒙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8]王蒙接受了苏联文学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精神,接受了其中的历史感、宏大、光明甚至是感伤的一面。同时,欧美文学丰富的想象力和文学经验也拓宽了王蒙的文学视野和精神空间,影响了王蒙的艺术观念和艺术形式,创作手法更加多样,使其具有更开放的文学视野,更加宽容、多元与兼收并蓄的文学观与世界观,当然这也与王蒙的个性与修养相关。这些都成为作者日后文学创作的滋养与灵感来源。王蒙坦言:“读书,也可以触发你写作的冲动。”[6]在写《青春万岁》的时候,作者一遍又一遍地读《青年近卫军》,甚至画出它的结构图,想要弄清作者是如何将那么多人物妥帖地放在这部鸿篇巨制中;《青春万岁》中有一段旁白:“我每每寻觅,一种光明的奇妙的生活……”王蒙在自传中明确指出:“这是王蒙学了法捷耶夫在《青年近卫军》里的旁白‘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最后是在纷飞的战火中,用靴子作容器,喝下了战友用生命代价舀来的带着战士的苦味与友情的浓郁的水。”[2]《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更是与《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共有其中一个相近的主题:反官僚主义;故事发生的环境都是在基层组织,人物也有相似的对应关系。但王蒙又超越了《拖》,他没有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文本发生的环境——娜斯嘉式的英雄是否存在于当时复杂的生活中,“我无意把他写成娜斯嘉式的英雄,像一个刚刚走向生活的知识青年能够像娜斯嘉那样。那似乎太理想化了。”[9]还有《风筝飘带》与杜富门·卡波特(美国)的《灾星》、《仉仉》与特奥多尔·施笃姆(德国)的《茵梦湖》,所不同的是,王蒙都给了它们光明的结尾:懂得了自己的幸福并相信什么都会有的佳原和素素,“其实挺好”的李文采。外国文学中的“恋头癖”或许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人头有关:《十日谈》《莎乐美》……,中国文学其实也有:《水浒传》《将军的头》……王蒙不仅从外国文学中汲取营养,更注重对中国文学的继承、发扬与有机融合,比如李商隐、老庄、《红楼梦》,这是其不断创新、不断突破、不断超越的土壤与来源。王蒙不论走得多远,脚步始终落在大地上,就像李文采虽然穿着奥地利的西式格子呢大衣,头上却戴着“本市卖烤白薯小贩常戴的灰蓝毛线软帽子”。
王蒙还非常喜爱音乐,“我喜欢音乐,离不开音乐。音乐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我的作品的一部分。有时候是我的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头等重要的部分。”[10]王蒙觉得自己写短篇小说就像在歌唱,“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我像一名歌手,怀着温馨和忧伤,怀着怜悯与嘲弄,含着泪或者微笑着大叫着歌唱。”[11]并提出要像唱歌一样地写短篇小说:“短篇小说应该是一首首发自心灵的歌。每一个作者在写每一篇作品的时候,应该确定这一篇作品的调子。它是一首颂歌吗?哀歌吗?浪漫曲吗?诙谐曲吗?”[5]一个人的青春记忆是不可磨灭的,王蒙的青春与音乐联系在一起,与歌唱联系在一起,“一九四九年给我的第一个记忆,就是‘哗啦’一下子,比钱塘江海潮都厉害——全是歌!”音乐影响了王蒙的生活和文学创作,也定将延续下去。1980年,王蒙在美国衣荷华大学参加活动时听到歌曲《偶然》(根据徐志摩诗谱写),触发了他写《相见时难》的灵感,而且,在写作过程中,歌曲也随行其中,“当我写《相见时难》的时候,我不停地与蓝佩玉和翁式含一起重温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那些歌儿。我是哼着那些歌写作的。”[10]1981年,王蒙重听了青年时代最喜爱的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后,王蒙对妻子瑞芳说:“我要写一部中篇小说,八万字,题目就叫《如歌的行板》。”后来,王蒙又写了散文《行板如歌》。还有《春之声》与约翰·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歌声好像明媚的阳光》与《喀秋莎》《仉仉》与德语民歌《勿忘我》。“音乐是我的老师,当然,音乐也为我服务,它可以引起我的回忆,触发我的感受。”[10]“并从中有所发现,有所获得,有所超越、排解、升华、了悟。进入了声音的世界,我的身心如鱼得水。”[3]音乐给予了王蒙生活的感怀与排遣,更滋养与丰富了其文学创作。
王蒙不仅欣赏,更加思考与突破,“文学与艺术,对我不仅是审美的对象,更不仅仅是娱乐的方式,接受它们的时候,我的投入我的激动我的沉浸,使它们成为我的年轻的生命的价值追求、价值标准、价值情愫。”[2]因而,外国文学与音乐不仅给了王蒙触动与灵感,作者也更加巧妙地将其与文章结合在一起,实现新的艺术探索。《仉仉》中外国文学与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且更加强化了人物性格,对外国文学的看法亦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语境。而且,《仉仉》虽深得《茵梦湖》的精髓,但却完全是王蒙式的题材,王蒙式的风格,王蒙式的艺术感觉,《茵梦湖》原文的引用更是画龙点睛之笔,更好地呈现了人物的心境,审美效果大大加强。而音乐不仅成为了文章的一部分,更营造了唯美浪漫的氛围,且更加凸显文章主旨与哲思。总之,《仉仉》将《茵梦湖》与《勿忘我》更为巧妙地融入了文本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性格的建构、场景氛围的营造与渲染,不仅浪漫、诗意,而且加入了厚重感、开阔感以及智慧与哲思,小说的整体结构更加艺术,布局谋篇更加精致,王蒙的创作手法与风格也更加成熟与精湛。60多年来,王蒙一直走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创新与变革之路上,一直在突破与超越自己。“虽然,我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但是我愿意把路子走得宽一些,我希望我的写作在艺术手法上呈现出一种多元的景象。”[5]《仉仉》展现了王蒙文学创作的新风貌与新可能。
三、“王蒙体”语言
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王蒙之于语言,恰如鱼之于水。”[8]王蒙是一位“感觉型”和“语言型”作家,具有超常敏锐的语感与非凡的语言学习能力和语言创造力。
《仉仉》延续了《闷与狂》的“耄耋抒怀”和“少年狂歌”,语言在舞蹈,修辞在狂欢。“恶霸家里有外国文学书的译本,没有人读,他读,一接触就如醉如痴如喝了糊涂汤。”“欧洲文学书,翻译过来气味与它的人物一样强烈,像酒非酒,像‘四合一’香皂,像龙涎香,……”“他信笔由缰,磕磕碰碰,东拉西扯,咕咕哝哝,诗诗文文……”仉仉朗诵《勿忘我》的时候,“诉说得好苦、好甜、好梦幻、好云彩,好大的西北风啊。她的声音是低语也是呐喊,是喁喁也是忽忽,是大火也是微风。”[12]语词的重叠,词组或短语连珠似的排比使语气淋漓尽致,推动了小说的气氛与节奏;博喻更是前呼后拥而来,“妙喻如舟”,令人目不暇接,如汉赋般洋洋洒洒,如交响乐般奔放激昂,而且多是“陌生化”、创新化的喻体,给人以新鲜感与刺激。“他将比喻和排比当成文学的舞步,闪转腾挪、大开大合、疾风骤雨、密不透风,恣意地宣泄自己的情感。”[13]王干说王蒙有语言的扩张欲,喜欢把各种各样的名词、动词、形容词进行重叠。王蒙自己还说“最喜欢用的是把矛盾式的词和句子用在一起,比如你这个崇高的卑鄙的人,我是经常用这种方式。”另外,王蒙还提出不仅古诗文、古典白话小说、翻译作品、“五四”新文学的语言可以作为我们写作的资源,时尚语言也可以是。《仉仉》中有“最新款的银器”与“路易·威登箱包的专卖店”,牛气冲天,每件衣服只做一件的“巴宝莉专卖店”,“高级香料与特级防腐剂”这样前卫时尚的语词。更为突出的是,《仉仉》的语言还有一种诗意,有一种浪漫,有一种韵味。不论是自然、梦境的描摹,场景、情境的营造,人物心境的摹写,都有一种意境、诗境和诗情,艺术性更高,更加流光溢彩,宛若天成。这样一种“众生喧哗”“杂语狂欢”“妙喻如舟”、排比如珠、诗情盎然、新鲜多样的“王蒙体”语言,这样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探索和试验”,实是“重建了另一种语言和存在(我们更习惯成为现实)的关系,重塑了语言与存在的一种动态的多向性、无序性和模糊性,在这种语言流中呈现为一种无限性的意义敞开。”[9]
语言既是工具,也是思想。人不仅能控制语言,语言也能控制人。“人一旦选择了某种语言,那么他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事实上就由这种语言从极宏观的限度内无形地决定了。”[14]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30年代的大众语文与拉丁化实际上也是思想的争锋。语言深深控制着人类的思想和思维方式。王蒙深刻地看到了语言文字推动思想的力量,“语言文字的这种促进思想的作用一方面说明了符号的功能,一方面说明了表达与思想的不可分。”“思想内容的发展变化会带来语言符号的发展变化,当然,反过来说,哪怕仅仅从形式上制造新的符号或符号的新的排列组合,也能给思想的开拓以启发。”[11]“王蒙体”实是突破了单一的文学观、单一的思维定势和线性思考,消解了一元和对立,消解了“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认为世界不只存在一种真理,一种可能,而是多元、多样、包容、理解与兼收并蓄。这从20世纪80年代王蒙对先锋文学的支持和保护中即可窥见一斑。而这种开放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反过来也滋养了王蒙的文学创作,使其更加多样,更加“活”,也更具张力和创造力。
总的来说,《仉仉》与王蒙之前的作品不仅有承接,更有突破。革命、青春、爱情的相互激荡,历史、政治、个人命运的变幻浮沉,文学、音乐的激发渲染,还有人性与时代的反思,“王蒙体”语言的波诡云谲。但《仉仉》更加浪漫,结构更加精致,更加艺术化,更加有意境,更加有情致,王蒙在其中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浪漫、美好、感怀却又韵味悠长的艺术世界,这也证明了老王蒙不仅能作小说,更能作风格不同的小说!
忧患春秋心浩渺,情思未减少年时!只要心儿不曾老,王蒙尚能小说也!
[1] 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12.
[2] 王 蒙.王蒙文集第4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7-163.
[3] 王 蒙.王蒙文集第1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75-192.
[4] 王 蒙.王蒙文集第2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47.
[5] 王 蒙.王蒙文集第2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67-335.
[6] 王 蒙.诗酒趁年华:王蒙读书与写作[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7-223.
[7] 王 蒙.王蒙文集第2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325.
[8] 温奉桥.王蒙文艺思想论稿[M].济南:齐鲁书社,2012:59-273.
[9] 温奉桥,编.王蒙·革命·文学——王蒙文艺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98.
[10] 王 蒙.王蒙文集第4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85-188.
[11] 王 蒙.王蒙文集第2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45-188.
[12] 王 蒙.奇葩奇葩处处哀[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103-126.
[13] 严家炎,温奉桥.王蒙研究:第二辑[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5:188.
[14] 高 玉.鲁迅的语言观与创作及其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关系[J].鲁迅研究月刊,2000(4):30-45.
(责任编辑:倪向阳)
I207.425
:A
:2095-4476(2017)03-0046-04
2016-12-15;
2017-01-03
赵 露(1992—),女,山东龙口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