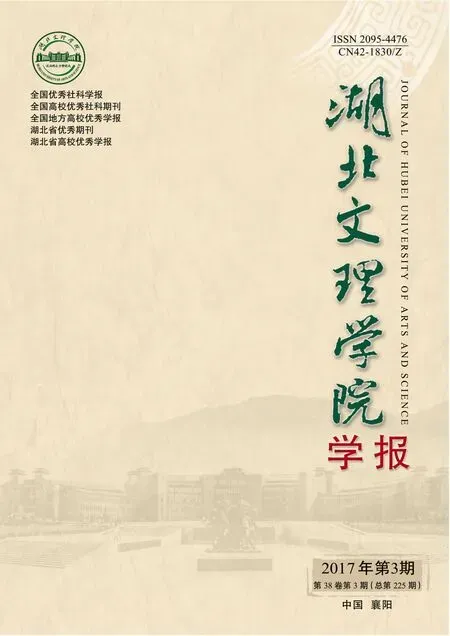规训·反抗·真实
——刘恒乡土小说权力与本能之辩
林业锦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规训·反抗·真实
——刘恒乡土小说权力与本能之辩
林业锦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刘恒乡土题材小说是一个封闭但又意义驳杂的文学文本,他将视野投注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转型的剧变环境中,对乡土个体进行探寻和剖析,从而揭示乡土个体或群体的真实生活形态、生存境遇和生命本能。窥探刘恒笔下所呈现的乡土权力空间,不仅对女性个体生理和心理造成极度的规训和控制,而且乡土权力执行者的男性也未能幸免于难。他用犀利的目光和同情的笔触描摹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乡土社会形形色色的众生相,尽管乡土个体以身体反抗权力失败了,但却表现“力气”、金钱、传统伦理等原始欲望空间下个体的真实生存形态。
刘恒;乡土题材小说;乡土个体;乡土权力
爱德华·索亚认为,“主体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与此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性或社会性生产出了更大的空间与场所,而人类的空间性则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因此,在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形塑我们的文化观念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1]个体心理空间暗指某个个体所在的特定地域以及内心隐秘的心理场所。它既是携带明显个体行为特征的地理景观空间,具有强烈的个人观念、情感色彩,又是一种多重关系组合的隐喻空间,呈现个体与自我、个体与他者、个体与社会等关系的对话冲突。在个体心理空间中,“自我”总是面临“本我”“他者”以及“世界”的混乱现实处境中,他们竭力要挣脱原有模式化生活的束缚,但又往往遭致所处地域空间的阻拒、“自我”与“本我”的冲突以及身份认同焦虑与重构等难题。纵观刘恒20世纪80年代乡土叙事题材小说,我们会发现一个由“食”“性”“钱”等欲望因子组成的传统权力空间结构,是一个封闭但又意义驳杂的文学文本。他摒弃了淳朴、静谧的美好乡村意象与作为“庞然大物”“罪恶”的都市文明,致力于对崩溃前夜的乡土文明中个体心理进行探寻和剖析。在乡土权力巨大整合力下,不仅女性个体生理和心理被规训和控制,而且乡土权力主体的男性也未能幸免于难。刘恒笔下的乡土空间没有牧歌,也没有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文明的侵蚀,有的只是历史因袭的“食”“性”生存困境下的罪与罚。刘恒的乡土权力空间在市场经济即将来临、社会结构转型的前夜诞生,他敏感地触碰到历史即将裂变的内核,用犀利的目光和充满人道的笔触描摹行将瓦解的乡土文明的众生相。然而正是这灰昧的历史一角,折射出乡土空间中个体与群体的真实生活形态、生存境遇和生命本能。
刘恒乡土题材小说个体心理空间在传统道德伦理规范下被挤压变形,他们也曾试图反抗传统权力空间,但往往以失败的悲剧告终,这是刘恒根深蒂固的悲观主义投射在小说文本所然,然而正是这种悲观主义心绪,才呈现出刘恒对中国传统男权主义、父权话语等权力空间的深刻洞察,以及传统权力话语对个体心理的严重压抑和侵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由男性为核心主体建构起来的传统乡土权力在用男权、父权制压抑、摧残女性个体心理的同时,男权、父权制异化出客体的对立面,对男性个体也进行压抑和解构。如果说《伏羲伏羲》的菊豆、《狗日的粮食》的曹杏花、《苍河白日梦》的郑玉楠等女性个体心理空间是男权主义的牺牲品,那么《力气》中的杨天臣、《狼窝》中的史家父子、《伏羲伏羲》里的杨天青等则是父权话语规范下人性扭曲的可怜灵魂。
一、对女性个体心理的挤压
纵观中国几千年浩瀚的传统文化,我们会发现一道挥之不去的精神伤痕:女性作为从属的客体,一直处于被压抑、书写的“他者”边缘地位。在强势的男权、父权话语规范下,女性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灰色的、布满泪痕的历史暗角。尽管历史上不乏饱读书诗之士,但真正能卸下传统男权、父权外衣去体察女性苦难的屈指可数,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坚船利炮轰开了天朝的国门,闭关锁国意识逐渐瓦解以及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等现代文明的不断传入,尤其是“科学”“民主”思想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冲击,对女性的关注、呐喊和“书写”才逐渐“浮出历史地表”。
为女性的正式呐喊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祝福》对“祥林嫂”底层苦难妇女命运的关注与反思,《伤逝》中对现代知识女性与家庭关系的探询,卢隐《海边故人》等对女大学生们婚姻的解剖,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对现代女性主体意识的开掘,胡适译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娜拉的出走,萧红《生死场》对乡土底层苦难女性身体书写与生育、死亡体验等等,无不显示着20世纪初人文知识分子对女性地位与命运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女性地位、女性问题不断被提出和引起关注,但她们的从属客体地位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在于传统男权、父权观念的根深蒂固,已然内化为一种集体民族历史心性,要彻底冲破男权、父权话语的樊篱,任重而道远;然而我们必须警惕的另一个事实是,女性自身方面的性格缺陷也是造成女性个体受压迫的精神枷锁。男权意识可以扼杀女性个体自由生命,女性个体内在人格缺陷同样可以颠覆自身,如女性自我沦落、自我压抑、自我矛盾心绪等等,无不对女权主义的自我拯救愿望构成“颠覆”“解构”。反观“五四”,其对女性个体解放的倡导不是女性群体自发的,而是由男性发起,以男性为中心建构女性“自我”。如卢隐小说从向往、渴望爱情到对爱情的恐惧、绝望进而拒绝爱情,丁玲从追求女性个体解放到向革命意识形态的妥协以致革命的“自我压抑”等等,无不构成对“女权主义”自身的挑战和颠覆。“祥林嫂”在传统道德文化的重压下凄然死去,“子君”也由先前“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而走进“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鲁迅清楚地窥见了传统道德文化这个“铁屋子”障壁之厚,呐喊之后也不免陷入傍徨,正如他在《娜拉走后怎样?》所洞悉的,在当时的特定历史语境下,女性冲出传统男权话语的重围后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性别关怀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在经历了“十七年”“文革”极左政治禁锢人性的特定时期后,知识分子接续“五四”启蒙的人道主义文学传统,重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呼唤人的主体性、文学本体独立性的回归。尤其是在性别关注方面,不仅男性作家掮起这扇“黑暗的闸门”,而且女性作家也加入到关注和提升自身地位的潮流中来。女性自身的性别意识在逐渐提高的同时,也通过女性主体的文本建构发出独特的声音。然而在不同的男性作家性别想象和建构里,女性意识也有着别样的价值和取向。20世纪80年代最早用小说文本关注女性的男性作家要数张贤亮,他在《马缨花》《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里通过对女性(母性)的推崇和赞美,解构“十七年”和“文革”时期极左政治对性别的压抑,使男性恢复阳刚,女性复归柔美,从而具有强烈的性别恢复的现实指向性。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张贤亮在反拨极左政治和纠正男性性别身份时,背后隐藏着一套吊诡的男权话语,虽然他尊崇女性,书写女性,但更多地只是将女性作为男性欣赏、品评的客体,而女性自身则一直处于仰视男性的地位,基本上没有进入女性的心理、精神层面去剖析她们的内心世界,最终女性成为男性献身的牺牲品,这是张贤亮小说女性意识的吊诡之处,也是学界对其进行指责的“罪状”。
细读刘恒80年代中后期乡土叙事作品我们就会发现,他摒弃了淳朴、静谧的美好乡村意象与作为“庞然大物”“罪恶”的都市文明,致力于对崩溃前夜的乡土文明中女性个体心理进行探寻和剖析。同样是女性书写与想象,但很明显刘恒脱去了张贤亮性别想象的痕迹。刘恒将女性个体放置在乡土这个隐形的空间场所里,融性别反思、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等因素于一炉进行对话和碰撞,以人道主义性别关怀为立足点,从外在的生理和内在的心理、精神两个层面剖析、探寻女性主体意识,不仅同情、肯定了女性“性”的自然属性合理性的一面,而且通过描摹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和反抗,从而对传统男权话语进行解构和反叛。
刘恒乡土叙事中的女性主体在面临传统男权话语时,呈现出身份认同焦虑心绪和身份重构困难的状态,然而正因为这一身份认同困境,女性个体心理的压抑和男权话语的根深蒂固得以更好地呈现。佛克马、蚁布斯认为,“一个人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群体或一个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陈规所构成,一个人可以归属不止一个群体。”[2]迈克·克朗对个体身份归属做了进一步阐发,“归属取决于诸多特征中哪些被选中为定义性的特征,将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3]如果说佛克马、蚁布斯指出了个体身份构成、身份认同的决定因素,那么迈克·克朗阐明的是个体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及身份重构的艰巨性。《伏羲伏羲》中菊豆嫁给临近50的老地主杨金山,地理空间上从外村史家营进入到洪水峪,心理空间从一个天真、淳朴、美貌的活泼少女过渡到为杨金山传宗接代的“工具”,菊豆的少女“自我”身份认同必然面临着与杨金山妻子“他者”的文化对话和冲突,以及在洪水峪“他者”文化中如何重构自己身份认同的难题。细察小说文本我们便可以发现,身份认同与身份重构的焦虑始终伴随着菊豆在洪水峪的日子里。在二十亩山地的交换下,20岁的菊豆牲畜般地成为杨金山制造后代的生育机器,她还没来得及确立为人妻的身份,便陷入了男权、父权主义的黑暗中。在老地主杨金山眼里,“她是他的地,任她犁任他种;她是他的牲口,就像他的青骡子,可以随着心意骑她抽她唤她!她还是供他吃的肉饼,什么时候饥馋了就什么时候抓过来,香甜地或者凶狠地咬上一口。”[4]159在根深蒂固的传统男权主义面前,青春活泼的少女个体彻底沦为“牲口”和“肉饼”和任人耕种的“土地”。
如果说未出嫁前只受到父权话语的规训的菊豆还有一个明确的少女身份认同,那么婚后遭受父权、男权和夫权的多重压抑则将菊豆的身份认同焦虑推向了绝望的境地。在性无能的杨金山面前,生命力旺盛的她不仅要面对生理得不到满足的严重压抑,还要承受夜以继日的性虐待折磨。作为男权代表的杨金山在施虐的过程中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方面都造成了对女性个体心理的严重摧残。面对杨金山这种丧心病狂的虐待和无法认可的身份认同危机,有着女性个体自由生命意识的菊豆试图做出反抗。
在同样备受男权话语侵蚀和性爱压抑的杨天青的同情和关怀下,菊豆义无反顾地迈出了反抗的第一步,起初用温情的言语互相抚慰对方,随着杨金山父权家长淫威的日渐高涨以及越来越病态的虐待,菊豆终于冲破了传统道德的牢笼,在杨金山外出期间和天青完成了性的释放和媾合。然而菊豆的“乱伦”式反抗非但没有获得女性个体心理的自由解放,反而加剧了身份认同的焦虑和父权话语的压抑。顺利产下儿子杨天白后,菊豆的身份认同危机随之也达到了顶点,在妻子不像妻子,婶婶不像婶婶的错乱身份煎熬中,她彻底跌进了男权、父权文化霸权的宿命悲剧,尤其是在杨金山得知天白不是自己的至亲骨肉后,乱伦禁忌对菊豆的道德惩罚达到了高潮。正如弗洛伊德在做少数民族部落田野调查时发现的,“禁忌不仅仅在于防范一个男子与母亲或姐妹间的乱伦,它也使一个男人不能够和同族的所有女人发生性关系,故而许多事实上并无血亲关系的女性也被当做血亲看待了。”[5]事实上菊豆和天青既无血缘关系且年龄也相差无几,但却共同受到来自父权制的强烈压抑。
因此,与其说是菊豆触犯了乱伦禁忌,不如说是父权话语侵吞了菊豆的个体生命自由,导致女性主体意识一定程度的觉醒和反抗。在压抑得令人发怵和窒息的男权空间里,菊豆终于爆发出女性主体意识的一面,“天青,我们领着天白逃了吧!去口外我当骡子当马伺候你,……天青,你就听我一句,领我们逃了吧!”菊豆热切渴望通过逃走的方式来重构自己的身份认同,然而可悲的是,卑琐孱弱的杨天青始终摆脱不掉父权和乱伦道德惩罚的阴影,“碗大一个天,窜到哪儿是个咋?”[4]227-228负罪感和宿命悲观心理笼罩着这个懦弱的男人,令人讽刺的是,尽管杨天青是如此的懦弱悲观,女性意识已经觉醒了的菊豆还是无法彻底逃脱男权话语的梦魇,苦苦哀求以“当骡子当马伺候”杨天青,渴望杨天青能带她一起私奔,骨子里依然存在男权话语规范的阴影,依然脱离不了男性,这也注定她身份认同重构的失败。当杨天青在“弑父”梦魇阴影下扎了缸眼子后,菊豆的个体心理被彻底压垮,同时女性觉醒身份认同重构也宣布溃败。“每逢清明时节,他就去杨家坟地在两个辨不清谁是谁的土堆中间坐下,掏出干干净净的手帕,抑扬顿挫地放开苍凉的喉管,为她伺候过的两个男人高歌一曲,……‘我那苦命的汉子哎’……”。[4]252-253与其说菊豆在为自己伺候过的两个男人歌哭,不如说是在为自己凄惨的身世与命运而哭,当她从女性意识觉醒反抗到回归男权话语空间,甚至对以前虐待自己的、让她恨之入骨的杨金山也唱起悲歌时,也意味着她完成了自己身份认同的重构——回归男权中心话语。
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洞察的西方以“自我”为标杆建构、想象东方“他者”的那种文化霸权,他认为“正是霸权,或毋宁说正是运作中的文化霸权的结果,给予东方主义以持久性和强度”,并指出“东方学自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男性领域,……女性通常是男性权力想象的产物。”[6]但颇具讽刺意味的地方在于,“她们或多或少是愚蠢的,最重要的是,她们甘愿牺牲。”[7]264刘恒通过这种女性觉醒——反抗——失败——回归的方式探寻剖析女性意识,在揭示、同情传统男权空间对女性个体心理挤压和侵吞的同时,也预示着女性意识觉醒的艰难。
《狗日的粮食》里的曹杏花也是一个在压抑中反抗的强悍女性,因脖子长瘿袋而显得丑陋的她被辗转卖了六次,最后以二百斤谷子的价格落在了独身汉杨天宽手里。生命力无比旺盛且健康的曹杏花只因长相丑了点,便成了男权话语下人人嫌弃的牺牲品。诚然,爱美是每个个体的天性,但我们在这里必须看清的一点是,曹杏花已经悲剧性地成为男性审美和压抑的对象。面对这种有失人性的压抑,曹杏花用超强生育能力产出六个“粮食”和巧妙的持家手段为家庭度过荒年而恢复了女性主体意识和地位,然而可悲的是,一次购粮证的丢失便夺取了她的这种女性主体意识甚至生命。她在临终中嘶吼,“狗日的!粮……食……”与其说是赖以为生的粮食夺走了她的生命,不如说是男权空间摧毁了她苦苦建构和恢复的女性主体意识。正如小说文本所说的,“他一辈子没有逞过大男人的威风,也许试过一次,但只一次便要了老婆的命。”[4]15
如果说《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是通过女性觉醒——反抗——失败的模式呈现男权空间对女性个体心理的压抑,那么《萝卜套》中韩德培与柳良地的妻子则始终处在一个模糊甚至缺席和被男性玩弄的地位。窑主韩德培在位期间,作为窑梆子的柳良地之妻成为丈夫权力欲望的工具,为了不惜一切往上爬,柳良地只能眼睁睁看着妻子忍受窑主的侮辱。然而权力更迭,韩德培在一次野外打猎时不慎摔下悬崖致残变疯,韩德培和柳良地的职位戏剧性地发生位移,而韩德培之妻也成为柳良地权力欲望和报复心理的牺牲品。值得注意的是,在窑主和窑梆子权力更迭前后,两个女性都处于模糊甚至缺席的地位,而且无论是谁当上窑主,对方的女人都成为男性的玩物和牺牲品,在权力空间里面,女性主体意识丧失、女性话语也完全失语,最终成为男权中心话语的牺牲品。
二、对男性个体心理的摧残
在乡土权力巨大整合力下,不仅女性个体生理和心理被规训和控制,而且刘恒小说中作为乡土权力主体的男性也未能幸免于难。乡土传统文化也有消极的一面,往往会催生出一种集体无意识心理,对乡土个体心理造成一种认同基础上的戕害。正如费孝通所言,“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但是乡土社会中,传统的现代性比现代更甚。那是因为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7]84费孝通在这里指出的是传统文化在维护乡土社会结构稳定性中的重要作用。只要回顾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就会发现,父权制不仅对女性集体造成极大伤害,而且对父权建构者的男性也进行压抑和规训,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无论是作为主体受害者的女性还是客体的男性,都一定程度上认同、接受父权制对他们的侵蚀,甚至往往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父权制从“家族”或“宗族”中演变出来,“家族,又称宗族,它是以家庭为核心实体的以血缘与性关系为纽带的人类社会自我协调的结构性产物和基本单位,是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双重互动的必然结果。”而父权制是指“一种家庭——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有机体系,在这个制度内的权力运行方向是:年老的男性有权支配青年男性,男性有权支配女性。”[8]父权制往往和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错综纠缠,共同构成对人们的规训和压抑。如果说父权制对女性个体心理的规训和挤压是乡土社会权力横暴的表征,那么“力气”、金钱、伦理则作为一种隐性权力结构自始至终规训乡土男性个体,它作为赖以生存和感知自身存在的精神支柱,一旦消退和瓦解,则预示着男性主体性的崩溃。
正如刘恒自己所说的,“……想寻找农民赖以生存的几根柱子。粮食算一根,再找找到了‘力气’。发现力气对于劳心者和对于劳力者是有区别的。又发现哪怕劳心者浮上塔尖,在塔基里垫着的还是那层‘力气’。力气绝了就全完了……。”[9]刘恒发现了“力气”对农民尤其是乡土男性的重要性,然而也正是“力气”的重要性造成对乡土男性心理的规训和侵吞。
正如《力气》中杨天臣自出生之日起便以惊人的力气震惊了整个洪水峪,因而赢得了“家伙!力气愣壮!”的美誉。他三岁便能随母上山剜野菜,四岁从父入山捡柴,七岁下地犁田,十三岁已经成为洪水峪响当当的男子汉了。杨天臣在洪水峪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身上仿佛拥有使不完的力气,不但用骄人的力气把自己庄家理得有板有眼,而且还自告奋勇用无尽的伟力去打日本、打蒋介石,赢得“地雷大仙”的美名,可谓一生坦荡、正直、仁义。然而随着身体的衰老,杨天臣身上的力气悄然流失,当八十多岁高龄不服老的他在一次摸黑下地不慎摔断胯骨后,拥有无尽伟力的“地雷大仙”再也起不来了。当儿子要送他去医院时,“天臣就是不让动他。他哪儿也不去,。……尸首扔到山外,魂就别想找回洪水峪,他可不想遭那个劫难。”[4]146从杨天臣的执意抗拒苟活中我们不难窥见一个安土重迁的乡土社会“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传统影子,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杨天臣宁愿病死家中也不愿外出就医的固执举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传统父权制对乡土男性个体心理的规训,在“乡土情结”“原乡情结”的背后,隐含着的是一套父权、男权中心话语。
这种顽固的拒绝治疗的情结不单盛行于过去,在当下城乡社会也随处可见。只要细心留意就会发现,这类人对外出就医怀有天然的恐惧,宁愿病死家中入棺入土安葬,也不愿死在医院被火葬。这种顽固的“原乡情结”我们当然可以用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来看待,尽可能地尊重、理解异质文化,不妄加评判,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文化相对主义”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建立在理解和尊重上的困惑和反思非但不是违背“文化相对主义”的客观性,反而是对自身传统文化一种负责任的、人道主义的表现。当杨天臣意识到力气快要消失殆尽时,他用尽生平的力气勒死了自己,临终时发出了最后的哀吼:“狗日的,力气哩……我那力气哩!”从杨天臣这种残忍极端的自戕方式我们可以看出“力气”对于农民的重要性,尤其在男性农民身上,“力气”已然成为他们区别于女性性别的标志,然而正是在对“力气”的渴望和推崇中,才建构起男权、父权主义的高塔,反过来对男性个体心理进行规训和侵吞。因此,与其说是“力气”的丢失夺取杨天臣的老命,不如说是男权主义、传统性别空间摧毁了乡土男性的个体心理。
如果说《力气》呈现的是以“力气”为表征的传统性别空间对乡土男性个体进行侵害和压抑,那么《伏羲伏羲》和《狼窝》则从传统道德伦理和金钱欲望角度侵吞乡土男性个体心理空间。《伏羲伏羲》中杨金山杨天青叔侄二人共处洪水峪封闭的乡土空间,共同受到传统宗法伦的规训和侵蚀。宗法思想根深蒂固的杨金山对年轻的菊豆百般虐待和压抑,对侄子也如长工般使唤,俨然一位封建家长权威的代表,但不可否认的是,杨金山也是传统伦理秩序的受害者。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百善孝为先”等传统伦理观点的浸淫下,杨金山宁愿舍弃农民看得比命还重的二十亩土地,为的只是娶回一个健康漂亮的女人为自己承续“香火”,然而生理上的无能宿命般地摧毁了他的美梦,在对菊豆施虐的同时自己也处于受虐的状态,当别人斥责他虐待菊豆时,他悲哀地反驳,“你孙子抱上了,扯啥清闲?……我断子绝孙不碍你们的事……”,“……揍出个活的来,我给她做猫做狗,揍不出活的,……我亏不亏?老子一辈子白活亏不亏!”尔后又绝望地嘶吼,“崩了我才好!我活够啦……。”[4]174-175诚然,杨金山的这种粗暴虐待心理是一种男权中心主义理应受到谴责和制止,但若透过男权、霸权的樊篱,我们还是不难看出,一颗被传统伦理道德侵蚀得千疮百孔的心灵,杨金山在行使男权、父权职能时,也被自己的异化所害。同样,杨天青在打破传统伦理禁区后,也掉进了乱伦禁忌的罪孽深渊无法自拔。面对女性意识觉醒了的菊豆的苦劝,杨天青非但没有私奔逃离的勇气,反而日渐卑琐消沉,沉溺在乱伦的罪恶空间里,最终以扎缸沿子的方式结束了自己懦弱的老命。
又如《狼窝》中金钱欲望对男性个体心理的侵蚀。史天会老汉和儿子史大笨几乎花光所有积蓄拿下狼窝煤窑的开采权,以为从此走上发迹致富之路,然而尽管积蓄耗尽,煤层还是没有出现,煤工纷纷离去,邻里也落井下石,流言蜚语铺天盖地地袭来,在财富欲望的驱使下,史大笨将全部精力倾注在煤窑里,不但自私地延误了妹妹的婚姻大事,忽略了家中妻子的感受,严重压抑了弟弟的自由,而且铤而走险干起了黑市交易,导致煤矿几近破产。如果说史大笨的荒谬举动是从自私的冒险角度去追逐财富,那么史老汉的带病留守窑洞防贼则是用生命控诉金钱欲望对个体心理的侵吞。当史老汉得知儿子黑市交易被罚款后,爱财如命的他也随之进入了坟墓。
乡土社会是一种较原始的传统社会形态,“土地”“粮食”“性”本能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支柱,“金钱”欲望是随着现代化进程逐渐发展和加剧的人性本能,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耕生产模式决定了其乡村社会形态,加之儒家“长幼有序”“克己复礼”等宗法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染及农民对土地固定性的依赖,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社会秩序结构。无可否认,乡土传统文化有其自身合理性的一面,但也正是这种传统的因袭在乡土社会建构起了一个权力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权力空间并不仅仅存在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错综纠缠的现代社会,传统乡土社会也一样存在。正如费孝通所说,“我并不是说在农业性的乡土社会基础上并不能建立横暴权力。相反,我们常常见到这种社会是皇权的发祥地,那是因为乡土社会并不是一个富于抵抗能力的社会。”[7]103费孝通在这里指出的是乡土社会超稳定结构背后所隐含的权力,正如刘恒本时期的乡土叙事小说,他将视野投注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转型的剧变环境中,用犀利的目光和同情的笔触描摹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乡土社会形形色色的众生相,从而剖析和探寻“食”“性”“金钱”“力气”等原始欲望空间下个体的基本生存形态。欲望既是人类的一种原始生命形态,也是人类感性生命自由本能的自然呈现。刘恒乡土叙事小说致力于对欲望空间的个体进行探寻和剖析,从而揭示空间中个体或群体的真实生活形态、生存境遇和生命本能。窥探刘恒笔下所呈现的乡土权力空间,不仅对女性个体生理和心理造成极度的规训和控制,而且乡土权力执行者的男性也未能幸免于难。刘恒在呈现乡土权力空间对个体、集体心理侵吞的同时,也给予人道主义关怀和同情。
[1] 包亚明.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1.
[2] 佛克马,蚁布斯.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M].俞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20.
[3]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95.
[4] 刘 恒.东南西北风刘恒小说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
[5] 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M].文良文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7.
[6]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0.
[7]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8] 杨经建.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M].长沙:岳麓书社,2005:1-2.
[9] 刘 恒.乱弹集[M].长春: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78.
Right and Instinct in the Local Novels by Liu Heng
LIN Yej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nning 530006,China)
Local novels by Liu Heng are of Closeness and Rich Meaning.Liu Heng focuses on local individuals or groups living in the 1980s,and explores their real living state,living circumstances and life instinct.Local right,described by Liu Heng,not only strictly disciplines and controls women physiologically and mentally,but also men,the executer of right.Liu Heng presents the appearance of all living creatures in local society with sharp eyes and sympathy.
Liu Heng;local novel;local individual;local right
I207.425
:A
:2095-4476(2017)03-0040-06
(责任编辑:倪向阳)
2016-12-12;
2017-02-23
林业锦(1985—),男,瑶族,广西平南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