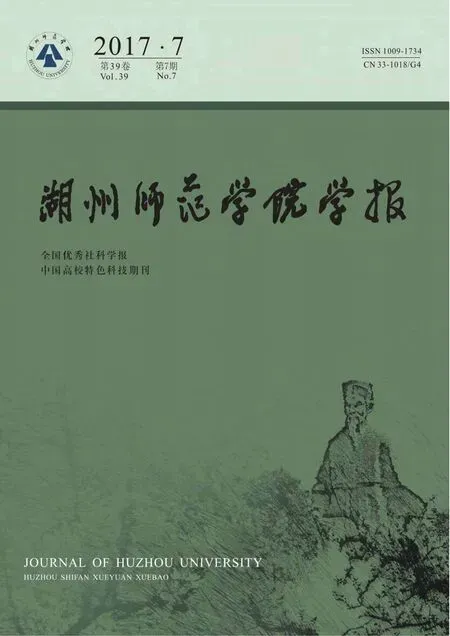“养生”与“革命”:未完成的对话结构*
——论张炜《独药师》
夏 靖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养生”与“革命”:未完成的对话结构*
——论张炜《独药师》
夏 靖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在张炜的新作《独药师》中,“养生”这一古老而神秘的领域走进了读者的视野。张炜试图让代表生命本身思考的“养生”与“革命”这两种话语形成富有张力的对话关系,然而种种原因使得这种对话结构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建构。一方面,“养生”作为一种古老的生命哲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而“革命”的内涵却被限定为具体的暴力行为,二者各自处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缺乏内在的对话基础。另一方面,小说对于历史的表现缺乏作家的主体性观照,历史仅仅作为故事背景被简单罗列,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内涵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
张炜;《独药师》;对话结构;养生
考察一部文学作品,对其主题与立意的基本评判是无法回避的,有时这甚至是决定一部作品优劣的重要因素。然而更重要之处在于,作者是否就这些主题、立意作了充分的文学性表达。从主题上来看,《独药师》所着眼的对革命乃至革命文化的反思,在张炜的写作生涯中从未间断过。《古船》将两次土地关系的变革作为背景,“土地改革”与“联产承包”,二者都被政治主流话语确立了权威性,前者已经被纳入革命话语中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对其最大限度的反思与批判也只能停留在暧昧不明的“扩大化”上。《你在高原》的第一部《家族》,回溯了民国时期知识分子革命家在建国前后的命运沉浮,后面的九部系列长篇,也大多聚焦于革命者后代面对新时期新的社会秩序时的生存困境。在张炜笔下,革命总是面目狰狞的,那少许被肾上腺素驱使的浪漫情怀无法掩盖革命带来的压抑、痛苦、妻离子散以及对生命的戕害。在《家族》中,张炜不惜笔墨地在历史叙述的缝隙间,插入大段大段散文诗般的抒情段落,热烈的讴歌胶州半岛、登州海角的一草一木。这种看似主观、感性的闲笔,与压抑而沉痛的历史叙述形成了互文的结构。自然与乡土的清新美好,无时无刻不在彰显着革命的狂暴与血腥。在《独药师》中,这种与革命行为、革命文化、革命心理对立的情感落到了实处,也就是代表着“东方神秘主义”的“养生”。可惜的是,这种能够扩大小说言说空间的对话型结构没有得到充分的建构。
巴赫金在《小说理论》中讨论“复调小说”的“多声部”特点时,重点论述了复调小说中的对话型结构,同时也对这种结构做出了意义上的限定:每种话语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无可争议,如果只展现为直接的对话,即与他人话语泾渭分明而又相互争辩的明显形式,而不利用话语的内在对话性达到艺术目的,则这种“对话性”不属于文学作品的“审美对象”范围。这里的“内在对话”并不指话语的直接内容,而是说者与听者的主观视野,在同一舞台上相逢碰撞。《独药师》中“养生”与“革命”这一明显的对立关系,就没能“站在同一舞台上”,它们各自处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无法在同一价值层面进行冲突、碰撞。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
“养生”作为一种生命追求,与世俗化的“保养”“健身”不可同日而语,它的终极目的是为了长生,独药师们就是“长生”的践行者。说到长生,这种文化心理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它与传统道家的“修身养性”有所关联,但并不能等同,更多是建立在道家学说的衍生物“神仙方术”之上。胶州半岛之所以能有浓厚的方术文化氛围,或许与秦末著名方士徐福在此东渡东瀛有关,这在张炜的其他小说中也有过展现。“养生”这种生命追求包含着“生命本位”的思想,任何其他的精神、理念都无法大于生命本身的意义,“生”乃是最高的正确。而革命往往带来对生命的损害,由此可见,“养生”与“革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然而在小说中,以革命党徐竟的保镖“金水”杀死来医院暗查革命党的醉酒商人为结点,小说前后的叙事中心发生了偏移。在此之前,小说叙事缓慢地推进,着眼于季昨非与邱琪芝之间,因“养生”与“独药”的牵绊而形成的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后半部分则急转直下,季昨非的单相思对象——麒麟医院的医生助理陶文贝,在季昨非的穷追猛打之下,终于对他产生了感情。自此,季昨非的“独药师”身份开始变得可有可无,他成了一个陷入爱欲而不能自拔的普通青年。在这场莫名其妙的感情中,“养生”成了人为设置的障碍,因爱而生的迷惘与彷徨并不是道德层面上的焦虑,而仅仅是内心理念之争的产物,即“养生”的“去欲”与爱欲的对抗,其实质只是一种道德化的想象与虚构。因此,季昨非之前对“革命”那“摇摆不定”的态度,因爱情的加入转变为“避之不及”,“养生”与“革命”的对话失去了根基。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季昨非与邱琪芝的前后言行会有那么多矛盾之处。面对革命者们暴力推翻清廷统治的诉求,季昨非出于对“养生”理念的坚持,曾做出这样的评价:“长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上天造出了这么完美的生命,不会就让他这么死掉,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1](P103)而当陶文贝受到革命党人牵连,被那个粗鲁的太子少保派来的专员伤害时,他怒不可遏,欲为陶文贝报仇,对伊普特院长说:“院长先生,他侵犯了陶文贝,就必得去死。”[1](P221)显然,这时候戕害生命的行为又不是什么“玩笑”了。邱琪芝前后不一的态度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小说中刚出场时,他像个世外高人一样纹丝不动,对一切世俗的争斗不屑一顾,认为那些都是妨碍“养生”的因素。然而当整个半岛被革命席卷,他终于无法回避之后,面对季昨非对革命的犹疑与恐惧,他劝慰道:“做大事怎可不狠!”[1](P309)紧接着,又向季昨非承认自己这辈子都在和季府较劲,争做半岛的头把交椅,甚至把季昨非视为潜在的对手。这是个莫大的讽刺,一个自称一生都在与欲望作斗争的养生大师,居然带着这么多精打细算的小算盘走过了一生,甚至在死前承认自己的年龄都是虚假的。这无疑将之前创造出的有关“养生”的神话击得粉碎。更为关键的是,“养生”神话的草草收场摧毁了它与革命、爱情三者间所形成的富有张力的叙述空间,养生、革命、爱情各自成为了三个独立的叙事单元。
曾有学者批评张炜小说中总是有着无处不在的“二元对立”情感模式,此言非虚。《家族》中,宁珂义无反顾地骑上那匹腾跃的红马,越驰越远,直面一切血污;除此之外的其他人,要么是凶暴的革命者,要么是懦弱苟且的所谓“知识分子”,要么是愚昧无知的群众。到了改革开放后宁缬这一代,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城市的、商业的一切无不藏污纳垢、愚蠢庸俗;乡土的、田园的一切无不清新美好、纯净高雅。在《独药师》的写作中,张炜似乎想打破这种“二元对立”的情感模式。他坦诚道:“在书中,我尽可能直言,陈列不同的认识。革命党人认为暴力也包含了仁慈;养生家认为革命与养生水火不容。二者好像都不可取代,各说各理,令人陷入‘悖论’。真理只有一个,回答却极不容易。”[2]这种尝试值得认可,然而结果与方式是不能本末倒置的,就如同世界观和方法论不能混为一谈。小说不是由作家告诉我们什么是现实,而是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什么是现实。换言之,无论是“二元对立”还是“罗生门”,它们只能是呈现出的结果,而不是得出这种结果的方法。正如一部小说的主题可以是表现虚无,但小说家写作时的态度乃至结构整部小说的方法绝不能是虚无。《独药师》中,“养生”与“革命”的存在,满足了张炜“陈列不同认识”的需要,但它们的背后恰恰缺少了一个能够统摄全局的力量,也就是作者的主体性观照,这一点后文还会有详细的论述。
二
张炜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有过这样的表述:“养生的基础与核心是仁善。自私狭隘的一己利益的博取者与养生要义背道而驰,所以断然不会成功。书中的养生大家与一般意义上热衷于保健的那些人,在境界上有云泥之别。养生大家们的理想是追求这个世界的至善,认为一切伤害生命的行为都算不得仁善。他们终生与死亡作斗争,其实就是抱定了与捉弄、与荒谬斗争的决心。”[2]前文提到,“养生”与“革命”的对话关系被打破,成为了独立的叙事单元。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从这段话中便可略知端倪。首先,“养生”的意义既高蹈又含糊,它博大精深,没有量化的标准,缺乏现实的体认;爱情,虽然也是感性而不可捉摸的,但它的生命体验非常直接,并不使常人感到陌生;至于革命,完全是具体可见的行为,或者说,是张炜将革命定义在了具体可见的范畴内。
阿伦特在《论革命》中提到,“‘革命’一词本来是一个天文术语,由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Derevolutionibusorbiumcoelestium)而在自然科学中日益受到重视。在这种科学的用法中,这个词保留了它精确的拉丁文意思,是指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运动…… 它肯定不以新,也不以暴力为特征。相反,这个词明确表示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周期运动。”[3](P31)“革命”作为一种社会学概念,第一次被史家使用时,并不是用于一场推翻旧制度的运动,而是用在英国1660年推翻残余国会之后恢复君主制之际。“这个词原封不动地用于1688年,斯图亚特王室被驱逐,君权旁落于威廉和玛丽”[3](P32),也就是“光荣革命”。这样看来,“革命”一词的原义恰恰是“复辟”,也就是要维护或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这在西方文化中不难理解,因为几乎所有西方主流国家都以古希腊的政治体系以及古罗马的法律体系为文化源泉,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都是对“伟大传统”的一次创造性复归。中国古代的崇古、法古思想也有与之相似的地方。古代以天子受天命称帝,凡朝代更替,君主易姓,皆称为革命。可见,革命的目的不一定是要推翻某个制度,摧毁某种思想文化,也并非必须伴随着巨大的暴力。它是为了保证社会处于某种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体系之下,一旦社会规则越过这种体系,就要使之复归,当然这个复归的过程必然也伴随着新的建构。
然而,在中国当代的主流政治话语中,革命的内涵被最大程度地限定了,它与上文所提到的革命内涵发生了偏移。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革命就是一个阶级以暴力方式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运动,“暴力”是它的行为核心。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史证实了这一点,小说中的革命者们也践行着这一点。“革命”这一内涵广远的概念被落实到了具体的暴力行为上。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来看,这也大体符合历史的“真实”。然而具体到每个个体,本该有更多的可能性,能够成为作家探索、表现的对象。历史作为客观存在,它的“真实”是在被不断言说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共语,是多种可能性的集合,是被意识形态权威化的话语。具体到个体,每个人的革命理想、革命诉求、革命手段都会有所差异。当虚幻的养生哲学与具体的革命行为碰撞时,它们缺乏内在逻辑上的关联,因为它们的“真实”内涵已经被限定,处在各自相异的话语体系中。作为两种价值观来看,一个虚一个实,一个形而上,一个形而下,认知世界的角度并不在一个层面。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作者具体而微地描写与刻画,让笔下的人物增加立体感,尽可能呈现出多样化的性格,构建出独属于作家本身的“真实”。很可惜,张炜还是化繁为简了。以季昨非为代表的“养生家”时时将生命的意义挂在嘴边,可是除了喝粥、吃药丸,偶尔像谈玄一般地讨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之外,能够支持他们作为“独药师”、“养生家”的例证实在是有限。因此,他们对“养生”看上去那么坚定,之后的舍弃却也那么决绝,这绝不是借着“为爱出走”就能自圆其说的。而小说中的革命者们(以徐竟为例),仍然是主流文学中最常见的革命者形象:坚定不移,不为世俗情感所动,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是彻头彻尾的行动派。当季昨非以养生的哲学来质疑具体的暴力革命行为时,徐竟反问,难道任由恶人继续迫害善良的人,也能算是仁慈?季昨非对此只能沉默,想反驳却又找不到能站住脚的立场。
三
《独药师》中的那场“革命”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在社会、文化、心理上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巨大的转折点。张炜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了鲁迅与《阿Q正传》,他认为鲁迅就是成功地将历史作为背景来表现的。的确,鲁迅的作品中少有对历史事件的直接描写,但历史无处不在的影响,以及那特殊时代的精神特质,都完美地被赋予他笔下人物的性格与行为中。从张炜之前的诸多创作中可以看出,他一直有着强烈的历史意识,擅长把握历史背后的民族文化特质,但这一点没能体现在此次创作中。《独药师》中的革命史书写,如果没有出现“推翻清廷”这一旗帜性的行为,或是没有“管家手记”的细节提示,就与任何中国近现代史中的“革命”别无二致。“历史意识不是体现在故事材料和细节中,它躲在时间的背后赋以故事特定的意义。所以叙事与历史,在时间的同一范畴内构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4](P218)“辛亥革命”这一具体的历史事件本该具有巨大的言说空间:传统与现代的断裂,旧时代遗老与新秩序的冲突,新时代“新人”与旧秩序的藕断丝连,传统文化与科技文明的碰撞,这些本该与“养生”、“革命”一起构成复杂的对话关系。然而张炜对历史的抽象、简化处理抹杀了这段历史的特殊性,使其成为可有可无的背景,并非不可替代。试想,既然“革命”只是作为“暴力”存在的具体形式,那么这场“革命”又何必非得是辛亥革命呢?
其实在任何文学作品中,历史都只能是一种文学话语的创造,包括那些打着“历史小说”名号的作品。将历史作为背景来表现,是绝大多数小说家的共同选择。然而,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期的历史,都不仅仅是人物与事件的简单罗列,而是某种意识形态与多种思想观念乃至世态人情的混合叠加。作家可以简化对历史细节的表现,但不能忽视历史背后的巨大的社会心理容量。中国当代作家习惯于将历史高度抽象化后,成为某种对当代现实的能指符号。例如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几乎是用“毛时代”的语体写了一个“毛时代”的故事,从语言、意象到描写对象都高度抽象化、寓言化。从某种意上来说,这些都是作家传达某种观念的叙述策略。但这种叙述策略与它要表现的对象本身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叙述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认知空间,无需其他历史细节作为旁证。“养生”与“革命”是宏大的文化概念,可以作为统摄小说的整体架构,但无法承担展开情节、塑造人物的实际叙事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小说需要创作主体的进入,这种“进入”并不是对叙事的主观干涉,而是为整部作品的价值取向定下基本的基调与方向。在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无论多么有魅力的人物,无论多么纷乱庞杂的叙事话语,都无法掩盖潜藏于文本背后那独属于作者的智慧。《独药师》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着不同选择、不同追求的各色人等,却独不见张炜的影子。
当然,通过一部小说妄自推测作家本人的价值取向是可笑的。更何况,张炜历来的主要作品中都有着作家强大的自我,这使得他的小说充斥着浪漫、抒情的基调。在《独药师》中,张炜似乎期望以更加冷静客观的视角审视历史,借以冲淡胸中那股压抑不住的激情,那种借虚构人物之口大段抒发历史情思的段落已很少见到。张炜的大部分热情都投注在了小说主人公季昨非身上。遗憾的是,季昨非只是引领读者走进“养生”这一神秘的领域,却无法为读者提供更多有关“养生”的思考。从他的人物设定就可以看出,作为季府的主人,“独药师”的第六代传人,他与“养生”是被外力强行绑缚在一起的。因此,他的行为逻辑从一开始就被限定在作为“独药师”的准则之内。这类似一些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无意间得知了自己的身世秘密,并意外地获得一本武林秘籍,从此便走上刻苦修炼、行侠仗义的道路,此后的一切行为准则、道德观念都受制于自己不同于常人的背景与身份。在这种设定下,读者无法期望这位侠客做出什么出人意料的举动,因为这种预先设定的身份原本就是这个人物得以存在的理由,更是小说叙事发展的直接推动力。
对于季昨非这个人物的塑造,张炜显然受到了这种身份设定的影响。张炜对于胶州半岛的历史文化、世情民俗如此迷恋,然而这种强烈的表达欲望钳制了张炜的想象力,使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缺乏横向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经过《你在高原》洋洋洒洒的第一人称主观叙事后,张炜似乎有意避免着在叙述中融入作家的主体性观照。季昨非这个形象缺少历史的投射,如果没有必要的提示,读者甚至难以判断他是属于哪一个时代的人。徐竟也是如此,一个标准的革命者形象(这还是在有人物原型的前提下),却唯独与那场特殊的“革命”之间缺乏关联,因而他的形象可以被移植到任何一个时期的革命者身上。“养生”与“革命”各自处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其实,作为背景的历史本该成为二者最佳的对话场所。历史兼具了理性与非理性、传统与现代的多重因素,“养生”与“革命”间的冲突也正与辛亥革命这段历史的特殊性不谋而合。在“养生”成为叙事工具,“革命”的内涵又被限定之后,对于历史的处理关系到小说的叙述空间、思想内涵的展开与提升。
总的来说,《独药师》延续了张炜的文学品格。张炜从来不愿落入“现实的泥潭”,也不满足于“重构历史”的遐想,他的小说总是包含着某种超越现实、超越历史的思考,这使得他的小说有着强烈的思想浓度,但有时也会影响小说在叙事层面的完成度。事实上,张炜并不擅长一板一眼地经营情节、设置悬念。就如同三十年前的经典之作《古船》,在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设置上其实是有缺陷的:他让一群乡民大谈国家前途与世界形势,让隋抱朴埋头苦读《共产党宣言》,这些都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符号化的处理方式。但这些描写、叙事上的缺陷,在隋抱朴十年如一日的自我忏悔、灵魂搏斗中,显得不再那么重要。《古船》颠覆了之前土改题材小说的写法,张炜以人道主义的视角辅以强烈的忏悔意识,让隋抱朴成为当代文学中最有力量、最富个性的文学形象之一。相比之下,《独药师》也有类似的野心,但缺少了作家主体性的参与,无论“养生”还是“革命”,都成了隋抱朴手中的那本《共产党宣言》;无论季昨非、邱琪芝、还是徐竟,他们都无法像隋抱朴一样从文本中挺立起来,成为一个独特而不可复制的文学形象。对于一部主题与立意都相当出色的小说,这是最大的遗憾。
[1]张炜.独药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2]陈龙,李培,张炜.张炜:为了那些倔强的心灵而写[J].南方日报,2016-07-26(A17).
[3]阿伦特.论革命[M].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4]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陈义报]
“LongevityPreservation”and“Revolution”:theUnfinishedDialogicStructureOnthenovelIndependentPharmacist
XIA J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29, China)
In the newly published novelIndependentPharmacist, Zhang Wei brought the “longevity preservation” into reader’s visions. He attempted to combine “longevity preservation” with “revolution” to form a dialogic structure but it remained unfinished. First of all, as an ancient philosophy, “longevity preservation” is highly abstract, but the connotation of “revolution” is defined as the specific acts of violence, they’re both in a different discourse system. Secondly, the description of history is simply listed as the background of the story. Therefore,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connotation behind the history is not fully excavated.
Zhang Wei;IndependentPharmacist; dialogic structure; longevity preservation
2017-04-29
夏靖,在读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7.425
:A
:1009-1734(2017)07-007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