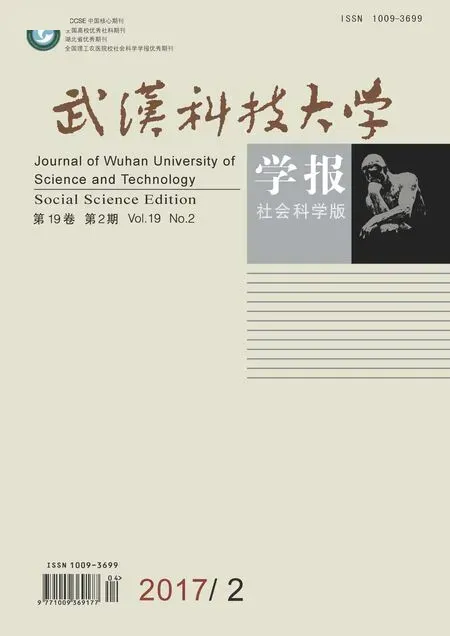从“整体式”视角对《哲学研究》第43节的四个疑问进行解答
徐 强
从“整体式”视角对《哲学研究》第43节的四个疑问进行解答
徐 强1,2
(1.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维多利亚大学 哲学系,加拿大 维多利亚 V8P2S2)
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在于使用”论点的确在《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并不是说这种重要性在该书每一节都有所体现。在该书前137节中维特根斯坦对语词意义的评论主要集中在语词的“使用”和“实指解释”,第43节因为提及了上述论点,因此显得重要。在§43b中理解“实指”概念必须以正确区分“实指定义”“实指解释”和“实指描述”三个概念为基础,维特根斯坦所使用的“实指解释”是在假定了说话者和听话者都具备了完整语言能力的情况下,才认为某个名词意义可以通过“实指”动作将语词“意义”和它的“承受者”联系起来以得到解释。“整体式”阅读主要关注后期维特根斯坦“描述”视角和“评论式”风格。基于“整体式”视角,在§43a有关“意义在于使用”的观念中维特根斯坦并不是在提供某种意义理论,他只是在对语词意义作描述而不是下定义。语词“意义”和其“用法”不仅不同,而且不能互换,这个“使用”概念只是对所有有关语言游戏事例的概括,只有在语词具体使用语境中才能理解语词意义。维特根斯坦在第43节是在谈论语词语言学意义而非形而上学意义。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整体式;语词意义;使用;实指
一、引言
《哲学研究》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大部分阐释者认为“语词意义在于使用”观点主要体现在《哲学研究》第43节中:(§43a)在我们使用“意义”这个词的各种情况中有数量极大的一类——虽然不是全部——,对之我们可以这样来说明它: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43b)而一个名称的意义有时是通过指向它的承担者来说明的①[1]。第43节由§43a和§43b两个句子组成。在§43a中,有两个着重强调的词,即“极大”和“全部”。维特根斯坦认为在“意义”这个词的实际使用中存在着某些特别场景,而数量是“极大的”,尽管它们不能概括“意义”这个词全部的使用情景。我们是通过在语言中具体使用“意义”这个词从而理解语词“意义”的意义。对于这些情况而言,它们的数量是“极大的”,但不是“全部”。为什么不是“全部”呢?维特根斯坦在§43b中给出了特例。在某些情况下名称意义是通过指向它的承受者来得到解释(或者描述),这个特例就是“实指解释”。第43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因为它表达了两个观点,即意义在于使用的论点以及“实指”。在维特根斯坦阐释者当中有关这一小节理解存在着两个争论,这两个争论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
第一个争论是维特根斯坦在第43节中的主要焦点是在§43a还是在§43b?不同阅读角度存在着不同答案。笔者认为有三个理解和对应答案:①如果基于“本地式”阅读,即关注第43节前后小节主要内容,这些阐释者认为§43b是主要关注点,代表人物包括萨维格力(Beth Savigny)[2]和张錦青(Cheung)[3]。②如果从《哲学研究》的写作背景、主要内容和目的,从全书角度,即“全局式”阅读来看,这些阐释者认为§43a是主要内容,代表人物包括哈列特(Garth Hallett)[4-6]、皮切尔(George Pitcher)[7-8]以及贝克和哈克(Baker & Hacker)[9]等。③“整体式”阅读的读者基于“全局式”读者观点来阅读第43节,他们将第43节中两个句子合起来作为整体看待,按照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方法(即只是描述而不作任何结论,评论式)来阐释,古斯塔夫森(Gutstafson)[10]和宾客雷(Binkley)[11]赞同这种“整体式”阅读,笔者也赞同这种“整体式”阅读。张锦青从他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重新理解和解答。张教授有关《哲学研究》第43节阐释的最新中文文章是有关§43b中的“实指”概念探讨,部分思想已经体现在文献[3]和文献[12]中了,所以本文主要涉及的是文献[3]。仔细阅读和推敲张教授对第43节的论述和理解,发现他是从“本地式”角度来理解的。笔者认为如果从“整体式”角度来理解第43节,上述两个争论有可能被消除。另外,萨维格力的相关文章也体现了“本地式”阅读风格,如果张教授注意到了这点,或许对他的理解会有更大帮助②。
第二个争论就是对第43节两个句子内容的不同理解和争论。这个争论体现在四个方面:①在§43a中维特根斯坦提出“意义在于使用”的理念,他是在对语词意义下定义还是在描述?②语词“意义”和其“用法”之间的关联是什么?“意义”和“用法”之间可以等同互换吗?还是有所不同?③在第43节中维特根斯坦是在谈论何种意义?他是在谈论有关语词“意义”的意义?还是在谈论“意义”的意义?④在§43b中“实指解释”和“承受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本文主要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
二、对“实指定义”“实指解释”和“实指描述”概念的澄清
自维特根斯坦1929年重返哲学以来,他就开始对他的早期哲学思想进行彻底反思和猛烈批判,而这些批判主要体现在《哲学研究》中。根据施罗德(Severin Schroeder)的理解,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对他早期哲学的批判主要体现在该书前137节中,其中第108节到133节是在探讨哲学本质[13]127。在这部分文本中,维特根斯坦以对“奥古斯丁语言图像”讨论开始,从语言的意义、使用和学习等多个角度对他在《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进行全面反驳③。 维特根斯坦主要评论了指称主义、意义决定性、逻辑分析观点、意义二重性、核心主义以及通过意味来表达意义等论点[13]128-161。在这些评论中,维特根斯坦一是对他在《逻辑哲学论》中的上述论点进行批判和反驳,二是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想法以及引出他在《哲学研究》中的主要任务和哲学视角。由于这两个活动同时进行,因此有关小节互相重叠交织在一起,笔者认为这也是导致他的思想很难理解的原因之一,而这些误解和争论就体现在第43节中。
维特根斯坦在§43b中说:“而一个名称的意义有时是通过指向它的承担者来说明的”[1]。在这个表述中,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名称的意义可以通过用手指向它的承担者来得到解释。“用手指向”就是指“实指”动作,而“实指”又是“奥古斯丁语言图像论”的核心要素之一,因此显得尤为重要。“实指”(ostension)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在“命名”框架下所进行的“实指定义”(ostensive definition)。在假设成人已经有了一套完整语言系统而幼儿不具备这套完整语言系统的前提下,成人为了教会幼儿某些名词,从而采取“实指定义”方式来对某些特殊名词进行命名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哲学研究》第一节有关奥古斯丁回忆他小时候学习语言的场景中体现着。与此相反的是“实指解释”(ostensive explanation),或者称之为“实指描述”。当我们在谈到“实指解释”的时候,具体语境是这样的:假设有两个成年人,在他们都熟练掌握了他们的母语的情况下,成人甲用“实指”动作来对成人乙并不熟悉的某个新鲜事物进行解释或者描述。这种情况既可以发生在同一个言语社团成员之间,也可以发生在跨语言交流过程中。例如,笔者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加拿大朋友为了告诉我什么是“Timbits”,为了更加直观地告诉我这个专有名词的意义,他特意带我去Tim Hortons买了一份Timbits④,然后利用“实指”方式来对“Timbits”进行解释,而我在这个过程中也就学会了这个词的意义。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开头部分时常在讨论“实指”概念,但是必须要清楚他是在何种情况下讨论的。很多阐释者(包括笔者)并没有注意到这两个概念的微妙区别,而忽视这些区别有可能会影响我们对这一节的理解。笔者发现张锦青在他的文章中也忽视了这两个概念的微妙区别,例如他先是表明在§43b中作为一个例外的情况,名词被它的承受者实指来得到定义或者解释。“在实指定义或者解释中,名词还没有被使用。实指命名只是对名词将来的使用所作的一个准备而已”[3]。接着他又说:“就是基于这个背景,维特根斯坦才想在第43节中表达观点,即尽管在大部分语词意义事例中,语词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而对于实指命名(定义或解释)例子中,意义不是使用”[3]。在这里张教授将“实指命名”“实指定义”“实指解释”三个概念放在一起等同使用,而这三个概念内涵是不同的。需要说明的是张教授在第三部分对“实指定义”和“实指解释”的理解是完全贴近维特根斯坦原文的,张教授认为“在有关§43b中虽然并没有实际发生对于语词意义的解释,也可以被当做一个实指定义”[3]。笔者不同意他的理解,认为他在这里再次忽视“实指定义”和“实指解释”的区别。另外,作为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30年代哲学转型时期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哲学合作者,魏斯曼在《语言哲学原理》中就对“实指”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魏斯曼运用他的“语言层”说来弥补“实指”存在的不足⑤。
三、对《哲学研究》第43节“整体式”阅读方法的阐明
首先,“整体式”阅读需要考虑到《哲学研究》本身的风格。维特根斯坦承认他所能写出的最好东西就是哲学“评论”。安斯康姆解释了维特根斯坦的“评论”:“这带来有关他(维特根斯坦)的独立的评论是什么的问题。在这些评论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分开的,也就是说读者们可以单独进行阅读而不需要考虑到前后文本;而且有人也许会听说该书作者(维特根斯坦)把许多同样的材料按照非常不同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他们也许就会猜测这些组合是相似的。但是事情远不是那样。常常某个评论和它之前的文本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不管这些材料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称为整体的,这些联系都被保存着。因此,不同结构的构造单元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单独的评论,它们也许如此或是彼此地简短串联。(但并不是所发现的那样,一个长长的思维链条是用来思考某个单独的主题。)不管是从整个评论,或者是部分评论而言,它们不管是一个句子,或是一组句子,或是段落,都不是可以直接用来讨论它们是否和周围的文本独立的。”[16]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所展现的是一种“评论式”风格,在不同小节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这种关联好似一个思维链条,从一个主题过渡到另一个主题。因此笔者认为第43节中的两个句子之间的不协调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不同的主题,维特根斯坦从语言意义的使用主题过渡到语言意义的实指解释主题。
其次“整体式”阅读方式还要考虑到两种类型的问题,即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所存在的某些表达不连贯的问题和读者对这些不连贯表达的理解问题。维特根斯坦将他的运思方式总结成“在其中思想从一个对象到另一个对象推进应该依照一种自然的、没有空隙的序列进行”。为了更好地理解维特根斯坦在他的著作中所表现的自然、平缓的思维链条,这需要“整体式”阅读。对于维特根斯坦阐释者而言,必须分清楚什么是维特根斯坦的问题,什么是阐释者的问题。我们不应当将维特根斯坦的问题当作我们自己的问题,果真如此的话,维特根斯坦的思维链将会被干扰和误解。他承认自己没有将这些问题表述清楚,笔者认为就是这个困境导致了对第43节的不同理解和争论。“整体论”式阅读的精髓就是要在不作主观判断的情况下将这个困境描述并展示出来。
最后“整体论”式阅读方式还涉及到有关《哲学研究》的结构问题。维特根斯坦把他的评论比作是“一大堆在这些漫长而繁杂的旅行中所创作出的风景素描”,而且“同样的地点,或者近乎同样的地点,总是重新从不同的方向接触到,新画一再地被绘制出来。其中的许多画画坏了,或者画得非常一般,具有差劲的画匠的所有缺点。将这样的画去掉之后,还剩下一些还说得过去的画,现在它们还得经过排序,常常还得经过剪接,以便能够为参观者提供一幅有关这处风景的图画。因此,这本书真正来说只是一本画册”[1]4。维特根斯坦暗示他在该书中编排和布局过程中存在着问题。笔者认为第43节可以视为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注意到了在大部分情况下,语词意义就是它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然而他又宣称在许多情景中语词意义可以通过指向它的承担者来得到满足。对于整个画册而言,这个不足又可以通过其他部分来得到弥补。如果我们将第43节的两句话当作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过渡,这个不足就变得非常自然和容易接受了。笔者认为“整体论”理解的本质在于不仅要时刻关注到第43节的相关段落,而且还要关注到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的特点和视角。
“整体式”解读与“全局式”解读有很多类似之处,同时也是对“全局式”方法的发展和升华。“整体式”阅读的特色就是将第43节两个句子作为整体来看待,对每个句子都给出同样的关注和阐释。在这之前“本地式”和“全局式”阅读都没有考虑到§43a和§43b是否互相融贯的问题,都一致认为这两句是互相矛盾的,必须要选择其一。与此相反,“整体式”阅读更多关注的是如何根据维特根斯坦的文本来尝试将两句弥合在一起。笔者认为这个阅读方式的主要代表是古斯塔夫森和宾克雷。古斯塔夫森的“整体式”理解是基于他对皮切尔的批判所作出的,他批评了皮切尔在理解第43节中的两个误解:皮切尔把意义和使用等同,认为维特根斯坦在第43节第2句中与意义使用论所对应小部分例外是微不足道的。皮切尔说:“很明显他(维特根斯坦)把这些例外情况当做琐碎和不重的。”[8]古斯塔夫森认为皮切尔的误解主要是因为他没有从“整体式”角度来阅读第43节。第43节评论不是有关“语词的意义”,而是关于单词“意义”的很重要的具体使用,维特根斯坦并没有提出很好的理由来表达意义与使用相等同的观点,因为将这两者相等同是无意义的。宾克雷认为尽管有很多人不同意第43节的主要内容是第1句,即语词意义在于不同使用,但是却没有人可以提供可替代方法,他建议不应该把第43节当作是对语词意义的定义。基于对1967年德英双语对照版《哲学研究》译文的分析,宾克雷认为如果把§43a中的德语词“Erkliirung”翻译为“定义”(definition),这立刻就会和第109节中的内容相冲突。从描述的角度来理解第43节,他并没有认为第43节哪一句是重要的,相反他建议从后期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框架出发,努力寻求提示物,不作定义而只作描述。基于这种观点,第43节两个段落可以被看成是整体,其中§43a所谈“语词意义就是语词在语言中使用”不是在对语词的意义进行定义,而是在作描述。因为“意义的使用论”在语词具体使用中并不扮演角色,而正如维特根斯坦在§43a中所言,这种情况并不是全部,也有特殊,即§43b。在“实指解释”中,语词并没有被实际使用,但是它却有意义。
描述视角是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的根本出发点,这种观点在其第二部分以及《纸条集》中都可以发现:“描述表现的是一种空间分布(例如时间的空间分布)”[1]187。“在哲学中,人们不允许切除思想上的疾病。必须让它顺其自然地发展,缓慢疗法是最重要的。(因此数学家都是如此糟糕的哲学家。)”(《纸条集》第388节)⑥宾克雷把他对第43节的理解同时也放在了维特根斯坦后期“治疗型”哲学背景下,这种治疗型哲学就是对问题进行描述而不作主观判断,这点在《哲学研究》的序言以及在魏斯曼的《语言哲学原理》和《我如何看待哲学》⑦等著作中都有体现。而把握好这些观点就是对《哲学研究》“整体式”阅读方式的体现,笔者同意“整体式”阅读阐释者对第43节的理解。基于笔者所倡导的“整体式”阅读方式,将分别对第43节中的四个问题进行分析和回答。
四、对第43节的四个问题的分析和解答
(一)维特根斯坦在第43节中是在对意义“定义”还是在“描述”?
下“定义”和作“描述”是从不同角度来讨论哲学问题。对语言意义的哲学追问也可以被认为是在解释语词的意义。语词的意义是什么?魏斯曼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分析。魏斯曼认为这个问题提出的原因就是我们通常认为语词的意义具有某种“本质”或者是“实体”。我们预设某种东西存在,而这种东西就是语词意义的对应物。因此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找到这种对应物。对于问题“……是什么?”虽然表达了人类永恒的好奇心(因为哲学问题就是因为好奇心),但是这个思维却往往误导我们⑧。对语词意义进行定义,包括对意义的解释(§43a)以及“实指解释”(§43b)都是在预设了某种语词意义“对应物”存在的前提下作出的。
与下定义相对比的就是对语词意义(或具体用法)进行仔细描述,通过对语言在日常生活中具体使用(包括语言游戏)大量鲜活例子进行观察和描述,从这些事例中理解了语词意义。因为不同语词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意义,语词意义是动态的。“整体式”阅读从描述的视角来分析语词意义,那么“语词意义是什么?”中存在的形而上学本体论预设就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就是无本质、无实体的描述。维特根斯坦在1929年重返剑桥之后的哲学态度就体现在对这种问题进行“描述”而不发表个人意见。另外,维特根斯坦是在整个《哲学研究》中都持有这种态度吗?包括第43节两个段落?“整体式”读者如哈列特以及宾客雷都一致认为维特根斯坦在第43节中所要表达的是对语词意义的“描述”而非“解释”。描述只是为语词意义提供更加全面的理解,是在扩宽看待问题的视角。“我们不应该假设,他说(这里指Bouwsma,他是维特根斯坦在剑桥的学生)维特根斯坦是想要某种对‘意义’的定义;他(维特根斯坦)的意思只是想改变我们的视角:如果你在书写和讲话的时候,你用说‘使用’和写下‘使用’来代替‘意义’的话,你可以成功进行正确的思维,那会是有帮助的。对什么有帮助呢?它会帮助你从那种充满诱惑的思维中解放出来,那就是认为意义作为某种事物,它躲在黑暗中你却不能将它看清楚”[5]。哈列特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动机和观点就是这样的,笔者也赞同上述理解。
那么在第43节中维特根斯坦是否是在对语词“意义”进行定义呢?哈列特首先对不同“意义”的概念进行区分,然后解答。他认为这个问题有三种不同理解,同时也有三种相应回答。第一种:“维特根斯坦是在对语词‘意义’进行定义吗?从广泛的对意义进行解释以及想要从语词实际意义的动机出发来进行解释的角度。答案:当然是的。而且他(维特根斯坦)至少暗示了指称同一性”[5]。第二种:“维特根斯坦是在对‘一个语词的意义’和‘在某个语言中对一个语词的使用’两者做出它们是同义词预设的前提下在对语词(的意义)下定义吗?答案:也许如此”[5]。第三种:“(在不管维特根斯坦的动机是什么的情况下)从事实上对意义给予某个好的同义词的角度下,维特根斯坦是在对语词进行定义吗?答案:是的”[5]。笔者认为哈列特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分析是基于他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手册》中所持有“整体式”理解前提下作出的。应该指出,哈列特对第43节的分析和回答是“中庸”式的,因为他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定义”和“解释”的区别。这样做确实能够让我们全面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然而他并没有说他的这些解答是针对第43节中的具体哪一小节,这样势必留给读者比较模糊的理解。
与此相比,宾客雷的观点较为明确。他认为不应该把第43节当作是维特根斯坦在对语词的意义下定义。笔者在前面提到宾客雷的视角属于“整体式”。首先,宾客雷将第43节中的德文原文和相应英文译文进行了仔细对比,认为如果把第43节中的“erkliren”翻译为“定义为”,而将第109节中的“Erklirung”翻译为“解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果我们从第43节的后一段中得到暗示,把第43节看成是对不同解释的描述的话,这个问题就可以被解决了”[11]。笔者认为宾客雷的主要论据来源于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其他小节中的表述,包括第109节、第127节和第128节。在这些论述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家的任务就是不断地为某个特殊目的收集提示物,而且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的任务并不是去找出某个理论或者定义(从解释角度出发),而是要从不同角度来理解语词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使用(从描写视角出发)。宾客雷认为我们之所以不认为维特根斯坦是从描述角度出发来考察语词意义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理解他所说的“描述”是什么意思,而他认为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第二部分以及《纸条集》中曾明确表明了“描述”的具体意谓。笔者认为正是大部分读者从“本地式”角度来理解第43节,所以才没有理解维特根斯坦所真正要表达的是对语词意义进行描述而不是下定义的观点。
基于“本地式”视角,张锦青详细分析和讨论了“描述”“解释”和“定义”之间的区别。“首先我要指出§43a是对语词意义的解释所作的描写,同时§43b是对名称如何被解释所作的描述。其次,§43a包含了一个解释,同时也是定义。第三,§43b中所指的解释,事实上在这个段落之中并没有实际发生,也许可以被视为是实指定义”[3]。他主要是对哈列特、贝克和哈克的观点进行分析和反驳。基于上述观点,他认为贝克和哈克等人之所以认为第43节重点在于第1句是因为将一个原理运用到讨论与这个原理有关的例外情况中是非常奇怪的,而贝克和哈克等人之所以有这种奇怪的观点就是因为他认为第1句是重点⑨。对于张锦青教授而言,为了消除这种奇怪理解,他认为应该把第2段看作是第43节的中心。张教授是从“本地式”角度来阅读第43节的。“在第43节前后诸小节中考虑和讨论了许多重要问题,它们是关于名称本质和实指定义……尽管在极大多数情况下语词意义就是在语言中的运用,但是在实指定义的例子中,意义不是使用”[3]。张教授认为既然§43b中所提出的实指定义是意义使用论的反例,那么必须在这两个句子中作出决断以便理解第43节中维特根斯坦的主要观点。维特根斯坦在第43节前后诸小节中主要在关注实指定义,而正是因为这个背景,张教授才认为第2句是维特根斯坦在第43节中主要观点。
基于对“本地式”和“全局式”阅读理解方法的分析,笔者发现两者分别从自己的视角来回答这个问题。“本地式”读者如张锦青认为维特根斯坦在第43节中是在对意义进行“定义”,而根据“整体式”视角以及宾客雷的阐释,本文认为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是对意义进行描述。“整体式”理解更加符合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特质。
(二)维特根斯坦在第43节中谈论的“意义”是什么?
维特根斯坦对语词意义的讨论集中在§43a。学者普遍认为他在这里表达了“意义的使用”理念,例如贝克和哈克。笔者认为“意义在于使用”不是有关语词意义的“理论”,最多只能算是某个理念或者观点。因为根据《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维特根斯坦反复强调了一点,那就是他从来就没有提出过某种“理论”,然而有关维特根斯坦谈论的“意义”是什么却充满疑惑。笔者认为维特根斯坦是在讨论两种“意义”:语词“意义”不同于意义和语词的意义,语词“意义”在不同情况下使用就是说我们在不同情况下询问语词“意义”的意思是什么;而语词的意义就是指我们在不同语境中询问同一个语词的意义,或者仅仅是在询问某个语词的意义。笔者认为如果不理解这个区别,就容易误解维特根斯坦。布莱克指出了上述混乱:“针对维特根斯坦是否是在关注极大多数有关意义的事例还是在关注极大多数有关语词意义的问题上存在着模糊。古斯塔夫森认为维特根斯坦关注的是前者……而我则认为维特根斯坦关注的是后者”[17]。不同“意义”指的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例如吃药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以及所需要的意义不是“语言学”上的意义:“维特根斯坦不关注非语言学的意义,例如生命的意义或是云朵意味着要下雨,他把这些方面搁在一边了。更重要的是,这种阅读方法完美地和第43节中的第2段契合在一起,而这一段往往是绝大多数评论者们所忽视的”[17]。笔者认为在§43b中维特根斯坦对§43a作了补充:有些语词,比如名称的意义不是用使用观点来解释的,而是借助于指向它的承受者即“实指解释”来实现的。
布莱克和古斯塔夫森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维特根斯坦在第43节中是关注语词的意义,而非形而上学意义,同时他认为古斯塔夫森所认为的就是维特根斯坦关注的是形而上学意义。果真如此吗?根据笔者考察,在古斯塔夫森的第一个观点中,他认为皮切尔误读了第43节:“第43节不是在讨论那些叫作“语词的意义”的东西,而是关于语词“意义”在某种重要情况下的使用”[10]。根据这个表述,很显然古斯塔夫森也认为维特根斯坦是在讨论语词的意义(语言学)。笔者认为事实上布莱克和古斯塔夫森的看法是相同的,他们都认为维特根斯坦在第43节中所谈论的是语词意义而不是形而上学意义。古斯塔夫森只是表达了他对这一节的疑虑:“事实上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个短语(语词意义)在形而上学之外有一种解释是值得怀疑的”[10]。结合古斯塔夫森的自述以及维特根斯坦的原文,笔者认为古斯塔夫森和布莱克的观点并不存在根本分歧,因此布莱克对古斯塔夫森的理解是错误的。而根据“整体式”理解视角,本文同样赞同古斯塔夫森的观点,维特根斯坦在第43节中是在谈论语词的语言学意义,而非形而上学意义。
(三)语词意义与它的使用是等同的吗?
有关语词的意义与它的使用是否等同的问题同样在三种阐释者之间存在着。笔者认为阐释者对这个问题存在两种理解,即(语词)意义以及(语词)使用的“等同”观点和“不等同”观点,其中前者包括哈列特、贝克和哈克以及皮切尔,后者包括古斯塔夫森和张锦青。维特根斯坦有关语词的意义在于使用的观点在《哲学研究》中不仅体现在第43节中,在其他地方也曾提到这个观点,例如第560节。首先要澄清的是把哈列特、贝克和哈克当作“等同”观点倡导者不是笔者的发明,而是由张锦青提出的。贝克和哈克并没有直接提到语词意义与语词使用相等同:“这个口号(意义使用论)只是对‘意义’的意义部分解释”[9]251,而且哈列特也并没有直接将二者等同起来。由于他们只是笼统地论述了第43节而没有仔细说出是在指哪个具体段落,所以他们的观点往往会被误解,而张锦青的观点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他们(指哈列特、贝克和哈克等人)坚持认为,就算是考虑到了§43a中的限制,将语词的意义和它的使用对等起来也是毫无例外的”[3]。笔者认为张锦青的观点是非常主观的,因为哈列特、贝克和哈克等人并没有直接表述那种观点,张锦青的观点是基于他自己的理解,根据笔者的考察,“等同”观点源于皮切尔。尽管皮切尔认识到§43b的内容是对§43a的例外和补充,但是“我们也可以安全地忽视这些例外……同时宣称对于维特根斯坦而言,语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尽管我们心中还意识到这一论断只有在大部分有关意义的重要的种类中才为真”[7]249-250。笔者认为语词意义和语词在语言中的使用是等同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成立。皮切尔的观点同样成立吗?对于这一点的反驳来自“不等同”读者。
“不等同”读者,如古斯塔夫森,他就认为皮切尔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古斯塔夫森认为把语词意义和语词使用两者等同起来是无意义的(nonsense):“我们怎么可能(显示它是错误的)对无意义的东西进行反驳呢?”[10]古斯塔夫森之所以认为皮切尔的论断是毫无意义的,是因为说语词意义就是使用的时候,我们其实对于语词具体意义根本没有涉及到,我们什么都没有说。例如当我们说“红色”这个词的意义在于它的具体使用的时候,“红色”这个词的意义还根本没有显露出来,只有在我们具体使用“红色”的语境中才理解它的意义。古斯塔夫森认为将语词的意义与语词的用法相等同的观点需要“对同一个个体的两个逻辑独立地描述”[10]。古斯塔夫森首先反驳了皮切尔的等同论。他认为我们混淆了认识论的和形式逻辑的推理:假言推理(modus ponens)在形式逻辑中是有效的,但是在认识论中却是无效的。第二个反驳则是第一个反驳的对立面,古斯塔夫森认为这个论证同样犯了推理前提的错误。“如果U=M,那么如果我知道X的使用(U),我就知道X的意义(M)是错误的”[10]。最后一个反驳是有关专有名词和意义之间的关系。皮切尔认为既然许多语词有用法却没有意义,那么说用法等同于意义就是错误的。基于笔者的“整体式”理解视角,本文同样赞同古斯塔夫森的“不等同”观点,语词的意义和它的使用不是等同的。
(四)“实指解释”和“承受者”的关联
如果按照“本地式”阅读角度出发(例如张锦青),维特根斯坦在第43节的焦点就转移到了第2句。“本地式”读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关注的是原初语言符号(primitive sign)及其意义。我们学习语言最初就是通过实指解释学会的,而笔者认为这恰好就是“奥古斯丁语言图像”所断言的。按照“奥古斯丁语言图像”观点来理解,实指解释过程就会假定某种意义的“承受者”的存在,而这种“承受者”大部分是“心理图像”,只有存在着某物才能对其实指。我们最初是通过这种叫作“实指解释”的游戏来将语词的意义和其“承受者”联系起来的,好比命名的过程就在于对物体贴标签。这些只是我们学习语言的准备,是为语词将来的使用作准备的。当我们学会语言之后,我们在具体运用中并没有时时刻刻都在想着语词的意义可以通过实指来实现,并不是每一次说话背后都有相对应的“承受者”存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实指解释”在原初的语言游戏中所起到的作用,当然“奥古斯丁语言图像”理论背后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言语-思想同形同构论”和“心理实体”存在的预设。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前面100节专门分析并批判了这种观点,尤其是对“实指定义”的批判[14-15]。
五、结语
不同理解角度对于上述争论有不同的解释。基于“整体论”的理解角度,笔者认为在§43a有关“意义在于使用”的观念中维特根斯坦并不是在提供某种意义理论,他只是在作描述,而不是下定义。对于语词“意义”和“用法”之间的关联,它们两者不仅不同,而且也不能互换。维特根斯坦认为在大部分情况下,语言的意义就是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而这个“使用”的概念只是对所有有关语言游戏的事例的概括而已。只有在具体的使用语境中,我们才能理解某个语词的意义。维特根斯坦在第43节中是在谈论语言学的意义,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意义,语言学的意义就是指某个语词的具体意思。在§43b中,理解“实指”概念必须正确区分“实指定义”“实指解释”和“实指描述”三个概念的使用背景。维特根斯坦所使用的“实指解释”或者“实指描述”是在假定了说话者和听话者都是成人且都具备了完整的语言能力的情况下,我们才说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某个名词的意义可以通过“实指”的动作将语词的“意义”和它的“承受者”之间联系起来以此来解释这个名词的意义。那么,在这种背景中,语词的“意义”和“承受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一一对应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只有通过“实指”动作才能建立起来。
注释:
①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时候,当笔者在谈到《哲学研究》第几小节的时候是指该书的第一部分相关小节,而且直接指出该小节内容而不说具体页码。当笔者在引用具体页码时是在引用该书的第二部分。本段中下圆点是笔者加上去的,原文是斜体,表示重点强调。参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韩林合,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②当然必须要明白对于维特根斯坦二手研究文献的完满收集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些文献的数量浩如烟海。例如Shanker等人在1986年就表明有关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二手文献数量有5868种之多。笔者只想表明这个工作的艰难。参见Shanker V A.LudwigWittgenstein:CriticalAssessments:AWittgensteinBibliography(London: Croom Helm, 1986)。
③有关维特根斯坦对“奥古斯丁语言图像”的分析和反驳参见文献[14][15]。
④Timbits是小的甜甜圈。Tim Hortons是加拿大本土流行连锁甜品咖啡品牌,Timbits是它们的招牌甜点。
⑤有关魏斯曼对“实指定义”的论述参见文献[15]。
⑥参见维特根斯坦:《纸条集》(涂纪亮,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⑦魏斯曼把他的哲学“视野”总结为6点。参见Waismann F:Harre.HowISeePhilosophy(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68)。
⑧参见Waismann F:HowISeePhilosophy(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68:11-15)。
⑨这里没有不连贯的地方。贝克和哈克在1980年合著了有关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阐释四卷本的第一卷,因此在本书中有关第43节的阅读理解就很难分清楚他们二人各自对这一小节的观点,因此笔者把他们的观点当作共同观点,虽然后来贝克单独分析了这一小节。
[1]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 Savigny B.The last word o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43a[J].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90,68(2):241-243.
[3] Cheung C K.Meaning, use and ostensive definitions in Wittgenstein’s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J].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2014,37(4):350-362.
[4] Hallett G.Wittgenstein’s definition of meaning as use[M].New York: Fordham,1967: 2-140.
[5] Hallett G.Did Wittgenstein really define “mean-ing”?[J].Heythrop Journal,1970, 11:294-298.
[6] Hallett G.A companion to Wittgenstein’s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M].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120-127.
[7] Pitcher G.The philosophy of Wittgenstein[M].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1964.
[8] Pitcher G.A book review of Wittgenstein’s definition of meaning as use[J].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969,78(4): 555-557.
[9] Baker G,Hacker P M.Wittgenstein: understanding and meaning, Volume 1 of an analytical commentary on the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M].Oxford: Blackwell,1980.
[10]Gustafson.On Pitcher’s account of investigations §43[J].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1967,28(2),252-258.
[11]Binkley T.On reading investigations §43[J].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1971, 31(3):429-432.
[12]张锦青.字词意义都是字词使用吗?——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探微[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69(3):69-77.
[13]Schroeder S.Wittgenstein: the way out of the fly-bottle[M]. MA: Polity Press, 2006.
[14]徐强,桑田.论维特根斯坦对“奥古斯丁语言图像”的反驳[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13-18.
[15]徐强,桑田.再论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对“奥古斯丁语言图像”的反驳[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94-99.
[16]G E Anscombe. On the form of Wittgenstein’s writings[M]// Raymond Klibansky.Contemporary Philosophy: A Survey(Vol. III). Firenze: La Nouva Italia Editrice. 1969: 376-377.
[17]Black C.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remark 43 revisited[J].Mind,1974, 83(332) :596-598.
[责任编辑 勇 慧]
2016-06-03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基金项目(编号:留金发[2014]3026号).
徐 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与维多利亚大学哲学系联合培养博士生,主要从事语言、艺术和音乐哲学研究.
B561
A
10.3969/j.issn.1009-3699.2017.0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