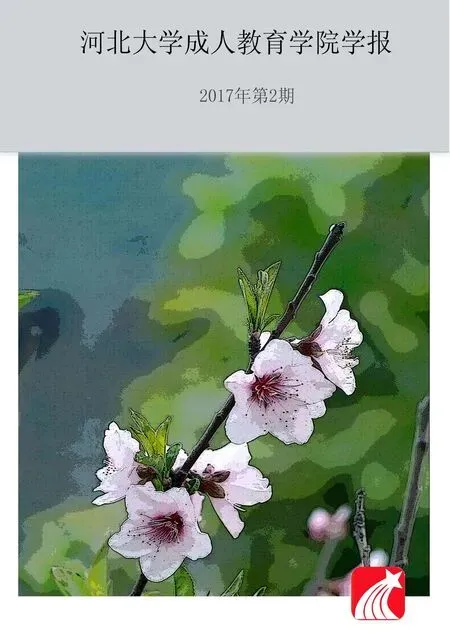田野调查法在民族社区教育研究中的应用探析
毛 艳
(云南大学 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田野调查法在民族社区教育研究中的应用探析
毛 艳
(云南大学 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教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指研究者把自己融入所研究的民族生活,以获取第一手资料的过程。将此方法运用于民族社区教育研究,有利于加深对特定民族社区成员及其自然-社会环境的认识,探索该民族社区最适合的教育模式。在民族社区教育研究中运用田野调查法,可以根据选题、选点来确定调查对象,进一步充分认识调查对象后进入田野,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确定基本的研究方法,在民族社区田野工作完成后,将田野调查各阶段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分类、整理、分析并加以理论提升后撰写调查报告。研究者要建立一种令人信任的田野关系,以保证田野调查的顺利进行。
田野调查法;民族社区教育;研究;应用
田野调查,又称“田野工作”(Field Work),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根本方法,是指研究者把自己融入所研究的民族生活,为了解人们的行为亲自深入某一社区,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住居体验等方式,与被研究者长时间相处,并试图了解、思考、感受、模仿另一种生活方式,以获取第一手资料的过程。在研究中,研究者虽然也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获取研究资料,但是到田野点进行实地考察几乎是每一位研究者获取资料的最主要途径。田野调查法自英国社会功能学派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奠定以来,在世界各国普遍使用并逐步得到发展。在我国的教育研究中,从人类学的视角解读教育现象、解决教育问题,探讨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教育的文化功能等,已经是教育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范式。[1]教育人类学研究不是从概念出发或沿用以往教育研究的解释套路,而是依据田野工作中与调查对象共同生活所进行的参与观察、访谈等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并使之与文化背景联系来加以分析和阐释。
在教育人类学的视野下对民族社区教育进行研究,在应用方法和研究视角上,我们不应仅仅局限在单一的民族群体或者教育上,还应置于少数民族所生存的自然-社会环境中,纵向分析其时间与空间特点,深度分析民族性格与认同心理,从而探索该民族社区最适合的教育。作为民族地区的教育研究者,要加强理论创新,形成自己的话语和表达方式,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由此运用田野调查法进行民族社区教育研究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
一、确立田野调查对象
在田野调查中,作为术语的“田野”原本是生物学家对于野外科学考察作业的表述,后由人类学家引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它的核心涵义是强调研究者进入研究对象所生存的自然-社会环境中,观察其原生状态,从而达到对研究对象的较深层理解。教育人类学中所说的“田野”是一个学术概念,泛指进行教育调查的现场,不一定是在田间地头,而是取决于所要研究的教育事象,即某种教育在哪里,哪里就是展开调查的“田野”。那么田野调查的对象就是教育所涉及到的人及其所生存的自然-社会环境。民族社区教育研究的“田野”是指西北、西南、东北等少数民族聚集地内以少数民族成员为主体,以民族社会成员的共同地缘和紧密的日常生活联系为基础的区域性社会,是一个兼具社会性和民族性的社会共同体,表现为小型民族社区(即一个村寨)或大型民族社区(多个村寨形成的地域综合体)。[2]民族社区教育涉及少数民族社区内民族成员的教育需求、教育内容、教育模式。由于民族社区教育的民族性使得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生活习俗、价值追求存在差异,所以在不同的民族社区内,社区成员由于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不同,社区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在进行民族社区教育研究时,对田野调查对象的确立可以遵循一定的方法。
对调查对象的确立可以根据选题来确定。一方面,可以是对一个族群或社区进行全面调查,比如在对彝族社区调查时应该把彝族人口占80%以上的几个社区作为调查对象。也可以是在几个社区或族群中,验证一个理论问题的定向调查。如果要探讨自主学习理念下民族社区教育的发展,[3]可以选择几个不同民族的社区来进行。无论是全面调查还是定向调查,都应该将调查对象视为一个生活整体或系统,考察其社区内的教育与整个社区的文化、经济、 政治、民族、医疗、艺术等多方面存在的相互关联。[4]另一方面,可以根据选点来确定调查对象。一是在原调查基地开辟新的调查点,选择别人或自己曾经调查的某个点做回访调查。二是在进行田野调查之前已有一个确切的调查点。如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云南大学在25个少数民族中都设立过调查基地。白族的调查基地在大理剑川、纳西族的调查基地在丽江、哈尼族的调查基地在红河元阳。在进行民族社区教育研究时,可以考虑依托原有的基地进行调查。三是通过阅读地方文献资料,大致确定一个区域,经过实地考察和比较后,再选择一两个比较理想的个案点做调查。
调查对象确立之后,在进入“田野”之前要做好三项工作。首先,进一步充分认识调查对象,通过阅读文献,了解调查点的地理和历史的背景材料,包括自然环境、气候条件、交通状况、人文环境、历史事件、地方民风民俗甚至是地方流行疾病、蚊虫、社会治安等。[5]同时还应该阅读民族志档案资料和地方文献书目,包括历代民族志、民俗志、地方志、文史资料,还有地方学者或外来文化学者的笔记、手稿、报告、日记。要了解该民族社区有哪些人做过调查、取得哪些成果、解决了什么问题,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其次,根据调查对象的具体情况,确定基本的研究方法,以差别对待的原则对待民族地区的多元差异。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具体技术一般为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参与观察就是要求研究者在调查点长期居住下来,参与被调查者的生活与学习,观察他们的教育活动和个人言行举止。民族社区的深度访谈对象可以是社区的长者、文化工作者、党政领导、学校的教师、学生和学生家长。[6]访谈的内容既可以针对访谈对象自身的教育问题,也可以是其所知晓的其他情况。一般而言,对访谈对象必须精心选择,对重点访谈对象更是如此。他(她)的年龄、性别、社会阅历、职业、文化程度、社会地位、工作态度、语言表达能力、社会关系等都是必须予以认真考虑的。 再次,田野调查点确立之后,田野工作者就要对民族社区内成员投入真情实感,同时把握自己的研究理智。围绕调查对象拟定调查提纲,明确自己调查的目的性和计划性。
二、建立田野关系
民族社区的田野关系是指研究者根据民族社区教育调查研究的需要建立起来的与社区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它的基础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学术合作协议。田野关系是一种从关系资源转化来的学术资源,居住下来和友好相处是建立田野关系的标志。和当地人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这对得到有用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当地人可能不会对研究者持一种开放的态度。研究者越熟悉当地人的生活,越能有效读懂所搜集到的信息的意义。建立一种令人信任的田野关系,能够使研究者得出可靠的研究结论。
在进入民族社区之初,可以向当地的领导者和民众说明来意,获得他们的支持。熟悉社区内环境,对社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解,包括人口调查、了解当地的禁忌,尽快地以当地人的方式行事。可以通过观察获得相关的信息,了解社区的每日生活程序,就如同本地人一样。此外,对于日常的琐碎事件,如争吵、戏谑、家庭趣事,有时是不引人注意的,有时是戏剧性的,但是对调查研究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如何与调查对象建立和维护关系?在民族社区内,研究者按照调查对象的时间表,随着对象的行动节奏,安排个人的调查活动。最好的方式是与当地人进行社会互动,使双方进入一种自然交流的状态,如一起参加劳动、傍晚时分一起娱乐放松。此时,两者之间的交流最为真实、自然,研究者很容易发现调查对象的内部游戏规则和游戏的细节,且民族社区成员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编造自己的文化行为。
研究者并非都能很顺利地进入田野,他们被不同的民族社区文化所接受是有条件的,起码需要宽容、理解和尊重对方的文化,要放弃自己文化的一些价值判断,尤其是对民族社区内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不能有先入为主的一些判断。[7]民族社区教育研究者在充分了解调查对象的基础上,其行为言谈基本符合他者文化的逻辑,才能换取对方的认可。而一旦获得社区居民的认可,即使有一些处理不周的做法也能得到他们的宽容,倘若偶尔因为不了解民族习俗而有失礼行为,已经与研究者建立感情的当地人就会像对待自家人一样毫无迟疑地指出来。
田野关系的常见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一是拟亲属关系,这是最典型的一种田野关系,创立这种关系的鼻祖是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研究者被当地人接受为他们的内部成员,得到当地人赠给的亲属称谓,然后在当地顺利住下来。在陌生的世界里,有亲属的称号,就像有了年龄一样,能让人找到位置。民族社区教育研究者在与社区成员共同生活中建立拟亲属关系后,社区成员对研究者就少了很多生疏感。拟亲属关系是“润滑剂”,可以在各类陌生的人际关系之间做“减震”处理。 二是熟人关系。与亲属关系和拟亲属关系相比,熟人关系是一个社会大网络,能够覆盖到他者文化分布的各个点。费孝通对江村经济的调查就是靠他姐姐的帮忙,建立了熟人关系后才开始实施的。通过朋友、师生等关系找熟人,通过熟人找研究对象,再从研究对象中发展新熟人。通过田野关系中的熟人找到同龄人做向导,再与对方从同龄关系发展为熟人关系。在民族社区教育研究中,通过熟人关系能够让研究者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三是官方关系。在地方政府管辖的地点做调查工作,要征得当地政府的支持。在民族社区教育研究中,田野工作者要善于把官方关系转化为熟人关系,这样更有利于研究的开展。
无论是哪一种田野关系,对当地语言的熟悉是很重要的,语言是理解文化的向导,在民族社区中尤其如此,学习当地语言是发展和当地人的亲密关系的重要步骤。在很多民族社区内往往是少数民族语言和当地方言并行,如果一个研究者连当地方言都不懂,那么就很难与社区成员进行沟通,更不要说深度的访谈。研究者只有熟悉当地的语言,从中找出话语,才能明白这些话语究竟是什么意思,才能减少自己作为外来者的文化权威感,缩小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距离。民族地区教育研究者在田野做调查时,应该发挥方言优势,发现和提取调查对象使用的表达自己文化的独特概念,并用这些概念与他们对话。
三、撰写调查报告
民族社区田野调查的工作常态可能是“白天到处跑,夜间不停地记笔记”。研究者每天要把自己融入到当地人的文化中,同时又要学会将自己从这种文化中“抽离”出来,这样才能科学地判断我们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事情,才能比较科学地记录和分析这些材料。[8]民族社区教育研究的开展应该以社区内的生活为基础,所以研究者在观察分析的时候要把视角扩展到社区内整体的生活。民族社区的生活每天、每周、每月、每年都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研究者在每天的调查结束后,晚上要做的工作就是及时地整理信息,避免信息积累太多而被淹没。同时要把一些背景性信息注释出来,这些也都是将来写作中可能会用到的。社区内的教育活动记录必须详尽、精确,以便在活动结束后不致漏掉重要信息。除了记录事实外,还要加一些旁注,写下自己的感受、初步分析和问题假设,以便进一步观察。访谈时尽量细致地记录社区成员用来描述他们的文化现象的概念、术语和分类方法。提问要简单明了,避免模棱两可的答案。要尽可能直接记录当事人的说法和看法,避免掺杂研究者的主观价值观和解释,以使资料保持客观。需要注意的是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和情感表达要与被访谈者所谈的内容区别开。
田野调查的前期文字工作完成之后,需要完成民族社区教育的调查报告。研究者要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情境,从多种角度了解、观察研究对象并对其进行充分诠释。在撰写调查报告时,要从历时的深度和共时的广度进行“深描”。这种“深描”可以借鉴人类学的民族志撰写方法,从宏观到微观角度,描述和解释民族社区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解决民族社区教育存在的问题,完成定向的理论分析。
在前期调查中所获得的关于民族社区成员的日常生活资料原是混沌的和混合的,在最后的调查报告撰写中,研究者首先要做的是把这些资料分类,系统地梳理,按照民族社区教育的各构成要素,如民族社区中社区居民的人口构成、教育需求、社区内的教育资源等组织材料,提供下一步的系统阅读、分析和写作。这是田野调查最出成果的阶段。强调研究者应从被研究者的角度出发,从其具体民族社区内在的角度分析事件,从而理解其背后的思维观念或文化逻辑,最终推断出民族社区教育切合的模式。通过深入民族社区进行调查,分析在田野中初步获得的资料并加以理论提升,就能在民族社区教育研究中实现实践和理论的极大推进。
四、结语
田野调查作为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带给从事民族社区教育的研究者从书斋到田野的研究范式的改变,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研究者的信念和科研模式。为了制定适合特定民族社区教育的模式,研究者可能需要长期与另一种文化的民族成员住在一起,学习、使用他们的语言,与他们建立社会关系,参加日常活动,以及进行单调、费时的观察与记录。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人类学范式指导下有扎实田野工作基础的个案研究,如果能深入民族地区开展调查,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探索民族社区教育的有效模式,那么在民族社区教育的实践和理论上应该能有所突破。当然,也会存在一些困难,比如,研究者田野调查时间周期难以保证;由于一些研究者缺乏田野调查的意识和专业训练,导致所获取的第一手资料不够翔实,这些都是研究者在具体的田野工作中需要面对的问题。
[1]滕 星.回顾与展望:中国教育人类学发展历程——兼谈与教育社会学的比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5):5-12.
[2]毛 艳.自主学习理念下民族社区教育发展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6(17):152-155.
[3]毛 艳.云南省民族社区教育及其独特性研究分析[J].中国成人教育,2016(3):149-152.
[4]石玉昌,张诗亚.“学在野”之“化”——兼论民族教育田野调查法[J].民族教育研究, 2015(6):17-23.
[5]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25.
[6]袁春艳,陈恩伦.田野调查运用于民族教育研究中的反思[J].贵州民族研究,2012(1):162-165.
[7]张诗亚.西南民族教育文化溯源[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67.
[8]樊秀丽.教育民族志方法的探讨[J].教育学报,2008(3):80-84.
(责任编辑:刘奉越)
Application of Field Investigation Method in Ethnic Community Education Research
MAO Yan
(College of Vocat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Yunnan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091,China)
Field investigation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refers to the process in which researchers integrate themselves into the study of the national life and obtain first-hand information. Applying this method to the study of ethnic community education will help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mbers of specific ethnic communities and their natural social environment, and explore the most suitable educational model for this ethnic community. Using field investigation method in the study of ethnic community education, can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bject selection, selection,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urvey into the field, according to their specific situations, determine the basic research method.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field work in the ethnic community, the first-hand data obtained at the various stages of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is classified, collated and analyzed, and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 is written after theoretical improvement. Researchers should be able to build a trusted field relationship to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fieldwork.
field investigation method; ethnic community education; research; application
G77
A
1008-6471 (2017) 02-0056-04
10.13983/j.cnki.jaechu.2017.02.009
2017-05-16
毛艳(1967-),女,云南思茅人,云南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学与成人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