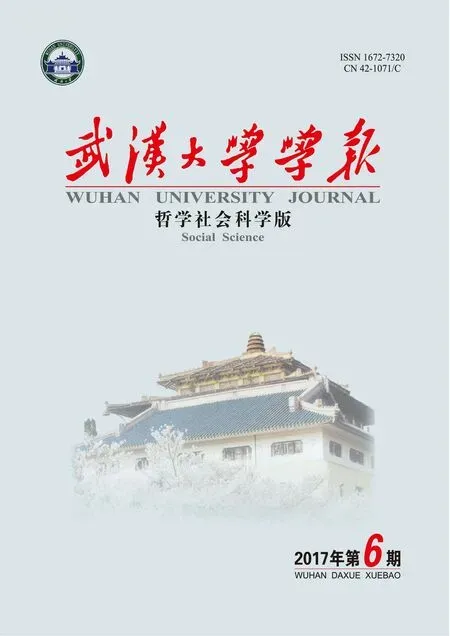香港基本法第158条与司法审查次终性理念
——基于基本法实施20周年的反思
程雪阳
香港基本法第158条与司法审查次终性理念
——基于基本法实施20周年的反思
程雪阳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58条所建立的香港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话式释法机制”并非是普通法世界的异类,相反,其与英国、加拿大以及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的宪法体制一样,共同分享着“法官有权解释宪法/高级法,但建制化的人民代表才是宪法/高级法终极守护者”的法律哲学,因此都可视为是以“司法审查次终性”理念来发展普通法的重要方式。在香港回归20年之际,当人们对第158条所建立的释法机制进行总结和评估时,应珍视这种业已构成“一国两制”和香港法治重要基石的法律实施机制,不宜将美国司法至上式的宪法体制照搬到我国香港地区。
香港基本法第158条; 基本法解释; 议会至上; 普通法; 司法审查次终性
自1997年香港回归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已经实施了整整20年。然而,在这20年内,如何理解、适用和评价《基本法》第158条的规定以及基于这一规定所建立的法律解释与适用机制,一直都是颇有争议的问题。
在香港回归之初,就曾有香港法律专家担心“基本法第158条核心中所潜藏的精神分裂症,将使解释制度其他方面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并会成为混乱和冲突的根源。”(Ghai,2000:35-37)在这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也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释法权对司法案件提供指引,是十分有争议的。因为普通法是香港法治的基石,而普通法的核心是法律的具体含义由法官说了算,人大释法并不符合这一普通法传统(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2012:9)。甚至还有法律专家总结说,“在香港很多人的眼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立法机关和政治机构来解释基本法缺乏正当性,第158条所建立的基本法解释机制是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宪法问题争议不断的主要原因。”(Kellogg,2008)
2016年11月,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第104条进行解释时,上述争议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有人指责说,人大释法危害到了香港的法治建设与司法独立。不过,更多的意见认为,人大释法是由《基本法》所建立的,应当得到香港市民的承认和遵守。由此观之,在《基本法》实施20周年之际,对《基本法》第158条所建立的释法机制进行全面客观地评价,是极为重要且必要的一项工作。本文希望完成这一项工作,但在展开具体的研究和论述之前,需要强调以下三个方面的前提。
首先,《基本法》第158条所建立的基本法解释机制固然受到了我国现行宪法第67条第1项和第4项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宪法和法律职权”规定的影响,但其同样参考了欧盟“先行裁决”法律解释机制的安排,而并非是对内地宪法体制的简单模仿和照搬(李昌道,2008:62)。
其次,普通法确实是香港地区百年法治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但却并非是香港法律的全部。在受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普通法也只是香港法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自英国本土的议会制定法,不但约束香港,而且比普通法的法律效力还要高。而在香港回归之后,宪法和基本法的法律效力也要比普通法要高。《基本法》第8条关于“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的规定,已经毫无疑义地说明了这一点。
最后,在讨论“宪法/高级法”的解释机制时,人们的视野不能仅仅停留在香港地区内部或者内地与香港的关系方面,还要有国际视野,特别是要考察那些同样实施普通法的国家或地区过去20~30年间在相关领域的制度变迁和理论发展。当然,普通法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法系,其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并不完全一样,特别是在宪法/高级法领域,美国与英国、加拿大等英联邦国家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相关比较和评价要尊重历史和现实,不宜宽泛或盲目进行。从历史角度来看,香港地区早年的法治是在英国人主导下建立的,源自英国的普通法也被《基本法》确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有效的法律渊源之一。从实践角度来看,回归以来,“香港终审法院一直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普通法地区邀请杰出的法官作为其‘非常任法官’,与本地法官一起审理案件;在终审法院的领导下,香港司法机关努力与普通法世界的法理发展趋势保持一致,以此建立其国际声誉”*根据林峰的梳理,从1997年7月1日成至2016年初,共有22人曾担任香港海外非常任法官,而所有海外非常任法官都是来自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三个普通法国家。林峰(2016).“一国两制”下香港“外籍法官”的角色演变.中外法学,5:1161-1162.(陈弘毅等,2017:39),因此,将我国香港地区的情况与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加以比较,无疑是合理且必要的。
一、司法审查次终性理念在英联邦国家的兴起
一提到以英国为首的英联邦国家法律制度,人们首先想到的应该不是“司法审查”或“违宪审查”,而是“威斯敏斯特式的议会至上模式”体制。所谓“议会至上”,用Dicey(1915:38)的话来说,那就是“议会可以制定或者不制定任何法律,没有任何人或组织可以通过英国法律推翻或废止议会的立法”。这种宪法体制拥有三个方面的特点:首先,不存在一部成文的宪法,因此法院无权依照宪法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其次,所有的议会制定法,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只存在新法与旧法的区别,不存在上位法(高级法)与下位法(一般法)的差异,因此议会制定法之间的法律冲突也是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来处理;最后,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但审查的对象只能是政府行为而不能是议会制定法。
这种法律体制如何避免多数人对少数人权利不当侵犯,又如何确保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统一呢?Dicey(1898:55)认为,主要靠民主自身和公共舆论,只要民主足够发达,公共舆论足够强大,“与人民意愿相悖,或换言之,与特定国家明显多数中普遍盛行的观念相悖的法律,是不可能获得通过的。”英国人以及那些被英国殖民统治的地区接受了这一看法,并在数百年间一直坚持这种建立在代议制民主基础之上的议会至上体制。不过,进入现代社会后,由于社会阶层的利益分化日益复杂,“委任立法”大量出现等原因,Dicey的理论和在这种理论影响之下所建立的“议会至上”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80年代以后,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等英联邦国家开始探索对“议会至上”体制进行改革。
1982年,加拿大通过了《宪法法案》,这标志着该国也建立了成文宪法体制。这部宪法的第一章《权利与自由宪章》设立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实施机制。即,虽然其第24条授权各级法院可以依照该宪章所保护的权利审查国会、省或者地方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Section 24 of the 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该条第1款规定“本宪章所规定的权利或自由受到侵犯或拒绝保护时,任何人都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救济,并由法院按照恰当和公正的原则进行审理。”,但第33条同时又规定,当涉及宪章第2条以及7-15条所保护的权利和自由时,国会和省级立法机关有权做出“该部法律或者法律中的特定条款虽然违反了宪章所保护权利或者自由,但依然具有效力”的豁免声明。该豁免声明做出以后,相关法律或者法律条款即使被法院认定违宪,却依然可以在5年内继续实施,而且可以在有效期届满后以5年为一期进行续期*Section 33 of the 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对于这种宪法适用机制的功能和意义,加拿大学者普遍认为,其就是“为了在引进美国式成文宪法的同时,又不改变源自英国的传统议会至上体制。”(Hogg,2002:5)具体来说,法院有权解释宪法并进行司法性的违宪审查,但司法权对于宪法的意见和判断并不具有最终法律效力,因为这种意见和判决可以被代表民主的立法机关以制定一般性法律的方式推翻,但与此同时,立法机关在立法时,也应当考虑法院的意见*比如,1988年时,在“福特诉魁北克”一案中,加拿大最高法院宣布魁北克省的《法语宪章》(Bill 101)部分违宪,因为该法关于“本省公民和社会组织不得使用法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制作商业标志”的规定,侵犯了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表达自由。为此,魁北克省议会通过启动宪章第33条所设定的机制修改了《法语宪章》(Bill 178)。修改后的法律规定,户外商业标示必须使用法语,户内商业标示则可以使用其他语言。不过,5年之后,魁北克省议会没有再依照宪章第33条延续该规定的法律效力,而是通过一般立法程序再次修改了《法语宪章》(Bill 86)。修改后的法律规定,商业标志可以使用法语和其他语言书写,但法语应排在首位。Ford v Quebec (AG),[1988] 2 S.C.R.712.。
1990年以后,受加拿大的启发,新西兰也开始改革“议会至上”体制,但该国十分谨慎。该国1990年的《权利法案》规定,首先,其他法案应当尽可能地解释为与《权利法案》是一致的;其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法院都不能以议会之前或之后所颁布的法律因为与《权利法案》不一致,从而将其撤销或废除,也不能使其失效或无效;最后,当司法部长发现某项议会立法(或立法草案)与《人权法案》不一致时,其应当及时通知下议院,然后由下议院做出修改与否的决定*New Zealand Bill of Rights Act (1990),Section4,6&7.。
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改革探索以及欧洲人权法院屡屡依据《欧洲人权公约》判决英国败诉的实践情况,督促英国人思考如何在一个新的时代来处理“议会主权”和“法治原则”之间的关系。
1997年大选获胜之后,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发布了一份题为《将权利带回家》的政府白皮书。该白皮书认为,英国自1951年就签署了《欧洲人权公约》,并且承诺绝不违反该公约。但长久以来,英国公民所享有的公约权利在国内法院无法得到保护,而只能到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去进行诉讼。在此过程中,英国公民平均一个案件需要花费3万英镑和5年时间,费时耗力且不利于英国的国家形象。有鉴于此,当时的工党政府决定通过将《欧洲人权公约》纳入本国制定的《人权法案》(Human Right Act),从而允许英国公民和法院在国内就可以适用《欧洲人权公约》。
将《欧洲人权公约》纳入本国法律体系后,如果国内法院认为一项国内法与《欧洲人权公约》不一致,是否应当赋予法院以废止该法律的权力?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时的工党政府在白皮书中首先考察了与英国宪法体制相似的加拿大、新西兰以及香港地区的做法,然后得出结论说,英国实行的是“议会主权”式的宪法体制,这种宪法体制“意味着议会有能力制定其认为必要的任何法律,而且还可以根据法律就重要事项做出公共政策的选择,对此没有法院可以质疑其正当性。……没有证据表明[英国]法院希望拥有宣布议会立法无效的权力或者英国公众希望法院这样做,……[因此]英国没有必要采用美国的宪法体制,……也不应当赋予本国法院依照《人权法案》所承认的欧洲人权公约权利来推翻议会在《人权法案》通过之前或之后所颁布的法律。”(The Sectary of States for the Home Development,1997:10)
为了落实上述改革理念,1998年通过的《人权法案》规定,首先法院在适用议会所制定的基本法律以及其他主体制定的附属立法时,应尽可能以与欧洲人权公约权利相一致的方式来加以解释*Art.3(1)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Human Rights Act 1998.;其次,穷尽所有可能的解释方法之后,如果法院依然认定议会立法违背《欧洲人权公约》,那么高等法院可以公开发布一个“该法律与公约权利不一致的宣告”(Declaration of incompatibility),但不得宣布其无效*Id.Art.4(1)-(2).附属立法(即议会以外的其他立法主体所制定的法律规范)与公约权利不一致的,《人权法案》第4条第3-4款规定,法院原则上可以废除,但议会立法明确禁止废除的,法院只能发布“不一致宣告”。;再次,法院所做出的“不一致宣告”,既不影响相关法律条款的继续实施,也不约束涉诉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但法院应依照法庭程序通知政府*Id.Art.4(6)&5(1).;最后,对于议会立法来说,如果内阁主管部长认为必要的话,可以修改相关法律并请求议会批准*Id.Art.10 (2).。不过,是否需要修改相关法律取决于内阁主管部长、政府和议会对《人权法案》的理解和判断,在法律上并不受法院的“不一致宣告”约束。另外,紧急情况下,内阁主管部长也可以在议会修改相关法律前,通过启动快速程序来发布一项在其看来可以使国内法与《欧洲人权公约》保持一致的命令,但如果议会在120天内没有批准这一项命令的话,该命令立即失效*Art.4 of Schedule 2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Human Rights Act 1998.。
对于这种制度设计,该白皮书解释说,“《人权法案》只是为法官解释所有的议会立法提供一个新的基础,并没有赋予法院依照该《人权法案》推翻任何议会立法的权力”(The Sectary of States for the Home Development,1997:11)。对此,英国的司法系统也表示认可和接受。比如,英国最高法院在其官方网站中就提到,“本法院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最高法院不同,不能推翻议会的立法。本法院的工作是通过判例法来更加清楚地解释国内法律和法令。当国内法关涉到《人权法案》所承认和保护的《欧洲人权公约》权利时,法院有权按照公约来解释国内法,并在这种努力不能成功时做出‘不一致宣告’。不过,如何处理法律之间的不一致,是议会而非最高法院的权力。”
就这套体制的运行而言,英国司法部(2016:45-62)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0年10月到2016年6月,英国法院共做出34次“不一致宣告”。其中,有 22项是法院的终审判决,有4项正在上诉中,相关判决尚未生效;还有8项高等法院的“不一致宣告”被上级法院推翻。在已经生效的22项“不一致宣告”中,有13项宣告被议会采纳,随后议会修改了相关法律;有3项宣告被政府主管部长采纳,而且主管部长已依据《人权法案》第10条的规定修改了相关法律,但尚未获得议会的批准;有4项“不一致宣告”在其做出之时,议会已经做了修改;剩余的2项,政府正在研究和考虑如何解决,尚未做出决定。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等英联邦国家的上述制度探索和改革并不完全一致。不过,从“宪法/高级法解释权分配”这一角度来看的话,上述英联邦国家所探索和发展出来的新制度,共性要远远大于差异性。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斯蒂芬·伽得鲍姆教授(2001:710、742)认为,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的上述探索,属于“通过司法保护基本权利”与“代表民主的立法机关是法律合宪性最终决定者”的完美结合,因此可以总称为“议会至上”与“司法至上”之外的第三种宪制模式——即“英联邦宪制新模式”(The New Commonwealth Model of Constitutionalism)。美国埃默里大学法学院迈克尔·佩里教授(2003:670、673-674)则认为,这种新的宪法实施机制的核心是“司法机关可以解释宪法,但司法对于宪法的解释只是次终性的意见,并不具有最终法律效力”。为此,佩里专门发明了 “司法审查次终性”(Judicial Penultimacy)一词来总结上述英联邦国家的新探索,从而将这些探索与美国式的“司法至上”模式加以区分。
对于这种制度探索的实践效果,哈佛大学的马克·图施奈特教授(2003:825)曾深表怀疑。他认为,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和英国《人权法案》所设计的“弱司法审查”模式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经过一段时间运作之后,要么会退回到传统的议会至上体制,要么会最终演变为美国式的司法至上体制*“弱司法审查模式”(Weak Form Judicial Review)这个概念是图施奈特首创的,用来与美国“司法审查至上”类型的“强司法审查模式” (Strong Form Judicial Review)相区别。本文之所以没有选用图施奈特的这一分类,主要是因为关于“强/弱”的标准常常会引发人们的误解和争论,而且很容易跟“司法能动主义/司法谦抑主义”这一分类混淆。。不过,十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图施奈特(2013:2250)写到,“弱司法审查模式是20世纪晚期,人类在宪法设计领域最为重要的创新之一。这种司法审查模式允许立法机关通过日常立法活动来审查法院对宪法含义的具体化是否恰当。司法机关所创造出来的宪法含义,很可能被政府的政治分支通过一定形式的日常立法而不是通过繁琐的宪法修改程序推翻。”
二、司法审查制度在香港地区的演变和发展
香港曾受英国的殖民统治。在此过程中,英国人将议会至上体制和普通法移植到了香港地区。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香港法院可以像英国法院那样,根据“越权无效”、“温斯伯里不合理”等原则,对政府的行政行为和附属立法(即授权立法)进行司法审查(陈弘毅等,2017:29)。但是,就像香港上诉法院在1997年的“马维騉案”中所说的那样,“在1997年7月1日之前,香港法院不能基于英国的不成文宪法或香港的《英皇制诰》来决定英国宗主国或帝国立法的合宪性。……依照英国宪法的结构,英国的议会法令和行政决定并不受制于香港的英皇制浩,所以香港法院也没有管辖权来质疑它们,……即使香港法院质疑英国的议会法令或行政决定,事实上也没有有效的途径*HKSAR v.Ma Wai Kwan David & Others [1997] HKLRD 761,paras.53-54.需要说明的是,当英国人在说“议会主权”(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或议会至上(Parliamentary Supremacy)时,“议会”(Parliament)仅仅是指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的上议院和下议院,而不包括郡议会、大伦敦议会(1986年4月后被撤销)、各伦敦市议会、教区和社区议会地方议会,当然,更不包括作为海外殖民地立法机关的香港立法局。。
新西兰颁布《权利法案》的第二年,港英当局也为香港制定了《人权法案条例》。该条例第3条和第4条规定,“所有先前存在的法例,凡可作出与本条例不抵触解释的,须作如是解释。但如果无法解释为与本条例相一致,抵触部分则予以废除”,“本条例之后颁布或生效的法例,如果可能的话,应当被解释为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香港适用的部分相一致”*Section3&4,the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 Ordinance 1991.。从这两项规定来看,当时的港英政府是想通过将《人权法案条例》以及这部条例所包含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建构成一种类似于宪法的“高级法”,然后赋权香港法院基于《人权法案条例》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进行违宪审查。在这种规定之下,香港法院一旦发现包括《基本法》在内的本地其他法律与《人权法案条例》或《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不一致,有权宣布这些法律无效。不过,《人权法案条例》的这种制度设计显然与《基本法》作为香港回归之后的“惟一的高级法”的地位和性质是冲突的。因此,在香港回归之前的1997年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条处理香港原有法律的决定》中指出,《人权法案条例》第3条有关“对先前法例的影响”和第4条有关“日后的法例的释义”的规定,因“抵触《基本法》,不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不过,基于对香港地区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尊重,《基本法》并没有强行废止在香港实施和延续多年的英国法律制度。相反,其第8条、第82条、第92条以及第93条第1款,不但规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而且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前在香港任职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均可留用,其年资予以保留,薪金、津贴、福利待遇和服务条件不低于原来的标准”,同时“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应根据其本人的司法和专业才能选用,并可从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聘用”,另外,“终审法院也可根据需要邀请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法官参加审判”。
更为重要的是,《基本法》第158条还为香港地区建立了一套特殊的释法机制。这种特殊的基本法解释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根据《基本法》第158条第1款的规定,该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与此同时,根据《基本法》第158条第2款和第3款的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外的条款,特区法院也可解释。根据这两项授权,香港法院对基本法的全部条文也拥有解释权。
不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特区法院对基本权的解释权是有区别的。其具体表现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所有条文都拥有解释权。对此,早在1999年的“刘港榕”案中,香港终审法院就曾明确承认,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基本法》的解释权源自中国宪法第67条第4款的规定,这项权力是“全面而不受限制的”。第158条第3款“香港自治范围之外的条款”,针对和限制的是香港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权,而非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权*Lau Kong Yung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1999] 3 HKLRD 778; (1999) 2 HKCFAR 300,paras.57-59,62,142.。也就是说,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的基本法解释权,范围涵盖基本法所有的条款而不仅仅是“香港自治范围之外的条款”。与之相反,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受权,香港法院可以对香港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但如果对基本法条款的解释涉及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且对相关条款的解释影响会到案件的判决,那么在做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之前,终审法院应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相关条文进行解释,但香港区域法院或高等法院等法院此前所做的非终审判决却并不受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的影响。
对于上述解释权的分配和配置,在基本法实施的早期,曾经引起过一些误解,但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20年的互动和对话,其已经为内地与香港地区社会各界广泛接受。2011年的刚果金案件就是典型。在这一案件中,终审法院主动依照《基本法》第13、19条以及第158条第3款的规定,就该案所涉及的“国家豁免”这一外交事务问题,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and Others v.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2011] 14 HKCFAR 395.。
2.香港法院可以对香港本地的立法进行司法审查,并有权宣布本地立法因为违背《基本法》而无效或将其删除和撤销。但是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颁布的法律、作出的决定或决议,如果香港法院发现其与《基本法》相冲突,其司法权行使的最远边界是发布一个“不一致宣告”,而不能宣布其无效或将其撤销。这一规则曾引发巨大争议,但在《基本法》实施20年后,其逐渐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接受。实践中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争议,是因为《基本法》第11条虽然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政策,均以本法的规定为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触”,但并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本地立法以及全国性立法与《基本法》相抵触以后,应当如何处理。
司法机关的本职工作就是处理法律规范的适用问题,如果法院发现了某一法律规范违背了《基本法》,基于“裁判者不得拒绝裁判”这一基本的要求,即便是《基本法》没有规定,其也必须直面和解决这一问题。如何处理这一法律上的难题呢?《基本法》将这个问题开放给相关主体的法律实践和对话沟通来加以探索并形成具体规则。在1997年的“马维騉案”中,香港上诉法院提出两个论点:(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主权国。在中国宪法之下,全国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其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起行使国家立法权。在这种背景下,香港法院作为地方法院,只能审查全国人大是否做出过决定或决议,但不能这些决定或决议的合法性,因为这种决定和决议是主权行为;(2)香港特区法院虽不能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但是可以审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所设立的香港临时立法会的权力行使行为是否符合全国人大的决定和决议。换而言之,其认为香港法院有权对特区本地立法进行司法审查*HKSAR v.Ma Wai Kwan David & Others,[1997] HKLRD 761,paras.59-61.。
到了1999年的“吴嘉玲案”中,香港终审法院支持了上诉法院的第二个论点,但否定了其第一个论点。终审法院认为:(1)对特区立法机关所颁布的法律或特区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符合基本法,特区法院拥有司法审查的权力,而且可以宣布与基本法不一致的本地立法或行政行为无效。终审法院还特别强调“虽然这点未受质疑,但我等应借此机会毫不含糊地予以阐明”。(2)“对于特区法院能否依据基本法来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颁布的法律,虽有争议,但答案应当是肯定的,而且特区法院确实有责任来宣布与基本法不一致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颁布的法律无效”*Ng Ka Ling and anothers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1999] 1 HKLRD 315; (1999) 2 HKCFAR 4,paras.61-62.。香港终审法院的这一判决引发了巨大争议,因为其不但违背了中国的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而且实际上也违背了香港地区原有的普通法传统——要知道,在英国普通法的传统之下,香港法官并没有审查议会立法的职权。
1999年2 月 4 日,特区政府律政司请求终审庭就该案判词中涉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部分做出澄清。特区终审法院在1999年2月26日最终解释说,其“在 1999年 1月29日的判词中,并没有质疑人大常委会根据《基本法》第 158 条所享有解释权,如果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做出解释,我等必须以此为依归。终审法院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权是不能质疑的,1999年 1月29日的判词也没有对此进行质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基本法》的条文及其所规定的程序行使任何权力,法院接受其是不能质疑的”*Ng Ka Ling and anothers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1999] HKCFA 81,para.6.。在随后的“刘港榕案”中,终审法院也表示“绝不怀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99年6月26日作出的解释。人大常委会作出该项解释,乃是行使《中国宪法》第67(4)条所赋予的权力。《基本法》第158条首段再次提到该项权力,并述明是解释《基本法》的权力。人大常委会并无借着任何条款放弃该项权力或将之转让给本院或任何其他法院”*Lau Kong Yung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1999] 3 HKLRD 778; (1999) 2 HKCFAR 300,para.142;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v.Chong Fung Yuan,[2001] 2 HKLRD 533; (2001) 4 HKCFAR 211,Sec.6(2).。
到今天为止,香港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再也没有发生过改变。比如,2017年的“行政长官及律政司诉立法会主席”一案(即“梁游宣誓案”)中,香港高等法院强调,首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基本法第104条含义的解释,是这一规定真实合理含义的组成部分,而且其效力可以追溯到基本法生效之日起;其次,根据终审法院在“庄丰源案”中所确立的先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基本法的解释权源自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条文做出解释之后,无论其是基于第158条第1款与其他任何条款,还是基于第158条第3款与自治范围之外的条款,香港法院都受其约束。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威在香港特区受到全面的承认和尊重”;最后,根据1999年香港终审法院在吴嘉玲案所做的声明,香港法院不能质疑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基本法的条文及其程序所做的任何决定。因此,对于梁游二人所提出的人大释法是否属于基本法修改而非真正的基本法解释等问题,法院无权作出裁决*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 Secretary for Justice v.the President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2017] 1 HKLRD 460,paras.29,53,54,58.另外,在2017年7月14日的“行政长官及律政司司长诉罗冠聪、梁国雄等四人”案件判词中,高等法院再次确认,“《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含义的解释已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6年11月7日解释的第1-3段进行了阐明,这种对于第一百零四条含义的真实和合理的解释约束香港所有的法院”。Secretary for Justice v.Yiu Chung Yim,Nathan Law Kwun, Lau Siu Lai & Leung Kwok Hung, In the High Court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list,No.223-226 and Miscellaneous proceedings No 3379-3382 of 2016(heard together),paras.19-20.。
不过,在对本地立法的司法审查权方面,终审法院并没有退让,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香港立法会也没有对此公开表示反对。在《基本法》实施20年来,香港法院一直在行使这一项权力。有统计数据显示,在2000-2007年间,香港法院在33起案件中,依照《基本法》对香港立法会的立法及行政机构的决定、附属立法及特首专项决定进行了审查,其中共有9 起案件的终审判决认定既有的立法、行政决定或其他规定违反基本法,24 个判决认定既有立法或决定符合基本法(程洁,2016:15)。从实践的结果来看,香港法院的这种做法虽然导致香港本地的政治生态和权力架构有“从行政主导滑向司法主导”的风险,但对于维护和落实《基本法》在香港本地法秩序中的最高性和权威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此可以在实践上予以认可。不过从理论上来说,香港法院最好还是发表“不一致声明”为宜,不宜直接宣布本地立法因为违反《基本法》而无效。
3.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基本法》拥有最终解释权,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作出解释后,该解释即为终局解释,应当受到陆港两地所有公权力机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尊重和遵守。对于这种终极性解释权的行使,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20年的探索,逐渐发展出了三种不同的释法机制,即(1)香港终审法院依照第158条第1、3和4款的规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2)其他适格主体依照第158条第1、4款的规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9年6月26日所做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解释》以及2005年4月27日所做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都是应国务院提请的议案而做出的。而国务院的两个议案都是应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或署理长官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八条第(二)项的有关规定提交的报告而提出的。;(3)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第158条第1、4款的规定主动解释《基本法》*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4年4月6日所做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以及2016年11月7日所做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都是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请的议案而做出的。。根据这三种释法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主动解释基本法,也可以通过接受香港终审法院的提请,或者接受其他在其看来适格的主体所提交的申请来解释《基本法》,但是无论采用何种机制,其都必须“事先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
在“刘港榕案”中,资深大律师张健利曾提出,除非香港终审法院作出司法提请(且其内容只能与“自治范围外条款”有关),否则常委会不能解释《基本法》,因为第158条对常委会的权力施加宪法约束,此举符合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基本法》所给予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包括终审权。但终审法院认为其“不能接受此项辩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该项权力及其行使并无在任何方面受到第158(2)和158(3)条限制或约制”*Lau Kong Yung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1999] 3 HKLRD 778; (1999) 2 HKCFAR 300,paras.57-58.。在2001年的“庄丰源案”中,终审法院再次明确坚持了这一观点*Director of Immigration v Chong Fung Yuen,[2001] 2 HKLRD 533; (2001) 4 HKCFAR 211,para.6.2.。从法解释学和法律适用的角度来看,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应当得到支持。因为人们一旦接受张健利大律师的观点,便会导致第158条第1款“事实上被废弃”或“被第3款架空”。
在2016年的“议员宣誓风波”中,又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目前宣誓风波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则静候法院的处理结果即可,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必要启动解释程序。这种观点也不宜得到支持。因为基本法第158条虽然建立了上述三种不同的释法机制,但却没有规定这三种释法机制的适用顺序。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当将这种情况解释为《基本法》作为一部宪制性文件,有意将三种释法机制的适用顺序问题留给未来的法律实践来加以形成和发展。换句话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依法作出自己的判断。在具体的个案中,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为了明确基本法特定条款的含义或者藉由基本法特定条款所产生的法律争端,有必要主动释法,那么这种做法也是符合基本法的。当然,笔者认为,在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及时通过完善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或者制定《基本法解释法》等方式,明确三种释法机制的适用时机和适用对象并将其规范化和制度化,从而增强相关释法机制的透明性、公开性和可预期性。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的解释,基于《基本法》序言所确立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则以及第158条第2、3款的规定,除了以下两种例外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则上应当依照“谦抑性原则”保持克制:其一,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解释“涉及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其二,在可以预见的情况下,香港法院有可能会对自治范围内的条款,做出有损香港地区根本利益,危及“一国两制”原则和底线的解释,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可根据案件或事件的具体情况,在上述三种解释机制中选择合适的释法机制对所涉条款进行解释。
三、《基本法》第158条与司法审查次终性理念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与加拿大的《权利与自由宪章》、新西兰的《权利法案》以及英国的《人权法案》相比,我国香港特区《基本法》所建立的“高级法”解释机制确实具有很多特别之处。比如,《基本法》是在中央与地方(特区)的特殊场域下发挥作用的。在这一特殊场域中,就该“高级法”的解释和适用进行“宪法对话”的主体,并非是位于同一层面的香港本地立法会与特区法院,而是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与作为地方司法机关的特区(各级)法院及其法官;再比如,香港法院关于《基本法》的解释不仅约束涉案双方当事人,而且基于普通法和判例法的传统也约束整个香港社会,而英国法院的“不一致宣告”不但不约束议会和政府,而且对涉案双方当事人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又如,在加拿大,联邦议会或省议会如果不同意联邦最高法院关于《权利与自由宪章》部分条款的解释,那么其需要制定专门的法律来推翻法院的意见(期限为5年),但在《基本法》的框架之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果不同意香港法院关于基本法的解释,其可以径直做出自己的解释,并不需要专门制定法律。
对于上述差异,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观察和思考。
其一,《基本法》并非是一项地方性法律,而是一项全国性法律,《基本法》所建立的是一套在宪法之下但适用于全国的“次级法秩序”,而不仅仅是香港本地法秩序*在中国境内,基于“一国四法域”的现实,在次级法秩序层面,除了中国大陆直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本地法秩序的基础外,在香港特区,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为香港法域法秩序的基础,在澳门特区,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为澳门法域法秩序的基础。台湾地区和台湾法域的情况比较特殊,待两岸统一之后,有可能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次级法律秩序。。因此,这套法秩序的运行和《基本法》的实施,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与该次级法秩序内的终审法院,而不应当由该次级法秩序内的立法机关与终审法院进行终极的宪法性对话。
其二,如果我们能够超越法律实施机制层面的差异,而将目光聚焦在法律哲学层面,那就会发现,《基本法》第158条所建立和发展出来的“释法机制”,不仅符合中国宪法体制(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且与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等英联邦国家近30多年来在“宪法/高级法”实施领域的改革和发展趋势也是不谋而合的,因为隐藏在第158条背后的法律哲学,同样是香港法院可以解释《基本法》这一“高级法”,但“建制化的人民代表”(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是宪法/高级法的“终极守护者”以及宪法/高级法含义的“最终决定者”。
其三,要注意“理念”与“制度”的不同。司法审查次终性模式代表的是这样一种法律哲学和法政理念,即,国家和社会应当由人民而非法官来进行统治,为此,人民(及人民的代表)应积极地、不间断地控制宪法性法律的解释和实施(Kramer,2004:247)。不过,就像花儿是万紫千红那样,任何一种法律哲学和法政理念是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加以落实的,其并不要求所有接纳这种哲学或理念的国家或地区必须建立完全相同的法律制度或法律实施机制,因为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政治结构并不完全相同。如果人们能够了解到这一点,那么就会发现,无论是英国的“不一致宣告”模式,加拿大“豁免条款”模式,新西兰“解释一致性”模式,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对话式释法”模式,都属于“司法审查次终性”理念的不同表现形式。虽然它们各自的制度设计存在差异,但却共同分享着“法官可以解释宪法,但其关于宪法的意见不具有最终法律效力,人民及其代表才是宪法的终极守护者”这一法律哲学和法政理念。所以,即便是从英联邦普通法的角度来看,这些落实“司法审查次终性”理念的不同模式,也都应当视为是对普通法精神的发展而非背离。
上文提到,香港特区有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专家认为,《基本法》第158条所建立的“释法机制”会危及香港地区的司法独立、普通法实施以及法治发展。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原因有二。
其一,在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同样是代表人民的立法机关拥有对“宪法/高级法”含义的最终决定权,但很少有人批评或指责这些国家司法不独立,法治不完善或不健全。为何在香港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呢?笔者认为,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外,法律上的主要原因是这些批评者对于“司法独立”持有错误的理解。事实上,当人们在强调“司法独立”的时候,主要是在说司法机关要在政治上独立于其他机关,从而“确保每个法官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判断和对法律的审慎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基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判”*The Bangalore Principles of Judicial Conduct 2002, revised at the Round Table Meeting of Chief Justices held at the Peace Palace (The Hague),Nov.25-26:2.,其并不意味着法官没有政治—道德信念或信仰,更不意味着法官应该对于“宪法/高级法”这种具有高度抽象和不确定的法律拥有最终的解释权*20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关于司法独立达成了许多共识并发布了许多宣言,但这些标准里面都没有将“法院对宪法/高级法拥有最终解释权”作为司法独立的内容之一。See New Delhi Code of Minimum Standards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New-Delhi Standards 1982),The Jerusalem Approved Standards as adopted in the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IBA Biennial Conference held on Friday,22nd October 1982.。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情况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其二,就像香港终审法院在“吴嘉玲案”中所指出地那样,像《基本法》这样的宪法性文件,通常都是由涵义广泛和概括性的语言来组成,而且配合时代转变和适应环境的需要来进行灵活解释*Ng Ka Ling and anothers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1999] 1 HKLRD 315; (1999) 2 HKCFAR 4,para.73.。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法院对《基本法》的含义拥有最终的解释权和决定权,就会侵蚀立法的权能,导致立法与司法之间的权力界限模糊。因为一旦法院被委以依据“宪法/高级法”来撤销或废除法律的权力,其就拥有了设定普遍性规范的权力。要看到,“撤销或废除法律”同“颁布法律”同样具有普遍性特征,在本质上,都是立法权的行使。换句话说,如果允许法院有权基于“宪法/高级法”撤销法律,那么法院就会变成一个享有立法权的机关*在《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第三章中,凯尔森专门讨论了“司法机关的立法职能”问题。其认为,当法院在被授权撤销违宪法律时就履行了立法职能。当法院有权以一个法规(regulation)看来是违反法律的或者似乎“不合理的”为理由而撤销该法规时,它们就履行了立法职能。当法院的一个具体案件的判决成为其他类似案件判决的前例时,法院又行使者立法职能。具有这种权限的法院就以其判决创造了与来自所谓立法机关的制定法处于相等的一般规范。参见[奥]凯尔森(2013).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389.。这样一来,在宪法问题上,国家将会由法官(特别是终审法官)而非人民及其代表来进行统治和治理了,因为当法官面对模糊、抽象和不确定的宪法条文并对其进行解释时,必然是基于自己的政治、经济或道德倾向来做出法律判断的。而这种情况的出现,既不是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也与民主原则存在着剧烈的紧张关系。
上文曾提到,有普通法专家宣称“普通法的核心是法律的具体含义由法官说了算”。这种观点抽象来讲是成立的,但需要注意,首先,在英联邦的普通法传统中,这里的“法律”并不包括成文宪法,因此这一主张不能自然而然地推论出“宪法/高级法的具体含义由法官说了算,属于普通法的核心要求”这一结论。确实,《基本法》第8条规定并承诺“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但香港原有的普通法、衡平法以及其他法律规范中,并不包含“法官对宪法/高级法拥有最终解释权”这一制度;其次,在美国的普通法传统中,经由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美国法院(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确实拥有了对宪法含义的最终解释权。但美国的这种宪法体制是在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既不是“大写的真理”,更不是普世标准,即便是在普通法世界,这种宪法体制也并不多见,因此人们不能将美国的标准当作是国际标准,然后要求其他国家或地区(比如中国的香港特区)也必须符合这一标准。事实上,香港地区无论是历史上受英国殖民统治,还是今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在宪法/高级法的体制层面与美国都不具有可比性;最后,美国式的“司法至上”式宪法体制,由于存在着“司法审查反多数难题”,两百多年来也一直饱受争议。特别是20世纪末期以来,这种宪法体制对于民主制度和对人民自我统治的能力的侵蚀愈演愈烈,对此不得不察*比如在2015年的“奥伯格费尔诉霍奇斯”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裁判结果,宣布同性恋婚姻符合美国联邦宪法。对此,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长达29页的反对意见中指出,联邦最高法院不是立法机关,同性婚姻是不是一个好想法,与法院无关。根据宪法,法官有权陈述法律是什么,而不是法律应该是什么。……在当下,同性婚姻的支持者们通过民主进程说服其他人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功。然而,五位法官今天终结了这些辩论,并且在宪法层面,强制灌输了他们对于婚姻的看法。他们把同性婚姻这个问题从人民手中偷了过来,带来了一个难以接受的剧烈社会变化。(不过)多数法官今天的决定不是基于宪法的中立原则,而是基于他们自己对于自由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的理解,他们所宣布的权力在宪法和最高院的先例中都没有根据,我必须反对他们的意见。Obergefell v.Hodges,576 US ___ (2015),Mr.Justice Roberts,C.J.,Dissenting.。然而《基本法》第158条所建立释法机制却并不存在这种问题,其一方面确保了法官在保护人权和实施宪法/高级法领域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又避免了法院基于自身对宪法的判断而侵犯人民及其代表的立法权力。
另外,从实践层面来看,香港回归20年来,围绕《基本法》第158条的适用和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终审法院虽然曾经发生过一些分歧,但这种分歧是较为正常的一种现象。因为,一方面,《基本法》作为一份宪制性文件,在很多规范领域只能使用较为抽象的语言来作出框架性或原则性规定,而将具体制度的建构留给相关主体通过实践来进行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基本法》所建立的“一国两制”以及特殊的释法体制是一个新生事物,如何落实相关规定,不同的主体(特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终审法院)基于不同的法律传统,法律解释方法以及不同的职权分工,必然会有不同的理解。如果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围绕《基本法》第158条所产生的一些争议,更像是一个新生事物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遇到了“青春的烦恼”,而并非是让《基本法》患上精神分裂症的“混乱和冲突的根源”。
事实上,人们在《基本法》实施20年之后回顾这部法律的实践时,就会发现,当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终审法院在《基本法》的框架内进行了数次“宪法性对话”后,已经逐渐形成了“良性的互动”,达成了“优雅的妥协”,并找到了各自在《基本法》实施过程中的位置。其具体表现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但极为审慎地行使《基本法》所授予的终极解释权,而且也开始使用香港法院所采用的普通法解释方法来解释《基本法》*香港《基本法》实施20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仅仅行使了五次“释法权”,而且在这五次“释法”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只否定过一次香港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就解释方法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比较重视通过使用历史文献等文本之外的资料来进行“原旨主义”解释。但2016年11月面对《基本法》第104条的争议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开始使用香港法院经常使用的普通法“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方法来解释《基本法》。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2016年11月7日)。。与此同时,香港法院也不断强调自己会尊重并遵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及其所做出的具体解释。
当然,也应当看到,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以及语言的模糊性,任何法律所建立的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比如,英国1998年《人权法案》在通过之后就曾多次修订。而在《基本法》之下,第158条所建立的释法机制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因为在解释方法上的差异性,确实容易引发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议;再比如,对于涉及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以及中央和香港特区关系的条款,《基本法》要求香港终审法院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首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但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终审法院在“涉及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的理解上存在分歧,相关情况如何处理《基本法》的规定也并不明确。
不过,这些问题都属于具体机制或制度细节方面的瑕疵,只需要进行微观制度层面的完善和修补即可*比如,有学者提出,人大常委会有必要根据《基本法》、《立法法》以及相关法律和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尽快出台具有法律意义的《基本法解释程序法》,这一观点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可以参见程洁(2006).论双轨政治下的香港司法权.中国法学,5:88-103;朱国斌(2008).香港基本法第158条与立法解释.法学研究,2:3-26.,并不表明《基本法》第158条所建立的释法机制存在根本缺陷,更不表明这种释法机制应当被推倒重建。应当看到,对于那些坚守“议会或民主代议机构在法律秩序内拥有最高法律地位”理念的国家或地区来说,法院在宪法/高级法解释和适用领域的首要功能是“通过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来促进民主”,而不是“用自身的判断来代替民主来对宪法做出最终的判断”。英国是如此,中国内地和香港也不例外*感谢杨晓楠副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批评意见,文责自负。。
[1] 陈弘毅、罗沛然、杨晓楠(2017).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合宪性司法审查与比例原则适用之比较研究.港澳研究,1.
[2] 程 洁(2016).香港基本法诉讼的系统案例分析.港澳研究,2.
[3] 李昌道(2008).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探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3.
[4] A.V.Dicey(1915).AnIntroductiontotheStudyoftheLawoftheConstitution,8thEdition.London:Macmilan and Co Ltd.
[5] A.V.Dicey(1898).LecturesontheRelationbetweenLawandPublicOpinioninEnglandduringtheNineteenthCentury.London:Forgotten Books.
[6] Stephen Gardbaum(2001).The New Commonwealth Model of Constitutionalism.AmericanJournalofComparativeLaw,49(4).
[7] Yash Ghai (2000).Litigating the Basic Law:Jurisdiction,Interpretation and Procedure.Johannes M.M.Chan,H.L.Fu and Yash Ghai (ed.).HongKong’sConstitutionalDebate-ConflictoverInterpretation.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8] P.W.Hogg(2002).The Charter Revolution:Is it Undemocratic?ForumConstitutionnel,12(1).
[9] Thomas E.Kellogg(2008).Excessive Deference or Strategic Retreat? The Impact of Basic Law Article 158.HongKongJournal:http://hkjournal.org/archive/2008_spring/5.htm.2017-09-02.
[10] Larry D.Kramer(2005).ThePeopleThemselves:PopularConstitutionalismandJudicialReview.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 Michael J.Perry (2003).Protecting Human Rights in a Democracy:What Role for the Courts?WakeForestLawReview,38(2).
[12]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2012).InformationNote-interpretationoftheBasicLawunderArticle158(1),IN29/11-12.
[13] The Minister of Justice of the United Kingdom(2016).RespondingtoHumanRightsjudgments.Report to the Joint 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 on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Human Rights judgments,2014-16.
[14] The Sectary of States for the Home Development by Commend of Her Majesty (1997).RightsBroughtHome:TheHumanRightsBill(CM 3782).
[15] Mark Tushnet (2003).New Forms of Judicial Review and the Persistence of Rights-and Democracy-based Worries.WakeForestLawReview, 38(813).
[16] Mark Tushnet (2013).The Relation Between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and Weak-form Judicial Review.GermanLawJournal, 14 (12).
Article158oftheBasicLawofHKSARandJudicialReviewPenultimacy:An Analysis and Review on the 20 Years’ Practice
ChengXueyang
(Soochow University)
The Basic Law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1997),together with the 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 (1982),the New Zealand Bill of Rights Act (1990) and the British Human Rights Act (1998),shares with the same philosophy of law,which is “The court should have the power to interpret constitution/high law,whil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represent of people must have the final wor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stitution/high law ”.Therefore,the model of “dialogue-oriented interpretation between Hong Kong Courts and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hich is established by article 158 of Basic Law,is a specific form of the “judicial review penultimacy model”.When observers make their comments on the Basic Law after its put into force 20 years later,the interpretation mechanism within the article 158 of the Basic Law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success model but not a “nature’s error” for the Common Law world,as this mechanism and model is not only the important cornerstone for the rule of law of Hong Kong and “one Country two System”,but also China’s contribu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n Law.
article 158 of the Basic Law of HKSA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c Law of HKSAR; parliament supremacy; common law; judicial review penultimacy
10.14086/j.cnki.wujss.2017.06.007
D921.9;D676.58
A
1672-7320(2017)06-0071-12
2017-06-28
■作者地址程雪阳,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江苏 苏州 21500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4FFX010);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特别委托项目(JBF201407)
■责任编辑李 媛